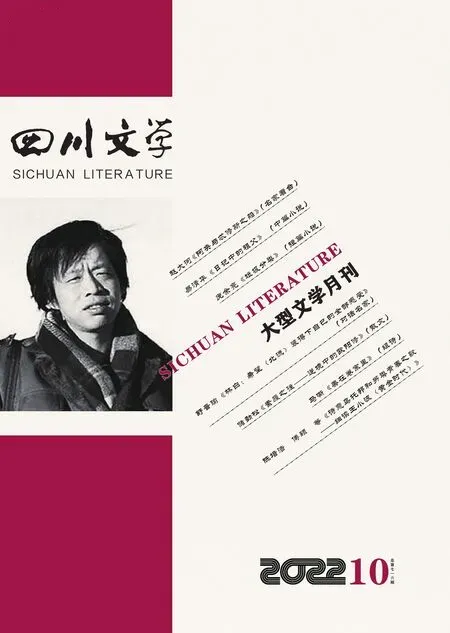1984年的裤子、西红柿和校园里的歌唱
2022-03-22尔雅
□文/尔雅
九月,镇上医院的尹大夫到家里来。他先后来过两次。尹大夫是个瘸子,脑袋和脖子一样粗,有一张脸盆那么大的脸。在平常,他摇晃着脑袋,从街道上走过去,身上有一股鸡蛋面片和药水混合的味道。他因为肥胖而骄傲,假装看不见我们,甚至不认识我们。他给这里的牛、马、驴和骡子看病,但也会给拉肚子、感冒、摔断了手和腿的人看病。他一边看病,一边不停地骂人。人们都赔上笑脸,忍着。因为他给人或者牲口看病就得骂人,就好像那是他看病必须的程序。
我们在学校里读书。父亲在麦场里收拾麦草。母亲在院子里打水、喂猪和鸡。尹大夫站在院子里,取出手绢擦脑袋和脖子里的汗。母亲热情地打招呼,问他喝不喝水。尹大夫没有说话,他的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动,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他站在我们家的院子里,但不和我母亲说话,就好像不认识她一样。父亲说,他没说干啥来?母亲说,没有,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这是第一次。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和妹妹们在地里拔草,父亲给驴子割苜蓿,母亲正准备做晚饭。尹大夫这一次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母亲热情地打招呼,问他喝不喝水。尹大夫的眼珠子在院子里扫来扫去。过了一会儿,他问母亲说,你儿子呢?母亲说,他去给猪拔草了。尹大夫的鼻子里哼了一声。母亲问他说,你是有什么事情吧?尹大夫说,也没啥要紧事,你忙你的,我就看一看。母亲说,好嘛,那你看吧。母亲就接着做饭。尹大夫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摇摇晃晃的,就像是跳一种奇怪的舞。他手里的棍子伸进墙角的一堆麦草里,把麦草扒拉散了,接着他又把棍子伸进鸡窝里,一只正在下蛋的鸡受了惊,从鸡窝里窜出来。一片鸡毛飞起来,落到尹大夫的头顶上。尹大夫的头顶光滑明亮,就像是一颗亮起来的灯泡。而他居然没有发现那片鸡毛。
他顶着那片鸡毛继续在院子里走,呼哧呼哧地喘气。他又去看我家的地窖、牲口棚、堆放草料的屋子,他手里的棍子戳来戳去。后来他进了上房里。棍子在房子里的柜子上和坛子上敲打,发出咚咚当当的声音。母亲在厨房里听得清楚,她就走过来,问他到底在找什么。尹大夫没有说话,手里的棍子仍然在骄傲地敲打。面柜上的一块黄漆被敲掉了,一只地上的坛子也被敲破了。坛子里是腌好的酸菜,汤汁正顺着破了的缝隙流出来。母亲很心疼,她就伸手挡住了尹大夫手里的棍子。她说,尹大夫,你看你这个人,你把坛子都打坏了。尹大夫这才停下来。他说,坏了就坏了。他说话的口气很骄傲,就好像柜子和坛子应该让他敲坏。然后他就像一只青蛙那样一跳一跳地离开了。
父亲非常愤怒,他在院子里转圈,像是一匹暴躁的马。他说,这狗日的欺负人。他又说,早年他在税务所当干部的时候,尹大夫还老叫他一起去打牌,喝罐罐茶,到他成了庄稼人,尹大夫就瞧不起他了,走在路上,也假装看不见。这就是狗眼看人低。父亲越说越生气,他决定立刻去找尹大夫算账。于是他大步流星地走出了院门,两条裤腿像是两面破败的旗帜那样飘荡。我们当然不担心父亲会有什么损失,相反,我们实际上支持他的愤怒。从母亲的描述中,我们仿佛看见了尹大夫拿着棍子到处翻搅和敲打的样子。骄傲而嚣张,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也许父亲的声讨能够取得胜利,然后尹大夫会赔偿柜子和坛子的损失。我们充满了期待。但不久父亲就回来了。他的神色看上去有些沮丧和失望。因为他没有找到尹大夫。医院里的另一个人说,尹大夫在黄昏时分,坐上一辆拖拉机,回他们村去了。
母亲很心疼损坏的柜子和坛子。它们已经用了十几年,一直很完好。她打算到供销社里问问有没有黄色的漆,这样就可以补上那块破碎的地方。她把坛子里的酸菜倒进了一只脸盆里,反复观察坛子上的裂缝。显然,这只坛子已经被尹大夫敲坏了。买一只新坛子的希望很渺茫,因为父亲没有钱,也许得一直等到年底才有可能。她忽然想起八月里来过家里的货郎。那人在我们家住了一晚,想买走那把三弦琴。母亲想起那人说过,他隔一阵子就会到镇子上来。货郎的箱子里什么东西都有,也一定会有办法把坛子修好。
很快,我们知道了尹大夫为什么要拿着棍子到处敲打。因为他的西红柿和一条裤子被人偷了。尹大夫的宿舍门前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有牡丹花、土豆和西红柿。到了夏天,西红柿的藤蔓就顺着插进土里的竹竿向上伸展,那些西红柿就长在上面,先是翠绿,然后逐渐变成鲜艳的红色。尹大夫很会种西红柿,又饱满又圆润,就好像随时都能够溢出酸甜的汁液。尹大夫经常一跳一跳地走到西红柿藤蔓跟前,伸手摘一颗下来,他要用它做鸡蛋面片吃。不久,我们闻见他的房子里飘荡出来的面片香气。我们都伸长了鼻子。我还清晰地听见嗓子里吞咽口水的声音。从前有一次,我和镇上的几个人躲在医院里的柳树下面,悄悄地观察尹大夫的动静。过了一阵,我们看见尹大夫从宿舍出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往后院走。他一边走一边打着嗝。我们知道,他是去后院拉屎。他一边拉屎一边读报纸,等他拉完屎他就撕一片报纸擦屁股。我们屏住呼吸,看着尹大夫走进厕所里。接着,我们几个人悄悄地溜进尹大夫的花园,摘了园子里的西红柿,然后一溜烟跑了。那天他们每人摘了两三颗,我只摘到一颗。西红柿的个头还没长起来,是绿色的。但我实在是馋得紧,等到我跑到街道上,看着没人注意,一口就把那颗西红柿咽下去了。实际上我都没有尝出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这一次,尹大夫的西红柿被人偷走了六颗,而且是已经长熟、鲜艳通红的西红柿。尹大夫本来正在计划把它们摘下来,其中的三颗要给他女人,自己留一颗做鸡蛋面片,剩下两颗则要送给杨大夫。杨大夫是新来的,刚从地区卫校毕业,头发扎成马尾,走路的时候那一股头发在身后甩来甩去,像是一匹马。杨大夫到了医院之后,医院里就显得热闹了许多。因为她总是大声地说话,经常发出笑声,她笑起来的时候,胸口的奶子就会摇晃起来。我们有时候会替她担心,她的奶子会不会挣脱她的衣服,突然跳出来。她身上还有一股香气。镇上的人只要走进医院,就会闻见她的香气。有些人就经常到医院里去,假装自己生病,其实是为了闻一闻杨大夫身上的味道。尹大夫当然也喜欢杨大夫的味道,经常一跳一跳地走过去,和杨大夫说话。杨大夫也喜欢和尹大夫说话,她看见尹大夫花园里的西红柿,就发出惊奇的叫声,因为她也没有见过长得这么好的西红柿。尹大夫高兴地说,等到西红柿长熟了,就送给她两颗。
这些事情镇上的人都知道。但在九月,尹大夫花园里那些好看诱人的西红柿被人偷走了。当然,更严重的问题不是西红柿,而是尹大夫的裤子。那是一条崭新的、的确良面料的裤子,是尹大夫特地到县城的百货商店里买的。整个县城里一共只有两条这样的裤子,尹大夫就买了其中一条。这条裤子花了20元。20元是一笔很大的钱,能够一次掏出20元买一条裤子的人,在整个县城都没有几个,在许镇就只有尹大夫能够这么阔气。但那是一条神奇的裤子,穿上这条裤子,夏天再热也不觉得,冬天再冷也是暖和的,而且无论你如何屈腿伸缩,裤子上一点褶皱都不会有。它看上去光滑明亮,还发出窸窸窣窣的低吟一样的声音,就仿佛那些料子里藏了一台收音机。更神奇的是,尹大夫穿上那条裤子之后,他的腿形显得十分笔直,几乎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瘸子;他走路的时候,身体摇摆,一高一低的姿势,就像是为了显示他的骄傲,而不是因为他是瘸子。人们都羡慕尹大夫有一条既高级又神奇的裤子。人们说,果然人都是衣服穿出来的,这么高级的裤子,就算是傻子穿上,也会看着像医院里的大夫了。人们这么说话的时候,傻子正从街道上走过去,他的嘴巴上糊满了鼻涕,手里抓着一个窝头,他没有穿裤子,黑乎乎的小鸡在大腿间晃荡。人们就都大笑起来。
尹大夫把的确良裤子洗了,挂在宿舍外面。他计划穿上洗好的裤子,再拿上新鲜的西红柿,去找杨大夫。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裤子和西红柿都不见了。尹大夫赤裸着上身,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裤衩,在医院的后院里跳动、转圈和咒骂。他的样子就像是一只不停转动的圆规。
不久,尹大夫站在医院门口宣布说,他已经知道是谁偷了西红柿和裤子,这是严重的破坏行为,是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捣乱。他讲话的时候,镇上的一群人围着他。有个人说,现在是新时代了,哪有什么地富反坏右,你不能随便扣帽子。尹大夫就朝地上吐了一口痰,说,那也是坏人搞破坏,是阻挠国家干部抓革命促生产。他又说,下一步他要把这事告诉公安局,公安局会把这些狗日的抓起来枪毙。
当然,尹大夫只是在发出威胁。他实际上不知道是谁偷了他的西红柿和裤子,但他圈定了几个可疑的目标。在他圈定的目标里,我是其中之一。所以他骄傲又蛮横地敲坏了我们家的柜子和坛子,而他根本就不打算赔。
在九月,尹大夫还没有找到偷了西红柿和裤子的贼,镇上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每天晚饭过后,人们聚集到街道上,热烈地讨论这件事情。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激动,空气中唾沫横飞,人们七嘴八舌,就像是一群吵吵嚷嚷的麻雀。人们热情地谈论的时候,尹大夫在他们跟前不停地走动,身体摇摆的幅度明显比平常夸张,还大声地咳嗽,朝地上吐痰。他希望镇上的人们继续讨论西红柿和裤子,不应该这么快就转移话题。他觉得沮丧又生气。
但是很显然,新发生的事情比尹大夫的西红柿和裤子要刺激得多。实际上镇上的人们并不喜欢尹大夫,而且也不见得非要讨好他。他这个人很骄傲,把很多人都不放在眼里,有些人其实还很高兴他的西红柿和裤子被偷了。他经常吃西红柿鸡蛋面片,穿着那么高级的的确良裤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算替他着急,说着奉承他的话,他也不会分给我们一点面片。
人们谈论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学里。九月的一个夜晚,徐老师在半夜时分醒过来,打算撒尿,却发现开不了屋子的门,有人把门外的关子扣上了。徐老师的儿子也在这间屋子里。他儿子起来,拍打桌子,大喊了几声,听到屋外有慌张的脚步声。他接着从窗户里跳到外面,手里拿着一把铁锹,一边喊一边追,看见两个黑影从校园的树荫里闪过去,很快就不见了。
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徐老师屋子外面的空地上有一棵苹果树,树上结了果子。屋子外面的水泥台阶上,摆放着徐老师一家人的物品,其中有一袋土豆、一坛酸菜、两棵新鲜的大白菜、一把葱、两个有彩色花纹的脸盆,以及晾在外面的几件衣服。但是树上的果子和屋外的物品都是完好的。徐老师一家人住在这里,有两间并排的屋子。他和儿子住一间,老婆和女儿住另一间。半夜里来的人把他和他儿子的这间从外面关上了。老婆和女儿的那一间到他们发现的时候,门已经被推开。徐老师的老婆是一个很老的女人,身体不好,听不见别人讲话。但是徐老师的女儿长得很好看,镇上的人都看得见,而且大家都说,她差不多是镇上长得最好看的姑娘。
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正在这里:那两个贼是什么时候关上徐老师的那间屋子门,又是什么时候推开他女儿的那间屋子门?这中间隔了多久,以及他们推开另一间屋子门之后到底干了什么?而徐老师的看法与镇上的人一样:他女儿那一边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
徐老师头发花白,戴了一副玻璃片很厚的眼镜,上衣口袋里总是插了两支钢笔。他眼神不好,我们有一次看见徐老师从校园里走过,结果撞到一棵杨树上,他手里的作业本、课本和粉笔落了一地。我们就帮他在地上捡。我们中的一个人还趁机把捡到的一支粉笔没有还给他。徐老师教高年级的地理课。他经常在课堂上说,从气候和土壤特征看,我们这里可以种植橘子,所以他希望大家读完高中后都去种橘子。很多人觉得徐老师的说法不可靠,橘子是一种很高级的水果,我们这里的土地哪能随便就长出来。很多人甚至都没有见过橘子,只有到快过年的时候,在县里工作的干部们从班车上下来,偶尔会看到他们提的塑料袋里装着十来颗红彤彤的、鲜艳的水果。那正是橘子。只有国家干部才能吃得起橘子。但是有人相信徐老师的见解,到徐老师下课之后,他们就去徐老师的房子里向他请教如何种植橘子的问题。起初是两三个人去,后来是五六个,再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聚集在徐老师的房子门口,就像是一群劳动的蜜蜂。徐老师十分高兴,以为大家都是来请教种植橘子的问题。他索性搬了一块小黑板,摆在外面的窗台上,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粉笔字。那样子就跟他在课堂上一样。人们在黑板周围挤来挤去,叽叽喳喳地说话。正在这个时候,徐老师隔壁的屋子里传出了歌唱的声音,人们就突然安静下来了。那是徐老师的女儿在唱歌。
事情就是这样,人们聚在一起,其实并不是为了请教种橘子的问题,而是为了听到徐老师女儿的歌声。她唱歌的声音好听极了,不光是中学里的人,整个镇上的人都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人们找了许多好句子来形容她的歌声,比如说她的歌声就像一个人在三伏天翻过一座山,喝到一碗冰凉香甜的山泉水;又像是眼前有一笼刚出锅的、白花花的馒头;还像是有人在过年的时候,吃到的一颗上海来的奶糖,刚放到嘴里,还没来得及嚼,那个糖就在舌头上化开了,那股子又酥又甜的味道在全身散开,人就像是长出了翅膀一样飞起来了。实际上人们说的每一样感觉在歌声里都有,但又不全是。就没有哪一个比方是恰当熨帖的。我们班的赵木匠有一次也去听她唱歌,回来的时候两条裤腿全都湿了,还发出一股浓烈刺鼻的尿味儿。他却一点不显得羞耻,只是不停地说,狗日的,狗日的。他说他实在是控制不了,而且那泡尿是他这辈子尿得最舒服的一次,一鼓作气,浑身舒坦,正是俗话里讲的,不枉来世间一趟。
徐老师的女儿名叫徐迎春,在师范学校上学,但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九月,还没有去学校。一家人不久前才搬到学校。徐老师之前在另外一个县里的学校教书。他快退休了,想住得离老家近一点。徐老师的老家在镇子西面山上的徐家庄。徐迎春开始唱歌之前,王老师是镇上唱歌最好听的人。王老师的个子很高,头发茂密,扎成一个马尾巴,垂到后背上。她走路很快,带起一股风,我们远远地就能闻到一股浓烈的雪花膏的味道。她的马尾在身后甩来甩去。她就像是一匹抹了雪花膏的母马。王老师唱歌的声音很响亮,她上课的时候,谁要是唱歌嗓门小,她就把那个人从座位上拎起来,扔到教室外面去;她很有力气,拎一个人的样子就像是拎起一只鸡。当然,这一点我们都不惊奇,王老师本来读的是体育学校,就应该这么有力气。有力气的人唱歌也一定唱得好,所以王老师教音乐课。不过有时候王老师也会在操场上打篮球,她穿着红色的线衣和线裤,脚上是白色的运动鞋。王老师奔跑的时候,男老师们在她身后拼命地追赶。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也在打篮球的队伍里。英语老师还把他的舌头伸出来半截,就像是随时要说一句英语一样。王老师脑后的一束头发在空中飞舞,看上去确实是一匹红色的、奔跑的母马。等到学校开运动会或者新年联欢会的时候,王老师就要登上用木头搭起来的戏台,给大家表演唱歌。王老师穿了一件又肥又长的红裙子,那是特意从县城里找来的。她往戏台上走的时候,身后有个人把裙子后摆托起来,人们可以看得见王老师结实粗壮的两条腿。脸颊上抹了两团胭脂,整个脸上涂了白花花的一层粉,看上去有点吓人。但是英语老师认为王老师很好看。平常王老师在教室里唱歌的时候,英语老师经常会搬一个凳子,坐在教室外面的一棵杨树下面。他假装在批作业,实际上是为了听王老师唱歌。到王老师在戏台上唱歌的这一天,英语老师早早地来到操场上,目光专注地望着戏台,就好像王老师已经在戏台上开始唱歌一样,实际上戏台上和整个操场都是空荡荡的。王老师站到戏台上之后,有个人说王老师的这个样子太难看,简直像个鬼。英语老师听见了,很生气,他对那个人说,你懂个屁,高级的唱歌就得是这个样子。王老师响亮的歌声回荡在操场上空,从镇上向四面的河谷和山峰扩散,比过年时候的锣鼓和炮仗还要响亮。人们说,发出这么响的声音,这得多大的力气,真是一匹母马。英语老师得意地说,你懂个屁。他看上去很欢乐。王老师唱歌的时候,英语老师睁大眼睛,热烈又专注地看着王老师。他的目光迷乱,嘴巴张开,半截舌头露出来,发出响亮的喘息声,一股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我们都见过英语老师的这个样子。
但是徐迎春开始唱歌。人们听见她的歌声,就觉得她是镇上唱歌最好的人。和她相比,王老师就不算什么了。不光如此,她的歌声甚至比收音机里那些女人还要好听。人们都聚集到徐老师的屋子外面,就为了听见她的歌唱。有一次,徐迎春从屋子里走出来,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还对人们说,她可以教大家跳舞。徐迎春的个子很小,圆脸,两片嘴唇饱满又红润,就跟抹了胭脂一样。她说话的时候人们都安静下来了,好像她施了一个魔法。她的邀请让大家惊慌又羞耻。人们不能随便就跳舞,何况是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只有在距离镇子很远的城里,男人和女人才可以跳舞。中学里的王老师也只是唱歌,人们没有见过她跳舞。徐迎春跳舞的时候,身体柔软得像是没有骨头,还有一股淡淡的香气,人们都看得痴呆了。人们说,你看看,这个女人,真是太放浪了,一点都不知道羞耻。不过人们也都承认,她跳舞的样子确实好看。她唱歌就得配上这么好看的舞姿。而且她有资格放浪一点。因为她的未来不会与我们镇子产生关系,她会在县城或者更大的城市里生活,在那里,她可以随时随地唱歌,一定也不介意随便和哪个男人跳舞。
徐老师去找校长,要求他找到那两个贼。校长就把那些听过徐迎春唱歌的人叫到一起,让他们排好队,站在他办公室外面,然后一个一个叫他们进来,问他们是否半夜到过徐老师的屋子外面。他们都说没有。我们班尿了裤子的赵木匠也说没有,因为那天是星期六,他回到赵家庄帮他父亲锯木头。他父亲也叫赵木匠。徐老师就用校长的电话拨县里的公安局。电话里有一个人问徐老师说,你家里少啥东西了?徐老师说,少了一把葱。校长这时插话说,那把葱是之前少的,你说话要实事求是。那个人又问,那他们进没进你闺女的屋子?徐老师说,不知道。那人说,你只是少了一把葱,这种事我们不管。那个人就把电话挂了。徐老师说,岂有此理。他就去镇上的政府里找人。政府里的人知道这件事,派了两个人到徐老师屋子里来。其中一个是老丁。老丁是个很有本事的人,早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打死了两个美国鬼子,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战争进行的时候他是解放军的伙夫,主要任务是到河边挑水,他说正是在挑水的路上,顺便用扁担打死了两个美国鬼子。他说美国鬼子的身上长满了毛,并且还有狐臭。老丁有时候走到校园里来,见到我们,就招手让我们过去,然后他就给我们讲用扁担打死美国鬼子的事情。我们都听了很多遍了,但是老丁每次都以为我们是第一次听他讲故事,因为他不认得我们。不过老丁很会抓田鼠,这事大家都知道,他一点都没有吹牛皮。他经常到自家的地里去抓田鼠,有一次抓到五只田鼠,他把那五只田鼠用一根铁丝串起来,提在手里,让镇上的人参观。那是五只肥胖的田鼠,在铁丝上挣扎叫唤,看上去丑陋又欢乐。他还说,早年的时候他吃过田鼠肉,把田鼠剥了皮,放在柴火里烤,那肉很好吃。
老丁到了徐老师的屋子里。他嘴里叼着烟卷,说话的时候烟卷在嘴唇上一抖一抖的。他问徐老师问题,徐老师回答,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捏一支铅笔,把问题和答案记到本子上。老丁接着到徐迎春的屋子里。徐迎春正在读一册书。老丁不太识字,他问徐迎春读的是什么书。徐迎春就跟老丁讲,她读的是一册小说,讲的是一个下雨天,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打着一把伞走在路上,遇见一个年轻的男人,然后他们站着说话,说了好久,等到他们说完话,发现雨停了,太阳的光芒照在他们身上,然后年轻的女人发现,自己站在一片美丽的花园里,花园里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蜜蜂和蝴蝶飞来飞去,更重要的是,那个年轻男人变成了花园里的一架秋千,正等着她坐上去,在芳香的花丛里快乐地摇摆。徐迎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神情很入迷,那样子,就像是她正是小说里的女人。老丁听了,摇摇头,他说一个男人怎么就变成一架秋千了,这明显是乱讲的;下雨了还站在雨地里说话,冷飕飕的多没意思,也是乱讲。徐迎春说,你不懂的。老丁有点生气,他认为徐迎春有点骄傲。他就给徐迎春讲他曾经打死过两个美国鬼子的事情,徐迎春听了他的故事,果然就露出很佩服的样子。老丁于是进一步教育徐迎春说,你一个年轻闺女,不应该当着那么多男人的面唱歌,更不应该随便跳舞,而且,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也不应该穿裙子——你穿过裙子对不对?徐迎春说,穿过呀,天热了穿裙子,这有什么问题呢?我为什么不能唱歌跳舞?老丁说,你这孩子,到我们乡下来,好多事情你不懂。总之就是你不应该这样子。
那天老丁给镇上的人说,经过他的调查,可以确定,半夜关了徐老师屋子门的贼,和偷了尹大夫的西红柿和裤子的贼,是同一伙的。而且他已经有了清楚的线索,不久他就可以把他们找出来。人们围着老丁,听他讲话,觉得老丁没有吹牛皮。他一次能抓五只田鼠,找到那两个贼也一定不在话下。人们又问老丁,那两个贼到底进没进徐迎春的屋子?老丁叼着烟卷,让它抖了一会儿。老丁说,这闺女有点神叨叨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等抓到贼,我们会搞清楚的。
九月我在学校读书。我已经决定报考师范学校。我不觉得学习困难,我的成绩遥遥领先。父亲也在期待着我能够考取,如果考得上,我就会成为吃公家饭的人,就会成为我们家族里的第一人。但这很难,每年能够考上的人只有一两个。我们年级有五个班,二百多个学生。在星期天,父亲不再叫我去干农活,这样我可以有时间学习功课。他甚至用讨好的口气和我说话。母亲有时候悄悄地给我一块白面饼,但我仍然饿。我的饭量惊人,因为我在学习,还坚持练习武术。
有一天,季强从县里回来。他在县上的中学读书。比我小一岁,按辈分是我堂叔。我们从小在一起玩耍。他回到镇子上一定会找我。他穿着干净的、白色的运动鞋,口音已经有县城人的样子,这让我很羡慕。他问我是不是准备考师范?我说是的,我父亲的愿望就是这样。他说考上师范就是到乡里当老师,就是我们这里,你不如读高中、考大学。我知道季强不考师范,他的目标是上大学,而且我知道他一定能考得上。他要去大城市里读书。但大学是遥远的理想,就像是梦里的事物。季强看出我的羞愧和惶恐,就安慰我说,上师范也行,上完师范还可以再考大学。我说好。
我跟着季强,到他家里。堂奶奶正在烙白面饼子,院子里有一股浓烈的香味。季强取了一块饼子吃起来。堂奶奶拿一块饼子叫我吃。我不吃。她抓我的手,要把那块热腾腾的饼子给我。我还是不吃。但我能听到口水在嗓子眼里吞咽的响声,这让我羞愧。堂奶奶叹口气说,唉,这孩子,志气的。她对我很好,我去家里的时候经常要给我吃的。但我坚决不吃。我从小不要别人给的东西,那会让我觉得羞耻。我从小这样,然后成了习惯。
季强的哥哥姐姐都读书,并且都读得好。我在他家里可以见到很多书,高中课本、高考练习题、师范学校的文学课本《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红旗谱》《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三国演义》《毛泽东选集》《儿童文学》《少年文史报》,还有很多册连环画,等等。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其中一册,坐在那里读很长时间,直到父亲在院子外面喊我的名字。他知道我在这里。季强有时候会背诵唐诗或者宋词,那是他的哥哥布置的任务,等他们回到家里,他需要在他们面前把诗词背出来。我知道背诵诗词是好的,正如我背诵课本上的那些诗词。我也会把它们背下来。通常,季强家里的书不可以带走,如果他的哥哥和姐姐知道了,就会生气。但有一次,季强悄悄地让我带走一册《千家诗》,我把书里的诗歌抄到本子上,然后把每一首都背下来。我在作文里经常引用书里的句子,有些句子语文老师知道,有一些句子不知道。因为这些句子我的作文会得到高分。
季强写日记,他写在有塑料封皮的、漂亮的本子上。他的哥哥和姐姐有时候要看他的日记,就像他们检查他的作文。我也写日记,我把用过的作业本拆开,然后把它们用绳子绑起来,在纸张的背面写。没有人会看我的日记。有时候,我会把一天的生活写得很长,里面的事件其实并不是真的发生过。但我假想有人会看到它们,父亲或者妹妹。于是我把它们藏起来。
我喜欢和季强在一起。他从来不会嫌弃我穿着破烂的、布满尘垢的衣服和鞋子,他也从来不会说我们家是镇上的穷人。在一些时候,我期待着假期到来,这时候季强会从县里回来。然后我就可以读那些书,可以听他讲起县城里的那些新鲜事情。他说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什么都是新鲜有趣的。
那天是周末。晚上,我跟着季强到学校里。我们到了他哥哥的房间。他哥哥在中学里教高中年级的语文,但在夏天的时候已经考上了北京的大学。镇上和整个县上都知道这件事。房间里的东西还没有搬走,摆放着整齐的书本和课桌,有一股清新干净的肥皂香味。季强的哥哥也是我的堂叔。在很多时候,我暗暗期许,未来的生活也如他这样。
季强在书桌的抽屉里翻动,找到一颗水果糖,剥掉糖纸,把它送到嘴里。我拿起桌上的一册高中语文课本,读里面的一篇小说。我很快读得入迷,但季强有一点无聊。他从房间出去,在门前的花坛跟前撒了一次尿。他叫我出去。我放下书,到了外面。月亮升起来,风吹动着树叶,发出细碎的哗响。季强忽然说,我们去摘苹果吧。我说好。我们往校园里的教室那边走。教室后面是一块空地,那里有几棵苹果树。苹果树的四周用插好的木条设置了栅栏。到了九月开学的时候,校长嘴里叼着烟卷,背着手,经常到栅栏外面走动,有时候在夜里也来看一看。苹果实际上还没有长好,但我们知道,树上的苹果已经剩得不多。有一次我看见班上的赵木匠匍匐在教室屋顶的瓦片上,伸手摘了树顶的两颗苹果,而校长正背着手从树底走过去。大家发出欢乐的哄笑。校长转过身来,威严地扫视了一番,但他没有看见屋顶的赵木匠。赵木匠就像一只难看的癞蛤蟆,紧紧地贴在屋顶。
这时我们走到栅栏边,季强叫我蹲下来。他左右张望,观察了一下动静。校园里没有什么人,只有风吹动树叶的声音。接着我们观察树上的情况。月光下的树叶亮晶晶的,那些剩下的果实则藏在树叶后边,是黝黑模糊的圆形,需要仔细察看才可以发现。季强的眼睛黑亮,就像是一只猫。不久他就确定了目标。他让我继续蹲守在栅栏外面,注意两侧和身后的动静。他猫着腰,从栅栏的缝隙里钻进去。他迅速爬上一棵树,灵活得像一只猴子。我在栅栏外面看不到季强,只听见他在树上拨动树枝和摘下果子的声音,那声音听上去十分美妙,竟至于勾引起我的口水。不久,我看见他从树上下来,回到栅栏外面。
正在这时,有一个黑影从远处走过来。那人一边走路一边讲英语,I am a teacher,you are a student.一听就知道是英语老师。他在夜色里蹦蹦跳跳地走路,显得十分快乐。他从栅栏外面的道路上走过去,并没有发现我们。季强说他的英语发音不准,他把a的发音搞成了前舌音,正确的发音是后舌音。我没有说话,但我认为季强的评论没有错,县里中学的英语老师水平当然高级。季强又问我说,英语老师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校园里走路、讲英语?我就说,估计是到教音乐的王老师宿舍那边去了。然后我简单地给季强讲了讲英语老师喜欢听王老师唱歌的事情。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到了周末,王老师已经回到县城里去了。但是不管王老师在不在她的宿舍,英语老师总会出现在她的宿舍外面,他走路、讲英语、唱歌,看上去十分快乐。季强再次评论说,很有意思。
我在期待季强拿出那些果子,但他并不着急。一直等我们回到房间里他才拿出来。一共摘了八颗苹果,那些果子在灯光里泛出青绿色的光芒。季强给了我三颗,然后我们开始吃起来。果子清脆,有一股强烈的酸涩,但酸涩过后有某种松脆和香甜迸发出来,这就像是一朵花忽然开放,神秘而令人惊奇。在吞咽那些果实的某些时刻,我竟然联想到徐迎春的歌声,以及她站在很多人面前,柔软自由地跳舞的样子。当然,这是不恰当的念头。我因此而脸红起来。
我们很快吃完了果子。看得出来,季强也很喜欢这种青涩的味道,他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打了两个嗝,用一根火柴棒剔牙,看上去像是一个老干部。我坐在一条小板凳上,接着读之前没有读完的那篇小说。题目叫《项链》,讲的是一个过着穷日子的女人,因为要去参加一场舞会而借了一串昂贵的项链,但那串项链丢失了。为了偿还项链,她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做苦工,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女人。到了故事的结尾,她意外地发现,当年借到的其实是一串仿制的项链,并不值那么昂贵的价钱。我读这个故事的感觉和课本里总结的中心思想不一样。我很羞愧地发现,其实我还很羡慕这个女人的虚荣,因为她花了十年的辛苦实际上攒了一大笔钱。我要是有这样的机会,也愿意这样去干,可我觉得我没有。
我正读得入迷,季强叫我停下来。他说,这本书你可以拿回去再读,反正我哥用不到它了。我就停下来,心里很感谢他的慷慨。我知道他有了新的主意。
九月里的某一天,镇上的傻子在街道上奔跑,他一边奔跑,一边发出欢乐的叫声。尹大夫手里举着一根木棒,正在傻子的身后追赶。他一跳一跳的样子像一只鸡。人们站在街道的两边看他们奔跑的样子。傻子竟然穿了一条裤子。那条裤子已经很脏,但仍然一眼可以看得出来,那是尹大夫丢失的裤子。傻子一边奔跑,一边用一只手提着裤子,因为他没有腰带。终于在一个时刻,裤子从腰里掉下来,把傻子绊倒在地上。尹大夫喘着气追上来,手里的木棒雨点一样落到傻子的身体上。尹大夫一边打一边说,狗日的,叫你跑,打死你这个狗日的。尹大夫的棒子准确地打在傻子的脑袋上、脸上和上半身,他没有打傻子的腿,因为那里有他的的确良裤子。傻子抱着脑袋,发出凄惨的叫声,他的脑袋上和嘴巴里流了血。尹大夫这才停了下来,他弓下腰,把那条裤子脱下来,裤子上沾满了泥巴、鼻涕和污垢,而且,在屁股的位置破了一道口子。它已经完全看不出是一条高级的的确良裤子,倒像是一块脏兮兮的抹布。裤子被脱掉之后,人们看见傻子肮脏的小鸡居然在可笑地挺立,就像一节烤煳的木棍。他的双腿间和地上湿乎乎的,还有一股浓烈的尿骚味。人们发出欢乐的笑声。
尹大夫再一次朝着傻子的脑袋打了一棒子,他说,狗日的,我今天要打死你。由于气急败坏,尹大夫的这一次打击尤其用力,那根棒子落到傻子的脑袋上之后,竟然断成了两截。而傻子也没有发出乌拉乌拉的惨叫,他的一张脸看上去像是一个破烂污浊的沙包。人们这时候安静下来,都低下头看着傻子的样子。有个人说,死了。另一个人说,这么一会儿就死了?他接着踢了一下傻子的屁股,结果傻子还是没有动弹。尹大夫的一只手抓着那条裤子,另一只手掏出手绢擦脸上的汗水。他还在生气。他一边擦汗一边说,你们大家要给我作证,是这狗日的偷了我的裤子我才打他的。有个人说,那你也不能把他打死啊。尹大夫一听,像一只青蛙那样跳了一下,他说,这狗日的没死,他在装死呢。
人们正围着傻子和尹大夫的时候,镇上的王老五赶着一群羊走过来,那些羊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叫唤,拉屎和撒尿。王老五停下来,鼻子里发出一声冷笑,接着他响亮地擤出一团鼻涕,用两根手指甩到地上,又拿手指在衣服上擦了一下。王老五说,你弄错了,傻子没有偷你的裤子,他是从荨麻沟里捡的。王老五又说,你的那几颗西红柿也在沟里,不信你可以去看,不过它们已经烂掉了。
王老五在东山上放羊,站在东山上看下来,许镇就像是一只搪瓷脸盆的底子,当然是破烂、斑驳、有好多个锡铁补丁的脸盆。人们和牲畜们在镇子上走动,看上去就像是忙碌的蚂蚁。东山上距离镇子至少有三里路那么远,但是王老五有神奇的视力,他能看得清是谁家的母鸡跑到了镇子上、谁家的驴拉了一泡屎,还能看见从厨房里端出来的碗里是白面还是杂面。医院里的杨大夫弯下腰提水的时候,王老五看见她穿了一件粉红色的、绣了一朵牡丹花的裤头,因为杨大夫这一天穿着一件黄色的裙子,她弯腰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裙子就像一面旗子那样飘起来。
杨大夫不久就听说了王老五看见她的裤头的事情,到了提水的时候,她就举了一把伞,那把伞朝着东山的方向撑开,这样一来,王老五就只看见一把伞在提水,而杨大夫的裙子和裤头不见了。
因此,王老五说看见了就一定是看见了。他说他看见傻子先是爬上了荨麻沟里的那棵槐树,然后从树上滑下去,到了荨麻沟里,然后他用一根树枝拨开一团荨麻,从下面拿起了尹大夫的裤子。他把裤子缠到腰里,爬上树,再从树上跳到地上。然后他穿上尹大夫的裤子,欢乐地奔跑起来。事情就是这样的,傻子只是捡到了尹大夫的裤子,而尹大夫却要把他打死了。
荨麻沟就在医院后院的围墙外面。那是一条幽深的水沟,里面长满了深绿色的荨麻。它们伸展出的枝叶就像是怪诞的锯齿。荨麻里还缠绕着别的种类的野草和花朵,草丛里爬行着数不清的蛇。没有人敢到沟里去,但是傻子可以,他在沟里腾挪游走,毫发无损,看上去好像他原本就是那里的一条蛇。在雨天,王老五不用去放羊的时候,他会站到医院后院里的围墙上,指挥着傻子在草丛里找东西,因为他可以从草丛里细小的缝隙里望进去,准确地发现丢到其中的物品。他们有一次找到两角钱,钱的边缘沾满了黄绿色的粪便,一定是医院里的某个人拉完屎没有找到纸,就用这张钱擦了屁股。另一次他们找到一个橡胶套子,傻子从扎着皮筋的开口处,把它吹起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的气球,气球的前端还突出一小块。傻子举着它在镇子上欢乐地奔跑。我们都被吸引了,因为它看上去古怪有趣,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气球。结果我们之中的一个,被他的父亲从人群里抓过去,并且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们才知道,傻子高举的气球是下流和肮脏的东西。还有一次,他们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具婴儿的尸体,尸体已经腐烂并发出臭味。镇上的人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传来传去,但最终没有明确的结果。
尹大夫打了傻子的那天傍晚,镇上的人们看见县里的张司机回来了。他把那辆洋气的吉普车停在医院门口,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擦车。他擦过的地方,车漆发出绿油油的光亮。人们围成一圈,看着张司机不慌不忙地擦车。过了一会儿,张司机停了下来,手里的抹布放到车头的盖子上,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包烟卷。取出一支之后,他并没有直接放入嘴里,而是用两根指头捏住,在烟盒上磕了七八次。那支白色的烟卷就像是一颗皮球一样跳动。之后他点着烟卷,仰起脑袋,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子里冒出来,那样子就像是踩着云彩往天上飞。人们都清楚地看见,他吃的是大前门烟卷,一包烟卷就得花六角钱。这么贵的烟卷,镇上的国家干部也吃不起,只有县长才吃得起。没错,张司机就是给县长开车的。这样气派的吉普车就是县长的。实际上,我们都觉得张司机比县长还要厉害,因为他会开汽车,而县长不会,到了星期天县长不用开会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吉普车开到镇上来。到了这一天,他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车子就跟他自己的一样。
张司机就是医院里杨大夫的男人。所以杨大夫有好几件不同颜色的裙子,她可以随时换着穿。这些裙子都是张司机在县城的百货商店里买的,就算是在县里上班的女人,也不是想穿就能穿得了。而且张司机每次回到镇上,擦吉普汽车的时候,都会给镇上的人说,杨大夫不久就要到县里的医院上班了,因为他已经给县长说过这件事情。张司机的原话就是这么说的,不是“县长答应这件事”,而是“给县长说过这件事”,听起来就很牛逼。不过杨大夫有一次给张司机讲,尹大夫种的西红柿又大又圆,色彩鲜艳,她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吃的西红柿。张司机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他说一个瘸子种出的西红柿不可能比县上和省城的西红柿好吃,她一定是在胡说。但是杨大夫坚持这么讲,两个人因此吵起来。张司机朝着杨大夫的脸上打了一巴掌,还把杨大夫的洗脸盆、一双皮鞋、几颗土豆、一袋白面从房子里扔出来。杨大夫大声地哭喊,威胁说日子不过了。张司机仍然很生气,狠狠地踢了一脚房门,然后钻进吉普汽车里,发动了汽车,一溜烟就不见了。这是某个星期天晚上的事情,镇上的人都知道。
那天傍晚,张司机在医院门口擦汽车的时候,人们跟他说起尹大夫找到裤子的事情,想听一听张司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张司机的鼻子里哼了一声,抬头朝天上看了一看,那意思似乎在说,这种事情不值得讨论。紧接着他朝地上吐了一口痰。他说,那条裤子20元?有个人赶紧说,的确良的裤子,人家尹大夫说花了20元买的。张司机又哼了一声说,那又咋样?就算他穿上40元的裤子,也是个瘸子。人们听了,都笑起来了。有个人问张司机说,还有40元的裤子呢?那得是啥样子的?张司机骄傲地说,我就有,下次我穿上,你们可以看一看。
九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季强去摘校园里的果子。等到我们吃完,季强说,他知道有棵梨树上结满了果子,而且那些梨子差不多都熟了。我知道他说的梨树在哪里,但我有一点犹豫。季强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别想那么多,梨树是学校的,又不是谁家的。但其实我想的不是这个问题,不过老实说,我也说不清楚我担心的是什么。
之后,我们又一次在校园里小心地走路,一直走到徐老师房间门口的空地上。那棵长满了果实的梨树就在那里。我跟着季强,蹲在树底下,听到树叶发出的婆娑声和我们的呼吸声。我们在黑暗中观察形势。那些鲜美的梨子长在树木的顶部,因为较低一些的梨子已经被摘完了。需要爬到树顶上才能够得着那些果子。当然是季强才能够爬上去。他站起来,像一只猴子那样,四肢并用,只用了几下功夫就爬上了树干。然后他踩着枝杈,准备继续攀爬,但这时候,徐老师的房间里发出一声响亮的咳嗽。我立刻很紧张,站起身来,就想往外面跑。季强在树上轻声地嘘了一声,他一动不动地贴在树干上,像一只黑色的壁虎。过了大概五六分钟,季强从树上下来了。我还以为他是要放弃这次行动,但他伸出手按了按我的肩膀,示意我继续蹲在树底下。接着,他蹑着手脚,靠近徐老师的房间门口。他把门链子提起来,扣到门框的关子上。链子扣进去的时候,发出一下轻微的咔嗒声。这声音让我心惊肉跳,但季强显得很从容,关好门之后,他悄悄地回到树底下。房子里没有什么动静,夜晚显得很安静。这时候季强再一次爬上树去,不久之后,他蹲着枝杈,爬到高高的树冠上了。
实际上在那天晚上,我不光是觉得紧张和害怕,我还被一种怪异的不真实感包围。我可能产生了某种幻觉:徐老师隔壁房间里的徐迎春并没有入睡,她站在窗户边,正在夜晚的月光下看着我们。她看见季强像一只猴子那样爬上了梨树,又看见我蹲守在树底下,猥琐又滑稽。她的身上有一股奇异的花朵和植物混合的气味,让我惶恐、羞愧又难过。到了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刻,我发现我尿了裤子。
后来我听见徐老师的房间里,她的儿子伸手拍打桌子,然后大声喊叫起来,房间的灯泡也亮起来了。季强这时候已经从树顶跳到地上,他迅速地奔跑起来,我跟着季强也拼命地奔跑,好几次我差一点就要摔倒。
那天夜里的事情就是这样。
此前,八月里的某天,我拉着架子车走过镇上的街道,我要去山上割苜蓿。经过中学门口的时候,我看见徐迎春站在那里。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头发扎到脑袋后面。她正在踢毽子。彩色的羽毛在空中飞舞。她看见我之后,叫我的名字。我以为她不认得我,这让我意外又羞愧。我拉着架子车,车子上沾满了牲口的粪便、杂草和泥巴。我停下来,脸孔通红,就仿佛我做错了什么。徐迎春走到我跟前,对我说,我看过你的作文呢,写得真好。我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话。她的身上有一股香气,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她又说,你想没想过要发表?我觉得你写得比报纸上的作文还要好呢。我站在那里,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因为炎热的天气,我的脑袋上出了汗,我搓着两只手,张开嘴巴,努力想说出一句话来,但最终没有说出来。我是如此羞愧又狼狈。徐迎春发出欢乐的笑声,她说,改天到学校里来玩啊,我有报纸和作文书,你可以看的。
我总算是说出来一个字,我说,好。
徐迎春和我说话的时候,镇上的一些人也都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这让我更加羞耻和不安。他们都认得她,她穿着好看的裙子,眼神明亮,正在读师范学校,是洋气的城里人、而我只是一个拉着架子车、在地里干活的穷人。在某些方面,我对他们是一种冒犯。
但是,在八月里的很多个夜晚,我都在心里秘密地想象她的邀请。有几个夜晚,我一个人在中学的门口徘徊,期待着徐迎春突然出现在门口。在夜晚的梦境里,我在和她大声流利地说话,她拿给我许多作文书,并且,她拉着我的手,亲吻我的脸颊。如果白天下了雨,我就躲到堆放草料的那间屋子里,在笔记本上写作文。我写了很多古怪荒唐的故事,在每一篇故事里,都会有一个穿着鲜艳裙子的少女。
有一天夜里,镇政府的老丁在校园里走动,看着英语老师站在徐老师房间门口,正对着门前菜园子的一片葱撒尿。老丁上前制止了他,并且质问他为什么要对着那片葱撒尿。英语老师不仅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反而骄傲地说,他想在哪里撒尿就在哪里撒尿。他的这个样子让老丁很生气。两个人就在夜晚的校园里打了一架。他们都没占什么便宜。但老丁警告英语老师说,等到天亮了他会拿上手铐把他铐起来。英经老师用英语骂了老丁一句,表示他根本不怕老丁,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
老丁给校长说,关了徐老师房门的人就是英语老师,因为他不想让人们觉得徐迎春的歌声比王老师好。他坚信王老师的歌声是中学里最好的,而且也是全县范围里最好的。谁要是说徐迎春唱得比王老师好,他就会跟那人吵架,用英语骂他们。老丁说,他关上徐老师的房门,不是要干别的,只是为了在徐老师的门前撒一泡尿。
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在九月,母亲有空闲的时候,总是提起那只腌了酸菜的坛子。它已经被尹大夫的木棒打破了。她不断地咒骂尹大夫,她说这个瘸子的心是黑的并且是一块石头。她要求父亲去供销社里买一个新的坛子来,父亲的答复含糊其词,显然,他没有买一只坛子的钱。九月里我们忙着收割和耕种,也只是能够吃饱饭。
那天尹大夫打了傻子之后,父亲决定再去找尹大夫理论一次。我已经洗清了嫌疑,没有偷他的裤子和西红柿。他应该赔偿我家的坛子。父亲在医院门口等到了尹大夫。尹大夫一跳一跳地走过来,红光满面,穿着他的那条20元的裤子。他假装没有看见父亲。父亲就大声地叫了一声。尹大夫停下步伐,扬起脑袋看着我父亲。他还是跟从前一样骄傲,就好像九月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父亲就提起那只坛子的事情。尹大夫的眼珠子转动了几下,假装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过了几秒钟,他说,不就是一个酸菜坛子?坏了就坏了。
父亲很生气,他挥舞了一下手臂,正想和他继续理论,但是尹大夫已经从他身边走过去了。走了五六步之后,尹大夫回过头对父亲说:不要再提坛子的事情了,等你家的驴拉肚子了,我给驴打一针,不要钱,成了吧。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在九月,我家里的两头驴子也正忙着干农活。它们没有拉肚子。实际上,我们也不能盼着它们哪天拉肚子。驴要是拉肚子,经常就会有生命危险,就算尹大夫打一针不要钱的,那也不够,得打好几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