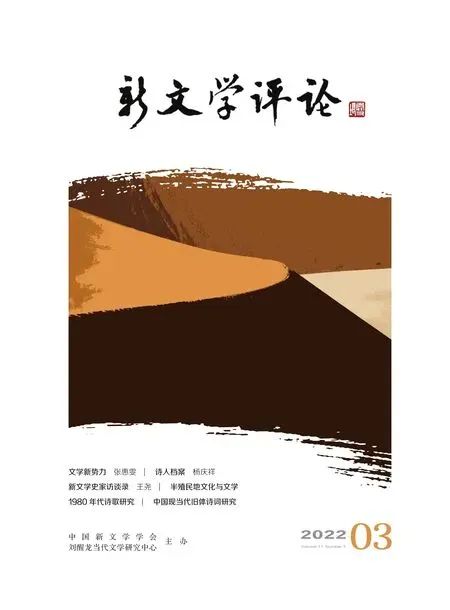面向西方世界的“中国文明”叙述
——解读林语堂《京华烟云》的观念矛盾
2022-03-22于相风
□ 于相风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期间,用英文创作了让他十分自豪的长篇小说《A Moment in Peking》(译为《京华烟云》)。目前学界对《京华烟云》的关注点多集中于这部小说的翻译情况,以及小说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对于小说内部观念的矛盾论述则相对较少。
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写道,《京华烟云》所要表达的是“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但在信的末尾他又强调小说“以道家精神贯串”,“以庄周哲学为笼络”①。勇猛抗日与柔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有着不同径向。如果小说意在纪念抗日勇士,那么以道家思想统摄小说,则削弱了对国人奋勇抗日的赞扬;如果以道家精神贯穿整部小说,那么与国人勇猛抗日的整体精神相龃龉,二者相互矛盾,难以和谐共存。林语堂何以要把二者组装在一部小说中?两种不同话语又是怎样融合的?
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认为《京华烟云》的创作动机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人”,林语堂在该书的《著者序》里也认为小说对中国社会“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而是要尽可能地反映中国人的生活。这部小说是否完成了林语堂的忠实反映中国社会生活增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的目的呢?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深入分析小说的话语结构,尤其是小说迎合殖民主义倾向的话语与反殖民话语糅合而成的、错综复杂的内部形态。
一、毫不妥协的反殖民姿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殖民中国的程度日益激烈,对待日本殖民主义,林语堂主张坚决抵抗。他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抗战,用英文写作文章,向国际社会揭发日本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暴行。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林语堂发表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国》的文章,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认为中国只要坚持抗战,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1938年日本侵略气焰日益嚣张,中国大片领土失守,国人对抗战前景忧心忡忡。在此时期,林语堂发表《日本必败论》,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国民心理多个方面,论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必定失败的结局。这篇文章与毛泽东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持久战》的观点不谋而合,给予在水深火热的抗战中的国人以必胜的信心和同仇敌忾的勇气。与此同时,这种姿态也深刻反映在《京华烟云》之中。
《京华烟云》在下卷《秋季歌声》中通过陈三、阿非、阿瑄等人物形象,揭露了日本侵华的暴行,表现出中国人的无畏抗日的爱国精神,具有反殖民的意义。小说中,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侵略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日本人在香烟里放置毒品,将香烟卖给毫不知情的中国人,让中国人慢慢染上毒瘾。“抽日本多福牌儿香烟”②很多人染上毒瘾,如果不再继续抽,“就两眼流泪,骨头节要断掉”③。博雅就是受害者之一。除此之外,日本还在中国明目张胆地制造和贩卖毒品,“在日本租界,没有一条街没有毒品制造厂,批发或是零卖,即便在最讲究的住宅区,也是如此”④。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殖民主义者还在小孩子喜爱的糖果里加入麻醉剂,对中国的下一代下毒,“一个外国医生在日本租界附近一个中国小学旁边,向一个小贩买了些糖果,化验的结果,证明那糖果里有麻醉剂”⑤。日本军队经过之处,中国的村庄成为“到处是死尸”的“鬼世界”⑥,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全被杀死。阿瑄的年仅五岁的儿子、阿瑄的妻子和曼娘都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日本人的残暴侵略没有让中国人胆怯,反而激起了中国人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勇气。亲人被日本侵略者残害的悲痛让阿瑄不再满足于反走私禁毒的工作。他要复仇。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在战场上手刃日寇保卫家园。木兰的儿子阿通也参军走上抗日之路,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不驱倭寇于东海,誓不归来。”⑦即使是无法亲自投身抗日前线的姚木兰,也在奔赴内地的路上,毫不犹豫地收养因为战争而被迫流离失所的孩子,抚育中国的未来栋梁,让中国人的血脉传承下去。小说刻画出的这些不同领域各凭自己能力积极抗日的中国人形象,表明日寇暴虐的侵略不但没有让中国人屈服,反而激发起中国人同仇敌忾抗日到底的爱国主义勇气和行为。林语堂以英语写作《京华烟云》,讲述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和中国人英勇抗日的故事,对于在国际上揭露日本侵华的残暴不义,具有反殖民的意义。
二、柔顺无为的道家思想内核
《京华烟云》预设了道家哲学思想作为小说的思想内核。小说分三卷,这三卷的卷名分别为《道家儿女》《庭院悲剧》和《秋季歌声》。每卷分别以庄子《大宗师》《齐物论》和《知北游》中的一段文字作为卷首语。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林语堂强调《京华烟云》是“以道家精神贯串”,“以庄周哲学为笼络”⑧。林如斯在《关于〈京华烟云〉》中也明确提出“全书受庄子影响”,认为每卷的卷首语是庄子“出三句题目教林语堂去做”⑨。
最能体现该小说所蕴含的道家思想的两个人物是姚思安及其女儿姚木兰。
姚思安是崇奉并践行道家宿命论和全真保命思想的典型人物。姚思安有强烈的宿命论思想,认为人各有命,物各有主,没有人能永远占有一件物品,如果不是命中注定的主人,即使得到宝物,“一缸银子也会变成一缸清水”。他想逍遥云游的时候一出去就是十年,十年间对生意和家人不闻不问,在这期间其财富却没有减少,回来后依然能够享受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道家宿命论的思想不仅视命运为神秘莫测,而且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姚思安认为要以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态度面对世事变化,保命第一,其他的身外之物都可以放弃。迫在眉睫的战乱让姚家不得不举家逃难时,姚思安妻子要带走古玩珠宝等贵重物品;姚思安则认为命比金银珠宝重要,他不仅不让带走贵重物品,还告诫留守仆人不要抵抗入室抢劫的强盗,“任凭他们拿。不要为不值什么钱的东西去拼老命,不值得”。在遇到强盗入侵抢劫的时候,姚思安的首要选择是妥协保命,隐忍不争,而非抵抗盗贼保卫家园。如他的名字“思安”所示,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姚思安思考和选择的原则是首先要确保个人安全,而非抵御外敌。
姚思安的女儿姚木兰在父亲的影响熏陶下,也以道家思想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婚姻大事上,她遭遇了爱而不得的遗憾。她深爱着孔立夫,父母为她与曾荪亚订婚后,她虽有些微悲伤,但随即也就顺从地接受了父母之命的婚姻,将对孔立夫的爱藏于心底。她没有悲痛欲绝,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进行任何的抗争。道家的宿命论思想是木兰顺从父母之命的主要原因。她将童年逃难时认识曾荪亚视为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父母安排给她的婚姻并不顺意。她人到中年后遇到曾荪亚婚内出轨的问题。发现丈夫荪亚出轨后,木兰没有吵闹哭啼,她没有执着地沉浸在痛苦的情绪中,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荪亚出轨的现实,随遇而安,甚至想顺应荪亚的意思为他纳妾。最终荪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回心转意,与木兰重回平静的婚姻生活。同时,她也面临战乱频仍的大时代下每个人都曾经历的悲苦。战争来临,家人四散女儿离世举家逃难的时代之苦她也要一一面对。但这些痛苦没有将她压倒。遇到生离死别,她也痛苦,但是不在痛苦的过往中沉浸纠结,不因痛苦的过往而悲观面对未来,她对未来仍有信心。因此在遭遇战乱中,她仍能保护自己的身体,维持精神上的平静,这让她获得了相对从容平静的生活。与木兰顺其自然的处世态度不同,木兰的哥哥体仁、木兰的母亲和丫鬟银屏三个人都拘囿于自己的情感之网中,违逆对抗情势,最终造成银屏自杀、木兰母亲变哑、体仁悲苦终生的悲剧。同样与木兰顺其自然不同的,还有木兰的妯娌牛素云。如果说木兰的哥哥、木兰的母亲还有银屏是执着于情,那牛素云则执着于获取金钱和权力。为了权势名利,牛素云将曾家搅闹得不安宁,更过分的是,她和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助纣为虐残害自己的同胞。牛素云的最终下场也十分凄惨。无论是执着于情感,还是执着金钱权力,都无法让这些执着者获得平静和幸福。秉持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道家思想的木兰才在战乱变故中获得幸福与从容。
由此可见,林语堂将道家听天由命柔静无为的思想作为统摄《京华烟云》的重要哲学思想。《京华烟云》的创作目的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人”。这部小说对于西方人从哲学思想、日常生活方面认识中国文明,尤其对于祛除西方从殖民主义立场上对中国文明给予的歪曲评价,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道家哲学中有阴阳互相转化、自然和谐相处等辩证思想,也有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林语堂既推崇道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也对道家随遇而安忍让无为的思想极力赞扬。《京华烟云》对北京这样叙述:“老北京遭受异族的征服很多次了”,“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老北京对他们一律欢迎”。小说将北京称为“老北京”。在此,老北京不仅仅是北京,它还具有象征意义,象征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明。老北京对各种身份、等级、职业的人和善包容,即使武力入侵者也能被老北京平静地接受。他对老北京的这段叙述意在强调在道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文明的包容与柔韧,赞颂道家思想柔顺无为随遇而安的精神传统。林语堂褒扬的道家思想柔顺无为,也正是日本殖民主义者论证中国易于被征服的内容。
三、被殖民者工具化的道家思想
林语堂向西方国家介绍无为包容的道家思想,日本殖民主义却也从中发现了有利于其对中国进行殖民征服与统治的内容。日本人靺鞨生认为中国人服从“强力”,如果中国人“见己强于他人”,就采取“横夺不法”的行动;但如果“见他人之力强于己”,就会偃旗息鼓,“直弃其反抗之念,而屈服他人之下手”。德富猪一郎在《日本与支那》中认为“支那人有忍性,灭其家,覆其国,杀其祖宗,割其土地,彼依然磕头,呼天恩高厚”,强调中国人对于残暴的杀戮侵略不作反抗,只知忍耐妥协。作为日本侵华战争右派的原惣兵卫,主张对中国采取坚决强硬的侵略政策,因为他认为“中国民族对于一切事物”具有“宿命的倾向”,认为中国人对于失败损失并不会耿耿于怀,而以宿命的观点解释和接纳失败,不思抗争。他举的历史的例子便是蒙古族和满族是被汉族“从来所蔑视的夷狄”,然而汉族一旦被这些所谓的蛮夷民族征服,“便平然地生活着了”,由此证明中国人“没有敌忾心与复仇心”,缺乏抗争到底的刚猛之性容易顺从屈服。原惣兵卫举的现实的例子是“昨日犹站在排日运动最前线的济南、满洲与上海,一到今天成为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后,他们就家家户户都挂起了日章旗来欢迎日本军队了”。虽然日本殖民主义者在立场态度上与林语堂不同,但是他们同样发现了中国人柔顺包容的特点,并由此认定中国人容易被侵略征服。
在日本殖民主义者眼中,道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包容忍耐的文化性格,不仅没有被视为中国人的美德,反而成为易于被征服的佐证。他们看到中国人包容忍耐,以为中国对外来的侵略并不会坚决反抗;他们看到中国的随遇而安,以为中国人可以接纳异族的入侵而不以为意。在日本殖民主义窥伺一切机会侵略中国的时期,赞美老北京的不在乎,无疑是对中国抗战不利的,还暗合了日本殖民主义势力侵略中国的野心。尽管这并不是林语堂的本意,但在全中国鼓足勇气顽强抗日的大背景下,林语堂对道家柔顺无为随遇而安思想的颂扬因此而不合时宜。
《京华烟云》中林语堂用以贯穿全书的道家思想与小说的抗日主题相矛盾。林语堂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认为《京华烟云》所要表达的是“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但是信的末尾他又强调小说“以道家精神贯串”,“以庄周哲学为笼络”。抗日与道家思想是极难调和的两极。抗日需要的是誓死抵抗顽强不屈,道家思想推崇的则是随遇而安柔顺无为,一个需要的是刚性,一个推崇的是柔性。如果小说意在表达抗日愿望,那么以道家思想统摄小说,则削弱了对国人勇猛抗日的褒扬;如果以道家精神贯穿小说,那么与中国人勇猛抗日的坚韧相龃龉。这两者显然相互矛盾,难以和谐共存于同一部小说中。但林语堂仍然把二者强行组装在《京华烟云》中,原因是什么?
四、缠足意象与自我殖民化倾向
《京华烟云》对缠足的迷恋性叙述具有自我殖民化的倾向。小说对缠足之美的首次叙述,视角在全知视角和姚木兰的个人视角之间跳跃转换。木兰第一次见到桂姐,她首先看到的是桂姐“身体颀长骨肉匀停”的大概身形,之后木兰的视线关注点在桂姐的小脚上。桂姐此时之于木兰,是一个陌生人。一般人见到陌生人的时候,首先要细看一个人的身形和容貌。此处虽有对桂姐身形的叙述,但对于桂姐容貌的描写却付之阙如。叙述重点落在桂姐的小脚上。桂姐脚“很小,裹得整整齐齐”,在将桂姐的衣饰一笔带过之后,木兰视线焦点重新落回至小脚,逐一描写桂姐弓鞋的颜色、长度及其装饰:弓鞋颜色是“红色”,长度三寸,弓鞋上面“花儿绣得很美,鞋上端缚的是白腿带儿”。这是从木兰视角进行的叙述。然后就小脚展开全知视角的议论,提出小脚是女性身体“完美的基底”,小脚让人喜爱的观点。在赞美桂姐脚纤小周正等诸多优点之后,叙述又转回木兰的心理视角。木兰见到桂姐的小脚时,她的内心波澜起伏,她的心先是“惊喜得跳了起来”,继而又“悔恨”,悔恨自己没有缠足,因为她自认为天足不如小脚美,由木兰的心理起伏再次反衬桂姐的小脚美。小说在此处以全知视角,以男性的赏玩的立场,用近一千字的篇幅不厌其详地叙述缠足带给女人的体态美。在第三十三章中,小说又借人物辜鸿铭之口,再次确认缠足对于女性的好处,并否认缠足给予女性身体的伤害。小说人物辜鸿铭认为缠足给予女性生理和道德等方面的种种益处,但对女性却“什么害处也没有”;与之相反,天足的女人“把蒲扇似的大脚各处踩,她就失去了女性生理和道德的特质了”。缠足甚至被叙述者视为女性的一项重要生理特质。
喜爱女性缠足属于个人审美趣味的领域,但在小说中将女性缠足作为叙述对象,以男性立场的一再叙述赏玩,则已经溢出个人审美趣味的范围,成为特定的缠足意象。
《京华烟云》的目标读者是西方人,而彼时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误解与歧视极深,中国女性的缠足即是他们歧视中国的原因之一。林语堂也早已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宣传中含有殖民主义的“卑污意志”。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谈到1935年《吾国与吾民》出版的时候,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殖民主义歧视:“白人种族歧视很深,对黄种人与对黑人一样,简直不把他们当作人看待……他们想起中国时,会想到龙、玉、丝、茶、筷子、鸦片烟、梳辫子的男人、缠足的女人、狡猾的军阀、野蛮的土匪,不信基督教的农人,瘟疫、贫穷、危险。”刻意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妇女的缠足上,恰恰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用来印证中国文明野蛮低等的话语策略的一部分。西方女性的束腰对身体的危害要远大于中国妇女缠足对身体的危害,但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无视自身陋习,仍然“将缠足与西方人眼中的野蛮民族的习俗置于同等的地位,这在向我们暗示,他们认为拥有这些非自然的、野蛮的习俗的文明形态必然是低级的”。从上面林语堂和林太乙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林语堂是清楚缠足与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策略之间的关系的。自1903年梁启超撰文抨击缠足以来,1911年开始官方就已经禁止缠足,到了民国初期,很多知识分子已经确立了女性缠足不但不美反而丑陋的观念。既然如此,林语堂为何仍然在《京华烟云》中对女性的缠足给予特别关注与相当长篇幅的叙述?
除了有林语堂个人审美趣味的原因之外,与其所处的异国环境,尤其是出版环境有关。“他们(主流出版商)只对‘东方异国情调’的套话感兴趣,如女人裹脚和男人吸食鸦片。”林语堂以作家身份在欧美社会以英语写作,面临来自身份、语言、出版、生存等多重压力。他以英语写作,必然希望作品能够获得欧美读者的接受和欢迎。既然欧美的主流出版商只对女性缠足男性吸鸦片等对中国的刻板套话感兴趣,那么欧美读者对中国的期待视域,也必然难以摆脱这些中国的刻板形象。来自弱势中国的林语堂,如果要在强势的欧美生存下去,必然不得不适应出版商的要求,在作品中使用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想象的规定性套话。国外研究者也指出《京华烟云》受出版商制约的情况:“约翰·黛公司的销售部门规定,像《京华烟云》这样的中国小说,应准确地记录美国公众所想象的中国生活应该具有的面貌。”如此一来,这就使得《京华烟云》的某些叙述就出现迎合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倾向,表现出自我殖民化的嫌疑。
五、西方作为救赎者的文化想象
上文已述,《京华烟云》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和对顽强抗日的支持,二者并不协调,如果必须要在二者之间找到关联,那么就是中国典雅精致的传统文明被日本殖民主义摧毁,既是道家“浮生若梦”思想的体现,同时也凸显了欧美作为“救世主”的救赎意图。
《京华烟云》前两卷向欧美社会介绍和展示中国人高雅悠然、富有艺术气息的生活。前两卷模仿《红楼梦》的人物设置,叙述了以姚、曾、牛三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上层社会,在和谐的家庭伦理秩序内婚丧嫁娶、宴饮雅集、吟风颂月等情趣盎然的生活,因此小说前两卷笼罩了一层华贵优雅的色彩。这些中国社会上层人物善于发掘生活中的美好与情致,结社吟诗,赏月品蟹,园林悠游,登山游水,享受着现世人生的乐趣。甚至在什刹海发洪水百姓被淹的时候,他们去什刹海也是为了观赏洪水的壮阔,而不是为了救人。即使木兰和荪亚到了杭州归隐田园,木兰也善于利用身边的特产风物精心烹调,享受美味带来的快乐。如此一来,中国人舒适惬意、精致高雅的生活就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木兰、莫愁各具美好品质之外,次要人物如曼娘,从年轻守寡,独自一人抚养儿子,善良忍耐,幽居深闺冰清玉洁,也深具中国文化所褒扬的贤良淑德的女性美德。通过前两卷塑造的建立在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优美雅致的生活、善良可爱的人物,林语堂将中国社会的美好情致,将中国传统文明的特点呈现在西方社会面前。
在日本的侵略面前,《京华烟云》塑造的中国文明精致优雅但柔弱顺从如古典美人的样子,以柔弱无力的面目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摧残,这除了刻画出日本殖民主义侵略的暴虐外,还含蓄暗示着中国需要欧美作为“救世主”来拯救。姚家和曾家这两个大家族迫于战争的威胁,脱离了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四散逃难,优雅舒适的诗意生活被艰苦跋涉的逃难生活所取代,柔弱美丽的曼娘被日本殖民主义暴虐摧残。为保护精美的王府花园——静宜园,阿非将花园卖给了美国人董娜秀,“董娜秀小姐为人正派,决不会占便宜。而那个合同不过是个形式”;阿非和经亚两家又在美国人董娜秀的干涉和帮助下逃出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和天津,他们逃难坐的是英国轮船;木兰和女儿阿眉在美国人司宽顿小姐的介绍下进入了天主教的修道院,从而躲避了日本兵的骚扰;阿眉遭受日本兵侮辱时,是法国修女出面阻止了日本兵的胡作非为;木兰和阿眉在美国医生的帮助下才免于被日本人抓走的厄运。在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灾难的时候,都是因为欧美人士的援手,一部分中国人才没有遭受更大的灾难。两相比较,曼娘在乡下,因为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欧美人士的援助而惨遭日本人凌虐。对比之下,西方国家作为“救世主”的拯救意味由此得以凸显,从而迎合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域。
林语堂之所以在《京华烟云》中迎合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凸显西方“救世主”般拯救中国的意味,一方面与林语堂基督教牧师的家庭出身及其所受的教会学校的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与林语堂写作《京华烟云》时的处境有关。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在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压迫的同时,也从意识形态上刻意丑化歪曲中国形象。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的目的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人”,是让西方了解中国。然而中国半殖民地的弱势地位与西方殖民主义强势国家的现实,使得林语堂对中国的介绍并未如实地反映真正的中国文明,反而在西方殖民主义权力关系作用下,出现迎合殖民主义话语倾向的叙述,表现出自我殖民化倾向。
结 语
半殖民地中国面临多个不同殖民帝国的压迫。由于各个殖民帝国对中国的殖民程度在不断变化,因此不同时期各殖民帝国与中国的矛盾也处于变化中。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从军事政治到经济文化的全面侵略日益深入,欧美国家对中国的殖民程度相对较轻。半殖民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和处理与不同殖民帝国的关系。
林语堂主张坚决抗日,但对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则是与之保持亲善关系,主动向其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对西讲中”,积极沟通,争取这些西方国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文明,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林语堂称自己为“两脚踏东西文化”,将自己定位为沟通东西文化的使者。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东方文化,是“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和西方这两者之间。
《京华烟云》的目标读者是西方人,在这个“对西讲中”的过程中,林语堂将道家思想作为主要内容向西方国家进行介绍。实际上,林语堂清楚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都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思想,共同影响着中国传统文明,“二者是使中国人能够生存下去的负正两极,或曰阴阳两极”,“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他所著的《孔子的智慧》和《老子的智慧》,分别对这两种思想进行了论述。但是结合《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苏东坡传》等著作来看,林语堂在向西方社会介绍时,对这两种思想做了简化处理,即仅重点向西方国家展示中国传统文明中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一面,对中国传统文明中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面则没有予以同等重要地位的介绍。以道家精神贯穿《京华烟云》这部小说,并不能反映中国人勇猛抗日顽强不屈的爱国精神,反而印证了日本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中国柔顺可欺的观点。这种矛盾可能是林语堂始料未及的。
半殖民地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和身处西方的写作环境,使得林语堂在写作中需要面对不同的现实考量。《京华烟云》的创作动机是将真正的中国介绍给西方,纠正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是含有解殖民意图的。但在西方出版方的殖民趣味的制约下,《京华烟云》却不得不表现出迎合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特点,显现出自我殖民化的倾向,解殖民意图并未得到有效展开。这也是小说的另一个矛盾之处。这种矛盾也给我们以提示,即中国知识分子要完成“拆解、消解、消融、抹去殖民化的不良影响,解构殖民宰制话语和西方中心主义,重建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的艰巨任务,难以仅靠知识分子的一己之力完成。
半殖民地知识分子在抗日与亲西方之间、在迎合殖民主义话语与反殖民话语、在寻求理解与被迫曲解等立场之间表现出的矛盾特征,使得《京华烟云》的小说结构繁复、充满张力,但另一方面也破坏了其观念的一致性,宣教意味过浓。这种矛盾性本身就是半殖民地中国作家们需要面对和超越的,在这方面,《京华烟云》有其成功之处,也有其不尽完美之处。
注释:
①林语堂:《给郁达夫的信——关于〈瞬息京华〉》,《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八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297页。
②林语堂:《京华烟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5页。
③林语堂:《京华烟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5页。
④林语堂:《京华烟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8页。
⑤林语堂:《京华烟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⑥林语堂:《京华烟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0页。
⑦林语堂:《京华烟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二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页。
⑧林语堂:《给郁达夫的信——关于〈瞬息京华〉》,《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八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297页。
⑨林如斯:《关于〈京华烟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一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⑩林语堂:《京华烟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一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