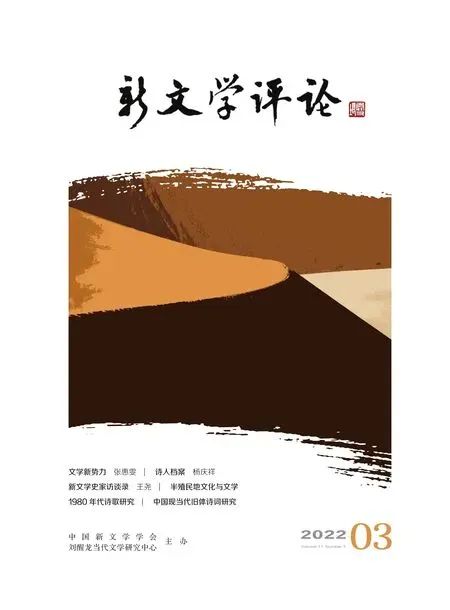胡风旧体诗词创作动因透视
2022-03-22易纾曼
□ 易纾曼
以新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身份为人们所熟知的胡风,其实还有着作为旧体诗人的一面。胡风一生创作了旧体诗词3000余首,目前仅留存400余首。而胡风一出狱,便再也没有作过旧体诗词了,甚至说“它限制严,早已僵化了,很难反映现实生活”,强调他的旧体诗词创作“是一种特殊环境下的产物,绝对不宜学的”①。
从创作时间上来看,胡风的旧体诗词创作呈现间歇性和爆发性的特点。他的旧体诗词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生时代,可惜并没有文本保留下来。第二个阶段集中于八年全面抗战时期,可见文本共计16题23首,时间跨度从1937年9月16日到1945年8月21日。第三个阶段是政治受难时期,即1955年至1978年,共创作旧体诗词3000余首,目前可见400余首。另有1951年《喜过三峡》一组(残句),1953年步韵鲁迅的《惯于长夜过春时》作诗二首,介于第二、第三阶段之间,可视为第三阶段的前奏。从创作心理上来看,胡风并不以他的旧体诗词为荣,甚至多次否定自己的创作,创作心理和行为上存在着割裂。这种否定式的创作态度,绝不仅仅是自谦,更多是与胡风多舛的命运带来的矛盾心理,以及他在新旧之间的情与理的纠葛有关。
对于胡风研究来说,忽视其旧体诗词创作的文学事实,无疑是不全面的。对于胡风旧体诗词创作研究来说,关注其间歇、爆发与否定式的创作特点,挖掘背后的创作动因,有助于还原一个现当代文学史上更为全面的胡风形象,展现其更为深广的文学史意义。
一、胡风早年的旧学修习
同那个时代很多新旧兼擅长的文学家一样,早年的旧学修习是胡风旧体诗词创作的基础动因。1902年11月1日,胡风出生于蕲春县赤东湖畔下石潭村。蕲春隶属黄冈,地处鄂东,坐落于长江中游之畔,大别山南麓,既为吴、楚、中原文明的叠合处,又得佛教的浸染,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蕲春有教授县的美誉,据该县博物馆统计,到2012年,蕲春籍教授、副教授人数达到4300余位,遍布海内外。蕲春东南面的蕲州东长街人称“博士街”,走出教授博士126人。赤东镇范铺村堪称“教授县”里的“教授村”,110多位专家、教授出自同一个村。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养育了诗人、文艺理论家、出版家和翻译家胡风。
旧学于胡风而言,缘起于儿童时期。胡风10岁以前,过着无忧无虑的农家生活。在他10岁的时候,由于邻里纠纷,家中陷入官司,这让父亲张济发意识到家里没有一个读书人是不行的。于是父亲将胡风送入蒙学,拜师陈南如先生,开始了旧式传统教育的启蒙。胡风在这里第一年学的是《三字经》《千字文》等旧学经典,第二年学民国小学的国文课本。两年之后,胡风的父亲张济发对先生的教育改革不大满意,自己牵头办起了蒙学,请了一位王姓老先生来教授四书五经,但少年胡风觉得枯燥无味,烦闷无比。一年之后,又转到下石潭垸张家的家学去学经馆。张家的老师是一名贡生,叫做张晓初,讲授的大多为古文,胡风在这里才忽然领悟到了古文的魅力,开始揣摩起古人的思想和生活,学会了欣赏古典名作。后来又接连换了郑先生与朱义甫先生。朱义甫先生是一位受过海外新思想熏陶的秀才,曾在南洋华侨子弟学校教过书。虽然他教授的依然是四书五经、古文诗词之类的旧学,但他思想开明,善于诱导,胡风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旧学的知识。
15岁的时候,胡风转到饶石波先生处继续念经馆,接受的是四书五经和君臣忠孝的学问道理。饶先生擅长古诗词,讲解下来,炼字格律,平仄音韵,头头是道,开启了胡风旧体诗词的第一课。胡风这时也学着写了一些旧体诗词,先生认为还可以,只是立意太直,没有诗味,还说他性情过激不适合写诗。胡风写的内容常常是自己的不满和抱负,还有些讥讽社会的诗作,可惜都没有保留下来。为了继续锤炼自己,胡风还在先生的建议下开始读《唐诗三百首》,以求“不会作诗也会吟”。在梅志的回忆中,胡风曾谈到他创作旧体诗词是受到饶石波先生的影响:“他后来说,我之所以能写旧体诗,还是从饶先生那里学到了一点入门的知识。”②在蕲州官立高等小学堂就读时,胡风以下联“满城桃李属麟岗”对上了国文老师的上联“六管笳灰更凤律”,这一下联打破了数对数、山对水的陈规戒律,充满了少年豪情,一时间为全校师生所称道。
古典名著的阅读也大大丰富了胡风的旧学修养。10岁开始读书后,胡风最期盼的事就是放学后回家,到大哥张名山的磨坊里听他讲戏文故事和民间传奇,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演义》。17岁在蕲州官立高等小学堂的第一个春节,胡风第一次从书本上读到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整整一个假期他都沉浸在古典小说的海洋里。从官立高小辍学后,胡风接触到了《西厢记》和好友叔公张香吾的诗词集《舟如屋诗稿》,张氏和官员名士之间的酬唱之作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
旧学的修习为胡风创作旧体诗词打下了基础,新旧之间的情理冲突却使他在学生时代就埋下了否定式创作的种子。虽然胡风在学生时代一开始接受的是旧式教育,且经常得到师长的称赞,但是胡风一直对旧形式没有表现出特别钟爱的态度,有时反而会主动地去疏离。在朱义甫先生门下求学时,一次先生讲韩愈的《师说》时对其推崇备至,胡风忍不住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韩愈所讲的道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所授之业是古代典籍,根本不足以谋生济世。胡风虽然很尊重朱先生,但对他常常以儒家卫道者自居十分反感。16岁在饶石波先生门下读书时,被先生评价为“不走正道,将圣贤之道胡乱批驳,非读圣贤书的学生所为”③。在蕲州高小读书时,虽然教古文讲经书的老师十分的开明,能欣赏有新意的作文,但还是觉得胡风的文章过于激进,对他大为不满。1920年五四浪潮波及了蕲春,学生们举行了爱国游行活动。为了制止学生,校长在校门口贴了“须学曾三颜四,勿忘禹寸陶分”的对联,胡风不以为然,提笔在旁边写下“须学辛亥志士,勿忘庚子赔金”,以强硬激进的态度正面对抗,并一怒之下辍学。1925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胡风曾选修过吴梅的《词选》,但他觉得这课程完全不合他求新的要求,感到十分无趣。从胡风的这些叛逆行为中可以看出,他对旧思想是反感排斥的。特别是在接触五四新文学之后,胡风全部的兴趣都被革命的、启蒙的文艺思想所吸引,开始对代表旧思想的旧式文化产生逆反心理。但这并不代表胡风是在与旧文化、旧形式割袍断义,而是作为新文学的拥护者自觉地与这种不顺应五四潮流的文学形式划清界限,这是他于理智上的选择。然而有着深厚旧学渊源的胡风是无法完全割舍掉对旧形式的牵挂,这就使他在特殊时期会不由自主地对旧体诗词倾注热情。而新旧之间情与理的冲突,又会使他产生一种不自然、不正规的矛盾心理。
二、胡风的“民族形式”立场
新中国成立前,胡风的旧体诗词写得不多,目前可见的有23首,基本贯穿抗战时期。在同期的文章里,胡风虽然很少谈及旧体诗词创作,但在“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围绕“旧形式”“民间形式”发表了不少观点。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这位不折不扣的新文学家在这一时期诗性“小”发呢?从胡风的“民族形式”立场中,我们可以深挖其对旧形式的思考,来一窥他这一时期创作旧体诗背后的复杂心理。
什么是“旧形式”?所谓的旧形式其实包括民间形式和传统文人的旧文体两部分。文艺界关于旧形式的探讨并非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然而旧形式问题始终与民族化、大众化问题的探讨分不开家。五四伊始,新与旧的碰撞便从语言、内容、体裁等各个层面展开论争。30年代初期,“旧瓶装新酒”的拟语已经开始使用。投身于大众化实践的作家们对民间形式中的连环画、唱本等加以利用,来反映爱国救亡的内容。在历时三年之久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关于旧形式如何利用的问题,始终是文艺工作者们阐述的重中之重。
“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发轫于延安。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提出了文艺工作者应该将具有民族特色的旧的艺术形式与抗日救亡内容相结合的建议:“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④10月,毛泽东在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进一步发起了要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文艺的号召。这一号召立马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中产生强烈反响,他们围绕如何看待旧形式、如何评价新文艺、如何界定“民族形式”内涵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1939年2月7日,柯中平发表《谈“中国气派”》一文,率先肯定了“民族形式”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4月,陈伯达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发表于《文艺战线》第3期,他将建设“民族形式”和其核心理解为对旧形式的扬弃,而非是将五四文艺传统进行传承。随后,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柯中平《介绍〈查路条〉并论创造新的民族歌剧》等文章的发表,基本上延续了这一观点。陈伯达等人的观点一经发表,立马遭到了何其芳、周扬等人的反对,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在如何评价新文艺和如何利用旧形式上。何其芳认为新文艺较之旧形式与民间形式,应该处于更高阶的地位。周扬也对五四新文艺做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旧形式即便是改造之后,也只是较低级的艺术⑤。但周扬总体上还是支持利用旧形式的,在《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中,他指出了利用旧形式的意义所在:新形式与旧形式共同发展,相辅相成,发挥旧形式的长处正是为了新形式服务的⑥。
香港文艺界也参与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1939年10月19日,《文艺》副刊为纪念鲁迅,召开了“民族文艺的内容与技术问题”主题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并得到了与延安文艺界相通的结论:“民族形式”构建是现阶段和中国文艺将来所必要的一条路,而现今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各种旧形式和外来形式,创造新的民族形式,来反映抗战的现实。随后,黄药眠、许予、文俞、杜埃、宗珏、安适、袁水拍、黄绳等人相继在《文艺》副刊发表相关文章论述,进一步推进了“民族形式”论争在香港的发展。
“民族形式”论争也在国统区文艺界和思想界引发了巨大反响。1940年3月24日,通俗读物编刊社成员向林冰发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⑦一文,提出“民族形式的创造”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究竟以何为中心源泉的问题。随后又接连发文十数篇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待旧形式(民间形式),向林冰也承认其有“反动的历史沉淀物”需要彻底肃清,但总的来说民间形式是创造民族形式的起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这一观点的提出推动“民族形式”的论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除少数人持有赞同态度外,不少文艺工作者难以认同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基本否定的态度。关于“民族形式”的又一轮论争,围绕何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再次展开,逐渐使论争陷入了对民间形式、旧文艺和新文艺的片面思考。此后围绕这一问题的论争,要么抬高旧形式的地位,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成果;要么过分强调新文艺而一笔抹杀旧形式。
“民族形式”论争前后持续三年之久,在延安、重庆、香港都引发了文艺工作者们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其讨论的核心为“文艺的民族形式”的构建问题,又围绕如何构建“民族形式”、何为“中心源泉”等问题展开论争,涉及了对五四新文艺和旧形式、民间形式的再思考。1940年,胡风撰写了长文《论民族形式问题》,对论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总结。胡风认为,“民族形式”的源泉不是旧形式,其真正的起点应该是现实主义的五四传统,他强调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地分开,“‘民族形式’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⑧。所以一切否认五四传统的观点、误解五四文艺传统的观点,将形式和内容分开而谈的观点,都没能正确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这种观点不仅不同于“通俗读物编刊社”一派的观点,也与其他左翼作家意见有所不同。
那么在“民族形式”构建中,该如何对待旧形式呢?胡风给出了他的答案。首先在基本立场上,他并不否认旧形式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胡风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客观现实:在抗日救亡这一特殊时期,“一切旧的形式,民间的以至士大夫的形式”⑨都得以复活,为现实主义的民族战争服务,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作用。所以胡风并不反对作家们从旧形式中汲取营养,丰富自我。民间文艺和传统文艺的利用在“民族形式”的创造里十分重要,也对实现现实主义的胜利十分有利。
其次,胡风强调旧形式存在着大量的不足,且其思想内容和形式是不可以被割裂开来谈的。在内容上,民间文艺在封建背景下产生的对于封建统治的暴露、攻击与讽刺等等,鲜有反抗权威的民主意味,没能打破窠臼。即使有,也仅仅只能在封建意识的框架里挣扎反抗,无法从内部打破自我,根本不能被称为“发自贰心的叛逆之音”(向林冰语)。在形式上,其故事化、直叙化的模式,“从形式方面感到了民间文艺被封建意识的内容所规定了‘宿命的’性格”⑩;旧形式的格式,是承载着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定形象的载体,是“通过它可以唤起特定封建意识的情绪的、象形文字式的符号”,其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及半封建的旧经济旧政治尚在中国占优势这一现实。所以在这一阶段,新的文艺运动必须要和旧形式作彻底地斗争,因为旧形式这种“旧瓶”具有相当的毒性。对于旧形式的缺陷和学界对旧形式的错误态度,胡风可谓看得十分透彻。
最后,胡风对旧形式基本意见与鲁迅是一致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绝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第一,必须毫不留情地对旧形式有所删除,不能因为构建“民族形式”的缘故本末倒置。旧形式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而将其中有毒的成分兼收并蓄,从而说它特别能表现中国民族特色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第二,“旧瓶装新酒”是完全不可采取的、违背了文艺史法则的一种理论。其本质上是旧的形式以温和手段以退为进,抢占新内容的复辟手段。第三,“民族形式”构建,始终要坚持以五四传统为前提,以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为中心。旧形式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所谓的“中心源泉”。在这一前提下,现实主义的作家去研究旧形式,利用民间形式,不是为了去学习它的形式或者内容,而是为了从其中得到帮助,更好地理解大众的生活,揣测大众的心理与观念,吸收大众的文艺词汇。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具备抗毒性,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从民间文艺以至传统文艺里面汲取营养。旧形式不但不能是民族形式的起点,也不能是大众化形式的替身,民族形式也不能被等同于大众化或者通俗化。这体现了胡风对五四启蒙传统的坚守。
那么根据以上的论证和结论,胡风在这一时期少量地创作旧体诗词就可以解释得通了。1921年,就读于武昌的中学时,胡风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他“狂热地像发现了奇迹地接受了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新文学的学习和创作中。抗战时期,胡风已逾35岁,早已从那个下石潭村懵懂接受旧式教育的孩童蜕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左翼启蒙战士。也许是战争引发了他的诗情,使他想要去写“从这样(战争)的现实生活中得来的真实的感动”,于是便有了“书生毛戟非无用,为杀倭儿拾铁枪”(《悼东平》三首之一)这样的豪情之句。也许是重返故里,触景生情,少年时期所学的旧学知识一一涌上心头,便有了“午夜凭舷望,乡园一梦横。欲呼卿小字,云水了无声”(《船过蕲春》)这样的深情之句。也许是在文艺论争的写作中,对旧形式的思考和探究使他欲对自己的理论有所实践,于是尝试着用这种旧形式来突入生活,有了“案头烂纸苍生哭,寨里堆金大盗狂”(《残冬雨夜偶成》二首之二)这样的感慨。胡风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他关于旧形式的理论:“胡风创作的这些出手不凡、滋味昂然的旧体诗说明,旧形式、旧语言在新的时代也可以旧貌换新颜,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和生机。”旧学的修习已经深入了胡风的血脉之中,在他偶有所感的情况下可以辅佐他的诗情,赋予他旧体诗人的身份。但是和这一时期的许多新文学家一样,尽管写旧体诗词,内心深处对“旧形式”有特殊的眷恋,但是他们对所处时代的清醒认识使他们给自己的创作行为打上了不合时宜的标签。旧形式是不应该成为主流、不应该被提倡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导致了胡风在抗战时期虽然创作了旧体诗词,但数量极少:1937年4首,1940年4首,1941年7首,1942年3首,1943年1首,1944年2首,1945年2首。值得注意的是,胡风这一时期所作的旧体诗虽然数量少,但都在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本质上与他新文艺的方向是一致的。
三、政治受难与旧形式的诱惑
1955年至1978年,胡风在狱中度过了他生命中的逾四分之一的时光。没有纸、没有笔,创作受限,他靠默吟在狱中创作了3000余首旧体诗词。据胡风1979年的回忆,他写的作品有《求真歌》(14章)、《怀春曲》(220余篇,共约3000首)、《红楼梦·人物悲剧情思大交响曲》(30余首)、《采世巨灵狂想大交响曲》(12首)、《创世巨人理想大交响曲》(12首)、《女性悲剧情思大交响曲》(12首)、《创世英雄悲壮大交响曲》(12首)、《过冬草》(律诗、词,约300首)、《报春草》(律诗、词,约100首)等。遗憾的是,这些诗作或因被遗忘,或因被收缴,大部分已经佚散。从《胡风全集》第1卷收录的旧体诗词作品来看,目前政治受难时期的作品仅剩400余首。另有笔者发现未被全集收录的《求真歌》(收录于陈思和主编的《史料与阐释》第4辑)。
根据梅志的回忆,胡风曾说过他一开始在狱中尝试着写的是自由体的新诗,但由于无纸笔记录,新诗也不好记诵下来,所以只好改写旧体诗了。胡风后来谈到自己的狱中创作时这样解释:“1955年以后,二十多年离群独居,和社会完全隔绝,又无纸无笔,只好默吟韵语以打发生活。因为只有韵语才能记住。最多是五律和五言排律。合成一部,题名《怀春曲》。”从这里不难看出胡风选择旧体诗词是无奈而为之的,因此心理上难免对自己的创作行为有抵触的情绪。然而这种退而求其次与他抗战时期将旧体诗作为消遣不同,在漫长的监禁生涯中,他完全地向旧体诗词这种传统的民族形式皈依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风向旧形式投了降,他的创作还是坚持着他对旧形式的一贯态度:格律诗僵化腐朽,很难反映现实生活。即使无可奈何要全然地进行这种创作,那么就尽自己所能地改进旧体诗词的形式,增强它的表现力,扩大其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量。胡风打破了格律诗不能重复字或词的规则,将字或者词当作音符,有意地成对重复,表达意义和情感上的双重旋律,他称这种手法为“连环对”。尽管作了如此改变,胡风仍强调自己的创作“是一种特殊环境下的产物,绝对不宜学的”,表现出一种自我否认的尴尬心态。实际上,这种心态正与胡风特殊的创作动因有关。
胡风创作的激情,首先来自强烈的情感抒发需要。政治受难、自由无望,狱中默吟已经成为胡风表达自我、发泄情感的惯有方式。对于一个文人来说,不写作是不行的,新文学的创作道路受阻,那只好退而求其次在旧体诗词这种比较熟悉的文学形式上找寻精神的自由。“胡风在狱中用诗的形式给自己构筑了一道精神壁垒,写诗成了他在漫长而孤独的监禁生涯中的精神寄托。”如果没有诗歌,很难想象这位诗人与战士能否坚持得下来。旧体诗词为胡风提供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心灵栖息地,使他得以在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中屹立不倒,始终保持钢铁般的诗人身躯。
1954年,胡风用5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本以为是“拈毫至信探三昧,荷戟孤忠走两间”(《次原韵报阿度兄》十二首之三),却没料到沦落至“竟挟万言流万里,敢擎孤胆守孤城”(《次原韵报阿度兄》十二首之一)。在这段时间的日记和给友人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历着常人难以体味的复杂心路历程。在1954年末到1955年的日记中,胡风用简短的语句频繁地记载着自己写检查和看材料。1955年3月1日记载有“到北京医院看病。有神经衰弱征象”。23日“休息,完全不能思索”。此后更是开始频繁接受水疗、电疗,身心状况十分不健康。正如他后来在诗中形容的那样“愁思结陷捕狼时,错把陈麻当铁丝”(《一九五六年春某日》三首之三),“深妨党德心都悔,大背文才齿也寒”(《记蠢事》)。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也一再地告诫友人要沉着冷静,“莫谓寻仇头冒险,拼他一煮学吾师”(《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四首之二)。
在漫长的监禁生活里,胡风经历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他先是因绝食抗议被撬掉了门牙,后因长时间监禁患上了严重的痔疮和前列腺炎。身体上的痛苦折磨着胡风,精神上的痛苦则更胜。长时间的审讯使胡风陷入精神的无边苦痛中,甚至患上精神分裂症。然而他还是保持着无法被打倒的战士本色,用绚丽多彩的诗句来展现自己依旧敏锐犀利的思想。他有过愤懑,如“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一九五五年旧历除夕》),“只因错把真言发,锁在囚房着黑衣”(《一九五六年秋某夜》);有过坚守,如“无知气壮心无愧,不悟声诚胆不寒”(《记刑事》),“愚忠不怕迎刀笑,巨犯何妨带铐行”(《次原韵报阿度兄》十二首之一);萌生过退隐之意,如“十年已醒痴情梦,扫地栽花好赋闲”(《鹧鸪天(谪住偏街闹市间)》),“牢房文苑同时别,脱却囚衣换故衣”(《拟出狱志感》二首之一);有过迷茫,如“信仰如何信,煎熬怎么熬”(《大号音·晨歌》五首之二),“无言怀手坐,惆怅望窗空”(《中音篇·骊歌》十首之十);有过悔恨,如“豪情重忆发言时,悔错心如剪剪丝”(《一九五六年冬某日》二首之二)。牛汉曾经问过胡风为何要采取默吟旧体诗词的方式来排遣,胡风道:“我是自言自语道出来的。自己念,自己听,天天如此。”牛汉就想到了他写过的一首叫《猞猁》的小诗,胡风就像被囚禁起来不停地在铁笼子里转圈的猞猁一样,在自言自语,诉说自己的苦难,强迫自己保持清醒。纵然身陷囹圄,精神也可以化作利刃,在有限的环境撕破一条自由的道路出来,这是胡风作为一个启蒙的诗人战士最后的坚守,而旧体诗词则成为胡风超越现实苦难的艺术方式。
胡风在这一时期专注创作旧体诗词的另一个动因为“旧形式的诱惑”。这一名词由刘纳在文章《旧形式的诱惑——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中用来形容郭沫若的旧体诗词创作现象。刘纳在文中指出,“在旧体诗定型化的表达方式和它所对应的情感现象之间,早就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感时书愤、陈古刺今,述怀明志、怀旧思人、送春感秋、抒悲遣愁、说禅慕逸……构成了吸引着历代诗人的情感圈”。在这样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情感圈中,众多文人骚客虽有着不同的个人风格,但却共享着相通的情感内容。在另一篇文章《旧形式的复活——从一个角度谈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刘纳又用“旧形式的诱惑”解释了以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家创作旧体诗词的现象。尽管茅盾不主张青年学旧体诗,一直强调新诗的地位,但他还是承认抗战时期与友人唱和的旧体诗比其他文章更显露了自己的情感。这种心理在那些新旧兼写的文学家那里是相通的,一方面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旧体诗已经是过时了的文学形式,因此旧体诗被边缘化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无法抵御旧形式的诱惑,甚至更能从中寻找到创作的快乐。从刘纳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两个意思,一是旧体诗定性化的情感圈诱惑着新文学家们去创作旧体诗词;二是某些时刻,有着旧学渊源的新文学家们在情感上更能与这种旧形式产生强烈共鸣,这是新文学所不能做到的。这种说法在胡风这里也行得通。
感事书愤、陈古刺今、怀旧思人、抒悲谴愁……胡风在狱中的诗作也没有绕开这些古代诗词题材中的常客。他反复地思索着这场牢狱之灾因何而来,不断地在对亲友和自己表白中确证自己。在向当权者提出质疑的同时,也不忘对党诉说衷心。胡风的这种矛盾心理,正如李遇春在他的著作《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中总结的那样:“虽然在革命文学语境中也强调诗人的‘战士’身份,但这和启蒙文学语境中强调的‘战士’身份有着本质的不同。革命诗人是阶级战士,是政治战士,而启蒙诗人是精神战士,是文化战士。革命的诗人战士以歌颂见长,而启蒙的诗人战士以批评著称。胡风的悲剧在于,他置身于革命文学语境中,却执拗地坚守启蒙文学立场。”在陷入双重身份认同的矛盾中时,胡风所积累的旧学修养在他波动的情绪中悄然生长发芽。旧体诗的情感圈在诱惑着他,使他不自觉地向这种旧形式靠拢,从历代旧体诗人都难以摆脱的情感圈里汲取温暖,追寻精神上的解脱。从他的创作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胡风与有着同种困惑的前辈们抱团取暖:他用鲁迅的《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作了组诗《怀春室杂诗》21首,用鲁迅的《亥年残秋偶作》原韵作了组诗《怀春室感怀》24首,并在许多诗中化用鲁迅的诗句和意象。如《怀春室杂诗》中的七律《一九五六年冬某日》(二首)中第一首的尾联:“极目两间休荷戟,铁窗重锁失戎衣”,就化用了鲁迅的《题〈彷徨〉》。鲁迅诗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显然胡风也感受到了和鲁迅一样的寂寞和彷徨,这种情感的相通诱惑着他以旧体诗的形式来呐喊。像这种情感上的共鸣不仅能从鲁迅那里获得,也能从古人那里寻到同感。在《一九五七年春某日》中,胡风用司马相如和李白的典故来展现自己对真理的坚守:“避贵相如宁卖酒,让才李白不提诗。”有时他又豁然开朗,在东坡诗的豁达之意中把握到了自己难得的幽默感,便步苏东坡原韵并反其意写下了《临江仙》(二首)。还有《〈石头记〉交响曲》,胡风以诗的形式来对《红楼梦》进行研究,并在其中找寻与曹雪芹精神的相通。
除了情感上的互通,旧体诗词特有的语言组成方式也是胡风在这一时期选择大量创作旧体诗词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纸笔,就算偶尔有机会把诗写下来,还会面临被收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形式固定的旧体诗词就成了胡风口头创作的首选。除此之外,旧体诗词还具有新诗没有的功能,那就是社交属性。1966年胡风被转移至四川成都监外执行,与熊子民、聂绀弩、萧军等赠答唱和,写下了不少诗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群”,朱熹《四书集注》注为“和而不流”,这指的就是旧体诗所具有的社会交往功能,人们可以通过唱和赠答来交流思想感情,从而起到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可以说,旧体诗满足了胡风难以用其他形式传达的情感需求。在这一时期,旧体诗的定型化的情感指向与特有的社会交往功能,使其对于坚守着五四文学传统的胡风来说不再是束缚,反而成为抒怀的凭借。
在胡风的人生经历中,少年时代的旧学修习经历是其创作旧体诗词的根本动因;抗战时期,秉持五四文学为中心、不完全否定旧形式的民族形式立场是其小规模创作旧体诗词的直接动因;狱中时期,强烈的情感抒发需要与旧形式的诱惑则是其大规模创作旧体诗词的主要动因。在胡风的思想认知中,新文学家的身份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旧形式的不足,给自己的创作行为贴上不合时宜的标签。在这样复杂动因的影响之下,胡风的旧体诗词创作就呈现出了时间上的间歇、数量上的爆发和创作心理上的否定这三个特点。
注释:
①绿原、牛汉编:《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②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③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④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史》(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
⑤徐酒翔编:《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⑥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报》1904年3月24日。
⑧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0页。
⑨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1页。
⑩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