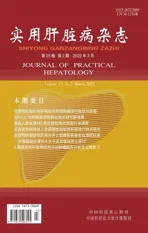NAFLD与肝细胞恶性转化相关研究新进展*
2022-03-21姚登福
周 平,姚登福,姚 敏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1]或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MAFLD)[2]发病率逐年增长,并呈低龄化趋势。真实世界NAFLD发病率可能较高,应引起重视。脂质及其代谢产物的分析鉴定、脂质功能与代谢调控(关键基因/蛋白/酶)、脂质代谢途径及网络调控等方面的研究非常活跃,成为代谢组学重要的分支之一。NAFLD与HCC发生的问题也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NAFLD是非酒精性脂质代谢异常导致肝细胞脂肪堆积、影响肝细胞的正常功能发挥、诱发炎症而引起的最常见的慢性肝病[3]。长期肝细胞脂质堆积,脂质毒性的影响将启动肝细胞恶性转化相关信号通路,引起致癌基因激活和免疫功能失调等一系列的改变,但其中确切的发生机制仍在探究之中。新发现线粒体功能[4]、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ncRNA)、肠道菌群和免疫系统,尤其是T淋巴细胞(T细胞)及其亚群等参与了NAFLD相关的肝细胞恶性转化[5]。
1 多基因参与NAFLD相关肝细胞恶性转化
NAFLD是最常见的肝病,其疾病谱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肝硬化和HCC等。在每千例NASH中,年HCC发病率约为5.29例,已是肝移植最常见的病因。随访NAFLD患者10~20年,肝硬化发生率为0.6%~3%,而NASH群体10~15年肝硬化发生率达15 %~25 %。NAFLD与HCC间存在因果关系。全球约13%~38.2% HCC患者与NASH相关,因为大多HCC发生于肝硬化患者[6, 7]。NASH患者发生HCC风险明显低于HCV感染者。虽染在肝硬化中HCC常见,但HCC也见于非肝硬化的NAFLD/NASH患者,约50%NASH相关HCC并无肝硬化基础,给HCC早期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
分析Omnibus数据库相关基因显示NAFLD、NASH、NAFL和正常对照组间存在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和关键基因。经Gene Ontology (GO)和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 (KEGG)通路富集分析,显示DEGs对NASH具有潜在的功能。以STRING数据库构建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网络(PPI),鉴定出249个DEGs。在NASH与正常组间有514个DEGs和11个关键基因的差异,其中3个基因与HCC患者生存或与NASH进展为HCC密切相关。KEGG富集分析显示了在NAFLD患者肝细胞脂肪变性和炎症反应相关通路[8]。对DEGs进行PPI网络分析,鉴定出MYC、CXCL8、FOS、SOSC、SOCS3、IL6和PTGS2等7个基因为中枢基因;巨噬细胞M2、记忆休眠CD4+T细胞和γδT细胞在NASH免疫微环境中起着重要作用[9]。AKR1B10是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ADPH)依赖的还原酶,属于醛酮还原酶(AKR)1B亚家族,催化醛、某些酮和醌还原,与乙酰辅酶A羧化酶和HSP90α相互作用介导了NAFLD的发生,是NASH进展的关键基因,有希望成为NASH的生物标志物[10]。
2 NAFLD与肝组织免疫细胞异常
病毒性或非病毒性因素均可导致HCC的发生。基础和临床资料证明NASH是HCC重要的病原学因素[11]。肝脏作为重要的免疫器官,含B细胞、树突状细胞(DC)细胞、库普弗细胞(Kupffer cell,KCs)和自然杀伤细胞(NK)等免疫细胞。B细胞可诱导IL-6、TNF-α和IgG2a分泌,活化CD4+T细胞和分化成Th1细胞参与NAFLD的进展[12]。NASH大鼠模型研究发现DC细胞抑制CD8+T细胞活化,减轻纤维化和炎症反应。在高脂饮食诱导的NAFLD模型大鼠,给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s)可有效抑制T细胞、B细胞、巨噬细胞、NK细胞和DC等免疫细胞活化。抑制脾CD4+IFN-γ+和CD4+IL-6+T细胞分化,可减轻体质量、脂肪变性、炎症和肝纤维化,且不影响CD4+IL-17+T细胞的活性。在NASH诱导HCC模型中,耗竭的、异常激活的CD8+程序性死亡-1(PD1)T细胞积聚,增加瘤内活化CD8+T细胞,损伤免疫监视。抗PD1治疗增加NASH进展为HCC发生率,与肝组织CD8+PD1+CXCR6+、TOX+和TNF+T细胞增加有关。NAFLD患者和动物模型均见类似表型和功能特征,CD8+T细胞是通过系列激活完成自身攻击,为免疫介导导致NASH新的发病机制[13]。对晚期HCC患者的荟萃分析发现,因CD8+T细胞活化致免疫监视受损,免疫治疗并未改善NAFLD相关HCC患者的疗效,提示NASH诱导的HCC患者CD8+T细胞激活损伤了免疫监视功能,为相关免疫治疗HCC患者提出了警示[14,15]。
在NAFLD动物模型和NAFLD患者的研究显示慢性肝病进展为HCC患者,选择性CD4+T细胞和CD8+T细胞功能发生了变化[16,17]。在高脂饮食(HFD)诱导的NAFLD鼠模型,早期CD8+T细胞无变化,8周时CD44+CD8+T细胞明显下降,第10周后持续升高,CD8+T细胞参与促进NASH发展,与NK T细胞共同作用促进HCC 发展[18,19]。在NAFLD患者,CD4+T细胞增加,而CD8+T细胞则降低。NASH患者Th1上调、Treg减少,Th17/Treg细胞比值降低。NAFLD患者肝组织Th17细胞分泌IL-17参与疾病进展,加重肝脏炎症和肝损伤,被认为是NAFLD向NASH进展的标志[20,21]。在NAFLD或NAFLD相关HCC患者,Treg减少,提示Treg参与了NAFLD向HCC的进展。
3 线粒体损伤加重NAFLD进展
肝组织脂肪堆积是NAFLD的显著特征。高热量饮食和饱和脂肪酸摄入增加脂肪积聚,损伤氧化应激和亚硝化应激作用[22],出现线粒体DNA(mtDNA)损伤,肝细胞凋亡/坏死增加、易导致NASH纤维化和肝硬化,甚至是HCC。传统的NAFLD发病机制包括脂质过氧化、细胞因子过表达、脂代谢异常、铁超载、免疫和药物、生活习惯等,其核心是胰岛素抵抗致脂肪积聚,三酰甘油堆积形成脂肪肝。氧化应激和过氧化加剧肝损伤进展,致肝细胞坏死、内质网应激、肠源性内毒素增加、脂肪因子失衡、肝星状细胞激活等,致使细胞外基质沉积,肝纤维化形成,累及肝实质,肝小叶重构发展至肝硬化,持续炎症激活癌基因,直接进展到肝细胞恶性转化,其机制较为复杂[23]。
在新发现的环磷酸鸟-腺苷合成酶/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cGAS/STING)信号通路中,作为DNA探测器的cGAS可检测到溢出的mtDNA,激活STING通路,有效刺激IFN-I等炎性因子表达,加重肝损伤[24]。非高血糖代谢综合征、多种抗原形成和免疫失调等病理学过程也可能参与了发病[25,26]。位于线粒体外膜肉碱棕榈酰转移酶-1(CPT-1)控制脂肪酸进入线粒体[27],CPT-1上调增加线粒体活性氧(mtROS),促进细胞凋亡。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受体α介导CPT活化,药物perhexiline阻断CPT-1,可减少肝组织CD4+T细胞凋亡,从而抑制肝细胞恶性转化[28]。另外,当脂质积聚时,线粒体内膜CPT-II失活,脂肪β-氧化受阻,能促进细胞恶性转化[29]。以高c18:2或蛋氨酸胆碱缺乏饮食(MCD)喂养制备小鼠模型,能重现CPT异常表达、线粒体内亚油酸(c18:2)高度增加,提示线粒体DNA损伤和CPT活性直接影响脂质氧化,在脂肪积聚状态下肝细胞发生恶性转化,也为NAFLD相关HCC的防治提供了新思考[30]。
4 肠道菌群与NAFLD相关HCC
肝脏与肠道密切相连,门静脉、肝动脉和胆管组成重要的代谢枢纽,涉及消化、解毒和清除菌群产物等功能。沿血管排列的肝细胞、内皮细胞和免疫细胞分布和功能相关联[31]。单细胞研究发现共生菌群调控Kupffer细胞,CXCL9趋化因子不仅调控巨噬细胞的分布,且具有宿主防御功能。肠-肝轴涉及多个系统,即将初级胆汁酸包括IgA送入肠腔。菌群相关分子模式(microbial-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MAMPS)和次级胆碱被输送至门静脉, 将食物代谢物、游离脂肪酸、乙醇和胆碱代谢物等,经毛细管输送至肠/体循环。肠-肝双向连接,调控肠道菌群、肠上皮、血管屏障和脂代谢过程[32]。代谢组学显示NAFLD相关肝硬化患者肠道菌群变化诱发了肝细胞恶性转化。在NAFLD相关HCC患者,菌群提取物可诱发T细胞免疫抑制表型,调节性T细胞增加和CD8+T细胞衰减,表明肠道菌群具有独特的微生物/代谢组学特征,并可调节宿主的免疫反应。
肠源性产物可经门静脉进入肝脏,肠道菌群为NAFLD的隐藏“器官”,在内环境平衡或NAFLD发病方面发挥作用[31]。肠道生态失调系益生菌耗尽、病原菌增加、短链脂肪酸减少致肠上皮细胞屏障通透性增加、胆汁酸合成改变、肝脏次级胆汁酸滞留、促胆碱代谢形成氧化三甲胺,促进NAFLD进展。炎性细胞因子(TNF-α、IL-8和IL-1)增加,触发Toll样受体(TLR)-4/9激活,介导由TNF-α和前列腺素E2引起的炎症,脂质堆积促进细胞凋亡,激活干细胞产生纤维化成分,促进NAFLD相关性肝硬化和肝细胞恶性转化的发生。益生菌有抗HBV和HCV活性,有益于减肥和防范NAFLD/ NASH风险,可上调抑癌基因和下调癌基因表达,降解膳食代谢物,减轻肝细胞恶性转化的风险。
5 ncRNA调控NAFLD
在NAFLD相关HCC,涉及抑癌基因失活或癌基因激活ncRNA过表达,且与HBV、HCV和脂肪堆积等因素相关。与DNA、RNA或蛋白相互作用的ncRNA包括miRNA、小干扰RNA(siRNA)、小核RNA(snRNA)、长链ncRNA (lncRNA)和环状RNA (circRNA)等。脂肪细胞外囊泡外泌体携带脂质、蛋白、核糖核酸和ncRNA等,传递生物学信息,维持胞间通讯,调节脂代谢。HCC细胞、免疫细胞和肝细胞分泌外泌体,在胞间转运DNA、mRNA、lncRNA、miRNA和蛋白等方面参与肝细胞的恶性转化,相关调控机制仍是目前研究的新领域,高通量测序发现基因转录后ncRNA起关键的调控作用。
临床和基础实验发现ncRNA具有调控作用。NAFLD患者血mir-29a低表达,其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AUC)、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68、60.9%和82.4%,而mir-122高表达,其AUC、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83、75.0%和82.4%。在高脂(HF)或低脂(LF)喂养的C57Bl/6j小鼠,血清胆固醇、LDL和HDL、TG和ALT升高,肝肿大,肝组织脂肪变性、炎性细胞浸润和肝纤维化,约20% HF小鼠见癌变的特征。癌组织15种miRNAs差异表达,含NAFLD相关肝病未见的mir-340-5p、mir-484、mir-574-3p和mir-720异常。在肝损伤早期,mir-125a-5p下调,而mir-182上调。外泌体miR-122、miR-192、miR-27a-3p和miR-27b-3p异常。miR-122致胆固醇和脂肪酸升高,促进肝纤维化,占肝组织miRNA的70%以上的miR-122是NAFLD或相关HCC诊断的有用标志物。干预mir-223可下调CXCL10表达,抑制脂肪变性,可能成为治疗NASH的靶点。
lncRNA是NAFLD重要的调控分子,比较NAFLD模型lncRNA和mRNA显示,89个mRNA水平上调,177个下调,291个lncRNA下调,涉及花生四烯酸、昼夜节律、亚油酸、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PPAR)信号途径、鞘脂、类固醇合成、色氨酸和酪氨酸代谢等。在NAFLD相关9个mRNA和8个lncRNA (FLRL)中,FLRL1、FLRL6和FLRL2分别调控昼夜节律,定位周期生物钟3(PER3)、PER2和芳香烃受体核转运(ARNTL),而FLRL8、FLRL3和FLRL7分别与脂肪酸结合蛋白5、脂蛋白脂酶和脂肪酸去饱和酶2结合发挥作用,干扰FLRL2后ARNTL下调,推测可能与NAFLD发病机制有关。闭环结构的环状RNA高度稳定,而circ_0046366和circ_0046367缺失是NAFLD的特征。circ_0067934促进HCC侵袭转移,circMTO1抑制HCC进展。环状RNA与NAFLD分子机制仍在探讨之中,期待高通量生物信息学分析能够开发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6 展望
NAFLD(或MAFLD)发病率逐年增长,已是除HBV或HCV感染以外诱发HCC的主要致病因素,引起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广泛关注。随着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等系统组学的兴起,伴随脂质(脂肪酸、甘油脂、甘油磷脂、鞘脂、固醇脂、孕烯醇酮脂、糖脂和多聚乙烯等)及其代谢产物、功能与代谢关键基因/蛋白/酶调控、代谢途径和网络信息等分析技术的进步,发现肝组织脂质堆积、线粒体损伤、遗传不稳定、脂代谢受损、氧化应激增加、炎症与凋亡、纤维化和相关通路激活等协同作用,促进了NAFLD/NASH相关的肝细胞恶性转化。然而,尚无法确定哪些NAFLD患者易发生HCC。筛选与发现监测NASH向HCC转变特异性标志物仍在探索中。同时,免疫调节与NAFLD的关系也逐渐被重视,探讨其发病机制,单独或联合抗纤维化、抗糖尿病、抗炎、抗生素/益生菌和降脂等综合措施都有益于NAFLD/NASH的治疗。然而,早期有效干预、预防或监测肝细胞恶性转化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