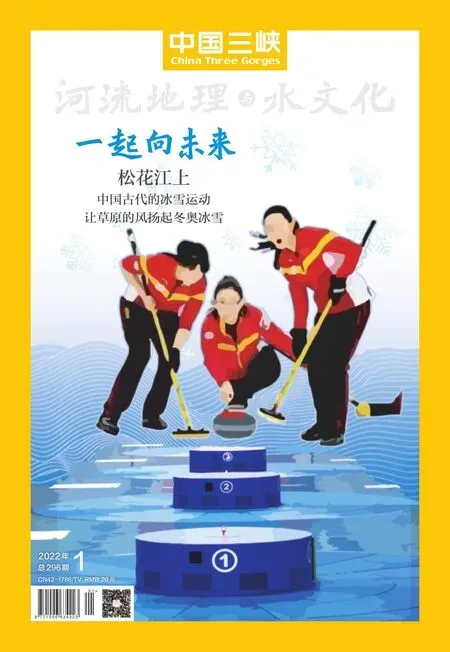松花江的冬与春
2022-03-19桑克编辑王芳丽
◎ 文 | 桑克 编辑 | 王芳丽

冬
每到冬天,松花江哈尔滨段就会如期结冰。
人们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因为秋天已经提前以其后半截之凄凉对他们进行过“降调培训”(秋天前半截之绚烂早已化身为美的背影)。当年冯至先生就领教过这种凄凉的厉害,可能是因为他孤身一人生活在此地,内心也不怎么喜欢这里的缘故吧,尽管他编辑的民刊叫作《松花江》,但是至今没有多少人见过这本民刊的真实容貌。
某年中秋夜,冯至先生逃离了一个当地热情而庸俗的宴会现场,独自来到松花江边。他在《北游及其他》里追忆过当时的情景:“我坐在一只小艇上,它把我载到了江心。”一个人没有玩伴,在浩荡的松花江上漂浮,恐怕也只有苦闷而没有荡舟的欢喜吧。再美的秋江也被内在与外在的凄凉淹没了。冯至先生接着讲述,“我望着宁静的江水,拊胸自问:我生命的火焰可曾有几次烧焚?……低着头望那静默的江水,江水是那样的阴沉,阴沉……”冯至先生的心情恶劣至极,你完全可以想象在寒冷的冬天里他又能拥有何种心绪。而朱自清先生泛舟松花江的心情与冯至先生完全不同,他觉得这里“比北平舒服多了”。
景色本身并无变化,只是由于人心的差异而导致景色的差异。同一个松花江,同一个哈尔滨,因为不同人的不同联想而产生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体验,更何况冬天的松花江看起来是那么特殊呢。有的人会为江岸冰挂的璀璨而流连忘返,有的人则为冰天雪地的冷酷绝情而恐惧不安。你跺着冻麻的脚趾,感受着风针或者风刀的凌厉,一针一针,一刀一刀,针针扎进你的肌肉,刀刀刺入你的筋骨。这些其实都是东北的日常,再特殊也都习惯了。
哈尔滨的冬天有多长呢?如果按照供热起止日期,也就是从当年十月二十日开始至次年四月二十日结束来计算,拢共一百八十一天,将近半年之久。现在因为地球气候变化,暖冬较多,所以实际意义上的冬天可能会少于一百八十一天。那么松花江哈尔滨段的结冰期有多长呢?整体上会短于供热起止日期,但是特殊的时候也是有的。
2020 年11 月初,松花江哈尔滨段开始局部结冰。一块一块薄薄的冰皮,像面膜一样贴在水面上。如果不是阳光反射,你可能根本不会发现它们。有趣的是,那些在江面上逗留的红嘴鸥们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有的站在稍微厚一点儿的冰皮上发呆,有的则在空中盘旋寻找着落足之地。那些不太适应新跑道新材质的红嘴鸥,在降落的瞬间会被光滑的冰皮弄得失去平衡,身子趔趄着,倾斜起来。
又过了两天,哈尔滨下起雪来,满江的水和冰都笼罩在迷蒙的雪雾之中,人们开始逐步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东北人的猫冬大戏正式启幕了。又过了十几天,相关部门开始封江。千余米宽的松花江上空空荡荡,渡船和游船全都被集中起来,停靠在江南江北的各个码头上。江南江北来来往往的人就只能靠江桥的帮助了。江桥很多,最有名的是老江桥。曹禺先生在《雷雨》中谴责周朴园修建哈尔滨江桥时所犯下的罪行,似乎在说周朴园是江桥的修建者——这当然只是一种虚构。这座老江桥全长1027.2 米,全金属构造,1901 年建成,正式名称是“滨洲线松花江铁路大桥”。这座江桥现在已停止运营,属于中东铁路公园的一部分。与之并列的一座白色大桥,也就是正在运营的高铁江桥。站在江边,望着一黑一白的江桥,历史感会不由自主地从心底冒出来,本来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也因为两座江桥的对比而有了实际的见证。

松花江边满树“银花” 摄影/郭俊峰
封江之后的松花江并没有完全冻成冰面,仍旧存在着流冰现象。大块大块的碎冰和水搅和在一起,或优哉游哉,或“群情激愤”,按照各自的节奏移动着向下游奔去。然而仅仅过了三天,随着大幅度降温,老天爷把松花江彻底冻成了一个大冰坨子。只是冰层有的地方厚点儿,有的地方薄点儿。比较有意思的是,去年江面结的冰并不是平缓的,不少地方都还保持着流冰的激烈状态,犬牙交错,虽然不如兴凯湖冰岸之恐怖,但是和往年平缓的状态相比还是挺惊悚的。
这时候的江面是不能走人的,那些胆子贼大的人从冰面过江其实全都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因为这时的江面只是看起来冻上了,其实冰层非常薄,可能承受不了人体的重量。我从报上得知,那些年的初冬时分,因为冒险过江而造成生命殒殁的事故并不鲜见。冬天不像夏天,人掉进江里可以自救或者被救,这时一旦掉进冰窟窿里,麻烦可就大了。落江的人如果移动到距离冰窟窿较远的地方,自救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更别提被救了。不同的年景,江面冰层的厚度也不同,有的时候能走卡车,但是暖冬的时候许多东西都走不了。我听说过不止一次车辆掉进松花江冰窟窿里的悲剧,无论是中游的哈尔滨还是下游的佳木斯。我自己则是一个比较听话的人,冬天如果需要步行过江,我一定会沿着两边由标志旗规划的安全路线走。至于如何避免走清沟(没有结冰的狭长水沟),一两句话还真讲不清楚,我只能说,如果你是外地人,如果你想冬天步行过江,最好还是让当地人引领着或者是与大批当地人一起走。

哈尔滨松花江上的流冰。 摄影/郭俊峰
进入十二月,各种与冬天娱乐相关的准备工作也就开始了。工人们剖开厚实的江面,用电锯切割着一长条一长条的巨大冰块,为冰建筑或者冰雕采集基本材料。人们嘴里哈出的热气碰到嘴外面的低温,就会变成一股漂亮的白色蒸汽。蒸汽也会把眉毛、头发或者胡须染白。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就此相互打趣,时间久了也就无所谓了。松花江边,修建中的雪雕和冰雕各式各样;松花江上,尤其是防洪纪念塔一带,各种娱乐设施渐渐搭建起来。几十米长的冰滑梯,人们从高高的起点滑下来,享受着速度的快感和跌跌撞撞的滑稽感。而围起布幔的小冰场,里面滑冰的,打陀螺的,划冰车的,各自都有各自的乐趣。电影《白日焰火》里王学兵滑野冰的场面就发生在类似的地方。电影里那种凄凉的氛围,固然与剧情有关,也可能与黄昏或者即将到来的寒夜有关。小孩子们之所以能够超越冬天,大多与冬天的游戏有关。我的冬天记忆除了冷,就是做陀螺。重点是绘制陀螺截面的图案,我每天都在琢磨,怎么画才能使旋转的画面更好看。堆雪人的快乐感比较一般,更好玩的是在厚厚的雪层下面挖地道,地道里不仅冰面是厚的,而且内里挖了地道的雪层也厚得能够承载人。
到了十二月下旬和次年一月,哈尔滨气温变得极其寒冷,零下三十多度是很寻常的。松花江由于身处空阔之地,气温比城区还要低。这时,大多数哈尔滨人喜欢坐在窗边,端着一杯热咖啡欣赏松花江。这时的松花江上仍有一些活动的人,其中最奇怪的并不是站在寒风中吃马迭尔冰棍的人,而是那些冬泳爱好者。虽然冬泳池的水温比气温略高,但是冬泳爱好者出水的瞬间,身体接受的却是难以忍受的冷。我很佩服这些冬泳者,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勇气,也因为他们正在凭借一己之力捍卫着正在消逝的东北传统。也许只有这种倔劲儿才适合寒地吧。

哈尔滨市,春暖冰融,鹭鸟、鹊鸭等候鸟感知春信,在冰面停留,在水面觅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春
每年三月中旬,松花江哈尔滨段的冰层开始融化。在此之前上游的江冰早已融化。滔滔不绝的松花江水,从稍暖的长白山北麓沿着西南、东北方向的河床向着微寒的松嫩平原昼夜奔涌着。当喧嚣的活水抵达哈尔滨的时候,就会遭遇死冰堡垒和低温天气的阻拦,因为松花江哈尔滨段还没解冻呢。但是随着气温逐渐上升,这里的松花江也就不得不加入解冻的行列之中。只是解冻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时间与机会。但是不管怎么说,死冰堡垒的防守阵线开始变得并不牢固了,而一波一波上游活水的冲刷也为死冰的加速融化提供着更多的额外支持。渐渐地,死冰堡垒的防守阵线全面松弛,死冰也渐渐变成了活冰。几乎在一夜之间,曾经刻板严肃的大一统江冰帝国就瓦解成不计其数彼此独立的诸侯城邦。松花江冰面破碎得如同百衲衣,而冰块浮沉其中则像几叶扁舟。如果赶上冰面融化激烈,冰块的诸侯城邦就会发生“战争”,彼此凶猛撞击,重叠缠斗,发出低沉而雄壮的裂帛之声,由此就会形成气势澎湃的开江景观。当地人称之为“武开江”,反之就是“文开江”。虽然这让不少人兴奋地站在萧瑟的江堤上摄影留念,但是更让人牵肠挂肚的主旋律却只有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春天,春天来了。
然而哈尔滨的春天几乎是全世界最短的春天。
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张,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短的时候,春天仅仅过了一个礼拜,就嗖的一声飞进炎热的夏天;而多的时候,春天也不会多到一个月的。
松花江哈尔滨段的春天期限一般在三月下旬与四月中下旬之间。
这里春天的主要特征就是冰雪融化,不像江南的春天,到处开花散叶、郁郁葱葱。北地的春天也就是脱掉厚厚的棉袄棉裤或者羽绒服,除此以外乏善可陈。如果非要说说这里的春天,仔细甄别其中的细节,恐怕也就是三个基本要点——早春冰雪融化、仲春地上长草、暮春开些小花,而且还没等春花凋敝,夏天就莽撞地闯进来了。但是人们才不管这么多,哈尔滨人尤其不管这么多。憋了一冬天的人,内心对自由的需要几近于疯狂,几乎每个人都想长出一双翅膀到处翱翔。有的时髦姑娘甚至刚脱了羽绒服,就露出小腿,把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或者中央大街当作秀场,喝酒的喝酒,撒欢的撒欢,追逐着乍暖还寒的春风。不释放一下,怎么对得起松花江解冻的内涵呢?怎么对得起生命这一珍贵的恩赐呢?冬天就是一根弹簧,压到春天的谷底也就反弹了。这一弹就把人弹到了天上。
春天里的人是最快乐的。但是冰雪融化之初,让人烦乱的事情也不少,比如说泥泞。但是它并不是荀红军先生翻译的“轰响的泥泞”,而是力冈先生和吴笛先生翻译的“噗噜噗噜响的泥水”,前者虽然更有气势,更有统治感与美感,但后者才是事实。而人工修建的江堤由于大多铺着水泥与步道板的缘故,并不存在严重的泥泞问题,尤其是松花江哈尔滨段江南部分的主要江堤,因经济眷顾而备受优待。当地人把这里称为“江沿儿”(“沿”字在哈尔滨方言里读作四声)。钱单士厘女士在1903 年《癸卯旅行记》里记载:“三局设于江沿附近。江沿者,沿松花江岸,距秦家冈三数里,今市廛集处,俄警察局暂设于此。”对于历史短暂的哈尔滨来说,“江沿儿”的历史算是其中比较长的,而且它的实际长度也比较长(虽然比起万古长夜还是太短了),走半天肯定走不完。其中最有名的“江沿儿”就是斯大林公园这一段。
斯大林公园是中东铁路留下来的,它的整体设计与施工都是园林典范。江边原来雕工精致的栏杆,后来被缺乏美感的但更实用的水泥和其他材料取代,这让怀旧的人唏嘘感慨不已。其实这个事儿也没有多旧,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事情呢。江边的雕塑全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风格,哈尔滨人也都很熟悉了,并没有违和感,正如防洪纪念塔周边的英雄雕塑,黑头发单眼皮的是哈尔滨人,高鼻梁深眼窝的也是哈尔滨人。而江边那些精美的老房子,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对江水讲讲自己听过的老故事,讲讲对面著名的太阳岛吧。
江堤沿途十几公里的风景之美是说不完的,更不必说由于草刚刚长出绿芽儿而带来的喜悦感。当哈尔滨人在社交平台晒这些融雪中的草芽儿的时候,距离上海人晒绿萼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还是说说松花江边的树和花吧——这些也许更像春天的正式代表。
起初,大多数树木只有树皮刚刚返青,个别树木则长出一点儿嫩绿色的叶子,但是这些足以让人欢喜不已。松花江边的树,近处栽植榆柳,稍远则以杨树居多。杨树先长银白的龅牙,后长褐红的穗子。一条条穗子落在地上,毛毛虫似的,虽然给人些许恶感,但因其沾了早春的光,人们并不讨厌。暮春和初夏的杨花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人们对杨花讨厌得要死,尽管它们在诗里“点点是离人泪”。榆树先是结了青绿的榆钱(从前穷人家和富人家都会吃的,现在谁也不吃,不知为什么它始终没有获得婆婆丁之类野菜的市场厚待),一嘟噜一嘟噜的,而后变色发黄,被暖暖的春风一吹,小小的铜钿一样的榆钱就落满松花江面,与水相互搅和着渐行渐远。

松花江带给市民无限的乐趣 摄影/郭俊峰
花是春天的皇帝,这是谁也撼不动的,虽然这种比喻从里到外都显得俗气。最开始是黄色的迎春花和连翘,可笑的是人们每到这时候都要争论一下什么是迎春花,什么是连翘,好像永远分不清它们谁是谁。至于杏花、桃红和榆叶梅,更是浓墨重彩,遮云蔽日。松花江边,桃红占着优势,但在整个哈尔滨,杏花才是真正的大佬,人们晒合影大多以杏花为背景。紫丁香是哈尔滨市花,过去满城都是,根本没杏花的话事权。不少人还记得青年宫当年的紫丁香盛景,现在它们只能出现在记忆之中。而与松花江垂直的兆麟街,过去则以栽植精美的紫丁香景观而闻名,其香气之粘稠,思之如在梦中。暴马丁香(白丁香/暴马子)虽然来得晚,但是花期长,它大概是潜入夏天领地的少数花木之一,但是爆裂的哈尔滨之夏能把它当盘菜吗?
春天只能留在春天里,虽然随后而来的哈尔滨之夏是最美的季节。那时异常凉爽,松花江边的纳凉闲人比过江鲫鱼还多,唱歌剧的,拉小提琴的,玩滑板的,玩帆船的……无论是九站还是航务局,在生机勃勃的市井百态之中活脱脱地上演着一出出人间喜剧,只是明显少了初春的小心与微喜。端午踏青是哈尔滨人的狂欢节,从深夜到凌晨,一百八十多万人沿着松花江两岸疾走如风,举着一束束正在散发刺激性香气的艾蒿,好像举着一支支“秉烛夜游”的蜡烛。然而不管松花江的夏天多美,让人想念的却始终是冬春交接的那个瞬间,冰雪消融的那个动人心魄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