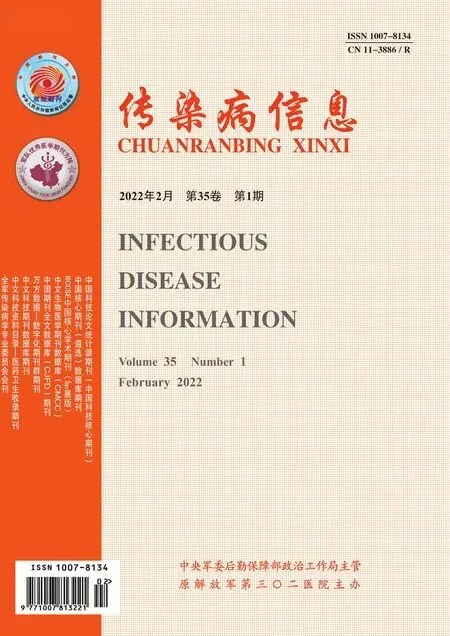蠕虫感染与肿瘤发生关系的研究进展
2022-03-19吴银娟殷颖璇潘筱雯何咏欣高若兮李学荣
吴银娟,何 晴,殷颖璇,潘筱雯,何咏欣,高若兮,李学荣
寄生虫病目前仍然是世界上具有严重破坏性且十分普遍的传染病,每年造成数百万人发病和死亡[1],其中以蠕虫感染最为常见,全球约1/6的人口感染了蠕虫[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群寄生虫感染率虽大幅降低,但重点寄生虫感染人数仍居高不下。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显示我国重点寄生虫感染人数为3859万,且大部分为蠕虫感染[3]。蠕虫感染可以引起人体营养不良,组织器官机械性损伤,并通过分泌毒性和抗原性物质对人体造成损害。调查显示,约17%肿瘤患者的发生可归因于慢性感染,感染被认为是肿瘤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4]。国际癌症研究所分类为第I类致癌物的11种感染性病原体中,属于蠕虫的有3种,包括麝猫后睾吸虫、华支睾吸虫及埃及血吸虫[5]。麝猫后睾吸虫和华支睾吸虫感染可导致胆管癌的发生,埃及血吸虫感染可导致膀胱癌的发生[6]。但是也有部分寄生蠕虫的感染可能具有抗肿瘤效应[7]。
1 吸虫感染与肿瘤
1.1 后睾科吸虫感染与胆管癌 后睾科吸虫感染是诱导胆管癌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后睾科吸虫病的流行地区。与胆管癌发生密切相关的后睾科吸虫主要包括支睾属的华支睾吸虫和后睾属的麝猫后睾吸虫[8]。人患后睾科吸虫病主要是通过生食或半生食含活囊蚴的淡水鱼引起的。在人体内,后睾科吸虫成虫可阻塞胆管导致胆汁瘀滞和胆汁压力升高,并通过胆管反复出现的溃疡和强烈炎症,以及胆管周围纤维化和DNA损伤来共同促进胆管癌的发生[9]。
后睾科吸虫感染人体后,成虫在肝胆管所产生的分泌排泄产物(excretory and secretory product, ESP)不仅能诱导机体发生免疫介导的炎症反应,而且在后睾科吸虫感染诱导的胆管癌癌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0]。
麝猫后睾吸虫分泌排泄产物(ESP of Opisthorchis viverrini, OvESP)是一种与肿瘤密切相关的复杂蛋白混合物,包括如颗粒蛋白、硫氧还蛋白及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等。它能被正常的胆管细胞内吞并诱导正常的胆管细胞与胆管癌细胞的增殖。同时OvESP还通过上调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 TLR4)、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 NF-κB)以及IL-6和IL-8的表达与分泌诱导炎症的级联反应。当NF-κB 活化后,通过产生过量的一氧化氮合酶与环氧化酶-2诱导胆管癌的发生[11]。已有研究证实,麝猫后睾吸虫颗粒蛋白在麝猫后睾吸虫感染诱导胆管癌发生的过程中可能起着较重要的作用[12]。华支睾吸虫分泌排泄产物(ESP of Clonorchis sinensis,CsESP)通过上调多种致癌基因以及细胞增殖相关microRNA的表达,并抑制凋亡相关基因以及抑癌基因microRNA的表达,在华支睾吸虫感染所致的胆管癌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而CsESP中也有一种生长因子类的颗粒蛋白能在体外诱导胆管癌细胞的增殖与转移[14]。以上这些致病因素通过联合作用引起胆管上皮增生和腺瘤样改变,并最终可能导致胆管癌的发生。
此外,感染麝猫后睾吸虫的仓鼠胆道与粪便中的微生物群与未感染组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感染的宿主胆管中独特微生物群影响着宿主组织微环境并可能最终导致胆管癌的发生[15]。另外,在慢性感染麝猫后睾吸虫的仓鼠肝脏中还发现了幽门螺杆菌这种I类致癌物。
1.2 血吸虫感染与肿瘤
1.2.1 埃及血吸虫感染与膀胱癌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埃及血吸虫长期慢性感染与膀胱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6]。膀胱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肿瘤,主要包括尿路上皮癌和鳞状细胞癌,前者占全部病例的90%[17]。埃及血吸虫感染会增加膀胱癌发病率,在埃及血吸虫流行地区,高达65%的膀胱癌患者同时患有泌尿生殖系统血吸虫病[18]。埃及血吸虫致膀胱癌的发病机制可能与虫卵引起的组织损伤、慢性炎症、氧化应激以及虫卵分泌物与宿主的相互作用有关[19]。
有研究发现,向小鼠膀胱壁注射埃及血吸虫虫卵会导致尿路上皮非典型增生,这是一种潜在的癌前病变[20]。埃及血吸虫成虫与虫卵的代谢物可刺激细胞增殖,干扰细胞凋亡,增加氧化应激,并对尿路上皮细胞产生遗传毒性效应。如来源于虫体的雌激素代谢物、鸟嘌呤衍生物的氧化产物、β-葡萄糖醛酸酶和环氧化酶-2等是潜在的膀胱致癌物[21],可能导致原癌基因如P53和/或抑癌基因发生突变,从而促进尿路上皮癌变[22]。已有研究证实,同时感染埃及血吸虫和细菌会增加患膀胱癌的风险,这可能与暴露于细菌产生的致癌物如N-亚硝基化合物有关[23]。由于埃及血吸虫与膀胱癌发生的密切联系,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埃及血吸虫列为I类生物致癌物[16]。
1.2.2 日本血吸虫感染与结直肠癌 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和病理学证据表明,日本血吸虫慢性感染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有关,尤其是结肠癌和肝癌[24]。研究表明,慢性日本血吸虫病患者患结肠癌的风险是非日本血吸虫感染者的3倍[25]。因此,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其列为IIB类生物致癌物,即可能对人类致癌[16,25]。日本血吸虫病的流行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与病死率之间有明显的地理相关性,感染日本血吸虫的患者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增加,并且与感染持续时间呈正相关[26]。在结肠癌患者肿瘤周围的肌层和邻近黏膜的黏膜下组织发现有大量日本血吸虫虫卵沉积,引起持续的慢性炎症反应,并进一步导致肠壁纤维化和假性息肉形成,这些变化被认为是血吸虫性结肠疾病的一种癌前病变。日本血吸虫诱发癌变可能与慢性炎症、血吸虫毒素、免疫调节、细菌共感染等有关,其中慢性炎症起着关键作用。
日本血吸虫可溶性虫卵抗原(soluble egg antigen, SEA)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可以激活巨噬细胞等炎症细胞,产生潜在的遗传毒性介质,如活性氧、活性氮以及促炎细胞因子,导致DNA损伤、突变以及癌基因和抑癌基因的失调[27]。研究结果表明,SEA通过激活JAK/STAT3信号通路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淋巴器官和肿瘤微环境中的积累,引起T细胞免疫应答失调[28]。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还能发挥非免疫功能,包括促进血管生成、肿瘤侵袭和转移,从而有利于结直肠癌进展[29]。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日本血吸虫卵源性的SjE16.7蛋白可能诱导结直肠癌进展,其与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结合,导致NF-κB信号通路激活、活性氧以及促炎细胞因子IL-6和TNF-α的产生增加,有助于肿瘤发生环境的稳定[30]。
1.2.3 曼氏血吸虫感染与肿瘤 曼氏血吸虫的生活史与日本血吸虫相似,流行病学资料表明曼氏血吸虫感染与肝癌、结肠癌、前列腺癌、膀胱癌等多种肿瘤的发生有关。此外,曼氏血吸虫性结肠炎与多中心性结直肠癌早期发病的关系也有报道[31],但目前仍然缺少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曼氏血吸虫感染与其诱导肿瘤发生的关系。在动物实验中发现,曼氏血吸虫感染肝癌小鼠能够加速肿瘤的发展。此外,与单独感染HCV相比,合并感染HCV和曼氏血吸虫的患者表现出明显加速和更严重的肝纤维化,并且有更高的肝癌发生风险[32]。曼氏血吸虫的致癌机制尚不明确,与日本血吸虫和埃及血吸虫相似,可能与慢性炎症、氧化应激、组织损伤和免疫失调等因素有关。
2 绦虫感染与肿瘤
由猪带绦虫幼虫感染引起的脑囊尾蚴病(neurocysticercosis, NCC)是常见的神经系统寄生虫病。有研究指出NCC患者在治疗前外周血淋巴细胞中1、2和4号染色体出现了高频率的损伤,而这种外周血淋巴细胞的遗传不稳定性可导致淋巴和造血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生风险升高[33]。此外,体外实验研究显示,单独使用猪带绦虫钙网蛋白或与5-氟尿嘧啶联合使用,通过与清除受体的相互作用可抑制乳腺癌和卵巢癌细胞株的生长[34]。
另一种与肿瘤发生密切相关的是由细粒棘球绦虫感染引起的细粒棘球蚴病,又名包虫病,其对于肿瘤的发生可能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土耳其的一项大型回顾性研究报告称,包虫病患者的癌症患病率显著降低。与此相反,在塞浦路斯进行的一项初步回顾性研究表明,包虫病可能会增加患者的癌症发生风险。更多的研究结果则支持细粒棘球绦虫感染能通过调节宿主免疫应答抑制肿瘤的生长。此外,由细粒棘球绦虫分泌的EgKI-1蛋白可能具有直接的抗癌作用[35]。
短膜壳绦虫能够把其肿瘤细胞传染给人,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寄生虫会把恶性肿瘤传染给人类。研究人员在1例感染HIV-1患者的淋巴结和肺活检标本中观察到癌细胞,然而这些癌细胞却不是人类细胞,而是由短膜壳绦虫传染给患者的,因为在这些癌细胞中检测出了短膜壳绦虫的遗传物质[36]。
3 线虫感染与肿瘤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粪类圆线虫感染与肿瘤发病率的增加有关。粪类圆线虫是一种土源性肠道线虫,可引起粪类圆线虫病。粪类圆线虫感染具有反复自身感染的特点,容易导致高度感染综合征、持续感染和死亡的发生。已证实粪类圆线虫的感染在一定程度上与Ⅰ型人类嗜T细胞病毒(human T-cell lymphotropic virus-1, HTLV-1)感染有关[37]。HTLV-1通过诱导感染T细胞的生长、转化、基因转录和遗传不稳定性导致成人T细胞白血病/淋巴瘤[38],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I类致癌物。研究发现,伴有粪类圆线虫感染的HTLV-1携带者前病毒载量显著高于未感染粪类圆线虫的HTLV-1阳性个体,提示粪类圆线虫可能刺激HTLV-1的复制[38]。此外,粪类圆线虫还可通过激活IL-2/IL-2R通路诱导HTLV-1感染的T细胞的多克隆扩增[39]。这些发现表明,粪类圆线虫是HTLV-1诱导的淋巴样癌发生的辅助因子。此外,也有研究报道粪类圆线虫感染与胃腺癌和结直肠癌的发生有关[40]。
某些线虫在感染机体后还可发挥抗肿瘤作用。旋毛虫的排泄分泌产物和虫体抗原中有多种与抗肿瘤作用相关的蛋白质,如原肌球蛋白、小凹蛋白1、翻译控制肿瘤蛋白和热休克蛋白等,这些抗肿瘤活性物质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41]。利用旋毛虫感染乳腺癌、肝癌、肺癌等荷瘤小鼠模型时发现,小鼠肿瘤的质量和体积明显减小,并且CD3+T细胞和CD4+/CD8+T细胞水平均升高,诱导宿主产生了抗肿瘤免疫反应[42-44]。在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中,旋毛虫感染可以通过减少趋化因子CXCL9、CXCL10的产生,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和转移[45]。
4 蠕虫与宿主的相互作用
蠕虫与宿主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代谢物可能有致癌作用。蠕虫的代谢物主要包括氧甾醇、儿茶酚雌激素等,以上物质都可能使宿主细胞DNA脱嘌呤,从而导致DNA的错误修复以及癌变驱动基因的突变[5]。DNA的损伤和基因突变的积累最终可能会导致癌变的发生。蠕虫导致癌变的基因突变情况可能与其他原因导致的突变情况不同。如后睾科吸虫导致的胆管癌与非后睾科吸虫导致的胆管癌相比,表现出了更高的体细胞突变率[46]。由后睾科吸虫导致的胆管癌患者的ERBB2基因有明显的扩增,而非后睾科吸虫相关的胆管癌患者则出现了高拷贝数改变和PD-1/PD-L2表达[46]。蠕虫感染还会导致宿主表观遗传学的改变。与非后睾科吸虫诱导的胆管癌患者和正常人相比,后睾科吸虫诱导的胆管癌患者显示出异常的DNA甲基化和转录模式[47]。在尿路上皮癌的外显子序列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突变差异[48]。但这种特定的突变在尿路血吸虫病诱导的膀胱鳞状细胞癌中尚未有报告。
蠕虫分泌的一些物质可以直接作用于宿主细胞,或诱导宿主启动免疫机制,分泌免疫物质,从而诱导肿瘤的发生。如麝猫后睾吸虫还会分泌细胞外囊泡,这种胞外囊泡膜富含4次跨膜蛋白。针对麝猫后睾吸虫的胞外囊泡的4次跨膜蛋白的抗体可以阻止胆管细胞对囊泡的内化,并抑制胆管细胞增殖和分泌IL-6[10]。一些蠕虫蛋白可诱导肿瘤标志物的变化,包括如上皮-间质细胞转化表型的改变、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和细胞凋亡的抑制[49]。葡萄糖转运蛋白1在正常的胆管细胞中不表达,但它在后睾科吸虫引起的胆管癌细胞中被表达,其在后睾科吸虫相关胆管癌的发展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50]。此外,血吸虫虫卵诱导的Th2免疫反应还能够调节血管生成从而促进肿瘤的形成[51]。
5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研究发现许多蠕虫感染与肿瘤的发生关系密切(表1)。而另外少数蠕虫可能有抗肿瘤的作用,如猪带绦虫、细粒棘球绦虫和旋毛虫等。蠕虫主要通过调节宿主免疫应答、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或者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来达到抗肿瘤的作用[52-54]。

表1 与蠕虫感染相关的肿瘤Table 1 Tumors related with helminth infection
随着分子生物学与肿瘤免疫学的不断发展,许多蠕虫致肿瘤和抗肿瘤的作用不断被发掘。蠕虫感染与免疫性疾病的关系已被广泛研究,而与肿瘤的关系尚需更多的探索。目前,肿瘤仍是困扰人类健康的顽疾。研发针对蠕虫和宿主间相互作用蛋白的疫苗不仅可以防止寄生虫的感染,并且有可能预防相应肿瘤的发生。拮抗蠕虫和宿主间相互作用的药物有可能应用于预防肿瘤的发生,如抗炎药物、免疫调节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或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抑制剂等。未来,研究蠕虫与肿瘤的关系有望为肿瘤防治带来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