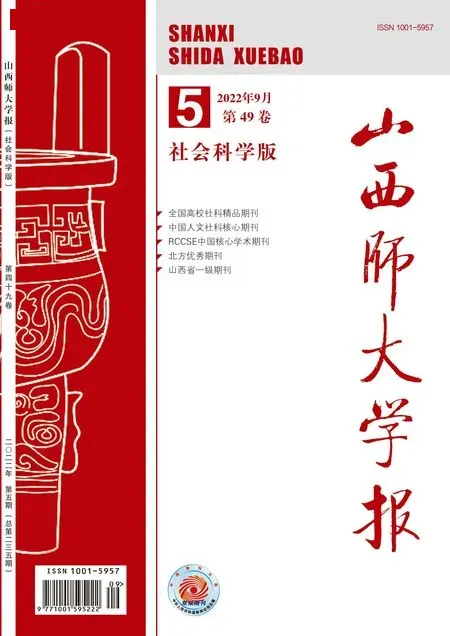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人民”概念的新时代阐释
2022-03-18豆颖康
豆 颖 康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人民”是当代中国政治理念的核心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关于“人民”的理论建设,提出并发展了一系列围绕“人民”概念的政治理论,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人民”一词共出现249次,成为中国共产党回顾奋斗历程和总结历史经验必须依托的主体概念。“人民”经常被作为起始性的概念来使用,表现为用拓展式的论述将“人民”包裹起来,论述“人民”的地位、作用、重要性等,但由于内向式的思考不足,即对“人民”概念具体所指的回答,使“人民”有可能成为一个假想的主体。在这种理论环境中,每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人民”,但也有可能陷入“我是不是人民”的困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到底什么是“人民”?“人民”究竟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概念的思想还有哪些价值?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概念的论述,有助于回答这些疑问。
一、中文马克思恩格斯译著中“人民”概念的词源考察
在汉语中,虽然“人民”“公民”“群众”“人”等主体概念的含义和所指各有不同,但在实际使用中区分度并不高,甚至在同一文献中会出现多个主体概念交替使用的情况,这主要由于它们都可以指代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并非是对概念的误用。但毋庸置疑的是,“人民”“公民”“群众”“人”都有其自身独特的政治含义和社会意蕴,如果细加研究的话,混用显然就是不恰当的。汉语中的这种情况难免使我们产生两个顾虑: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会不会混用主体概念?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译作中文时,会不会出现翻译过程中的混用?因此,对“人民”概念进行词源考察是必要的。
本文查证的德文版文献主要来自德国柏林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治书籍出版社,主要出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传记和国际共运史方面的文献。在1976年出版的Zur Judenfrage,即《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使用德文“Volk”指代“人民”,如马克思在批判国家异化时指出:“Die politische Emanzipation ist zugleich die Auflösung der alten Gesellschaft, auf welcher das dem Volk entfremdete Staatswesen, die Herrschermacht, ruht.”(2)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Karl) Dietz Verlag, Berlin.Band1.Berlin/DDR. 976. S.,347—377.对应的中文译文为:“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其中德文“Volk”即“人民”。这篇文章中还有一处:“Die politische Revolution, welche diese Herrschermacht stürzte und die Staatsangelegenheiten zu Volksangelegenheiten erhob, welche den politischen Staat als allgemeine Angelegenheit,d.h.”(4)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Karl) Dietz Verlag, Berlin. Band1.Berlin/DDR. 976. S.,347—377.对应的中文译文为:“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现实的国家。”(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其中德文“Volksangelegenheiten”被翻译为“人民事务”,“Volk”对应德文中“人民”一词的词源。
恩格斯关于“人民”概念也有精确的使用。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恩格斯在分析“人民”的状况时指出:“‘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像在 1848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通过查证,这句话对照的德文为:“Das ‘Volk’ wird also immer geteilt erscheinen, und damit fehlt ein gewaltiger, 1848 so äußerst wirksamer Hebel.”(7)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Band 7, S. 9-107.Dietz Verlag, Berlin/DDR 1960.其中德文“Volk”即“人民”。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单独将“人民”一词标注了出来,因此指向性更加明确,可见恩格斯是在有意地使用“Volk”指代“人民”。通过这些对照可以比较明确地从词源的角度确证,中文马克思恩格斯译著中关于“人民”概念的使用是准确的,即“Volk”——“人民”。
在德文原著中,“人民”与“公民”的使用是有明显区分的,“公民”一般使用的是“Staatsbürger”一词,在从德语翻译到汉语的过程中,也并不存在“人民”与“公民”混用的情况。以《论犹太人问题》为例,马克思在揭示犹太人解放的实质时指出:“那么你们犹太人有什么理由渴望解放呢?为了你们的宗教?你们的宗教是国教的死敌。因为你们是公民?德国根本没有公民。因为你们是人?你们不是人,正像你们诉求的对象不是人一样。”(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在这段论述中,“公民”和“人”都是主体概念,马克思将二者作为比照列出。对照1976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的德文版ZurJudenfrage,此段表述为“Auf welchen Titel hin begehrt ihr Juden also die Emanzipation? Eurer Religion wegen? Sie ist die Todfeindin der Staatsreligion. Als Staatsbürger? Es gibt in Deutschland keine Staatsbürger.Als Menschen? Ihr seid keine Menschen, sowenig als die, an welche ihr appelliert.”(9)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Karl) Dietz Verlag, Berlin. Band 1. Berlin/DDR.1976. S. 347—377.其中“Staatsbürger”即“公民”,而“Menschen”是“人”“人类”的意思。在这篇文章中,“Staatsbürger”也会根据使用语境发生词性调整,如在“Bauer verlangt also einerseits, daß der Jude das Judentum, überhaupt der Mensch die Religion aufgebe, um staatsbürgerlich emanzipiert zu werden.”(10)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Karl) Dietz Verlag, Berlin. Band 1. Berlin/DDR. 1976. S. 347—377.中,“公民”一词使用的就是“Staatsbürgerlich”,由此也可以进一步确证“公民”与“人民”的不同。
与“人民”“公民”“人”类似的还有“群众”概念,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使用的主体概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所持的思辨唯心主义立场,论证“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多次使用“群众”概念。《神圣家族》第六章第一节(a)的标题即为:“‘精神’和‘群众’”,对照德文为“Der ‘Geist’und die ‘Masse’”,其中“Masse”即为“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思辨唯心主义者意图通过制造“群众”的落后性以证明自身时指出:“绝对的批判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对照的德文为:“Die absolute Kritik hat die ‘Masse’ für den wahren Feind des Geistes erklärt. ”(12)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 2, S. 3-223. Dietz Verlag,Berlin/DDR 1972.其中“Masse”被译为“群众”。另外,马克思恩格斯也对理论中的“群众”与现实中的群众做了区分:“这样一来,群众也就不同于现实的群众,群众只是为了‘批判’才作为‘群众’而存在。”(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0页。对照的德文为“Die Masse ist also unterschieden von den wirklichen Massen und existiert als?die ‘Masse’nur für die ‘Kritik’.”(14)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 Band 2, S. 3-223. Dietz Verlag, Berlin/DDR 1972.“Masse”被译为理论中的“群众”。通过反复比对可以发现,“群众”即为“Masse”,与“人民”——“Volk”、“公民”——“Staatsbürger”、“人”——“Menschen”有显著差异,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有意识地区分这些主体概念。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广泛使用了“人民”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中国的“人民”概念就是一个舶来品,而是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想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人民”一词在古代中国就有,但使用频率较低,且含义与“平民”“民众”基本一致,指被统治者和被管理者,这种意涵持续了整个中国古代时期。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学者在翻译引介西方资产阶级著作时,将英语中的“people”、德语中的“volk”、法语中的“peuple”和意大利语中的“popolo”等词译作“人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概念的思想也随之传入中国,结合当时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人民”一词才被赋予了主权者、统治者等内涵。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吸收传统“人民”理念、批判借鉴西方资产阶级“人民”概念、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概念的思想,创立了以“人民”为核心的现代政治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他在批判西方现代政治理念时指出:“因为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15)《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96—397页。毛泽东则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人民”概念,“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这些论述极大地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概念的思想,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人民”概念的词源考察,可以明确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的“人民”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概念的使用是一致的,通过回溯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的“人民”概念以解决今日关于“人民”的问题,是可以成立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人民”概念的意涵
概念显然不仅是反映着文字的表象,对概念的理解要回到概念得以形成或使其意涵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中去,确切地说,要回到概念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概念的思考贯穿于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和分析,这一时期,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也日益显现,旧式的土地贵族、金融家、资产阶级、人民群众等社会主体力量相互对抗,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概念也逐渐立体和生动起来。
(一)基于所有制分析什么是“人民”
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展开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法,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人民”的主要方法。虽然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以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洛克(John Locke)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使“人民”取代君主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17)卢梭是从理论上为“人民”赋予政治权力的重要思想家,他认为国家的权力属于全体人民,这也就是人民主权。“人民”具有至上性,“人民”的“公意”表现为最高权力,“人民”的本质就在于自己是主人而不是奴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洛克认为,虽然人民在多数情况下是“沉默”的、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但政府合法性的源泉是人民主权,政府是建立在人民的自然权利基础之上的,一旦政府侵犯人民的个体权利,人民就可以选择回到自然状态重新选择,以此来主导政府。,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人们发现启蒙思想家们建构的“人民”概念只能停留在抽象的政治理念中,现实经济关系中的“人民”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思考“人民”概念的起点。
在西方国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指代的是精英、贵族、教士、统治者等中上层,而不是底层民众。柏拉图指出,国家是由哲学王和执政者、武士(军人)和人民三个阶层构成的,工匠、体力劳动者、商人等能够自食其力,没有多少财产,不参与政治活动,也不拥有政治权力的社会成员,就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并且“国家的正义在于构成国家的三个阶层的人各司其职”(18)《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1页。。但中世纪的奴隶制和农奴制还制造了大量毫无权利的奴隶,这些奴隶并不属于“人民”的范畴。而在中国封建时期,“人民”指代的就是底层民众,与西方不同的是在民众之下没有奴隶,即使旧式官员、地主家中的家奴、仆人,实质上也可看作是一份工作,也有告老返乡的权利,并非制度层面的人身依附。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奴隶阶层的消失,“人民”才开始指称绝大多数人,也就表现出重心下移的趋势。(19)[美]汉娜 ·阿伦特:《论革命》,周先旺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62页。“人民”的这种变化趋势,与当时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一致的,即社会成员越来越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类,不掌握生产资料或即将丧失生产资料的民众成为“人民”,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产阶级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呈现出脱离“人民”的趋势,成为“人民”之上的那类人。
基于对这种趋势的把握,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关系的维度指出“人民”是由不掌握生产资料或掌握较少生产资料的阶级组成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分析了构成“人民”的必要条件:较低的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等,这些因素决定了“人民”是一个国家中的被统治者。马克思认为:“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当它不考虑这些差别而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作为文化程度、作为职业来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本质。”(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1页。在私有制社会中,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等领域的差别都是私有制的体现,如果抛开这些因素空谈“人民”理念,“人民”显然就难以避免地成为空洞、抽象的存在物,就像回避经济关系的政治权利只能是抽象的权利一样。可以说,对所有制的剖析是马克思恩格斯认识“人民”的第一步,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超越启蒙思想家最重要的一步。
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掌握生产资料也就决定了“人民”是资产阶级之外的那些人。在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现代政治理论中,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人民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人民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在人民之外,没有其他政治势力存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人民缺少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人民不仅无法摆脱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没有充分的途径行使政治权利,启蒙思想家建构的社会契约、自然权利、自由、民主等政治理念只能停留在形式上,现实的政治权利只能是属于少数资本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指出:“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报刊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恩格斯指出德国人民是由无产者、小农、小资产者构成的,也指出了压迫人民的那些人是由贵族、资产阶级、官吏组成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掌握生产资料,进而掌握着政权。
所有制是决定“人民”构成的根本要素,也是导致“人民”的行动能力增强或减弱的影响因素。“人民”并非是稳定不变的,财产的有无以及多寡、职业和文化程度的差异都会导致作为集体的“人民”在某一时期的团结或分裂,也会影响作为个体的“人民”的行动或情感倾向,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民”内部起作用的体现。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曾提出不能简单地将“人民”看成无差别的合集,受限于所有制导致的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生活差别,人民总是不同阶级的集合体,因此必须要动态地看待“人民”:“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也曾指出:“‘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像在1848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指出“人民”是变动的,是会发生分裂的,并非指“人民”就是一盘散沙,而是解释了“人民”为什么总是发生着变动,为什么用静止的理论来解释“人民”会导致理论的抽象或空洞。
(二) 基于现实考察“人民”的处境
无产者、小农、小资产者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人民”,不掌握或掌握较少的生产资料是构成“人民”的根本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与启蒙思想家完全不同的“人民”。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现实生活中的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的生活处境如何?马克思恩格斯从宗教、教育和生产关系等维度展示了人民生活的真实面貌。
在西方社会,宗教是社会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一环,甚至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将宗教置于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马克思认为,宗教不是关于世界本源问题的正确答案,而是诞生于国家和社会的缺陷,宗教不过是人们对外部的支配性力量的幻想,这种幻想被剥削阶级所利用,成为麻醉人们的精神工具。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宗教批判出发,认为正是由于现实的苦难无从化解,人民才会寻求宗教作为解脱:“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在这段话中,马克思以宗教来论证人民生活的苦难,并将人民等同于被压迫生灵,认为人民信奉宗教的行为其实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是面对现实苦难无法化解的被迫的自我安慰。
马克思对宗教进行批判的目的之一,是要在揭示宗教本质的基础之上揭示身处宗教之中的人民的现实处境,并寻求实现人民现实幸福的途径:“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宗教是人民关于现实生活的幻觉,因此不改变人民的现实生活,仅批判宗教本身是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处境的。正如即便将宗教从政治国家中废除,宣布宗教不再与政治权力直接相关,也无助于人民在生活中继续信奉宗教,这是因为产生宗教的土壤,即苦难的、被压迫的现实生活没有得到改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总是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身处资本主义的反动教育之中,也是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现实处境。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在批判奥地利梅特涅政府伙同封建地主和大资本家,将工人、农民、小资产者、小手工业者封闭在他们所属行业内时指出,统治集团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7页。还不够,还要对人民施行精神控制,“被允许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都要经过最审慎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7—378页。。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反动教育的批判揭示了反动教育在加重人民所承受的压迫,致使人民无法形成对社会生活的正确认知,难以搞清楚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生活的苦难。
与经济剥削和国家暴力不同的是,反动教育不会带来直接痛感,但它却与其他苦难息息相关,它是国家在废除了作为直接统治工具的宗教以后的崭新宗教。反动教育在当时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冤仇,不管人民对国家的下层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来说,他们对于中央政府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不满情绪。”(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8页。但只要压迫人民的生产关系没有发生改变,人民就必然从现存的统治秩序中感觉到痛苦,这是任何反动教育都改变不了的,企图以此维持压迫显然是空想。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这些高级教士及其人数众多的、随着政治煽动和宗教煽动的扩大而日益强横的修道士打手队伍,不仅引起了人民,而且也引起了贵族的切齿痛恨。……他们的奢侈生活越是同他们的说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人民就越是怒不可遏。”(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由此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对人民施加的反动教育不会长期有效,原因在于上层建筑始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试图单方面改变上层建筑而不触及经济基础,效果必然是有限的。
在生产和分配领域中,人民直接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掌握大多数生产资料的封建主、金融贵族、资产阶级处于人民的对立面。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恩格斯在批判“鼓动家”海因岑时指出:“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1页。恩格斯还提醒人民注意,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人民要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只能通过自己掌握生产资料,进而掌握政权来实现。在《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委员会》中,恩格斯也言简意赅地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这就基本阐明了压迫人民的各种力量以及他们实行压迫的工具和手段,指明了只有通过生产关系变革,人民才能获得真正解放。
(三) 基于革命行动分析“人民”的主体性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的现实处境,论证了人民所受的多重压迫。但人民并不是逆来顺受、无所作为的消极主体,而是在实践中摸索着属于自己的行动方式。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论述人民在政权、军事、教育、普选权方面的行动集中表现了人民的主体力量。
人民在对旧政权的批判中探索解放自身的政权形式。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总是借助已经掌握的政权报复威胁到自身统治的人民。但革命也塑造着无产阶级,锻炼着人民。人民逐渐意识到阶级国家的压迫本质,意识到国家政权不过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巴黎公社则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巴黎公社采取的如取消面包工人的夜工制度、严禁雇主们以各种借口克扣工人工资、把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交给工人协作社等举措显示出政权被人民掌握。另外,巴黎公社的两项制度性安排也体现出了它的人民性,“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这项安排目的在于使公社委员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保证公社始终为人民服务。“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这项关于公社委员工资的安排有助于将公社祛魅,使公社委员、公社政权回到人民生活的水平,也就是政权的应有水平,以弱化政权高于人民的错误观念。
人民通过重建军队、教育实现自身的独立性。在封建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常备军和警察队伍是国家政权施行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两支队伍虽然也承担着维护外部安全和内部稳定的职能,但在旧社会已经逐渐异化成为施行阶级压迫的工具。因此巴黎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这项措施不仅减轻了公社的开支,武装的人民也体现了与旧式常备军截然不同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战斗力,这是人民自我力量而非异化了的武装力量的体现。巴黎公社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剥夺教会的私有财产,要求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些举措有助于人民接受全面的教育,为人民开启了精神解放之路。
人民通过普选权表达观点,争取民主。马克思恩格斯曾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普选权,但并没有对普选权进行彻底否定,在巴黎公社时期,当政权可以由人民掌握时,普选权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关于普选权的问题,恩格斯晚年也有过深刻的思考,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指出:“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45页。恩格斯认为,普选权既能够提供计算自身力量的参考,又能提供衡量自身行动是否适度的尺度,在为了履行普选权而进行宣传竞选时,普选权还提供了接触人民的手段。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不信任被资产阶级操纵的普选制度,但依然认为在巴黎公社的条件下,普选权是人民掌握政权、表达自身观点的重要手段。
三、马克思恩格斯“人民”概念的新时代启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3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6页。,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人民理论。时过境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概念的思想对今天还有价值吗?可以从哪些维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概念的思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加立体和全面地认识新时代的“人民”概念。
要保证人民的经济地位,这样人民的各项权利才不会是抽象、空洞的。现代的“人民”概念是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提出的,但为什么没能在西方社会完善起来,反而遭受各种批评指摘?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能给人民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在所有制层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逐渐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分配制度层面,确立了与所有制配套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经济运行层面,妥善处理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在内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人民”概念的真实性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提供了根本物质保障。
但有制度不等于现实,还要把制度利用好,让人民充分享有制度优势。习近平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39)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服务于人民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私利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起到了基础性的保障作用。还要理性地看待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讨论。基于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观察,一些人认为彻底的私有化才能最高效地利用资源,但事实证明西方的私有制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人民丧失政治权利等问题。公有制经济不等于僵化和低效,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压舱石”和“稳定器”,是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的经济基础。处理好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40)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这是保障“人民”概念真实性的所有制基础。
要处理好“人民”概念抽象性和具体性之间的张力。从“人民”概念的形成历程来看,“人民”主要是作为一个集体性的政治力量在行动,“人民”概念展示出巨大的号召力和行动力,为行动者赋予了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都是“人民”概念的整体性和抽象性所带来的积极一面。整体性和抽象性并非仅是“人民”概念的缺陷,而是共同利益的体现。但如果只停留在整体解读上的话,“人民”就会因为缺乏个体关怀而丧失说服力。习近平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人民”概念的抽象性是建立在具体的人民之上的,脱离具体的人民,“人民”就会成为抽象的符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个体性得到了更多保障,作为物质需要的衣、食、住、行和作为精神需要的尊严、隐私、自由、权利等都有了显著进步,那些认为中国以“人民”的抽象性抹杀了个体性的观点是不正确也不客观的。但也要注意的是,不是讲个体就是自由主义理念的体现,更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政治理论才重视人的个体性,社会主义也重视个体,并且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发展个体、实现个体。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对“人民”个体性的肯定。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火焰普照大地。”(4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7页。与资本主义政治理论空谈“人民主权”不同的是,“中国的命运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指的是操在具体的人民手中,人民不仅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现实层面的人民也是真实的,人民被纳入经济保障和各项政治安排之中。这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是主体与客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主体与主体间性”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明确,强调“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43)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9页。,把脱离群众视为最大危险。党将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评价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44)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9页。。这里的“人民”当然都是现实存在的、具体的人民,否则群众路线不仅不能在现实中践行,在理论中也无法成立。
要坚持文艺服务于社会主义、服务于人民这个根本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产品就必然处在人民的对立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人民在文化领域当家作主奠定了根本的物质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缺乏国家观念、集体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的错误价值观依然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人民的利益就得不到全面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生活中的欢乐忧伤、酸甜苦辣不仅有被文艺反映的需要,也有被进一步挖掘和思考的必要。为此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4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14页。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工作导向,要求认识到人民有对能够反映自身利益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人民也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离开人民,文艺将丧失其根基。要使文艺服务于整体的人民利益,也要服务于具体的个人,并在这个过程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明德引领风尚。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这就使人民在文化领域不仅不会感到“失语”,而且成为人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
要通过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促进人民成长和进步。在以往的旧社会,教育总是被赋予阶级统治的使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甚至成为服务于资本对人的异化的工具,以至于“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47)《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实现教育目的转变奠定了制度基础,赋予了人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明确了教育的人民性。
我们也要理性看待关于教育的不同声音,一方面要意识到教育绝非传授知识那般简单,以往的历史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教育完全可以被有心之人利用,为此要始终保持谨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为新时代教育的立场问题指明了方向。(48)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求是》2020第17期。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社会主义教育保有充分的耐心和信心,教育制度的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政治原则,始终擦亮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底色,让教育真正成为人民成长和进步的途径。
要在全过程民主中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在资本主义政治理论中,“人民”总是跟民主问题相关联,但是西方民主并没有完成“人民”的使命,反而在愈加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民主过程中削弱着“人民”概念的内涵,“通过制造代表人民利益的‘超阶级国家’的精神幻想以实现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并通过行使公共职能实施对人民的现实统治”(49)鲁品越:《全过程民主: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西方民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沦为“钱主”,仅通过投票程序形成的“多数决原则”也不可能形成代表多数人意志的“集体意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民主制的批判在今天仍有强烈的针对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找到了一条超越西方民主制的国家政权形式,并通过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以实现“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5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页。,这正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习近平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51)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03页。全过程民主通过民主协商形成人民的集体意志,在人民的民主参与下,政府部门执行、实施和改进这些法律和政策,并对此形成民主监督,实质上形成了人民从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全过程参与,真正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实现了对西方“人民”概念的超越,真正实现了“人民”概念与人民现实的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