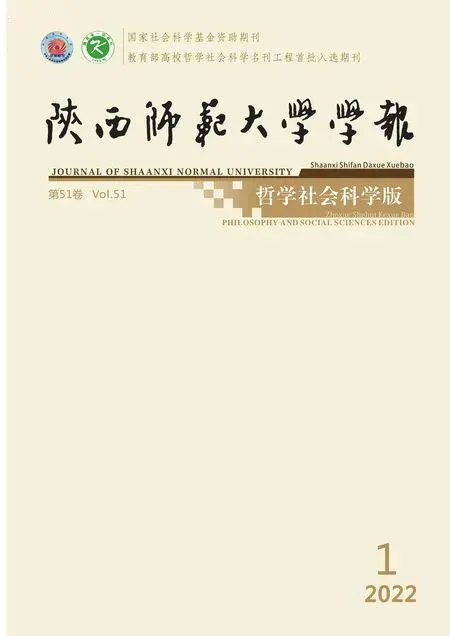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夏商周王制时代的“中国”认同
2022-03-18田广林任妮娜
田广林, 任妮娜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81)
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5 000年一脉传承、延绵不断的国家文明发展史,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成果,可以从宏观视域角度,把5 000年间连续性发展的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内在演化轨迹,概括为3个大的发展阶段: 《史记》所载“五帝”时代的邦国联盟、夏商周之际的王制国家、秦汉以降的帝制国家。关于夏商周时期的“中国”认同问题,笔者曾在《从多元到一体的转折:五帝三王时代的早期“中国”认同》一文中有所涉及,认为早期的中国认同肇源于遥远的史前时代,经历了由多元并存到趋于一体的、十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互为表里,相辅而行,并伴随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发展演化而同步递进,应时升级。[1]由于该文的重点是在考证“中国”一语最早出现的根本机制及其含义的基础上,围绕中国国家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之际所表现出的由多元并存到趋于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中的“中国”认同问题展开的讨论,限于篇幅,未能对夏商周三代之际的“中国”认同问题做出深入论证。这里拟在现有认识基础上,重点围绕此间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层面的“中国”认同,做进一步的讨论,藉以深化对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续性发展的深层机制和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史实等根本问题的认识。
一、 王制的建立与夏代的“中国”认同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本来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历史常识。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普遍都以夏商周作为一脉传承、前后相继的3个朝代。如《尚书·召诰》:“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2]212-213《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554只是到了20世纪初年,由于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曾经对传世文献所载夏朝的一系列史事提出质疑,[4]130-202,88,199-202,139-198;[5]4-5但他对夏朝客观存在的基本史实并未否认,不仅认为商汤伐夏是信史,而且还曾就夏朝的地理方位及其与周边诸小国的关系进行过深入论证[6]1-10,20。目前,尽管当年的疑古思潮余波尚有一定影响,但夏王朝历史的客观存在却是多数学者的共识。
夏王朝建立的基础是对五帝时代邦国联盟政治上的认同改造和文化上的绍续承袭。《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时,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7]7,《尚书·尧典》颂扬帝尧的美德与政绩,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8]6-9。这里的“万国”“万邦”,应指诸多彼此不相统属、各自独立的社会共同体,其中既有已经进入初级文明阶段的政治实体,同时也还包括一些尚未进入国家发展阶段的部落或部族组织。“九族”,是指建立在血缘氏族基础之上的同姓宗族共同体。“百姓”,则是指以同姓宗族组织为核心,融汇其他异姓氏族或宗族而构建起来的地缘性社群组织。这种超越单纯血缘关系的地缘性社群组织,即为星散于各地的邦国,又曰族邦。所谓“平章百姓”,是指辨别邦国内部上层的身份等级,这里行使的是邦国之君的职责;而“协和万邦”“监于万国”,所体现和行使的则是超越于诸邦之上的邦国联盟首领的权威和职责。
五帝时代的邦国联盟,在夏禹继任盟主之际,发生了重大蜕变,即由当初的“公天下”一变而为“家天下”,其显著标志有两点: 一是夏王朝的建立,取代了传统的邦国联盟; 二是传子制度的建立,取代了传统的禅让制度。夏朝的“夏”,原是以夏禹所从出的姒姓宗族为核心,整合其他同姓、异姓宗族或家族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即占据中原一带的夏邦或夏国。夏禹继舜主政邦国联盟之后,随即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把夏人原有邦国之名扩大、升级为他所统领的“天下万邦”的国号,从而破天荒地第一次正式创建了以家天下为显著内涵特征的夏朝。《史记·夏本纪》载:“禹践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史记正义》:“夏者,帝禹封国号也。”该书又引《帝王世纪》曰:“禹受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7]102-105从夏禹到夏启,再到太康,其间虽曾一度有过沿袭传统的禅让制度,企图立益为君的反复,但最终的历史发展轨迹却是天子之位父死子继,辅之以兄终弟及,姒姓宗族一脉承传,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王朝君位继承的传子制度。
春秋战国之际的先秦典籍,普遍把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元首称为“王”。夏朝的建立,便同时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王制国家的正式创制。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在于中国的国家文明历史从此超越了松散的邦国联盟阶段而跨入大一统王朝国家的王制时代。
王制国家的建立,赋予夏王以凌驾于众邦之上天下共主的地位和权威。当初与夏国并存的众多邦国在新兴夏朝的旗帜下,构建起王国与大大小小邦国并存的政治体系格局,其中与夏同姓的邦国主要有“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7]109;异姓邦国包括诸如己姓的昆吾和顾、彭姓的豕韦以及嬴姓、偃姓、姜姓等国[5]242-245。在王制体制下的万国互存、万邦并峙政治关系格局中,由夏邦或夏国升华而来、超越众邦之上的夏王朝,由于地域居中、国势强盛、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很自然地成为所属大小邦国从风膜拜、心向往之的“中国”。而附属于夏朝的诸多邦国,在那些地域更为偏远、社会发展程度相对低下的周边诸部心目中,也同时又都被视为“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此初步形成。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便出现了层级有别、维度不同的3种“中国”认同模式: (1) 夏朝所依托的夏国(邦)内部,众多血缘关系不同的异姓宗族和氏族对以姒姓宗族为核心的夏后氏的认同。这种认同本质上是建立在血缘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基础上的夏国(邦)所属族群社会内部的认同。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层面的认同机制,才使夏国(邦)所属居民成为夏人或夏族。夏人或夏族,是为华夏民族形成的雏形。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认为:“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四大要素。[9]61-64而这四大要素的同时具备,是以民族国家的出现为基本前提的。一变传统的“公天下”而为“私天下”的新兴夏朝,相对于互存并立的天下诸邦,是天下共主,而相对于夏国(邦)或夏民,则具有早期民族国家色彩。夏人对夏国(邦)的自觉认同,既是早期华夏民族形成的内在机制,同时也是夏朝得以凝聚华夏与四裔人心,维系天下共主地位的根本所在。(2) 诸多邦国对以夏王为代表的夏代政治秩序的普遍认同。《尚书·大禹谟》所谓“野无遗贤,万邦咸宁”[2]134,《史记·夏本纪》里的“众民乃定,万国为治”[7]89,《左传·哀公七年》所说的“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0]1 642,讲的都是号称“万国”“万邦”的诸多邦国对夏王朝的政治认同。通过这种政治层面的认同机制,使夏朝王城周边的众多同姓和异姓邦国及其居民显著增进了文化趋同的一元化特征而被纳入“中国”和“华夏”行列之中,从而出现了所谓“复数中国”的现象,极大地扩展了华夏文明的覆盖面。(3) 以夷、蛮、戎、狄为代表的僻在四裔、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周边部族对夏朝及其所属华夏邦国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夏朝所以“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11]507的社会物质基础。
夏代的“中国”认同,还可以通过《禹贡》所载九州、四海、五服所代表的天下观念和夷夏秩序中获得进一步认识。《尚书·禹贡》是研究夏史的重要文献,在古文和今文《尚书》中,均列为夏书之首。该书载夏禹平治水土,分天下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在此基础上,根据土壤肥瘠程度的不同,将九州各地的土地区分出若干不同的等级,并相应地制定出不同的贡赋级差,即所谓“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2]146。与此同时,还以王城为中心,把天下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8]202九州的“州”字,本作“洲”,义为水中可居的陆地。《汉书·地理志》:“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12]1 523关于尧时十二州,颜师古注曰:“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营州,故曰十二。水中可居者曰州。洪水泛大,各就高陆,人之所居,凡十二处”;关于禹更制九州,任土作贡,颜师古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贡赋之差也”。[12]1 523这就是说,唐尧十二州,最初仅是一个单纯的人文地理概念。夏禹以来,随着王制国家的出现,始被纳入管理天下的政治轨迹。与尧舜时期不同,夏代《禹贡》九州视土地肥瘠,区分等差,任土作贡,从而使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传统九州升华到文化学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天下一统的秩序格局层面。所谓:“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四海会同。六府孔修……中邦锡(赐)土姓。”郑注:“史迁‘邦’即‘国’。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国,诸侯祚之土,赐之姓,命之氏。’”[8]202显而易见,这里的“九州”,即是夏朝及其所属华夏邦国,而“中邦”,便是夏朝所代表的“中国”。所谓“中邦锡土姓”,是指夏朝对九州之内大大小小受封邦国的胙土赐姓。《吕氏春秋·慎势》:“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13]305通过这样的礼仪程式,九州之内的诸邦,便都被纳入“中邦”的序列,从而实现了“九州攸同”的政治局面。《禹贡》九州语境下的“九州攸同”,本质上反映的是诸多接受胙土赐姓的邦国对位于万邦之上的夏王朝的政治认同。
而与九州对举的“四海”,则是一个九州之外的人文地理概念,这是通常被称之为夷狄戎蛮的欠发达诸族所居之地。《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14]2 616这一地域及其居民,又称蕃国或蕃服,所谓“九州之外,谓之蕃国”[15]2 980。蕃国或蕃服对九州的向化,就是《禹贡》所讲的“四海会同”。孙星衍疏解“四海会同”曰:“《周礼》云:‘合通四海。’(郑)注云:‘使之同轨也。’”[8]201不难看出,所谓“四海会同”,四海“同轨”,本质上讲的是九州之外的周边地区对九州之内的“中国”的文化认同。
至于《禹贡》五服,也是损益尧舜五服的结果。《尚书·皋陶谟》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汉孔安国《注》引郑康成语,曰:“尧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孙星衍《疏》引《史记》述《禹贡》“五服”文,曰:“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8]114-115这里的“天子之国”,是指夏王朝的都城。王城之外500里是谓“甸服”。这里的甸服,相当于后来西周时期的王畿(1)《国语》卷1《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三国韦昭注云:“邦内,谓天子畿内千里之地。《商颂》曰:‘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书》曰‘五百里甸服’,则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职业也。”参见《国语》,鲍思陶点校,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3页。,这是夏王直接管理的地域,境内居民按距王城道里的远近,分别缴纳不同等差的实物贡赋。甸服以外500里范围内为“侯服”,这是与夏朝有邦国联盟关系的各地方邦所在地域。侯服以外500里区域为“绥服”,这是夏朝的文教与武力可以推及的地域。绥服以外500里的“要服”和要服500里以外的“荒服”,是夷蛮戎狄诸族所居之地。其中,要服之内,是夏政推行和夏文化浸润区域,是为九州。九州之内的政治组织,称中邦或中国,九州之民,是为华夏。要服之外,不在九州之列,是为“蕃服”,号称“四海”。《禹贡》载:夏制五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8]207,这是说有夏之时,不仅华夏同轨,九州攸同,周边诸族所居的蕃服之域,也广被声教,普遍认同夏王朝的政治秩序和九州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曾出土一批以成套的鬶、爵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风格礼仪用器,[16]196-199这是中原华夏文明因素传播到北方草原地带的典型例证,于此可见当时周边四裔普遍认同华夏文明之一斑。通过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机制,极大地扩展了夏朝的文化灌溉面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夏王拥有天下,诸邦各有其国,诸部各有分地的天下四方体系格局。
二、 内外服制与商代的“中国”认同
商朝是在直接承袭、损益夏朝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国家。《史记·殷本纪》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7]125-126这里的“作夏社,伊尹报”,是指在伊尹的主持下,商汤于原夏朝国家礼仪中心举行的祭天仪式暨代夏即天子位的开国大典。商汤之所以保留并沿用“夏社”,其深层意蕴是出于治统维度上对夏朝历史文化的认同。而商汤即夏社告祭天神“践天子位”,则意味着秉承天命而变夏为商,从此获得夏朝原有的天下共主地位。所谓“诸侯毕服”,是指与商结盟灭夏的邦国以及未参加灭夏的夏朝原有诸多邦国对殷商变革夏命、改朝换代的政治认同。商革夏命、建都中原,不仅拥有了夏朝居于天下之中的地位,同时还接替了夏朝天下共主的权威。商代天下各地邦国对商王朝的政治文化认同,也就是对当时“中国”的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政治认同,从而赋予代夏而立的商王以协调四方诸邦的天下共主的地位与权威。当时王权运作的基本体制机制是在天下范围内推行的“内服”与“外服”制度。有商一代的“中国”认同,始终与内外服制度的推行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关于商代的内服与外服,以《尚书·酒诰》的说法最为完整。该篇为西周初年二次东征之后,周公告诫卫康叔以殷亡为鉴之作。其中有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2]207可以与《酒诰》相互参证的考古发现的文字材料是同属西周初年文献的《大盂鼎》铭文,其中有:“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17]1 517。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盂鼎》的“殷边侯甸”说的就是《酒诰》中“越在外服”的“侯、甸、男、卫邦伯”,而“殷正百辟”指的就是“越在内服”的百官。由此可证《酒诰》关于商代内、外服制之说的信而有据。[18]31-46服,汉儒在经籍笺注中通训为职事和服从。所谓“内服”,是指在原有商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商王直属地域,是谓王邦或王国,相当于后世周代的王畿。商朝初年,执掌商朝内服事务者,主要都是商王的宗姓贵族。《逸周书·度邑》载,西周初年武王追述商汤胜夏史事曰:“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19]71。周武王这段话在《史记·周本纪》中作:“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7]165有学者认为,“这里所说天登进三百六十天民就是商汤的族属,是商汤代夏时商族的基本力量,于是商汤根据这三百六十个族属建立了内服制度,此后商代的内服主要来源于这三百六十个族属之中。”[20]50此外,商朝的内服执事,还包括部分追随商汤胜夏的异姓或异族功臣以及夏朝原来的部分臣属。如东夷出身的伊尹,原为“有莘氏媵臣”“汤举任以国政”,先后历商汤、外丙、中壬、太甲、沃丁5朝,皆位在机衡,执其政柄,为商汤代夏及早商政权的发展与稳定,曾经做出重大贡献。[7]122-123,128-129商朝内服任用夏朝遗臣之事见于《尚书·多士》:西周初年,周公迁殷顽民于洛,殷遗多士举证商革夏命,简择夏朝故臣“服在百僚”故事,而抱怨西周不用殷士。周公乃作《多士》,告殷遗多士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8]429。《尚书·多士》虽为周初文献,但有关商初以夏朝遗臣执事内服的信息却是出自亡国不久的“殷遗多士”口中,故可信度极高。由此可以知道,商朝内服的产生和形成,本身就是有商故邦及其与国与夏朝遗族重新整合、多维认同的结果。
有商一代,曾经数次迁都。目前已经确知,考古发现的河南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都曾用为商朝前期都城。今河南安阳殷墟一带,则是商朝晚期建都之地。《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7]136《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对魏武侯曰:“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21]813可以肯定的是,商朝立国期间的所有都城,均应建在商邦亦即王邦之内。故南起今河南偃师,北到河北邯郸,西自山西晋中,东到河南郑州一带,是为商朝内服的核心区域。这一地域远自虞夏以来,就以地处天下之中的人文地理区位原因,成为环处四方的社会共同体心目中共识的“中国”。商代与夏代一样,都属于王朝与邦国并存时代。《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13]347当商之时,以商王直辖的内服王邦(国)疆域最为广阔,势力最为雄强,因称“大邦”“大邦殷”,在殷墟卜辞中则作“大邑商”或“天邑商”,有时也简称为“商”,与列在外服系统的侯、甸、男等邦伯诸侯的方国领地——“四土”“四方”对贞。商朝内服,是商王朝据以制衡四方、维护天下共主地位与权威的根本所在。于是,商王朝直辖的内服王邦或王国也就同时成为外服方国心目中的“中国”。《诗经·殷武》中的“商邑翼翼,四方之极”[3]626,讲的就是内服王国在外服四方中所具有的向心作用,而四方诸国以商朝为中心的观念意识,正是天下四方对以商朝所在“中国”认同的客观反映。
商代“外服”,则是王邦或王国之外以其与商朝关系的亲疏,区分为侯、甸、男等不同等级的服属于商朝的诸多小国。这些小国,有的是受商封册,有的则是自行立国,但均已得到商朝承认而被纳入商王朝政治序列。其中,受商封者,在先秦典籍中,其爵名之前往往冠以“殷”字,如《尚书·召浩》:“命庶殷侯、甸、男邦伯。”[2]211自行立国者,往往称之曰“有方”“四国多方”,如《尚书·多方》:“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王曰:‘乌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2]228-229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商代的外服邦国,又称方国。《尚书》等先秦典籍所说的外服邦伯,又称诸侯,名义上都是殷商王朝的属臣。在殷墟卜辞中,“邦伯”又作“方伯”,或简称“伯”。邦伯、方伯、伯,都是对外服邦国之君的尊称,其所领有的邦国或方国,都是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政治实体,与商朝的关系是大国与小国,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有别于秦汉以后作为帝制国家地方行政建置的郡县。外服所在地域,是为殷商王朝政治控制的最大范围,内服与外服相加,即为商王领有的天下。
商代外服方国的来源,主要有3种情况: (1) 夏亡之际与商邦结盟倒夏的各盟邦,夏灭商立后,这些盟邦自然而然地接受商朝的册封,从而转为商朝的属国。《史记·夏本纪》载:“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7]108这里的“代夏朝天下”,也就等于说在认同夏朝政治文化统绪基础上取代了夏朝天下共主的地位,而“诸侯皆归汤”则说明原夏属诸邦对殷商王朝的政治认同。 (2) 被商朝征服的夏朝原有属国以及存在于先商时期的部族势力,在商朝的军政压力下,改换门庭加入商朝序列而成为附庸。《史记·殷本纪》:“汤既胜夏……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帝太戊立伊陟为相……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7]125,129,129-130不唯受封诸侯,各地自行立国的方邦,也陆续“来朝”或“来献”,构成了当时“中国”认同的基本内容。《诗经·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郑笺:“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享,献也……成汤之时,乃氐羌远夷之国来献来见,曰:‘商王是吾常君也。’”[3]627僻在西北的氐羌邦伯的“曰商是常”,即如汉儒所说的以商王为常君,这里面既包含有政治层面对于商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同时也有文化层面接受华夏礼仪风俗的观念认同。 (3) 商朝王室的部分宗族,通过武装殖民的方式进入灭夏过程中出现的可供商王支配的权力真空地域,形成商朝建在新征服地带的可靠武装藩卫。而这些与商朝有着特殊亲缘关系的新建邦国的出现和存在,又都以其所具有的较强军政势力和较高的文明发展程度,成为凝聚和融合各地人群的政治文化中心,从而客观上促进了商代各方对商王朝的认同。
三、 宗法分封与西周的“中国”认同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继夏商之后出现的第三个王朝。西周建立后,通过“制礼作乐”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实现了新的政治秩序重建。其中最重要者,是在王朝全境实行的宗法分封制度。宗法分封的实质是如史墙盘铭文所说的“分君亿疆”[22]25-32,即封藩建卫,巩固周疆。周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各级贵族,在此基础上由受封者在各地建立起大小不等的二级政权体系,形成拱卫西周王朝的军政藩屏。《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11]1 475从空间维度上观察,西周的封藩建卫与商朝一样,也以王朝直属的周邦为中心,对能直接控制和不能直接控制的区域,实行内服和外服分区管理。所不同的是,西周的分区管理模式与商朝相比,显得更加细密,其突出表现就是通过推行宗法分封制度,把商代以来的内服与外服制度发展改造为畿内采邑和畿外诸侯封国制度,从而使西周王朝超越夏商而达到王制国家的全盛。无论是历史的表象发展,还是典章制度乃至观念形态的深层演进,西周时期都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而此间的“中国”认同,也获得了同步发展。
兴起于“西土”的周人,灭商前的根据地是以丰镐为中心的宗周地区。武王灭商后,认为商朝统治中心的河洛一带,平阔居中,地近天室,自夏以来,就是建都之地,乃谋于新得故商王畿营筑新京洛邑以图长治久安。《逸周书·度邑》曰:“维王克殷国,君诸侯……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室,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洛,无远天室,其兹度邑。’”[23]234-237。其事未果而武王病死。周公二次东征后,以洛邑一带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乃“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作为就近管控殷商故地及其遗民的王城,是为成周。功成之后,遂把夏商以来象征天下共主地位的王朝传统礼仪重器——九鼎安定于洛邑,所谓“卒营筑,居九鼎焉”[7]170,同时迁殷遗民于此。《尚书·多士·序》所谓“成周即成,迁殷顽民”[2]219。洛邑的营建和迁殷遗民,意味着商王故邦正式并入西周王畿。宗周与成周相连,因有邦畿千里之地,这是西周依以立国,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根本所在。而定鼎成周,其政治意义在于以此标明周王膺受天命,代商而为天下共主的合法与正统。这种宣传,客观上十分有利于促进殷商遗族及四裔方国部族对新兴周王朝的政治归属与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西周本照宗法原则通过对畿内和畿外的分封,实现了新兴王朝政治秩序的重构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其总的精神实质是在王畿内部,对殷遗多士及姬姓宗族实行封授卿士、大夫的内服采邑制度,在王畿以外地区,对各类各级贵族实行外服分封诸侯制度。
西周的分封,大体上有褒封和实封两种类型。所谓褒封,主要是对古帝王后裔所属政治势力及各地原有方国的承认或认定;所谓实封,是对同姓宗族成员和部分异姓功臣实行授土领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隐公元年三月》何休注曰:“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24]2 197可见,褒封的实质是对三皇五帝以来的旧贵族势力、商代原有各地土著方国势力在新兴王朝中政治地位的一种认可,其本身并不需要周王另外拿出土地和人民来授予受封者,只是通过“班赐宗彝”等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来完成。《史记·殷本纪》载:周武王代商为天子,“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7]139。《史记·周本纪》载:灭商之际,武王乃“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又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7]163周公二次东征之后,又“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7]169。西周初年对古帝王之后以及夏商王朝宗室后裔的褒封,本质上反映出的是原为“西土之人”的西周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古史体系及其文化传统的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其深层用意和根本动机在于强调新兴的西周王朝是一脉相袭、直接承继三皇、五帝、夏、商王朝的正统所在,藉以彰显其天下共主的合法地位。
实封,是周王对同姓亲信和异姓功臣的授土授民。其中,封在王畿者为内服卿士、大夫,属于周王身边的百官系统。封在王畿之外者为诸侯,本质上是宗族分支,武装殖民。周王在象征王权的国家社坛之前举行授土授民的分封仪式后,受封者各自率领自已的族人和宗族武装,到所封之地建立起附属于周朝的二级封国。受土、领民和命氏是实封外服诸侯的三大要素。《左传·隐公八年》载,众仲语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预注曰:“建德者,建立有德之人而以为诸侯也。”[10]60-61包括畿内卿士、畿外诸侯在内的所有受封者,都须通过定期纳贡和朝觐来表示对西周王室的服从,这是西周王朝天下共主政治地位在经济上的集中体现。在当时国野异制、分区管理的体制机制下,天下各地封君以及四裔部族,各以其与王室关系的亲疏、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和军政实力的强弱,区分为甸、侯、宾、要、荒五等服级。《国语·周语上》载,西周穆王时的祭公谋父语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三国吴韦昭注曰:“邦内,谓天子畿内千里之地……京邑在其中央。”“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谓之侯服。”“侯,侯圻(2)这里的“圻”,系指各种服级的边界。也。卫,卫圻也。言自侯圻至卫圻……中国之界也。谓之宾服。”“蛮,蛮圻。夷,夷圻也。周礼……卫圻之外谓之要服,此言蛮、夷要服,则夷圻朝贡或与蛮圻同也。”“戎、狄……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故谓之荒。”[15]2-3由此可以看出,周礼的甸、侯、宾、要、荒五服与夏制的甸、侯、绥、要、荒五服之间有着一脉承袭的内在渊源关系,所不同者,周礼制度更形完备,管控更形细密而已。其中,列在甸服、周人称之为“邦内”的西周王畿,是在周族旧邦基础上,兼并故商内服辖区,认同虞夏以来文明成就而形成的天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为各地诸侯和周边部族心目中共同的“中国”。王畿之外列在侯服或宾服的各地诸侯,其出身背景或为古帝王之后,或为西周王室亲族,或为西周开国异姓功臣。其所属人群与王畿之内居民,共同构成华夏民族的主体。在当时周边诸部心目中,由西周畿内采邑和畿外诸侯封国构成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均以其文明发展程度较高而被视为“中国”。宾服之外,即属文化欠发达的周边诸族居住区,以其对周王朝政治上、文化上的认同,分别列在要服和荒服。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是一种多层次的宗族贵族占有制度。名义上,周天子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周天子以天下大宗和天下共主的身份,把畿内和畿外的土地分别封授予卿士百官和各级诸侯。所有受封的内服卿士与外服诸侯,相对于周王,均属小宗。内服卿士与外服诸侯在其封域之内,又均为大宗,这些受土封君在各地也按照周王的办法,再把直接控制区域以外的土地封给自己的亲族,于是便出现了更次一级的封君,称大夫,大夫所领封地称为“采邑”。大夫再把直接控制区域以外的土地封赏给自己的亲族——士,士所有的土地称“禄田”。士以下不再分封。上自天子,下到诸侯、卿士、大夫,各级封君的政治地位与经济资产,都实行世袭制度,正所谓:“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25]601。有资格继承爵位与资产者,必须是嫡妻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妻无子,则另立庶妻中地位最尊的贵妾之子,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23]2 197。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异姓封君还是同姓贵族,每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奋斗,更重要的是来自于血缘宗族背景,这就叫世卿世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辨别血统、祭祀祖先和天神,便成为当时国家行政的要务。周礼规定:只有作为天下大宗的周王才有祭祀天地和周人共同祖先的权力。天子祀天祭祖,内服、外服中各级各姓封君贵族均有从祭和助祭的义务。当异姓封君贵族履行从祭与助祭义务之时,其原有族群背景便被极度淡化了,由此于无形之中融入西周王朝的统治阶级阵营。如此一来,便把王畿内部的异姓内服卿士和王畿之外所有褒封、实封的异姓诸侯全部巧妙地整合到西周王朝统一的政治序列之中。“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0]334,是周代通行的祭祀礼文。西周时期畿内、畿外异姓封君被周王统一纳入从祭和助祭序列,既是西周王朝对三皇、五帝、虞夏、殷商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整合、认同的历史产物,同时也客观地证明当时姬周以外的广大异姓卿士和诸侯,对以西周为代表的中国的高度认同。
四、 结 语
夏朝开创的王制国家,为后世商周王朝所沿袭认同,其核心体制机制在于夏商周三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通过祚土赐姓的政治运作,构建起王国与诸邦(诸侯国)两级国家政权互依并存的政治关系格局,从而赋予三代之际“中国”认同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文化内涵。夏王朝建立的基础是五帝时代的邦国联盟。夏朝建立的里程碑意义在于,中国的国家文明历史从此超越了松散的邦国联盟阶段而跨入大一统王朝国家的王制时代,从而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必备的社会物质基础。由于诸多邦国对以夏王为代表的夏代政治秩序的普遍认同,使夏朝王城周边的众多同姓和异姓邦国及其居民显著增进了文化趋同的一元化特征而被纳入“中国”和“华夏”行列之中,早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由此初步形成。
商代与夏代一样,都属于王朝与邦国并存时代。商汤因“夏社”而代夏之政,其深层意蕴是出于治统维度上对夏朝历史文化的认同。商代天下各地邦国对商王朝的政治文化认同,也就是对当时“中国”的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政治认同,从而赋予代夏而立的商王以协调四方诸邦的天下共主地位与权威。商朝王权运作的基本体制机制是在天下范围内推行的“内服”与“外服”制度。商朝内服和外服的产生和形成,本身就是有商故邦、夏朝遗族及各地各级属国重新整合、多维认同的结果。
西周初年对古帝王之后以及夏商王朝宗室后裔的褒封,本质上反映出的是原为“西土之人”的西周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古史体系及其文化传统的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其深层用意和根本动机在于强调新兴的西周王朝是一脉相袭、直接承继三皇、五帝、夏、商王朝的正统所在。西周的封藩建卫与商朝一样,也是以王朝直属的周邦为中心,对能直接控制和不能直接控制的区域,实行内服和外服分区管理。相形之下,西周的制度显得更加细密,其突出表现就是通过推行宗法分封制度,把商代以来的内服与外服制度发展改造为畿内采邑和畿外诸侯封国制度,从而使西周王朝超越夏商而达到王制国家的全盛。
拥有天下共主地位与权威的夏商周三代王朝的相继出现,均是纵向上传承和认同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横向上获得天下各地邦国、诸部政治与文化认同的产物。夏代的九州、五服、四海,商代的内服、外服,周代的王畿内外各种居民对夏、商、周王朝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是三代王朝在近2 0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维系天下共主政治地位的深层机制;天下各地邦国与诸部对于三代王朝政治上、文化上的普遍认同,则是古代“中国”最终走向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根本内在原因;而夏商周三代王朝对三皇五帝以来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绍续和发扬光大,是为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续性发展的精神纽带和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