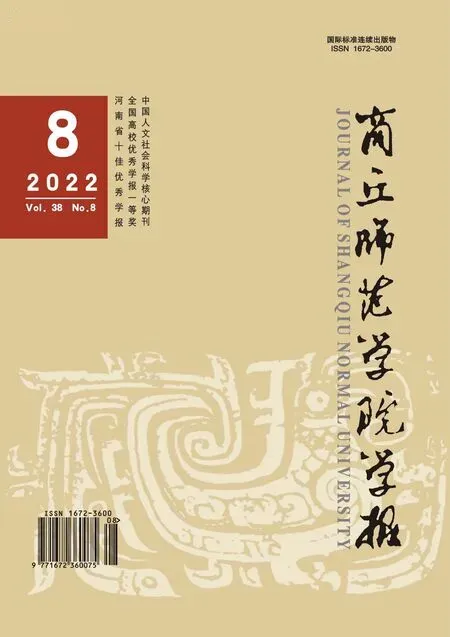略论古代商丘的军事地位
——以汉、唐、宋为例
2022-03-18刘洪生
刘 洪 生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今商丘地处河南省东部,在豫、鲁、苏、皖接合处。沃野千里,交通便利,历史悠久。相传五帝之一的帝喾居于高辛(今商丘市南),后妃简狄,吞食燕卵生契。契,即商部落的始祖。《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亦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1]91此后,商汤建都于南亳,周封微子启于宋,秦置睢阳,汉设梁国,宋作应天府,均在今商丘市附近,皆为通都大邑。这里号称中原门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周朝时封微子启于宋延续殷商,汉时梁孝王守睢阳而平“七国之乱”,唐张巡抗逆贼以孤城佑护江南,赵匡胤节度宋州而育宋基业。明清以降,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天国、捻军均长期活动于商丘,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奠基礼”的睢、杞战役,淮海战役,也都以商丘为主战场。在这座巍峨的城池下,上演过无数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此仅以汉、唐、宋为例,略论其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
一、汉朝平定“七国之乱”的首功藩国
“七国之乱”始作俑者吴王刘濞,乃汉高祖刘邦次兄之子。在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时,“年方二十,有气力”,紧跟刘邦,作战勇猛。又因“吴、会稽轻悍”,诸子年少,“无壮王以镇之”,不得已,刘邦乃封侄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临行前,素狡诈多疑而有远谋的刘邦,以相士之言告之:“若状有反相……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刘濞顿首曰:“不敢。”汉惠帝、吕后时期,朝政动荡,吴王刘濞乘机占有豫章郡铜山资源,煮海水为盐,又享有不纳税的特权,更“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而国用富饶。汉文帝时,吴王在诸侯国中越发优尊,其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王之子在饮酒博戏时,骄悍霸道,出言不恭,争执中被太子以博具版(棋盘)误杀。刘濞拒绝其归葬吴国,并怨恨说:“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从此称病不朝,并刻意保护那些犯法逃窜的亡命者。对此不臣之心,汉天子虽有所觉察和调查,赖吴国相袁盎,擅长“傅(附)会”,左右逢源遮掩,而暂安。为此,贾谊上《治安策》,痛陈这种形势“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太息”,强烈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空置其国”。而汉政府仍仅作局部调整:“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公元前169年,汉文帝之子梁怀王刘揖坠马死,无子嗣),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徙淮阳武为梁王(即后来的梁孝王刘武,初为淮阳王),北界泰山,西界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这样,因文帝宽仁,吴王日益骄横。此后,晁错为御史大夫,随着矛盾加剧,再次上书“削藩”。汉景帝二年(前155)秋,下诏大力削夺吴、楚等诸侯王封地。次年正月,吴王刘濞策动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布檄文,联合起事,史称“七国之乱”。
得到七国反叛消息,汉朝制定战略部署:“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1]2830叛军正面的主战场,吴王刘濞举国内六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兵卒二十余万,号称“百万之师”,自扬州汹涌西犯,卷土而来。汉军统帅周亚夫觉“吴兵锐甚,难与争锋”,而“引兵东北,壁垒昌邑,以梁委吴”,率领三十六军在今山东巨野高筑营垒避敌,牺牲梁国,使“彼吴、梁相敝,粮食竭”,再以“轻兵绝淮、泗口,塞吴粮道”,“以全盛制其罢(疲)极”。《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
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1]2082
就这样,来势凶猛,令汉朝野震恐的“七国之乱”,在梁国的坚决抵抗下,三个月后被最终平定。
“七国之乱”是汉中央政权与藩国矛盾斗争累积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汉立国仿效周朝世袭分封制,幻想以血缘宗法为纽带,巩固统治。但所埋下的祸乱的种子,随着血缘宗亲的递减,终于在汉景帝时爆发。如果“七国之乱”得逞,将又是一场丧乱。因而,“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诸侯王的威胁被基本清除,汉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加强。而梁国在平定这场叛乱中的顽强抵抗,为中央主力军赢得了宝贵时间,使周亚夫偷袭敌方粮仓、断其后路成为可能。无论正面战场还是侧面接应,梁国都是当之无愧的首功。《史记·韩长儒列传》:“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充分说明了梁国都城睢阳在这次平叛中的战略价值。
“七国之乱”时两个细节颇值得玩味: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佗(它)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佗(它)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1]2832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1]2832
叛军中吴臣田禄伯和少将桓将军,倒是深谙用兵之道,深知在广袤的地理环境下,像睢阳城这样高墙深池的都邑,是不易攻取、也不宜攻取的,建议绕过去。多亏骄横而多疑的吴军主帅没有从其计,否则战争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七国之乱”后,西汉政府认识到梁国的重要性,遂加强对其都城睢阳的巩固和扩建:
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1]2083
这样,梁国也逐渐成为西汉第一强藩,扼据帝国东部核心,左右中央安危。其都城睢阳,更成为一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佑护大唐复国的半壁河山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举十五万众,号称二十万大军,起兵范阳,“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倪裳羽衣曲”。唐承平日久,百姓数世不识干戈,叛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所到之处,守将不战而逃,或望风而降,京师震恐。
至德二载(757),安庆绪遣大将尹子琦率军南下,企图开辟第二战场,攻取江南,占领唐军的大后方,切断其后勤保障。这支劲旅,自洛阳出发,一路东南,势如破竹,不料却被豫东重镇——睢阳城——阻隔。无数次攻城不下,不得不全力围城。“尹子琦将同罗、突厥、奚劲兵与朝宗合,凡十余万,攻睢阳。”[2]5537睢阳城军民在张巡、许远、姚阎、南霁云等将官率领下,与叛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睢阳保卫战”。战斗中,守城将士以弱抗强,灵活机动,一次次挫败了攻城的悍匪:
(张)巡夜鸣鼓,严队,若将出。贼申警。俄息鼓,贼觇城上兵休,乃弛备。(张)巡使南霁云等开门,径抵(尹)子琦所,斩将拔旗。[2]5537
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骑麾帜乘城招(张)巡。(张)巡阴缒勇士数十人隍中,持钩、陌刀、强弩,约曰:“闻鼓声而奋。”酋恃众不为备,城上噪,伏发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缒士复登陴,贼皆愕眙,乃按甲不出。[2]5537-5538
(张)巡欲射(尹)子琦,莫能辨,因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张)巡矢尽,走白(尹)子琦,乃得其状。使(南)霁云射,一发中左目,贼还。[2]5538
以云冲傅堞,(张)巡出钩铭干拄之,使不得进,篝火焚梯。贼以钩车、木马进,(张)巡辄破碎之。贼服其机,不复攻,穿壕立栅以守。[2]5538
守城的唐军,或迷惑敌人,突然大开城门奇袭;或利用城墙,夜缒突袭队,如神兵天降;或利用护城河(隍),进行伏击,活捉贼酋;或用系绳的铁钩,在城墙上钩取敌兵攻城的器械;或以火攻焚烧敌军的云梯;甚至以草秆作箭射向敌军,诱辨出叛军首领尹子琦面目,居高临下射瞎了他的眼睛。“大小四百战,斩将三百、卒十余万。”[2]5550这一切如果没有睢阳城高墙深池的地理优势,都无从谈起。如果不是粮尽弹绝,睢阳保卫战不会那么快结束,甚至最后的胜负也很难预料:“初,睢阳谷六万斛,可支一岁。而(王)巨(时为河南节度使)发其半餫濮阳、济阴,(许)远固争,不听。济阴得粮,即叛。至是食尽。士日赋米一勺,龁木皮、煮纸而食。才千余人,皆癯劣不能彀。”[2]5538守城战士最后瘦弱得连弓箭都拉不开。甚至因为“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3]4900。
睢阳保卫战,自757年农历正月开始,至十月陷落,苦撑危局近整年,佑了江淮半壁河山。“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的抗战,主要靠江、淮流域的赋税支撑(1)“安史之乱”爆发不久,唐朝国家经济中心的中原腹地,即遭严重破坏。可参见“诗圣”杜甫的“史诗”作品“三吏”和“三别”等。因此,当时安庆绪叛军,主力军向西攻陷唐都长安,与唐军主力正面决战;再兵分一处,向东南进发,攻取唐朝赖以支撑的江南后方,对唐朝是十分致命的。可参阅石云涛《安史之乱——大唐盛衰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彭丽华《安史之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文献。。而睢阳城位于隋唐大运河中段,是一个漕运重镇和枢纽,如果轻易失守,运河阻塞,后果不堪设想。睢阳城坚守的十个多月,太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在西北战场,源源不断地获得江淮财赋的接济,完成了在战略上的恢复、准备到反攻的过程。睢阳城陷落十天后,唐军就收复了东都洛阳,叛军再无力南下,“肃宗诏中书侍郎张镐代(贺兰)进明节度河南,率浙东李希言、浙西司空袭礼、淮南高适、青州邓景山四节度,掎角救睢阳。(张)巡亡三日而镐至,十日而广平王收东京”[2]5540。如果没有张巡和许远的死守,后来“广平王收东京(洛阳)”,绝非易事。因而某种意义上,唐最终恢复,全仗睢阳城艰守的十余月宝贵时间。《新唐书》赞曰:“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2]5544韩愈《张中丞传后叙》:“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4]201高度评价睢阳保卫战以孤城死守,苦撑危局而存天下,义薄云天。
三、赵宋王朝的龙兴之基
后汉乾祐四年(951),赵匡胤积极拥立郭威代汉建周,因此被重用。周世宗柴荣继位,又提升赵匡胤为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在宋州,故又称宋州节度使)。再因节度宋州之功,赵匡胤被升为殿前都点检,逐渐成为禁军的总帅。
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以镇(河北正定)、定(河北定县)二州的名义,谎称契丹勾结北汉大举南侵,请求急速派兵抵御。宰相范质、王溥等不辨虚实,委派赵匡胤率军出征。至都城开封东北陈桥驿,赵匡胤弟赵光义与掌书记赵普等将士,以黄袍披于赵匡胤,举为天子,回师开封,取代后周,宣布周恭帝退位。就这样,赵匡胤兵不血刃当了皇帝。因其曾为宋州节度使,故称国号为“宋”。由此可见,宋朝的建立及名称的由来,均与宋州有关。
宋朝统治者自认发迹于宋,顺应了天命,景德三年(1006),即升宋州为应天府,诏曰:“睢阳奥区,平台旧壤;两汉之盛,并建于戚藩,五代以还,荐升于节制。地望雄于征镇,疆理接于神州;实都畿近辅之邦,乃帝业肇基之地……用彰神武之功,具表兴王之盛,宋州宜升为应天府。”[5]599-600
大中祥符七年(1014),再诏升应天府为南京,与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府一起,作为三大陪都,与东京汴梁,合称四京。诏书云:“岱宗汾壤,接统于千龄;宝绪璇源,发祥于百世。将肇升于吉土,期大报于高旻。……怀艺祖之膺符,徇乐郊之望幸。仰昭前烈,肇建新都……应天府升为南京,正殿以归德为名。”[5]598宋真宗出于感恩,加封宋州作为一方圣土对其祖父赵匡胤建国的祐护。《归德府志》记载,宋朝时南京城:“城周十五里四十步,东二门,南曰延和,北曰昭仁;西二门,南曰顺城,北曰回銮;南一门,曰崇礼;北一门,曰静安。内为宫城,周二里三百六十步,门曰重熙、颁庆。京城中有隔城,门二,东曰承庆,西曰祥辉。东有关城,周二十五里八十三步,东、南、北各有一门。”据此可知,南京城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城池。直到清初,朱彝尊《枫香词序》还描绘当时此地的盛景:“商丘,宋之南京也。东都盛时,由汴水浮舟达通津门,三百里而近,车徒之毂五,冠盖之络绎,妖童光妓,自露台瓦市而至。乐府之流传,朝倚声而夕勾队于碧堂上。”
北宋末,社会积贫,国势衰微,金政权崛起,不断侵扰。终于,宋徽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同年,宋徽宗之子赵构,于南京(今商丘)即帝位,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宋高宗之所以辗转于此登基称帝,也是相信这里本是赵宋的龙兴之地,意在寻求一种冥冥中的福佑,能够再次庇护新兴政权长盛久安。北宋开国第一个年号为“建隆”,“隆”即“高丘”,寓含“商之丘”之意;南宋第一个年号“建炎”,“炎”即“大火”,仍然是寓含“商”“宋”之意。《史记·天官书》:“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左传·昭公元年》:“辰为商星。”“宋,大辰之墟也。”《汉书·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野。”“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阳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也。”心星,又称大火、辰、大辰、天王、商星,分野上对应宋地。因此,“建隆”“建炎”两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号,本身就表明了两宋与商丘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
当然,宋州被作为北宋陪都,也与其实际地理位置相关:“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梁连其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峡,为大河南北之要道。”[6]17“舟车之都会,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睢阳为腰膂之地者。”[6]18
北宋时,由于辽、夏政权的并存,以及首都汴梁地处平原等原因,国家核心军事力量——禁兵,主要屯扎于北方,在北方驻兵1732指挥(2)1指挥即1营,每营约500人。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页。,而南方仅驻兵195指挥。甚至南方很多州,无官兵,而仅有地方武装。“庆历三年,因王伦、张海等狂贼数十人,更于江、湖、淮、浙、福建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挥。”[7]222—223可见当时宋朝在兵力部署方面的特殊安排。又据《曲洧旧闻》卷九记载:“艺祖(宋太祖赵匡胤)养兵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历代兵制》卷八:“京城之内,有亲卫诸兵,而京师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师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这两则史料,则又可看出当时宋州对于首都汴梁的双重意义:既保卫京都的外患,又可制约京城的内乱。这还可从当时首都与周边各地驻军的具体数量上反映出来,据宋史专家王曾瑜统计,当时开封府驻军476指挥;京东路的应天府46指挥;京南路的许州33指挥;京西路的河南府(洛阳)33指挥;河东路太原府36指挥;京北的冀州20指挥,定州25指挥,大名府13指挥[8]34—44。这些数据可见,应天府的驻军是首都汴梁之外数量最巨者,亦足见当时该地的战略地位。
四、宋城所隐喻的文化含义
今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商丘古城,雄踞一方,巍峨之势,仍依稀可睹。《归德府志·武备略》云:“自古论治国者,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夫世当至治,思患预防,武备岂可不讲哉!况宋中当齐楚之交冲,为江淮之屏障,乩《春秋》经传及历代史书,屡纪被兵。如华大夫之易子析骸,张中丞之罗雀掘鼠,祸斯酷矣!……是在师武臣力者,平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训练士卒,缮完甲兵,以有备而无患也。侯方域有言曰:豫州乃天下之腹心,而归(德)郡又豫郡之腹心也。”[9]844—845历叙了古代商丘的战略地位和价值。在技术有限的冷兵器时代,在四周均是广袤的平原,而没有山河之险的地理条件下,商丘高墙深池式城堡建筑,在攻守方面的战略意义是非凡的。
脱离“语境”的历史阅读是看不出真相的,也是乏味的,故需要冯友兰所要求的那些标准: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根本上说,宋城的建筑设计,原是出于宋国殷遗民的防范和自保心理。
“牧野之战”后,周虽然灭商,但毕竟是西部边陲的部族方国——“小宗周”(姬姓),颠覆了宗主国——“大殷商”(子姓)。遵古制,周保留商人的宗庙祭祀,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其旧都朝歌,为“三恪”之一的一方侯国;同时,周文王又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于周边“三监其国”,再以晋、鲁姬姓诸侯国重加防范。周文王卒,继位的成王年幼,武庚乘机联合因继承权问题而不满的管叔、蔡叔一起谋反。成王在周公的辅佐下削平叛乱,但仍保留商人血祭,封殷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四周仍以郑、鲁、曹、戴、陈、滕、徐、郯等诸侯国予以监视和防范。当时的宋国,虽传说是商人部落的早起都城和活动地,但早已是一片废墟和荒丘,地势低洼,沼泽遍布,土地贫瘠,尤其致命的是无险可守。而宋国却传三十二世君,与东周相始终,所谓“宋以亡国之余,争长于山东诸侯数百年”[5]17,其所赖有二。
一是高墙深池,在城堡规模和结构艺术上最大限度设防。春秋时的宋城,“其城东门曰扬门,又东北门曰蒙门,南门曰卢门,东南门曰垤泽门,西北门曰曹门,北门曰桐门,又外城门曰桑林门”[9]390。据张光直中美联合考古发现,春秋时宋城,方圆约十里,总面积10.2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今商丘古城的10倍。城外再有海子一样的护城河,可以想象在广阔的大平原上,在当时条件下,攻打这样的城堡是多么不易。据《春秋》记载,鲁宣公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围宋”,直到次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也就是说,当时第一军事强国楚,历时八个月,还有公输盘造“云梯”相助攻城,最终还是楚军撤兵,和平解决。又据《左传》记载,这次战争中,楚军围宋经年,“筑室反耕”[10]281,即在城外宋人的土地上反宾为主,建房屋居住,并耕收了一季小麦。城外喊话或劝降,需要“登诸楼车”[10]281。现存商丘古城,建于明正德六年(1511)。俯瞰城池,里方外圆,形如古铜钱。砖砌城墙周长达四公里多,四墙基本对称相等,城墙高6.6米,基宽10米。四门:东曰宾阳,西曰垤泽,南曰拱阳,北曰拱辰。四门外又设四瓮圈小城,瓮城各有一个扭头城门,缓冲对主城门的直接打击,即:北门向西,西门向南,南门向东,东门向北,有“四门八开”之说。又根据五行相生相克,为防金木相克,古城东西两门相错一条街,东门偏南,西门偏北,出现了与南北轴线分别相交的两个隅首,成为中国古城中的唯一。事实上,明人修缮宋城的这种“高筑墙,广积粮”的思想,仍有殷遗民的传统。
二是在强邻环伺下,“以德存国”。依靠尊礼、诚信,赢得良好的“国际信誉”。有学者论:“从文化渊源上看,宋承袭了先民商文化中‘阴’‘柔’的特点,讲礼重义,艺术气质较为浓厚。”[11]宋国很多君主以“厚德”著称:微子启号称“仁贤”,“殷之余民甚戴爱之”;宋景公以“谦德”闻名,祭祀时不愿把天灾转嫁给邻国;执政官华元和向戌两次促成众诸侯国的“弭兵”之盟;“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即使面对来犯之敌,仍不鼓不列阵,不击半渡,不擒二毛。《列子·说符》记载:“宋人有好行仁义者,三世不懈。”正是其国风、民风的缩影。这绝不是什么“愚宋”或“郑昭宋聋”,而是一种大智若愚的智慧和情怀。这在一个充满“不义之战”的时代,作为一种非军事力量,其感召力是巨大的。毕竟社会需要诚信,人类渴望和平。《春秋·公羊传》记载:
(楚)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司马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人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军有七日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后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10]281
这次“楚围宋”,最终和平解决,楚“引师而去”。其关键正是宋国大夫华元待人以诚的君子之风,“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打动了强敌主帅司马子反:“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何)以楚而无乎?”《史记·礼书》云:“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事实上,一部《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结论就是:国家的安危“在德不在险”“不以兵强天下”“非兵不强,非德不昌”[12]。而宋人备战、慎战、止战的军事理念,具有崇高的人文精神和卓越的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传统和素养。或许正因如此,商丘在历史上有“应天”“归德”(3)《逸周书·大聚》:“譬之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此谓归德。”五代后唐同光元年(923),唐庄宗将宣武军改为归德军,治所即在今河南商丘古城。南宋绍兴二年(1132),对峙北方的金政权,将宋朝南京(今河南商丘)降为归德府。民国二年(1913),国民政府恢复商丘之名,归德府设置800年之久。等称谓,既有其实,方当其名,名实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