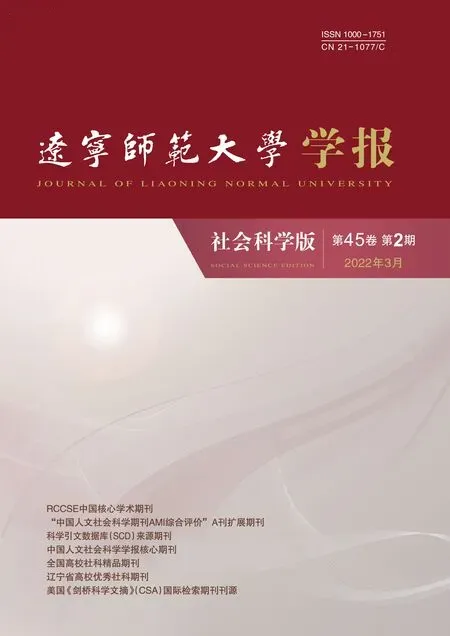论体认概称思维
2022-03-18张凌
张 凌
(1.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一、引 言
体认语言学[1]、体认翻译学[2]等的诞生,催生了体认概称思维的研究,就像认知语言学引爆了其他领域一样[3]。
思维是人类体认世界的一种活动或方式,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4]1771。思维的基本过程是分析与综合,比较和分类,以及抽象同概括。“人的一生就是体认的一生”[2],人类体认世界,对万事万物的各种属性特征或感觉与料如颜色、声音、形状、大小、产地等进行分析比较[5],依据某种感觉与料从某个角度进行综合分类,然后再根据各类事物的感觉与料,进行抽象概括,把体认结果熔铸到口头语言或书面文字里,便于交流与传承体认结果。在思维的基本过程中,每一步都存在概率、随机或者不确定现象,如选择事物的颜色、声音或者形状等感觉与料分析比较,仁者见仁,不是固定不变的;对选定的某个感觉与料进行综合分类,人言人殊,不是逻辑先设的;对综合分类的事物进行抽象概括,也存在概率,不是面面俱到的,同样的事物,“土豆”是根据生长地,“洋芋”则是根据来源地进行比较、分类或概括的结果;把经由上述过程,即分析比较、综合分类、抽象概括,获得的体认结果诉诸语言文字,进行凝化储存时,概率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并没有事前既定的法规或者章程可循,如除了“土豆”“洋芋”之外,还有“马铃薯”“地瓜”“山药蛋”“馍馍蛋”,等等。究竟选择哪一个?在命名时看,是有概率或随机现象的,并没有事先存在于大脑中的所谓观念。事物本无名,为了交际,以物示物不方便,人们就需要给事物起名。根据事物的某种感觉与料起名后,用的人多了,也就成为代表事物的名称。在交际中使用名称,能收到以言代物的效果,避免以物示物的麻烦和局限。
诉诸语言文字之前,人类主要以肢体语言和实物进行交际,交际的范围,无论是广度或者深度,都非常有限。语言文字形成后,人类主要以概念方式进行交际和思考,为了扩大对世界的体认范围,拓展对世界的体认深度,概念继续形成判断,判断进一步形成推理。无论是从事物形成概念,对概念的概然分类形成的范畴,还是对范畴的语言文字凝化,每一步也都存在概率或随机现象。同样,概念形成判断,判断形成推理的过程中,概率依然存在。因此,从事物到概念,从概念到判断,从判断到推理的从有形事物到无形概念、从有限公理到无限推理的扩展过程中,就形成种种思维方式如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归纳思维、演绎思维等。其实,这些思维方式过程中都含有概率或随机现象,因此,可以说,人类思维的根源是体认概称思维,其他形式的思维,都是对体认概称思维进一步分类的结果。
二、思维方式略述
思维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逻辑学就是研究思维形式和规律的学科。逻辑在中国大致相当于墨子(公元前480?—公元前420?)、杨朱(公元前450?—公元前370?)、荀子(公元前313—公元前238)等的名学,朱熹(1130—1200)、王阳明(1472—1529)等的理学。中国的名学、理学等哲学门派,大多都以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通过训诂确定古籍中汉字的意义,进而探索宇宙人生、致知方法的道理。其实,逻辑的英文单词logic,词源是希腊语的logos。logos最初的意思是“词语”或者“言语”,后来才引申为“思维”或者“推理”。Logos何以引申出“思维”之意?其实很容易明白。与logos相对的是graphein,意思是“书写”,后来演变为英语单词grammar(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语法是词法、句法的基本规则”是有很大差距的)。因此logic和grammar原来与语言文字紧密关联。现在西方国家的很多文法学校都叫作grammar school,这些学校传授的并非是词法、句法等语法知识,而是包括逻辑和修辞在内的教学内容。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以语言文字为径路,探究逻辑、思维等哲学问题都是常态,历史都源远流长,并不是从本体论、认识论转向后的语言论才开始的。
“思维”两个字的概称功能非常强大,有丰富多样的含义,从不同角度都可以进行诸多分类。譬如,从形式入手,有感性具象思维、抽象逻辑思维、理性抽象思维等;从目的出发,有上升性思维、求解性思维、决断性思维等;着眼于技巧,有归纳思维、演绎思维、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对比思维、辩证思维等;从学科角度,则有科学思维、艺术思维、法治思维,等等。上述这些思维,都是从某个角度体认世界后,对思维划分的结果,含有概率和随机现象。因此,可以说人类的种种思维根源都是体认概称思维。
三、体认概称思维及其运行过程
所谓体认概称思维,就是人基于一定的目的体认世界后,通过概括抽象或者想象获得概念,然后借助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的,从有形事物到无形概念,经过判断和推理,从已知获得新知的活动与过程。凭借概念形成假设,然后进行推理或者验证,从而不断体认变化发展的世界。从事物开始,进行抽象或者想象,得到一些概念;经由概念,继而进行判断和推理,旨在进一步体认世界。这就是体认概称思维及其运行过程。
事实上,面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具象、属性特征或者感觉与料,人会根据一定的目的进行体认和想象,在想象过程中有意识地抽象,获得一定的概念。然后又用抽象得到的概念对世界进行更加深入的体认。概言之,人对世界的体认,一方面是具象、想象、抽象的周而复始,从有形到无形的体认过程,另一方面是从抽象得到的概念,经过判断和推理,从有限到无限的体认过程,对万事万物、宇宙人生进行分类探究。这就是中国典籍《礼记·礼运》《孝经·圣治章》《白虎通义·三军》等讲的“人为万物之灵”,刘勰(465?—521?)讲的“惟人参之”;西方人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公元前480?—公元前420?)讲的“人为万物尺度”,康德(Kant, 1704—1804)说的“人为自然立法”的核心要义。
(一)概念的形成是从有形事物到无形观念体认概称世界的结果
概念是什么?据《辞海》,概念是“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其特有属性概括的”[4]551。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6]可见,概念是人体认世界的结果,不是像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等许多西方哲学家认为的那样,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大脑里。“概念”的英文是concept,据《英汉辞海》,concept相当于thought, idea或者notion,是“一种概括性的或抽象的观念”[7]。什么是《辞海》里说的对象的“特有属性”?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容易众说纷纭,不如说成某种属性,因为人是根据事物的某一属性,对事物进行抽象和概括形成概念的。究竟选择哪种属性,是形状?是颜色?还是产地抽象出概念,就存在概率或随机现象了。譬如,相同的东西,在有的地方叫洋芋,在另一个地方叫土豆,还有叫马铃薯、地瓜等的地方。再根据以上释义,毫无疑问,概念是对事物的某种属性进行概括后形成的思维形式。“概括”两个字,就是概念、思维具有概率的应有之义。具有某种属性的事物就是概念的具体对象,概念就是对具有某种属性的事物抽象出来的“象”。
“象”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里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关于“象”字来历,有不同说法。《系辞传》中的“象也者,像也”遭到胡适反对,因为“古无像字”;《韩非子》《解老篇》载“人希见生象也,而案其图而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胡适认为非常牵强。胡适提出,象字在古代大概用“相”字,既指体认的对象如事物,也指事物的形象,还包括相。随着相人术的发展,相成为专有名词,普通的形相之意就用“象”表示了[8]84。本文暂用胡适对“象”的界定,即体认的对象,尤其是事物的形象。
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其实就在一部《易经》,虽然《易经》解读千千万,但胡适认为《易经》精髓在三:易、象、辞[8]81-82。究其实质,整部《易经》的核心就是一个“象”字。因为易者,象也,一切变化都因象而生;辞者,象之用,在于解释象的吉凶,达到鼓天下之动和禁民为非的双重目的[8]84-95。
先民对世界体认后,总得把体认结果表征出来,文字是一种重要的表征手段和符号。中国汉字源于象形文字,是先民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体认结晶。中国最早解释汉字六书的,当推西汉刘歆(公元前50—23)《七略》:“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可见“象”在汉字构造中的重要作用,“六书”中就有“四书”与象密切相关,是先民体认世界的结果;转注、假借属于用字法,是对“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书的认知加工。许慎(58-147)在 《说文解字》中沿袭了刘歆汉字源于六书,有造字法与用字法的观点,只是更换六书的部分名称,并把六书顺序调整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并沿用至今。仔细看看刘、许的六书,“象形、转注、假借”为共有项,说明象形在汉字形成中的奠基作用。再看看许慎对“转注、假借”的界定和例示,“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可以看出转注类似于刘歆的“象”意,假借则类似于“象”声。如此一来,刘歆的六书,完全可以“象”为根脉,证明汉字构造源于“象”了。汉字而外,世界上很多文字的起源也都是象形的,如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文字、古印度文字,等等。文字起源以“象”为基础,但具体是“象形、象声还是象意”等,就有概率问题,可能一种文字重形,而另一文字则重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象”的基础可能会逐步减弱,不同文字走上不同的发展简化道路。
孔子把“象”分为两种,一是自然物的现象,二是人见物后的想象[8]86。由现象和想象得到概念,继而进行判断和推理。因此,“象”在思维的基本形式,即概念、判断和推理之中居于基础地位。概念的形成基于现象,究竟选择事物的哪些现象进行抽象或想象,存在概率或随机性,因此才出现一物多名的情况,根据不同的现象对事物进行不同的命名,才出现了命名转喻的情况[9-10]。此外,如上文所述,人在体认世界后,也会根据可见的事物,进行想象,得到一些概念。譬如,上帝、鬼神、神仙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表达的都是一种神秘莫测的超人类控制力,究竟选用哪一个概念,同样存在概率和随机现象。可见,概念的形成有概率和随机性,用来凝化概念的文字,其形成也有概率,那么,就可以说概念就是人概然指称世界的结果,含有概率性和随机现象。
(二)判断是对有形字词之间、无形概念之间关系的一种概称表述
“判断”两个字本身也具有概称性,表达不同的意义。譬如,有辨别、判定之意,如《北齐书·许惇传》“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断,见知时人,号为入铁主簿”;有鉴赏之意,如宋刘克庄《贺新郎·寄题聂侍郎郁孤台》词:“倾倒赣江供砚滴,判断雪天月夜”;还有一个意思是,对事物的情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4]1410。“判断”的英文大致相当于judge或者judgment,有辨别、判定之意,但没有鉴赏的意思。本文讨论的是《辞海》最后一层意思的判断。
“判断都用句子来表达,……同一个判断可用不同的句子来表达,同一个句子也可表达不同的判断。”[4]1410判断是一种思维形式,在语言中体现为把字或词连接成句子。既然“同一个判断可用不同的句子来表达,同一个句子也可表达不同的判断”,都存在概率或随机现象,那么便可窥见作为思维形式的判断本身也具有概率或随机现象。也就是说,判断是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经过体认后获得的一种含有概率的思维形式和体认结果。
在语言层面,判断常常用表示判断的“是”,把不同的字或词连成句子。譬如“人是会死的高等动物”“鸡是能下蛋的家禽”“象是有长长獠牙的动物”。无论是这些判断句,还是表示判断的“是”,都含有概称性。先论证“是”的概称性。一般情况下,“是”表示等同,如1+1=2,我们可以说1加1是2。但在很多情况下,“是”还可以表示大于或者小于,如“我是张凌”,其中的“是”就不是表示等同关系,因为我不仅是张凌,还是教师,还是家长,还是男性,等等。从这个角度体认,“是”表示大于和包含关系,因为我有非常多的属性和特征,只要借助“是”,就可以形成不同的判断句,都只能对我的某个方面做出判断。从另一个方面体认,“张凌”是两个字,同样具有概称性,可以表示人名,也可以表示商标、地名,甚至是某种精神,等等,似乎概称的内容无法确定。“我”仅仅是“张凌”概称内容中的某一个;退一步说,即使把“张凌”限定为人名,世界上叫作张凌的人并非我一人,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从这个角度体认,“是”表达的是一种小于和被包含的关系。可见,即使是表示判断关系的“是”字,本身都包含多种含义,在使用时都得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才能确定。
现在看看这几个表示判断关系的句子。“人是会死的高等动物”“鸡是能下蛋的家禽”“象是有长长獠牙的动物”,这三个句子中的“是”,都不是等同关系,因为“人”并不只是“会死的高等动物”;“会死的高等动物”也不仅仅是“人”。体认得知,这三个“是”都表示大于或者小于关系,究竟是大于还是小于,需要这些句子之外的其他条件辅助,才能确定。因为跟上文讨论“是”的情况一致,不用过多论证。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受经济性、省力原则或者交际目的影响,“人是会死的高等动物”“鸡是能下蛋的家禽”“象是有长长獠牙的动物”等判断句会进一步简化为“人会死”“鸡能下蛋”“象有獠牙”等概称句[11]。
“人会死”“鸡能下蛋”“象有獠牙”等句子从形式上看,似乎只能描述各自对象的某种属性或者特征,已经没有判断句的形式要件和功能特征了。但是,这些句子都是判断句简化而来的,表达的意思跟各自以前的判断句也差不多。如此说来,“人是会死的高等动物”和“人会死”都是表示判断的句子,正如上引《辞海》那句话所言,“同一个判断可用不同的句子来表达”。究竟选择哪一个表示判断,存在概率现象。此外,“同一个句子也可表达不同的判断”,如何理解这些不同的判断,就存在概率或随机现象。就从“人会死”“鸡能下蛋”“象有獠牙”等句子本身来说,每一个都含有概称性,体现语句使用者的主观性[12]对语句概称表达的体认。
因此,不论是判断所依赖的前提,即概念,还是判断字“是”,还是由判断句简化而来的句子,都具有概称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判断其实只能是一种对事物某种特征或者属性的概称表述。判断是连接概念和推理的中间桥梁和纽带,推理中也存在概率或者随机现象。
(三)推理是对概称表述从已知到新知的概率推衍
推理又叫推论,是由一个或一组命题,即前提或已知,推出另一命题,即结论或新知的思维形式。“推理是客观事物的一定联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4]1910事物的什么联系,存在概率,因为事物之间的联系纷繁复杂;在哪些人意识中的反映,这也存在概率。同样一个事物,人们对其抽象后得到的概念都可能不同,上文已经论证,不予赘述;再体认事物之间的“一定联系”进行推理,人言人殊的概率就更大了。以因果关系为例,同一个原因可以导致多种结果,同一个结果可能缘于多种原因。此因和彼果之间的联系,以哪一个为准呢?因此,推理这一思维形式,本身也蕴含概率因素。
推理要正确,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前提真实,二是推理形式正确[4]1910。什么叫真实?什么叫正确?似乎没有客观标准。譬如,病人吃了苹果,有的说味道很苦;身体健康的人,很多体认到苹果味道不是苦,而是甜的。哪一个算是真实的体认结果?再看看下面这个句子。“全班同学都考得不好,只有张书源750分总分,考了702。”如果从形式上看,这个句子肯定是错误的,是个彻头彻尾的语法病句。既然全班同学考试成绩都不理想,那么肯定谁的分数都不高,那怎么还有个同学考了702分呢?难道张书源不是这个班的吗?这种看似病得不轻的语句,却在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广受青睐,表达说话人或者语言使用者的某种情感[12]。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流传甚广的推理。只要保证大前提正确,小前提也正确,那么结论必定正确无误。譬如,大前提:人都会死;小前提:王小二是人;结论:王小二会死。问题是,大前提“人都会死”怎么就是正确的?用什么方法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这个句子要正确,前提是古往今来的人都会死,就算没有所谓的张果老这种长生不老之人,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其他长生不老的人,因此暂时得出“人会死”这个结论;但在浩渺的未来,怎么就能保证将来的人也会死,从而得出“人都会死”这样的结论呢?前提的真实性,是不是就遇到致命的挑战了?注重实证的科学发展到了今天,但对类似于“人都会死”的所谓全称命题,其真实性是无法得到验证的,再大的语料库,什么样的大数据,似乎都无济于事。因此,推理中也存在概率现象。“人都会死”的真实性,来源于经过人们的体认,发现没有不死的人,于是就凭借体认世界得出的常识,勉强接受这类语句的真实性了。
四、余 论
经过论证,可以发现,在人类思维中,无论是概念,判断,还是推理,每一步都存在不确定的概率现象。换言之,推理的基本形式存在概率。因此,可以说人类思维是概称性的,即本文的“体认概称思维”。概念、判断、推理是逻辑学的常用术语。在语言文字中,概念相当于词语,判断相当于句子,推理相当于语篇。一般来说,语言文字是由词语、句子和语篇构成的。既然概念、判断、推理都有概率,那么词语、句子和语篇也自然会有概率,语言文字就是概率性的。语言文字的主要功能是人用来有目的地指称世界的,指称世界含有概率,则语言文字理应是概称性的。这就是我们最近探究的语言文字概称性问题,简言之“语言概称性”[5]。由此观之,体认概称思维是语言概称性的根本之一,语言概称性是体认概称思维的一种表现。
体认概称思维是体认世界的过程与结果。语言文字是体认世界、不断思维的结晶,是一种表征体认结果的方式,又是继续体认世界的一种手段。体认概称思维是根底,语言文字概称性是表象。研究体认概称思维,可以发现语言文字是人类体认世界的结果,语言文字来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体认。从功能上来说,语言文字是体认概称思维的表现,是人类赖以继续体认世界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人类思维是概称的,语言文字也是概称的。那么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思维,哪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难以完全表征真实变化的世界,都只能是盲人摸象、管中窥豹[13]。因此,就有必要进行语言文化交流,获得对真实世界的体认知识。只有这样,各个民族从各自的思维,利用各自的语言文字,加上对世界的体认,加强各自的语言文化建设;同时,增强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彼此融通,才能获得对真实世界的体认,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方面都值得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