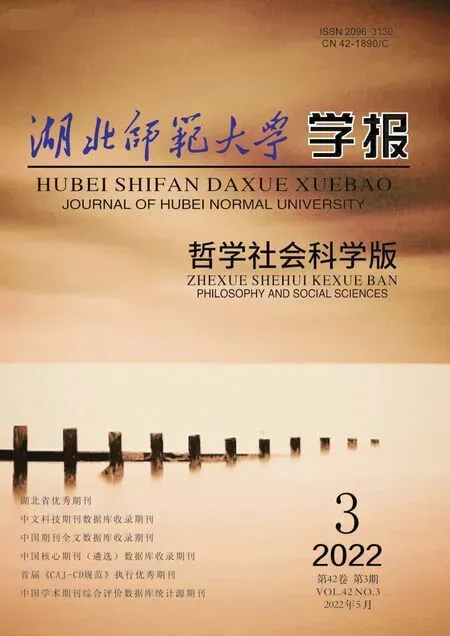谈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
——独舞编创发展
2022-03-18董欣
董 欣
(湖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知往鉴今: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编创历程
中国民族民间舞中的独舞,作为独立体裁的作品,其编创是民族民间舞创作的核心和重点。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独舞作品通常需要通过个性鲜明、情感细腻的人物形象来演绎、刻画以及传达人物的内在情感。它与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等形式有所不同,它以典型形象抒志言情,强调个体情感。因此,中国民族民间独舞的编创需要舞蹈编导拥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与洞察力,在古典文化和现实生活中捕获典型的人物形象,并融汇合适的民族民间舞语汇素材,进而完成艺术创作,最终呈现于舞台之上。
中国民族民间舞可理解为中国 “各个民族的民间舞”。它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具有可行性的。首先,从舞蹈教学中、舞台化的“民族民间舞”中来看,它们是依据一种风格性强的民间舞创作的舞蹈作品。其次,从民间舞的内涵上来看,它在农业文明之下诞生,总的来说中国少数民族的舞蹈是属于民间舞的性质,“中国民族民间舞”对民间舞的称呼虽然引用了“民族”,但其与“民间舞”表达的内涵却是相同的。
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创作的现代发展主要起源于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为群众服务,要把立足点放在工农兵的立场上,强调必须走群众路线,要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1942年底,鲁迅艺术学院组建起一支秧歌队,走向街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自此以后,奠定了深入群众的舞蹈创作道路,回归向民间学习的舞蹈创作道路。
到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诸多优秀的舞蹈家深耕中国民族民间独舞创作。如戴爱莲先生1946年在重庆举办了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嘉戎酒会》《瑶人之鼓》等,受到当时青年人的喜爱;再如被誉为“人民舞蹈家”的贾作光,扎根内蒙古,创作了《牧马舞》《雁舞》《鄂伦春舞》等一批反映草原牧民劳动和生活的独舞作品;还有维吾尔族著名舞蹈家康巴尔汗的《顶碗舞》《盘子舞》等等。20世纪50年代期间,众多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的成功举办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独舞的创作注入了全新的力量。改革开放后,我国又相继出现了《雀之灵》《水》《残春》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21世纪以来,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的创作在舞蹈风格上不断推陈出新,从安徽花鼓灯《徽娘》到藏族独舞《转山》,从傣族舞蹈清新婀娜的《花儿》到蒙古族豪放豁达的《长调》,从朝鲜族舞典雅含蓄的《扇骨》到维吾尔族舞蹈热情洋溢的《心弦》,还有安徽花鼓灯《醉忆生声》,山东秧歌《一支红杏》等等,其艺术形象的塑造更为生动,民族风格的展示更为完整,主题立意的表达更加精炼,动作语汇的演绎更加精准。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的影响下,艺术跨界合作的兴起与科技的繁荣使得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编创更加朝气蓬勃。
有口难言:思维桎梏下的现实困境
一个时代的舞蹈艺术成就衡量标准最终还要看作品。迈入21世纪,我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民族民间舞中的独舞也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但也不能否认,在民族民间舞中独舞创作方面,仍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还存在着缺乏现实关怀的问题。中国民族民间独舞创作不能在市场经济驱使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人民而舞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它便失去生命力。
在一些舞蹈比赛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民族民间独舞创作集中于汉、藏、蒙、维、朝、傣这几个民族。然而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还有不少民族舞蹈独舞创作相对稀缺甚至空空如也。在艺术高考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有部分民族民间独舞作品被作为艺考剧目的频率非常高,比如《羽化灵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花儿》等等,民族民间组合最常见的也只有六个民族,稍微再多的也只有苗族、佤族、彝族等等屈指可数。
分析创作走向单一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从教材层面,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国民族民间舞教材的影响。作为我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主力军的许多专业舞人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学习经历的影响,各地教师们会把自己已经学到的知识依样画葫芦地传承下去。虽然这套教学体系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民族民间舞蹈编导人才,但时间一长,编者们在思维上便会不自主地不考虑其他民族。
其二,从编导个人层面,来自于舞蹈编导自身的喜好,人们会挑选自己所熟悉的素材入手。多数舞蹈编导可能一般优先选择自己熟悉、了解的民族进行编创。且对于编导来说,将某一民族的舞蹈和其背后的文化了如指掌,再创作出好的作品,可能甚至需要毕生心血,这导致其他民族舞种“门前冷落鞍马稀”。
舞蹈编导对某一民族舞种认知程度的深浅,直接决定作品的质量。所以作为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的编导,不仅要熟悉该民族舞蹈动作语汇的时空运动规律和风格审美流变,还要知晓该民族舞蹈动作的产生背景、舞蹈的结构功能、服装道具以及表演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等。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贾作光、吴晓邦、戴爱莲、盛捷等先辈们就已为我们开辟了民族民间舞蹈创作的道路,做出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榜样。
我们延续先辈们的优良传统,有美好初心,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随着农村人口逐渐转向城市,随着人们的文化生活逐渐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重视采风的意识弱了,似乎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作品与民间的纽带在逐步不见。部分舞蹈编导对于我国某一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内涵的挖掘浅尝辄止,既不“身入”,更不谈“心入”和“情入”,用自身所拿手的情感抒发方式去替换原有的族群生命情感体验,导致民族风格性审美和个人内心情感的把握不准确,做出的作品跑题较远。
黑格尔曾说:“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而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更应伴着泥土而升华,凸显个人内心细致入微的感性体验。既表现人民的生活,将其艺术化,又关照人们的情感与诉求。任何忽视人民现实生活而做出的创作都将是不完整的作品。
历史上的经典告诉我们,文艺作品创作的主题还是要紧跟现实生活与时代潮流,才能朝气蓬勃;只有顺应民意、反映人民的关切与精神,才能充满活力。若我们放大视角,以文学艺术为例,《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反映青年爱情生活的《关雎》、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采薇》、反映游牧生活的《敕勒歌》,还有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等,反映的都是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心声,直击人心,轰动当时,传之后世。
反观当下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作品,很多作品还缺乏对那个民族人民生活和情感的深切关怀,导致题材和情感表现单一等等情况,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维吾尔族独舞大多表现个人“似火的热情”,蒙古族大多表现一男子或女子的“豪迈与洒脱”,傣族独舞多表现“清新与舒缓”,仿佛这些民族只有一种情感体验。
这大多是因舞蹈编导对现实生活观察与体验不够,缺乏对田野对象个体的观察,缺乏捕捉时代变化之处的敏感,造成独舞创作捕捉不到共性与个性并存的人物的内心,使得独舞作品千人一面。
限定有解:生命体验的不倦寻绎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在我国民族民间舞独舞作品的编创之中,我们需时刻怀着一份对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将那一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镌刻在作品之中。中华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民间舞的精神命脉,同样是我们在世界舞蹈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以第七届桃李杯金奖作品《扇骨》为例,这个作品中渗透着编导的民族根性意识。其中的“鹤步翻身转”是以朝鲜族经典舞姿“鹤步”变换而来,将鹤步与点翻身技巧相融合,通过节奏的递进来烘托气氛增强视、听觉的冲击;另外,作品末尾处在“查津莫里”节奏的底子上改变了动作力度,随铿锵有力的节奏而向后吊腰,突出的是向后吊腰反弹的韧劲,它恰好也和作品的“骨气”遥相呼应,体现了朝鲜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气质。编者也谈到过,无论在编创过程中以哪一种方式组合,无论思维方式如何超然,风姿如何飒爽,在朝鲜族舞蹈《扇骨》创作的始终,朝鲜民族所特有的风格、韵律始终浮现在脑海中。编者还强调:“我所表现的个性并非一种可以寻求标新立异的个性张扬,而是那将朝鲜族风格根深蒂固的融入自己血脉中的一位朝鲜族女子内心情感的外化,是在民族风格基础上的一种主题明确的即兴情感。”[1]可见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编创中编导个性的发挥是以了解舞种风格韵律和民族情感为前提的。由此看来,中国民族民间独舞的编导还需在编创过程中认真研究那一民族特有的风格和韵律,并时刻贯穿于作品之中,才能做出真正体现民族根性的优秀作品。
我国民族民间舞独舞编创的创新离不开如今的人民。热爱人民对于我国的民族民间舞独舞编导来说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还要有具体的实践行动以及深刻的理性思考。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创作应该去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而非流于表面的动作,人民生活是一切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我们的各民族人民处于同一个时代,经历着同样的变革,体会着一切现实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也讲到过:“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2]而我们的舞蹈作品里更应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写照,因此,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编创应更加“身入”“心入”“情入”。
回望历史,舞蹈艺术的先辈们在创作上为我们做了榜样。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牧马舞》为例,这是著名舞蹈家贾作光老师来到草原后创作的第一支舞蹈。他与人民同吃同住,把生活中的舞蹈加以提炼,编创了策马、牧马、遛马、放马等一系列舞蹈符号,得到了牧民朋友们的喜爱。《牧马舞》也成为了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但贾作光老师在编创《牧马舞》过程其实并非一帆风顺。最初所创作的牧马舞并不被草原人民接受和认可,刚开始他给老百姓跳的舞是西班牙舞,跳完以后遭到所有老乡的笑话,因为他跳的西班牙舞的“范儿”完全是“斗牛士”的范儿,斗牛士与蒙古族牧民的“范儿”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蒙古族人民不认可,后来经过反思,经过进一步的深入生活,他决定跳“套马”的舞蹈,就把长长的马杆直对着自己肚子,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可后来牧民又指出了他的错误,说:“如果你这样拿马杆,万一马挣脱了马杆,你一松手,马杆就会戳进你的身体,你会出人命的。”他再仔细观察牧民套马的动作,才发现其动作实则是英姿飒爽的,其实牧民们全是侧身拿马杆的。一经点拨之后,贾老师立马改了动作,整个《牧马舞》几经修改以后,终于得到了牧民朋友们的认可。
再以2019年广受关注的电视舞蹈节目“舞蹈风暴”中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作品《醉忆生声》为例,笔者认为这是一部成功且具有创新性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作品,无论是结构的设置、道具的使用还是服装的设计都体现了编导的巧妙新颖的想法。这部独舞作品主要讲述一位花鼓灯老艺人回忆往昔的故事。其结构简要概述为:饮酒醉、忆往昔、再少年、难舍情。其创作主要来源于舞蹈编导多次田野作业的积淀。编导跟随团队多次赴安徽省多个地区采风,在安徽颍上县做田野作业时,一位花鼓灯男性艺人让编导印象深刻,这位男艺人所跳的动作新颖,有自己独特的套路,连接方式也较为鲜见,表演极为出众,也因此有了别样的视觉动感,也引起了编导的关注,关注的一个是他动作的样式,另一个是他在座谈时表露出的心态,他对往昔时光那有感怀却不守旧,有情愫却很淡然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编导以老艺人为原型来编创,提炼了老艺人身上的三个素材点:一是亲身经历过当地花鼓灯的不同时期;二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有深深的情怀;三是其舞艺经由前辈传承,也有自身的理解和表演风格。然而独舞的形式对作品的叙述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动作风格和连接可以加工提炼,但如何在人物身上设置与当下两种记忆就较为困难了,而且这种双重时空必须是自然的、不漏痕迹的,不能生搬《一个扭秧歌的人》这种倒叙的编创方法,经过反复推敲,编导选择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切入点——酒醉,酒醉可以让人物以轻松惬意的状态进入回忆,完成了对往昔与当下的过渡,巧妙新奇之处就在于,编导选择了以一个酒葫芦作为道具,在叙述中引出醉的铺垫,且经过了“醉”与“醒”的转换,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饱满。除此之外,服装设计采用阴阳袖、垂式灯笼裤、长筒靴的设计,为作品增加了不少时尚感,既保留了传统的符号,又满足了当下的审美。该作品经优秀舞者的演绎后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从这两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真正编创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的正确道路,“身入”“心入”“情入”必不可少。同时,我们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窥探出当下的时代、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人所发生的各式各样的变化,以独舞的形式,从多个角度表现普罗大众的生活。好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作品是不拘于一格、不定于一尊、不形于一态的,它既要顶天立地,又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感染力,打动人心,能够传得开,又留得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就是优秀的中国民族民间独舞作品。
匠心独运:大千世界的别样选择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纵向观察,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与进步正引领着各门类的艺术传播走向新发展,而舞蹈紧追时代步伐,在新媒体舞蹈的发展中已经有了多媒体全息剧场舞蹈、人影互动舞蹈、装置舞蹈、虚拟舞蹈等表现形式。
在从其他艺术门类与科技的结合实践中,似乎可以获得关于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创作的灵感。在文艺节目《经典咏流传》中,古典诗词遇见科技创新,二者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在节目里,戏剧大家王珮瑜携手虚拟歌手洛天依合作了一首歌曲《但愿人长久》,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与科技制造的虚拟人物同处一舞台之上。当他们一同唱起歌、一同挥起手时,优美的古典诗词跨越了时间、穿越了空间、突破了次元,为观众完美的呈现出了苏轼心中的“天上宫阙”和“琼楼玉宇”,让观众看到了传统诗词独特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也看到了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美好未来。节目演绎中,舞台上的人并未成为“挂在机器上的肉”,科技亦并未“盖住”艺术本体,反而辅助性地创造了更加余音绕梁的歌声,营造了更加诗情画意的意境,我想这是科技为艺术所带来的奇妙体验之一。一个是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一个是人类未来想象的寄托。
类比古典诗词和音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的独舞编创是否也能跨越时间、穿越空间、突破次元,通过现代科技的进步来展现舞蹈艺术独特的生命力呢?当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遇上21世纪的二次元,在保障以舞为本、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可否瞬间将观众带入一个全新的意境呢?若用虚拟舞蹈呈现出各个民族的传奇故事,我们是否可以创作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藏族“格萨尔王”,耳目一新的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别出心裁的蒙古族“江格尔”呢?再者,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在原始时期就大多是载歌载舞,歌舞相伴,我们大可让科技、音乐来辅助舞蹈,创造别具一格的中国民族民间独舞作品。同时也可以适当加入现代舞的元素,实现动作语汇上的创新。比如德国现代舞家玛丽·魏格曼曾说过“脚在笑,手可以哭泣”,那是否也可以用自己的后脑勺来表现独特的内心情感呢?又或是可以通过自己敲打或者摩擦劳动工具来作为独舞的配乐呢?
我们也不妨设想,在某一动画人物风靡全国之时,借助全息成像技术为其编创一支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例如,在2019年夏天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让哪吒深入人心,若让哪吒来一段苗族舞,或者让颜值在2019年发生转变的敖丙来一段潇洒帅气的蒙古舞,既引了目光,又拓宽了舞蹈在大众眼中的可见性和可及性。
从编创素材来看,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创作有别于其他舞种,它的编创素材源于全国各地。各地舞蹈院校、歌舞剧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和地方歌舞剧团都为本土的文化进行推广,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要想独舞的编创素材取之不尽,还要继续发挥地方优势,形成科学、系统的教材。笔者认为地方性高校舞蹈专业师生应加强发挥其“近水楼台”的优势,记录、保存和挖掘那一片地域的传统民间舞蹈文化,分析研究,形成独具一方特色的舞蹈课堂教学组合,并从课程设置着手,编撰出科学的教材,开设一门主干课程,让学生们能够专门学习本地域特色的传统民间舞蹈,并在这样的课程实践中鼓励学生用本地域的民间舞蹈素材来编排独舞小作品,创造更多奇思妙想,让充满潜力的舞蹈专业大学生们也承担起传播和创造传统舞蹈文化的使命。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国民族民间舞需要继承、保护,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时代的创新[3],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独舞更亦是如此。我国民族民间舞独舞作品若想在当下和未来继续发挥其光亮,其编创还需要加强研究各民族的民间传统舞蹈和其背后的文化底蕴,需要身心并入地扎根进群众生活,需要各地域发挥其自身的优势,也需要与新兴科技自然相融。如何使之紧随时代发展不断融入新鲜血液,又不失其根本,使中国民族民间舞独舞编创更有创新性,是一个仍需不断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