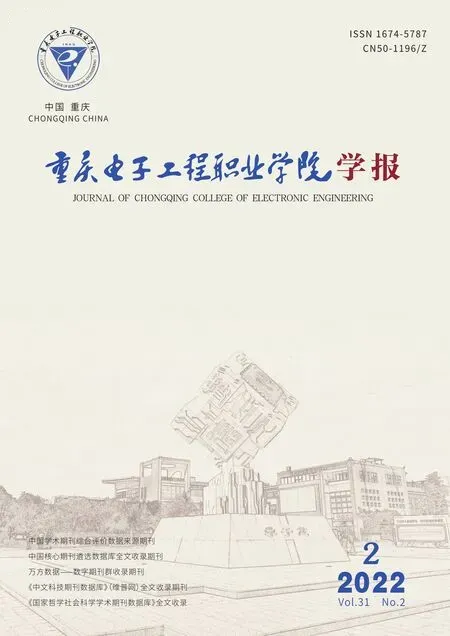刑事司法与社会民意的融合
2022-03-18石天瑜
刘 超,石天瑜
(上海政法学院 刑事司法学院,上海 201701)
1 问题的提出
2010年10月20日夜,某音乐学院的大三学生药家鑫驾驶一辆小轿车撞倒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下车查看后发现被害人躺在地上呻吟,为逃避法律责任最终将被害人杀死。案件发生后,网络上爆发了对药家鑫及其家人的强烈议论与谴责,一时间民意汹涌,纷纷要求判处药家鑫死刑以示公正。该案于2011年4月22日经一审判处死刑,5月20日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最终于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2016年11月3日凌晨,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女留学生江歌被其室友的前男友杀害于住处,其室友因躲入屋内没开门而逃过一劫。之后,该案同样引发了国内巨大的民意谴责,其母亲在微博发起的征集签名以希望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活动中,签名者达到了450万之众。不过最终该案在日本审判,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于2017年12月20日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20年有期徒刑。该裁判结果由于没有达到国内网友预期中的死刑效果从而引起了舆论的哗然,甚至吸引了许多学者参与讨论。
这两个案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地方是均引起了汹涌的网络民意,民意内容均是强烈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不同的是一个在中国被审判,法院充分尊重民意判处了被告死刑;一个是在日本被审判,法院似乎并没有完全理会我们的民意要求,只判处了被告20年有期徒刑。
面对这一次民意在日本的“碰壁”,很多人都在反思。有学者从法律意识层面考虑,认为“‘江歌案’中所表现出来跨国‘舆论审判’,充分暴露了国内新老媒体和网民自媒体法律意识的欠缺……当下公民(包括媒体)信息素养和法律常识亟待普及和加强”[1]。另有学者从对比中日的司法裁判制度以及社会观念的差别出发认为“日本的判例及司法实务都会考虑社会反映,但只是把它作为众多的量刑要素中的一个极小的酌量要素,社会反映不会对定罪量刑产生根本的或重大的影响”[2],“中日民众对法律和道德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别……日本社会公众对审判结果出现极大转向的期待度低,类似签名呼吁这样的行动在日本人看来‘不现实’,因此也无法获得很大响应”[3]。
2 问题的明确
从表面来看,江歌案的确应该算是国内民意的一次碰壁,从而导致学界对其的讨论自然而然地关注于中日文化、政治、法律的差异对比,然后通过差异对比又自然而然得出我们的民意对司法存在不当的干涉、我们民众的法律意识存在不足、我们的司法机关不够独立导致对所谓民意的盲目屈从;日本法院的裁判能够充分独立、日本司法机关从业人员具有的强烈自尊心和使命感等。最后综合我们的差异和不足再进行呼吁:加强媒体自律完善信息自我净化机制,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自觉规范参与行为,积极进行法治信念和精神的塑造,培育理性的公共舆论和公民的理性参与[4]。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并非不当的干涉,刑事司法应当体现民意,日本的司法机关也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言不考虑民意,我们之所以与日本具有不同的民意表达是因为我们所持的刑罚观是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报应刑罚观,而日本社会所持的刑罚观则是以功利为基础的预防刑罚观,刑罚观念的不同最终导致了对于类似案件的不同判决和社会的不同表现。因此,大多数学者的探讨都只浮于表面,没有发现中日民意间刑罚观念差别的本质,以及民意的实质与民意的表现形式的区别。
2.1 刑事司法应否尊重民意
第一位对民意进行系统阐述的学者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其将民意表述为“公众意志”,并进行了相关的解释:“一是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二是公意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对全体都适用;三是公意是永远正确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四是公意永远是稳固的,不变的而又纯粹的。”[5]我国学者一般将民意定义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国家意识相对应的,人民在政治、经济、物质文化生活等诸方面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综合趋势。还可以更简单地概括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人民对其社会存在的反映趋势。”[6]因此,民意是社会民众意志的公共表达,代表了一个国家人民的意志追求和普遍愿望,是社会规则形成的重要来源。
民意应当被尊重,不仅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行为均要尊重民意且服务于民意。中国向来是一个知道民意重要性的国家,“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和民意以安四乡”等顺乎民意之思想早已有之。步入现代社会,我国更是一直强调司法的裁判活动不仅要注重法律效果,还要重视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公正司法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在理论上对民意加以重视,实践中我们更是如此。正是由于民意的推动,许霆[7]才有可能从一审的无期徒刑在二审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也同样因民意的重大影响,邓玉娇[8]虽被法院判处有罪却免于处罚。因此,刑事司法必然要体现民意,其对民意的尊重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
2.2 民意的实质与表现形式
既然民意应当被尊重,那么刑事司法如何尊重和体现民意?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了解民意有实质与表现形式之分。民意的实质即人们内心的一种价值观,是支撑民意如何外显的指导原则,是真正的民意。民意的表现形式则是民意外部展现出来的为人们所熟知的各种形态,如言词、示威、游行等,网络表达也是民意表现形式的一种。由于民意的实质不是外显的,因此只能通过对民意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来了解民意的实质。
了解了民意的实质与表现形式的区别,就可以对“江歌案”和“药家鑫案”中的民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江歌案中,对于凶手而言,民意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是强烈要求判处其死刑;对江歌的室友,民意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是予以道德谴责和咒骂;对江歌的母亲,民意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则为积极参与其发起的签名请愿活动。药家鑫案中,民意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同样是强烈要求判处药家鑫死刑,在得知其是富二代和官二代后,要求判处其死刑的这种民意的表现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在这两个案件中民意的实质内容又是什么?通过上述对民意的表现形式的分析可以发现:江歌案中对于凶手,我们民意的实质是杀人者死的正义观;对江歌的闺蜜,我们民意的实质是对恩将仇报和见死不救的唾弃;对江歌母亲,我们民意的实质是对受害者的同情与怜悯。药家鑫案中,我们民意的实质则同样是杀人者死的正义观。
经过对以上对两个案件中民意的实质与表现形式的分析,可以发现民意的实质才是真正应该关心的内容,才是人们内心价值观的体现,民意的表现形式受所了解的事实的完整程度影响,当人们掌握的真实情况不够或有偏差时,民意的表现形式往往也会产生偏差。如果当我们得知江歌的室友之所以没开门救下江歌并不是因为她故意不开门而是因为门打不开时,或者是因为当时情况危急凶手已经杀红了眼,若贸然开门的话不仅救不下江歌反而自己也会送命时,我们是否还会继续对她进行谴责?显然应该是不会的。
因此,民意的表现形式可以被误导、被煽动,民意的实质则不会。我们不能将民意的实质与民意的表现形式混为一谈,真正应该尊重的是民意的实质而非其外在表现形式,因为民意的实质才是真正的民意。具体到两案中,即我们真正应该尊重的是人们心中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正义观,以及对弱者予以同情和对见死不救者予以唾弃的道德观,而非仅仅盲从于对某个人的死刑呐喊和怨毒咒骂中。
2.3 日本的刑事司法是否不考虑其民意
日本的司法裁判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言不考虑民意或极少考虑民意,相反他们的司法裁判也同样尊重民意的指导和监督。比较著名的案件如1999年发生的山口县母子被害案,当时被告人在其刚满18岁时强奸且杀害了一名23岁的女性和其11个月大的婴儿。由于被告人刚满18岁,日本法院便判处了被告无期徒刑,二审维持原判。该案的裁判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议论,人们普遍同情受害者而谴责被告,并对法院的量刑过轻表示不满。最终日本最高裁判所将案件发回重审,原裁判所重新审判后改判为死刑[9]。另外,日本的死刑标准即“永山标准”中就明确有一项要求“社会的影响”,即死刑的裁判要考虑社会的影响,这也直接表明了日本的司法裁判要尊重民意,特别是死刑案件。再比如,位于日本东京的成田国际机场是日本第二繁忙的机场,也是日本最大的国际航空港。然而让该机场闻名世界的并不是其先进的设备和强大的吞吐量,而是其中的8个钉子户。由于钉子户们的存在,成田机场从196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4年仍只修建了一半。并且,为了不损害到钉子户们晚上的休息权利,机场晚上11点之后便不准起降飞机,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
以上事例足以说明日本对其民意也会予以充分的尊重,不仅是多数人的众意,对少数人的个意同样也会予以足够的照顾。因此,以日本的司法只考虑犯罪事实不考虑民意,而中国的司法容易被民意绑架这一说法来评判中日对“药家鑫案”和“江歌案”的差别裁判是行不通的。不仅仅是日本,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都应当尊重和体现民意,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权力行使也必须服务于民意,越是尊重民意的国家,才能取得长久稳定的发展,才能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和信任。当然这里的民意是指民意的实质,是指对民意的内在实质的尊重,而非对民意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盲从。
2.4 中日民意间对死刑适用的差别
中日间对“江歌案”和“药家鑫案”的差别裁判并不是因为国内民意对刑事司法进行了不当的干涉,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中日民意间对死刑的适用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即正义的报应刑罚观和功利的预防刑罚观间的差别。报应目的刑罚观以社会正义理论为基础强调刑罚的报应目的以维护社会正义,预防目的刑罚观则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强调刑罚的预防目的以追求社会功利。报应目的刑罚观认为 “犯罪的实质是行为对法益的现实侵害或危险,是对法律所维护的公正和秩序的破坏。刑罚作为惩罚犯罪的手段,是国家就危害行为对行为人的一种报应”[10]。因此恶有恶报、杀人偿命是人之常情,是社会的公理,报应目的论反对为追求刑罚的功利目的而违反刑罚的正义性,反对废除死刑。预防目的刑罚观则认为刑事处罚的目的不在于对犯罪人的报应,不应过分关注对犯罪分子的刑事处罚,而应注重通过对犯罪人的隔离威慑或教育改造,使其避免继续危害社会或使其能够正常回归社会,最终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的预防目的论认为仅仅处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而应当从人道主义出发,主张废除死刑或严格限制死刑。
通过“江歌案”和“药家鑫案”可以发现我国在死刑适用上的民意实质——正义的报应刑罚观。在这种追求社会正义的观念下,我们对死刑的适用标准非常低,对残忍程度的认定标准同样很低,几乎只要是杀了人就可以要求判处死刑以维护社会正义,如果在杀人时多捅了几刀则可能会被认为是残忍,如果再有一些受害者的父母亲人出来呼吁一二,那么则有可能会被认定为特别残忍,更别说肢解、抛尸、虐待、杀害多人等这些足以被生吞活剥的行为。而根据日本对“江歌案”中凶手的非死刑判决以及日本民众对这一判决的无异议可以发现日本在死刑适用上的民意实质——功利的预防刑罚观。在这种刑罚观下,对死刑的适用要求则比较高,当适用死刑不能带来比不适用死刑更大的功利时,死刑的适用就会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根据日本司法实践中死刑适用的“永山标准”,在决定是否适用死刑时要对九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功利权衡,这九个方面分别为:犯罪的罪质、动机、样态(杀害手段方法的执拗性和残酷性)、结果的重大性(被杀害者的数量)、遗族的被害情感、社会的影响、犯人的年龄、前科、犯罪后情节[11]。因此,由于“永山标准”所需考察的方面之多,导致日本对死刑的适用极其严格和稀少,在1991年至2015年的25年间,一审程序中共有19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年不到8人,死刑判决率每百万人为6.3[12]。
综上,中日民众对死刑态度的对立可归结为报应目的刑罚观与预防目的刑罚观的对立。我们的民意中对于死刑所持有的是一种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报应目的刑罚观,日本的民意中对于死刑的观念则主要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预防目的刑罚观。正是由于这两种基本刑罚观的不同,才最终导致“药家鑫案”与“江歌案”中日两国间社会民意的不同表现,以及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不同判决。
3 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合理融合
尊重民意是司法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是能动司法的重要载体,是开放性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依托,是检验两个效果统一的重要标尺[13]。因此,刑事司法应当尊重和体现民意,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民意是判定社会问题的重要尺度[14]。刑事司法与民意的充分融合,首先要准确把握民意的历史性与地域性,其次要注意区分民意的内在实质与外在表现形式,最后则是要灵活运用民意与刑事司法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以推动民意的进一步发展。
3.1 准确把握民意的历史性与地域性
民意具有历史性的特点,即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意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如封建社会的“妇德”具有明显的男女不平等的内含,人们允许一妻多妾却不允许一妻多夫,社会对女性不忠的憎恨程度也普遍高于对男性不忠的憎恨程度,而现代社会的“妇德”内含则早已抛弃了封建社会的不平等思想。因此,准确理解当代背景下的民意至关重要,只有以当代社会发展现状下的民意为背景才能设计出符合当代历史条件的司法制度,才能促进社会正义的发展,才会符合现时人们利益的迫切需求。
民意还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即不同的国家因其社会现状和人文背景的不同而存在着民意差别。如中日民意在刑罚观上的差别即是一例,正是因为报应与功利刑罚观的差别,才最终导致我们与日本在对死刑的态度、刑罚严厉性的容忍程度、刑罚目的与性质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不同。如果我们的法律不以我们的民意为基础来设计刑罚,而是一味地追求与发达国家的功利刑罚观相接轨,那么设计出的刑罚必然会招致民众的反对和抗议。因此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不仅要准确理解民意的当代内容,还应当从本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了解本国的民意实质,尊重本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民意的这种显著的地域性特点,“仰赖一种久远的文化传统,根植于一套模式化的社会结构之中,需要整体的社会支持条件或社会生态环境”[15],因此即使在法律交流不可避免、法律移植日益频繁的今天,也必须考虑社会观念的地域性特点。
3.2 注意区分民意的实质与形式
与刑事司法相融合的民意应当是民意的实质内容,而非单纯的民意的外在表现形式。如前所述,民意的表现形式仅仅是民意实质内容的外在表现,如语言或文字的指责和谩骂、身体行动的羞辱以及静坐示威等。这些外在的表现形式必然有内在的民意实质的指导和支撑,如要求判处药家鑫死刑的实质是杀人者死的正义报应。由于民意的外在表现形式非常容易被误导和煽动,因此探寻支撑这些外在表现形式下的实质至关重要。刑事司法与民意的融合是与背后的民意实质的融合,而非与这些单纯的外在表现形式的融合,这是许多学者最容易忽视的一点,也是导致产生“民意会不当干涉刑事司法”这一观点的原因所在。
如何从民意的表现形式中准确地发现民意的实质内容,是刑事司法过程中的难点。简而言之,应当明确以下几点。首先,民意表达所依据的基础信息是否准确而完整。不准确或不完整的信息极易误导民众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从而实施不恰当的行为;因此,刑事司法应当努力还原案件的事实,只有人们基于完整而准确的事实所做出的表达才是真实的民意实质的反映。其次,民意表达的主体是否全面且适格。民意来自于众意,民意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普通的社会民众,具有广泛的群众性[16]。因此,民意表达的主体至少应当满足一定的数量要求,不能将少数或边缘群体的表达当作社会主流的声音,更应当警惕一些媒体为了限制主流民意的表达而进行的恶意引导。最后,民意表达的渠道是否畅通且健全。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健全是民意得以理性且准确表达的重要保障,是畅通司法民主渠道的重要举措,只有表达的渠道健全且畅通了,民意表达才更准确和完整,才能更真实地反映民意的实质。
3.3 积极发挥刑事司法对民意的推动作用
民意与刑事司法具有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民意决定了刑事司法的基本制度和方向,同时,刑事司法对价值观的宣传和追求又反作用于民意,进一步推动着民意的发展。刑事司法对民意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违法犯罪的依法打击而带来的规范上的引导,这种引导作用进一步促使公众对相应的法律及其所依据的价值观的尊重和认同。因此,司法机关的裁判活动在尊重和体现民意的同时也应当充分发挥其对民意的这种促进作用,对于非理性的、恶意的、不完整的意见,予以坚决抛弃,对于理性的、善意的、积极的意见予以充分采纳和支持,积极做好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引导,维护社会价值朝着良善的方向发展。
民意与司法活动并不相违背,法律是民意表达的结果,刑事司法是依法裁判的过程,因此刑事司法本身就是民意的具体表现,是维护民意的重要手段。司法独立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民意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所以司法不能与社会脱节,既需要民意的监督,也需要民意的支持,二者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体现,程序正义以追求实体正义为目的,实体正义的实现也离不开程序正义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