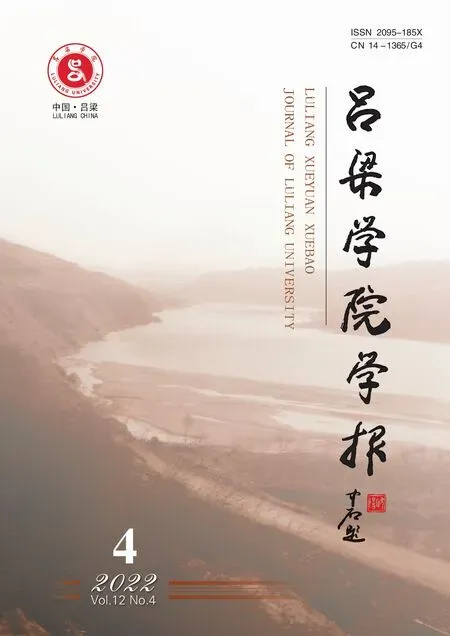孔子的“性”概念与“有教无类”
2022-03-18毕明良
毕明良
(西藏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历来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175与“有教无类”[1]168的疏解和讨论甚多,但将二者放到一起联系起来讨论却不多见,似乎觉得这二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殊不知,正是因为看不到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致对这二者的认识都产生了一定的偏差甚至错误。其实,孔子的“有教无类”表达的主要是一种人性观,而不是一般认为的普及教育理念。只有准确把握孔子的“性”概念,才能正确理解“有教无类”。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历来疏解讨论,大多都将重点放在“性”上,仿佛孔子在此处阐述的主要是一种人性理论,而实际上孔子的重点则在“习”,阐述的主要是学习的重要性,而不是人性问题。“有教无类”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含义相通,实际是从不同角度表达了相近甚至相同的意思——人与人的德性差别主要来自于后天的教育与学习,不是来自于先天。
孔子所说的“性”字是何含义?“有教无类”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孔子的“性”概念
对《论语》中的“性”字,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傅斯年“立于中途”[2]617“犹去生之本义为近”[2]510最为确当。
朱熹认为《论语》中两个“性”字含义有所不同。“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1]79“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1]175-176依程、朱的看法,“性即是理”,“性”具有本体意义,而具有本体意义的“性”则不可能有相近与不相近的问题,因此程颐说“何相近之有哉?”朱熹认为“性与天道”的“性”是本体意义上的性,而“性相近”的“性”依程颐之说则是指“气质之性”。不过,如依宋儒张载、朱熹对“气质之性”的解说,人天生所禀之“气”有清(美)浊(恶)之不同,且从清浊程度来讲,人与人之间会有极大差别,也就是说,即使是“气质之性”也很难说相近。朱熹为了弥合他的学说与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间显而易见的距离,乃以“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强为之解,显然有些牵强。
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3]1517,包括朱熹的历来注解者,大多都将阐释重点放在了“性相近”,而孔夫子要强调的则是“习相远”,是“习”的重要性。注此八字最简洁而切要者无过于孔安国“君子慎所习”[3]1522五字。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3]411从子贡的话来看,至少可以知道孔夫子在学生面前是不太谈“性”或者不太愿意谈“性”的。为什么孔子不太愿意在学生面前谈“性”呢?并非如何晏解释的“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3]414,或如朱熹所说“盖圣门教不躐等”[1]79。孔子不愿意在学生面前多谈“天道”,乃是因为“天道远,人道迩”,就教育引导学生培养德性来说,他更愿意谈切近的“人道”而不是渺远的“天道”。孔子之所以不愿意在学生面前多谈“性”——天生,乃是因为“天生”之“性”乃是人不能做主,无法决定的东西,多谈无益——无益于德性培养。孔子在学生面前更愿意谈的是人能做主,能决定的“习”。强调“学”和“习”乃孔夫子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在《论语》中随处可见。“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1]84“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1]79“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83“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178孔子后学编辑《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篇首,应该即是本着孔子的这一基本精神。孔安国用“君子慎所习”五字解“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八字,可谓深得孔子之意。
程朱从他们自己的人性理论出发,认为《论语》中这两处的“性”字含义不同,实则这两个“性”字含义完全相同,都是“天生”——“性”字的本义——之义。首先,显然孔子所说的“性”绝不可能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因为本体含义与“相近”绝不能相容,这也就是为什么程颐说“何相近之有哉”;其次,孔子所说的“性”也不具有适合于所有人的普遍意义,因为适合于所有人的普遍意义之“性”,意味着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相同的,而不仅仅是“相近”;再次,孔子所说的“性”也不具有形而上学——“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这一意义也与“相近”不能相容。孔子说“性相近”,其意思很浅显,很直白,就是说人天生下来都差不多。他要强调的也不是这一点,而是后面的“习相远”。“习相远”是说人与人的巨大差别源于后天的“习”,这是孔子所要强调的。孔安国很好地把握到了孔子所要强调的东西,所以注解“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既简洁又切要——“君子慎所习”。
从《论语》中的两个“性”字来看,孔子所说的“性”并不具有适合于所有人的普遍意义,更不具有追问“人之所以为人”的形而上学意义。孔子之前中国尚无普遍之人性观念,人们认为人因族类(1)此族类并非现如今所言的民族,更不是种族,而是以“姓”划分的氏族、宗族之意。之不同而心与德皆有所不同,此点后将详述,此不赘言。诚如傅斯年所言,“《左传》《国语》时代犹以此类别的人性论为流行的见解。”[2]603傅斯年所说的“类别的人性论”,即认为人因族类之不同而心与德皆有所不同这样的人性观念。傅斯年认为中国思想史上孔子之前是“特别论之人性说”(即人因族类等而不同),直到孟子才有“普遍论之人性”(人人相同),而孔子的人论则立于中途(2)参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617页。。这就是他为什么说“后人所谓性者,其字义自《论语》始有之,然犹去生之本义为近。至孟子,此一新义始充分发展。”[2]510“立于中途”应该来说是对于孔子人论的确当评判,而“犹去生之本义为近”则是对《论语》中两“性”字字义的确解。人天生下来都差不多,不会因为族类而有不同的心与德,人与人的差别主要来源于教育,这是孔子“性”概念的主要内容。当然,孔子也还是认为人天生下来有上智、中人与下愚之别。“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172-173“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89“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176所以孔子认为性(天生)相近,而不是人人相同。上智和下愚都属于极少数,大多数人属于“中人”。孔子正是在“中人”的意义上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此,孔子的“性”概念虽然相对于他之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语后将详解)的类别的人性观念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仍然不具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意义。当然,如与之前类别的人性观念相较,“性相近”及“有教无类”在人性论方面还是向普遍之人性观念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傅斯年说孔子的人论“立于中途”应该来说是很确当的评判。不过,傅斯年因未及见郭店楚简,认为直到孟子才有“普遍论之人性”。显然,“普遍论之人性”并非迟至孟子才提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已有非常明确的“普遍论之人性”观念。其实,《吿子》篇中的“性无善无不善”[1]328和“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1]328之“性”皆具有适合于所有人的普遍意义。提出“性无善无不善”的吿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而“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虽未知是何时何人之主张,但这一主张的提出显然不迟于孟子时代,且极有可能早于孟子的性善说。孔子的“性”概念虽然相对于他之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类别的人性观念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仍然不具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意义。孟子的“性”观念则既具有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普遍意义,又具有形而上学(人之所以为人)意义。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性”观念则介于二者之间——具有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普遍意义,但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4]136能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表明《性自命出》篇作者的“性”观念具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孔子的“相近”而已。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性相近”,再到“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我们不难看出先秦儒家“性”观念演进的痕迹。“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则可视为承自孔子的“习相远”和“有教无类”,强调的是德性差异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学习;甚至可视为上承孔子“有教无类”而直接针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观念,强调心之不同非因所生族类之不同,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如果郭店楚简中的儒家文献“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其中也包含子思一派的东西”[4]6,那么《性自命出》从时间上来说正处于从孔子到孟子的“中途”,其“性”观念也正好处于从孔子到孟子的“中途”——具有普遍意义而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这里说《性自命出》处于“中途”,绝不是对傅斯年孔子“立于中途”说的否定,反而是对傅斯年在未及见郭店楚简就能悬断孔子人论“立于中途”所展现出的犀利目光的极大肯定。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性相近”,再到“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再到孟子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性”概念,其间不仅有“性”观念清晰的演进痕迹,而且环环相扣。相对于傅斯年的论述,这里只是补充了“四海之内,其性一也”这一环而已。
二、春秋时代的“类”概念
今人一般认为“有教无类”谈的是教育对象、普及教育问题——孔子针对当时只有贵族享有受教育特权,主张所有人都应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无分贵贱,无分贫富,无分智愚,甚至无分华夏与夷狄。对“有教无类”的这种看法,是一种严重误解,而误解的根源则在于对春秋时代“类”概念的含义认识不清。
今人以人人应享有平等受教育权解孔子的“有教无类”,一方面自然是无意中受了现代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前有所承——历来对“有教无类”四字的注疏。无论“平等”还是“权利”,都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观念,因此所谓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样的观念,绝非孔子所能梦见,这一点无须赘言,需要澄清的倒是历来注疏者对“有教无类”四字的误解。
“有教无类”四字,历来的注家皆不得孔子之意,根源在误解了孔子所说的“类”。马融注曰:“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3]1450皇侃疏曰:“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5]226刑昺疏曰:“此章言教人之法也。类,谓种类。言人所在见教,无有贵贱种类也。”[6]5471马融将孔子所说“类”解为“种类”,至于他所说的“种类”是何义,并不是很清楚。从皇侃、刑昺的疏解来看,他们将孔子所说的“类”,马融所说的“种类”理解为人因贵贱、文鄙而有的差别。这样孔子的“有教无类”就是指普遍的施教,不因人的贵贱、文鄙之不同而在教育上区别对待,对所有人普遍施教则所有人都能归于善。不难看出,马融、皇侃、刑昺等人的疏解,正是前述今人如此解读“有教无类”四字的依据,或者说今人一般的解读,正是承他们的疏解而作进一步的发挥。显然,马融、皇侃、刑昺等人这样诠释“有教无类”,是将其诠释成了一种政治主张——孔子即使不是在主张一种普遍的受教育权利,也是在主张应对所有人普遍施教,而不仅仅只让贵族子弟受教育。这种诠释,如果联系到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德治”“教化”,似乎也能说得过去,而且也的确抓住了这四个字的某些重要方面,但却是基于对“类”的误读,因此不可取。
孔子所说的“类”要放到春秋时代使用这个词的背景中去理解。这个词在春秋时代指的是以“姓”划分的氏族、宗族之意。“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6]4128杜预认为史佚乃“周文王太史。”[6]4128季文子引史佚之《志》表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能是从周初一直延续到鲁成公时代的一种观念。这里的“族类”二字是何意?杜预以“与鲁异姓”[6]4128注“楚虽大,非吾族也”,以“爱也”[6]4128注“字”。鲁成公欲叛晋而与楚国交好,季文子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观念出发,认为楚国与鲁国不是同姓之国,楚人断然不会爱鲁人,以此劝阻鲁成公。鲁国之祖乃周公之子伯禽,姬姓。晋国则源于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唐叔虞,也是姬姓。鲁与晋乃同姓之国,楚则属于异姓诸侯。“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为晋侯。”[7]1635-1636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也提到了史佚这个人。依《史记》所载,史佚当为周成王时的史官。周武王在位不过十余年,因此据杜预与司马迁两人之说,史佚很有可能乃文王、武王及少年成王三代的史官。不管怎么说,史佚乃周初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乃周初观念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依杜预“与鲁异姓”之注,“非吾族”的“族”当指与姓相关的氏族、宗族,具体来说“非吾族”的意思就是“不是我们同姓(姬姓)”。如果说“族”是指与姓相关的氏族、宗族,“类”又是何意呢?“类”与“族”同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6]3910这句话是说神(祖先神)不会享用非其子孙的祭品,人也不应该祭祀非自己本族之神(祖先神)。此处“族”“类”二字同义,“族”即“类”,“类”即“族”。二字连用,构成同义复合词,其义与单字同。“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6]3976这句话与“神不歆非类”意思完全相同,“非其族类”即“非类”。
前面我们解释了 “非我族类”四字,我们再来看看“其心必异”四字,以便全面了解西周初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观念。“公子欲辞,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彭皆为纪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彭,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纪、滕、箴、任、苟、僖、姞、儇、衣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故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性。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义以道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8]333-338这段话是司空季子劝说晋公子重耳(晋文公)娶秦穆公女儿怀嬴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提到了周代的同姓不婚之制,此处的关注点则不在于此,而在“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从这句话可看出“类”与“姓”之间的紧密关系。这句话表明秦穆、晋文时期的人认为“姓”不同则“德”不同,“德”不同则“类”不同。“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这一句话表明那时候的人认为“同姓”(意味着“同类”)的人“德”相同,“心”相同,“志”相同,反过来说,异姓之人则“德”“心”“志”皆不相同,这就是周初史佚所言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可见,从周初直到鲁成公时期,并没有普遍的人性观念,有的只是人因族类而“德”不同、“心”不同这样的观念。人人有“同然”之心,仁、义、礼、智之德人人固有,四端之心人人相同,这种孟子的主张,孟子的人性观念,非孔子之前的人所能梦见。
三、结论
有了前面的这些讨论,我们才能对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背景有一认识,认识了这一背景,我们才能真正领会孔子“有教无类”说的是什么意思。孔子所说的“类”与史佚、季文子及司空季子所说的“类”含义相同,是春秋时代“族类”的含义,指的是以“姓”划分的氏族、宗族之意。孔子说“无类”是指人不因“族类”而有异,不因姓不同而“德”“心”“志”皆不相同。也就是说,孔子反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西周初以来一直流行的思想观念,反对傅斯年所说的“类别的人性论”,其“有教无类”表达的是一种人性观。作为一种人性观,“有教无类”有几层含义:其一,人与人的差别来源于教育,这一点由“有教”二字表达,与“习相远”——人与人的差别来源于后天的教育学习——相对应;其二,人与人的差别不是来源于族类,这一点由“无类”二字表达,与“性相近”——所有人天生下来都是相近的——相对应;其三,人不会因“姓”、族类之不同而“德”不同“心”不同;其四,“德”与“心”的不同源于教育(3)《性自命出》用“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明确说出这一点。,只要施教,人人都能成就善德,因此应该对所有人普遍施教。故而,孔子的“有教无类”虽然有强调对所有人普遍施教的含义,也有人人应普遍享有受教育权的含义,但其针对的实际上却是当时流行的类别的人性观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孔子“有教无类”要表达的是一种人性观念。这种人性观念接近普遍的人性观念,认为人天生下来都差不多,不会因为族类不同而有不同的心与德,且皆可以因后天教育而成就善德。因此,孔子在春秋时期宣称“有教无类”,实际上具有宣扬人性平等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