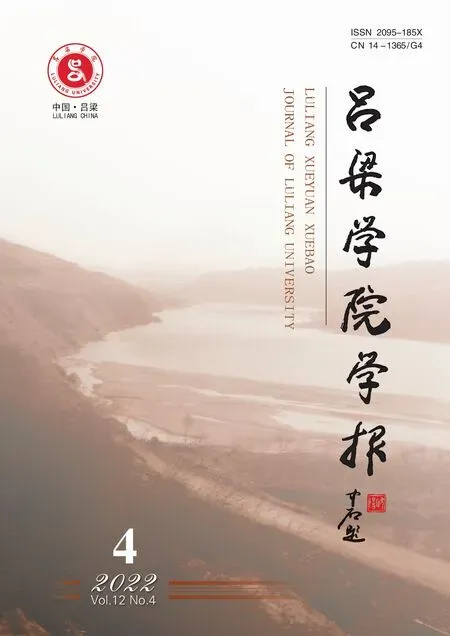哲学与问题
2022-03-18安希孟
安希孟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
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
智者问的巧,愚者问的笨。
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
——陶行知
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记忆、回顾,死记硬背,洞穴中人。知识是生活。智慧是超越。智慧是前瞻,展望、面向未来、飞天。大智慧是大怀疑,大智慧是大问题。怀疑为知识之钥匙。一个聪明人,永远会发问。稽古揆今,缺乏质疑、怀疑,是科学不昌明,技术匮乏的主因。哲学就和问题、怀疑、诘问、质询结下不解之缘。哲学乃千古司芬克斯之谜。“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为什么是奇文?因为有疑义。什么是欣赏?就是“相与析”。欣赏什么?分析疑难。孔夫子提倡“每事问”——然而毕竟不是神秘之问。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康德提出的四个问题是: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什么是人?这都是“疑义相与析”。蒙台涅的座右铭是:“我究竟知道什么?”。培根也说,假如一个人想从确定性开始,那么,他就会以怀疑告终。但是,假如他乐于从怀疑开始,那么,他就会以确定性告终。这是说怀疑的重要性。人生离不开怀疑。怀疑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
胡适名言:多研究些(具体)问题,少谈些(抽象)主义。这真是高明之见。只有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实现主义。主义产生于问题,旨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解决主义的具体办法。主义是解决问题的高度抽象。“主义”由问题产生,由问题组成。一个问题的解决,又带来新的问题。一系列问题,形成主义。胡适说:做学问的要件是问题意识、怀疑、质询。有人写不出文章,乃因为发现不了问题。问题是自我困境,没有陷入困境,不会有问题,就无从研究。
知识,中国古人叫“学问”。学习就是学会提问、学会查询、学会责难、学会质疑。在学习中,知识越多,问题也越多。学问家,就是咨询家、提问家、疑问家。作为批判精神的疑问是知识们起点,哲理的入门与途径。一切空谈之所以为空,在于它们不包含任何问题。只有提出问题才能给出方案。没有发现问题,没有惊讶,没有诧异,没有神秘,可以说是我们的代“病”。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的一生。如果我们停止追问,我们的生命即告结束。笛卡儿是欧洲哲学史上著名的怀疑哲学大师。“我思故我在”,就是“我怀疑,故我在”。在这个意义上,“我思故我在”,其实就是“我思故我问”“我问故我在”。没有审问,便没有思想,没有文章,没有人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问题、不会提问的人,能谈到自己的存在。没有思考,就没有存在。一个人存在,在于他怀疑、思索,在于他有疑难问题。他怀疑僵化学理,提倡怀疑一切,实即对任何事物都问一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何时”“何地”“何人”“何物”。然而他却遭到我们的耻笑。这不正常。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哲学乃怀疑哲学,即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识”提出质疑与询问。最厉害的打击、最深刻的思虑、最深沉的感情、最炽热的爱意、最解气的仇恨、最伤感的悲哀、最昂扬的喜悦,是反诘、质询、质疑。质疑、谴责、追咎、审问,是哲学的法官。法庭的威力和实质是质询、质证。滔滔不绝的陈述,得接受法槌的质询。进入哲学学院,你得学会发问。发出疑问、探询、质疑,这是最能引起思索的句子。最有才华、最聪慧的人,是提出问题的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唯有博学者,才能审问;唯有审问,才能慎思、明辨、笃行。
我们自幼就破解谜语。谜,就是问题。问题拉近了我们与答案的距离。距离产生探究;距离引出奥秘;距离表示亲近;距离使我们不断追求生活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把答案摆上供桌,而在于求索本身。有了问题,有了谜语,才有人生。未经省察的人生,未经发问的意见,未经破译的人生,乃没有价值。有了问题、有了思想、有了探究,生活才有意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没有求索,生活本身就没有意义。然而求索什么,我们并不了然。求索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我们说话,是道出生活之谜;我们写作,是破解生话之谜;我们做梦,也是参与生活之谜。生命是过程,是求索、追问的过程。生命之树的奥秘,在于它不断提出生活的“为什么”。提问便有了生活;破解,是生话的全部内容与构成。生活之谜比宇宙之谜还要奥秘。
我认为学哲学的人首先应当学会提问题,要求人们善于破解生存之谜。有人悍然宣布:哲学并不神秘。然而我们知道哲学乃是一种神通冥合。它通过“天问”达到天人合一。哲学有几分神秘和玄奥。哲学家应当恍焉忽焉,神兮秘兮。同样,促使科学发明创造的动机,往往也是个谜。求解谜底的种种努力,促成了科学。科学问题只有在具备解决的方案时才可能出现。只有在具备解答的条件成熟时问题才能被提出。问题和答案是社会条件科技进步的孪生子。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原因和结果同时发生。生活中处处都是谜。世界是谜一般的宫殿。我们时时接受试探和拷问。生活构成了要求我们破解的人生之谜。世界充满神奇、鬼魅与奥秘,我们当常存敬畏之心。发问,乃是表达渴求神秘之心。
哲学不是咄咄逼人的斗争。哲学不是万应灵丹宝葫芦,不提供万能钥匙破解一切疑难。它自身就是谜团。哲学不回答现实问题。它隐居隐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个问题原不是邀人回答的,而是探究最高存在、终极真理、宇宙存在的“有”“无”问题乃在表达高远志向。最深刻的问题无答案,无解之谜是最深远的谜,这是智慧而不是知识,无人可以回答或破解。广而言之,哲学问题,至高的存在,无解之谜,无定于一尊的答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里涉及宇宙根基、存在根本、时间永恒。这好像是问:大地靠谁维持才不至于沉降。古人以为大地在龟背上。然而毛泽东的提间乃是形而上学的预设。他设想有比龟背更可靠的存在基础。对哲学家而言,这问题关系到宇宙的根基所在。苍茫宇宙,浩荡乾坤,必有不以有限短暂的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法则和规律。我们生也有涯的人类怎么能主宰茫无涯际的宇宙沉浮?原诗并非要人作答,也没有做出回答,意境反而更深邃。
哲学就是询问、疑问。哲学的标志永远是“?”,而不是“。”。哲学的问题可问而不可答。对哲学问题的解答永远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智者所能提出的问题总是比一百个蠢人所能回答的还要多十倍。重新提出问题,乃是对先哲的问题的真正回答。我们若不“离经叛道”,就不要冒充先知,贸然作答,而应当以问题对问题。知识始于无知、困惑和疑难问题。科学、史学、经济、法律的研究,起源于困境、疑难、踌躇、困惑和问题。提出问题,只有在给出解决方案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时才有可能。提出问题,等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门径。问题是指示器、方向盘和路标。我们以问题的形式表达我们的惊讶和诧异。问题不止一个,对问题的选择与表达决定着探究的方向。每个问题都是一个预想的模式,对杂乱无章的惊讶加以整理,决定思考这一题目的过程。问题是一个化了妆的答案,明乎此,是起码的智慧。问题表明深渊的存在。没有问题,当然表明人生的匮乏。问题表明人意识到生存的危机;问题表明对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的寻求。基础乃是某种植根或设立的地基。丧失了基础的世界悬浮于深渊之上。生活乃是一系列的问题。生活对于哲人,不是现成的恩赐,而是一种挑战、一种邀请、一种机遇,邀他参与追问。
哲人是不安分的。哲人躁动不安。哲人的惊人之语是发问、怀疑、疑虑、哀怨、叹惋。他的询问,是天问,皓月长空,对天长叹。在一切语言句式中,最有价值的是疑问句、反问句、质问句、设问句。它引人深思,指示通向真理路标。疑问是探询,是寻索。哲人惴惴不安,不安于现状和答案。哲人无知、恍惚、踟蹰、怀疑、缄默、思虑、提问、质询、聆听、哀怨、惋惜。这是他们的主要使命。有一天,你做到上述中的一项,你就是哲人了。面对浩瀚知识汪洋,哲人惊异,哲人聆听,而非滔滔言说。哲人是童子,无知故坦诚,好奇而天真,诧异且质询,缄默以聆听。哲学日,没有哲学王国,没有哲学王子。哲学没有殿堂,没有供垫脚的哲人之石。除了巉岩攀登和林中小径,没有哲学的宽阔大道和繁华市井。除了冷清伶仃,没有哲学桂冠冕旒。
疑问句,因疑而问,哲学的怀疑态度,不是日常疑心。它是哲学的起点,探讨究竟至极原理。这并非指日常生活起疑虑重重犯疑心病(怀疑出轨,疑邻窃斧)。日常人际交往为琐事反诘、反问、设问、追究、追问、责问、审问、堂审、法棰庭审,不在此例。哲学是疑问与探究。当然,有些疑问句是修辞手法,胸有成竹,加强语气,或引起议论,是设问、反诘、肯定、坚信和反驳(难道?莫非?岂是?),并非疑问、怀疑、质询。修辞学的设问,是为了引起议论,启发思想,当然也是表示肯定,愤慨。这是明知故问,咄咄逼人的论战手法,表示肯定语气。“难道……?”,“莫非……?”“果真……?”“岂有……?”“究竟……?”,“为什么……?”,“何去何从,拭目以待”。例如“天涯何处无芳草?”处处是芳草。“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吗?”。没有!“天下谁人不识君?”无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无人。“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反问可以加强语气,激发感情,加深印象。有的是问而无答,有时是肯定句表示否定:“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有时是否定句表示肯定:“难道没有自责的地方吗?”这种反问也叫激问、反诘、诘问。“池水涟漪,莺花乱飞,谁能说它不美呢?”,无人。“宁静的竹海里难道没有人家?”,有。
有一位教授做完报告开始回答学生的提问。一个中国学生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教授说:“Yes,I know.But,what is your question?”。不会提问,没有问题,可以说我们时代的“失语症”。聪明的学生是提出问题的学生。我们应当时时警戒: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会提问题,常提问题,是好学生,不提问,无异议,不怀疑,不是好学生。
苏格拉底置人于死地的武器是质询、质疑。他不停地提问,使对方处于尴尬境地。苏格拉底并不认为可以解答一切问题。老师的答案通常是反诘。据说希腊先哲的授课方式就是对话。他像接生婆那样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引导学生“顺产”,而他又对这些问题报以问题。接生婆接生的是一个大“?”。希腊哲学乃是问答哲学,或曰“问-问”哲学,是向茫茫苍天提出的宇宙究竟至极的创世与末世问题。
威尔·杜兰特说:哲学的探险一旦产生了可用定理表达的知识,这知识便不再属于哲学了。哲学总是把她的产儿送人,自己再去提问,自己再去生育。或者说,哲学是不结果实的花。科学却是源于哲学家的疑问,而归结为功用。哲学总是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究,是“围攻真理的第一道壕堑”。哲学提出怀疑,比科学验证更困难。科学在已经被哲学探究过的领土圈地耕耘,哲学却又去提出新的疑问,开辟新的疆域。然而,哲学的无上乐趣,乃在于“怀疑之乐”。西方哲学自古就包含形而上学之问,即包含关于神的学问,属于超验范围。关于神的学问,指的是:对于神,我们可以问。超验的问题,不可说,但可问。一个有知识的人发出疑问:“什么是知识?”。明明知道,却提出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无知,而是引领思考。
古人把怀疑与学问联系在一起。程颐说:“学者先要会疑。”张载也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顾颉刚认为,对于传说,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便相信。怀疑的精神是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例如听说“腐草为萤”,就要问:死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这样一追问,虚妄学说便不攻自破。他认为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书本才是自己的书本,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尽信书不如无书”,也是指要有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便会发展起来。大学问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1]。
西谚云:“我们背会了各种可能的答案,却不知道问题是什么。”这大概是我们时代的通病:我们准备了一大堆现成答案,但忘记了问题本身。我们的习惯是不善于提问题。但提出问题恰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提出问题表明解决问题的时机已成熟。提出问题已经找到了答案的所在。一个哲学学生,应当满腹狐疑,而不是满面春风。他总在思,他总在疑——疑就是思,思的形式和内容就是疑,就是问题。他有永远解答不了的问题。我们时代许多人的痛疾在于对任何问题都不假思索、不甘寂寞地做出回答。他好像是百事通,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然而,即使是认识论的问题,也同探索诡谲问题联系在一起。
中国古代屈原的《天问》,可以说是心灵盘根问底的真正冲动。这也是哲学的开端。《天问》乃是没有答案的亘古奇问,绮丽之至,富于哲学魅力。《天问》共有174个疑难问题,并不和形而上学有关,只和宇宙天体、自然物候、民生人事有关。然而柳宗元却写了《天对》——他“替天行道”,代天做答。我始终认为,《天对》远不像《天问》那样传世和引人入胜。《天问》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提出宇宙最深邃的问题。只要人类存在,这些问题就要一直问下去。
哲学史上许多名篇巨著的题目是问句,或者是引起思考的发问。疑问、发问,包含着答案。那一定是胸有成竹。这不是明知故问,而是问题指明寻找答案的方向。问题提示答案。问题揭示、暗示、启发、指示答案,或答案的方向。能提出问题的人能先人一步找到关于问题的答案或通向答案的路径。提问是发难、挑战,激励思考、引出结论、得到答案。答案常常隐含在问题之中。问题常常包含着答案。无所不知的人,不会提问题的人,没有狐疑,布袋里装满着的答案,可惜都是垃圾。有许多哲学问题一直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哲学是无知之子”。学园派的哲学家们明智地第对任何未经证明的命题都保持缄默。没有比草率的判断更糟糕的事,也没有比不加批判地接受错误观点、或者顽固地坚持尚未充分探讨的理论更缺乏哲学家的尊严和诚实。
问题引出答案、启示答案、揭露答案、鉴定答案。问题使人思考,问题引出答案,问题使人清晰,问题使人缜密,问题使人巧慧,问题带来人生意义,问题推动历史。没有问题,便没有思考。万有引力来自于思考和问题。一篇文章,通常要满足五个要素:who,where,when,what,why。时间、地点、条件、人物,都以问题的面目出现。答案隐藏在问题里。在所有的标点符号中,逗号、句号、顿号、分号、破折号只表示停顿、转折和隔断,此外没有别的意义。只有问号、叹号、引号、省略号才具有情感意义或实在意义。问号兼具感叹、思索、追究、惊惧、情感、质询和疑问的意义。它当然也具有停顿、提示的作用。问题并不仅仅表明无知和怀疑。问题表示一种态度、一种寻求、一种挑战、一种希冀和愿景。
赫胥黎说:关于人的问题,是其它一切问题的基础,比其余问题更有兴味。它决定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乃是由人会发问、会思考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类能提供丰富而正确的答案决定的。按赫胥黎:世人常提出的能给人无穷兴味的问题乃是:人类从何而来?人的界限和大自然的界限何在[2]65?人类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又是一连串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能表达的解答来说,人们也不能把问题表达出来。这种谜是不存在的。如果一般地能把问题提出,则也能对它加以解答。……只有在有答案的地方才有问题,而这只有在有某种可以说的事情的地方才有。”[3]19-20他又说:“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这是自己表明出来的。”这东西应当包括人的存在及人的问题。在我看来,人的问题不可用逻辑与科学语言言说,但并非不可提问,并非不可思议。人的问题是自己显现出来的。维特根斯坦说,凡是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为思维划定一个界限,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一个界限”,“为可思的东西划界限,从而也为不可思的东西划界限”[3]20。不可思的、不能言说的、无含义的包括形而上学主体、“神秘的事物”。对于不可言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但它们引人沉思冥想,并非毫无疑义。大智慧是沉默寡言不落言筌不搞争论。庄子的理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
难道哲学真的不是向内求心而是向外问天(“天问”即“问天”)吗?我以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乃是反躬自问:“人是谁?”“人是什么?”。“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镌刻的神谕,苏格拉底很赞同这句话中所内含的精神,认为哲学就是要“认识你自己”,并以此把哲学拉回人间。哲学关乎人自身,而不是关乎昊天。真哲学不是“天问”,而乃“人问”,即“问人”、自问。你不可能期望从别人或宇宙得到答案。哲学的根本问题因而就是“人是谁?”,“人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真正回答是:“我是谁?”,“我是什么?”。这种反躬自省,乃构成一种沉思默念,一种玄览静观,一种忏悔反思。然而,“我是谁?”与“人是什么?”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希腊哲学通过亚里士多德问:“人是什么?”,然而印度吠檀多哲学和禅宗却提出:“我是谁?”。问题的提法制约了答案。“人是什么?”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我是谁?”则不是认识论问题,因为你不能把自己当作对象和客体。它不是一个理性问题,没有合理的答案,有时反到荒诞不经。
“人是谁?”“我是谁?”,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哲学家的根本问题“根本”不是“科学是什么?”。古人云:“知人则哲”。如果要问“科学是什么?”,那也只能先提问:“科学对人而言是什么?”。然而,这又回到了“人是谁?”的问题。“我是谁?”的问题是关系到我自身及我的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夜阑人静、扪心自问时才临到我的。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的繁华闹市,你想不到这个问题,因为那时,你不是“我”自己,你是他人,你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个样品。当提出“我是谁?”这个问题时,人陷入两难境地:他既是发问者,也是被问者(注意:不是回答者)。他拷问自己。这个问题引来的是一个新的问题,而不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