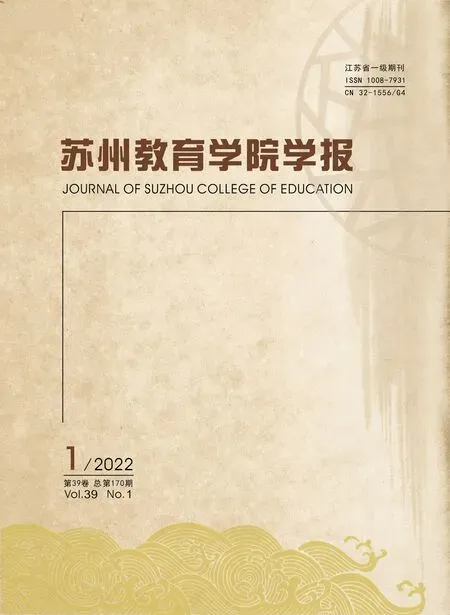革命小说《风雨桐江》的通俗化书写
2022-03-18张丝涵
张丝涵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革命题材小说《风雨桐江》[1]出版于1964 年,作者为司马文森(1916——1968)。据司马文森友人秦瘦鸥所述,司马文森约从1956 年开始创作该小说:“1956 年以后,他主要担任对外文化联络工作,但还在百忙中不断写稿,长篇小说《风雨桐江》就是在那个时期里陆续积累,而于1964 年初脱稿的。”[2]123小说讲述了1935 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北上长征后,共产党于闽南地区领导侨乡人民坚持地下工作与农村武装斗争的故事。作为一部出版于1960 年代的革命小说,《风雨桐江》的革命叙事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的传统革命题材小说,有其特殊性,却并未在以往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将从人物塑造、文学书写与情节设置等方面出发,探究《风雨桐江》所具有的通俗文学特质,及其背后所涉及的革命题材小说通俗化问题。
一、革命队伍中的“才子佳人”
《风雨桐江》中身份最为特殊的人物形象,无疑是两位负责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党员——大林和蔡玉华。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小说中,主人公大多为生存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或工人,他们往往来自贫苦家庭或革命世家,“根正苗红”的家族谱系赋予了他们一种天然的正当性,他们在黑暗社会中的受害者身份使革命道路成为了他们人生的必然走向。但在《风雨桐江》中,作为一开篇就出现的重要人物,大林和蔡玉华却并没有这样正统的革命家世。蔡玉华出身于进士家庭,“从小追随父亲,熟读诗书,玩弄文墨,却也沾染她父亲高傲自负的旧知识分子习气”[1]20,她的伯父则是监察院委员,完全属于社会上层。蔡玉华自己也读过大学,容貌出众,知书达理,堪称才女。大林虽出身于石匠家庭,父辈饱受压迫,但他本人则是一名成绩优异、心怀抱负、年轻有为的大学生。一位是出身高贵、才貌双全的“佳人”,一位是虽出身贫寒却能力超群的“才子”,蔡玉华与大林的结合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革命题材小说,反而极具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意味。
张清华在分析中国文学中的才子佳人模式时指出,“才子”们的价值取向一般分为两类,要么抱着“胸怀天下积极取仕的态度,将至高的社会理想与至美的人生追求溶为一体”,要么“返身自然,让他们的非凡才情与壮美的自然和充满浪漫情调的性爱生活溶汇在一起”。[3]而《风雨桐江》则将才子佳人模式中所蕴含的这种传统知识分子式的志趣替换为大林与蔡玉华的坚定的革命理想,由此完成了才子佳人模式与革命话语之间的融合。在大林与蔡玉华因投身革命而不断经受磨练的过程中,两人之间浪漫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恋也得以在革命叙事中取得正当性。在大林与蔡玉华这对“才子佳人”的爱情中,还暗含着另一必须解决的问题,即他们两人,尤其是蔡玉华的阶级属性问题。在同时期其他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革命小说中,知识青年们往往需要通过与自身所处的阶级彻底决裂来完成其向革命者的转变。譬如在杨沫所著的革命小说《青春之歌》中,革命青年罗大方便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永远断绝联系,而主人公林道静也必须背叛自己地主阶级的父亲林伯唐和小资产阶级的丈夫余永泽,才能真正加入革命队伍。[4]张清华在分析《青春之歌》时曾指出,林道静与胡适信徒余永泽、革命青年卢嘉川的爱恋,分别是“才子佳人”式与“英雄美人”式的故事,且后者的出现是因为“英雄美人比才子佳人更容易‘改装’为革命叙事”。[5]可见《青春之歌》虽然借用了才子佳人的通俗小说模式,但在剧情的进一步发展中,小说仍然需要舍弃“才子佳人”的浪漫幻想,以完成与无产阶级革命叙事的统一。
在《风雨桐江》中,蔡玉华始终没有主动与自己兼具封建性与资产阶级性的家庭断绝关系。在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的同时,她与大林仍然享受着由蔡家提供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甚至大林还因颇得蔡监察的赏识而成为其私人秘书。直到蔡监察得知两人的真实身份后,他们才与蔡家关系破裂。可以说,大林与蔡玉华最终是被动地被掌握权力的资产阶级所抛弃的。由此可见,小说对大林与蔡玉华的阶级属性问题的处理方式与其他革命小说有所不同。大林与蔡玉华并未通过舍弃“才子佳人”的身份、宣告与敌对阶级决裂的常见方式,直接达成与意识形态的统一,而是以另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二人身份的合理化,这一特殊的方式得益于“革命的地下工作”这一题材的暧昧性。想要深入开展地下工作,就必须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敌人信任,因此无论是大林为了取得更多情报而成为蔡监察的私人秘书,还是他借助于蔡玉华居住的“进士第”所意味的特权阶级身份来保护自己,都可以被宽恕和理解。蔡玉华在大林被捕后主动求助于蔡监察的行为,也因以保护重要地下工作者为目的而变得情有可原。与此同时,地下工作本身的危险性与传奇性,也有利于小说内容向着更为丰富曲折的通俗化方向发展。而司马文森作为曾经的地下工作参与者,在创作中选取了这样一个特殊题材,或许也有其个人经历与叙事策略两方面的考量。
在地下工作隐蔽性的要求下,大林与蔡玉华的身份问题被暂时搁置。但作为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蔡玉华终究还是要经历痛苦的蜕变才能真正为革命叙事所接纳。在爱人大林被捕入狱、生死不明之后,蔡玉华终于迎来了她的考验:其一是她怀有身孕却被国民党抓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又被吴启超囚禁;其二是她安全抵达游击队驻地后担任了政治教学工作。前者是对她的革命信仰的再次确认,后者对她来说则是一次同时来自外部与内部的思想改造与磨砺。她通过游击队员的态度与老黄的建议认识到了自己脱离群众的思想错误,并在自我反思中不断进步,最终与游击队员打成一片。在这样的重重考验中,蔡玉华最终完成了由名门闺秀到革命战士的蜕变。在小说的结尾,“蔡玉华已不再是娇柔脆弱的小姐,而是一个面孔黝黑,身体强壮,行动机敏,敢作敢为的战士,她像颗刚出土的钻石,斗争把她磨出了光辉”[1]539,从娇柔的“小姐”到身强体健的“战士”,蔡玉华以自己的身体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对她的成功改造。通俗文学作品中引发人们美好想象的“佳人”形象,也由此被内化为论证“革命终将胜利”这一坚定信念的革命叙事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蔡玉华的成长历程和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主人公相比,仍然是特殊的。王斑曾分析电影《青春之歌》中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他们站在历史的外面,从一个无名小卒成长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并获得由革命历史规定的政治身份,即历史的主体。”[6]这一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小说《青春之歌》,知识分子林道静一开始身处革命之外,在卢嘉川、江华等革命青年的领导下,才逐渐完成了由旁观者到参与者,由革命队伍之外到革命队伍之内的成长。与林道静不同的是,蔡玉华的成长是发生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她与大林的党员身份在小说开篇就已明确,因此,她并不需要通过一场痛苦的决裂来获得革命队伍的准入证,她对自身错误思想的反思也仅仅是革命队伍内部的一次温和的纠偏。她的成长甚至与革命工作的发展同步——一开始玉华与大林居于城镇,后来玉华来到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空间的转换同时也代表了革命工作的重心不断向农村转移,而小说中故事的发生时间又恰恰在刚举行过遵义会议的1935 年春天。这体现了《风雨桐江》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与成长问题持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除了与旧有身份完全决裂、以“新人”的面貌加入革命队伍之外,“才子佳人”们也可能在革命队伍内部不断反思与完善自我。他们不断改造自身的过程可以与革命的历程相协同,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具有主体性的革命亲历者。
小说中除大林、蔡玉华外,还有另一“才子”形象也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同属于革命队伍的黄洛夫。作为一个浪漫多情的诗人,黄洛夫虽忠于革命,但问题同样不少。他不仅被吴启超迷惑而逃离学校,对劳动人民也抱有成见,“认为干文化工作就得由像他这样的人来干”[1]302,而且,相较于蔡玉华,黄洛夫的成长并非那么明显。作者似乎对这位诗人格外宽容,不仅保留了他身上的豪情与才气,还在小说最末特意让他作诗一首,恣意奔放地歌颂祖国与革命。但黄洛夫的浪漫也仍然要被革命话语收编,在小说中,他与质朴的渔家女孩阿玉相爱结婚,并在与顺娘、阿玉等群众相处的过程中纠正了自己过往的许多错误认识。“才子”的浪漫情怀与革命话语的要求最终达成了统一,而其达成的方式与玉华的成长一样,是温和的,是与革命发展的历程共生的。
通过蔡玉华、大林和黄洛夫这三个人物形象,可以看出《风雨桐江》在秉持以革命为纲领、以群众为主体的政治立场的同时,又以独特的叙事策略将才子佳人式的浪漫爱情写入了革命叙事,并将其中所包含的身份问题巧妙地合理化,叙述了几位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转变。通俗小说中引人入胜的爱情故事与革命小说所坚持的政治话语由此达成了融合,其中反映出的是《风雨桐江》作为革命题材小说对于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身份改造问题的特殊理解。
二、情与性的大胆书写
关于爱情与性的叙述,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中相对较少,即便偶然出现,也大多含蓄委婉,且基本服务于小说的政治主题,个人情感与革命主旨往往在文本中彼此交织。陈顺馨也由此指出,“五六十年代大多的小说中,英雄人物的爱情必然是为革命服务的”[7],如萧也牧的《秋葵》中对于“我”与农村姑娘秋葵的暧昧情感的叙述,以及《青春万岁》中关于杨蔷云暗恋张世群的描写等,都将青年的爱情刻画得单纯、天真,而很少涉及爱情中更为激烈甚至接近于性的部分,且主人公的爱恋往往与更为崇高的革命情谊和远大志向紧密相连。《青春之歌》中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则更为鲜明,女主人公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坚定的革命青年的转变,完全与其三段爱情经历相同步。
相比之下,《风雨桐江》中有关情与性的书写则更为大胆,这首先体现在小说直白的爱情书写中。除了蔡玉华与大林知识分子式的浪漫情感,小说还刻画了蔡老六与玉蒜、许三多与苦茶等底层民众质朴真诚的爱情,以及前文提到的黄洛夫与阿玉这样的知识分子与渔家女的结合。小说以热烈的笔调表现了这一对对恋人之间浓烈真挚的情感,在大林与蔡玉华久别重逢时,作者写道大林“把她从书台上拉了起来就是几个热吻”[1]115;在黄洛夫与阿玉正式结为夫妻的那一晚,“黄洛夫紧紧地把她抱住,直在那儿亲她……阿玉让黄洛夫什么地方都亲过,头发,眼睛,嘴唇”[1]444,年轻恋人之间激烈热切的爱恋由此跃然纸上。
但作为一部革命小说,《风雨桐江》中多数的爱情书写仍然与其政治主题密不可分。如蔡老六之所以改变对被强奸的玉蒜和私生女红缎的态度,是因为共产党员陈鸿开导并要求他“把她们也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1]103。而他最终对玉蒜恢复感情,是因为玉蒜向他表达了自己的进步要求:“我看你同许多人在谈,谈革命的道理,我也很想听听,知道知道,你却不找我谈。”[1]111听到玉蒜这样的表白后,蔡老六才真正将玉蒜视为爱人,同时也是革命的同志,两人之间情感的转变基本围绕着党和革命的主题而展开。
《风雨桐江》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上述政治与爱情相统一的书写外,它依旧保留了部分抛开意识形态、纯粹描写男女之情的片段。如苦茶和许三多一同在青霞寺过夜,她真挚地向许三多诉说了自己对他的感情:“我不愿意,我还一心一意地在等,我等你,等你一句话,一个知心的表示。我只有一个想头,一颗心,我相信你,相信你会。”[1]240许三多在听过苦茶的哭诉后终于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给了她一个热烈的拥抱。小说中关于青霞寺这一夜的描述,紧紧围绕着许三多与苦茶两人的心理活动与语言对话展开,叙述的完全是他们矛盾纠结的情感。革命话语在此时消失,只剩下相爱之人真切的情感在文本中激荡。仅仅在这一部分的末尾处,作者才略显突兀地将许三多的思绪由对苦茶的复杂感情拉回到有关革命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的想象。同样,在许三多与苦茶的新婚之夜,作者也着重描写了苦茶内心由于许三多屡次离开而产生的委屈,她神情悲苦,一会儿怀疑“难道他的心中人不是我”,一会儿又想质问许三多“为什么在这样大喜日子,这样地冷冰冰”。[1]275-276女性敏感柔软的心思在此处被描摹得淋漓尽致,引发读者共鸣,这是无关革命理想与地下工作而独属于个人爱情的心理描写。许三多和苦茶的婚礼是全村的喜事,有扮作“叫化子”的人们按照风俗跳起欢庆的“拍胸舞”,“这样跳着,唱着,一段过去了又来一段,有人把双腋、胸脯、大腿拍红了,嗓子唱哑了,跳出人圈又补进一个,跟着唱,跳。一直闹到深夜”[1]279。两人的婚礼如同一场盛大的狂欢,一直闹到清晨才结束。同样的“拍胸舞”在小许与杏花成婚时再次上演,这样朴素而热闹的庆祝仪式,呈现的正是普通农民在革命之外的日常生活。
当老黄初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听到的小林与阿玉之间对唱的“褒歌”,也同样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无论是小林唱的“你我相爱是应该,别人闲言不理睬”[1]39,还是阿玉唱的“出出入入都相见,胜过牛郎织女星”[1]39,都是乡间人民对男女爱情率真的歌颂。在小说浓烈的生活气息中,作者叙述的已不仅是革命的进展与胜利,更是当地人民质朴纯真的生活图景。真挚的男女情爱与热烈的日常生活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独立于小说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丰富了小说本身的文化意涵与通俗色彩。
另外,小说对反面人物的性书写也极为大胆。如蔡老六的父亲老鬼曾奸污自己的儿媳玉蒜,并使其产下私生女红缎。共产党的叛徒陈聪与革命者沈渊之妻玉叶有着越轨的关系。小说中的另一个叛徒银花也被塑造为一个风流善妒的形象,她起初暗恋许三多,之后又勾引学校老师小许,“故意拿她发育得特别饱实的胸膛去碰他”[1]265,她最终落入国民党手中,在威吓之中叛变,自己也沦为他人的玩物。对于国民党蓝衣大队的骨干吴启超,小说亦通过描写他囚禁、凌虐被唤作“小东西”的女孩,刻画了他的变态癖好。土匪许天雄之女许大姑在许大头口中是一个极度放荡的女子:“身边那几个人谁不和她胡搞过,她要的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要年青的小白面。”[1]471虽然以上描写的主要目的是从情欲角度塑造反面人物淫秽不堪的形象,但能够在革命叙事中如此直接、频繁地描绘人物不同寻常的情感与欲望,这本就是《风雨桐江》在革命题材小说通俗化书写过程中极具冲击力的探索。
司马文森在《风雨桐江》中对情与性的直白描绘有其超越常规革命叙事、书写人性本真情爱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文森的笔下,书写热烈爱情的革命作品并不少见,对男女情爱的赞颂是他颇具自觉意识的一种尝试。他创作于1941 年至1942 年的长篇小说《雨季》所写的便是与爱情相关的革命故事。据司马文森自述,他意识到了当时“在我们的文坛上的确是充满了‘冲’‘杀’等类的英雄史诗,所谓‘恋爱’故事,也许会使人认为与‘抗战无关’”,但最终还是因为“我的故事诱惑了我,我的故事中的人物诱惑了我,而冲杀等类的作品,也已使我感到厌倦了”。[2]231他出版于1942 年的小说《希望》与出版于1950 年的小说《折翼鸟》也同样将革命与青年的爱情相联系。其中《折翼鸟》更是“把一个年轻寡妇不堪寂寞,大胆追求新的爱情的热烈神态心情,写得哀婉动人,传神逼真”[2]376。情与性的书写是通俗小说中常见的话题,却也是许多革命小说常常弱化或崇高化的部分。司马文森在革命文学作品中对爱情的书写大胆而直接,在革命话语之中难能可贵地保留了对纯粹爱情的描写,这不仅体现了司马文森在坚持意识形态的同时,对描写自然人性与生活的创作追求,还体现了其对革命文学的丰富性与通俗性有意识的探索。
三、勾心斗角的反革命形象
《风雨桐江》对国民党军官、地主乡绅等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同样别具一格。小说没有一味地贬低这些革命斗争中的“阶级敌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这些人物的智慧才能。如小说开篇便出场的国民党官员周维国,是“蒋介石派赴法西斯德国受训的少壮军官之一……学成返国,升迁极快,从上校而准将而少将,一帆风顺,即使蒋系军官前辈,也为之侧目”[1]8。他手下的吴启超伪装成支持共产主义的文人的计谋也骗过了黄洛夫,并差点抓到了黄洛夫。国民党特派员林雄模则更具政治才干,他不仅四处搜集材料,进行实地调查,准确判断整体局势,还敏锐地找到了陈聪这一共产党内部的突破口,成功接近他并诱使其叛变。另外,他还拉拢利用了知道不少内情的万歪,更从许德笙那里打探得知了土匪许天雄的要害,其手腕高超、能力强悍,对共产党造成了不小的挑战。在中了“打狗队”的计策后,临死前的林雄模更是宛若一个即将光荣牺牲的“英雄”:“那林雄模已伤重流血过多,说不出话来,只指了指那只大皮包,用低到不能再低的声音说:‘一定要按我写的做……’便闭目断气。”[1]454在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中,如此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国民党军官形象是极为少见的。
也正是由于小说没有绝对化地贬斥反面人物形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他们的能力和才干,小说的情节才得以一波三折,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智斗勇中呈现出丰富的矛盾冲突与文学张力。同时,反面人物形象的机敏也导致了“反革命队伍”内部的彼此算计与利用。以周维国和林雄模为代表的国民党、以许天雄为首的土匪、以许为民为代表的地主和在多方势力中摇摆得利的万歪,这些不同势力之间时而合作、时而敌对的复杂关系,使小说的情节展开更为跌宕起伏。而共产党作为革命力量,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这多方势力中的一支。如土匪许大姑与共产党方面的许三多讲和时,两人都怀着利用对方的目的。由此可见,《风雨桐江》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其将地主、土匪武装之间的“内部矛盾”与他们和农民武装之间的“阶级矛盾”放置在一起,刻画其中错综复杂的氏族、宗派、政治力量的反复缠斗与较量。相较于一般革命小说中“敌我”二元对立的简单关系,《风雨桐江》中至少包含了四方势力的彼此纠缠,并由此展现出了具有通俗性与传奇性的革命故事。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文森在小说中对土匪势力的处理。土匪是革命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一类群体。正如蔡翔所指出的,“革命通俗文学”中的土匪形象往往分为两类:一类为负面的恶霸形象;另一类则为相对正面的英雄好汉,其中对于后者的刻画,常常在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强化了他们身上或者行为的‘阶级反抗’的特征”[8],由此产生了一群可以为革命所改造与领导的“英雄”式的土匪。相较于这种较为二元化的叙事模式,《风雨桐江》中的土匪形象则更为复杂。以许天雄为首的土匪势力始终没有被革命队伍收编,而是在自身的内斗中走向灭亡。他们不具有“阶级反抗”的属性,是一群凶残暴力、自私自利的暴徒。但他们的形象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在某些时刻,他们又对共产党方面抱有同情与敬佩的暧昧情感。他们拥有一种既不归属于国民党或地主阶级,又不服从于革命力量的独立性,他们作出的种种决策完全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这使他们成为了小说多方力量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也导致他们无法被阶级叙事完全收编与定义。与一般革命小说中的“英雄”土匪相比,他们更像是一群常见于通俗演义中、游荡于政治力量之外的“枭雄”。
《风雨桐江》中土匪形象的复杂性尤其集中于许大姑身上。作为少见的女性土匪,许大姑将土匪的正反两面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性格中有极为负面的一面,除了前文提及的荒淫无度外,她还桀骜不驯,“发誓不嫁人,却喜欢骑马打枪,平时剪男人头,穿男人衣”[1]58;她又骄傲自负,不把许大头放在眼里,并且心狠手辣,随随便便就枪杀了许大头虏来的“四大天王”。与此同时,她又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仗义与直爽。她与许三多讲和时的坦诚爽快,让许三多觉得她有丈夫气概,而三福也称“人人都在夸许大姑,看来名不虚传”[1]380。在立场上,她主张与共产党许三多讲和结盟。她照顾许三多的部下,借给许三多子弹,也说明她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自己与共产党之间的同盟关系,虽然这种认同并不来自于其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的一致,而是出于对双方利益与血缘关系的考量。或许也正因为许大姑这一形象承载了这样正反两面的复杂性,她的结局必然以悲剧收场,她与许三多讲和的愿望也注定无法实现,否则这一形象的存在便难以被革命话语所接纳与规约。但从司马文森对这一女性形象不无欣赏的刻画中,已经可以鲜明地发现其超脱革命意识形态的迹象。事实上,如果褪去“土匪”这一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较为固化的身份,许大姑是一个极为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她豪爽直率、骑马打枪的一面,还是她淫荡放纵、目中无人的一面,都极大地冲击了当时文学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描绘与想象。通过许大姑这一形象,不难看出《风雨桐江》所具备的某种常见于通俗小说中的传奇色彩,也更能理解《风雨桐江》处理土匪形象的特殊之处。
《风雨桐江》对反面人物形象的刻画及其对革命过程中多方力量相互较量的叙述,显然不同于一般革命小说一味贬斥阶级敌人的做法,而是通过发掘人物内在的矛盾性与丰富性,描绘不同人物和不同势力之间复杂的关系,使小说情节更生动。这样的叙事或许并非完全是“革命”的,却是精彩的。这种充满张力、扣人心弦的故事性与传奇性,正是通俗小说一贯追求的,也是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由此可见,《风雨桐江》在革命叙事之中,隐含着与通俗文学相通的强调故事性、曲折性与传奇性的取向。而且,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革命文学作品,《风雨桐江》在处理这种取向时有着更为大胆的对于意识形态与革命话语的突破。
需要补充的是,司马文森是颇有资历的革命者,同时也是闽南地区革命工作的重要参与者。他在15 岁时就加入了“互济会”;16 岁时任共青团泉州特支委员;17 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8 岁时,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员,由于中共泉州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而转往上海。[2]14-16因此,《风雨桐江》所描写的波澜起伏的革命历程,不仅蕴藏着一种将革命文学通俗化的力量,还能为后来者探究革命历史的真相提供一种特殊的视角。
四、结语
《风雨桐江》出版后不久,便在“文革”中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一部典型的、专门歌颂错误路线的大毒草”[9]。司马文森也于1968 年含冤离世。“文革”结束后,该小说于1983 年重新出版。作为一部与同时期其他革命题材小说有着鲜明差异的作品,《风雨桐江》并未完全囿于革命政治的框架,而是在革命叙事之中蕴藏着强烈的通俗文学特质,以极具传奇色彩的笔调讲述了一个风云变幻的精彩故事,呈现出引人入胜的独特魅力。然而,这部小说的价值在当代文学史中却并未被充分发现。或许由于其内容情节仍主要围绕革命展开,或许由于在“文革”时期它遭到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严厉批判,在“文革”结束后关于《风雨桐江》的解读仍然更侧重其中有关政治与革命的方面,而相对忽视了其超出革命范畴的其他价值。1988 年改编自《风雨桐江》的电影《欢乐英雄》《阴阳界》上映后,人们也更多地将这部原著归类为“简单地从阶级性出发去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10]的作品,并盛赞电影对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与阶级叙事的摒弃和超越。包括司马文森之女司马小加也认为,这部小说的局限性在于“政治面目鲜明的人们,在谁也无法跨越的‘阶级斗争’雷池内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11]。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当时好评如潮,但《风雨桐江》却并未因此得以“复活”,其沉寂于革命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表层主题下的更多特殊之处,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