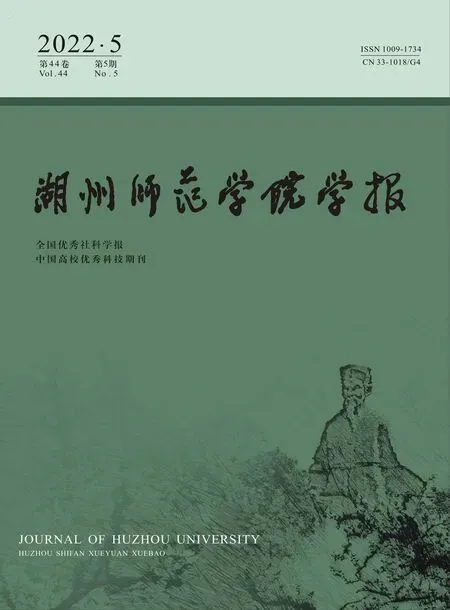权利与监管:客籍化背景下清代官员的管理制度*
——以汉员文职为例
2022-03-18周向阳
周向阳
(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君主只能依靠官员这一媒介来管理国家与子民。为了政权安全和行政的严明、公正、廉洁,国家推行官员任职回避制度,对官吏铨选、作用和执行职务过程制定了系列限制性规范,以避免因某些社会关系网络给官员的行政行为实施带来不必要的干扰[1]29-37。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私人关系、重视亲情与乡情,故历代在吏治行政方面,对防范血缘、地缘关系,最为显著[2]281。官员任职籍贯回避制度也因此产生。此制发韧于东汉桓帝时期的“三互法”①《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此后,历代或多或少遵循沿用。到清代,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皇权绝对专制,官僚机构膨胀,再加上其少数民族政权的性质,因此,清朝更加严格了对官员的管理。不仅继承了历代回避制度,并将之空前严密化。而对于官员任职地方的禁限,亦更周详缜密②关于清代任职回避制度,前人已经有非常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具体可参见魏秀梅:《清代之回避制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张建伟:《论清前期官员的任职地方回避制度》,《满族研究》2003年第2期,第29-37页。。
任职籍贯回避制度意味着读书人一旦为官,便须“避籍”,即要拿着身份证明,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另外,为防范官员因久于一职一地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朝廷在人事制度上也不令官员久任,取而代之以任期制。官员一般三年一个俸期,某些时候经考核本应升迁,但因百姓请求亦可连任,而连任也不是无限期的。任期制使官员频繁调动,旨在保持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这样,官员在全国各地任职奔走,几无安定之时,以致古时人们把出外为官称为“宦游”。
关于清代官员的生存状态和管理制度,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不过,以往的研究多从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角度展开,考察官僚管理制度的内容、特征,并论证其合理性。在研究者眼中,官员只是帝国控制的工具,很少有人会关注到官员的客籍这一特殊的身份,既没有把他们当作有血有肉、有家庭亲情需要的活生生的人,也没有考虑到在国家强制力下,被迫飘零羁旅的他们有何权利,如何来安放自己的人生,如何满足自己的情感,如何尽到赡养父母、抚养后代、扶养亲人的责任和义务。本文试图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为中心,以清代汉员文职为例,对此进行梳理和探讨。权利是一个法学概念,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认定及保障。虽然法学属于晚近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它所指代的内容就只能出现在法学诞生以后。清朝是帝制,权利的概念虽然并未产生,但并不是说,当时人们就不会享有一定的权利。所以,在这里姑且用后来的名称去称呼它在历史上的面孔。如此,既可了解身在异乡的官员的生存实像,又可为深入理解大清帝国客民控制与管理制度提供一个重要且有趣的途径。
一、官员的路费:经济扶助与监管
(一)赴任预支路费与借债限制
清代官员赴任,朝廷并不给予旅费补贴,且赴任时不得使用朝廷的驿馆系统,只有赴任里程在1 500里以上,才可以由驿馆提供脚力;赴云南、贵州、四川、陕西边远地区的州县官,才可以由驿馆提供交通工具(陆路驴车一辆、水路红船一艘),但仍旧不得由驿馆提供伙食。因此,长途跋涉的旅费官员们要自己设法筹措[3]54-55。而这笔费用显然不低。其一,路途遥远。帝国幅员辽阔,官员们的赴任地点离家距离通常非常遥远,“赴任之人,动数千里”[4]卷8《选补》。跋涉之劳,“近者或至旬日,远者不止于旬时”[5]2243。有时,赴任的距离更加遥远:“以极南之人遇极北缺。极西之人遇极东缺。路途甚有在七八千里外者。”[6]630其二,人员众多。官员赴任,并非一人,一般会携带家人随从,“纵令妻子眷数至少,亦且不下八九口、十余口人,况等而上之,自二十口以至三十口者往往有之”[6]630。如此,舟车、驴马、人夫之费甚巨。这就意味着官员除授官之后需要不菲的应酬交际费用外,还要自己设法筹措较大数额的赴任费用。
官员们为此费尽了心力,“非斥产即揭债”[7]26。甚至一些官员去借高利贷——京债。京债始于唐朝,是中央政府新任命的外省官吏离京上任前,为贿赂当局及置办行装、筹措旅费、应付官场等费用而向人举借的款项。据《唐会要》卷92载:会昌元年,“选人官成后,皆于城中举债”。自唐以后,举借京债成为官场一种常见的借贷形式。京债利息极高,清人赵翼记载:“至近代京债之例,富人挟资住京师,遇月选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远近,缺之丰啬,或七八十两作百两,谓之扣头,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8]300如此一来,读书人“甫入仕途,而有满身之债负”,“不但科贡从寒士出身为然,即荫生捐纳,亦往往一赴远任,即债累满身矣”[6]630。官员到任之后,为清偿债务,只好加倍搜刮民财。有时,债主还随官员赴任所,肆意逼偿,甚至逼毙官吏。
官员路费筹措的艰难以及举债带来的严重后果,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为体恤官员资斧缺乏之艰,朝廷特别允许官员出京赴任可预借养廉路费,以免“借给重利之累”。具体规定为:外任官于引见得缺之后,“准于户部具呈预支,酌量道路之远近以定多寡,知照该上司,于该员到任后扣除归款,不愿者听”;借款之人,一是月选官由京赴任,二是佐杂微员在籍候选;至于借款之数量,则视路程远近、官阶高低而定。如江西、浙江、湖北、江苏、安徽、陕西等六省,道府借银七百两,州县三百两,同知通判二百五十两,州同州判一百两,在部领凭佐杂官四十两。云南、贵州两省,离京最远,所借银数稍多。赴任云南,道府借银一千两,州县六百两,同知通判四百两,州同州判二百两,在部领凭佐杂官六十两。当然,所借银两,都须于到任后抵扣。但有些官员“既借官项,复借多金,俾市侩随任索取”,这就引起乾隆皇帝的不满,因此,乾隆二十七年(1762)乃下令停止该项制度,不过,第二年,又马上恢复[9]216-221。
在给予官员经济帮助的同时,朝廷又严格规范官员之借债,特别禁止债主随官员赴任所追债。《大清律例》规定:“凡听选官吏、监生人等借债,与债主及保人同赴任所取偿,至五十两以上者,借者革职,债主及保人各枷号一个月发落,债追入官。”[10]264
然而,朝廷预支的费用数量有限,根本不能满足赴任官员的开支。官员借高利贷赴任的现象并未消除。清朝中期小说《歧路灯》第84回里描述:“说起这一官利债,三个月一滚算,作官的都是求之不得,还要央人拉纤的。犯了原要过刑部治罪,其实犯的少,拉的多,……若不拉,怎治得行头?讨得美妾?无非到任以后,侵帑克民,好填这个坑。”[11]第84回故事虽是小说家之编造,但小说往往是社会现实的缩写。而且,也不乏现实案例为之注脚。乾隆四十八年(1783),山西发生一起折扣放债逼死职官的案件:贵州举人张有蕴,经会试后挑发山西,路费无措,在京向商人马廷璧借得四扣三分利银七百两,实银二百八十两使用。嗣后,马廷璧赴晋追债,张有蕴实在没有办法,找太谷县人武凝寓借用九扣三分银二百七十两,偿还马廷璧部分利银。之后张有蕴署任灵丘知县,马、武二人闻讯相继赶到逼债,张有蕴“因负欠累累愁急自缢”。[12]373乾隆五十年(1785),山西又发生民人刘姓等重扣放债索欠逼毙黄陂县典史任朝恩一案,连皇帝都深受震动。乾隆皇帝一面降旨将刘姓等严究办理,痛斥京债“尤出于情理之外”、举债官员不知自爱,一面又强调朝廷之禁罚[13]281。
(二)微员支给还乡路费及限制
除了赴任可以预支路费外,基层官吏还乡遇到困难时,也可以申领一定的经费。乾隆三年(1738)议定:“各省文职县丞、主簿、巡检、典史等微员,倘有离任、身故,实系穷苦不能回籍者,除参革人员,有贪劣重款,系有罪之人不得滥行给予路费外,其余虽经参革而无劣迹,及丁忧、解任、告病、身故者,该地方官各就本省情形,按照该员家口多寡,程途远近,于存公项内,酌量赏给还乡路费。”[14]537乾隆十四年(1749)又奏准:“各省教官,如遇病故、休致、及因公革职并无余罪之员,有相隔本地在五百里以外,实系艰窘不能回籍者,该州县官结报上司,照县丞以下微员例、核实支给。”[14]537上述规定反映出:第一,赏给回籍路费是基层官吏专门享有的一项福利政策。“八品之下方准请领,其七品之上人员,例不准支。”之所以如此规定,应是考虑到七品以上官秩较高,“廉俸较优”,自有积蓄[15]484。不过,佐杂微员有在任与试用之别,试用微员是否也如在任微员一样同等享有上述权利,法规没有明确,因此,在实际中,具体情形依各地而异。第二,微员支给路费的情形相当广泛,非因贪污离职、丁忧、解任、告病回籍、身故等都可以支给。不过,清廷对微员预支路费仅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具体如何运行,由“地方官各就本省情形”操作。这一方面使该制度在各省具体的运作并不一致;另一方面,这貌似因地制宜的举措,实际上却是将具体决定权交给了地方,由于不是国家统一的硬性规定,以致有时微员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
《福建省例》记载了该省微员支给路费的制度变迁,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该制度在地方上的实际运作情况。从史料记载来看,支给微员路费,一开始是在任者的权利,试用人员不享有。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从九品吕国熊在省候补病故,“所遗眷口,实在穷苦,无力扶榇回籍”,其家丁乃请给路费。由于情况特殊,闽县知县焦长发就应否给予路费一事向上级请示,巡抚衙门不仅同意支给路费,并定例:此后试用杂职病故,“果属贫窘难堪,柩属不能还乡者,准其通融,酌给资助”。当然,巡抚衙门也强调指出,试用微员给予资助仅限于身故之情形,如遇到其他事故,“概不准其请领”。此后,由于额销之数“有余剩银两”,福建又将支给微员路费的情形扩大,“试用人员丁忧、事故,亦一概准其支给路费”。但后来随着发闽试用佐杂人数增加,奏请支给银两增多。从嘉庆七年(1802)开始,福建省对微员支给路费进行了紧缩,终养、告病、参革人员请领路费,概行批驳,停其给领。到嘉庆十八年(1813),这种限制更加严厉:“佐杂教职,如莅任未满五年,遇有丁忧、病故,眷柩实在无力回籍,准其给领路费。如莅任已满五年,官久俸深,遇有各项事故,不难设措回籍。及莅任虽未满五年,而告请终养及告病、参革人员,均一概不准给领。其试用杂职,仍照乾隆四十四年详定之案,唯在省在差病故、果属贫窘难堪、柩属不能还乡者,准其给领路费。如别项事故,概不准其请领。” 那么,朝廷赏给微员还乡路费数量有多少呢?据《福建省例》的记载,微员丁忧病故路费,岁有定额,每年“原准酌给银九百四十一两有奇,五年比较,共应给银四千七百七两,不许出此范围之外”。即五年之内,在此范围内匀计咨销。实践中,也很少有超出额定之数,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报销,“支银七百八十六两九钱八分”。次年正月至十一月,亦仅支给银两“四百四十三两七钱四分”。而且,这一额定数目并没有随物价上涨而变化,到嘉庆十八年(1813),仍是五年共定额银四千七百七两。那具体到个人,能得到多少银两呢?以乾隆四十四年(1779)吕国熊案为例,吕国熊籍隶安徽旌德县,计程3 176里,按照程途,应给银三十一两七钱六分,外扶榇夫八两,总计应给银仅三十九两七钱六分。这个数额并不算丰厚。有些官员去世后,无人扶柩归里,官府还有义务帮助运送其棺柩回籍。法律规定:“病故之员,并无亲仆与代送之人,该督抚仍照例给发勘合,令地方官选差的役二名,务令送回原籍,取具地方官印结送部。” 如果出了差错,地方官员还将受到处分[15]482-485。
二、艰辛旅程:官员赴任期限与违限处分
清代臣民出行限制甚严。顺康年间规定:“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16]488到雍正三年(1725),朝廷废除此例,但民众出入关津仍需通关文碟之类身份证明。而处于治民之位的官员的出行,其所受限制更甚于普通民众。首先,官员不能轻易出辖区或在籍之地,无论现任、候补、候选官员,都是如此。只有遇到特殊事故才能外出,但必须事先呈明朝廷请假,给咨才能出行。其次,官员出行,无论赴任或回籍途中,必须要有文凭路引。文凭既是官员做官之凭证,亦是通关之路引。《大清律例》有“诈冒给路引”罪。据沈之奇注:凡有照身不应给路引之人而混行给引则要处罚,“如僧道有度牒,官吏有文凭,举人有咨文之类,亦是不应给者”。也就是说,官吏因为有官凭,不应再给路引,违反则要受处罚。可见,官吏的文凭实际上也是其出入关津之凭证,具有类似路引的性质。再次,朝廷对官员出行,按道路远近,规定了严格的程限,违限者要受处罚。下面以官员赴任为例,看朝廷对官员出行的规制。
(一)领凭赴任与缴凭
清人一旦为官,首先便要拿到身份证明——文凭。《大清会典》规定:“官员赴任,必有文凭。”所谓文凭,是清代官员任用的手续和制度,也是通关之路引。顺治三年(1646)规定:“在京官,以除授日为始,在外官,以领到吏部照会日为始,各依定限赴任。外官升转京职,亦行给凭。”[17]386但到康熙九年(1670)情况有所改变,该年覆准:“凡在京官员,无论初选升授,皆停其给凭,命下之日,宣旨赴任。”这样,凡升选官赴任者,京官只要由吏部知照有关衙门,毋须给凭。但外官升选京官,仍需由吏部发给文凭。在本省升任,或在籍候选不必引见者,吏部将文凭咨发各省督抚转给。在京候挑八品以下官员,及奉旨引见降至八品以下得缺,并留各馆候选之员,仍由吏部给凭赴任。(1)相关内容详见刘子扬、李鹏年、陈铿仪编著:《清代六部成语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第80页。另外,关于清代官员赴任给凭的法律规定,可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5《汉员铨选·官员给凭》,卷90《处分例·给发文凭》。武官则由兵部给标。乾隆四十一年覆准,兵部推升武职,亦照文职给凭之例。“奉旨后,十日內满限票封发各该督抚,俟该员交代清楚,领票之日起。限十日內、严催照限赴任。如该督抚不于限內满限票给发者,亦照钦部事件违限例,分別议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0《吏部·处分例·给发文凭》,载《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7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477页。官员领到文凭之后,必须认真保管,不能污损、破裂、虫蛀。所以,黄六鸿郑重告诫即将赴任之官员要详看官凭并仔细保管,“凭给入手,详看明白。如有伤损洗补,即当官禀明,或求盖印,免到任缴凭致藩司驳查。凭用绢幅包好,护以油纸,再置一缎囊盛之,上牢缀挂带,起程悬于项下,暗置胸前,夜则置之枕畔以防不虞”[18]卷1《画凭领凭》。官员赴任途中,如果不慎丢失文凭,则须“取该地方官印结,并本处巡抚或布政司咨文到部”,如此才能改给执照[17]389。官员到任之后,必须将文凭上缴交回。由布政使汇造清册,声明有无违限,同文凭封送督抚覆核,咨缴查销。不过,文凭如“有油痕、水碛、破损等事,不得任意驳回”[19]209。
(二)期限与处分
官员领凭之后,应于十日内起程。相关官员承担催促之责,否则,罚俸六月[14]477。为了避免官员因事或规避苦差故意于赴任途中滞留迟延,清廷严定官员赴任“程限”。一开始,程限的设定尚不精细,只是依照路途远近,酌量凭定。自雍正七年(1729)起,清廷详细规定了自京城出发赴任到全国各地的程限,及从各个地方出发到全国各地赴任的程限。该规定相当细致具体,某地出发至某地限期多少日,一一详列明白。如官员自京至各省府(州)赴任,顺天限十日,程限最短;至云南省程限最长;云南临安、楚雄、澄江、曲靖、东川、广西、武定,限百有十日;大理、顺宁、永昌、开化、景东、蒙化、永北,鹤庆、元江,限百十五日;广南、丽江、镇沅,限百二十日;之后,随着陆续增改、新设之府并直隶州,朝廷又对这些新设之行政区域的赴任程限做了修订[14]472-477。官员赴任必须严格遵守程限,如有逾限,“一月以上者,罚俸三个月,两个月以上者,罚俸六个月。三月以上者,降一级调用。四月以上者,降二级调用。五月以上者,降三级调用。半年以上者,革职。不及一月者,免议”[17]387-388。嘉庆二十年(1815),朝廷对官员赴任程限的限制有所放松,减轻了对违限官员的处分,规定逾限“三月以上降一级留任,四月以上,降一级调用,五月以上,降二级调用,半年以上,降三级调用,一年以上,革职。其违限不及四月各员,吏科将应否宽免之处声明请旨”[14]480。
《大清律例》还专设“赴任过限”之罪,“无故过限者,一日笞一十,每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并留任”[10]151。这意味着赴任违限官员可能遭受刑罚。从规范内容来看,《大清律例》的惩罚明显重于吏部处分例,两者不无参差之处。根据清代法律运行实践,当时官员违限应主要适用吏部处分例处分,按刑律处罚只是例外。
(三)展限之规定
官员赴任途中,可能发生意外事件,如患病、风水阻滞、遇贼受伤、遇道路梗塞等。如遇此等意外,赴任官员须呈明当地官府,由当地州县官亲验证明,出具印结,申报部科,可以获得2~3个月额外展限。此外,官员赴任,严禁绕道。但有时,赴任官员由于离家日久,在顺路或绕道不多的情况下,往往萌生看望父母、祭扫祖坟的渴望,特别是新科进士往往渴望“衣锦还乡”。于此,乾隆四十年(1775)特别恩准,“由京领凭赴任官员,有在部呈请回籍省亲修墓等情,无论是否顺道,俱准给假,并准其一体扣算往还程限”[14]480。除了赴任,官员请假回籍或解职回籍的部分情形,也规定了严格的程限和程序(详见下文)。
清代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出行相当艰辛。为了不误期限,官员往往必须风雨兼程,特别是被派出到偏远省份和地区做官,更是辛苦。如从京师到云南曲靖府,7 900里路程, 定限为110天,那就是说连续三个多月,每天必须赶72里,这无疑是相当辛苦的。因此,即使不是出于故意规避,官员们要在期限之内顺利到达目的地也是困难重重。为了防止逾限受罚,官员们想出了诸多作弊的手段,清时“仕途宝典”——《福惠全书》就给赴任官员们想出了避免赴任违限惯用的造假招数及注意事项:“途次偶有躭延,恐到任逾限,须预先取经过州县患病印结,粘连医生、店家甘结为据。到任后,于缴凭文书声说明白,将印结连凭申缴。其取结之处,要看凭限日期,不可太迟,亦不可太早。约在中途与限内程期相仿,方可取结,若限外日期取结不准,仍照违限处分。[18]卷1《取结附》
不过,《大清律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显示,朝廷在不断地重申和严密修订官员准时赴任的规范制度,这说明官员违反出行规定的情况屡禁不绝。而实际上,违反规定的官员真的比比皆是,如嘉庆七年(1802),新授江宁副都统田国荣简放之后滞留不赴任,被皇帝召见训诫[14]480。到晚清时期,官员赴任延宕的现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同治元年(1862),有“四百数十员之多任意延宕”,以致御史刘庆奏请军务省分新选人员严定到省限期[14]482。
三、伦理亲情:官员的家庭生活与限制
官员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于到任。除了依照王命履行职务外,他们也必然要有各自的家庭生活。那么,经年流离在外,亲老的侍养、子孙之抚养如何处理?他们对亲情的情感需求怎样得到满足?在君王之命和伦理亲情的纠结之间,朝廷又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以实现两者兼顾的平衡呢?这种安排是否能真正满足官员伦理亲情的需要呢?
(一)官员履行赡养义务之制度设计
古代有“迎接尊亲同居一起,以便孝养”的迎养之制。宋真宗曾“诏群臣迎养父母”[20]卷6。清廷也并不禁止官员携眷上任,甚至鼓励官员迎养祖父母、父母等亲老。乾隆年间,朝廷因直隶按察使裴宗锡“母已年老,相依官署,难于迎养他往”,是以格外开恩,数年都“久留不调”[21]299。但是,毕竟这是体现君恩的特殊事例。对大多数官员而言,宦游无定,且路途遥远,迎养并不现实。如此一来,官员不得不与亲老分隔两地。这就与以忠孝等伦常为本的中国政教传统相违背。为此,朝廷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行政管理中融入家族主义因素,以求既满足官员个人侍养父母的情感需要,又“以政治的力量来提倡伦常,奖励孝节”[22]95。
1.省亲的规定
所谓省亲,指官员请假回籍探望亲老[23]40。清廷允许在外任职的官员,定期回籍省亲。不过,官员省亲必须告假,朝廷对告假资格、往返程期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如以在京汉员省亲告假为例:(1)资格。顺治初年规定,京官省亲告假,必历俸六年以上[17]395-396。也就是说,一个京官只能在任职六年之后才能请假回家见一次亲人。乾隆年间,开始放松对京官省亲的限制,一些特殊情况不再遵守六年之限。乾隆五年(1740)奏准:“在京官员,有闻其父母患病,急欲省视,或父母年逾七十而衰惫者,均不俟六年俸满。”另外,新科庶吉士请假省亲,也不必论历俸年分[14]504。(2)程序。一般情况下,取本衙门堂官,或同官,或同乡京官印结,具呈吏部代题,准给执照回籍[17]397。特殊情况下的省亲告假,则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具呈本衙门,该堂官具奏请旨,给假回籍。乾隆二十九年(1764)奏准,京官省亲告假流程进一步简化,三品以上,自行具奏,请旨开缺;四品、五品京堂,均由本衙门具呈咨部,吏部即行据咨单题,俟奉旨准给假后,再行开缺;其五品之科道以下等官,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具呈本衙门堂官,咨部开缺[21]658。(3)定限与程期。省亲官员“在家许住四个月。违限,一年以外者,罚俸一年,二年以外者,革职”[17]396。关于往返路途,也严格规定程限:直隶限四月;山东、山西、河南、限六月;江南、江西、浙江、湖广、陕西、限八月;福建、四川、广东、广西、贵州、限十月;云南限一年。[17]397(4)开缺。顺治十年(1653)以前,官员省亲告假,俱限六个月,并不开缺。但从顺治十年开始,官员给假都要开缺。即使特殊情况下,止请暂假数月,仍行开缺。[17]397
至于外任汉人文官,一般只有于赴任、回任途中,顺道之时才能回籍省亲。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规定:同知以下在部领凭赴任各官,如实系顺道,准予给二十日省亲假。[24]189具体规定为:如系赴任,事先向吏部呈明,回任赴吏部,则要呈明任所督抚,俱不得私自绕道归里;违反者,一经查出,照违令私罪律罚俸一年。[19]205在实际中,道、府等官往往“于请训赴任时,有面奏暂假回籍经允准者,皆于次日具呈吏部覆奏”。因此,乾隆十六年(1751)明定条例予以禁止,“各省道、府等官,皆不得于请训时自行乞假,皆令赴部呈明,其应否准行,即由该部酌定,给以假期”。至于省亲的期限,由于是顺道探亲,假期不可能很长,按乾隆十六年(补公元纪年)的规定:“除去往返程途计算,如呈请省亲祭扫者,准其告假二十日。修墓及迁葬者,准其告假一月。总不得逾一月之限。”[14]506到乾隆四十年(1775),官员省亲告假规则放宽,“由京领凭赴任官员,有在部呈请回籍省亲修墓者,无论是否顺道,俱给假”[24]191。
教职官员,或任主考、学政等官员差满回京时,亦可请假顺道探亲。另外,乾隆五年(1740)又议准,“各省教职,食俸三年以上,如有父母在家不能迎养,欲回籍省亲、及葬亲、省墓等事,准其咨明州县官,转详该管上司,查明委系实情,取具该州县印结,计其程途远近。酌给假期”。而且,相对于其他官员,教职省亲请假还有一个特殊待遇,即“员缺毋庸开选”[14]506。
省亲只是对官员的亲年尚未年老或已有人侍养的情形下的安排。如果亲老年老之后或无人侍养之时,清廷则允许官员告近和终养。
2.告近的规定
告近是指官吏因任所离本籍过远而不能迎养父母,请求改任于近地。如道光年间,江苏无锡人邹鸣鹤,“云南即用知县,亲老告近,改发河南,署新郑,补罗山”[25]11815。亲老告近制度最早推行于汉族文官(2)至于武官与旗人告近,直到乾隆时期才得以推行,且与文官告近存在差别。见《(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71,《职制·武职养亲》,载《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8页。,这应是清统治者出于不希望激起汉族士大夫的反感而尊重传统文化习俗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此举表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从而把汉族士大夫约束在儒家规范之中,达到使其尊重满族皇权的目的。汉员文职告近有相当苛刻的条件和限制,具体细则如下:(1)关于年岁的限制。康熙五十年(1711)奏准:“候补候选汉员,凡独子之亲,年七十以上,众子之亲,年八十以上,停其铨选。”[21]643到嘉庆元年(1769),清廷将年限的规定放宽到65岁,即:“亲年六十五岁以上,方准改补近省。”[21]717(2)亲年既可是父母,也可以是祖父母,如系承重孙,“因祖父母年老呈请告近者准”[21]644。(3)亲年有无供养。亲年达到法定的可以告近的年岁,但如果已有其他有供养义务的人告近时,其他人则不得再行告近。如同胞兄弟中已经有一人声明亲老告近者,其余人再行申请“概不准行”。而承重孙因祖父母年老呈请告近,“若已有胞叔业经告近”,亦不准行[21]644。
3.终养的规定
终养即奉养父母,以终其天年,多指辞官归家以终养年老亲人。清廷规定,当官员祖父母、父母年事已高,无人照顾侍养,官员可以离职居家奉养。申请终养的条件和情形为:(1)官员亲老,家无次丁,或有兄弟而笃疾不能侍养,或母老,虽有兄弟而同父异母。《大清律例》律文以祖父母、父母八十为准,例文推广为七十亦准归养,因此,实际中应是按亲老七十为准。(2)家有次丁,父母年至八十以上,愿请终养亦准。(3)出仕后兄弟忽遭事故,无人奉事。(4)继父母已故,其本生父母老病,愿请终养者。至于应补、应选人员因为侍养亲人不到任亦不为罪,且告假规定较现任官员宽松许多,只云亲老,并未注明七十以上。(5)凡呈准终养之汉籍官员,俱开缺给假回籍。事毕起复时,京官,坐补原衙门之缺,外官道以下,赴部引见,除奉旨另班铨选外,俱坐被原缺。
由于清朝宣扬以孝治天下,对于汉族官员来说,终养是强制性的。一旦出现亲老需要离职居家奉养,则官员必须告假回籍侍养亲年。但由于请假终养官员必须开缺,一些官员为了个人官途,往往隐瞒不报。对此,《大清律例》定“弃亲之任”的罪名,违法官员,“杖八十”,令归养,候亲终,服阕降用[10]295。直到清末法律改革,沈家本删订的《大清现行刑律》,仍保留该律条。[26]168
4.丁忧与守制的规定
丁忧原指遭父母或祖父母等直系尊长等丧事,后多指官员居丧。按惯例,官员闻父母之丧,无论官居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大清立国之初,即在官员中推行丁忧守制制度,无论旗员、汉员,俱须遵守,只是在守制期限长短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守制的基本规定:(1)程序。《大清律例》规定,官员例合守制者,“在内,经由该部具题,关给执照;在外,经由该抚照例题咨,回籍守制。京官取具同乡官印结,外官取具原籍地方官印甘各结,将承重祖父母,及嫡亲父母,与为所后父母,例应守制,开明呈报。”(2)开缺解职。守制期间,官吏解职守丧,不准任官,除服乃得起复(夺情者例外),严禁冒哀求仕,《大清律例》规定:官吏父母死,应丁忧,“诈称祖父母、伯叔、姑、兄姊之丧,不丁忧者,杖一百,罢职役不叙……若丧制未终,冒哀从仕者,杖八十(亦罢职)”[10]293-294。(3)守制期限。汉员文官,丁忧二十七个月,以闻丧月日始,不计闰月,扣足二十七个月为满,服满起复。(4)居家守丧。按规定,官员守丧,汉员则须回原籍。并且,丁忧官员回籍,严禁逗留,乾隆三十七年(1772),严定汉员回籍之条:“在任丁忧人员,自应遵例回籍守制,不便久留任所,令该管上司于交代完日,限三月内催令起程,仍令原籍督抚,将回籍日期报部存案,不准在原任省分寄住。如有逗遛,将本员照旗员处分;该管官及该上司,即照容留旗员例议处。”[14]529
清廷上述制度之设定,其出发点是既想使官员认真履行王命,又能够满足其伦理亲情之需求,似“为天理人情之至”。但正如冯桂棻在《免回避议》一文所指出的,这些制度条目繁多,“有年岁之限,有次丁有无之别”[27]25-27,且门槛过高,在实际中实窒碍难行。比如终养亲老年龄的规定,独子七十,多子八十,才准告假终养。但在古代人们能活到如此高寿之人应不多(3)关于清代国人平均寿命,并无确切的资料。据杨建伯的研究,中国自1935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国人平均寿命在30~35岁之间,至1985年接近70岁。根据近现代人均寿命不断增长的规律,清代人口平均寿命应该不会超过现近现代人的平均寿命。见杨建伯:《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及流行病学意义》,《中国地方病学杂志》,2003年第2期,第43-46页。。所以,这些制度有多少实效实在值得怀疑。这招致了清代学人的批评。御史王心敬言:“今有如两亲已老,更无昆弟。而一选远地,即平日至性天成之士,不能不违其本心。”[6]631冯桂棻在另一文《省则例议》中也对官员侍养制度条例的繁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于治天下非徒无益而又害之”[27]43-44。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亲迎、省亲、告近、终养,都是官员亲年在世时侍养的制度安排,丁忧则是官员亲年去世后的制度设计。从上文所述来看,亲迎、省亲、告近、终养有诸多窒碍,如此造成官员一入仕途就很难能亲自侍养亲老的后果。而令人讶异的是,官员亲老去世之后,朝廷却大张旗鼓地执行丁忧与守制制度,不但强制官员回籍,而且还强制要求在家守制近三年的时间。朝廷的理由是要让官员尽孝。但无论如何,孝的首要含义应该是侍养父母、承欢膝下,即以“父母在,不远游”为指归。清廷在亲老侍养和丁忧守制制度设计上的差别,体现的却是轻生时的侍养,重死时之守孝,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孝”的真谛。这种“重死轻生”的制度安排折射出一个令人心寒的事实:国家并不真正关心官员内心的伦理情感需求,也并不在乎现实中老年人的真实生存状况。他们只是希望利用守制这一外在的、固化的仪式,以一种 “炫耀的方式表现孝”[28]703,借此引导人们移孝作忠,驯服于专制权力之下,达到王朝永固的目的。
(二)官员抚(扶)养晚辈义务之制度设计
除了侍养亲年,官员还有其他亲属需要抚(扶)养,对此,朝廷允许官员携带眷属同至任所。至于随任眷属的数量、年纪,对汉员并没有做出严格限制规定(4)对于旗员子弟,朝廷限制甚严,专门制定“旗员子弟随任”条例予以规范,其中明确规定随任旗员子弟的年龄和数量。。但携眷赴任,官员则又面临着重重困难,尤以户籍与教育科考问题为最。
1.随任亲眷的户籍问题
官员到异地任官,其户籍并不随之迁移,去职之后,也不能随意寄居他省。而官员的随任眷属,也禁止在随任地方入籍。官员死后,“子孙有田土丁粮已入版图者,回籍附籍,听其自便”(5)康熙四年(1665)规定:“罢职官员,本身寄居各省者,勒令回籍。若本身既殁,子孙有田土丁粮已入版图者,回籍附籍,听其自便。”(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口·流寓异地》,载《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62页。。清代许多政策规定都与户籍捆绑在一起,官员及随任子弟异地入籍的禁令和严格限制,给官员及其家庭在异地生活增加了许多困难,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子弟的教育和科考。
2.官员随任子弟的教育与科考
清代进入官学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俱以户籍为准,如顺治九年(1652)规定:童生入学考试,有“称游学、随任等事别送者,悉不准行”[29]169。而根据清代法律,官员及其随任眷属一般禁止入籍任所地。即使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入籍异地,也必须入籍二十年以上方能应试[30]374。这就意味着,正常情况下,随任子弟不能在随任地官学开始学习及参加科举考试。
为了解决随任子孙的教育和科考问题,一些官员开始不顾禁令,采取种种手段以谋求子弟于任所地学习、考试,而职掌此项事务之各省学政更方便上下其手,因此,朝廷对各学政官员随任子弟监管更严,颁布了针对教职子弟学习、考试的特别规范。顺治十一年(1654)题准:“教职子弟随任入学者,严加考试,如文理明通,发回原籍肄业,其余严行黜革。”[17]2471雍正十二年(1734)覆准:“各省教官有随任子弟,遇考试时,即在现任地方冒籍入学,殊干定例。嗣后遇岁科考试,令该教官出具并无子弟随任冒考印甘各结,申送学政衙门存案。如有仍前冒考者,一经发觉,除将本童及廪保褫革治罪,仍将该教官题参议处。”[29]245但是,学政利用职权给随任子弟上下其手的情形并没有消失。有鉴于此,乾隆六年(1741),朝廷干脆釜底抽薪,规定各省学政眷属“概不准其随带”。不过,乾隆皇帝自己很快就意识到该禁令的荒谬,第二年就颁旨废除[30]721。
朝廷并没有为官员子弟的教育和应试权利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官员或者将子弟留于原籍读书应试,或于任所地请私塾教育子弟,或者违法违规暗地里在任职地解决。这样一来,弊端显而易见。把子孙等眷属留在原籍,则需要将妻子留在原籍管教子弟,官员只能长期忍受亲人离别相思之苦,平常只能依靠书信与家中保持联系并教导子弟。而留于原籍的子弟,一般都由母亲等女性亲属照管教育,难免娇惯纵容,渐渐发展为横行乡里的恶霸。至于请私塾教导弟子,由于官员平时忙于公务必疏于约束,又因为子弟不能进入官学,空闲时间较多,缺乏严格的管理和约束,这也可能导致官员子弟干预地方政务,作威作福。
此外,官员随任眷属的管理也是一个令朝廷头痛不已的问题。随任眷属往往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干预地方事务。对此,清廷制定法规,试图对此进行监管。乾隆六年(1741)议准:“外任官员,如有随任父兄,与地方绅士晋接,出名拜贺,燕会应酬,……令各督抚据实查参,将私相交接之随任父兄,不行劝阻之现任子弟,……俱照违令私罪律议处。”[14]552除了对随任眷属妄行交游予以惩处外,官员如果纵容子弟亲友在任所招摇撞骗,则被革职(私罪);失于觉察,降一级调用(公罪);官员如失察子弟夤缘纳贿,亦降一级调用(公罪)。[19]365不过,对官府禁令的效果,我们不能抱过于乐观的期望。
清廷虽然对于因王命需要而被迫远离家乡的官员们造成的伦理困境,努力进行弥补和平衡,显示出家族主义对行政方面的深切的影响;但由于制度设计本身的不合理性,导致官员在侍养亲老方面,很难真正尽孝,而在抚(扶)养方面,又很难真正尽责。在君主专制下,官员的伦理情感永远只能屈从于王命之下。
四、衣锦还乡:官员回籍之规定
(一)在任告假回籍之规定
清朝法制,官员不能随意出入辖区。在任官员如果想回原籍,则只能告假。关于告假的具体规定如下:(1)告假事由。官员告假的因由较多,除前文叙及侍养亲闱的省亲、终养、丁忧等事故可以告假外,送亲、祭祖、迁葬、毕姻、患病、回籍措资或赴别处措资等俱可告假。(2)京官告假。顺治初年规定,在京大小官员,“省亲、送亲、祭祖、迁葬、毕姻,俱准给假”。但告假祭祖父者,必食俸十年以上;省亲者,食俸六年以上;迁葬者,食俸五年以上;只有送亲老回原籍以及毕姻不拘年限,不论食俸[17]395-396。京官因归祭、省亲、迁葬、送亲、婚娶等事告假者,除去往返日期,“在家止许住四月”[14]504。新科庶吉士因未符省亲例限,纷纷托词患病告假,嘉庆十五年(1810)乃特别定例,“庶吉士有因省亲、接眷、修墓、葬亲,并实因资斧不给,请假回籍措费等事,不必拘以历俸年限,准其取具同乡京官印结,据实声明,具呈本衙门,咨明吏部,附入汇题”,并遵守在家居住四个月的限制;京师各衙门额外人员也如此例[14]505。(3)外任汉员文官告假。外任汉员文官告假,限制较京官为严。道府等官,“如呈请省亲祭埽者,准其告假二十日,修墓及迁葬者,准其告假一月。总不得逾一月之限”[14]506。而且外任文官告假省亲、修墓及迁葬者,只能于赴任顺道之时。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朝廷才改变顺道给假回籍的规定。
在告假回籍事故中,因病告假是较为特殊的情形,因为因病告假并不必然可以回籍。清初官员因病例可回籍,康熙九年(1670)定例:“在京汉官告病给假者,回籍调理”,按职位高低,或由官员自行具奏,或官员具呈该部院衙门,并取具同乡京官“并无假捏印结”[14]507。因病告假官员至少能得一年休养的时间,清廷规定,汉员告病之后,待一年限满,方准起病补用。当然,这也意味着至少休养一年,因为如有不及年限咨部者,概不准行。之所以规定一年期限,应该是为预防某些官员借病规避不好的官职。
对于外官患病告假,一开始朝廷也允许回籍调养。雍正五年(1727)例:“外官告病,督抚查明确实具题,令其回籍。”[14]511可见,当时外任官员患病,朝廷是强令其回籍调养的。后来,为了杜绝官员借告病之机规避、瞻徇之弊,朝廷规定:道府告病人员,惟准督抚题请,解任调理,“至应否回籍,由内阁票拟双签请旨。其中有准回籍者,亦有不准回籍者”[21]293。雍正十三年(1735)则进一步明确:“布政使以下等官告病,该督抚委官验看确实具题,令该员解任,留于本省调理,病痊之日,该督抚给文赴部,仍以原官补用。”[14]511外官告病后留于本省调理之规本为防范官员规避之弊,但到乾隆年间,皇帝对自己的眼光充满自信,认为可以洞烛方面大员“捏饰规避、托病回籍等事”[14]513,故清廷的政策又渐次软化。乾隆八年(1743),以外省官员告病解任后复留于该省调理“未免食用艰难,情亦可悯”,乃颁发谕旨,同知以下官员告病者,皆准其回籍调理,不必留于该省。道府等官,该督抚具题请旨,并“着为定例”[14]512。乾隆二十三年(1758),又放宽到布政使以下等官患病解任,“即准其回籍调理,毋庸再奏请旨”[14]513。不过,清廷关于官员告假可否回籍的规定颇有歧异矛盾之处,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保宁奏潼川府知府张松孙因病恳请回籍调理。乾隆帝在批覆时却又强调:“嗣后遇有道府以上告病人员,止应循照向例,题请解任调理,其准令回籍与否,听候部议请旨。”[21]293这里实际执行的仍是雍正十三年旧例,可见旧例并未废止,明显与乾隆二十三年布政使以下等官患病告假之规定互相矛盾。
总之,官员任职期间,要回原籍困难重重。有些官员从步入官场起,直到解职归乡,可能几十年间都没机会回到家乡。自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官员的文学作品会蕴含深切的思乡之情了。
(二)官员解职回籍之规定
官员解职,有革职、休致、解任之分(6)革职,清代官员处分的等级之一,撤掉所任官职。休致,官员因年老有疾而辞退官职。解任,官员因故交卸篆务,离任或临时离职。清制,裁缺、请假、丁忧、终养等官员,请准后,均须交卸印篆。 见刘子扬、李鹏年、陈铿仪编著:《清代六部成语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第32页、第36页。关于解任的规定,前文告假回籍有叙述,在此不再赘述。,朝廷对此的处置也有差别。清廷规定,因故革职官员,“本身寄居各省者,勒令回籍”[31]562。可见,对罢职官员而言,回籍是强制规定。且他们回乡路途还受严格限制,关于程限、出行方式与路线等都有法律规定或官府指定。康熙二十九年(1690)议准,“汉官革职离任者,照旗员之例,勒限回籍,将起程日期报部”。雍正三年(1725)又详定革职官员回籍之规范:“汉官革职提问,应于原籍地方追赃治罪者,在内令司坊官,在外令该督抚,作速催令起程。将起程日期报部,并知会原籍地方官,仍照旗员归旗例,按各省远近程途定限。有驿站者,每日行一站,无驿站者,每日行五十里。除从陆路者任其由陆路外,其有由水路者亦听其便,并将由某省水路之处即于呈内开明,自本任地方,照水路程途站数里数,扣定到籍日期。该督抚俟本人到籍,将日期报部查核。其革职免罪之员,外官交代完日,限三月内,京官限一月内,该地方官催令起程,按照程途定限回籍。”[14]527-528
休致官员,清廷一般也要求回原籍养老。康熙中期规定,凡京官革职、休致、解任,严催起程。后来朝廷对解任、休致、丁忧官的政策有所宽容,听其自便。但囿于成例,事实上,即使留居京师,亦多占籍大兴、宛平二县[32]。至于下层微员小吏,役满之后,则必须离京回籍。康熙三十八年(1699)定例:“凡部院衙门书吏,五年役满考职,一经出榜晓示,即令五城司坊官严催回籍,取具地邻一月内起身甘结,并司坊官印结报部。倘有潜住京城、不行查催,将司坊官照容留废员例处分。”[14]408京员离京回籍可能与朝廷限制京师人口的意图有关。
外任官员休致之后,是否也应当回籍呢?据乾隆元年(1738)规定:“老病告休官员,该督抚委员验实出结之后,亦照丁忧官员之例……给咨令其回籍。”可见,外任休致官员,一样也须回籍。不过,回籍路途“听其便”[14]528,不似革职官员那样严格。即使官员去世,朝廷也会想方设法,送其棺柩回归原籍。至于官员随任亲眷,除可以入籍的特殊情形,一般都要求回原籍。
五、结论
本文仅就清代官员客籍化的视角来讨论清代官员的管理制度问题。首先,清代任职籍贯回避造成地方官员的客籍化,官员成为特殊的流寓人口,个人生活面临着很大不便。朝廷专门赋予官员游宦生涯一些权利,并构建了缜密的法律制度进行保障与监控。这在一定程度上纾缓了官员的经济困难,平衡了他们在服务王权和个人伦理亲情需求之间的矛盾,这对调动和激发官员对皇权和朝廷的忠诚性、履行职务的积极性无疑具有积极效应。
其次,出于皇权安全和行政效率、公平、廉洁的考虑,朝廷在赋予官员权利的同时,又对他们的宦游生涯做出严格的限制,官员权利被大大“压缩”。而且,过于严格的限制、过高的门槛和过于琐细的规定又使官员保障制度窒碍难行,甚至带来新的制度性障碍。官员在异地的生活困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特别是家庭伦理亲情方面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很难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样,官员在表面的风光之下,与社会上普通流动人口一样,不得不承受飘零无依、身不由己的孤苦,忍受着孤身一人到陌生的远方做官的恐惧,及对故乡、亲人刻骨铭心的思念。在这种生存状态之下,希望官员以积极的精神状态尽心履行职责恐怕只能是奢望。正如庞慧所指出的:“当官员们只能在他乡思念故乡,噙着泪水怀念祖先庐墓、家园亲人时,他还有几分治国平天下的豪气?他还能不能‘以天下为己任’?”[33]18-22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削弱了官员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消解了行政效率。另外,客籍官员情感生活的境遇也反映出,大清帝国治下,所有社会成员都不允许自由流移(7)关于普通流寓人口的管理,可见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口·流寓异地》,载《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62页。,那些拥有一定声望和权力的人也是一样。帝制时代,臣民的社会生活环境相当压抑,无论是拥有特权的官员,还是普通民众。
最后,从本文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如何在对官员实施有效监管的同时,保证官员履行职务的积极性,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他们行为的得当与否关系着皇权的安全、国家的稳固和民生幸福。所以,清代注重约束官员职务行为的同时,也对其生活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这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作为一种研究和反省,也应当注意到,官员也是有血有肉、有各种物质和情感需求的人。因此,在设置相应监控制度之时,应当保持必要的人文关怀,以充分调动和激发官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这才是合理的、得法的官吏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