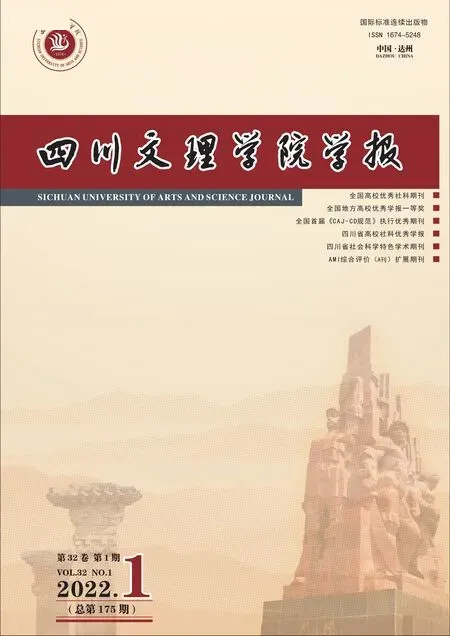美学的新起点 生命的新境界
——兼论潘知常教授生命美学研究的意义
2022-03-17范藻
范 藻
(成都锦城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众所周知,有关美的思考,乃至美学的研究永远没有终点,但一定有起点。这个起点不是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而是来自人生的生命活动,这就正如是母亲怀里婴儿第一声啼哭的顿悟、月下初恋情人第一次亲吻的感悟,还有夜阑垂暮老人最后一句话语的醒悟。诚然,这些是生命现象,而不是生命美学,但构成了我们对生存的醒悟、生活的感悟和生命的顿悟,如《诗经》里的“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如《春江花月夜》了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它们不是美学,是生命的叹息,这应该是美学的原初形态,更应该是生命美学的真实形态。面对如此“常识”,不少美学理论家却熟视无睹,只会终日沉迷于“象牙塔”里纸上谈兵式的“实践”,全然不顾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鲜活存在。对此,潘知常在1985年第一期《美与当代人》的《美学何处去》一文斥之为“‘冷’美学是贵族美学,它雄踞尘世之上,轻蔑地俯瞰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冷’美学是宗教美学,它粗暴地鞭打人们的肉体,却假惺惺许诺要超度他们的灵魂。”
一、带来了美学的生机
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是从一般美学到审美哲学:从“爱”到“审美”——从爱美之心到审美之智,从爱生命到爱美,落实到生命美学的核心就是“我审美故我在”:因生命,而审美,因审美,而生命。所以,审美活动是生命活动的必然与必需。由此形成了潘知常生命美学研究的三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其一,美学的历史性还原:一个中心是“生命为何需要审美”,两个基本点是“因生命而审美”与“因审美而生命”。
生命为何需要审美,是潘知常创立生命美学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他整个美学体系建构的中心问题。诚然,动物的生命只有吃喝拉撒和繁殖交配的生理本能,以及躲避危害和趋近舒适的心理本能,这是符合它在自然意义的进化规律,这种状态与洪荒的自然界是高度适应的。随着类人猿的出现,以至于早期人类的出现,工具的发明和使用,语言的出现和运用,洪荒的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环境,也还是人类生产的对象,更是人类生命成长的刺激物和进步的推进器,于是内在生命的进化和外在生命的完善都将美的需要和美的力量聚焦于个体的生命之中。
内在生命的进化就是快感产生的意义。美学理论中有一条著名的“快感导致美感”定律,对于正常的生命而言,没有快感绝无产生美感的可能,如人类对饮食为何喜欢甜味而厌恶苦涩,是因为甜食含热量高,对生命来说是“增热”与“赋能”,而苦涩含热量低,于生命而言是“清火”与“消食”。还有“性快感”对一些动物如雄性螳螂是高潮即死亡,而对人则是生命的享乐和奖赏,从而使得人类生命得以生生不息。
外在生命的完善就是美感产生的意义。内在生命的进化让人类越来越有“人”性了,而外在生命还需要不断的完善才使人愈来愈像“人”样了,我们所处的大自然环境有两个最鲜明的特征投射或体现在了人的身上,一是对称,二是曲线,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为什么虎背熊腰的男性和丰乳肥臀的女性更容易赢得异性的青睐呢?因为男性的生产生命是直线式的刚毅,蕴含着生命进化和成长一往无前的向力,而女性的孕育生命是曲线式的包容,给予了生命不断自我完善和适应外界的容忍和调适的韧劲。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为此,潘知常总结道:美感“同样也是对生命进化中的创新、进化、牺牲、奉献的一种自我鼓励。在这个意义上,美感与快感其实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当然,美感又有其特殊性,严格而言,美感是一种只属于人类的特殊的快感。”[1]就这样快感和美感内外双向同时发力,共同促成了人类生命从体质到精神的强壮和丰富。
“生命为何需要审美”的中心问题的解决,那么“因生命而审美”与“因审美而生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生命而审美”侧重的是生命的存在是审美发挥效力的前提,而此时的生命是一个追求意义的生命,正是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让审美成为了生命须臾不可少的“标配”。“因审美而生命”侧重的是审美的作用发挥是生命发展的结果,正是因为审美的加入,让人类的生命更是如虎添翼,以至于臻于完善和完美而使得生命的意义锦上添花,从而让生命成为了审美理直气壮的“标志”。对此潘知常深有感触地说:“审美与生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两面,是因生命而审美,也是因审美而生命。这一切,就正是我与我的同道们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美学研究称之为生命美学的根本原因。”[2]由此导致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重大分野,并使得美学终于找到安泰立足的大地。
其二,美学的时代性体现:一个中心是“生命意义的审美活动”,两个基本点是“个体的觉醒”与“信仰的觉醒”。
既然生命与审美一体两面,携手并进,那么审美活动就是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尤其是在世界进入了尼采揭示的“上帝死了”以后的虚无主义时代,能让人类心安理得的生存和气定神闲的生活的依托是什么呢?“赛先生”只能提供科学的物质保障,“德先生”只能提供民主的制度保证,如何安放我们的灵魂和抚慰我们的心灵,就惟有“美先生”了,于是“生命意义的审美活动”就必然成了救渡人类的“诺亚方舟”。因为惟有这种活动可以超越穿衣吃饭和规章制度,或者说是在满足穿衣吃饭和规章制度后的“意义”寻求与满足,从而让人的生命更加具有人的“样子”。
20世纪以来的中华民族,曾经寄希望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事实证明,二位先生管得了物质和社会,而管不了精神和审美,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是借助艺术和审美而实现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惟有单纯的形式愉悦的审美活动。它之于生命活动来说,是对生命本身的自组织、自调节和自鼓励,是在宗教和理性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唯一能在审美活动中通往灵魂救赎和信仰启蒙的康庄大道。
那么,审美活动是什么呢?因为有“活动”就是实践活动吗?当然是的,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但不是实践美学概念里的社会意义的外在实践,而是与生俱来和伴生而行的生命活动。阎国忠先生说道:“把审美活动归结为一种生命活动,而不仅是一种实践活动,这无疑拓宽了人们的视野。生命活动,可以理解为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活动,植根于人的生命的活动,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命投入其中并使人享受生命的活动,也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命为寻求自我保护、自我发展而不断超越自身的活动。”[3]一言以蔽之曰,由于生命先于实践,因此生命活动由于审美活动的存在和介入,不但大于实践活动和高于实践活动,并且优于实践活动。
为此,潘知常在《诗与思的对话》一书的开篇就说道:“审美活动的根源包括两个方面,即审美活动的历史的发生与逻辑的发生。不过,不论是历史的源头还是逻辑的源头,所涉及的都并不是传统的关于审美活动是‘何时发生的’之类的问题,而是审美活动‘为什么会发生’这类的问题。”[4]就这个意义而言,审美活动是创造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人类生命的实践活动,凡是满足人类意义追求的活动或事物都属于这个范畴,如欣赏美的事物、创造美的作品、研究美的理论、展示美的情怀,还有评论文艺现象以及美化自我和环境等,其中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是主要的形式和重要的途径;作为审美活动的文艺创作既为文艺欣赏的审美活动提供具有审美价值的对象,又能培养新的审美主体,提高其审美能力,从而促进人类整个审美活动的不断进步和日臻完善。
相应的,“生命意义的审美活动”这个中心问题的解决,那么“个体的觉醒”与“信仰的觉醒”两个基本点的确立就顺理成章了。个体是如何的觉醒的?由于审美活动在现实意义上不是一种“类”的和抽象的活动,而要体现出这种活动的效果,也只能是单个生命体具体而生动的活动,所谓“我美故我在”,因此能创造并享受这种活动的生命个体,一定是摆脱了动物的束缚和外界的局限后的生命觉醒,正如黑格尔说的“审美具有令人解放的性质”。信仰又是如何觉醒的?衡量个体生命质量的指标既不是中国古代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也不是儒家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四阶段”,当然更不是金钱和地位,甚至与身体的健康都没有太大的关涉,羸弱的康德有一颗伟大的心灵,瘦弱的梵高有一种高贵的气质,病残的史铁生有一身顽强的意识,身处逆境矢志不渝,面对困厄斗志未减,“虽九死犹未悔”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最后直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胸襟,那就是为爱而爱的信仰。
其三,美学的现代性追求:一个中心是“生命必然追求自由”,两个基本点是“在灵魂面前人人平等”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在前面的生命与审美需要、生命与审美活动的基础上,既是时间性又是逻辑性地引出了美学第三个核心问题:生命与自由追求,尽管“自由”是人类最古老的向往,从中国唐代不太知名禅僧元览的“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的意象到匈牙利伟大的革命诗人裴多菲“若为自由故”生命与爱情“皆可抛”的意志。可见,生命的真正而最高的境界,似乎已经超越审美、爱情,甚至生命本身直至人类最崇高的信仰,她既具有时代性的社会价值,也充满现代性的理想情怀。正如潘知常所说的:“信仰之为信仰,最为重要的,是可以导致一个充分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自在稍后于发展的社会共同体的出现,具体而言,就是导致在这个共同体中的‘一点两面’亦即自由与‘在灵魂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出现。”[5]潘知常对自由的理解,不但超越了我们熟悉的社会层面,我们向往的情感领域,而且提升到了生命终极关怀的信仰高度。
潘知常为美学所建构的“自由追求”的生命必然和灵魂与法律两个“平等”的人人有份,既显得理论站位的高大上,又具有现实操作的快准灵,更充满生命风采的精气神,所以它才是美学的,也是生命的,更是生命美学的。因为生命的介入,美学研究找到了崭新而鲜活的起跑点,因为信仰的引入,美学理论拥有了全新而神圣的制高点。
二、开阔了研究的视野
视野常常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和深度。
在中国美学界有的人一辈子要么固定于哲学王国的美学,要么执着于艺术园地的美学,要么拘泥于文学世界的美学,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终其一生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高度的起点,只能是原地打转。
而潘知常则不一样了,孔子所谓的“君子不器”在他身上得到了最生动而完整的体现。由于他将自己的美学研究牢牢地锁定在了“生命”的大地上,以此为起点向四面出击,以此为圆心向四周画出了一条条闪光的射线,从而让一个平凡经历的人生活得丰富多彩,让一门哲学属性的美学显得生意盎然。他除了研究生命美学的原理外,已经出版了七部专著,他还研究中国美学史,出版了《美的冲突》《众妙之门》《王国维:独上高楼》《中国美学精神》等,还有比较美学和审美文化的研究,如《中西比较美学论稿》和《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等。
沿着美学的思维半径,他又顺理成章地辐射到了文学、艺术的研究,如《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头顶的星空》和三部《红楼梦》研究一部《聊斋》研究等。他还跨越文艺美学涉足文化产业的研究,2013年香港银河出版社推出了《不可能的可能:潘知常战略咨询策划文选》,2014年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他和刘燕、汪菲联合撰写的《澳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同时长期从事战略咨询策划和企业、地区、政府与媒介等领域的各类策划、创意工作。他还参与了2003年南京的第一届“世界历史名城博览会”的策划,使得“世界历史名城博览会”成为树立南京形象的一项重大活动;2004年他又提出了要把南京建设为“和平南京”,指出南京要左右开弓,要打两张牌,一张牌是:“文化”,一张牌是:“和平”。现在,经过他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文化南京”“和平南京”,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最后,他居然溢出美学的边界,涉足传播学和政治学领域,撰写和主编了《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传媒理论批判》《怎样与媒体打交道》等六部著作;还有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在《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一书中,他首次提出了“塔西佗陷阱”,这源于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怀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6]后来潘知常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所谓‘塔西佗陷阱’指的是任何政府一旦‘从根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不惜以掠夺作为立身之本的时候,这个政府不论做好事和做坏事,其结果最终也都是一样的’,就会落入‘塔西佗陷阱’。”[7]由此便成为了一个源于塔西佗,但并非塔西佗提出的,而是由中国美学家提出的一个政治学概念。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明确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他先后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产业委员会委员、澳门国际电影节秘书长、澳门国际电视节秘书长、澳门传播学会会长、澳门比较文化与美学学会会长、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企业形象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还兼任澳门电影电视传媒大学筹备委员会执行主任、澳门国际休闲学院校监、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博士导师。《美与时代》编委、《城市研究》编委。
一个美学家居然会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不可思议”的领域,这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这与其说是学术的魅力,不如说是生命的美丽。君子之所以“不器”是因为不论什么样的或多么大的“器皿”都是有局限的,而一个热爱生活的学者生活有多宽广和丰富,学问之“学”与“问”就学海无涯和问而不倦,这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理想的现实化。在学术之于生命的意义问题上,李泽厚是从人类生命宏观视域起步的,而潘知常却是从个体生命微观视点出发的。
其次,这不但是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生命美学的当仁不让之事。其实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和潘知常的“生命美学”都没有本质性的不同,他们的关键词都是“自由”,但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却多出了“超越”“境界”两个关键词。如同样都是理性和情感,李泽厚醉心于从思想史领域来思考人类理性的积淀和情感的张扬,而潘知常却从生命力效能来展示个体理性的意义和情感的价值,前者着眼于抽象的“人类”,而后者立足于具体的“个体”;因此,于潘知常而言,凡是有生活之美的地方,一定有生命之力的足迹。
最后,这不但是学问研究的兴趣,而且是学者生命的意义。每一个学者研究什么或不研究什么,似乎是一件个人学术兴趣的事情,除了有时要完成“指定”的课题、“下派”的任务和“中心”的工作外,旁人是无权干涉他的学术自由的;但是作为旧时天下之“公器”的学术和当今社会之“公知”的学者,知行合一,学道一体,学问不仅是不断的追思疑问,学术也不仅是不断的改变方术,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发现的乐趣、满足探索的好奇,让有限的生命得以无限的延展。
三、扩大了学术的影响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
生命美学自从创立以来,尽管历经坎坷,饱受诟病,但她依然在倔强地生长,这如同潘知常经常说的那样: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生命美学之所以崛起为新的美学学派,充分体现了“荀子从建构‘群居和一’的交往共同体出发阐释其礼乐美学思想”,[8]当然,这与其说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志同道合的精神性契合,不如说是如潘知常所的“爱美学之心”应该“人皆有之”同频共振的生命美效应。
在当代中国美学的园苑里,能堪称学派的有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四大派别: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吕荧和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统一派”和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统一派”,及至80年代这四大派或自然消失,或后继乏人。由于李泽厚、蒋孔阳和刘纲纪等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经典著作里美学思想的极力推崇和大力阐释,于是以李泽为代表“社会实践派”蔚为壮观并独领风骚。到了九十年代,“后实践美学”异军突起,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杨春时的生存美学、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曾凡仁的生态美学、王一川的体验美学、张法的存在论美学等,一时蜂起;但遗憾的是,他们要么是孤军奋战,要么是师徒联盟,要么是学友呼应,而只有潘知常倡导的生命美学不但获得了众多的学者响应,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据笔者2015年的不完全统计,国内“属于生命美学研究著作的,有58本;论文达2200篇,其中有少量的研究艺术的‘生命意识’的论文;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也有180篇。……属于实践美学研究的著作的,是29本;论文3300篇,如果将其中的后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和‘社会实践’意义上研究文学、艺术、教育和文化的论文剔除的话,这个数字将大大降低;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200篇。……属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研究的,只有8本;有论文200篇;在报纸发表的文章20篇。……属于新实践美学研究的,有8本;论文450篇;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23篇。……属于和谐美学研究的,有12本;论文1900;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62篇。”[9]
又据范潇兮整理,收录在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生命美学,崛起的美学新学派》一书的附录《中国当代生命美论文论著目次汇编(1985—2018)》所显示,围绕生命美学发表和出版了的论文和著作,数量不断攀升,仅2018年公开发表的论文就达到38篇。
再从2018年中华全国美学学会陈政提交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学的热点嬗变研究——基于CitesPace以CNKI数据库为中心的可视化分析》一篇学术论文,又可见一斑。文章指出从1978 至2018 年间,美学研究热点一直聚焦于“艺术、美学、审美”三大方向,其中2000年、2010年生命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范畴、美学思想等概念一样属于高频次出现的词语。
“满园春色关不住”,在潘知常和潘知常生命美学的指导和影响下,不少非美学界的人士也纷纷在自己的领域为生命美学增光添彩。国家“文华奖”获得者的江苏省国家一级作家、著名剧作家徐新华,在从演员到编剧的奋斗过程中充分体验到什么是生命的创造美,她倾注生命热情创作的大型淮剧《小镇》,让淮剧走出国门进入欧洲。南京师范大学的齐宏伟博士,也是深得生命美学的真谛,一手做研究,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学术专著,一手搞创作,在海内外发表诗歌散文多篇,还出版诗集《彼岸的跫音》。毕业于南京大学,也是潘知常学生的青年作家崔曼莉,出版小说散文诗歌,多次获得国内外文学大奖,是江苏文学界崛起的新秀。还有熊芳芳,“生命语文”首倡者,湖南师范大学特聘硕士研究生导师,人教社部编教材培训专家,多家核心期刊封面人物及专栏作者,人民出版社“名著课程化阅读丛书”语文统编高中名著图书主编。潘知常还为熊芳芳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语文审美教育12讲》,写一篇序言《教我灵魂唱歌》。
这些专家学者名师在说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无不感慨道:是潘知常老师的生命美学不但给予了创作的灵感、生活的启迪和事业的引领,而且让他们体验了最美的生命是奋斗。
还出乎意料又难能可贵的是,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赵晓教授在阅读了潘知常发表在2015年《上海文化》第8、10、12期连载的《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后指出:“这篇文章让我感觉到潘教授实乃人中翘楚、不可方物。”“或许有一天,潘教授能把神学、美学与哲学完美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奥古斯丁。”“潘教授一系列哲学、美学与信仰的文章,相当了不起、非常有力量。如果潘教授在信仰上有经历和实践,在知识上有神学、哲学和美学的打通,那他很可能会是中国奥古斯丁式的人物。”[10]甚至连四川偏远一小县城宣汉县政法委当公务员的向杰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业余时间醉心于美学,先后在《美与时代》《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生命美学研究论文多篇,2014年还与谭扬芳合作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体验美学》。
2015年《贵州大学学报》也专门开设了生命美学的研究专栏,从2016年到2021年《四川文理学院学报》每年开设一至二期生命美学研究专栏,201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展示美学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重要成果,作为生命美学的诞生地,《美与时代》杂志社也开设了生命美学专栏,刊发了26篇学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