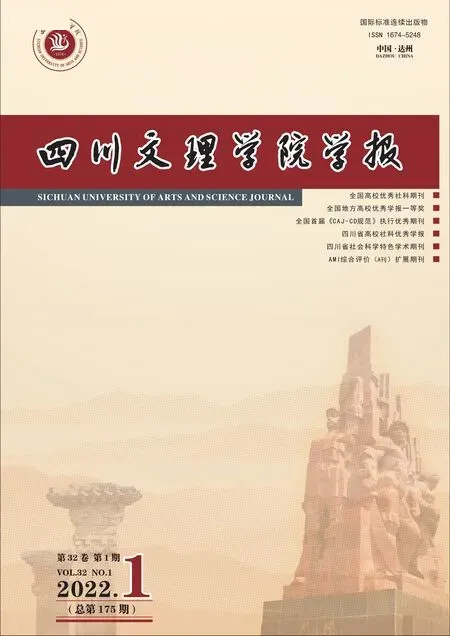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两个“哥德巴赫猜想”
2022-03-17潘知常
潘知常
(南京大学 美学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0)
一、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之一:“以美育代宗教”
在我看来,“以美育代宗教”与“生命/实践”,堪称百年中国现代美学中的两个 “哥德巴赫猜想”。一个是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命题,一个则是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问题。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命题。
众所周知,也无可争辩,当然应该是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1]
美育问题,是20世纪中国美学与艺术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百年前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这可以被看作20世纪中国美学的第一美学命题。近年习近平总书记也曾专门就此问题给中央美术学院8位老教授回信,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因此,回顾中国百年来关于美育问题的思考,回应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问题,对于“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意义重大。
更为重要的是,百年前,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百年中,影响如日中天,同时,回应者也不绝如缕。究其原因,无疑是因为审美与艺术的作用与意义在20世纪始终是一个前沿问题,它是一个真正世界性的命题,也是一个真正切入了世界的命题。因为上帝的死去以及宗教的颓然退场,审美以及艺术的作用与意义被突然关注。而且,西方康德的“美学革命”(审美王国)—尼采、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的“革命美学”(审美乌托邦)—福柯的“生命美学”(审美异托邦)的对于审美与艺术的作用的高度关注,也期待着中国美学的参与与对话。
出版于2019年的拙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人民出版社),关注的就是这个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命题。百年中,以五十五万字专著的方式回应蔡元培先生并且与蔡元培先生对话的,应该说,这本书还是首次。刘燕博士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可以拒绝信教,但不能拒绝宗教精神,在当代世界,信仰不是万能的,但是,假如没有信仰,却又是万万不能的。”[2]
拙著从“针对世界性虚无主义的中国方案”的角度,尝试着重新为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定位。它是对于原有理解的新突破,而且由此揭示了西方“因宗教而信仰”与中国“无宗教而信仰”的基本差异,以及中国的“因审美而信仰”的特殊路径,最终,由此而给出了我本人的关于“以信仰代宗教”以及“以审美促信仰”的全新思考。同时,拙著对于审美与艺术的对于人类虚无主义的“救赎”与“拯救”,以及审美与艺术在‘宗教弱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信仰建构的重要作用,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国内学界过去对于美育的看法往往是集中在艺术教育、情感教育或者人格教育之上,存在对于宗教(基督教)、信仰、审美、美育问题的误读。有所不同的是,拙著则从维护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审美权利以及捍卫生命的尊严、弘扬生命的自由、激发生命的潜能、提升生命的品质角度为美育重新定位。同时,百年来,因为意识到灵魂旅程必须在宗教之外进行,学界提出过“以科学代宗教”(陈独秀)、“以伦理代宗教”(梁漱溟)、“以哲学代宗教”(冯友兰)、“以主义代宗教”(孙中山)、“以文学代宗教”(朱光潜)、“以艺术代宗教”(林凤眠)……这无疑并非偶然,因此,对于“以美育代宗教“的讨论,已经不仅仅是在谈论一个纯粹的美学问题,而且还是在孜孜以求置身现代文化困境的救赎方案,涉及的是人类生命本身的发展路向的深长反思,因此,已经不再是生命美学,而是进而拓展为生命政治学与文化政治学了,理论价值重大。对此,拙著也理所当然地有所回应。至于研究方法,拙著则力图在“大历史”“大文化”“大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具体的探索是:美学研究与宗教学研究协同;框架预设与观念史解读结合;义理阐释与文本辨析兼顾;理论探索与个案视阈一体。
拙著的基本观点是:美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代替宗教,而在于:“以美育促信仰”!也就是:在“宗教弱化”的“无宗教而信仰”的时代,亟待以审美与艺术去促进信仰的建构。
具体而言,拙著分为导言与五章,全部内容都可以看作是一次百年之后的隔代对话——一个美学后学与蔡元培先生的美学对话。“以美育代宗教”还是“以信仰代宗教”,并且进而“以审美促信仰”,则是其中的关键。
同时,拙著第二章、第三章的部分内容曾经以《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为题,分为上中下三篇,约4,5万字,在《上海文化》2015年8、10、12期刊出,并引起广泛关注,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上海文化》编辑部在北京,以及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学术月刊》编辑部、《上海文化》编辑部在上海,曾分别举办过专题讨论会,北京大学、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陈伯海、阎国忠、毛佩琦等约二十位学者教授参加了讨论。从2015年开始,《上海文化》针对此文开办过“信仰讨论专栏”,刊发了14篇讨论文章,《四川文理学院学报》也开办过“信仰讨论专栏”,刊发过六篇讨论文章。《上海文化》2020年第4期、《美与时代》2020年第3期、《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发表了国内学界几位教授学者关于该书的书评,《中国社会科学网》、《新华日报—交汇点》(2020,3,6)、《中华美学学会网站》、《天津社会科学网站》、北京师范大学的“京师美学”网站也发表过本书的书讯或介绍。在这个方面,国内的绝大多数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当然,偶尔也有商榷的意见。例如罗慧林的《一种空洞而中庸的生命美学——与潘知常先生商榷》,载《粤海风》2006年第3期。文章反对生命美学对于“信仰”与“爱”的提倡,但是又“我并不是在否定爱的力量,信仰的力量,而认为必须时时对于一些虚空抽象的口号和理念怀有警惕,而更提倡一种平实低调的实践性建设性的社会思想。”因此全文都可以看作是罗慧林在与罗慧林商榷,而不是在与潘知常商榷。由于我2007年以后的工作就以澳门为主了,因此很晚才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就没有撰文回复。再如翟崇光、姚先勇的《潘知常生命美学“信仰转向”批判》,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2期。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12月,拙著《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荣获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二、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之二:生命/实践
当然,以五十五万字专著的方式回应蔡元培先生并且与蔡元培先生对话,也许还仍旧未能对于所讨论的第一美学命题做出全面的回应。但是,就当下而言,我以为,这个讨论已经堪称相对全面,也相对深刻了。因此,我在《走向生命美学——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中,又开始关注在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命题之外的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问题,这就是:生命还是实践?
它期望回应的,就是这个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问题。
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直面的问题无疑纷纭众多,争论不休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据我所知,不乏相当多的一些学者很喜欢这种现状,并且认为这才是美学界应该有的样子。因此,他们沉浸其中,甚至乐此不疲。我的看法却有所不同。我始终认为: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为美学作做加法,要不断提出一些全新的问题、全新的角度,把美学讨论的广度无穷地予以拓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还要为美学做减法,而且,要减而又减,要把美学讨论的深度同样去无穷地予以拓展。因为,正如老子所提示的:“大道至简”。为了更好地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先找到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开始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的时候,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才会浮出水面,我们也才能发现美学论争中的真正优先级的问题。西方学者加里·凯勒甚至强调: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只是,这个“最重要的事”只有在我们砍掉90%的“可以做但不应该做”的事情之后才能够呈现出来。显然,我所提出的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问题,就正是在砍掉90%的“可以做但不应该做”的事情之后得以呈现出来的美学问题——第一美学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提示:美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是两句话,第一句是:重要的不是美学的问题,而是美学问题。第二句是,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这当然也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呼吁我们不但要关注“美学的问题”,而且更要关注“美学问题”的原因之所在。
也因此,找到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问题,而且去倾尽全力研究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问题,无异于正是从“做正确的事”开始,也正是从从“美学问题”开始。倘若我们意识到:在美学研究中,对于“美学问题”的关注不但远比“美学的问题”更为重要,更为根本,而且也远比“美学的问题”更加“美学”。那么,我们也就会知道:也许这才是一项最为重要的、真正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做好的学术工作。
无可置疑的是,“生命还是实践”,就正是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问题。
显然,这个问题在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后半段是不存在异议的。实践美学(1957,李泽厚)与生命美学(1985,潘知常)、超越美学(1994,杨春时)等的长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而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争论,双方在背后各执一端的,正是:“生命还是实践”。在实践美学一方,李泽厚之外,刘纲纪、蒋孔阳……都是以“实践”为立身之本,即便是高尔泰,也仍旧没有完全离开“实践”的根基。在生命美学、超越美学等一方也如此。生命美学姑且不论,超越美学当然应该是“生命”的“超越”,存在美学也当然应该是“生命”的“存在”,体验美学也当然只能是“生命”的“体验”……至于新实践美学(2001,张玉能)、实践存在论美学(2003,朱立元),那毕竟还是围绕着“实践”展开的(尽管它已经不是“实践美学”,而成为了“美学实践”),还有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其实也没有离开“生命”的基本规定(尽管各派对于生命的解释可能会有所不同)。生态美学展开的是“生命”的“生生”维度(甚至,它一开始就是自称为“生命美学的生态美学”的)、生活美学展开的是“生命”的“生活”维度,身体美学展开的则是“生命”的“身体”维度。显然,“生命还是实践”在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后半段是贯穿始终的,因此也不存在异议。
问题的复杂性在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前半段。当然,在“生命”一方,其实仍旧是一点也不复杂。从王国维到宗白华、方东美甚至是朱光潜(早期),毫无问题,依然都是“生命”的提倡者。倒是在梁启超、蔡元培那里,直到蔡仪、周杨,似乎是都没有立足于“实践”。不过,问题也并不是很大。我们所谓“实践”其实并非狭义的,而是广义的,指的一种美学立场。这就是:人类中心论的、理性的、主体性的立场。显然,倘若由此出发,即便是“实践”,也仍旧是在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前半段一线贯穿的。例如,区别于王国维的审美—生命一本体论,梁启超的启蒙—社会一工具论就是直接李泽厚的“吃饭哲学”和“实践美学”的。从表面看,梁启超主张文学要为当下现实服务,而不赞同王国维的美学应追求"天下万世之真理",主张“诗界革命” “文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 “欲新一国之民”“欲新道德”“欲新宗教”“欲新政治”“欲新风俗”“欲新学艺”,因此而要借助审美活动的四种力:一曰“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3]而李泽厚围绕着“自然的人化”这一基本美学命题,推崇的是“实践”与“主体性”,两者的话语系统似乎并不相同。但是,倘若究其本质,我们则会发现:其中的人类中心论的、理性的、主体性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改变了的只是从认识论到本体论、从客体性美学到主体性美学的美学转进。所谓“人的自然化”,也无非就是人类中心论的、理性的、主体性的立场的集中体现。因此,李泽厚的美学只能被看作梁启超美学的升级版。就犹如我所提倡的生命美学,围绕着“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基本美学命题,推崇的是“生命”与“超主体性”,其实也只能被看作王国维美学的升级版。
更何况,从横向的东西角度看,百年中国现代美学所一线贯穿的,恰恰正是在中华文明第三期中贯彻始终的“生命”与“实践”的冲突。
在2005 年出版的《王国维:独上高楼》一书中,我曾经把中华文化的思想历程概括为三期。其中,我把我们当下所置身的界定为中华文明的第三期。具体而言,中华文明第三期,主要特色是中华文明就是与异邦文明的对话。不过,这一次与第二期不同,已经不再是针对“西天”,而是针对“西方”了。它从清末民初之际开始。其中,有“五四”与“八十年代”两次思想高峰。
其实,宋人王安石就曾经总结说:“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于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于佛中。”从中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内部的自我对话以及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的对话,正是中华文明“天问”与“天对” 的第一期与第二期思想历程的根本取向。而在中华文明的第三期,中华文明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又将形成新的根本取向。其中,西方的理性思维固然可以给古老的中华文明以深刻启迪,而古老的中华文明的诗性思维,也必然给古老的西方文明以深刻启迪。在这当中,充盈其间的,恰恰还仍旧是人类中心论的、理性的、主体性的“人的自然化”的立场与“生命”的、“超主体性”的“自然界生成为人”的立场之间的冲突。其实也就是“实践”与“生命”的冲突。
再从纵向的古今角度看,百年中国现代美学,其实也无非两大美学思潮的双重变奏——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双重变奏。在其中此起彼伏的,还仍旧是 “生命”与“实践”的冲突。
这当然也就涉及对于现代性的深刻理解。所谓现代性,在康德看来,及时"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在鲁迅那里,则更是简而言之:“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而且,万变不离其宗,说一千道一万,根本的根本、合心的核心,无疑还是理性的觉醒,或者,无疑还是为世界祛魅。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我们的思考往往就停留于此,以至于始终无法看清百年现代中国美学的根本区别,因此也就无法把握其中的美学命脉。其实,为我们所忽视了的恰恰是,所谓现代性,其实又存在着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截然区别。
启蒙现代性,孜孜以求的是现代性的建构,与此相关的,则是对于工具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孜孜以求。审美现代性不同,它孜孜以求的是现代性的自我反省,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工具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自我反省。因为,在它看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4]因此,正如贝尔所说:“从一开始就有着共同的根源,即有关自由和解放的思想。……尽管两者在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同出一辙,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或醋,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启蒙二重性。类似于中国的“儒道互补”结构。启蒙现代性在现代性的建构中起着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审美现代性针对的是启蒙现代性的缺憾与不足,但是又彼此对抗与抵牾。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经济冲动与文化冲动的冲突、启蒙现代性与浪漫现代性的冲突、社会现代化与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启蒙与反启蒙的启蒙的冲突,现代性的反传统立场与现代性的反现代立场的冲突、宗教去魅与理性的去魅的冲突、以解构与反思去直面社会现代化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以至于在齐美尔那里,干脆就直接明确表述为“生命”(审美)与“形式”(社会)的冲突。
由此我们看到,从启蒙现代性出发,美学就必然走向实践。现代性的建构,自然离不开启迪民众,离不开改革社会,也离不开开发民智。因此,不惜高扬审美与艺术的现实功能,主张审美与艺术的主体性、审美与艺术的理性、主张审美与艺术的作为启迪民众的有效工具、主张审美与艺术的鲜明的社会功利性、主张审美与艺术的为政治改良和社会革命服务,也就被看作唯一的选择。总之,因为毕竟是在审美与艺术之外来讨论审美与艺术,是在启蒙工具的意义上来讨论审美与艺术的,因此,立足于启蒙现代性的立场的美学研究,其实更多的是借题发挥。最终把审美的性质等同于实践的性质.不但无视社会实践的异化性质,而且混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区别,更对于审美与艺术的的超越性、自由性视而不见,则是必然的必然。当然,实践美学的强调“适者生存”、实践美学的强调“自然的人化”、实践美学的强调“我实践故我在”、实践美学的强调审美活动是实践活动的附属品、奢侈品,也都是源于这一前提。
从审美现代性出发,美学则必然走向生命。属于“明天之后”与“未来美学”的生命美学应运而生。审美、艺术与生命之间的更为密切、更为直接的根本关系的得以呈现。审美与艺术成为解除理性束缚并且指向自由的生存路径,审美与艺术的超越现实的自由品格与解放作用也也得以凸显。人类因此既向美而生也为美而在,并且以“通过审美获得解放”作为资深的归宿。因此,“我爱故我在”“自然界生成为人”乃至“我审美故我在”,也就全都应运而生,因此,不但“因生命,而审美”的享受生命,而且“因审美,而生命”的生成生命。以生命为视界,以直觉为中介,以艺术为本体,诗与思的对话,就是这样地进入了人类的视野。正如范藻教授所说的那样:“因审美而生命,在潘知常的生命美学思考蓝图上,与其说是他为美学而发现的生命因由,不如说是他为生命而开启的美学通道。”[5]
当然,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对抗与抵牾格局最先是出现在西方,中国的情况只能说是基本类似或者彼此神似。稍显复杂的是,在中国,启蒙的批判与对于启蒙的批判,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所无可逃避的命运,导致的是所谓历时问题的共时解决。这,应该就是20世纪中国的特殊文化主题,也是20世纪中国的双重难题。然而,这一切也仍旧无法遮蔽我们对于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双重变奏的关注。
三、众多的中国现代美学家都关注到了美学第一问题
事实上众多的中国现代美学家都是关注到了这个美学第一问题的,例如,对于百年中国的现代美学,李泽厚先生就总结为“无人美学”与“有人美学”,无疑,其中的原因就正是敏捷地看到了上述的所谓双重变奏;杨春时先生也总结为“启蒙美学”与“现代美学”,无疑,其中的原因也正是因为敏捷地看到了上述的所谓双重变奏。只是,前者不太公正。本来在正视美学历史的时候,应该给双方以同等的尊重,但是李先生以理性、社会作为判断依据,并且因此而称(其实是“表彰”)自己的实践美学为“有人“,却把生命美学、生态美学、超越美学从动物、非理性的角度贬低为“无人”。后者则有点脱离了“现代性”这一中心。他所谓的现代美学,被游离于“现代性”之外了。因此,在我看来,最为简洁明快的概括就应该是: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主旋律其实就是两家:启蒙现代性的美学(实践美学)与审美现代性的美学(生命美学与超越美学等)。
以王国维为例,第一代的美学家,起码应该是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这“美学三英”,至于第二代的美学家,则最少也应当是方东美、宗白华、朱光潜这“美学三雄”。而在这当中,提倡生命美学的,起码要占四席。这就是:王国维、方东美、宗白华、朱光潜。而就中国的第一代与第二代的生命美学家而言,无论如何,都应该毫不夸张地说,王国维才是二十世纪生命美学的一代宗师。对此,我们只要想到王国维始终固守着生命视界,就已经足可为之赞叹,更不要说,在王国维,竟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把中国古代美学的生命传统从群体毅然还原回了个体。毫无疑问,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已经领略到王国维作为“但开风气不师”的先行者的敏锐眼光。须知,恪守自觉原则,忽视自愿原则,逃避自由个体、自由生命的建构,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生命美学传统的根本缺憾,走出这一缺憾,无疑正是时代的使命。而且,他敏捷地在西方寻觅到了叔本华、尼采等生命哲学、生命美学的思想资源,这无疑是为中国现代的哲学革命、美学革命平添了一个西方的渊源,而且也意味着他对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现代性要素的先天匮乏的敏锐洞察。这使得古老的中国美学得以顺利地跨越了自身的美学传统,也顺利地跨越了启蒙现代性的社会美学,迅速地与以早期现代主义美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美学成功对接。因此,即便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所有中国学人之中,王国维也是唯一真正进入了中国哲学、中国美学的现代思路的学人、唯一真正领悟了西方哲学、西方美学的内在奥秘的学人。
因此,意识不到上述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审美现代性以及“自由存在”、“我审美故我在”的转向,以及从中国美学的独立发展走向与西方美学的对话转向,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王国维的“卓绝”之处。百年以来,“生命还是实践”这个百年现代中国美学历程中的第一美学问题之所以成为美学讨论中最具优先级的问题,王国维功不可没!由此,始终关注着从王国维开始的美学道路,并且希望由此入手,寻找一条重新理解美学与美学历史并叩问美学新千年的现代思路,也就成为一代又一代的美学家们的共同思考。在这方面,当代中国的生命美学的崛起,则是无论如何都不容小觑的一次美学的首创与独创。
再以李泽厚为例,不难看出,他继承的其实是梁启超的美学衣钵(所以,他自己也常常自诩为“当代梁启超”),坚守的也是启蒙现代性的道路。而且,他所提倡的实践美学也确实曾经盛极一时。准确而言,在1979年前后,实践美学曾经达到了几乎是“一统天下”的顶点,遗憾的是,此后很快就走了下坡路。首先是高尔泰、潘知常,接着是陈炎、杨春时、张弘,都是对之加以严肃的批评,后来的新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也都是在反思实践美学的缺点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的。简而言之,从上个世际80年代开始,完全赞同实践美学的,几乎一个人都没有。几乎所有的人在提出自己的美学观点之前,都是从批评实践美学开始的。“解实践化”“泛实践化”乃至李泽厚自己的“弱实践化”,是其中的共同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去实践化”的共同趋势。不过,我们却是也恰恰因此而看出,从梁启超到李泽厚之间的一脉相承,因此,实践美学所遭遇的美学困局,无疑就是启蒙现代性所遭遇的美学困局。
总结上述思考,我认为:较为适宜的做法,是提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双重变奏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式,并且以之去总结概括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进程(当然,在这一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进程的主线之外,其他美学流派的贡献也理应得到应有的关注)。而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双重变奏的根本不同,则就体现在“生命”与“实践”之间的根本不同。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为“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6]的现代文明而深深忧虑的时候,曾经想到“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显然,以我之见,这应该就是以“生命模式”为导向的“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也因此,直面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去完成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无疑,也理应隶属于以“生命模式”为导向的“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
而且,倘若我们想到宗教业已黯然退场,灵魂旅程必须在宗教之外进行,因此美学的思考已经不仅仅是在谈论纯粹的美学问题,而且还是在孜孜以求现代文化的救赎方案、人类灵魂的救赎方案,也是孜孜以求人类生命本身的发展路向;倘若我们想到美学的思考涉及的是梁漱溟先生所关注的“中国问题”之外的“人心问题”,是对于“无神的时代”的人类所期待着的“无神的信仰”的积极回应——东方回应;倘若我们想到既然外在于生命的第一推动力(上帝作为救世主)并不可信,而且既然“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那么,生命自身的“块然自生”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了亟待直面的问题,并且更合乎逻辑地成为了美学亟待直面的问题,无疑就不难意识到“生命/实践”的哥德巴赫猜想的重大意义。
因此,“以美育代宗教”与“生命/实践”,堪称百年中国现代美学中的两个“哥德巴赫猜想”。一个是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命题,一个则是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美学问题。对于它们的回应,是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关键所在,无疑,也是百年之后新的中国美学的起点之所在。在我看来,这,应该就是我们对于百年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最为基本的美学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