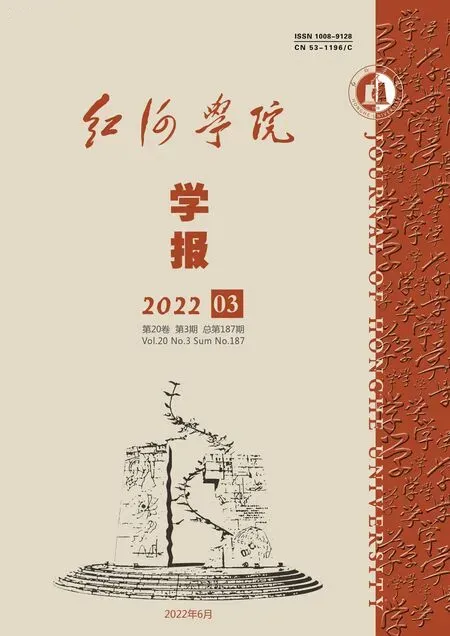论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疾病医疗叙事的转变
——从《摩雅傣》到《虎日》
2022-03-17杨运来
杨运来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疾病医疗叙事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集中体现在《摩雅傣》和《虎日》两部不同时代的电影上。季康与公浦编剧、徐韬导演的傣族题材电影《摩雅傣》(1960)采用的是一种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诉求的现代性叙事,而庄孔韶与王华编剧、王华导演的彝族题材电影《虎日》(2002)则采用的是一种以回归民族文化传统为诉求的文化叙事。这两部影片都以少数民族乡土社会为背景,但它们却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疾病医疗叙事,表达不同时期的时代诉求。这种转变反映了不同时期现代性与民族传统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不同定位,体现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秩序中的影响。
一 《摩雅傣》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羸弱不堪常常被列强比喻为一具病弱而急需救治的躯体。新中国成立后,“原来在外国列强眼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病弱需要救治的对象,现在则转换成国家内部中的少数民族是一个病弱需要救治的对象了。”[1]75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奴隶主、封建地主、土司等地方势力及其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则被视为陷人民于困苦和病弱境地的罪魁祸首,成为需要进行革命和改造的对象。在这里,旧社会制度及其反动阶级以及宗教迷信、风俗、习惯等文化传统成为少数民族疾病的隐喻;而新中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政策等则成为医疗的隐喻。1960年季康与公浦编剧、徐韬导演的电影《摩雅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摩雅傣》是一部以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为时代主题的影片,而其中的疾病医疗叙事则是借以表现这些主题的重要内容。影片一开始,傣族人民是一个受阶级压迫、受宗教迷信欺骗、受传统文化习俗束缚的困苦病弱形象。他们的困苦病弱被认为是旧社会的制度、阶级的压迫和落后的民俗风习所导致的结果,暗示需要对其进行革命和改造,即需要在总体性社会工程的设计下将边疆少数民族改造为与内地相同或相近的政治经济文化,从而实现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在这里,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进行现代性启蒙,将少数民族从疾病、落后和被压迫的处境中拯救解放出来。这一叙事暗合以现代性的视角表现“解放”“进步”“文明”和“发展”的时代主题。那个时代相关的电影还有《山间铃响马帮来》《农奴》《五朵金花》《天山红花》《草原晨曲》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一体化的现代性工程设计下,民族文化传统作为地方势力的意识形态成为需要被统合或改造的对象。《摩雅傣》暗示,现代性是少数民族的治病之策。作为现代性一部分的现代医疗高效地医治了少数民族身体上的疾病;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更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和实践,它们去除了少数民族人们精神上的枷锁,将他们从困苦病弱中解救出来。通过这样的疾病医疗叙事,《摩雅傣》进行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将边疆少数民族塑造为一个由病弱到健康、文明和进步的新形象,将新中国建构成一个自由、解放与和谐的民族国家。
这一时期,疾病通常与少数民族农村乡土、家族(家支)、宗教、习俗等传统文化因素相联系,这些因素被视为少数民族疾病的致病之因;医疗则与民族国家、医学科学、阶级斗争等这些现代文明相联系,这些因素被视为少数民族的治病之策。电影《摩雅傣》正参与了这一文学的疾病医疗叙事。《摩雅傣》首先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几近停滞、族群世居的少数民族乡土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疾病总是会不时地光顾这里的人们,“我们寨子年年都有,老人们说是有琵琶鬼放鬼,邻村曼赛闹琵琶鬼闹得还要凶呢!”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导致了这里傣族人们的迷信、野蛮和对宗教的顺从。吸大草烟的老人对岩温说:“波依汗的老婆就是因为放鬼让大家用火烧死了。”“一胎生两个是遇了鬼了,会给寨子带来祸事。竜巴头就领着一伙人把我们房子烧了,我(扎娜)刚生下孩子,就被打出了寨子。”傣族人们的习俗更是给这些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帐幕。寨子里发生疫病,岩温敲锣打鼓通知人们把病人送到医疗队救治,这里的人们不仅投以不信任的目光,而且心怀愠怒:“抬到城子里去?让孩子做野鬼吗?不行!死也要死在家里!”佛寺大佛爷为虎作伥,他不仅主持烧死依莱汗母亲的仪式,还借帮助人看病造谣诬害依莱汗,甚至恐吓岩温:“小伙子!你被那些汉人迷了心窍了,医疗队能医病,可是他能医命吗?”这里是一副由头人叭波竜、农村乡土族群、宗教习俗等构筑起来的帐幕,山寨头人们与寺庙佛爷正是通过这一帐幕对少数民族人们实行控制和压迫,疾病与医疗则是支起这一帐幕的重要部分。依莱汗的母亲被头领叭波竜欺辱并被叭波竜造谣诬害为“琵琶鬼”而被活活烧死;十七年后,依莱汗又被叭波竜与佛寺的僧侣佛爷借疫病(流行性大脑炎)造谣诬害为“琵琶鬼”,父亲因此被赶进大森林饥寒交迫而死,依莱汗也因此历经磨难。解放军医疗队、工作组、现代医疗等则是要冲决这一传统的帐幕,构建一个保护少数民族生命财产安全的新世界。在电影《摩雅傣》中,解放军部队拯救了依莱汗,并将她教育培训成为一位傣族医生——摩雅傣。两年后,她回到少数民族故土乡村,与解放军工作队一道和叭波竜、寺庙佛爷等反动势力以及宗教迷信、旧风陋习进行斗争。依莱汗给少数民族同胞带来了现代医疗,保护并哺育了扎娜的双胞胎孩子。最后,在现代医疗事实面前,傣族人们逐渐觉醒,“‘那些害人的风俗全都改掉了!’热梭抢着说:‘事情摆得很明白,你给(两个)孩子做妈妈,什么灾祸也没有降给你,鬼是没有的。过去竜巴头,还有那些有钱人,净拿鬼吓唬我们,骗我们。’”现代医疗将依莱汗和傣族人民从自然蒙昧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解放和新生。电影《摩雅傣》通过疾病医疗叙事表现了对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及其宗教、迷信、习俗等传统文化的斗争,通过斗争,少数民族人们从阶级压迫、蒙昧黑暗、疾病羸弱中获得解放。
二 《摩雅傣》中传统疾病医疗话语的隐约身影
电影《摩雅傣》表达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疾病医疗叙事对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的主导性诉求,但透过《摩雅傣》中的传统病因观、求医行为、治疗方式、医患关系等,我们仍然能看到传统疾病医疗话语的隐约身影。
(一)传统病因观
新中国初期,各种宗教迷信、鬼神巫术思想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盛行。不仅普通民众主要通过占卜、杀牲献祭等宗教迷信、鬼神巫术来祛病消灾,而且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也通过这种疾病医疗话语来进行族群或社区内部关系的建构和维护。如在信仰巫蛊的苗族传统社会中,“人们又对那些房族小、社会关系差人缘不好、迁居却不能融入当地社会的少数人进行想象和指控。巫蛊是一种对于他者的巫术想象和恶意指控,人们通过这种想象和指控力图构建和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权利关系。”[2]人们通过这种疾病医疗话语来对族群“异质”进行排斥和封锁,巩固族群内部的团结和自我认同。在《摩雅傣》中,傣族人们普遍相信,疟疾、流行性大脑炎等疾病是由于琵琶鬼等鬼魅在作祟。因此,傣族妇女们虔诚地到寺庙向佛顶拜、敬献礼品,请求神佛给孩子祛病消灾。“一个老头子,摇着满头的白发,也在一边说:‘这是有琵琶鬼在作祟,不是病啊!’岩温一怔。……岩温拉着刚才说话的老头子:‘谁说的有琵琶鬼在作祟?’老头子回答说:‘叭波竜说的,这事可一点不假,要不病能闹得这样凶吗?’”人们普遍认为,疾病是源于鬼魅的作祟或神灵的惩罚,医疗就是要人们牺牲献祭、巫师僧侣或其他通灵者通过祈祷以使鬼神息怒,只有这样才能祛除病痛、恢复健康。因此,尽管这种病因观在当时受到否定和批判,但对于当时的傣族人们来说却是一种合理的认知和重要的精神慰藉,因为这种思想观念已是其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民族传统的医疗基本上是一种家庭式的公开治疗,通常会有亲友的在场;而现代西医则通常是非公开的委托治疗,这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陌生的医疗空间。这种现代的治疗方式因人们的不适和疏离感而受到激烈的抵制和排斥。在《摩雅傣》中,小依珍弟弟得病了,叭波竜与佛寺的大佛爷到米爱金的家里为她儿子看病,他们的治疗是在大家看得见的氛围中完成的,所以获得了信任。岩温配合医疗队叫傣族老百姓到医疗队看病,但老百姓并不买账。“岩温面色忧愁,从这个寨子赶到那个寨子,站在寨口一边敲着铓,一边吆喝着:‘有病的小孩,快送到城子医疗队去呀!不要耽搁时间,医病要紧啊!’人们站在晒台上,不相信地看了他一眼,就关上了门。”后来民族医疗队也开始进入村民家庭进行治疗,依莱汗就是来到扎娜家里为她接生出双胞胎的。电影通过疾病医疗叙事表现现代医疗的先进、科学和进步,进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但也在不经意中反映了民族传统的疾病医疗话语对现代医疗话语的抵制,以及现代医疗对民族传统医疗某种程度上的妥协,显现出民族民间医疗话语的隐约身影。
(二)传统求医行为
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转型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转变,文艺的现代性叙事受到质疑。“现代性所有主要的‘解放叙事’……此类现代(意识形态)元叙事已丧失了可信性。普救论被驱除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让位于大量异质的、局部的‘小史’(petites histories)。”[4]这种“小史”性叙事逐渐代替宏大的现代性叙事,它批判科学理性对人性的贬抑,批判现代性一体化对地域文化的摧毁。这些“小史”性叙事深入到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寻求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以修复被破坏的传统社会和被侵蚀的民族精神。电影《诺玛的十七岁》(2003)、《美丽家园》(2004)、《可可西里》(2004)、《花腰新娘》(2005)、《吐鲁番情歌》(2006),以及2002年庄孔韶与王华编剧、王华导演的影片《虎日》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小史”性叙事。这些影片通过自然、社会、人的身体、人的精神的疾病来批判现代性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破坏与伤害,表达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和对民族主体性的追寻。
(三)传统治疗方式
在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应该结合事业单位管理的实际需要,建立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科学合理的设置事业单位的组织架构,完善事业单位内部的决策议事机制、授权审批机制,严格执行事业单位内部的不相容职务分离制度,强化信息内部沟通,进一步增强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此外,在事业单位财务内部控制管理方面,还应该重点加强财务监督管理,尤其是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对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结转和结余管理、专用基金管理、资产管理、负债管理等具体执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同时积极推进审计监督向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转变,及时发现解决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四)传统医患关系
影片《虎日》以疾病医疗为切入点表现了彝族人们通过民族文化传统对吸毒上瘾症的斗争。这里是一个偏远宁静的少数民族乡村,彝族家支头人们开会决定召开近50年没有开过的盟誓大会。家支头人们在大会上一致确认,现在的吸毒成瘾已经成为彝族社会的毒瘤,参加盟誓仪式的家支成员不得吸毒,已吸毒成员必须戒毒,毒贩子不得进入盟誓家支的地域。他们将彝族历法中向敌人宣战的“虎日”仪式转换为打击毒品传播的禁毒戒毒仪式。在“虎日”这一天,整个家支的男女老少都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来到一个四面环山的山坳台地(边上的一座山被认为是这个家族的神山),参加一个重要的盟誓仪式。“虎日”是彝族人传统上进行战争或其他重要军事行动的日子,现在彝族人们选择这个日子意在向毒品宣战以及戒毒的决心。在电影《虎日》中,彝族智者“德古”是当地的权威,他们精通彝文经典古籍和熟悉国家法律,他们多通过习惯法和宗教思想来平息纠纷,处理家支内部和家支间的具体事务,处理的过程都伴随着仪式和起誓程序。“虎日”仪式开始,家支头人手握象征吉祥征兆的新鲜牛胆猪胆宣布盟誓仪式开始,并发表激情的言说。接着毕摩头戴法帽、身穿法衣出现,毕摩是彝族社会的宗教师,他有着渊博的彝族文字典籍知识。在毕摩仪式的场景中,摆放着许多牺牲供物,毕摩用铃铛——“毕九”、扇子——“日土”等法器作法,诵读古老的彝族经文和咒语,毕摩用锋利的刀子切入鸡嘴的深处以示对盟誓食言者的惩戒。盟誓大会仪式后,吸毒人员回到家中举行个人家庭祈祷驱秽的“钻筐”“招魂”等仪式,以示获得新生。彝族家支大会、神秘的盟誓仪式、仪式中人们的盛装服饰、彝族的原始宗教仪式等场景在电影《虎日》里一个个地呈现,充满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蕴,表达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
我国高校的机构库建设在数量上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在建设的深度、影响力、参与度方面,与国外也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在机构知识库建设过程中要保持清醒头脑,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灰心丧气[6]。
三 《虎日》中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
“在传统的医病关系结构中,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择医求治,……病人对医生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医生自然对病人谈不上负责。”[3]而在现代西医中,医生成了医疗的主体,具有对病人的权威和责任。这种医治行为中“主体”位置的改变却在传统民族民间医疗中遭到了质疑和抵制。在传统医疗中,患者是作为主动的主体而不是作为被动的客体而存在。在《摩雅傣》中,小依珍的弟弟得重病了,叭波竜与佛寺的大佛爷到米爱金的家里为她儿子看病,这种传统的医疗方式使他们得出的诊断具有强烈的暗示效果和影响力,以至于叭波竜与大佛爷说米爱金的儿子得病是因为“琵琶鬼”依莱汗作祟,他们也就信了。拥有现代医疗的医院对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空间,他们对其充满着疑虑和恐惧。因此,后来民族医疗队也主动巡回上门服务,争取病人信任,而不再只是打敲锣打鼓叫病人到医疗队来治病。这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医疗中将医生作为主体而将病人作为客体进行被动处置的抵制,显示了以病人为主体的传统医疗的身影,反映了现代医疗对民族传统医疗某种程度上的妥协。
从《论语·子罕》可以看出孔子对“权”的评价:“可以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共学”、“适道”、“立”与“权”是治学的四个不同境界,孔子将权放在较高的的地位。懂得通权达变是尤其重要的。徐向群(2006)将其概括为,孔子的经权思想保持仁、礼的根基不动摇,即在坚持原则性的基础上,从其所处的时代出发,在特殊情况下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对经进行适当调整,对基本原则变通,进行损益。“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春秋繁露·玉英》)
在《摩雅傣》中,作为本族本土的村民,依莱汗对自己的族群和乡土有着天然的情感。依莱汗关心扎娜,亲自到她家里接生,并收养了扎娜生下的双胞胎。岩温为了同胞百姓的健康也呼号奔走,他“从这个寨子赶到那个寨子,站在寨口一边敲着铓,一边吆喝着:‘有病的小孩,快送到城子医疗队去呀!不要耽搁时间,医病要紧啊!’”这里尽管有政治的因素,但也包含了一种浓郁的乡土亲情,而重视乡土亲情正是民族传统医疗的一个重要体现。“新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通常是以革除地方文化传统为代价,如农业合作化运动、除‘四旧’等改造乡村的一系列现代性事件对乡土人情网络的破坏,这个时期代表国家的乡村干部也通常以强硬的形象出现。但重视乡土亲情的民族民间医疗话语却在无意识中反映了对民族乡土伦理的守护……同样是代表国家的乡村医生形象、同样是改造乡村的医疗活动,俨然更符合乡土伦理。”[1]81在电影《摩雅傣》中出现传统医患关系的身影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根基。此外,民族传统医疗话语还隐含在《摩雅傣》中的医疗内容上。在《摩雅傣》中,大佛爷是以念经文和咒语来给依珍看病的,傣族民间也用老虎的牙骨戳病人的胸肋来治病(治疗流行性大脑炎)。尽管这些医疗是作为新中国现代医疗的衬托和批判的对象而出现,被视为迷信、愚昧而遭到贬斥,但它们还是以其深厚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深入民众,仍然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时隐时现。
在素质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实行有效的小学生德育教育方法,怎样形成良好学生思想教育素养,是摆在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个值得深思的课题。下面我就结合自己学生教育工作的实例,浅谈几点我自己的认识和做法:
在《虎日》中,吸毒成瘾症和艾滋病等疾病正侵袭着凉山彝族的社会肌体,然而现代的自然科学方法不能有效地应对吸毒和艾滋病,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虎日”盟誓仪式成了治疗这些疾病的有效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族群认同、家族尊严、地方信仰、公序良俗等彝族传统文化共同参与到对吸毒成瘾症、艾滋病流行等问题的解决上。彝族人民采用的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透过“虎日”盟誓仪式运用彝族传统的习惯法、家支组织、信仰与尊严、亲情教化等民族传统文化来战胜人们现实中的疾病。在《虎日》里,彝族人们不仅依靠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激活文化传统,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所进行的自救。在这里,民族文化传统成为医疗的隐喻。
四 现代与传统的对话
如果说《摩雅傣》在通过疾病医疗叙事进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中,主要表现现代与传统的冲突,那么《虎日》则在通过疾病医疗叙事进行民族文化传统的回望和重建中,主要表现现代与传统的对话。《摩雅傣》和《虎日》两部影片都选择以少数民族的乡土世界为背景进行疾病医疗叙事,一方面是源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世居农村乡土这一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农村乡土也是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最为集中、最具生命力的地方。在《摩雅傣》中,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是一个主导性诉求,因此民族文化传统与疾病相联系,成为现代民族国家需要革命和改造的对象。依莱汗原来是被欺压凌辱、任人宰割的柔弱女子,经过解放军工作队和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医疗救治和改造,她变成了一位阳刚雄壮、英勇无畏的战士。这体现了女性阳性化的现代性思维以及现代性向传统乡土农村的渗透,展现了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冲突。同时,《摩雅傣》中的新生人民政权将家支(家族)活动解释为宗教迷信活动并予以禁止,现代医疗对身体疾病的治疗成为新中国消除地方传统思想观念和地方势力的隐喻。因此,疾病医疗总是带有一种阶级斗争的影子。这是一种权力取代另种权力、一种观念取代另一种观念的斗争,是现代民族国家一体化取代地方割据势力的暴风骤雨式的斗争,显示出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冲突。相反,《虎日》则是体现了男性阴性化的思维以及向民族文化传统和乡土世界的回望和重建。《虎日》中需要被拯救和改造的对象成了吸毒成瘾的男性,现代医疗不能很好地救治他们,民族文化传统为他们提供了可能。阴性化的农村乡土文化为现代性所产生的不安、焦虑、疾病等提供了缓冲、舒解和救治,民族文化传统像母亲阴柔的胸怀,容纳着现代性一体化的坚硬外壳。在《虎日》中,吸毒成瘾和艾滋病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而现代文明却又不能有效应对,彝族人民只能重新回到民族文化传统中来寻求自救,民族文化传统成了他们医疗的手段。在“虎日”仪式中,家支和家庭成员都视吸毒者为家支群体中平等的一员,而不像在现代化的戒毒所,将吸毒者视为一个与正常人相对立的角色,是一个需要被惩戒和改造的对象;“虎日”仪式的全民参与性本身也消解了所有的不平等,因为所有人都是禁毒和防治艾滋病的平等参与者。患者不必在戒毒所受到监禁,而是与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受到家支和家庭成员亲情的感化。在这里,患者获得了人性的关怀,获得了作为正常人的尊严,也增强吸毒人员戒除毒瘾的决心和意志力。这就是民族文化传统阴柔的一面对现代疾病的治疗。
在表现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中,《虎日》也隐含了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在宏观上,这里有着现代国家与地方传统的合作与对话,“虎日”疗法是在现代国家的认可下进行的,现代国家也是在“虎日”疗法中获得更有力的认同。在激烈竞争的全球化环境中,现代化不会停止,“现代化乃是一种理智化和效率化的过程,其效果则见于能有效地动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力物力,并且在国家体制的有效管理下和民族国家的理念之催化下,强化这一国家和地区。”[5]因此,现代医疗仍将是国家医疗体系的主体。但现代医疗在社会和民间也有着难以触及或不易奏效的领域,这就需要民族文化传统合法地参与到公共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建构中来。因此,新时期以来,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宗教信仰、家族伦理、习惯法等民族文化传统在公共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建构中发挥作用。基督教的公义、佛教的慈悲、儒教的仁爱以及各种民间思想兴盛起来,家族伦理、习惯法也逐渐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地方性思想观念。民族文化传统因其阴柔性的一面给国家的政治经济变革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弥合了社会急剧变革所带来的创痛,抚慰了受现代文明侵害的乡土世界。因此,《虎日》包含了对族群认同、家族尊严、地方信仰、公序良俗、习惯法等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极看法。但“民间宗教向自然宗法和鬼神崇拜方面收缩,由于民间宗教缺乏高级宗教所具有的内在自我调节机制(如神学和佛学的自我批判功能及其对教会或佛教徒群体生活的规约功能),它们的社会功能的模糊性更大:既可能稳定基层社会群体的人心秩序,亦可能为极端社会行为提供组织化的条件。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社会动荡,是在民间宗教逾越出意识形态的制度结构后发生的。”[6]因此,国家原则上反对家支家族的活动和各种自性宗教活动,因为它也可能发展成为无视国家政府权威和与现代性一体化相左的力量。在微观上,地方政府给予民间家支以适当权力,对吸毒人员进行文化戒毒和治愈后的监管(而这正是现代国家很难办到的),从而将戒毒工作消化在民族民间之中。这样既便于政府对家支组织的管理和控制,又“可以避免政府及其缉毒机构在高山峻岭的广大天地间疲于奔命的困境……将戒毒人员的监督教育工作转交给了家支”[7]。这样,吸毒患者所在家支和家庭也通常能给予特别护理和人道关怀。反过来,民族民间的戒毒活动也增强了政府对涉毒行为的行动能力。这是正是《虎日》中的疾病医疗叙事所体现的现代与传统的交流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