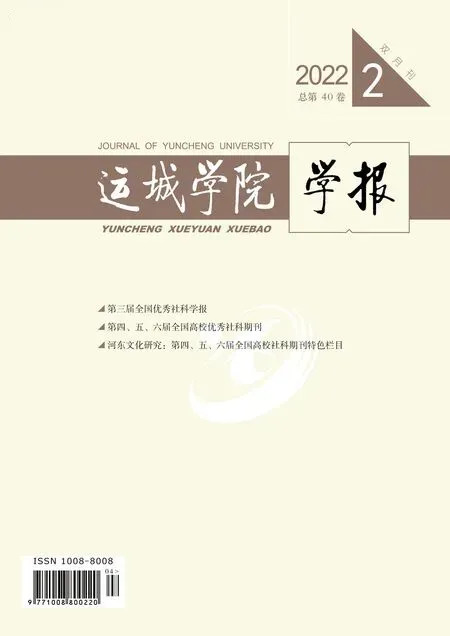道德主体的确立与德性生命的展开
——《论语·学而》第一章释义
2022-03-17肖俊毅
肖 俊 毅
(武汉大学 国学院,武汉 430072)
《论语》开篇第一章可谓家喻户晓,但人们对这一章的理解往往停留于文字表面,未经深入分析,其中所蕴含的隐微而深刻的义理往往被人所忽视。这一章是总领全书的纲要,是孔子教导学生为人为学、立身处世的根本要义之所在,其义理之精微处值得深入发掘。《论语·学而》第一章全文为: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一章共有三句话,分别描述了人生的三种状态,这三种状态之间表现为层层递进的内在关系,并渐次开显出了儒家淡泊高远的生命境界。从哲学的义理层面上看,这一章共由八个核心概念所组成,即:学、习、说、朋、乐、知、愠、君子。要探究这一章的义理结构,首先必须对这八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其意义进行一番深入辨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明白这三句话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联以及儒家思想是如何以此章为基点所展开的。
一、学习之说
“学”在《论语》中作为独立的语词凡64见[1]298,是孔门进德修业、立己立人的根本途径,也是一种涵育个体心性的教化之道。因此,孔子十分重视学习的重要性: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在孔子看来,每个人都必须经过学习、教化方可成就自我。但是,孔子所论之“学”并非是单纯地学习客观的经验性知识,而是注重主体自我的道德圆成;并非是单纯地追求知识理性的向外开拓,而是注重德性生命的内在体证。从孔子的几段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在第一则材料中,樊迟向孔子请教耕稼知识,孔子不予回复,并在樊迟离开后表达了礼、义、信等伦理价值在国家治理中要比耕稼等物质技能更为重要的观点。在第二则材料中,“俎豆之事”代表礼乐,“军旅之事”代表军事知识、技能,在孔子看来,军事知识与自身的主体生命和道德修养无关,不是君主所该关心的事,且为了争夺利益而征战杀伐有违仁义之道,是故孔子避而不谈。在孔子看来,礼乐是由人的内在之仁心而生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这是每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也国家秩序赖以维系的伦理基石,其在本末层级上是高于“军旅之事”等知识技能的,君主应致力于礼乐教化之事,而非殚精竭虑于军事杀伐之事。在第三则材料中,子贡认为孔子的学问是“多学而识”,即学习大量的客观知识,而孔子则强调自己学问的根本是一以贯之的“道”。由此可见,孔子所重视的“学”并非是单纯地对于外在知识的追求,而是注重道德主体的挺立,通过不断地学习以涵育品行高尚的君子人格。
牟宗三先生说:“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2]7确然,儒家从孔子伊始,其所关怀的主要对象便是人的主体生命,而非客体外物。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器”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特定的概念,与“道”相对。《礼记·学记》:“大道不器。”[3]3304《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171“道”是无形无相的形上本体,“器”则是有形有相的具体化的万物,孔子说“君子不器”则意味着君子的终极关怀当是超越性的、与人的内在生命相贯通的“道”,而非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知识、技能之中,将主体生命旁落于客体外物——“器”——之上。然而,孔子并非排斥知识与技能,而是将客观的知识技能统摄于“道”之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根据孔子这句话断定儒家拒斥专门性人才:“受过儒学教育的候补官员出身于旧传统家庭之中,在他们的心目中,欧洲式的专业教育只能误人子弟,教人俗不可耐,很难办成什么好事。这里无疑有一部分是对任何西方式的‘变法维新’的顽强抵抗。‘君子不器’,这个基本原则的意思是:他是自我目的,而不像工具那样只能派一种专门用场的手段。”[4]231在韦伯的现代官僚政治理论中,理性的政治形态应是专家行政,即由掌握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来承担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孔子“君子不器”的思想却排斥知识与技艺,阻碍了政治的理性化进程。韦伯的这一观点对儒家思想存在严重误解。孔子“君子不器”的思想在于确立人生的根本意义,即对“道”,对主体生命的终极关怀,并非排斥对知识、技能的学习。道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本末关系,而非处于相互排斥的对立面。《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5]3,即是此意。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也表明了这种关系,“先立乎其大者”便是要挺立道德主体,成就君子人格,只有这样,其他的一切知识技能才能被合理地掌握与利用。因此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之言为孔子的思想作出了完善的注脚。孔子论“学”,最根本的目的便在于修身,涵育一颗仁爱之心,成圣成贤,知识则处于次一级的地位,被“仁”与“道”所统摄。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这表明,孔门所重视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践行仁爱之心,这是学问之道的根本。孔子亦有相似之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亦认为践行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是人生之大本,学习文献知识则居于次要地位,同时也可看出,孔子并非拒斥知识,而是说在培育了内在之仁心、践行了道义之后,有所余力便可去学习文献知识充实自己,这正是《大学》所强调的本末关系的义涵。
孔子重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主体性贯穿了其思想体系的始终,是其一切价值理想的出发点和根源性动力: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
在孔子的思想中,真正的好学之人是坚守道义、谨言慎行、忧道不忧贫的君子,学问与人的主体性道德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还可从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中看出: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
《论语》中两次出现孔子称赞颜回好学,而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是淡泊高远、忧道不忧贫的典型。因此,孔子称赞颜回好学,即是认定学问之道的根本在于道德主体的挺立与君子人格的培育。孔子的弟子对待学问之道亦有类似的态度: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
可见,学以致道、笃志于仁是孔门论学的根本旨归。“学”强调的是主体性的进德修业的学习,即“为己之学”,同时,这种“学”又含有一种宗教性、超越性的维度,即“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通过自我德性生命的圆成从而与天道相契合,实现“内在超越”的生命境界。
由此,《论语》以“学”作为开篇之要旨,从而确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展现了孔子对人的内在生命的关怀,孔门之教化便是以此为基点而展开的。
在“学”的同时,孔子又强调“习”。“学而时习之”的“习”,何晏注为“诵习”[3]5335,皇侃注:“‘习’是修故之称也。言人不学则已,既学必因仍而修习,日夜无替也。”[6]3朱子注:“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又引程子之言:“学者,将以行之也。”又引谢氏之言:“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立时习也。”[5]47可见宋儒将“习”理解为与“行”相呼应的“践习”“修习”。杨伯峻先生考证古文献中的“习”含有习礼乐射御等现实性的内容,因而将“习”解释为“实习”“演习”[1]1,其说可从。概而言之,“习”有诵习、温习之意,更有与现实行为相结合的践习、修习之意,也即是“行”的维度。在孔子看来,道德人格的培育是一个合于内外的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个体心性的修养工夫,而且还需要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将内在之仁心践行出来,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即是合内在之仁心与外在之礼节于一体的涵养状态,这也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理路。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又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孔子重视在道德实践中发显内在之仁心,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并在此一“践仁”的过程中不断充盈内在之仁心,成就完满之人格。孔子与子贡的对话中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孔子认为真正的仁者能够将内在之仁心从身边的细微处渐次推广,从而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倘若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不仅可称之为仁者,更可称为圣者。可见,孔子对于仁与圣的价值评判不仅是基于内在的心性修养,更是基于其在现实的道德实践中的落实程度。
《论语》中还有一段对话,直接道明了孔子对于“行”的认识: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忠信、笃敬均是孔子教学的基本德目,而这些德目都具有高度的实践性特质,是必须落实在现实世界中的道德实践活动。所谓“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便是强调“学”与“习”的一体性,必须随时随地将自身所学之道践习出来,不敢有丝毫懈怠。这体现了孔子将内圣与外王相互贯通的整体性思想。
正是因为“学”与“习”具有一体性特质,故而孔子不仅开辟了主体性的内在道德世界,而且还更将此一内在的德性生命发显于外,从而开拓出了践行生命价值的广阔空间。可以说,孔子的生命境界是消解了主客对立而全幅展开的人文精神的世界。
通过对“学”和“习”这两个概念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而时习之”一句展现了孔子对内在德性生命的深切关怀和对生命呈现状态的高度关注。“学”确立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主体地位,而内在道德理性的完满可引导主体自我去实现其存在性价值,开展道德实践,同时,在现实世界中不断践行仁义的过程又反过来促进了自我生命之凝练、道德品性之涵育。经由“学”与“习”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内圣与外王便贯通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种生命关照之下,人心中便自然流淌出了“说(悦)”的情感。
关于“说”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孔子有一段话可作为参照: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
可见,在孔子看来,“说”是人人皆有的情感,但却有君子之“说”与小人之“说”的区分,君子之“说”是以道为悦,而小人之“说”则枉顾道义,以身外之物为悦。很明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说”无疑属于君子之“说”,这种“说”并非物交于物而产生的观感之悦,而是一种内在的对生命意义、对“道”的体证之悦,是一种自得与自足的生命之悦。这种“说”源自于“学而时习之”的德性生命的全幅展开。君子通过“学”挺立道德主体,存养内在心性,同时在家庭、社会乃至家国天下的政治领域中推行自己的道德理想,将内在之仁心向外拓展,通过道德实践施及万物,倘若真正实现了这种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至高境界,其德性生命便已臻至圆满自足的至圣状态,由此,其生命体验中、其道德本心中便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说”的道德情感,这是一种崇高的生命情怀。从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中亦可反映出这一点,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朱子注:“颜子于圣人之言,默识心通,无所疑问,故夫子云然。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5]125朱子的注解完整地阐释出了孔子之言的深层含义。颜回对孔子之“道”所表现出的“说”正是一种德性生命的全幅展开之“说”,孔子对颜回能够默识体证“道”之广大而深表赞许。
由此可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可谓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要义,也是孔子一生所努力贯彻的最根本的人生态度,其所显现出的是一种道德主体的确立与德性生命的全幅展开的至高境界,其所流露出的是一种对“道”的不懈追求与默识体察的生命之悦。这句话总领《论语》全书,是孔子对其人生哲学所作出的最凝练、也是最深刻的表达。
二、朋来之乐
有了“学而时习之”的涵养与成就,德性生命的光辉自然发显于外,感化他人,于是便形成了第二种人生状态,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关于“朋”,何晏引包咸之言:“同门曰朋”,邢昺引郑玄注《周礼·大司徒》:“同师曰朋,同志曰友”[3]5335,此古注将“朋”解为同在师门受业者。朱子注:“朋,同类也。”[5]47古代很多文献中引用此句时将“有朋”之“有”写作“友”,程树德先生通过考证认为:“作‘有朋’者,《鲁论》也。作‘朋友’者,《齐(论)》《古论》也。”[7]6-7繁复的字词训诂与本文宏旨关联不大,不必过分纠结,单从义理上而言,此句话大致表达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与自己切磋论学的意思。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朋友会不远千里而来?其内在动因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便需要联系上一句的文本,从上下两句话之间的内在承接性入手去思考。
很明显,“学而时习之”与“有朋自远方来”不是孤立的两句话,二者之间存在着前后承接的关系,后者的实现必以前者的落实为前提,前者的达成也自然会产生后者的归往。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层次上来看待:
首先,君子通过“学”与“习”的人格养成,使自我之道德主体得以充实完善,德性之光辉远播四海,于是,海内的仁人志士均被其所感召,自然会慕名而来与之结交。《周易·系辞上》引孔子之言:“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3]164,正表达了这样一种人生状态。这表明,在孔子看来,交友之道的根本在于修善己身,只要自我之心性涵养充盈完满,以仁义忠信待人,成就高风亮节之品性,志同道合的君子仁人自然会聚合至我身旁,所谓“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是也。因此,交友不必费尽心思刻意为之,更不必依靠各种外在的社交技巧谄媚于人。
其次,君子通过“学而时习之”的德性涵养,确立了对“道”的信仰与坚守,于是必然会生发出“好善恶恶”的道德情感以及对于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表明“仁”作为价值本源具有内在决断的能力。由此,落实在交友问题上时,君子必然会根据交友对象的内在品格而作出慎重选择,所谓“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孔子依据道德原则对人群作出不同的区分,从而与品性正直、志同道合的君子交友,而对于被世俗社会的种种不良习气所熏染的人,孔子则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甚至“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对于交友的类别以及自身所处的群体环境非常重视,这一点从孔子的其他言谈中亦可看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论语·阳货》)。因此,孔子交友处世的原则是亲近善人君子、结交益友,同时远离品行低劣的小人、拒斥损友。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品性与志向的人自然便会聚合为不同的社会团体,并相与为伍。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君子对于“道”、对于善的执着坚守,以及对于违道行为、对于恶的强烈排距,所以君子在交友群体的选择上慎之又慎,其人际网络的建立是以共同的信仰与志向为界限的。正因如此,君子与君子之间才能够产生一种内在向心力,从而聚合在一起切磋琢磨、讲学论道,正所谓“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由此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孔子说的是“有朋自远方来”,即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赶来,而不是其他的无志于“道”的人从远方赶来了。换句话说,君子对道德价值的强烈坚守促使他只会寻找志同道合的君子为伍,而拒绝与小人交友,另一方面,小人因其道德本心的缺失也无意与君子结伴。如此一来,“有朋自远方来”便成为了君子“学而时习之”之后的一种自然的交友状态。
基于以上分析,“有朋自远方来”的众所归往绝非偶然,而是“学而时习之”之后所呈现出的一种必然的人生状态,而这样一种友人相聚的状态自然是可“乐”的。上文已述,“有朋自远方来”表达的是与自己志同道合、有共同理想与追求的君子远道而来,一起切磋琢磨、谈经论道,这是传统文人雅士间的交往之乐,是一种辅仁共勉的仁者之乐。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乐”作为一种人皆有之的个体情感亦有正面与负面的双重区分,“乐多贤友”正是对自身进德修业有所补益的正面情感,是志士仁人所独有的精神交往之乐。
关于“说”和“乐”的区别,邢昺注解:“谯周云:‘悦深而乐浅也’,一曰:‘在内曰说,在外曰乐’。”[3]5335皇侃言:“‘悦’之与‘乐’俱是欢欣,在心常等,而貌迹有殊。悦则心多貌少,乐则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讲习在我,自得于怀抱,故心多曰‘悦’。今朋友讲说,义味相交,德音往复,形彰在外,故心貌俱多曰‘乐’也。”[6]4朱子引程子之言:“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5]47可见,传统经传注疏对这一问题已有较为深入的辨析。从总体上看,“说”和“乐”这两个概念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分,都是对于仁者的生命状态与心灵境界的描述。但从具体上看,二者所描述的状态之间又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说”是由“学而时习之”所生发出来的情感,是在德性生命全幅展开的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一种自得与自足的内在情感;而“乐”则是由“有朋自远方来”而产生的情感,是与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共同讲学、切磋于“道”的精神交往之乐,这种“乐”因为由君子群体间的交往互动所产生,因而存在着发散于外的向度。
综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承接上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而来的,前后两句话之间在义理上有着递进关系。正是因为有了“学而时习之”的德性生命的展开,才会产生出“有朋自远方来”的结果,从而达成君子之交,并在这种心灵的交流互动中生发出“乐”的情感。马一浮先生说:“悦、乐都是自心的受用。时习是功夫,朋来是效验。悦是自受用,乐是他受用,自他一体,善与人同。”[8]34-35确是这两句话所表现出的思想境界。
三、不知不愠
有了以上的生命积淀,接着孔子又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句又是承接上文的两句话而来的。“愠”是愠怒、生气之意。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君子能做到“人不知而不愠”?“不知”的内容又是什么?换句话说,别人不知自己的什么事情?要回答这些问题,同样必须从此句话与上文两句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入手进行考察。
从“学而时习之”与“人不知而不愠”的关系上看,“学”所凸显的是主体性的“为己之学”而非功利性的“为人之学”。此时的“人”泛指主体以外的一切客体与他者。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为己”便是彰显“学”的主体性特质,“学”是以自我德性生命的完满为终极指向,具有高度的个体性与内向性;“为人”则是将主体生命旁落于客体外物之上,是为了实现某种外在的目的,求取别人表示赞赏与认同。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表明“仁”是由主体自我的内在动力来完成,不需要依附于任何外在的力量,更不需要依赖于他者的评价。概而言之,“为人之学”取悦于人,“为己之学”不求人知,也难以为人所知。仁者对“道”的默识体证、对生命的感通只能自己心所独知,故而孔子有“莫我知也夫”(《论语·宪问》)的慨叹,并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表明孔子所追求的生命之“学”具有主体性与独知性的特质。基于此一特质,“人不知而不愠”自然便成为了仁者的情感状态。综合来看,“人不知而不愠”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1.“为己之学”只求自我之内在生命的通透与圆满,不求为外人所知,是以不愠;2.“为己之学”以及孔子所论之“道”具有独知性的特质,只能通过一己之心的默识体证来实现,其过程本就难以为外人所知,是以不愠。同时,此处“不知”的内容也有两个方面:1.别人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我自身所完成的内在生命体验之“学”;2.别人不知道也无法切实体会到我自身通过“学而时习之”的过程所产生的“说”的生命情感。可见,由于孔子所论之“学”具有独知性的特质,“人不知”便成为了一种自然的现象,因而君子不会也不必对别人不知道、不理解自己而感到愠怒。君子做学问并不断践习完全是为了自我之主体生命的通透与超越,而不是为了表现给别人看,赢得别人的赞赏与认同。因此,“人不知而不愠”是在“为己之学”充分落实之后所自然呈现出的一种崇高的君子风度与人格修养。
从“有朋自远方来”与“人不知而不愠”的关系上看,“朋来之乐”是君子群体聚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精神交往之乐,是志同道合之人所共享的心灵之乐,那些对“道”、对真善美缺乏信念与追求的人是难以体会这种崇高的情感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此时的“人”则指圣贤君子以外的一般人或常人,因其德性修养与生命追求较低,故而难以体会君子群体所处的生命状态与生命情感。对于君子群体而言,“朋来之乐”完全是发自于其群体内部的一种自足之乐,只有处于此一群体之中的人方可领会,不足为外人道,所以,德性修养较低的人自然无法理解君子们的心灵之乐,君子不会也不必因此而感到愠怒。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人不知而不愠”一句与上文“学而时习之”和“有朋自远方来”两句话之间在义理上均有着密切联系,正是因为上文的两种生命状态的充分展开,“人不知而不愠”的修养境界才能够得以实现,故而孔子感叹“不亦君子乎”。此处还须对“君子”一词的内涵略作一番探讨,以便说明为什么实现了以上生命状态的人会被孔子赞许为君子。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共出现了107次[1]238,其词意有时指代有德者,有时指代有位者。从语词的历史流变上看,西周时期已有“君子”一词,阎步克先生指出,此时“‘君子’既是包括‘王’在内的贵族统治阶级之尊称,同时又是个道艺礼义拥有者的美称。‘君子’这种角色形态,不仅显示了‘尊尊’与‘贤贤’的一致性,甚至还显示了‘亲亲’与‘贤贤’的一致性,因为‘君子’之‘学’是以‘尊尊’‘亲亲’为内容的。”[9]88因而,“‘君子’这种特殊社会角色则是尊者、亲者、贤者或君、父、师的三位一体。”[9]416也就是说,此时的君子既是有德者又是有位者,既掌握了政治管理的职能又掌握了文化教育的特权,呈现为一种“官师合一”的形态。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学术文化逐渐从上层贵族的垄断中分离了出来,下落于民间社会之中,此时,政统与道统、德与位也开始分离,贵族掌握了政统(位),而道统(德)却由学士群体所承担,因此,原先表示德位合一的“君子”一词,现在则分化为有德者与有位者这两层不同的含义。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分化导致了“君子”一词语义的分化。因而在《论语》一书中,“君子”一词有时是就“德”而言,有时是就“位”而言。
在《学而》第一章中,“君子”明显指代有德者,是孔子根据人的内在修养所作出的一种群体划分,一般与“小人”相对成文。在《论语》中,“君子”所涉及的德性义涵非常广泛,本文限于篇幅,难以对其作出全面的论述,此处仅选择与本章相关的几点作一番简要概述。
在人生志向上,君子以“道”为终极追求,不计较现实生活中的贫贱得失: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这几句话是对君子生命追求的最佳描述。君子在贫贱困苦之中依旧能够坚守理想,并自得其乐,所谓“孔颜乐道”,正是对这一生命境界与生命情感的描述。
在实践层面上,君子慎于言、敏于行,积极开展道德实践,践行内在之仁心: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孔子强调君子应当具备求真务实的品性,以行动为本,切勿巧舌如簧、虚饰浮夸。
在社会群体的交往中,孔子强调:“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之间的交往是以“道”为基点而展开的,并非基于利害关系,因此不必党附。
从上述几点可以略窥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所应当具备的德性生命的高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才有了“不亦君子乎”的慨叹。从“学而时习之”到“有朋自远方来”最后实现“人不知而不愠”,完成了这样一种渐次递进的生命开展过程,便可谓具备了君子的人格境界。
四、结语
《论语·学而》第一章是总领全书的纲要,点明了孔子以教化为本的“学”之特质,揭示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哲学理路,展现了一种淡泊高远的生命境界与自得于心的生命情感,可谓孔子思想的根本要义之所在。
此章三句话分别描述了三种渐次递进的人生状态。“学而时习之”体现了经由道德主体之确立从而开展道德实践的过程,并由此在内心中自然生发出了“说”的生命情感。继而,由德性生命的全幅展开招致了“有朋至远方来”的群体聚合,并产生出了君子之间的精神交往之“乐”,这是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所共享的心灵之乐。在完成了前两种人生状态的基础上,主体自我自然便具备了“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境界。“为己之学”不求人知,也无法为人所知,因而只能自心所独知;“朋来之乐”是由君子群体内部的交流互动所产生,一般人自然无法理解这种君子之乐。由此,“人不知而不愠”便成为了君子修养的自然结果。此章三句话之间存在着相互承接的递进关系,共同串联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并渐次开显出了孔子为人为学、立身处世的根本原则及其所呈现出的生命状态,其中隐微而深刻的义理值得细细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