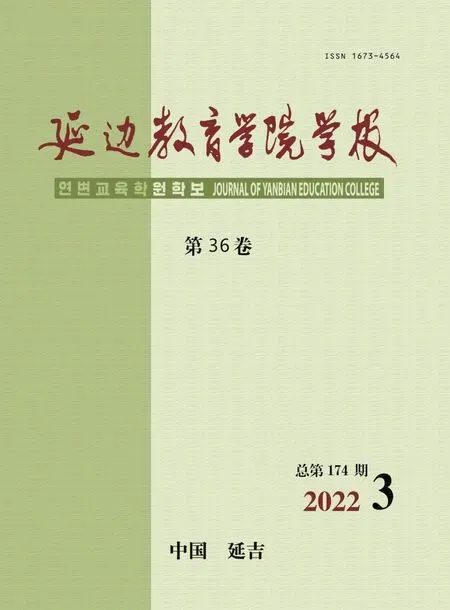浅析陶渊明对左思咏史诗的继承与发展
2022-03-17朱林
朱 林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以咏史为诗始于东汉班固,至西晋左思《咏史》诗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而具有强烈的个性表现。左思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1],清人何焯言“太冲多自摅胸臆”,认为左思的咏史诗超越了前人就史论史、为咏史而咏史。东晋陶渊明诗的咏史诗作虽然不多,但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1]钟嵘评价陶渊明的诗歌“协左思风力”,认为他与左思同得建安文学之精髓,思想感情鲜明爽朗,语言质朴刚健,风格遒劲。在咏史诗的发展中二人均占有重要地位。纵观左思与陶渊明的咏史诗,既有秉承的相似之处,同时又各具特色。
一、陶渊明咏史诗与左思咏史诗的内向性
左思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是其五言《咏史》诗八首。全诗并非作于一时,却以作为一介寒士的耿直风骨与精神气度为线,直指门阀制度重压下寒士壮志难酬的社会现实。《咏史》八首旁征博引,列举了英俊人物主父偃等四贤沉埋下僚,荆轲、高渐离等卑贱者睥睨四海,慷慨悲壮中又有苏秦、李斯等人求富贵而丧生,他在诗中并不是要对上述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和作出历史评价,而是从天下寒士的共同命运中悟出人生真谛和启示,因此他使得咏史诗具有了内向性,具有了自我思考的倾向。“左思的《咏史》诗共八首,并非专门咏叹古人古事,很多情况下是书写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怀”。[2]而陶渊明的咏史诗也同样并非单纯地怀古、崇古,而是以古喻今。“他将目光转向了古代,儒道固穷守节、安贫乐道赋予他精神力量,而古代的同行者又给他以榜样的激励”[3]。陶渊明的《咏贫士》历咏前代贫士,赞美他们既安贫乐道又拥有无上的道德,以表自我要以各种高士为典范,固穷守节不改初衷。从这一点上说,陶渊明延续了左思以史抒怀的范例,他沿着左思所开创的咏史诗借史抒怀的道路继续前行。不同的是左思“八首《咏史》诗体现其不断变化的思想”[4],由进可为国立功、退可揖归田庐的平生抱负最后无奈转而作出悲凉凄怆的退居乡野的选择,展现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的思想变化。而陶渊明的咏史诗却坚守故辙,始终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究其原因在于二人所处时代与社会地位不同,左思属西晋寒素之士,在当时统治阶级门阀垄断的制度下屡不得志,他向往歌咏隐逸生活而又想成就一番事业,因此他的思想与感情始终徘徊在仕与隐之间,仕而不得便看透世事隔断抱负,守着洁身自好的美好追求隐世而居。陶渊明的咏史诗则大多作于他辞去彭泽县令之后,此时他已无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的选择困扰,而是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相违背,因此其咏史诗中思想恒一,坚定固穷守节的归隐之志。
二、图景式呈现历史人物与诗中的精神合一
左思的《咏史》八首因并未作于一时而思想感情比较复杂,他的咏史诗早已超出了一人一事的叙述范围,且每一首均可独立。左思《咏史》八首并不仅仅控诉门阀制度,他精心选择史实,列举了段干木、鲁仲连、许由、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苏秦、李斯等十几位历史人物,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出现在同一诗中,多引史实,形成了一幅形象万千又内涵丰富的人物图,真切关注到历史事件背后的个体生命。左思在错综复杂的史实中展示了以上三条寒士不同的人生道路,进而由人思己“吾希段干木”“吾慕鲁仲连”,他想以己报国又想功成身退,然而现世“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他又想像许由一样不营世利隐居山林,又想像荆轲一样酒酣高歌般洒脱,这不难看出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正因为他深深的思考,有对自己人生出路的苦苦追寻才使《咏史》八首以组诗形式出现,每首又超出了一人一事的叙述,在历史的抒怀与追寻答案中始终有自我该如何影子的存在。这种不加分类,不重点分析,呈现历史人物图景式的咏史诗也可看作是早期咏史诗的特色。
而陶渊明的咏史诗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陶渊明的《咏贫士》《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等咏史诗从题目上便可清晰看出所咏历史人物。《咏贫士》总共七首,同左思的《咏史》诗一样均为组诗形式,却是一个完整体。其以一二首为纲,述说自己宁愿忍受饥饿寒冷也要力守故辙作一隐士,接下来的三至七首列举了古代隐居的贫士或失志的贤士,分别为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慰、黄子廉,除第三首、第五首于一诗中提及两位隐士,其余均是一诗议一人之事。如果说左思的《咏史》八首借所列举的历史人物体现对个体生命的关照,进而探寻自我作为一介寒士的出路,那么陶渊明的咏史诗则要以这些贫士、隐士为榜样,把他们作为审美对象,与他们的精神合一,证明自己所选择的隐退道路是正确的。陶渊明自辞去彭泽县令后便隐居避世与自我达成和解,左思的出世思想不得已而为之,是无奈的选择,陶渊明的出世则是自愿的结果。他摒弃掉对世俗门阀以及晋宋易代之际复杂政治环境的批判,只求返归自我,恢复清静自然的本性,保持宁静、淡泊。相对于左思列举出历史人物与事实而不作展开描述,不作具象的人物事迹阐发,陶渊明的咏史诗则专注于一诗议一人之事,“不可能所有人的经历都与他一致,但这些人的精神内质都与陶公想通甚至合符之处”[5],更妙在切合诗人本身行事。
三、直观的史事观点与解读的无限可能性
钟嵘《诗品》置左思为上品,评其诗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可见,左思的《咏史》八首情感多在一“怨”字上,究其原因,既为咏史诗,包裹了个人情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个人色彩。纵观左思的《咏史》八首“史事与观点之间关系直接而简单”,一史实对应一观点,就事论事,如“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只是说明金日磾、张汤两家子孙亲近,七世得荫,暗示当下腐败无能的世族子弟早踞高位。再比如《咏史》组诗第六首中写荆轲的英雄气概“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来说明荆轲高视不凡。左思透过列举的历史人物及他们的事迹所要表达的旨意单纯且明确,并不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与解读的无限性。他先写荆轲与高渐离慷慨悲歌旁若无人只为引出他们蔑视豪门势族的英雄气概,这种“史实+结论”的写法使左思的咏史诗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广义的咏怀诗。
反观陶渊明的咏史诗,他的《咏三良》《咏荆轲》《咏二疏》都作于晋亡之后,基本是同时所作,这三首的诗体大致相同,互相阐发。南宋汤汉注说:“二疏取其归,三良与主同死,荆轲为主报仇,皆托古以自见云”。学人又多认为《咏荆轲》是诗人愤于宋武帝刘裕的弑夺之变,想求如荆轲那样的人物为晋报仇,是出于忠晋报宋而作。清代经世派学者陶澍《靖节先生集》卷中载《咏三良》“此诗悼张祎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陶渊明的咏史诗在托古述怀、寄寓感慨的一般意义上有着无限解读的可能性,诗中的荆轲、“二疏”“三良”又可以看作是诗人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究其原因在于陶渊明的咏史诗直接的抒情和评述较少,但倾向鲜明、爱憎强烈自在不言中。他较左思相比,站在历史的高度,跳出焦虑的社会心态,用与历史人物精神合一的眼光来深情礼赞!再比如可归于咏史诗类的《读山海经》十三首用简妙的语言对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神话世界里的人物被赋予了无限意蕴与丰富的审美怡悦,既可说这些诗中寄托了陶渊明自己一生的心事,又可与他其余咏史诗并读参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