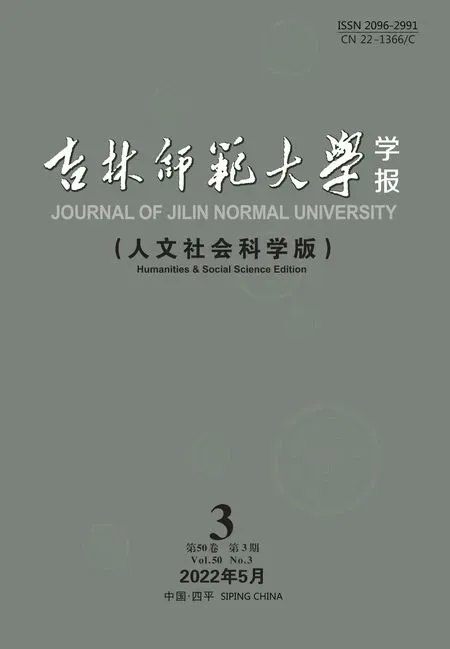林黛玉“恶梦”的神话原型式解读
2022-03-17张丽红李晓瑞
张丽红 李晓瑞
(吉林师范大学 东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一、《红楼梦》梦书写的意义
《红楼梦》在表现贾宝玉的现实故事之前,创造了一个“石头记”神话故事,又把这个“石头记”神话嵌入了贾宝玉的现实故事之中;《红楼梦》在表现诸多女性悲剧命运之前,还以贾宝玉的“太虚幻境梦”再造了一个女性悲剧命运的神话,即“金陵十二钗簿册”和“红楼梦仙曲十二支”,使《红楼梦》的女性悲剧命运成为“金陵十二钗簿册”和“红楼梦仙曲十二支”神话的重演。这便构成了《红楼梦》一个最重要的创作方式:神话决定现实、现实重演神话。
《红楼梦》这种大结构的创造方式同样是曹雪芹创作人物的方式。在许多重要人物的塑造中,曹雪芹都是或先或后地表现人物的梦,人物的梦就相当于人物的一个神话原型,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情感、命运遭际则是那个相当于神话的梦的重演。
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林黛玉的“恶梦”出现在小说的第八十二回,但它的书写与前八十回脉络完全一致。从这一点,似乎也可以就《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展开思考①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问题,是学界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话题,红学界诸多大家都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是曹雪芹的原稿,如海外红学家周策纵先生、台湾红学家高阳、台湾著名学者白先勇、中国红楼梦学会首任会长吴组缃、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吴新雷先生、宁宗一、郑铁生等都持这种观点。。林黛玉的这个“恶梦”虽然不像甄士隐、贾宝玉、甄宝玉等人的梦那样具有非常典型的神话特性,但是,这个梦和《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的其他梦的象征性质是一致的,仍然是作为人物的神话式的梦来表现的,仍然是将梦作为现实生活的原型来呈现的。
二、林黛玉神话式的梦
林黛玉的这个“恶梦”不仅表现了林黛玉的内心深处的极度恐惧和渴望,还表现了林黛玉的心理原型,甚至命运原型。书中对林黛玉恶梦的产生先进行了前期的环境铺垫。
曹雪芹极有层次地描写了黛玉做梦的起因:袭人对自己命运忧虑的情绪感染了林黛玉,袭人揣测贾母、王夫人和凤姐露出将来要为宝玉娶黛玉的意思,林黛玉是不清楚的;而那个婆子“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的话更牵引了林黛玉的思绪。正如张新之所评批的那样“春梦婆来矣。模模糊糊,已入梦境,是文字争先处”[1]2008。曹雪芹这样描写了林黛玉的心理:
一时,晚妆将卸,黛玉进了套间,猛抬头看见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间老婆子的一番混话,甚是刺心。当此黄昏人静,千愁万绪,堆上心来,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纪又大了,看宝玉的光景,心里虽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深恨父母在时,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又转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时,别处定了婚姻,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才心地?不如此时尚有可图。”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竟像辘轳一般。叹了一回气,吊了几点泪,无情无绪,和衣倒下。”(第八十二回)①曹雪芹、高鹗著,启功注释:《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如无注明版本均见该书,不另注。
正是这种忧虑的思绪才引出了林黛玉的梦,她梦到自己的父亲不仅没死,而且升了湖北的粮道,还娶了一位继母,要把黛玉嫁给继母的亲戚,还说是续弦,黛玉苦苦哀求贾母留下她,却遭到了贾母无情地拒绝,黛玉只好去见宝玉,
便见宝玉站在面前,笑嘻嘻的道:“妹妹大喜呀!”黛玉听了这一句话,越发急了,也顾不得什么了,把宝玉紧紧拉住,说:“好!宝玉,我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宝玉道:“我怎么无情无义?你既有了人家儿,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黛玉越听越气,越没了主意,只得拉着宝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谁去?”宝玉道:“你要不去,就在这里住着。你原是许了我的,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我待你是怎么样的?你也想想。”
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许过宝玉的,心内忽又转悲作喜,问宝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瞧瞧我的心!”说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只见鲜血直流。黛玉吓得魂飞魄散,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道:“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你先来杀了我罢!”宝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给你瞧。”还把手在划开的地方儿乱抓。黛玉又颤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黛玉拼命放声大哭。(第八十二回)
林黛玉这个“恶梦”,表现了她多种心理内容:一是对离开贾宝玉的极度恐惧;二是对没有人能为她的爱情做主的极度忧虑;三是产生了没有贾宝玉的爱要自尽的想法;四是觉得贾宝玉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五是对贾宝玉爱的极度渴望。
林黛玉这个恶梦的五种心理内容,既是黛玉思想情感的投射,又是黛玉未来人生状态的一个象征。
三、林黛玉恶梦的潜意识投射与神话关系
在曹雪芹的描写中,林黛玉的梦是具有神话性质的。它虽然不像贾宝玉、甄宝玉的“太虚幻境梦”那样,是以太虚幻境的神话世界来表现的,而是以林黛玉现实生活的形态、样式来表现的,但是,曹雪芹仍然是把它当作林黛玉的一个神话性质的梦来写的。
神话是人将潜意识心理投射成了一种超现实的人物和故事,神话的主角是神,是关于神的故事。按照这种神话观念来理解黛玉的梦,它显然不是神话。因为黛玉的梦中没有神,也不是神的故事,而是黛玉自己的故事。但这并不妨碍曹雪芹仍然把它作为一个神话性质的故事来表现,只要表现了人物心理,并对梦主人后来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梦,都能够成为后面人生的先例和范型,就相当于神话式的梦,就在这种神话式的梦中表现了原型。
曹雪芹的这种理解被后来的原型批评家弗莱用“移位的神话”理性概念给予了阐释。弗莱指出:
在神话中,我们见到文学的结构原理是离析出来的;在现实主义中,则见到同样的(而不是相似的)结构原理纳入一个大致真实可信的语境中。尽管如此,既然虚构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存在一种神话的结构,这就向我们提出如何使作品显得可信的一些技术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可以概括地称之为“移位”。[2]193
关于“神话的移位”弗莱有进一步深刻的解说:
文学中的神话和原型象征有三种组成方式。一种是未经移位的神话,通常涉及神祇或魔鬼,并呈现为两相对立的完全用隐喻表现同一性的世界,人们向往其中之一,厌恶另一个。与这种文学同属一个时代的宗教中存在着天堂和地狱,所以人们往往把文学中的两个世界分别与天堂或地狱等同起来。我们把这两种隐喻式对立形式分别称作神谕式的和魔怪式的。第二种组成方式便是我们一般称作传奇的倾向,即指一个与人类经验关系更接近的世界中那些隐约的神话模式。最后一种是“现实主义”倾向,即强调一个故事的内容和表现,而不是其形式。[2]197-198
弗莱对神话“移位”的论述当然是指文学形式的,但是,弗莱揭示的规律同样可以理解梦,特别是适合对作家创造的梦的解释。人类的梦也具有弗莱所论述的三种形式:神话式的、传奇式的、现实主义式的。
如果追溯神话的源头,神话就是来源于梦的,是梦形式的口头讲述和独立发展。从心理表现的角度来说,神话和梦的本质是一致的,神话和梦都是心理投射的形式。神话很多时候是以梦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弗莱就曾说:“在一切梦幻中都含有一种具有独立交流力量的神话成分。”[2]153
在《红楼梦》中,神话式的、传奇式的和现实主义式的梦都有很典型的表现。甄士隐的“识通灵”梦、贾宝玉的“太虚幻境梦”和甄宝玉的“太虚幻境梦”是典型的神话式的梦;王熙凤的梦、秦可卿托梦是典型的传奇式的梦;而黛玉的梦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式的梦。
在《红楼梦》中,先是从整体上表现神话式的梦,然后在现实对神话原型重复的过程中,又进一步表现传奇式和现实主义式的梦,这其实是曹雪芹表现神话的另一种移位:从整部小说到人物心理的神话“移位”。
当我们有了上面的一个初步梳理,对黛玉梦的神话性质就有了理解的可能。黛玉的梦当然不是“石头记”神话和“太虚幻境”神话的“移位”,但是,它确确实实是现实主义式的神话移位,是用现实主义形式表现神话原型的方法。换一句话说,黛玉的梦仍然是曹雪芹用“石头记”神话和“太虚幻境”神话表现先例和范型的“移位”。
四、林黛玉恶梦的心理原型与小说神话因缘架构
神话的象征就是原型的象征;梦之所以采取神话的形式,其目的也是要获得原型的双重象征。甄士隐的“石头记”神话和贾宝玉的“太虚幻境”神话,作为一种原型象征,既是过去心理的投射,是过去思想情感或潜意识心理的一种凝结形式;又是未来命运的一种先例和范型,是未来人生命运要重演的形式。
曹雪芹创造的黛玉神话式的梦也是一种双重象征。一方面,作为黛玉心理原型的象征,它表现着黛玉过去的思想情感,是过去思想情感的一个凝结形式;另一方面,作为黛玉未来人生的象征,它又表现着黛玉未来的命运,是黛玉未来命运的一种原型性象征。
林黛玉的梦可以概括为极度恐惧和渴望,即黛玉对失去贾宝玉爱的极度恐惧和对获得贾宝玉爱的极度渴望。林黛玉的这种极度恐惧和渴望的心理原型,来源于她的“情结”。荣格说:
梦常常是由一种情感失调而引发的,其中涉及某些一贯性的情结。这种一贯性的情结是心理的脆弱点,它会对可疑的处境最快地做出反应。[3]149
荣格进一步阐释道:“情结是联想的聚结—一幅多少有些复杂的关于心理本质的图景—有时是创伤性人格的,有时只是一种痛苦或者被高度渲染了的人格的。”[3]58“具有特定压力和能量的情结,有形成其自身的一些人格的倾向”[3]59,“在我们的潜意识心理中,存在着一些具有其自身特定生命的典型角色”[3]59-60。
林黛玉具有严重的创伤性人格,因而,黛玉也具有强烈的创伤性“情结”。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了黛玉创伤性人格形成的过程。林黛玉的创伤性人格是在“木石前盟”神话和“金玉良缘”神话两种冲突中孕育形成的。这两种神话的对立与冲突造就了黛玉创伤性人格。曹雪芹之所以表现这两种神话就是要表现这两种神话象征的原型及其冲突,也是要表现这两种神话内在冲突与黛玉的心理联系。
林黛玉虽然不知道这两种神话,但林黛玉时时都能感到两种神话原型所象征的力量对她的撕扯、折磨与煎熬。一方面,是来源于林黛玉与贾宝玉前世“木石前盟”的爱情,支配着她要以“还泪”的方式酬报前世贾宝玉对她的灌溉之恩:这就决定了她与贾宝玉至真至纯、至情至痴、至死不渝的爱情;另一方面,是薛宝钗与贾宝玉“金玉良缘”的婚姻对林黛玉“木石前盟”爱情的威胁、压迫与毁灭。这两种神话原型的交织、纠葛与冲突,在林黛玉的内心中如影随形、始终如一地存在着。就这样,林黛玉的恐惧和渴望心理原型就渐渐生成了。
曹雪芹非常有层次地表现了黛玉心理原型的产生过程。作为“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神话冲突的结果,当然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毁灭。但是,那种冲突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正是在那种冲突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林黛玉的创伤性人格,其典型特征是,恐惧、忧虑、感伤和多疑,并且是以林黛玉每况愈下、弱不禁风的身体状况表现出来的,这种生存状态最终导致了林黛玉的“恶梦”。
弗洛伊德指出“梦的思想和梦的内容是两种语言对同一内容的两种描述,或者更明白地说,梦的内容是用另一种表达方式来体现梦思想的翻译。我们只有把这个译本与原文对照才能了解它的构成符号和构成法则”[4]260,林黛玉“恶梦”中的人物、事件是她思想的表现形式,尽管这些人物事件均幻化变形,失去常态,但透过林黛玉梦中这些显像的解析却可发现、发掘其后隐藏的潜意识。凤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宝钗等笑着向她道喜、送行,却“都冷笑而去”。林黛玉被迫去跪求贾母时,贾母却呆着脸儿笑道“这个不干我事”,“续弦也好,倒多出一副妆奁”,“鸳鸯,你来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闹乏了”。这里,平日里对她十分慈爱的女保护者们,都变换了一种姿态,成为了赤裸裸的毁灭她幸福的无情者。梦中的情景虽然怪诞变形,但却是林黛玉在现实生活中日益积累的潜意识的外化。尽管,林黛玉一直受到贾母等人的关心爱护、衣食无忧,但孤洁敏慧的林黛玉还是从种种微妙的迹象中敏感地意识到了这层层嘘寒问暖背后的特殊内涵:凤姐曾将林黛玉比之于低贱的小戏子(第二十二回);元春赏赐的端午节礼物,只有薛宝钗与贾宝玉相同(第二十八回);王夫人在金钏被逼跳井之后说林黛玉是个“有心的”(第三十二回),并曾在指责晴雯时影射到林黛玉,“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第七十四回);贾母曾亲自替宝钗过生日,而黛玉却从未这样受宠过。贾母对才子佳人故事的批评,也是为黛玉敲响的警钟(第五十四回)。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林黛玉强烈地感受到在这贵族大家庭中“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精神重压,林黛玉梦中的情境是如此的鲜明,如此的触目惊心,使林黛玉警醒于这些亲人们的冷漠无情。
林黛玉的“恶梦”不仅是她之前心理的集中、典型体现,还是她后来心理甚至人生命运的一个原型,黛玉后来人生命运就是以这个梦为先例和范型的,甚至,黛玉后来人生就是以这个梦为模板的。
林黛玉梦到父亲续娶,又把她嫁给了继母亲戚做续弦并且派人来接她,这件事确实没有实际发生过,但是,如果把这件事作为黛玉恐惧失去父爱、恐惧离开贾府、恐惧离开贾宝玉的心理象征来理解,那就是十分真实的。
父亲续娶是女孩失去父爱的最典型的象征形式;而家里人来接也是她恐惧失去贾宝玉之爱的象征形式。在这个梦之后,黛玉的这种恐惧失去依托、恐惧失去呵护、恐惧失去贾宝玉之爱的心理与日俱增。
在梦中,黛玉失去了父爱,父亲又把她嫁给了别人,贾母王夫人等都不给她做主,这是黛玉的爱和生命都失去了依托与保护的象征;而正是这种失去依托与保护才导致了爱的彻底失去,因而让她产生了想自尽的想法。
这种失爱和自尽的思想便成为一种原型性思想,这种原型性思想十分严重地影响了黛玉的思想精神,是她由病情任意发展到有意糟践自己身体的根本原因。黛玉死于过度忧郁,但是,归根结底,黛玉是死于“自尽”的。是黛玉要“自尽”的想法使她放任自己的忧郁,放任自己的病情,放任了自己的“泪尽”。黛玉的死是因为失去了爱因而要自毁生命的结果。失去贾宝玉的爱,使黛玉调动了生命中的“死本能”,从而加速了她的病情,也加速了她的死亡。
黛玉的“恶梦”,成为“全书大转关”[1]2013,它不仅表现了人物性格,而且在全书的主题与结构上有重大意义,构成了《红楼梦》结构线索上的一大关键环节,堪与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相比翼。
五、林黛玉恶梦对其未来人生的象征
小说中多次写到黛玉得知贾宝玉要娶别人时,黛玉想要自尽的想法,一处是第八十九回“杯弓蛇影颦卿绝粒”,一处是第九十七回“泄机关颦儿迷本性”。林黛玉为情而生,又为情而死,她对宝玉爱得深、爱得真、爱得生死以之,当这种爱情被毁灭时,她就“焚诗”“绝粒”以生命相殉。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决定着她的整个生活道路、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没有贾宝玉的爱,林黛玉就不能活,也不愿活,更不屑活。
相比于林黛玉的唯一的神圣的爱,贾宝玉的选择无疑是多元的,因此,无论贾宝玉如何向林黛玉剖腹挖心,林黛玉也是不可能完全放心的。这种忧虑始终弥漫于林黛玉的生命之中,因此,产生了梦中对贾宝玉无情无义的看法。这既是林黛玉对贾宝玉的担心,也是林黛玉担心应验了的心理感受。
对贾宝玉无情无义看法的应验,主要是来源于“金玉良缘”的婚姻。正是这个婚姻给了黛玉致命性的最后一击。尽管这个致命一击不是贾宝玉造成的——贾府告诉贾宝玉,他的结婚对象是林黛玉,而实际上是与薛宝钗结婚的。这个“掉包计”贾宝玉事先是不知情的,但是,林黛玉是不知道贾宝玉是被贾府众人欺骗了的。当林黛玉恍恍惚惚听到结婚的音乐声——其实那是林黛玉的幻觉,她确确实实地感到了贾宝玉的无情无义、绝情绝义、背情叛义,林黛玉感到了彻彻底底的绝望。林黛玉临终之际的“宝玉,你好”,这未完的话语中肯定是包含着对宝玉“好绝情”“好狠心”的怨恨。尽管,贾宝玉曾经对黛玉海誓山盟,曾经信誓旦旦地对林黛玉说“你放心”,曾经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而今,这一切都随着贾宝玉和薛宝钗婚礼到来,最终将林黛玉推向了绝命的深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林黛玉是带着对贾宝玉爱的极度失望,带着对贾宝玉的极度绝望,带着对这个人世间的彻底绝望而离开的。
梦中林黛玉看见了贾宝玉拿刀挖自己的心,这其实是林黛玉对贾宝玉爱的极度渴望的变形投射。这是由于林黛玉极度渴望和极度恐惧心理形成的幻想形式。幻想贾宝玉拿刀挖自己的心给她看,是林黛玉渴望得到贾宝玉心的变形形式:林黛玉极度渴望贾宝玉把他的心给她是一种象征,象征了贾宝玉对林黛玉爱的专一、独一,于是,便产生了贾宝玉拿刀挖心的梦幻意象。黛玉梦见贾宝玉“剖心”的荒诞情景预示了宝黛爱情在现实生活中的虚幻和破灭,进而成为贾宝玉命运的一种凝缩。
当贾宝玉把心交给黛玉之后,他就因失去“心”而疯癫,成为了一具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躯壳,游走于尘世之间。当王熙凤巧施“掉包计”,假意给贾宝玉娶黛玉,贾宝玉听说之后道:“我有一个心,前儿已交给林妹妹了。他要过来,横竖给我带来,还放在我肚子里头。”(第九十七回)林黛玉并没有嫁给贾宝玉,所以贾宝玉也无法在失去“心”的情形下安然无恙,“在林黛玉之死的推动下,贾宝玉完成基本义务,便要放弃人生,回到太虚幻境‘销号’”[5]。贾宝玉最终“遁世”,离开了这个无情的尘世,重返大荒山青埂峰。
先表现整体性的神话或梦,然后再在神话指引下进行原型叙事,是《红楼梦》最重要最独特的创作方法。“石头记”神话和“太虚幻境”神话就是为表现贾宝玉人生道路和贾府女性悲剧命运而创造的神话原型。也正是在这种创造方法的制约下,曹雪芹在表现具体人物命运的时候,还要具体地表现人物的心理原型。这就形成了大的神话原型和小的梦对心理原型的表现相结合的方式。
以林黛玉这个形象来说,曹雪芹既在“石头记”神话中表现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木石前盟”,表现了林黛玉用一生的眼泪来报答贾宝玉的灌溉之恩,又在贾宝玉的“太虚幻境梦”中以“玉带林中挂”和“终身误”表现了林黛玉悲剧命运的原型。但是,这只是从大的方面来呈现悲剧命运原型的,而缺少具体的内容。
很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曹雪芹又在林黛玉形象的具体表现中,以林黛玉的梦表现了她的心理原型的。这样,在林黛玉形象的表现上,就形成了宏观的神话和具体的梦(也是相当于神话的)相结合的方式。而正是这样宏观神话表现命运原型和具体梦表现心理原型相结合的方式,使林黛玉的形象得到了更为丰富、深刻和生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