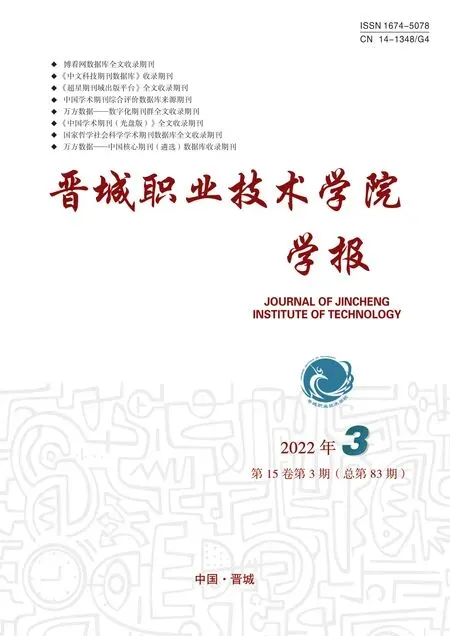儒骨、释经、道风——试析柳宗元山水游记中儒释道精神的统一
2022-03-17傅水怒
傅水怒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晋城 048026)
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众体兼长,作品丰富,现存的四百余篇散文作品代表了他从事古文运动的成就,奠定了他在唐宋八大家中的地位。其中的山水游记是柳宗元诸类散文作品中成就最高的,也最富艺术独创性,尤以《永州八记》更胜,历来被推为柳文的最高成就。
《永州八记》均作于元和四年以后,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描写的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但非纯客观的景物描写,作者把自己的人格、情怀、处境、所思、所感融入了对景色的描写之中。有的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如《石渠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有的借景物写感受,含蓄地表现了作者处境的寂寞和哀怨、凄怆的心境,如《小石潭记》《钴鉧潭记》;有的物我交融,作者写的乃是心中之景,对景物的描摹实是对自我的描绘,如《石涧记》。这些游记大都以情观景,因景抒情,情景交融,笔下的山水景物都各具特色,个性鲜明;文笔则时而峭拔峻洁,时而清邃奇丽,与所绘之景、所抒之情达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其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堪称古代山水游记至臻的典范。
永州十年是柳宗元一生的转折期,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永州,从踌躇满志的京官一下子变为落魄蛮荒的罪臣,柳宗元的人生骤然改写。荒远的贬地,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加之政敌毫不松懈的人身攻击,火灾的多次光顾,亲友的疏远,母亲的离世,回京的无望,使柳宗元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重创。他的内心充满了悲愤、忧郁、痛苦,身体急剧地衰弱,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与李翰林建书》)”的程度。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艰苦的生活,痛苦的处境,使他获得了更多的锻炼和体验,使他进一步接近、了解了人民的生活,更深刻地认识到权贵的丑恶和社会的不公。闲适的生活,使他有时间广泛地钻研古今典籍,认识水平和文学修养在这期间大大提高。他大量的批判黑暗现实和宣传进步主张、提倡古文革新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大都是在这时期完成的。为了排遣心中的郁愤,他常常披荆斩棘,探幽访奇,徜徉于永州的奇山异水之中,暂时消解痛苦,舒展情怀。永州澄静秀美的山水也仿佛理解作者,使他每有所获,于是永州的山水在作者笔下具有了生命和灵魂,使他从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和解脱,化解了郁结心中的苦闷和困惑。孤苦的柳宗元经历了这番炼狱,跨进了“唐宋八大家”之列,再一次印证了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至理名言。
奠定柳宗元唐宋八大家地位的山水游记散文,其艺术性毋庸置疑,很多学术性的研究论文已对它们做了方方面面的分析,本文不再涉及。关于他游记的思想性也有许多的论述,有的关照它里面的佛家思想,有的研究体现其间的道家思想,然而,作为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柳宗元,其作品中体现的思想性既非单一的某种思想,又非各种思想简单的荟萃,本文试图从最能代表他散文创作成就的山水游记入手,重点探讨柳宗元游记散文中儒、释、道精神的和谐统一,即儒家的骨骼、佛家的经络、道家的风采。
一、儒家的骨骼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幼时,父亲去南方做官,他跟随母亲卢氏住在京西庄园里,母亲信佛,有文化、有见识,给了柳宗元很好的启蒙教育。十一二岁后他到父亲柳镇身边,父亲深明经术,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其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青年的柳宗元入世思想很明显,他积极进取,有着建功立业的抱负:“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科举进士入仕后,力主革新,成为王叔文变革集团的中坚人物,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尽显无遗。父母亲给予柳宗元儒、佛双重的影响,奠定了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基础,柳宗元母亲和岳父信佛对他虽有影响,也只是让他对佛教不那么排斥,进而去研究它,为我所用。他骨子里始终都是以儒家有为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的。在《愚溪诗序》里,柳宗元把他居住地的一条小溪更名为愚溪,把与这溪水有关的景点都冠以“愚”字,先嘲溪水之“愚”又以自嘲的口吻写己之“愚”,说宁武子、颜回之愚“皆不得为真愚”,今己“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从末尾的对愚溪发自肺腑的赞叹中,我们不难体会作者因不为世用而胸中愤懑不平:“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特别是从继之而来的“寂寥而莫我知”的慨叹中,不难体会出浓重的人生失意之悲凉和不得伸志之苦涩。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以“自余为僇人”开篇,表面上看好像自嘲,也不难感受其中暗含受辱和被害的悲愤。《钴鉧潭记》中叙述得潭经过带出了一个社会问题:潭上居民不堪忍受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情愿把潭上土地卖给作者,逃到山里去开荒。结语的哀怨之音尤令读者唏嘘:“孰使余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在《石渠记》中写了泉、渠、石、流、泓、潭的蜿蜒纡曲、坎坷艰难、清幽孤寂,暗与作者自身遭遇相合,但作者心底并没有被这些磨难击垮,他“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使读者看到了一个忧郁中不绝望、重压下不易辙的傲岸形象。《游黄溪记》中,写黄溪山水之胜而不为人知,末段写黄神因失掉政治靠山而逃居于此,这些和作者遭遇何其相似;又写黄神为人时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死后人们立祠纪念他,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这些游记中幽静自然的美令他欣喜,更令他怜惜——如此美景却被世人冷落,由此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的命运,感叹之情油然而生。可见山水之美只能让他暂时轻松,却无法令他真正地忘怀国事,乐以忘忧。但他面对险阻总是百折不回,时刻不忘惩恶扬善、匡扶正义,渴望为社稷、为百姓做事,这些品格不正是儒家思想的浸染造就的吗?可见儒家思想始终是他思想的主导、精神世界的重心。就像人的骨骼是人体的支柱一样,儒家思想是柳宗元人生的支柱,也是其游记散文的精神支柱,是其游记散文的“骨骼”。
二、佛家的经络
当然,柳宗元的思想是复杂的,佛家思想对于柳宗元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柳宗元信佛缘于家庭小环境与社会大环境的双重影响:家中母亲和岳父都信仰佛教;长安作官时,德宗皇帝又崇信佛教,在朝堂上搞“三教讲论”,使朝野崇佛空气很浓,柳宗元心里自然亲佛崇佛。佛学在柳宗元的思想、认识、情感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他自己在《送巽上人赵中丞叔父召序》中写道:“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他立志“统合儒释”(《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他的佛学观中,一直有佛为儒用的思想,他认为佛学“往往与《易》《论语》合”(《送僧浩初序》),可以“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斜”(《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他任柳州刺史后所作《柳州复大云寺记》对修复大云寺的原由这样说明:“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当然,以柳宗元的智慧,佛家思想调节内在精神的特有功用自当为我所用。当正值壮年、满怀理想的柳宗元遭遇永贞革新失败,无罪被贬,远离朝廷,升迁无望时,他所受打击之沉重,精神之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始得西山宴游记》)。这时,精神需求的寄托,使早年扎根在内心的佛教意识得以迅速滋长、发展。在这一时期,柳宗元的佛学作品最多,佛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透过他这一时期的游记散文,我们能感受到潜伏在如诗如画的优美文字下面的一种精神内核,即:空旷、宁静,清幽、冷寂,也隐隐感觉到作品意蕴中弥漫着的隐忍达观的情绪。在这些山水游记中,他笔下的山、水、石、竹、树、草、鱼、鸟等各类事物虽各具特色,但其境界都或空旷宁静,或清幽冷寂。如《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不直接描绘西山的雄伟壮阔,而是写登上山顶鸟瞰和远眺的感受“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令人感到清幽空旷;《石渠记》中:“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让人感到虚空、静远,身心也为之空明澄澈起来。再如《钴鉧潭记》写潭水“其清而平者且十余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境界幽寂、清冷;《小石潭记》先写了潭水之清,游鱼之乐:“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好像在写游人的快乐,然而从“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等句中不难体会出作者内心的寂寞和凄清。这些景物描写体现出的空旷、宁静,清幽、冷寂,给人宁静、空灵、澄彻的感觉,明显受到了佛教“空”“寂”观的浸染。佛教认为“空”性才是一切事物的真正本质,空又是一种心灵的境界,是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也能超然物外的一种心境,一种平和安乐的情怀。而“寂”是达到“空”的途径。在他的游记中,我们也常读到“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冉众草,纷红骇绿,蓊郁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飏葳蕤”(《袁家渴记》),这种以动写静,动静相生的句子,让人仿佛置身奇异的世界,心旷神怡。正是内心的宁静,才能听到、看到、感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才能让作者走出世俗的烦恼,而这正是作者通过对佛教天台宗教义的深入研习获得的。正是缘于对天台宗教义“无情有性”的认同,柳宗元山水作品中的自然之物,即便是不能发心修行的无情识之物也都具有佛性,都那么善解人意。在自然与佛理的相通相融中,柳宗元实现了自我的超越,摆脱了外在的束缚,与天地精神相通,体悟出生命本质。而像“无情有性”“卓然孤立”“止观双修”这些佛学思想在柳宗元山水游记中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但文章中没有了它,便没有了内涵和神韵。它就像人体的经络,虽然不易看见,但却是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人体输送血液和养分。
三、道家的风采
作为一代宗师、思想家、哲学家,柳宗元推崇儒学,但统合儒释、兼容百家,取诸子中“与孔子同道”的一面(《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排斥其异于孔子之道的一面,这使他的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读他的山水游记,除了感受到儒家思想是其骨骼,佛家思想为其经络之外,还有明显的道家色彩,道家思想可以说是其山水游记的风采。
《永州八记》处处浸淫着道家天人合一、神遨八极、逍遥玄远的思想。《始得西山宴游记》让我们与柳宗元一起徜徉在“悠悠乎与颢气俱”“洋洋乎与造物者游”的意境中,“不知日之入”“犹不欲归”,进而“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这种自得无碍之游让柳宗元身心真正得到了放松,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游”,因此说自己“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这里所说的“游”明显是指心灵之游,是心灵的真正解脱,而非以前的“身游,神不游”。正是领略了道家精神“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内在实质,柳宗元内心才真正接纳了永州山水,从而与它们同呼吸,共命运,彻底融入自然,从抑郁惴栗中解脱出来,灵魂得以放飞,真正享受到了出游的快乐。这一点我们从作者以后的《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愚溪诗序》等仍以山水为题材的游记作品中也很容易捕捉到。如:《钴鉧潭记》中“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日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等。细察这些篇章的行文用语,不难发现这些游记的精神内涵与老、庄的精神境界相通。同时,柳宗元山水游记中还蕴含着道家的思辩精神,像《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小大之变,《愚溪诗序》中有用无用之辩等,都是道家辩证思想的体现和传承。尤其是他游记散文的语言风格,更是将老庄文章汪洋恣肆的韵味神形兼备地继承并发扬到了空前水平,“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然不动,傲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这样的笔触使人油然想起《庄子·内篇·大宗师》中“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以及《庄子·杂篇·天下》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叙述,以及《庄子·秋水篇》中“鱼之乐”的描述,柳宗元不仅写出了鱼之乐,更写出了人鱼相乐。读柳宗元山水游记,我们总会不自觉地沉迷于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超然飘逸而又清幽宁静的浪漫氛围里,陶醉于物我两忘、天人化合的意蕴境界中,这种最宜于文学表现的道家色彩给柳宗元山水游记抹上了独特的美学风采。
苏轼评说:“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绝妙古今,儒释皆通,道学纯备,自唐至今,欲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的确,柳宗元不愧是一代宗师,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机完美融合了儒、释、道思想与形骸的划时代人物,儒骨铮然,佛经舒畅,道风飘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