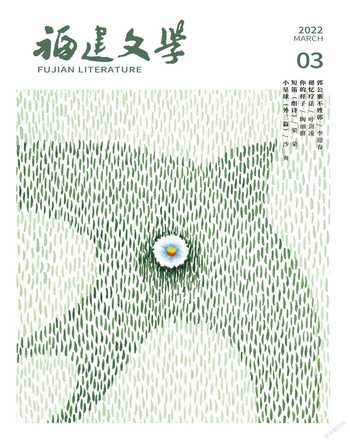故乡年味长
2022-03-17阿丁
阿丁
一
一晃离开故乡二十余载。
二十多年来,不曾再回乡下石厝老屋住过一晚。每年春节前一两天,我一定会随父亲母亲回去贴贴春联,看看日渐年迈的伯母,再到村头的那口老井旁转转的。在老家邻里一座座爬满苔藓的老宅间徜徉,我更想让自己化身为一只忠诚的家犬,穿行于曾经闭着眼也能走得来的房前屋后巷陌田埂,嗅一嗅袅袅炊烟和芬芳泥土,找寻当年家家户户窄窄的窗门里飘出的诱人年味。
幼时对四季变换没有太多认识,大抵是因为冷得浑身哆嗦、手脚长满冻疮而记住了有一个难挨的季节叫作冬天,因为可以顶着烈日上树捕蝉、下海游水而记住了虽挥汗如雨却能肆意狂欢的夏季。至于文人墨客笔下的郁郁春华和金黄秋实,在我当年的记忆里实在难以找出太多清晰的东西来。小时候冬天总是漫长。实际上长大后才知道,每年都会有倒春寒,正如民谚所云“清明谷雨,寒死老鼠”。硬生生地把原本属于春季的料峭之寒也给算到了冬天的头上,这对冬季是不公平的。年,是在寒冷的冬季里才来的。以前农家里很少看得到日历,乡亲们虽能掰着手指准确说出当天是农历的哪一天,可对孩子们来说,究竟是在冬季的哪个时段快要过年,简直就是哥德巴赫猜想——但我是猜得出的。也不知何方神圣给了我这个先知先觉,现在想想、那是多么有趣啊。
从前,有“冬婚夏不婚”的习俗。说的是正人君子、正道人家嫁娶时间定在腊月或正月二月,而那些大热天结婚的恐怕是姑娘的肚子大了捂不住,才做出此等“打倒人世”(意即丢人现眼)的事情来。至今我仍然无法确知此说法的由来,但冬天结婚的人一多,就意味着年的脚步近了。
那年冬天,堂叔用邻村租来的一辆大型拖拉机接新娘,进村的黄土路虽然只有几百米长,车屁股后扬起的灰尘加上柴油机“突突突”的轰鸣声中大口排出的黑烟,却几乎把整个小村庄熏了个遍。一大群毛孩跟在拖拉机后撒腿狂追,一边追一边用方言拖着长腔整齐划一地吼起了村庄里特有的“迎新歌”:“新娘新郎婿,赤尾(即虾米)煮紫菜。紫菜煮没熟,新娘偷吃肉。”这时候,被拖拉机晃得颠来倒去的新娘再怎么晕车也不会忘记掏出备好的糖果和宝丸(桂圆干)撒到路上,捡到胜利果实的孩子们一哄而散跑到一边慢慢品尝去了。有的新娘比较小气,抛下来的东西不够分,没捡到的孩子就会恨恨地扯起嗓门,涨红了脸,以更大的嗓门和更快的语速继续高声起哄“迎新歌”的第二章:“肉夹单单骨(把肉全都吃了只剩下骨),新娘呛(雇请)摩托。摩托抵吊吊(摩托车在起伏的路上摇晃前行),新娘大拉尿。尿拉嘘嘘叫,新娘被人撬。”谁家姑娘在大喜之日众目睽睽下受得了这铺天盖地的阵势?早就羞红了脸,乖乖地把口袋里的喜糖再掏出来天女散花了。
腊月里,但凡一个村里有一户人家办喜事,这个村子就会热闹几天,要是再有一两户人家也连着办喜事,整个腊月里满村子的空气都是油香四溢。乡村的喜庆在年轻人嫁娶的喧嚣热闹中蔓延,年味也就此逐渐弥漫开来。
二
《梦粱录》有曰:“士庶家不论大小,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整个腊月里,只要遇上好天气,主妇们就会把家里的门窗桌椅、床头铺尾、衣裳被褥、灶前灶后挨个洗得干干净净,以最清新整洁的姿态迎接年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生活日用品还得靠计划供应,置办一些酱醋糖之类的简单年货成了孩子们主动请缨之事。记得有一次,大约是春節前一个星期,村里的孩子们三五成群,拎上几个油瓶子和布袋子,兜里紧紧攥着油票、糖票到邻村的合作社买年货。回家路上,一个小伙伴实在无法抗拒红糖的诱惑,半路上打开布袋子伸长了舌头舔了几口,结果五六个小孩全都跟着打开袋子吃开了,回到家时已是所剩无几,有的为此还挨了一顿打。
门上贴了大红春联,春节的喜庆气氛就愈加浓厚。过去农村很多人大字不识几个,一个村子里很难找得到几个会写春联的人,有的人家干脆去繁就简,用碗底沾墨水在红纸上印一个圆圈贴在门上,算作春联。他们的心愿倒也简单,只要门上有红,就能驱邪迎福,来年的日子就会红红火火。
以前会写春联的人少,但贴春联的地方可比现在多得多。除了门窗以外,猪栏、鸡舍、水缸、风柜、瓮子、烟囱,甚至马桶、尿壶等也要处处见红,写的一般都是六畜兴旺、鸡鸭满圈、猪肥牛壮之类的大白话。
曾经见过几户人家贴的春联,至今想起仍觉得好笑。有的人家的框联写道:我爱过年,我真高兴,多养母猪,真的好吃。时隔多年后再去品味这些春联,倒觉得这些平白朴实甚至略带滑稽的文字背后,正是当年的人们基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感受和对新一年的最纯朴的期盼。
三
娶亲、净庭户、贴春联,都是大人们的活。只有穿上新衣裳、吃上美味、玩起了新鲜好玩的东西才是孩子们真正向往的过年。
腊月廿五六过后,主妇们就开始忙着张罗过年的吃食,美食的味道开始在乡村里一波又一波地飘逸开来。油炸“浮丸”“糖鬼子”的工序相对简单,也是过年的常见食物,但打“白丸”(鱼丸)却并不是家家户户都要做的。“白丸”的原料大多取材于新鲜的鳗鱼或马鲛鱼,鱼去皮、脱骨后的精肉放在石头做成的舂臼里打磨捣烂,加上适量的地瓜粉,再撒一把剁成小小片的葱花搅拌在一起,等到锅里的水烧开后,手巧的主妇抓一把鱼肉泥,在拇指与其他四指并拢的哧溜声中,一粒粒圆滑可爱的鱼肉丸子接二连三地跳进了沸腾的汤锅里,不到几分钟,品相诱人味道鲜美的“白丸”像是落入玉盘的明珠一般雀跃在热气蒸腾的水面上。那个味道啊,才是地道的爽口又走心。
如果说打“白丸”只是少数人家的自选项目的话,那么炊发糕一定是家家户户的规定动作。或许缘于发糕与“发高”谐音,承载着海岛人家对新的一年发大财年年好节节高的美好期望,再加上制作发糕对面粉的调和、发酵的时长、糖分的多寡、火候的大小等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只要其中一个细节稍有差池,就可能导致发糕变形、变硬甚至变质,所以许多主妇对炊发糕心存敬畏,轻易不敢下手。母亲能做一手好菜,但她每次炊发糕时都是怀着仪式般的庄重,早早就把我支开,生怕我站在灶旁因为好奇而在嘴里蹦出诸如“肥母有起没(酵母有没有发酵充分),糖够不够甜,灶火够不够大”之类的话。在母亲心中,能不能做出一床外形好看甜度适中筋道恰好的发糕对她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可不能让孩子们的口无遮拦打了彩头影响了发糕的质量。
新炊出来的发糕蓬蓬松松的,周身散发着诱人的甜香,但此时万不可以拿来就吃。母亲会在散着热气的发糕上抹一层“绛红”(一种可食用的红色染料),插上两朵塑料做成的小百合花,再放一打还没开封的筷子,恭恭敬敬地把它摆在厅堂的八仙桌上,等到正月初四开假时才能切开来吃。
家乡过年的美食品种繁多,以地瓜、花生、海鲜为原料的风味菜肴被冠以“时来运转”“天长地久”“一团和气”等美名,每一道美食都蕴含着吉祥寓意,但从未有其他任何一种美食像发糕一样被海边人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賦予信仰般虔诚敬重的内涵。
四
“一年做到晚,那等三十盲铺顿(一年忙到头,只等着大年三十的晚餐)”,这句俗语道出了海岛人家对除夕年夜饭的格外看重。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是主妇们辞旧迎新的最强挑战,这一餐的食材一定是最丰富的,烧出的味道一定是最鲜美的,展示的厨艺一定是最高超的。家家户户都会做好几道菜,把桌子摆满,但邻里之间一般不会有人真实地告诉别人自己家做了三道、五道还是七道、九道,人们只会习惯于用“煮几碗”来表达年夜饭的丰盛。每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不一样,说多了有摆阔之意,说少了怕被人笑话。“煮几碗”,这简简单单三个字,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技巧,更是乡里人朴素中的智慧。
老家还有个习俗,年夜饭的菜都是单数(只有在祭祀亡灵时才摆双数碗的饭菜)。如今,人们上馆子点菜和酒席上的菜一般不是双数就是这个由来。年夜饭的丰盛自然不必多说,各家各户的菜肴也各有千秋,但每家每户都要煮一些干饭是约定俗成的,美其名曰“隔年饭”,这道“隔年饭”不能在除夕当天晚上吃,而是留在次日的正月初一当午饭吃。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岁饭”,把大米装在一个小塑料桶或者瓮子、钵子里,上面插一打新筷子,等到正月初四开假后再拿去煮。“隔年饭”和“岁饭”的形式有所区别,但都包含着同一种寓意,都是人们对来年五谷满仓年年有余的虔诚寄托。
除夕夜里大人给小孩压岁钱是各地都有的习俗,但是,给床铺、水缸、橱子、抽屉等物件压岁,可能是我们家乡特有的。老人说,万物皆是神明,给这些物件压岁,它就会为主人家带来滚滚财源。那时候的硬币面值都是一分、两分和五分,谁家草席下橱子里的五分硬币放得越多,来年收获的财富也会越多。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一,天寒地冻,几个小伙伴起了个大早,偷偷潜伏到邻居家捞水缸里的压岁钱。有的在门外望风,有的揭水缸盖,有的负责往水里捞钱,分工非常细致。大个子堂哥撸起了袖子,把手伸到水缸底,正摸索着刚要把硬币捞起来时,大伯突然走进来把他逮个正着。钱没捞到,把过年头一天穿的新衣服弄得湿淋淋的,还挨了一顿训。类似水缸里捞钱、在牛粪上放鞭炮等恶作剧经常在儿时的春节里上演。
如今的故乡之于我,虽未隔着千山万里远,却好比长大成人的男子,可以轻轻地牵一牵母亲的手,但再也无法像幼年那样随心随性地在母亲的怀里打滚撒欢。
在渐行渐远的岁月里,年是一种埋在心底深处的守望。儿时故乡的年味悠长,如今已然无法回首触及,可我依然相信,只要心中有暖眼里有盼,纵然走得再远,那一怀故乡的情愫永远都在心里蒸腾缭绕。
责任编辑 林 芝
2613501705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