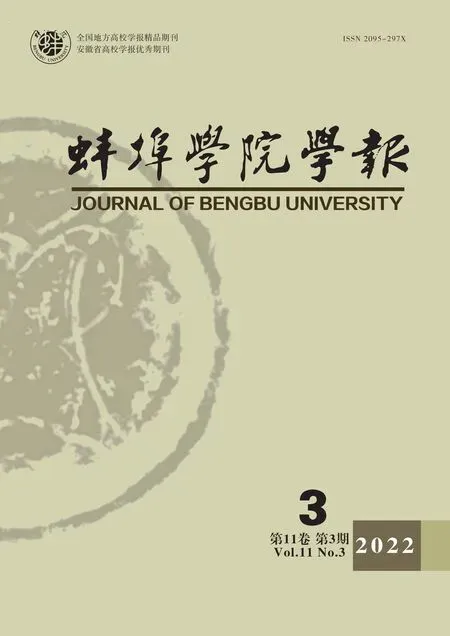论程嘉燧的日常生活审美实践及其成因
2022-03-16林瑶
林 瑶
(深圳大学 中文系,广东 深圳 518000)
叶朗指出:“日常生活的美, 在很多时候, 是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氛围给人的美感。这种生活氛围, 是精神的氛围, 文化的氛围, 审美的氛围。”[1]216“中国古人特别追求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营造美的氛围。”[1]217中国人历来重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可以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以生活审美化为底色的。从先秦时期孔子欣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2]的惬意生活、老子追求自然无为的本真生活、庄子向往逍遥天地的超脱生活;到魏晋时代陶渊明逃避政治而回归田园之美、谢灵运不得志而寄情山水之间、竹林七贤在“肆意酣饮”中发泄生命的苦闷;至唐宋时期白居易提出“中隐”的生活观念,与张浑、刘真等人结成“香山九老”,一起吟诗谈禅,颐养天年;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在西园中吟诗作赋、抚琴挥毫的雅致集会等,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文人对于审美艺术化生活的追求。而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在时代的发展中有向世俗发展的形而下趋势,直至晚明达到巅峰。晚明文人在混乱黑暗的政治背景下,受心学和禅宗的影响,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文化与生活样态。程嘉燧活跃在晚明时期,虽未曾入仕,但他交友广阔且热爱游赏山水,作品中蕴含着富有晚明文人特色的日常生活审美实践。
1 程嘉燧日常生活审美实践
程嘉燧(1565-1643),字孟阳,号松圆、偈耕,徽州歙县人,侨居嘉定,与李流芳、唐时升、娄坚并称“嘉定四先生”。他生于嘉靖末年,卒于崇祯末年,主要生活于明朝政治衰败倾颓时期,这时候的部分文人士大夫们因为害怕受迫害而与政权疏离,心学禅宗的兴起使得他们更加关注自然人性,纵欲放荡、向往归隐、闲赏山水、各种奇癖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审美活动特征。程嘉燧生活在富庶的江南地区,文人聚居,文化发达,因此他的作品创作中带着明显的晚明文人的时代生活审美实践特色,而独特的心态人格又使其日常生活审美带着个性化色彩。
1.1 释情有度,率性有节
晚明是一个情欲较为放纵的时代,“情”“欲”在许多晚明文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生活重心从重视社会伦理关怀转向个人身心愉悦的追求上。如在袁宏道看来,人生的真正乐趣就在于身体感官本身的快乐:“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3]张岱更是在《自为墓志铭》中直白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4]可见晚明文人对于身体感官愉悦的沉迷。身体的愉悦带来了精神的愉悦,晚明文人以此来获得对于生命价值的重新体认,将重心转移到自身日常生活的审美享受上,构建起生活氛围的美感。
程嘉燧在这方面不同于晚明绝大部分文人的纵情纵欲,而是释情有度。他的作品中也有深夜携伎与朋友在舟中听歌饮酒,如《舟夜伎饮同子柔即事》:“急觞似欲追清管,高调偏疑压翠眉……深杯百罚那抛得,莫负欢娱少壮时。”[5]54强调要及时行乐。《再过娄上看桃花即事与伎》:“迟日才开妆面镜,晓风先动舞衫罗。欢心宛转流莺说,酒态妖娆细马驮。”[5]82描绘了歌伎们梳妆时的娇柔之态和携伎游玩的愉悦之情。他在出游时也要带上歌伎,如《载伎重游王潭马砦岩》:“此日川光容易夕,相呼秉烛莫言回。”[5]87流连忘返的原因除了自然山水的美丽,也有与歌伎们狎昵的欢乐。他的诗中对歌伎们有“燕赵莫矜颜似玉,都门漫咏女如云”[5]251的赞美,也有专门创作送与歌伎的诗,如《泛舟席上题扇与伎》:“邀得红妆消别恨,曲终无奈翠眉愁。”[5]88将歌伎们的愁绪描绘得十分灵动。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程嘉燧并没有像其他晚明文人那般放肆沉溺于情欲之中甚至达到“色癖”程度,而更多的只是欣赏歌伎们的音乐才艺,且诗中提及她们时也多用含蓄温柔词句,有情感的放任但更有限度。
而能进一步体现出程嘉燧在男女关系方面态度的当是与柳如是之间一段似是而非的缘分。在柳如是游历嘉定之时,他创作了一组《朝云诗》[5]433记述他们之间的交往。先是写与柳如是约定游玩时的兴奋心情,“林风却立小楼边,红烛邀迎暮雨前……数日共寻花底约,晓霞初旭看新莲”,而后写“邀得佳人秉烛同,清冰寒映玉壶空。春心省识千金夜,皓齿看生四座风”。表达了和佳人一起游玩的愉悦,对柳如是毫不吝啬赞美之词。“谁能载妓随波去,长醉佳人锦瑟傍。”直白地表达对于柳如是的倾慕,甚至说出了长醉身侧的放荡话语。“针楼巧席夜纷纷,天上人间总不分。绝代倾城难独立,中年行乐易离群。”则描绘了与柳如是在一起游玩时的沉迷,但却因为世俗和年龄的阻碍而不能长久相伴的遗憾。“今夕何夕织女降,南邻玉盘过八珍……玉人羽衣光翯翯,似有霓裳来碧落……只云三万六千是,莫惜颠狂且行乐。”[5]434更是将柳如是比作织女,形容其姿容如玉般美好,最后表达了与柳如是相携游玩而不知疲倦的心情。在柳如是离开嘉定时,他创作了一组《縆云诗》[5]441表现对于佳人的不舍之情。“遥知一水盈盈际,独怨春风隔送行。”表达对于不能一路送别佳人的遗憾。“悠悠春思长如梦,耿耿闲愁欲到明。”写出了对于柳如是的思念。“闲坊归处有莺声,白发伤春泪暗生。”表达了对于柳如是走后不知归期的伤感。携伎游玩增添了其日常生活的愉悦,欣赏歌伎们的曲艺更是一种审美化生活的享受,和柳如是的交往宴游、谈诗论画表现了文人集会的高雅情致,这些无不体现了程嘉燧在日常生活中构建的审美化生活氛围。
除了身体愉悦,晚明文人同样追求心灵的自由,如李贽的童心与狂禅、陈继儒的焚冠绝意仕进等。在他们看似洒脱自由中总带着世俗名利的羁绊,所以晚明才会出现一大批所谓“山人”出入富贵宅门之间的景象,就像人们讽刺陈继儒“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一般。程嘉燧一生不曾入仕,在追寻心灵的自由方面真正做到了身心合一。他只在少年时期考过一次科举,不中后遂弃之,而后终身不试。在别人推荐他去做顾养谦的幕僚时,他在途中与友人酣饮三日,写了一组咏古诗歌后,根本没见顾养谦就返回了,真正做到了不慕富贵,从心行事。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描述他:“嗜古书画器物,一当意辄解衣倾囊。”[6]576他嗜好古玩书画就倾囊以购,甚至常常购进赝品,但却不以为意。他不善经营家中生意,最后落得只能向朋友写信求资助的地步,但依然视名利如云烟。学剑未成便弃之转从诗画,作画时“酒阑歌罢,兴酣落笔,尺蹏便面,笔墨飞动”[6]576,但在别人向其索画时却“或贻书致币,郑重请乞,摩挲瑟缩,经岁不能就一纸”[6]576。写诗更是强调必须出于真情实感,不仅学古人之诗更应学古人之为人,志洁行芳,温柔而敦厚。与人交往时“在里中,兄事唐叔达、娄子柔,肩随后行,不失跬步。与人交,婉娈曲折,临分执手,口语剌剌”[6]577,礼仪周全,待人和悦。可见程嘉燧是以道德和礼节制自身,在此基础上追求心灵自由。这样的生命自由感使其获得精神愉悦,从单纯感官上的欲望满足上升到追寻心灵自由层面,体现了生命意义的快感,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美感体验的组成部分,构建其审美化的生活氛围。
1.2 闲赏山水,钟情绘画
闲暇的生活状态本就是审美实践发生的文化场域,程嘉燧在日常生活中闲赏山水,游踪遍布江南各地。而对于绘画的喜爱甚至达到“癖”的程度,这也是他脱离世俗功利,带有主观色彩的美感世界的沉浸表现。这样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带有艺术化和审美化追求。
自然山水总是具有治愈功能,张岱对于西湖风光的偏爱,袁宏道唾弃为官生活而向往自然山水的闲适,李流芳山水游记中的清新秀美江南风光,这些无不表现了晚明文人对于山水自然的向往。但许多晚明文人虽向往“闲赏山水”,却放不下繁华世俗中的名利富贵,因而只能停留在“濠濮间想”的层面,而程嘉燧一生未曾入仕的经历则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真正沉浸于山水自然风光中。
程嘉燧诗中多有与友人出游欣赏自然风光所作。如《同闲孟长蘅出郭看梅期游江桥作》:“薄薄晴云漏日微,风江连郭雪花飞……浊酒半倾还自恋,扁舟一弄已忘归。”[5]100表现了作者沉醉在江桥风光中不愿离去的留恋之情。而《石冈园杂诗五首》[5]101中有“沿林新笋成,柳桥尘乍染,枳径雪初明”“不识涧花落,惟闻潭水香”“泉酒带冰绿,园瓜出井甘”等清新动人的诗句,描绘了自然风光的秀美和游玩时的情态,生动体现了他对于自然山水的热爱之情。“清风明月本无价,纵尔不禁宁非贪。”[5]179称自然山水乃是无价之宝,不应让世俗之人的贪心玷污。“画取铁花岩壁去,千金休买碧玲珑。”[5]193同样强调山水景物的珍贵,不可用金钱衡量,其爱念山水之情可见一斑。此外,他还有很多的山水游记,记述其游玩的景色,如《余杭至临安山水记》:“远山色若翠羽,时出松杪……远水穷处,爰有高山入云,黛色欲滴,与丛林交青、深溪合翠,森沉蓊薆。”[5]309将山色的青翠描绘得清新灵动。《临安至昌化》:“望见九里桥,山峦岑秀,松柏槠楠,蒙茏其上,人家倚薄其下。危桥浅沙,马渡沙际,人行树间,暮色晻霭,宛在画中。”[5]310葱茏的山林云气层叠,作者在其中穿行宛如入画,这样的山水在作者眼中别具情致,有着画意之美。
程嘉燧以诗画家身份闻名于晚明东南文坛,善画山水,兼工写生,且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绘画的喜爱甚至已经超越了诗歌。《题张伯美画留通州天宁寺》[5]83中有“爱画余宿习”之句,可见其热爱绘画时间由来已久,“主僧爱入骨,此幅原相乞。”则表现自己的画技高超,带着一种自己心爱之物被人承认的骄傲之感。“纵耽书画癖,难使饥渴济。”[5]85则表达即使沉溺书画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却还是不能放弃对它们的热爱。“开书同愈疾,爱画即忘形。”[5]106更是描绘了一个痴迷书画,沉醉其中的痴人形象。“独惭爱画淹行色,看饱何殊说食时。”[5]134写出对画的喜爱已经到了忘食地步,可见其热爱程度。而且他还有对自己画技直白称赞的诗句,如“自笑前身应画师,能描露叶与风枝”[5]211“临行尚自爱余笔,点染得似云林逸”[5]452等。借友人对自己画作的喜爱侧面烘托自己的绘画技术,且称自己绘画风格有倪云林的潇洒飘逸。如果不是极度的癖好,是不会有如此直白自负的描述,而他的作品中却不见他对自己的诗歌作如此评价,可见他钟情于绘画,甚至可能一度超越了诗歌。这样对于自然山水和绘画艺术纯粹的欣赏表现了审美活动的无功利性特征,体现了程嘉燧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化享受。
1.3 企慕隐逸,安于闲淡
在晚明时期,国家政治衰颓、内忧与外患并存,备受迫害的文人士大夫们与政权疏离,志趣转向隐居山林和平淡悠逸的生活方式。文人们不管是身在庙堂还是江湖之间,大都羡慕隐居和闲淡生活的舒适安逸,作品中也多流露出向往企慕之情。这样一种安于闲淡的生活态度是出于热爱日常生活的一种审美实践表达,它指向一种精神境界,而达成这种精神、生命自由实质上就是一种“闲”的境界,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审美境界[7]65。
程嘉燧作品中多有企慕隐逸生活的表达。如“自识戴颙招隐处,闲心常挂白云岑”[5]50直白地表达了诗人心中对于归隐生活的向往。“浣溪花里人高卧,不为苍生起谢安”[5]230描绘了在山水中徜徉之乐,竟不忍为了苍生而起用谢安打扰他的隐居生活,可见程嘉燧对于隐居之渴慕,就连民生疾苦也无法与之相较。“岁寒知自保,终作鹤鸣皋”[5]241则写出了作者在历尽人生疾苦之后,才明白“自保”的人生态度和贤士最终也得回归隐居来获得完满的人生道理,表达了隐居终是人生归宿的思想。“梦想东山下,春风几度花”[5]242更是以谢安的东山之乐作为人生梦想,直接表现了作者对其种生活的企慕之情。在《陈眉公七十赠诗》中,程嘉燧夸赞眉公德行和隐居山中的惬意生活:“纫兰为佩制荷衿,婉娈书堂十亩阴……山中宰相神仙箓,海上园公绮季心。直与冥鸿恣寥廓,漫容鸥鸟自浮沉。”[5]253可见其对于眉公隐居的羡慕和向往之情,因此在他的眼中隐居生活才会如此快活似神仙。同样在《赠西邻唐隐君》[5]432一诗中,他首先写“仲长岂羡帝王门,樊须自习丘园乐”,描绘了隐士们在田园中自得其乐,不慕世间繁华富贵,以“安得逐君种鱼剪酒仍披葱,不愿吹芋列鼎兼鸣钟”之句表达自己向往隐士的隐居安逸生活,不愿挣扎于名利场中。而“遥知逢旧侣,云外自招邀”[5]104则描绘了诗人想象中与昔日旧友在山水之间相约隐居的美好生活。在年老之后与钱谦益在耦耕堂隐居之时,诗人对于即将到来的隐居生活更是兴奋不已,畅想着过上“相随种豆南山下,草长苗稀计已疏”“秋水濠边问园吏,桃花源上狎秦渔,卧游四壁神仙画,行把残编老易书”[5]462等像陶渊明一样种豆南山下,似桃花源中人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书画山水相伴的隐逸生活。这些无不表现着程嘉燧对于隐居安逸生活的向往和渴慕。
除了企慕隐逸之外,程嘉燧的作品中更有许多不慕富贵繁华,安于闲淡萧散生活的表达。如“兴阑白日忘归缓,看剑摊书正满床”[5]55“山月下来残酒醒,摘将荷叶盖头归”[5]150“林烟未散远峰出,手卷残经看夕阳”[5]150等句,描绘了一幅幅慵懒惬意的生活画卷,或是倚床读书,或是泛舟赏月,或是在夕阳西下时手拿佛经对山远望,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对于闲逸生活的享受。“最爱田居情味好,驱驰人事莫相催”[5]65“嚣然轻王侯,讵屑瓶罍诮”[5]83“若闻富贵荣枯话,但指浮云与太空”[5]185则是写出了作者不愿为世俗琐事所累,不追求富贵功名,向往安闲生活。与友人外出赏花时写道:“远岸夭桃看不尽,舟人舞道彩霞生……枝枝含笑留人醉,逢著深藂来去行。”[5]60以景物的动人姿态表达出游玩时的享受快乐。更有想要买田宅但因为银钱不够而有俚语“城南水竹称幽情,几念还乡买未成……好语山妻与村婢,莫贪春睡饷春耕”[5]60。可见他对于闲散生活的享受和向往,安于闲淡隐逸,并不求富贵功名,更愿在山水之间随意著几间茅茨,过上“何日枕书茶榻畔,松风无恙竹平安”[5]239的安逸舒适生活。这样的安闲状态构建了其特色的审美意境,即在平淡生活中寻找生命之美,将日常生活提升到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层次。
1.4 喜好交友
从根本上说,中国古典哲学或美学就是一种生命哲学或生命美学,以人的生存或生命为支点展开思考与论说。“生”的核心是对生命的礼赞、颂扬、崇敬、祈望、思考[7]182。而这种对于生命的尊敬在生活中有很多表现,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与人交往。正如林语堂先生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说道:“他如更想要享受人生,则第一个必要条件即是和性情相投的人交朋友,须尽力维持这友谊,如妻子要维持其丈夫的爱情一般,或如一个下棋名手宁愿跑一千里长途去会见一个同志一般。”[8]与志同道合的人交往可以在精神沟通上得到认同和互相成就,谈诗论画、品评艺术等雅致活动构建起日程生活审美实践的文化氛围。
程嘉燧的生活审美实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与人交游中构建起来的。他喜好交友,提到他的好友,首先无法绕开的就是钱谦益。他与钱谦益是经由李流芳的介绍认识,相熟于程嘉燧中年时期,到了晚年时更是一起在耦耕堂隐居数年,足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深厚。程嘉燧诗中常有记述两人之间交往的情景,如《和钱受之劝酒》:“玉色新醪忆共持,岂无他友独君思?闲宜白传开斋日,达似刘伶席地时……”[5]252《再叠前韵和受之失子》:“良醖今朝且共持,无穷身外莫闲思。只如南郭遗形后,何异东门失子时!思酒但知陶令是,消忧唯恐杜康迟。醉乡一往无多地,除却尊前更诣谁?”[5]252两首诗都是在钱谦益失去儿子悲痛不已之时劝慰他所作,真诚动人,可见两人之间的友情。在崇祯三年时,程嘉燧与钱谦益隐居在耦耕堂,时间长达十年。这十年中间他们晨夕游处,数次共同守岁度年,优游于自然山水之间,诗酒唱和,访禅悟道,佳文共赏,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两人之间的深入交往使钱谦益得以从程嘉燧身上学习作诗之法,更发出“孟阳诗律是吾诗”之语,也正是因为钱谦益这位影响力颇大的文学家的推崇,才使得程嘉燧在晚明文坛上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与钱谦益之间的交游之外,程嘉燧同样和与他并称“嘉定四先生”的其余三位交往至深。他与李流芳之间不只是朋友更是表亲关系,作品中常有与之交游的记述。如《寄李长蘅》:“知君明月中峰夜,梦与谁人共往还。”[5]56表达了对于朋友的思念。和李流芳出门游玩而不愿离去之时有“浊酒半倾还目恋,扁舟一弄已忘归”[5]100之句。送别时更有表现万分不舍的“何当与子别,恻恻乃多违”[5]136。还有表现与娄坚之间交往的记述,如《送娄兄子柔赴京兆试三十二韵》《送子柔兄金陵试三首》《送子柔乡试》,几乎每一次娄坚的考试,程嘉燧都会写诗送别表达对于娄坚的祝愿,可见两人之间的友谊深厚。他与唐时升之间有《唐叔达兄五十》《唐叔达兄六十初度》等祝寿诗,称赞唐叔达不慕名利的高洁情操,更有与其一同游玩的若干诗歌记录。并且在他们的生日之时都有寿序之文,朋友死去之后也各有祭文表示哀悼,情真意切。除此之外,程嘉燧还与李茂修、孙履和、宋比玉、许康侯、金子鱼、丘子成、瞿起田、郑闲孟、张伯美等人有密切的交往,更是与徐学谟、陈眉公等名望甚高的前辈之人也有诗歌往来,且他们都对程嘉燧充满欣赏之意。他的作品中大半都是和这些朋友交往游玩或送别的诗文,他们一起赏花泛舟,品评书画,享受生活的艺术,构建起程嘉燧日常生活审美实践中的文化氛围。
2 日常生活审美实践的成因
2.1 心、儒、禅的熏染
晚明文化与心学关系密切。阳明心学崛起于明中叶,盛行于明代后期,在哲学上,它以“心即理”取代朱熹的“性即理”,以反朱学姿态出现于思想界,认为心就是性,就是天理,就是天地万物本体。心是精神本体,是宇宙最高本体,心有至高无上的功能[9]33。这样的理论将人的主体精神标榜得至高无上,发展到晚明时期就成为了文人士大夫们纵欲风气的挡箭牌。他们将自身肉体欲望和精神欲望合理化,因而走上了沉溺声色、注重享受的精致审美生活。程嘉燧主要活动于晚明时期,受心学影响,因而其生活审美实践活动中带有任情之风,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享受身体感官的愉悦,追求世俗男女之情,行事作风率性从心。
儒学在整个传统文化的脉络中传承已久,它的影响不会消退。自先秦而起至明清,儒家思想贯通于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历史长河,君子人格似乎已经刻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骨子里,故而晚明文人在纵情声色、自我享受的生活之外,依然会对自身行为进行反省。他们好像被分为了两个部分,一半追求闲适享乐,另一半却依然以儒学传统反思自身行为。且程嘉燧的父亲从小跟着舅舅读书学习,因此在家庭教育中仍然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教育子女,所以程嘉燧的骨子里依然流淌着儒学传统,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释情而有度,率性从心但也以礼和道德标准节制自身。
而明代中叶之后禅宗的兴起使得晚明文人们在世俗中备受迫害之后,转向修习禅佛,为的是安顿身体,获得超然解脱。程嘉燧在生命的后期皈依佛门,常读庄老、禅宗之类清心养性之书,并且依靠这些书籍来缓解内心对于生活贫困和生命衰老的焦虑。也正是因为禅宗的影响,他才会向往隐逸闲淡的生活,不愿再受羁绊于凡尘俗世中的名利富贵,只想在游历山水中安顿身心,获取内心的平静,养生养性,享受闲淡生活,表现出特有的生命意识。
2.2 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
社会时代背景对于晚明文人生活审美实践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一是由于明代政治从弘治、正德年间就开始走下坡路,自嘉靖以后更是混乱不堪。主政中皇帝的长期缺席导致宦官专政,有志之士缺乏有力支持,无实权何谈治国?官员升迁无门致使文人士大夫们对于科举入仕的热情大为削减。在朝大臣中的正直之士大多受到宦官集团的迫害,宦官们甚至在皇帝的默许下对士人们施行暴政,致使士人们身心都受到严重迫害。宦官魏忠贤广设锦衣卫,监视大臣,四处捕风捉影陷害正义之士,导致整个社会上下人心惶惶。士人们与国家政权疏离,对于朝廷和政治绝望,甚至出现了“断指不仕”的情况,足见政治黑暗给文人士大夫们带来的毁灭感。
这样的政治状况下,出现了大量“山人”和“闲人”。他们不入朝堂,却活跃在江湖之间,或用纵情声色、放诞怪奇的生活来麻痹自己备受迫害的身心,或寄情山水,用自然景色来抚慰伤痛,因此整个晚明社会呈现出一种纵欲与闲赏并行的状态。政治的黑暗导致文人不仕,于是转向寄情山水,程嘉燧就是在二十岁时参加科举不中遂弃之,因此也就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游山玩水,作诗学画,闻名诗坛和画坛。其二是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商业文化的兴起,使商人这一群体在社会中凸显出来,他们掌握着社会上大部分的财富,有奢侈的生活水平,甚至可以用金钱去换取走向上层社会的途径。这便使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受到冲击,“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现象越发严重,本该处于社会最上层的士人却常常因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售卖自己的作品,于是就出现了“士商合流”的现象。为了逃避政治伤痛和维持生计,士人们逐渐融入市民世俗生活,体认到了繁华生活所带来的迷醉感,于是他们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因此他们在世俗中找到了生活乐趣,抚慰了受伤的心灵,但同时也沾染上了世俗生活气息,行事愈加放诞不堪。
2.3 个人因素
除了思想和社会的大背景之外,程嘉燧的生活审美实践中呈现的独特性更有其个人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先贤之人的影响。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有言:“孟阳之学诗也,以为学古人之诗,不当但学其诗,知古人之为人,而后其诗可得而学也。其志洁,其行芳,温柔而敦厚,色不淫而怨不乱,此古人之人,而古人之所以为诗也。”[6]576可见孟阳学习古人之诗更学古人为人,而他在诗集自序中提到自己少学唐人之诗,精熟李、杜二家,而后转为宗宋,常有和苏轼的作品。可知程嘉燧当是学习了李白的潇洒飘逸,才可以在一次科举不中之后便绝意仕途;学习杜甫的忧国爱民,才会以布衣之身深切关怀国家民生,更有着和杜甫“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般的博大心胸,期冀以布衣之身得庇九州寒;学习苏轼的豁达从容胸怀,才可以在家贫生计无继之时依然热情好客,从不讳言自身的贫穷困窘之境,甚至于直接写信向朋友讨要钱财,视富贵名利如过眼烟云。程嘉燧不仅是诗人还是画家,他的画学元代四大家中的“倪、黄”二人,尤其是倪云林萧散空疏之境。元代画家由于政治上的压迫黑暗,在生活中和作画时会刻意追求孤洁、高逸之气,倪云林正是其中典型代表。程嘉燧学云林画法,更学其为人,因而不慕富贵,安于平淡,向往“玄经读罢心如水,松风无恙竹平安”[5]239的生活。程嘉燧在学习先贤诗画时更学习他们的为人,将他们的高尚品格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审美特征。
其次是交往之人的影响。程嘉燧喜好交友,朋友遍布,他们在一起出游、作诗、绘画、赏花,密切的交往使他们在思想人格心态上相互影响,其中尤以与他交往密切,并称为“嘉定四先生”的另外三人影响最甚。李流芳是孟阳表亲,吴承学先生在《晚明小品研究》中评价他:“李流芳的特别之处,是保持一种高洁雅致的审美趣味,与流俗相去甚远,有一种孤芳自赏的意味。”[9]211可见其志行高洁,人品贵重。唐时升是他们中对于武学较为精通之人,在他的影响下程嘉燧少年时学击剑不成之后,在此后人生中与“武”字总有粘连。而对于唐时升,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有评价:“少有异才,未三十而谢去举子业,读书汲古。通达世务……”[6]579可知其也是一位率性而有才之人。娄坚则有“经明行修,学者推为大师”[6]581之评价。其余的如金子鱼、宋比玉、孙履和兄弟等人,在程嘉燧为他们作的祭文和序中都可以看出是品行高洁,为人和善的有才之人。日常生活和这样的朋友交往,程嘉燧才会形成平和从容的积极生活审美实践。
3 结论
通过程嘉燧的日程生活审美实践可以看到,他既有晚明文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共性生活方式,也有来自于他个人成长和经历带来的个性化生活审美思想。相对于整个晚明时期文人而言,程嘉燧的生活审美观总体来说是积极向上、闲适而自由的,与同时代晚明文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儒学传统在他身上保留得较多,影响也更为深厚,因而他的日常生活审美实践在晚明畸形的社会状态下是难得的平和积极。这样的审美实践也使得他的创作具有简单清丽之美,脱离矫情做作的文风,并以布衣身份在晚明东南文坛占据一席之地。
刘悦笛先生在其访谈中说道:“美是从生活中生发出来的,中国古典美学就是原生态的生活美学传统,从而形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中国人的生活艺术。”[10]探究古人的生活审美实践,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使古典生活美学传统在当代得到现代转换,让审美化的生活成为改变世界的高级标尺,促使现代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追寻更高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