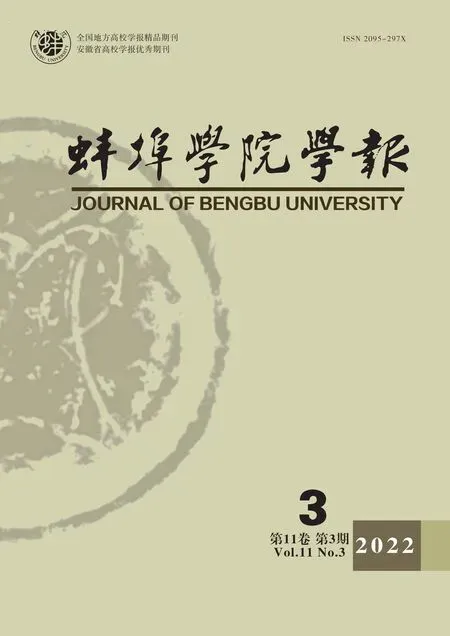萧红笔下人物蕴含的作者情感密码探讨
2022-03-16王肖迪
王肖迪,任 强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才女,其杰出的创作才能与复杂的情感纠葛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与其短暂的创作生涯相比,学术界对萧红生平及其作品的研究显得漫长而曲折,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生平身世和文学创作两类,生平身世类的有葛浩文《萧红评传》[1]、季红真《萧红传》[2]等,文学创作类的有郑莉《悲悯与彻悟的独特表达——简论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文本特征》[3]、刘银芳《论萧红小说的空间叙事》[4]、沙媛媛《萧红小说的空间叙事》[5]、钟蓓蓓《萧红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6]等。综合前人研究,生平经历和作品创作都已有相当深度,但对其生平经历与创作关系的深入研究似乎还比较少,仅有谭桂林《论萧红创作中的童年母题》[7]、易惠霞《论萧红小说的童年母题叙事》[8]、任双《东北文坛三杰的情感及其创作》[9]、袁国兴《萧红“寂寞”的“问诊”和“疗伤”》[10]等。因此,需要在对萧红悲情命运的探索和文学作品[11]精读的基础上,分析其情感与创作两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发掘隐藏在作品人物身上的作者情感密码。
1 女性悲剧命运的哀歌
萧红幼年时期就失去了生母,母爱的缺失,使萧红幼年便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格外敏感,而父亲的冷酷强权让萧红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这些童年带着性别色彩的记忆在幼年的萧红心里扎了根,影响萧红的一生。而成年后追逐爱情的惨痛经历使她再次感受到男女在对待婚姻恋爱中态度的巨大差异,及家庭生活中双方地位的巨大悬殊。通览其一生的文学创作,可以说萧红一直在带着女性的身份去写作。
1.1 追求爱情而不得的女性
无论任何时代,爱情都是女性视为第一生命的东西,而萧红笔下的爱情婚姻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灰黑色。梳理萧红一生的情感经历,她先是不满父亲的包办婚姻,与表哥陆哲舜出走北平。在表哥迫于现实的压力向家庭妥协后,无奈的萧红又投奔汪恩甲,但身怀六甲却被抛弃。而后与萧军幸福结合又痛苦分离,最后和端木蕻良的貌合神离,令萧红心力交瘁,悒悒不得振作。萧红一生多次承受着被自己所爱之人无情伤害的痛苦,感情上的一再受挫,使得这个原本极富理智的女作家被自己所诅咒的狭小圈子所束缚,内心时常充斥着无从言说的孤苦和寂寞。这位寂寞的悲情女子只好将自己浓烈的情感体验诉诸于文字之间,以企自我的寂寞情绪得以宣泄。
《呼兰河传》里原本被人们盛赞的漂亮能干、带有福相的王大姑娘勇于寻爱,没有经过父母的准许就与冯歪嘴子同居生子。这与小城居民固守传统、严恪礼教的风俗习惯大相径庭。围观者幸灾乐祸般地给王大姑娘作传,肆意传播着关于王大姑娘的“恶言恶行”。在无数流言的诋毁以及他人的戳戳点点中,王大姑娘成了周围看客所组成的无意识杀人团手里的牺牲品。
最能体现萧红泣诉女性爱情追求悲剧的当属她所创作的《生死场》。金枝由于自由恋爱,受到了母亲和村里人无尽的嘲讽,使得这个初尝爱情美好的女子,只能独自一人在寂静的黑夜里低声哭泣,哭得又是那样的低声,“还不如窗纸的鸣响。”[12]60此处因自由恋爱而受尽人们嘲讽的金枝,实际上体现了当时社会是不允许女性勇敢逐爱的现实。通过阅读萧红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萧红笔下的爱情追求里的女性是不幸的,她们长期生活在男性拥有绝对话语权的笼罩下,没有丝毫自由呼吸的机会与可能。
1.2 被包办婚姻束缚的女性
与成长在父母双亲庇佑下的孩子不同,自幼缺少父母双亲精神抚慰和亲切教诲的萧红没有享受到足够的安宁与欢乐,作品中多次描写到阴暗恐怖的人生状态和淡漠冷酷的人际关系,并对人性本质不断进行拷问。
《小城三月》温婉可人的梅姨恪守封建礼教,向来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无奈接受了母亲的包办婚姻,并且始终觉得自己是寡妇的女儿比别人低一等,在生命消弥之际也不向自己所爱之人吐露自己的思念与爱恋,任凭自我在极端痛苦与抑郁中走向死亡。梅姨的人生经历充分体现了包办婚姻对女子的毒害。
《呼兰河传》里长得黝黑壮实的小团圆媳妇,仅仅是因为刚进婆家多吃了两碗饭,见人一点也不害羞,便被小城人们定义为“不守礼教”,不像一个小团圆媳妇,就受到婆婆的惩罚,开始了自己如噩梦一般的非人生活。而后又在愚昧无知的围观者的推波助澜下,她遭受到请道士、看神医、洗热水澡诸多封建迷信的荒谬治疗,最终一个鲜活生动的生命被无情夺去,令人叹惋。
《生死场》里的麻面婆好像永远没有脾气似的,“她一遇到不快时,都是像一摊蜡消融下来。 ”[12]38麻面婆的这种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选择忍气吞声的性格,正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要求女性一定要“贤良淑德”的体现,也是包办婚姻束缚女性时代缩影的一种表现。
萧红笔下的女性无一不被封建包办婚姻束缚,在各种势力的压迫下,她们无法畅快呼吸,只能承受着种种迫害,既不能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更不能自由地选择爱人伴侣,只能在这种极度压抑的环境中默默承受,孤独终老。
1.3 陷入生儿育女困厄的女性
女性的生儿育女似乎一直承载着延续香火的功利色彩,萧红一生有过两次怀孕分娩的经历,而且生育之时孩子的生父都没有陪伴在萧红身边,出生后的孩子也没有得到她自己的照顾,一个送人,一个夭折。这种情感的断裂、骨肉的剥离给萧红心理上造成了深重的创伤,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一点一点吞噬着萧红的生命。对于这种无法弥补的直击心灵的伤痛,萧红只有将其诉诸文学书写中,才能达到自我寂寞的疗伤作用。
萧红在自己的很多创作中都写到了女性的生育。最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便是《生死场》里对女性生产情境的描绘,面临生产之痛的女性在这里似乎毫无尊严可言。文中所描绘到的女性生育场面无一不是血腥裸露的。赤身待产的五姑姑的姐姐,生产之际忍受着极端的痛苦却不敢哼叫,生怕惹得自己男人不高兴。“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12]124“二里半”的老婆在生产之际不禁直呼:“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肚子给割开吧!”[12]128而女性这一用生命孕育生命的伟大过程竟被看作如同动物产仔一样随意自然。将女性与动物等同起来,实属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悲哀。
萧红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描写,为爱情婚姻、生儿育女、封建礼教扼制下的女性苦难披上了一层阴冷的外衣,女性的苦难在这里得到全方位的展示,这些始终生活在社会与家庭双重压迫中的女性承受着灵魂和肉体的双重磨难,苦苦挣扎却效果甚微,这使女性生存的原始混沌、苦涩意味更见深厚。
2 男性英雄神话的解构
因幼年母爱的缺失、父亲的淡漠,祖父离世后,萧红彻底与家庭决裂,开始了自己的漂泊孤苦生活。在“从异乡又奔向异乡”的流浪中,经济持续窘迫、物质极度匮乏的状况深刻地影响着萧红的文学创作,她塑造了不少艰难跋涉的女性形象。而与女性形象相对的男性形象,在萧红笔下则愚昧无知、自私冷漠。也许父亲的冷酷强权,使萧红感受到男性主导的社会里的压抑,在以往的文学史中,男性形象总是承担英雄或者“拯救者”的角色,但在萧红作品中,却解构了传统文学史中的男性形象。
2.1 自私冷漠的乡村愚夫
萧红描写的劳苦大众女性更多地表现她们在悲惨生活中的挣扎。《王阿嫂的死》中善良朴实的王阿嫂,拖着病重的身体在地主的土地上艰苦劳作,最后却被地主踢得早产,与肚子中的婴儿一起死去。《弃儿》中的芹,于极端孤苦的环境下无奈抛弃自己的孩子,在陷入困境之际,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死去的祖父,以及自己这些年来离家漂泊的悲惨遭际,潸然泪下。《朦胧的期待》里已经在国共相争中失去了第一个情人的李妈,还要面对爱慕倾心的金立之在抗日战争中走向战场的生死未卜,独留她一人品尝着无尽的思念与心酸。 萧红看来,女性的悲剧固然有多种原因,但男性的愚昧无知且自私冷漠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正是基于这样的切身感受和清醒意识,萧红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自私冷漠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乡土农村愚夫形象。
《生死场》中胆小怯弱的主人公“二里半”因自家山羊丢失,外出寻找,在寻找山羊的路上不小心踩到了邻居家的白菜与人发生争执,被人家打得丢掉草帽仓皇逃跑。逃回家里不仅不接受老婆的安慰,反而将一腔怨气撒在她身上,骂自己老婆愚蠢。对外唯唯诺诺,在家霸道冷漠,在“二里半”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狂热的成业不仅没有因为金枝怀有身孕善待她,反而时常无缘由地迁怒于她,又因米价的跌落暴跳如雷,极度残忍地摔死了刚刚足月的小金枝。五姑姑的姐姐成日里任劳任怨,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她的酒鬼丈夫不但对其毫不疼惜,反倒对她颐指气使,任意打骂;月英的丈夫对瘫痪在床的月英不管不顾,态度冷漠得像一块儿石头,还极为残忍地把月英床上所有的被褥都撤掉,只留几块砖头让她倚靠,致使月英下身生蛆,活活烂死。
由此可以看到,萧红笔下的男性总是将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如意无端迁怒到自己的妻子身上,直接地摧残了她们的身心健康,践踏了她们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可见,萧红不仅能从自身的生活实际出发,以一种贴近生活的笔触将自己生活的苦楚展示给读者看,亦能跳出了个人的狭小圈子,将自己的目光直接对准自己所熟悉的劳苦大众,直接去描绘女性的悲惨生活,又表现乡土农村愚夫的自私冷漠。
2.2 卑怯懦弱的城市知识分子
萧红笔下的女性知识分子往往表现得很坚强。《广告副手》里的芹,显然有萧红自己的影子在里面。萧红与萧军生活在一起后,为缓解两人的生活压力,曾去电影院画过广告画。小说中,芹为了解决温饱问题,给自己家里添些柴,买些米,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给电影院画广告,强忍病痛工作,却不被心爱的人所理解。芹的忠贞不渝、不怕吃苦,也是大多数陷入贫苦的知识分子饥寒交迫下仍积极上进的典型代表。
而与之相对的男性知识分子则不然。萧红笔下的男性知识分子并不多,但却更能体现其解构男权中心文化的力度和彻底性。在自叙性散文《夏夜》中,萧红不无揶揄地说许多男人骂涂了口红的小姐们是“恶魔”,实际上是害怕自己被她们拒绝的卑琐措辞;在小说《三个无聊的人》中,她更为直接地揭示出知识分子的虚伪无耻,讽刺了他们拿别人的痛苦取乐的变态癖好。“胖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一心只想着嫖娼,美其名曰是为了“在女人身上研究出更多科学”;“窄肩头”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便到公园去看一个没有手脚的乞丐在公园小道旁滚叫;“老黑”或躺在床上睡觉,或就着沙门鱼吃面包,最无聊的时候则和着不成调的四弦琴唱“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如此种种,可谓斯文扫地,丑态毕露。
最能体现萧红对男权中心文化讽刺的当属她创作的《马伯乐》。马伯乐在家庭中丝毫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与担当,有的只是无限的卑怯和懦弱,不但经济上不能自立,总是畏畏缩缩地向父亲与妻子讨钱,而且在拿到钱后马上变了一副嘴脸,而且人格上十分自私,只爱自己。当危险来临时,他总是不顾亲人,只想着自己一个人能逃到最安全的地方去。在火车站逃难时马伯乐也只顾得一人往前走,以致自己的太太与三个孩子全都没有挤上火车,骂骂咧咧的他只好再跳下来,令人啼笑皆非。
在社会上,马伯乐也丝毫没有应有的民族使命感,他眼里只有钱,恬不知耻地打着爱国抗日的幌子写抗战小说猎取钱财,苟且偷生中竟然希望凭借战乱把妻子带的钱归为己有,因为他的世界观是只要有了钱,世间的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这里的马伯乐既没有男人的担当,也没有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格、廉耻与同情心,就是一个自私怯弱的苟活者。
萧红从知识分子这一立场出发,通过书写知识分子的苦闷与不幸来表现社会生活的残酷性。在创作中,萧红正是借他人之泪诉自己之悲,将自己的故事书写到文中主人公身上,从而释放自己多年暗藏于心中的矛盾纠葛。当生活的苦难朝他们袭来,弱小的他们向来迎难而上却仍然无法改变悲惨的命运结局。萧红笔下的许多女性都与作者一样,她们每个人在苦难的生活面前都没有退缩,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相信自己能够战胜苦难的坚定力量。这种力量也是支撑萧红于无数次颠沛流离之中不断前行的精神支柱。
然而,萧红的笔下的男人不是女人们托付终身的依靠和“保护神”,也不是艰难生活跋涉中的坚强支柱,反倒是给女人带来苦难的灾星。以上两类男性形象的刻画,深刻反映了萧红作为一名敏锐深刻的现代知识女性对男性英雄神话的解构与颠覆,和对男权中心文化的嘲讽与批判。
3 永恒的憧憬和追求
有研究者曾说:“创作主体的情感由文学语言表达出来,文学语言是创作主体情感表达的媒介。”[13]幼年亲情的极度缺失、成年感情的屡次受挫,使得本就敏感脆弱的萧红变得更为悲情低落。她害怕孤独,需要情感,追求自由却又不想被羁绊,这让萧红长久地生活在一种无从言说的寂寞之中,从而加剧了自我人生的悲情色彩。但观其一生,萧红都在憧憬与追求着,追求那真挚的感情,憧憬那温暖的爱。
萧红这种憧憬和追求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多有流露,阅读萧红的著作能充分感受到她对纯美爱情与炽热温暖的憧憬,且这种憧憬是完全超越身份地位的差别悬殊的。如《小城三月》里温婉动人的翠姨,又如《马伯乐》里胆小怕事的马伯乐,《后花园》里谦逊卑微的冯二成子,以及《生死场》里的金枝、“二里半”等。萧红正是借用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向读者言说着自我对温暖与爱的渴望。
3.1 对温暖的家庭无限憧憬
郁达夫曾说一切的小说都是作者所作的自叙传,任何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总会不可避免地将自己本人的生活经历贯穿于自己的文学创作里。孤寂乏爱的童年生活,坎坷多难的爱情遭遇,困厄窘迫的经济条件,使得悲情的萧红无比向往世间的一切温暖与平静,追求真爱、远离孤苦寂寞,便成了萧红一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萧红在不少的文学作品中都表达了自己对温暖家庭的憧憬与向往。
母亲离世后,幼年的萧红不被父亲善待,漫长的灰暗生活里只有年迈的祖父带给她些许色彩,给予年幼的她少许温暖,让她知道了这世界上除了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令人贪恋的温暖与爱。她“既无母爱,又无父爱”[14],祖父是萧红在漫长岁月里唯一可以依存的对象,祖父的离世使萧红感到世间的一切“爱”和“温暖”都变得空空虚虚,因此在萧红心里,祖父死了,自己的家也便没了。后来,萧红被赶出家门,真正成为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在离家后的流离漂泊中,萧红身上一直怀揣着一种“无家情怀”,这在她的自叙性语言“我没有家,我连家乡也没有”中便有流露。这种无家情怀一直影响着萧红的生活和创作,使她的作品总是充盈着一种淡淡的忧愁与涩味,从侧面流露出她对温暖家庭的憧憬,她将这种美好的憧憬诉诸于文字,借文中的人物来言说自我的向往。
《生死场》里被迫前往都市谋求生活的金枝,是如此的不舍离开自己的家乡与母亲,“她对于家乡的山是那般难舍,心脏在胸中飞起了!她不愿走了。”[12]212此处金枝的不舍,与作者当时离家远走之际的难舍难分是相通的,所以她能准确地描摹出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再看“二里半”在自己的老婆死后,在青山家里一连吃了三碗米饭仍不舍离去,作者这么描绘:“他自己没有了家庭,他贪恋别人的家庭。”[12]249作者此处对“二里半”的评断,实际上正是自己内心对温暖家庭憧憬的真实写照。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到自己笔下人物的身上,隐晦地传达出自己对家庭的向往。长久的漂泊生活使得萧红渴望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这一美好憧憬成为她写作的内在动力。
3.2 对真挚的爱情永恒追求
在中国现代知名女作家中,萧红的情感经历无疑是最复杂的。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与萧红曾有亲密关系的男性有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三位,除此之外她还有两次怀孕分娩的经历,复杂的情感纠葛对萧红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便是她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来的自我对真挚爱恋的深切渴望。
《小城三月》里温婉动人的翠姨如此炽烈地暗恋着“我”的表哥,独自一人品尝着这朦胧爱恋背后的寂静与欢喜,甚至在其生命濒临枯竭之际仍将自己单纯真挚的爱埋藏在心底。这种坚定真挚的爱恋正是萧红所向往的,她巧妙地借文中翠姨的心理倾诉着自己对真挚爱情的渴望,令人为之动容;《后花园》里辛勤卑微的劳动者冯二成子,亦怀揣着对邻家娟秀姑娘的深深爱恋,让作者感叹道:“他爱了她,好像在信仰一种宗教一样。”[15]行文之间,无不流露着作者对深情之恋的向往。在萧红心里“真爱”便是她宗教般的信仰,她于短暂的生命中为这一坚定信仰不断前行,不断努力。
除此之外,在萧红笔下即使是像马伯乐那样怯弱、自私胆小不为世人所看好之人,仍旧怀揣着对纯纯恋爱的憧憬,在马伯乐写给王小姐的情诗——“我为你,我舍弃了我的生命,我为你,我舍弃了我的一切”[16]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马伯乐对王小姐爱得炽烈浓热。此处作者借马伯乐之口再次表达出自己对真挚爱情的强烈向往。
春光烂漫的三月,草长莺飞的大好时节,朦胧真挚的爱恋,这是萧红向往的感觉。但现实却是,与未婚夫汪恩甲在东兴顺旅店同居,经济状况十分窘迫直至最后被抛弃;与萧军、端木蕻良在一起颠沛流离最终爱意消散。在她的小说中,她如此向往明媚纯净的恋爱,并于短暂的人生里不断追求与寻找理想伴侣,这是文学作品对作者人生创伤的一种补偿。
4 结论
寂寞乏爱的童年生活、成年感情的屡次受挫,使萧红长久地陷入一种无从言说的寂寞孤苦之中,好比人在生病时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一样,这位悲情的女子唯有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人诉说的诸多忧愁尽情流溢于笔端,从而宣泄着自己的丰富情感。这是萧红对现实人生问诊的尝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把萧红的文学创作理解为情感的宣泄、寂寞的疗伤。她在有限的生命里创作出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在自己所塑造的人物身上倾诉着自己一生所感受到的、所经历过的孤苦和悲凉,言说着自己对温暖和爱的向往。萧红与故事中的人物一起体验,一起抗争,从而使作品产生出一种极具震撼力的悲剧性力量。
这位悲情的女作家用自己特有的才情表达着自我内心的抗争和不满,表述着自己内心的向往与渴望。她笔下的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凄凉与绝望,正更加突出地表达了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种高贵的人性关怀,这正是萧红用悲凉的情感书写所想要表达出来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