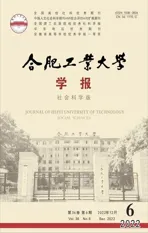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契合到结合探析
2022-03-14陈鸿海赵明月
陈鸿海, 赵明月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马克思主义萌发和初创于欧洲大地,为何不同于其他西欧文明,能够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如何与我国传统文化相适应?未来又该怎样实现两者的进一步结合?十几年来,学术界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社会和谐、伦理契合等宏观角度,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契合性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在此基础上,还应当从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层面,解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与中华大地上的传统文化为何能够融会贯通,又如何持续开花和结果。
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中国传统重民本情怀
立场指的是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持有的基本态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体现为马克思主义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以人民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的。究其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将精神、观念等当作历史的起点,也不是纯粹地从客体的方面理解历史,而是认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2]。就立足点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是从笼统的“人”出发,而是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立足点。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信“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从归宿上说,马克思主义最终是要建立“自由人联合体”。
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是在与神本思想、君本思想的对抗中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夏商时期,政权神授的观念逐渐系统化,“天命”彰显绝对权威。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的瓦解,神本位思想遭到极大冲击与动摇,重视人的地位与作用的思想纷至沓来。墨子提出“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舟也;民,水也”。此类“贵民”思想包含“以民为本”的进步色彩,但其本质上还停留在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君主本位。从东汉时起,人定胜天的观念在诸多思想家头脑中挥之不去。王允反对将天看作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提出人是有思想的存在。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黄宗羲以民本思想向君本思想发出挑战,主张“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一主张以严格制约君权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近代孙中山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地结束了在我国封建社会盛行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浇灭了压抑人性的君本思想火焰。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和中华传统重民本思想都呈现出“人民物质和精神共富”的追求。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贫苦大众的物质利益已经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成为他们急切关注的问题。从各等级代表对出版自由的态度中,马克思发现利益在人们思想与行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看到“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4],物质利益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从对英国曼彻斯特工业发展的观察,青年恩格斯也萌发了对工人贫困原因的思考。中国传统“以民为本”思想作为一种古代政治思想,在漫长的封建君主统治时期发挥着正理平治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上主张“富民”,通过调节百姓的生产与分配以实现物质上的富足。一方面,重视对“农时”的把握,禁忌侵夺农民劳作的时节。先秦管子将“无夺民时,则百姓富”提升为一项制度,保障了百姓基本生存需求;另一方面,反对苛捐杂税,主张轻徭薄赋。“易其田畴,薄其税敛”,通过减轻田租来缓解百姓的生活负担。但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最终旨归。马克思是要打破自发性的社会分工体系,充分施展自身才干,消除劳动产品与自身的异化,使其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而服务。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尽管是为了维护“君主”统治而论述“民”的重要性,却也已在相当程度上培养了民众内在的德行,具有培养民族品格的进步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立场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重民本的思想,虽然在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点和归宿上有着明显区别,但在对贫苦大众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强调以民为本的价值原则等方面的共通为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立场的探索与坚持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文化基因。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自身的文化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以人民为根基,将人民立场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进程。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时代之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立场的指导下,不断对传统专制视角下“人”与“民”的内涵和地位进行科学界定,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知行之辩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实践概念和实践理论,尽管在社会历史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但是由于物质生产水平低下限制着人们的眼界和思维,因此它们总是看不到实践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过程,正如其原理本身所说的那样,是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和研究而得来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已思考到社会关系存在的客观因素与主观能力的关系;在博士论文中由原子发生的偏斜运动已经联想到人的自由意志发生作用;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从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中开始深入关注现实物质利益矛盾;1845年马克思更是正面阐释实践观,指明“改变世界”高于“解释世界”的彻底性与革命性。
随着对现实市民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史前社会的进一步认识,马克思对实践内涵的理解逐步深化。首先,现实的实践活动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人的现实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社会特性,并受到某些社会历史条件的约束。同时,人们又是在物质生产实践、科学文化实践乃至虚拟实践中建立相应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等社会关系,从而划分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等。其次,实践是自觉能动的活动。就实践活动与意识的关系来讲,实践活动结束时所得到的结果,在活动者行动之前就自觉能动地在头脑中产生并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只是通过活动转化为现实。最后,实践是检验真理是非的客观标准。马克思不是将实践纯粹地归结为满足生理需要的活动,而是将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领域成为“理论思维真理性的证明”[5]。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对‘知行’关系的探讨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6]对这一主题的探讨贯穿我国上千年来的历史进程。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主张言行一致、少说多做;荀子以“学而知之”主张通过自身践履获得理性认识。由此观之,早期思想家虽然没有提出“实践”这一概念,但十分强调通过后天学习知识来提高学识和修养品性。随着汉王朝进一步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思想背后是将天意作为个人行为的是非标准,蕴含着“知先于行”的主张。从北宋时期到明末清初,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出知行关系的三种不同结论。宋朝程朱理学强调知先于行,知是行的本原,了然一定的知识是行动的必要准备;到明朝,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政治思想,认为知可以指导行,行又能体现出知。明末清初王夫之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揭示行是人们获得真知的根源,凸显了我国古代知行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提出“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透辟地论述了朴素辩证的知行关系。
由是观之,虽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古代知行观产生的时代背景、提出者所处的社会阶级等诸多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视角与研究目的上有所差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视角下以改造世界为目的对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的探讨,中国古代知行观则是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提供伦理道德规范,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主客体相统一的普遍联系又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国传统知行观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始终蕴含着联系、发展和矛盾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又不断深化前人对知与行关系的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与中国古代先哲们不谋而合地对“实践”与“认识”、“知”与“行”两对基本范畴的含义及其关系进行了辩证性和批判性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都在强调亲身躬行必要性的同时注重“知”对“行”的指导作用,主张对实践基本范畴的阐释要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前进的。这种异曲同工之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理念的高度契合,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行动指南。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下不断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以探索民族化、本土化的实践道路,又在中国具体实践中不断推进传统知行观的现代转化,创造出体现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晶和实践成果。从“反对本本”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知行观的契合、磨合与结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了思想与理论根基,而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实践的思维方式。
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日新求变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指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所获得的或所产生的基本观念及其在认识和改变现实世界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包括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辩证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等。其中,辩证思维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方法之中,以辩证分析方法较为典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将“现实的人”作为辩证方法的出发点,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超越。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考察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揭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7]。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强调以联系、发展和全面的眼光分析和解决问题,即从现存事物的联系中抓住问题的本质,从事物的运动变化中把握问题走向,从事物的矛盾转化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马克思晚年曾强烈斥责一些批评家把他关于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理论说成是一切民族相同的历史哲学理论。他以古罗马为例,指出罗马社会并未由于剥削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走进了奴隶制时代。由此印证,“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8]。
此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还体现在对每一现存事物、既成形式都是从肯定和否定两方面来理解,将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贯彻到底。马克思主义虽然竭力揭示资产阶级的丑陋本性,但是未曾否认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9]。他既看到了资产阶级对贫苦大众进行无情露骨的压迫,使包括生产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状况动荡不安和强迫一切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揭示了资产阶级在斩断人们之间封建宗法的情感羁绊、创造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奇迹和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财富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我国传统思想中存在凭借顿悟来领会天地万物的思维方式,但这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朴素辩证思想并不冲突。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思维方法是以朴素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具体表现为“天地一体”的整体观、“万物有对”的矛盾观和“日新又新”的革新观。孔子言“君子有三畏”,“敬畏”就意味着要依据客观规律行事,不可固执己见;《汉书》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要求治学需从文本出发考证古籍的真实内容和意蕴;清代朴学大家颜元坚持“以物为体”,主张要身体力行地认识客观事物。我国古人在这种朴素唯物论基础上,力戒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和胶柱鼓瑟等行为,要求把天地、个人和社会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由“推天道以明人事”开启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也奠定了我国传统整体思维方式的基石。董仲舒更是将阴阳二气、“金木水火土”五行与人的道德伦理相结合,构建了一个天人一体的宇宙系统。自此,人类与万事万物之间相互影响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日渐根深蒂固。与康德、黑格尔的那种基于自身逻辑演绎的辩证思想不同,我国古代辩证思维方法注重从观察自然和社会中揭示“万物无不有对”的矛盾观。道家学派老子在论及事物现象,提到美与恶、善与不善、难与易都是相比较而存在;在论及物品功用,提出器皿正因中空而能盛物、车轮正因有毂方能转动;在论及生命力量,提出舌头柔软而常存、牙齿坚硬却易损,柔软有韧胜过刚强粗壮。此外,中国传统辩证思想中还蕴含着日新求变的革新观。这种革新进步的思维方式不仅体现在器物的发明创造和道德上的修身自省,还体现在敢于推进社会治理变革的行动,如《周易》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尧舜主张根据当时具体环境对神农氏的治国之道加以调整;《孙子兵法》提倡求变用兵而制胜的策略。
尽管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辩证观念受到农耕经济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却仍然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不约而同地主张“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思维方式,这高度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精神深度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不在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去改造、重塑传统文化”[10];中国传统思维观念的当代价值不在于安常守故,而在于其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碰撞所迸发出的强大能量。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将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思维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方法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双重滋养,总结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儒家“执两用中”思想进行重整,阐述了矛盾即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邓小平吸纳与创新传统哲学中辩证性和创新性思维方式,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一国两制”构想等原创性成果。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辩证思想的运用提升到新的高度,提出有守有为的“底线思维”、靶向发力的“精准思维”、稳重执着的“战略定力思维”,这些科学思维方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相契合的生机活力。
四、从契合中探索结合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着眼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是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内在要求,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要求;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接续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路径,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思想需要,是实现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文化需要,是凝聚中华儿女大团结齐奋斗的实践需要。
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人民立场的契合,要求我们厚植人民情怀,秉持人民至上理念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保民”“爱民”和“为民”等精神。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提出,“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2];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13]。在新时代推动两者正确结合,就应当紧紧抓住人民大众立场这一契合点,尊重人民群众在“结合之路”上的主体地位,集聚全体中华儿女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力量,激活华夏儿女血液中流淌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激发中华儿女奋力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热情;将保障人民正当利益、满足人民切实需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价值遵循,以人民群众听不听得懂、记得牢不牢、用不用得上为标尺,衡量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终成效。
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知行关系的契合,要求我们固本培元,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并举中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之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奋进性力量必须在与具体民族的基本国情、文化特征和现实需要等实际结合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面对孤立无援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突破思想的枷锁,推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提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带动我国经济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新发展。由此观之,在新时代推进两者有机结合,就应当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并举,既要在发展原创性成果中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又要在鲜活实践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方面,要科学总结我国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并将其升华为原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原理科学回应时代课题和任务挑战,增强科学真理与人民大众的亲和力;另一方面,要在有效应对国内外环境考验中育新机开新局,将“实践结合之路”走向深入。既要树立全球视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主动共享中国智慧;又要坚守历史使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凝聚民族力量。
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辩证方法的契合,要求我们推陈出新,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中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之路。“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鲜少论述“文化”“传统文化”的明确概念,但是从未忽视过社会存在基础上社会意识的能动反作用,在很多思想观点中彰显出对待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5]。在新时代推动两者有效结合,就必须紧紧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科学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既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理论的研究与阐发,规范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在提炼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实现传统文化的内涵价值重赋,又要将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时代元素与现代文化科技相结合,拓展传统文化传承边界。
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构建起气势恢宏的精神谱系。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考量,我们需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力争在有机和有效的统一中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创新人类文明发展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焕发更旺盛的生机活力。
五、结 语
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精华,可以发现两者在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具体方法上存在诸多契合。由是观之,思想具有个别性,又具有一般性;文化是分民族的,同时又是世界性的;人类文明延续着共同的思想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可以跨越地域时空界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不拘泥于一时一世。坚定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固本培元、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双向互动,推陈出新、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构成了新征程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