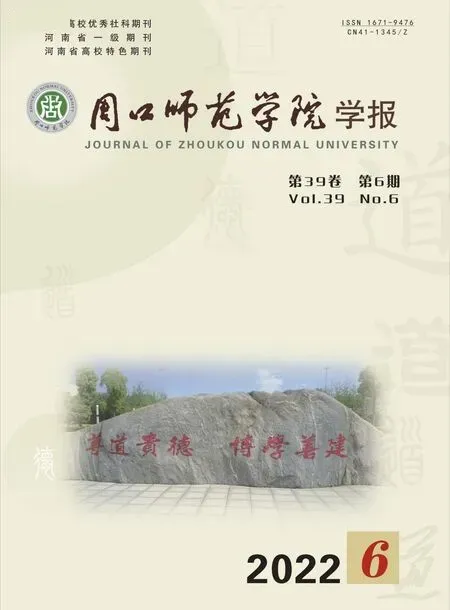揭开陶诗的生成机制
——读《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
2022-03-14张德恒
张德恒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诗人陶渊明(365-427)存世诗歌数量并不甚丰,而影响却甚大,苏轼评陶诗,谓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1]35,三复其言,倍感深含理趣,确实是关于陶诗的深造自得之论。然而,由于东坡评语的简省赅括,致使人们并不容易把握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风貌特征,于心虽有冥会,下笔却难追摹。换言之,“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陶诗,其创作机制安在?
近日,重读范子烨先生《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下引此书,皆据此本,为清眉目,简称“范著”),掩卷沉思,感慨良多。在笔者看来,虽然范著主要论述的是陶渊明《拟古》九首及《止酒》的内在机理和外部结构,但实际上对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探知陶诗的创生机制乃至中古文学创作趋向深具启发意义,而范著取融西方现代派的“互文性”理论(1)此处的“互文”是指“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互文性研究》,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5页)以观照陶诗,不仅对《拟古》九首和《止酒》作出了全新的迥异前人的解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互文性”理论本身,据此可说,范著的实践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其具体结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范著海涵地负,征引、融摄了极为浩繁的文献资料,其中不少资料及相关论述都可为研究者提供有益的研陶思路。
一、借助“互文性”理论,范著实际揭示出陶诗生成机制
范著第一部分“绪论”从“互文性”角度深刻、全面地阐述了锺嵘品陶的成因、意涵,为我们重新理解《诗品》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评价开辟了思路、拓展了疆域。
锺嵘《诗品》卷中“宋徴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2]41
上引这段话中的“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长期以来成为人们研究、争论的焦点,因为从人们对文学史的一般认识来讲,应璩、左思的作品无论如何也难以笼罩陶渊明的创作。职是之故,锺嵘《诗品》对陶渊明“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的评论,实际成为陶学研究的瓶颈。
关于应璩与陶潜,从“互文性”角度,范著提出,第一,陶潜《归园田居》其五“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杂诗》其二“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其十一“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时运》诗序“偶景独游,欣慨交心”、《时运》诗“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等诗句皆以应璩《杂诗》“秋日苦促短,遥夜邈绵绵。贫士感此时,慷慨不能眠”为底文,而陶潜《杂诗》的命题,亦当与应璩《杂诗》有关[3]30。第二,陶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说”、《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饮酒》其四“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其十五“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斑斑有翔鸟,寂寂无行迹”、《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饮酒》诗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等诗文皆以应璩《与曹昭伯笺》“空城寥廓,所闻者悲风,所见者鸟雀。其陈司空为邑宰,所在幽闲,独坐愁思,幸赖游蚁,以娱其意”为底文[3]30-31。第三,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与陶诗具有互文关系。如陶诗《赠羊长史》“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以“德非陈平,门无结驷之迹”为底文;《劝农》“董乐琴书,田园弗履”以“才劣仲舒,无下帷之思”为底文;《饮酒》其十六“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以“家贫孟公,无置酒之乐”为底文;等等。另外,范著还指出,应璩《与韦仲将书》与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咏贫士》其三,应璩《与夏侯孝智书》与渊明《饮酒》其十五,应璩《与阴中夏书》与渊明《归园田居》其一之间的互文关系。总而言之,以“互文性”为观照,范著较为合理地解释了锺嵘《诗品》中所谓的陶渊明诗“其源出于应璩”(2)笔者近撰《锺嵘〈诗品〉陶渊明诗源出应璩说辩证》(待刊),亦从肯定锺嵘角度论证其评论之合理性。事实上,关于锺嵘品陶问题,实际存在“绝对正确”与“相对正确”两个认识思路,所谓“绝对正确”意谓锺嵘品陶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延之万世而无别之结论,所谓“相对正确”意谓锺嵘所论在锺嵘所处时代以及锺嵘《诗品》语境下是正确合理的。不少研究者将锺嵘品陶假设为“绝对正确”之结论,然后再举证反驳锺嵘之论,实际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深化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其实,我们更应该从“相对正确”之思路,努力还原锺嵘品陶的时代风尚以及锺嵘本人诗学观、《诗品》语境等,从而深切认识锺嵘之论。。
关于左思与陶潜,从“互文性”角度,范著提出,第一,左思《杂诗》(秋风何冽冽)与渊明《和郭主簿》其二,《己酉岁九月九日》,《杂诗》其二、其四、其五,《九日闲居》,《岁暮和张常侍》,《咏贫士》其二等诗之间存在互文关系[3]35。第二,在揭示左思《招隐诗》其一末句“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与渊明《和郭主簿》其一末句“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互文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两首诗有六个韵脚“今”“琴”“林”“音”“襟”“簪”是相同的,从而确证了陶诗是对左诗的模拟、仿作,并申述“用韵选择上的亦步亦趋,已经触及了艺术形式的互文性问题”[3]35-37。第三,着重从作品形式、艺术风格的角度阐发左思《咏史》其六(荆轲饮燕市)与渊明《咏荆轲》、左思《娇女诗》与渊明《责子》诗之互文关系,从而突破单纯从作品内容、文学语言互文性角度论述问题,深化、丰富了互文性理论。总而言之,以“互文性”为观照,范著有力地彰明了锺嵘《诗品》中所谓的陶渊明诗“又协左思风力”。
为了更妥帖周密地诠释锺嵘“品陶”,作者还从家族与政治两方面分析了锺嵘品陶局限性的成因。作者通过考证,指出浔阳陶氏与颍川锺氏、浔阳陶氏与汝南应氏、浔阳翟氏与临淄左氏和浔阳陶氏等五个家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对锺嵘品陶的“局限性”作出切理餍心的析论,彻底突破了这一陶学研究的瓶颈。
范著第二部分深入挖掘、深刻论述了陶诗《拟古》九首与曹植的关系,这是该书的重心所在。而范著对《拟古》其九(种桑长江边)的考论则为阐发其他八首《拟古》诗奠定了基础,质言之,作者确认渊明《拟古》九首“这组诗乃是用曹植的口吻、眼光与心态来叙述、观照曹植的生活和思想,用曹植的文学语言、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来表现、刻画曹植的心态、思想和经历”[3]67-68的最有力的论证即是对《拟古》其九的探赜发微。作者以近50页(第69-117页)的篇幅详阐《拟古》其九与曹植的关系。指出曹植《转封东阿王谢表》之“雍丘下湿少桑”及《艳歌》之“遥望湖池桑”即陶诗“种桑长江边”之所本;《转封东阿王谢表》之“臣在雍丘,劬劳五年,左右罢怠,居业向定”及《自诫令》之“于今复三年矣”即陶诗“三年望当采”之所本;《转封东阿王谢表》之“园果万株,枝条始茂”及《艳歌》之“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即陶诗“枝条始欲茂”之所本;《转封东阿王谢表》之“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饥者易食,寒者易衣”“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即陶诗“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之所本;而陶诗“忽值山河改”之“值”与“植”字谐音,“这是子建自述在朝廷的指令下骤然变易封号与封国”[3]72;陶诗“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乃是子建《迁都赋序》‘余初封平原’的谐谑表达”[3]73,“平原者,非高原也,其位置本来不在高原,由此而注定了子建后半生的坎坷命运,其人生之长恨与深悲,竟从此生发开来。在这里,种植的‘植’与曹植的‘植’,自然界的平原与平原侯的平原,都是一语双关,明显具有隐语的特征”[3]73。关于陶渊明《拟古》其九,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然而,像范著这样举出如此众多的同一前代作者之诗文以释证渊明此诗,则绝为前所未有。或许,这种现象本身即已说明:渊明《拟古》其九确与曹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范著从互文的角度切入,确证渊明《拟古》其九与曹植之关系,为我们重新解读渊明此诗,乃至重新审视渊明诗学,均提供了重要维度。
范著对渊明其他八首《拟古》诗的阐发紧紧围绕曹植展开,胜解鳞萃,启人心目,体现出作者雄厚的学养、卓绝的识见,以及严谨矜慎的治学态度。如论《拟古》其三(仲春遘时雨),作者结合《水经注》卷二十三《濄水注》及“注”中提及的《大飨之碑》等文献,深细抉示了曹氏族人对故乡谯国寄予的深情,为陶诗“始雷发东隅”之“东隅”找到切实依据。而从作者所述“‘濄水’,就是今日亳州人所说的涡河,至今河面依然很宽,水质也非常清澈,常有渔民捕鱼。位于谯城东的曹操‘故宅’,也临近涡河,这是曹丕的出生地,也就是子建诗中所说的‘旧居’”[3]125-126来看,作者无疑对该地作了认真的实地考察,做到了文献与遗迹彼此印证、互相发明,从而加强了立论的可信度。再如论《拟古》其六(苍苍谷中树),作者从“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切入,认为“这首诗写曹植回顾当初即将就国于临淄的思想意识”[3]148,复据《文选》卷四十二《与杨德祖书》之“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3]150及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赠徐干》之评语“诸子在当时,皆以文人畜之,如齐稷下士,不治事而议论”[3]152,切定“结友到临淄”句是写子建在初徙封临淄侯时携郑袤、徐干、邯郸淳等“临淄侯文学”一同赴齐。理据充实,论证缜密。又如论《拟古》其七(日暮天无云),作者认为此诗“主要歌咏发生在建安时代的由南皮之游与西园雅集所彰显的邺下风流”[3]153,进而抉示了此诗与曹丕的两封《与吴质书》,以及曹植《杂诗》其四等作品间的互文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论述此诗的过程中融注了自己很多独到的考证见解,如谓“铜雀园位于铜雀台之后,在邺城的宫城之西,故名西园”[3]158,这个考证明确了“西园”的地理位置,对于我们正确解读相关诗作颇呈裨益。作者在本节乃至本书中多有类似的“小考”,俨有“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态,读者徜徉其间,必有意外之喜,此处恕不一一。
范著第三部分对渊明《止酒》诗的诗体形式、艺术渊源、题旨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论。首先,范著揭示《止酒》的诗学核心是“作品全篇的每一句诗都重复使用同一个字‘止’,即通过‘复辞’的修辞手法结构全篇,并由此使作品的风格形成浓郁的谐谑情调”[3]214。以此为切入点,作者例举了鲍照以下数首类似的诗作,而最终将这种诗体形式的滥觞追溯到汉代乐府诗《江南》古辞(江南可采莲),但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对渊明诗文中与乐府古辞具有互文关系者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从而确证《止酒》与《江南》之间的传承关系。其次,范著通过分类综述前人对《止酒》诗题旨的考察,深入揭示了《止酒》对《周易》《太玄》思想的表呈,从而指出“《止酒》诗表现的正是固穷守道的精神品格和弃繁从简的价值取向”[3]233,这就避免了仅以“游戏”“戏谑”的视角浮光掠影地解读渊明《止酒》,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渊明哲学思想的认识。再次,范著将后世模拟渊明《止酒》的作品分为“步其韵者”“步其韵,且每句用‘止’字者”“每句用‘止’字者”“仅以《止酒》为诗题,或化用陶渊明《止酒》诗意,或加以发挥者”“属于严格的典型意义上的‘《止酒》体’者”五种类型进行析论,深度阐释了渊明《止酒》对后世的影响。另外,作者还对与渊明“《止酒》体”相关的《观化决疑诗》、梁元帝《春日诗》进行了析论,多有胜解,如作者指出“在中国文学史的满目琳琅中,六朝‘《止酒》体’诗歌算不上珍品,现存的此类作品也不是很多,尽管如此,它们却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存在,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也很值得玩味”[3]254。这样就通过剖析一首体式独特的陶诗,而为研究者指出了“走入文学史深处”的蹊径。尤当指出的是,范著在此部分明确提出,“西方后结构主义学派的互文性理论,在阐释文学文本的生成机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学者在此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应用主要偏重于作品语言、内容方面的阐发,对作品的艺术形式的互文性极少关注。我们通过对《止酒》诗和‘《止酒》体’的讨论,实际上揭示了艺术形式的互文性在构建文学文本方面的重要作用,那就是文学创作如果实现艺术生长的扩大化,就必须建构合适的有效的艺术形式的互文性链条”[3]254-255。这样的论述既拓展了“互文性”理论的外延,也使全书充溢着理论的辉光,更为我们利用“互文性”理论研究其他文史命题指出“向上一路”。
范著另有附录三篇,其一《写在陶集的边上》当是作者阅读陶集的札记,其中精见甚多,对于陶集的校勘,以及深入探求渊明交游、陶诗陶文的语句渊源,皆有裨益,吉光片羽,可宝可珍。其二《陶渊明与张衡、束皙之关系发微》(《九江师院学报》2011年第1期)抉示陶渊明作品与张衡、束皙作品间的互文关系,通过文句比勘,指出束皙“《近游赋》很可能是《桃花源记并诗》的蓝本之一”[3]297。其三《惊鸿瞥过游龙去,虚恼陈王一事无》(《文艺研究》2012年第3期)征引多重证据,从多个角度证伪曹植“感甄故事”,还陈王以清白,正读者之视听。三篇附录各有特色,而又皆与本书题旨紧密相关,内义脉注,跗萼相衔。
除了考据的坚实密栗,义理的严谨清晰,范著在具体行文上则体现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特征。譬如作者感叹锺嵘《诗品》在构建中古诗人谱系方面所运用方法与“互文性”理论之暗合:“实在不可思议,一千多年前的伟大诗论家锺嵘那运用自如的极其成熟的‘历史批评法’或‘推源溯流法’,竟然与一千多年后西方文论家的互文性理论若合符契,形神毕肖,其周旋动静,万里如一,正所谓‘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尽管如此,在人类诗史以及诗学理论的演进历程中,锺记室的孤明先发与孤光独照,也的确令人啧啧称奇。而笔者有缘发此千古之覆案,也深感愉悦和幸福。”[3]60再如,作者评述关于“西园雅集”的诗歌:“在诗人的笔下,西园的天空通常蕴藏着寂静的清夜、温柔的和风、皎洁的明月与璀璨的华星,在西园的地面通常跃动丛生的花木、飘忽的月影、移动的轮毂、长歌的佳人、陪侍的文臣、高贵的主人以及逸乐的激情和流荡的诗思。”[3]162又如,作者评价汉代乐府诗《江南》古辞(江南可采莲):“这首带有浓郁江南风味的歌诗,本身就是一朵盛开的莲花,它在我国古典歌诗的浩淼碧波中从流飘荡,任意西东,时时呈现出柔美、轻灵、娟秀的风姿;它素雅而朴实,纯洁而高贵,清丽而自然,后世之儒雅君子、倜傥骚人,或仰其风华,或揖其清芬,而多有受其浸润者。”[3]216以上所举文句,无不爽健警拔、文质兼胜,既体现出作者独具的玄心、妙赏、洞见、深情,亦表呈出作者精深的辞章修养,超卓的文字功力。
总体来看,范著借鉴西方现代派“互文性”理论,深刻严谨地阐明锺嵘品陶、陶诗《拟古》、陶诗《止酒》的耐人寻味又殊难索解之处,实际揭示出陶渊明诗的生成机制,亦即通过套改、融摄、借鉴前代作家作品,实现前人与陶公在生平、思想、感情上,前作与陶诗在形式、内容、表意诸层面错综复杂的交融互动,从而铸就陶公独具特质的超越时空壁垒的意蕴丰富余韵深长之作。就此而言,范著实际将陶诗文本研究推向一个认知的新高度。
二、依据丰富文献,范著实际揭示出陶渊明与“元嘉三大家”之关系及《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部分内容的互文本
优秀的学术著作因其论证材料“采铜于山”“淘金于沙”,故往往具有学术的启发性,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意想不到”又在“情理之中”的文献线索,从而为解决相关学术难题提供有益思路。在范子烨先生所著《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一书中,很多被作者征引的文献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研究具有较大启发性,尽管作者的意图是从“互文性”角度切入研探陶诗以及渊明创作机制,但是书中援引的不少文献“秘响傍通,伏采潜发”[4]525,已经使许多与陶渊明其人其作相关问题之答案呼之欲出。此处试举三个例证。
第一,范著在论述鲍照(415-470)诗与陶渊明诗的互文关系时指出,鲍照《学刘公干体》五首其四“不愁世赏绝,但畏盛明移”之底文为陶诗《拟古》其六“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鲍照《拟古》八首其七“河畔草未黄,胡雁已矫翼”之底文为陶诗《述酒》“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3]175,而鲍照作于元嘉时期(424-453)的《学陶彭泽体·奉和王义兴》“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尊酒满,朋旧数相过。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琴当户坐,叹息望天河。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之“长忧”四句的底文为陶诗《游斜川》“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秋风”四句的底文为渊明《与子俨等疏》“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乖。缅求在昔,渺然如何”;“保此”二句的底文为渊明《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阻(迥)且长,风波阻中途”及《归去来(兮辞序)》“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3]176。据此,作者进一步指出,“(鲍照)此诗的出现,说明陶集在元嘉时期即已广泛流传。鲍明远此诗涉及陶公之《九日闲居》《移居》《拟古》《游斜川》《饮酒》《归去来》《与子俨等疏》等多篇诗文。”[3]176(3)鲍照此诗“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与陶诗《九日闲居》之“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但使尊酒满”与陶诗《杂诗》其四“樽中酒不燥”,“秋风七八月”与陶诗《拟挽歌辞》其二“严霜九月中”,等等,似亦关联。
范著以上论证,为我们研究陶诗的早期流传,以及陶渊明与“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之关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新思路。鲍明远得以接触陶诗,可能是由于颜延之的推介。《南史》卷三十四《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5]881由此可知鲍照与颜延之彼此相识。而颜延之与陶渊明情款交契(详见下文)。邓小军先生曾指出,“颜《诔》虽未对渊明的文学成就作出直接评价,实际是以一种特殊方式作出了评价”,该文列举了多个颜《诔》化用陶诗的语例,如“颜《诔》‘夷、皓之峻节’,‘夷、皓’用渊明《感士不遇赋并序》‘故夷皓有安归之叹’,‘峻节’用陶渊明《饮酒》其二‘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颜《诔》‘南岳之幽居者’,‘南岳’用渊明《述酒》‘南岳无馀云’,及《饮酒》其五‘悠然见南山’,‘幽居’用渊明《答庞参军》‘我实幽居士’,及《答庞参军并序》‘乐是幽居’”[6](4)邓先生在其另一篇论文《〈西青散记〉与贺双卿考》(《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收入作者所著《古诗考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版,第132-184页)的一则注释中提到,“古代述人诗妙用所述之人之诗文众多今典,是中国文学史之一重要文学现象。笔者曾经列举颜延之《陶徴士诔并序》妙用渊明诗文大量今典,计二十组例证,提出:‘只有对渊明诗文爱之至深,寝馈至深,才能妙用渊明诗文大量今典如此娴熟、贴切,如数家珍。此实际是延之对渊明文学成就之极高评价。’”(邓小军《古诗考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64页)另,关于此种文学现象,沙红兵《“文体对拟”:古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个特点》(《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的论述,颇有参考价值。等,充分说明与陶渊明有两度交往的颜延之,其对渊明诗文作品具有极为深刻之知解,这说明在陶渊明甫逝乃至生前,其诗文作品即已深刻影响到作为“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颜延之。尤为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两位先生几乎是用同样的方法,分别证明了颜延之、鲍照作品对陶潜作品的吸收、融摄,而这种比勘语句、发明作品间“互文性”的考证方法,则为我们考察陶诗乃至其他诗家作品的流传情况提供了一种极为有益的新途径(5)鲍照曾为临川王、江州刺史刘义庆佐吏,寓居浔阳,鲍照集中有《登庐山》《登庐山望石门》《从登香炉峰》《上浔阳还都道中》诸诗可证其与陶渊明故乡浔阳之因缘。另外,鲍照《拟古》其五“伊昔不治业,倦游观五都……管仲死已久,墓在西北隅,后面崔嵬者,桓公旧冢庐。君来诚既晚,不睹崇明初,玉椀徒见传,交友义惭疏”与陶诗《拟古》其八“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实相类似。王壬丘谓鲍照《拟古》其五“微似渊明”(鲍照著,钱仲联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页)并非无因。鲍照《凌烟楼铭并序》“即秀神皋,因基地势”与陶渊明《游斜川序》“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鲍照《与荀中书别》“抚己谣渡江”与陶渊明《岁暮和张常侍》“抚己有深怀”,乃至《南史》卷十三《鲍照传》中鲍照之语“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属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与陶渊明《饮酒》其十七“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皆有关联,当非暗合。。
第二,范著在附录一《写在陶集的边上》的最后一部分考证了陶潜与张野(349-418)的关系。作者引用了两则史料,一是《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陶潜》:“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二是《莲社高贤传》:“张野字莱民,居寻阳柴桑。与渊明有婚姻契。野学兼华梵,尤善属文。性孝友,田宅悉推与弟,一味之甘,与九族共。州举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征拜散骑常侍,俱不就。入庐山依远公,与刘、雷同尚净业。及远公卒,谢灵运为铭,野为序首,称门人。世服其义。义熙十四年与家人别,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3]290
范著引录的以上两则材料,为我们重新考察陶渊明与“元嘉三大家”之一的谢灵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谢灵运(385-433)比陶渊明小21岁,晚陶渊明6年卒,由上述两则材料可知,谢灵运与陶渊明的亲家张野当是认识的,那么可以说,张野的存在,使谢灵运极有可能在生前阅读到陶渊明的诗文(6)《陶渊明集》卷二有《岁暮和张常侍》诗一首,或以为诗题中的“张常侍”即张野,如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云:“张常侍盖即张野。义熙十四年十二月,刘裕幽安帝于东堂,而立恭帝。野卒于是年。诗题云《岁暮和张常侍》,是十二月野尚存。盖陶公和其诗之后乃卒耳。”(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但也有学者认为诗题中的“张常侍”并非张野,如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谓:“安帝之亡在义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次年正月朔日为壬辰,依此推算,安帝之亡在十二月十七日。消息传到寻阳,渊明得知最早在十二月二十日。张野卒于是年不知何月,然以常情推断,卒于十二月下旬渊明和其诗之后可能性甚小。所以如据诗意认定是义熙十四年刘裕弑安帝之后所作,则此张常侍是张野之可能性亦甚小。”(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7-118页)笔者认为,陶公《岁暮和张常侍》诗无疑包蕴易代之悲,诗中的“寒云没西山”可与渊明《饮酒》其二“夷叔在西山”参读,二句皆用《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而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史记》第七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583页)。实际就是表明刘裕篡晋后自己的政治态度。而由上引《莲社高贤传》之“(张野)义熙十四年与家人别,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可知张野去世并非正常死亡,而是一种绝决的抗争,他的“与家人别”并非一般意义的告别,而是死别,而“入室端坐而逝”则是从容赴死。职是之故,由刘裕篡晋与张野之死同在义熙十四年,并参与陶渊明饱含易代之悲的《岁暮和张常侍》诗,可以断言张野之死乃是痛惜晋亡,乃是表达对刘裕篡晋之愤恨。由此似可推断,张常侍写给陶渊明的诗,其内容一定包含易代以及易代之后的政治态度、人生取向等内容,由陶诗和陶公的作为来看,陶渊明和张野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无疑都是晋之遗民。。
范著指出陶谢可能相识的另一个“中介”是颜延之(384-456)。首先,颜谢是相识的。据《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传·庐陵孝献王义真》:“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7]1635-1636再,《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王弘之》:“始宁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阮万龄辞事就闲,纂成先业;浙河之外,栖迟山泽,如斯而已。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闻,虚想岩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颜延之欲为作诔,书与弘之子昙生曰:‘君家高世之节,有识归重,豫染豪(毫?)翰,所应载述。况仆托慕末风,窃以叙德为事,但恨短笔不足书美。’诔竟不就。”[7]2282-2283以上材料说明:第一,庐陵王义真与谢灵运、颜延之关系密切;第二,庐陵王义真与谢灵运、颜延之皆嘉尚隐士之风。尤其是,王弘之生前深受颜谢钦重,王氏死后,颜延之“欲为作诔”,这和陶渊明既殁,颜延之为之撰写诔文消息相通,颇堪玩味。又,据《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陶渊明》:“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7]2288可知陶渊明与颜延之情款交契。据缪钺先生《颜延之年谱》所考,颜延之任刘柳功曹在晋义熙十一年(415),本年颜延之32岁[8]464-465;颜延之出守始安郡在宋永初三年(422),本年颜延之39岁[8]467-469。由此可说,颜延之与陶渊明前后两度交往,绵延时间近8年。在颜延之身处中朝期间(418-422),由于与庐陵王义真、谢灵运关系密切,便极有可能将浔阳隐士陶渊明的作品介绍给希企隐逸之风的谢灵运,甚至庐陵王义真。
范著通过撮述日本学者石川忠久的论述,揭示了陶诗与谢诗的“互文性”关系。“现存谢灵运诗歌作品的年代,除了《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等数首外,都可以确定作于永初三年永嘉左迁之后,因此其诗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逝世的陶渊明的诗歌先后,大体上可认为是陶先谢后。谢灵运的‘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晚出西射堂》)可相较于陶渊明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谢诗早期作品的表现手法与陶诗尤其相似。而且,谢灵运在陶渊明的‘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基础上多扩展了两句,成为‘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宵愧云浮,栖川怍渊沈’(《登池上楼》),扩展的两句诗起到了确立主题的修饰作用,可视为谢在陶诗基础上的扩展添加作用。而且,谢灵运的代表作品《过始宁墅》,其全诗的表现手法、结构等,仍与陶渊明的代表作品《归园田居》其一相类似,但与其说是两者的诗具有相似性,不如说谢灵运对陶渊明诗进行了有意识的模仿。再者,谢灵运借用了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中‘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一句中的‘怀新’一词,将它融入到《登江中孤屿》诗中的‘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一句中。”[3]199
由陶渊明与颜延之、张野的关系,以及张野、颜延之与谢灵运之关系,加之陶谢诗客观存在的“互文性”,足可说明,谢灵运可能阅读过陶渊明的诗文,谢诗的创作受到陶诗的影响。
综合上述一、二两例可说,陶渊明(365-427)对“元嘉三大家”颜延之(384-465)、谢灵运(385-433)、鲍照(415-470)具有重要影响。从“互文性”的角度看,“元嘉三大家”的部分诗文(其中不乏名作)无疑受到陶渊明作品的深刻影响。这为我们重新且深刻认识陶渊明在晋宋诗坛的地位开辟了新的视野,意义重大。
第三,范著在论述唐人对应璩及其诗文的接受时举出《唐代墓志汇编》麟德069《大唐故张府君墓志铭并序》中的“君讳宽,字士裕……追仲理之良田,叶应璩之菀柳”[3]27。由范著所举唐人墓志铭中的“追仲理之良田”,足可窥见仲长统《乐志论》“使居有良田”一段于后世影响之一斑。而仲长统这段文字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尤其是《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深有影响。试读《后汉书·仲长统传》引统《乐志论》: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帀,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生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9]506
以上这段文字中,“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帀,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与《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10]329,“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与《桃花源记》“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10]329,“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与《归去来兮辞》“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10]318(7)笔者认为,渊明《归去来兮辞》此四句或当连读,句法形式乃如钱钟书《管锥编》所论之“丫叉句法”(钱钟书:《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4-115页),亦即“ABBA”式,“或命巾车”对应“亦崎岖而经丘”,“或棹孤舟”对应“既窈窕以寻壑”。而“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实际就是《桃花源记》中渔人“舍船”入桃花源之境界。,“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与《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10]318,“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与《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10]318,皆有语词乃至语意上的类似、相关性,其内在关系恐怕是不言而喻的。而仲长统文中所描述的逍遥、徜徉之境界,与陶渊明归耕后的精神状态、生活状态,又是多么相似,乃至相同!由此可说,仲长统文无疑对陶渊明及其作品尤其是《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的创作具有深刻影响。
以上所举三例,或非范著全书论述之重点,然而,由于作者取材弥广、运思弥周,故使该书具有“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之特质,珠藏川媚,玉蕴山辉,其给予人的启发性是巨大的。
三、结语
综上可说,第一,范著对陶诗陶文与其他作家作品“互文”关系的揭示,皆有赖于作者本人对相关文献的熟稔,通过零散的字词、片段的语句,以及类似的形式、风格去挖掘作品间的关系,倘非对所研究的内容极为精熟,是绝难从事并取得成功的。第二,范著从“互文性”角度对陶诗《拟古》九首与《止酒》诗创作机制的坚确考证、深入析论,为人们进一步深微探抉中古文学作品力辟蚕丛、导率先路。这是因为,“无论就诗赋书表等文章,或子史政论等成一家言的作品说,就现在考证所得,魏晋间人诚有许多依托或伪作的情形,但其动机实在至要还是为了拟古和补亡,并不是故意作伪欺世的”[11]170,这种拟古和“作伪”的时代风气,恐怕不能不对彼时作家的其他非“拟古”、非“作伪”的诗文产生影响。质言之,“互文性”写作可能普遍存在于中古作家作品之中,而这或许是我们深入认知中古文学作品的有效途径。第三,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陶渊明的研究已经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然而,如何利用既有研究基础,以彻底解决与陶渊明生平及诗作紧密相关的命题(如“锺嵘品陶”等),如何进一步开拓陶学研究的纵深以嘉惠今人后学(如探索、揭示陶诗的“创作机制”等),就成为陶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范子烨先生的《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无疑在以上两个方面均作出重要贡献,切实有力地推进了陶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