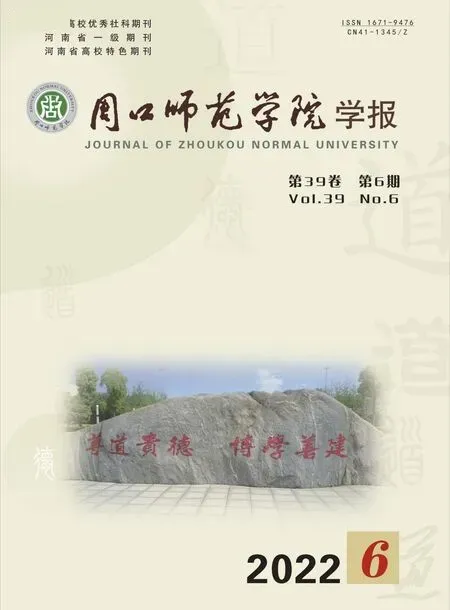将道德自觉带入乡村文化变迁的中心
——评申端锋著《道德自觉:乡村文化的变迁与重构》
2022-03-14杨殿闯
杨殿闯
(江苏海洋大学 乡村振兴研究中心,江苏 连云港 222005)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乡风文明与文化振兴成为焦点议题,引起了学界和政策部门的广泛关注。在乡村文化建设研究领域,已有研究多采用政策分析法和制度分析法,相对缺乏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经验研究,尤其缺乏对乡村生活变迁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证研究,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乡村文化建设方案。在上述政策背景和研究脉络中,申端锋的新著《道德自觉:乡村文化的变迁与重构》(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让人眼前一亮。该著采用道德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对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变迁进行整体考察,聚焦乡村文化中的道德自觉,抓住了乡村文化变迁的核心问题,并提供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方案。该著将道德带入乡村文化研究的中心,为学界研究乡村文化提供了一个新框架,也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道德自觉:乡村文化的变迁与重构》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该研究对乡村文化变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并运用扎根理论和案例研究法的资料分析技术,对访谈资料进行了较为规范的编码。作者长期从事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研究,具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在调查中不带任何理论预设,先进行整体调查,再进行专题研究,保证所搜集的资料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避免强制数据,真正做到从资料和数据中提炼概念并建构理论。该著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田野发现和理论建构值得关注。
第一,城市化与乡村文化变迁。城市化深刻地影响着乡村文化的变迁,其影响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劳动力商品化,二是日常消费商品化。前者是以生产为中心的考察,后者是以消费为中心的考察,通过这个框架,作者成功地将城市化对乡村文化的影响操作化了。劳动力商品化是乡村道德变迁的主要动力,正是普遍的外出务工,引起了农民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向农村地区的渗透,消费主义下乡,乡村社会也成为消费社会,消费成为农民生活的中心。消费主义导致农民过于关注家庭生活,公共生活趋于衰落,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提出了挑战。
第二,家庭义务与家本位文化的再生产。家庭义务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均围绕着家庭再生产展开。外出务工是农村经济的主要影响变量,作者以务工经济为中心,通过呈现不同年龄群体在外出务工上的表现,分析了代际传承与家本位文化的再生产。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劳动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他们无法在城市里完成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和家庭再生产,经历了青春期的探索之后,农民工最终回归乡土价值,在家庭义务中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中年农民是家庭再生产的责任主体,他们具有高度的义务自觉。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出卖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获取货币收入,将自己的情感编织成为家庭义务。同时,在消费主义和高成本生活的压力之下,代际之间的义务配置出现了新变化,老年人开始对家庭承担更多的义务,出现了老人自立养老的现象。老人自立是一种新型的代际关系,对家庭再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本位文化通过家庭再生产得以延续,家本位文化背后是家庭义务。家庭义务是无条件的,充分体现了农民的义务自觉。家本位文化是义务文化,而非权利文化,亦非个体主义文化。
第三,共同体义务与弱整合的村落共同体。在家庭之上,存在着一个共同体,农民就生活在村落共同体之中。该著以人情与纠纷为中心,呈现了村落共同体的建构机制。村落共同体是义务共同体,通过人情义务得以建构。人情意味着共同体内部家庭之间的义务担当,同时,人情又是建构性的,属于私人义务,而非公共义务。共同体义务是有条件的,虽然农民对其所在的村落有一定的义务自觉,但这种义务自觉随时可以中断,这就导致村落共同体的弱整合特征,具有脆弱性和动态平衡性。农村集体经济解体之后,共同体生活得以复兴,在共同体生活中,农民运用人情编织着关系共同体,共同体能够为农民的日常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完成一些靠单个家庭无法完成的事务,如红白喜事。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村落共同体也受到了冲击,表现为共同体内部的合作收缩,生产领域的合作难以为继,共同体舆论无法发挥作用,退出纠纷调解,目前的村落共同体只是保持着脆弱的整合。在弱整合的村落共同体中,每个农户都积极建构人情关系,而每个人又都能轻易地中断和他人的人情关系,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关系网中,家庭之间出现了相当强的竞争,导致和谐与紧张并存,乡村社会成为一个靠私人道德维系的弱整合共同体。
第四,集体义务与公共生活。在家庭和村落共同体之上,还有一个集体,也就是所谓的公共生活。传统社会,官不下县,农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家庭和村落共同体之中。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农民要更多的与国家打交道,国家成功地在农村建构了公共生活,这个公共生活以村落共同体为基础,但又不同于村落共同体生活。公共生活表现为集体经济、村民自治与社会治理三个方面,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管制权的弱化以及村民参与的不足,公共生活呈现衰败之势。集体经济解体之后,集体义务受到行政权力和私人关系的侵蚀,越来越无法维系,村民更加依赖私人关系,或者高高在上的国家,其结果是村落社会的公共性匮乏,导致公共治理出现了私人化和行政化的双重趋势,公共生活衰落。基层组织想重建集体义务,但很多时候建立的是强制性义务,即采用强制权让农民履行集体义务,虽然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合法性不足。公共生活背后是集体义务,集体义务不是强制性义务,体现为农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是在认同基础上的集体共识和一致行动。重建农村公共生活,就必须要重建集体义务,这是当前农村公共文化建设面临的难题。
第五,义务自觉与文化建设。作者在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提出了义务自觉的核心概念。中国乡村文化是义务本位的文化,义务分为家庭义务、共同体义务和集体义务。家庭义务是强义务,共同体义务是弱义务,集体义务更弱;家庭义务是无条件的义务,而共同体义务和集体义务都是有条件的义务;家庭义务是情感主导,共同体义务和集体义务则是利益主导。家庭义务根据情感来配置,共同体义务和集体义务则根据契约来配置,当前公共生活和公共文化建设的困境,就是共同体义务和集体义务的契约性受到了冲击,导致村落共同体解体和公共生活的衰落。家本位文化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就在于家庭义务的强大,这就是义务自觉,村落共同体生活之所以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系,就在于共同体的义务自觉也在发挥作用,但共同体的义务自觉比较弱,这也导致了村落共同体的弱整合。公共生活衰落,乃是因为集体义务的自觉几乎没有,村民对集体的义务也就是所谓的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消失殆尽,其结果就是集体义务解体,乡村文化的公共性缺失。所以,乡村文化建设就是要建设农民的义务自觉,具体而言就是保持家庭义务自觉,强化共同体义务自觉,重建集体义务自觉,从而重建乡村文化的公共性和主体性,这正是乡村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总之,该著将乡村道德作为乡村文化的核心,采用道德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和资料分析,对乡村社会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变迁进行了全面考察,呈现了家庭义务、共同体义务与集体义务的非均衡变迁,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以道德自觉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建设整体方案。作者的这一学术努力,丰富了学界对乡村文化变迁的理解,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经验和理论基础,也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政策议题。期待作者今后能够进一步深化对道德自觉实现机制的研究,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集成化的道德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