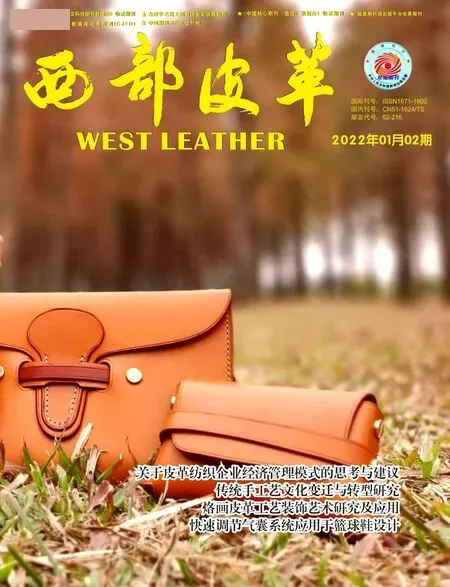刺绣艺术发展中“他文化”嬗变
——以徐州刺绣为例
2022-03-14王欣雨王慧灵
王欣雨,王慧灵
(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前言
刺绣,俗称“绣花”,因多为妇女所作,故被认为是女性的艺术,即所谓“女红”。在以“男耕女织”为社会分工的小农经济时代,出现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因为男女天然的体力差别,因而妇女成为了编织、缝纫、刺绣等家庭手工业中的核心角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刺绣成为了女性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践行着“男女有别,男外女内”的性别文化观念[1],因此,一提起刺绣人们往往会想到婉约柔美的女性,但这实际上是一种性别刻板印象。为了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越来越多的男性毅然踏足刺绣行业,为传统刺绣艺术在当今时代的传承和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徐州,就有这样一位“绣郎”,打破了人们对于“刺绣”这一行业的性别刻板印象,他就是“一席地”刺绣品牌的创始人、徐州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席建勋。席建勋先生祖籍河北,因为喜欢美术所以不远千里南下深圳大芬油画村求学,因缘际会下爱上了刺绣,自此便深深扎根于刺绣行业。后来为爱人落户徐州,被徐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深深吸引,便下定决心用一针一线来织就徐州两汉文化与刺绣文化的传承梦。
笔者通过采访席建勋先生,得知许多人对于其“绣郎”身份非常诧异,甚至不自觉地将他往女性化特征方面联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破除刺绣性别刻板印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大众对于男性刺绣的认识基本是空白的。但实际上,从古至今,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男性绣工一直存在。
1 古与今:令人惊艳的男性绣工
据《女红传征略》中的记载,明万历丙辰年间的进士来复,天资聪颖,善诗文通书画,琴棋剑器百工技艺样样精通,惟未习女红,至吴门学之旬日,吴中女红具叹赏焉;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书画家万寿祺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天文地理、诗文书画、女红刺绣、革工缝纫等百工技艺,无不通晓;清乾隆年间徽州的徐履安精通刺绣,曾经绣过十八罗汉图,形神具备,被人们誉为“神针”。
此外,“流传于宋元明清的宫廷之中的京绣一直都是由男绣工从事,称之‘宫廷男工活’。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绣娘的出现。”[2]
徐蔚南在《顾绣考》中写道:“迨至清乾隆间,顾绣半多男工为之,不仅女也。”也就是说,在家庭手工业之外,刺绣产业化之后也有男工从事。清道光年间,蜀绣逐渐进入市场,并开始进行专业化生产,这一时期蜀绣出现了大量的男性绣工,“据说有一位从苏州调任四川的官员,随带戏班中,便有3 个绣衣师傅,均为男子,皆顾绣技法。后招徒授技,顾绣之法遂融于蜀绣。后来,蜀绣老艺人几乎都是男子,其因就是当时招徒囿于世俗之礼而不能招闺中女。”[3]因此,蜀绣的名家有不少男性,例如以山水花鸟见长的张万清,善绣人物的叶兰廷、叶春元父子,以精细著称的叶绍清,蜀绣名作《芙蓉鲤鱼》的作者彭永兴等。
无独有偶,在少数民族的刺绣艺术领域,男性绣工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畲族刺绣是畲族女子完成纺线、织布后,畲族男性技师继而量体裁衣、绣花镶边。畲族谚语中所谓的‘男绣女不绣’,即指畲族‘做衫师傅’均精通女性上衣、裙子的装饰性的绣花工艺,整个绣花过程均由男性师傅完成。”[4]此外,“云南石林彝族的小答村有8 名男子会刺绣或以之为业,而且他们的手艺并不亚于女性。”[5]
到了今天,“姑苏绣郎”张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其母亲——苏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薛金娣的影响下,从各个角度对苏绣融入生活的方式进行了探索,并尝试以苏绣为窗口,促进传统文化与年轻人的“双向奔赴”。在他看来,“对于苏绣作品的创作,男性角度确实有别于女性视角,两性对苏绣的思考各有特点,创作各有所长。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都能为作品赋予别样的感觉。”
可以看出,这些古往今来、不同民族的男性绣工们,绣艺精湛、成就斐然,在刺绣这一领域并不逊色于女性,他们往往还能够以令世人惊艳的姿态展现出男性在刺绣方面的独特魅力。
2 破与立:性别与角色重塑
如果把中国女性千百年来创造的刺绣工艺史比作一本书,那么活跃在这本书里的那些男性绣工们就是其中璀璨的篇章,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向世人宣告:刺绣无分男女,只要热爱,都可以从事刺绣。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男性思想观念的解放,现代社会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尝试在刺绣领域施展拳脚,但普罗大众还是习惯性地将刺绣视作女性的艺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板印象”。
2.1 “刻板印象”的破除
所谓“刻板印象”,最初专指印刷铅版。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1922 年的著作《舆论》中,首次将“刻板印象”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引入到传播学领域。在他看来,“刻板印象”指的是社会生活中固定成见的现象,这种“固定的成见”就像浇铸的铅版一样牢固,并且难以改变。正如他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一旦我们牢固地产生了这种成见,就很难摆脱它。”我国著名的传播学者郭庆光基于此提出:“‘刻板印象’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
这种“刻板印象”在刺绣领域的表现就是人们对刺绣群体或行为的特征、属性等产生了固定化的认知,这种认知在社会互动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反应,久而久之,人们便将“刺绣”与“女性”之间划上了等号。这种性别刻板印象的存在无疑给男性绣工们制造了庞大的社会压力和心理障碍,但总有一些人,敢于跨越性别制度,身随心动,在大众异样的目光下和种种质疑声中破浪前行。
徐州“绣郎”席建勋便是乘风破浪的其中一员,漫漫刺绣路,绣里寻乾坤,席建勋先生用他二十年如一日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择一事而终一生”。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一席地”刺绣品牌现如今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其所推广的徐州刺绣也得到了社会以及大众的认可和支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开始关注到席建勋先生的“绣郎”身份,纷纷从这一角度切入进行报道宣传,一定程度上破除和消解了人们对于刺绣群体及行为的刻板印象和固定成见,让刺绣不再简单地被定义。
2.2 “再做性别”与观念重塑
在社会学和性别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性别研究范式,即“再做性别”,“它是指在互动过程中改变或扩展与性别相关的各种规范,重新定义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相关联的属性,改变人们施加在男性与女性身上的各种角色期待,从而挑战本质化的性别特质及其权力结构。”[6]通过“再做性别”,可以扭转人们自发给“刺绣”和“女性”这两者建立关系的认知和行为,重塑刺绣与性别之间的内生逻辑和认知观念。
刺绣因其特殊的属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女性,它本身的细腻、柔美与创作时所要求的专注、耐心、细致等确实与女性的诸多特性一一对应,再加上男女天生的体力差别,类似刺绣这种轻松的手工活儿就被看做是女性的专属。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人们施加在男性和女性身上的角色期待,也就是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如果不考虑这种约定俗成的认知观念,而是以更加平等、客观的视角来看待刺绣以及刺绣者,或许男性从事刺绣行业也未尝不可。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刺绣早已不再是为维持生计的技艺生产,也不再是用来规训和教育妇女的工具和方式,刺绣已然走向了高端的艺术行列,对于男性而言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特别是徐州地区的刺绣文化,兼具南方的秀丽和北方的粗犷,素有“南秀北雄”的美誉,既还原了男性身上的阳刚与粗犷,同时还激发出男性心底潜藏的细腻与柔情,正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徐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蕴养出这独一无二的刺绣文化,为男性绣工们创造出更多、更自由的发挥空间。
在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大环境下,通过“再做性别”来重塑人们对于刺绣及其群体的认知和观念,便有望吸引更多对刺绣心怀热忱的男性加入到刺绣这个行业之中,并且他们往往能迸发出与女性不一样的创作灵感与刺绣技法,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待被女性所“统治”的刺绣艺术,也许能为现如今刺绣文化及艺术的复兴和传承提供新的思路。
3 刚与柔:“他”的刺绣艺术观
刺绣作为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汉·王粲在《为刘荆州与袁尚书》一文中写道:“当唯义是务,唯国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刚柔相济,然后克得其和,能为民用”;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中写道:“凡为将者,当以刚柔并济,不可徒恃其勇”;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曾国藩悟出天地之道,同样认为“刚柔互用,不可偏废”;中国道家哲学也一直遵循着“刚柔并济、阴阳相生”的辩证原则……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骨子里追求“刚柔并济”的性格底色,无论是书法、戏曲、诗词抑或是治国之道,都蕴含了“刚柔并济”的思想精髓,刺绣也不例外。
针为“刚”,线为“柔”,穿针引线这一个回合便是刚柔相济、阴阳相生的过程,如果是技艺娴熟的刺绣师傅,还能够做到收放自如,针随心动,线随人走,在一吐一纳间完成针与线的律动。如果说,针与线算是“刚”与“柔”的一种缩影,那么席建勋先生针下的徐州刺绣则将“刚”与“柔”体现地更为淋漓尽致。
3.1 徐州刺绣之“刚”
在席建勋先生看来,徐州刺绣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徐州的两汉文化和红色文化,这也是徐州刺绣与其他地方名绣最显著的区别。独领风骚的两汉文化以及昂扬向上的红色文化直接为婉约柔美的刺绣注入了深沉、厚重的文脉基因和发展动力,此为徐州刺绣“刚”的一面。
3.1.1 两汉文化书写楚汉雄风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徐州,古称彭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的徐州金戈铁马、英雄辈出,尤以帝王闻名于世。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事”,正是这些千古风流人物,造就了徐州“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九朝帝王徐州籍”等美誉。回望历史,徐州可以算是当之无愧的两汉文化发源地,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丰富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例如汉太祖刘邦及其能臣虎将萧何、曹参、樊哙等一干英豪在反秦、建汉过程中的政治理念、诗文著述、历史功绩等汉文化典故;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汉代三绝”、古城遗址以及在徐州出土的汉代玉器、青铜器、陶器等汉文化遗存,都完美体现了“粗犷、雄浑、博大、超越”两汉文化精神。
千年的艺术积淀为徐州这座城市注入了不朽的灵魂,同时也为艺术创作者们提供了绝佳的素材来源和艺术灵感。图1 为席建勋先生所绣制的两汉文化创意绣品。

图1 《大风歌》
该作品便是取材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所创作的诗歌《大风歌》,以书法和水墨为载体,盈盈几针便刻画出刘邦道不尽的豪情万丈,针线流转间又透出几分他忧心国事的惆怅。透过这层绢布,我们似乎看到了千年前那个立下不世功勋的人物顶天立地、指点江山的英姿。
3.1.2 红色文化彰显英雄本色
徐州自烽火狼烟中走来,带着满身的荣耀和光辉。千年来,不屈不挠、英勇抗争似乎成为了徐州人民的性格底色。直到今天,徐州依然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这片热土上有着浓浓的红色印记,在默默纪念着那段艰苦斗争、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抗日战争时期,徐州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了湖西、鲁南、沭宿海、萧铜等抗日根据地,组建了运河支队、人民抗日义勇队、邳县青年救国团抗日义勇队,并打响了抗战时期一次大规模的防御战役——徐州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大大迟滞了日军进攻的步伐;解放战争时期,徐州作为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在与80 万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的过程中孕育出“淮海战役精神”这种具有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的伟大革命精神。
除了广为人知的淮海战役,徐州还是“一门三烈”(烈士宋绮云、徐林侠夫妻及其幼子宋振中)的家乡,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的诞生地。可以说,徐州的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绵延不绝。
如何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这是徐州的文艺工作者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对于席建勋先生而言,他一直致力于挖掘优秀的红色资源并将其融入到传统刺绣的创作之中,在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的融合碰撞中寻找文化传承的真谛。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百周年,为献礼建党百年、传承红色文化,席建勋先生历时4 个月创作出《红船》(见图2)这幅作品。

图2 《红船》
顾名思义,《红船》即以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的红船为创作元素,以针为笔,以线着墨,以丝帛做纸,描绘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源头——“红船精神”。在问及创作理念时,席建勋先生谈到:“100 年前,中国共产党从南湖上的一叶小舟起航,披荆斩棘,建国立国,富国强国。想想历程,我心潮澎湃,于是决定用自己的刺绣手艺为祖国献礼,为弘扬红船精神,故决定绣制主题为《红船》的作品。”
3.2 徐州刺绣之“柔”
刺绣之“柔”,一为题材的灵秀与柔美,二为针法的精细与雅致,三为丝线的光泽与鲜艳,四为刺绣者的细腻巧思与平和心绪。若四者能得其一,则可谓柔矣。
徐州山水形胜,大运河进入江苏后蜿蜒绵亘,绕城而过,古黄河穿城南北,与云龙山遥相呼应,再现了“一城青山半城湖”的盛景。席建勋先生便以徐州山水为元素,用刺绣来展现徐州“运河彭城”“水韵江苏”的灵秀,此为题材之“柔”。
若论针法和丝线之“柔”,席建勋先生绣制的那幅被徐州博物馆收藏的《龙形玉佩》(见图3)实乃典范,整幅作品针脚细密,丝丝入扣,甚至还泛着光泽,将玉的温润和精美表现地淋漓尽致,就连龙身局部由于埋藏两千余年所呈现的沁斑都被席建勋先生以针线细细勾勒出来,几乎是一比一复刻了龙形玉佩。

图3 《龙形玉佩》
如此精细的刺绣能够成形同样也离不开创作者的细腻与专注,一旦拿起针线,就意味着一天的时间都要尽数交付给这一块小小的绢布,一针一线一世界,一人一绣一乾坤。每一件作品往往需要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因此刺绣实际上也是修身养性的过程,“绣”也是“修”。所以在席建勋先生的刺绣艺术馆中,处处可见雅致,可以欣赏古玩字画,可以围炉煮茶,甚至还有打坐的净室,这些都是席建勋先生为了陶冶心性、静心刺绣所做的努力。
再加上席建勋先生天生细腻,性情柔和,所以在刺绣时更能沉浸其中,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巧妙融入到作品中,一枝一叶总关情,一针一线见初心。
3.3 徐州刺绣之“刚柔并济”
其实在一幅刺绣作品之中,“刚”与“柔”是相伴相生的。纵观席建勋先生所有的刺绣作品,无一不是刚柔并济、粗中有细,完美契合了徐州“南秀北雄”的城市风格。而这些作品中最为典型的当属《锦绣彭城》系列作品。
《锦绣彭城》系列作品即《锦绣彭城之山水云龙》(图4)、《锦绣彭城之秋风戏马》(图5)以及《锦绣彭城之驭风汉行》(图6)。这三幅作品有一个共性,就是“‘彭’松针”的运用。“彭”音同“蓬”,是为蓬松之意,因徐州又名彭城,故席建勋先生将此针法命名为“‘彭’松针”。常见的刺绣作品绣面光滑、平整,而以“‘彭’松针”绣出来的绣品则能明显看出起伏,因为绣线离绢布1.5~3 毫米不等,故能营造出高低错落的层次感和蓬松的视觉感。

图4 《锦绣彭城之山水云龙》

图5 《锦绣彭城之秋风戏马》

图6 《锦绣彭城之驭风汉行》
在这三幅作品中,上方的银杏叶极尽精细之能,针脚细密有致,绣面光滑平整,看起来栩栩如生,几乎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而其他部分则运用了“‘彭’松针”,以极其强烈的视觉感抓人眼球,让人耳目一新。整幅作品用针灵活大胆,在精细与粗犷的转换中,将徐州的山水美景、运河文化以及两汉文化等娓娓道来。秀丽兼具雄伟,实乃刚柔并济的典范,在大开大合之中还能隐约窥见创作者的细腻巧思,达到了人与刺绣合一的境界。
纵观席建勋先生的刺绣艺术观,既吸取了传统刺绣的精华,又有创新之处,无论是题材、针法、创意还是情感,与女性刺绣所关注的角度确有不同,但二者同样精彩。可以说,席建勋先生在这条并不容易的道路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脚印,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传统刺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结语
中国传统社会将刺绣作为规训、教育妇女的工具和理想方式,于是刺绣逐渐演变为伦理道德的表意符号,成为了禁锢妇女的精神枷锁,也造成了世人认为刺绣乃女性专职的局面。但是刺绣无分男女,两性对于刺绣的思考和见解也各不相同,男性甚至能迸发出更具创意、更为大胆的刺绣灵感与技法。倘若能够放下世俗的成见,以更加宽容的态度来看待“绣郎”的出现,相信会有更多对刺绣心怀热忱的男性加入其中。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男女两性共同探索刺绣这片广袤的天地,为传统刺绣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开辟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