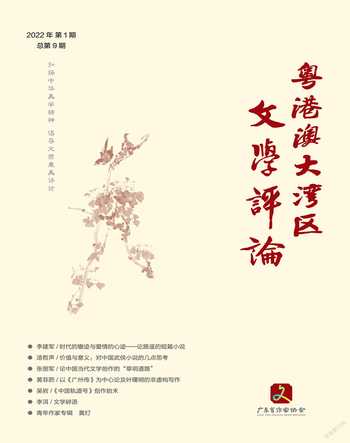重审文学的使命及其伦理
2022-03-14谢尚发
摘要:当下的写作呈现为一种“讨巧式”的趋势,但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一书则反其道而行之,聚焦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以此来探讨阶层固化、内卷等社会现象,以文学肩负起探究时代命题、吁请时代问题的解决等重任,这也是文学本该有的题中之意。
關键词:黄灯;《我的二本学生》;文学伦理;阶层固化
《周易》贲卦《彖传》中有论述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这一观念从未断绝,以至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被极致地夸大:“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后人刘勰更是在《文心雕龙》开首就强调:“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3]得益于文化教育的普及,这些论述已成为极显白的常识,甚至人们生活中有意无意地附庸风雅,将其设为座右铭或书之于堂室。但越是如此,越有被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的风险。只要稍微侧目于当下文坛的写作,面对着极度繁盛的文学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却几乎无法寻得能担负起如此文学重任的作品,我们就能知道,这样的风险正一步步成为现实。重提文学的使命及写作的伦理,即便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它旁落以至无人顾及时大约也仍有新意。
“文德”实乃“人德”。然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行为,“文学之德”已经超离了个体的“个人仁德”,具有了自属的品格与德性。可是很显然,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作家们愈发懂得如何取巧于时代、应和于社会,作品的数量丝毫不耽误的情况下,写得很欢实,成绩也斐然,却给人一种疲软无力、自我陶醉的印象。几乎与此同时,有感于这种状况的存在,责任感较强的作家起而以“非虚构写作”之名,重拾文学交付于他们的巨大使命,再次强调“文学之德”并试图扛起“化成天下、经国大业”的“文之为德”的旗帜。任重道远,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优质作品数量有限,高质量的作品则又有限中再复有限,乃至于“非虚构写作”本身逐渐被泛化,变成了模糊不清的概念。这并不妨碍有识之士以此为披肝沥胆之心,去触碰时代、社会和现实的诸种讳疾,泼洒“文德”,继承古圣先贤的文学理念。将之称为“文学的良心”有夸大之嫌,然其所提出的问题着实令人深思,不可回避,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虽小,但引起疗救之注意则大。以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为话题,这样的讨论也许会有所依傍,不至于空言无当。
一、“讨巧时代”的文学写作
对当代文坛少有了解的人都清楚,至少有几个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发清晰:其一,文学创作越来越丰饶,量的积累越来越大,每年动辄3000多部的长篇小说生产,几于流水线上的商品相当,然质量越来越堪忧,不但遍寻不到名著级别的作品,甚至连经典作品都不见了踪影;其二,作家不是不聪明,而是太过于聪明,知道时代需要什么于是便提供什么,知道暗礁险滩在何处于是十分巧妙地就躲过去了,自然也对深水区谙熟于心而不去触碰;其三,文学作品的故事与形式臻于顶峰,讲故事的技术愈发成熟,形式探索也几乎到达极致,但思想匮乏,深度与厚度都交给了轻巧的故事,思想冒险、灵魂追索等成为明日黄花;其四,文学现场越发热闹,而文学本身越发寂寞,各种研讨会、新书发布会、分享会、文学专题会议、期刊杂志的集体亮相、新人推介会等热闹非凡,文学场成了走秀场,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亮相而无法顾及速朽的命运。对文学而言,避免速朽的方式不再是文学杰作的书写,而是变成了争夺聚光灯的战争。将这种现象命名为“讨巧时代的文学”应该是恰当的,且在这样一个“讨巧时代”,文学的生产也逐渐呈现出一些独有特质,形成了三大类型的讨巧写作,带来讨巧写作的三种特征,其产生的原因也不难找出。
三种主要类型的“讨巧写作”,首先是对时代热点的追踪式写作。在论述“无边的现实主义”时,罗杰·加洛蒂从毕加索的绘画、圣琼·佩斯的诗歌和卡夫卡的小说三个侧面入手,认为现实主义可以在艺术所允许的范围内,“无限制地扩大”,因而“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4]成了他所追寻的道路。这个当年引起巨大争论的观念,放在当代文坛变得极其合适——许多作家把现代主义乃至于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借用过来,但内里依旧是现实主义的方法,故事的讲述、情节的构造、人物的塑造、主题与思想的传达,都是当下的、社会的、现实的、时代的。在这个类型之内,新乡土、老龄化、离婚率、贪腐大案……成为他们笔下最常见的“现实主义”,当年被加洛蒂一再扩展的现实主义,也一转在如今作家手里变成了无所不能,又安全可靠的方法。第二种类型,是对“安全的现实主义”的转化与细化,即迷醉于私人化的小叙事。把一己经历中的爱恨情仇、吃喝拉撒、痛不欲生等作为小说唯一的取材,并且试图从中挖掘出高深的命题,又往往跌落在私人化叙事的深渊之中不能自拔。这种类型的作品在“80后”和“90后”的创作中尤为明显:现代都市的灯红酒绿催化出性爱的纠缠,器物的细致性描摹与展示成为纸醉金迷的资本钥匙,声色犬马如果还算另类,那么他们就选择时代大潮中的自我跌落与悲惨……个人的悲喜尽管往往能映照出社会的巨大变迁,但这一类作家几乎沉迷于私人化的那些小情绪、小感伤、小确幸、小悲喜之中,自命不凡地铺排故事而无所寄托,根本不去触碰时代问题,成为速朽的热闹烟火[5]。为了避免这种“安全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往往会选择第三种类型,即“历史的沉重型叙事”。他们往往躲进历史的故事中,试图以时间的灰尘所累积的厚度来达到提升作品思想深度的目的。但他们的聪明并未保证这种思想的自然流露,反而迷醉于稀奇古怪的传奇故事,把历史上真实与虚构的故事尽力渲染,若非能够形成一些有噱头的闹剧,这些小说几乎都成为市场的产品,影视改编等的转化能带来丰厚利润,却唯独淹没了它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所谓历史书写也就变成了走过场。
三类主要的“讨巧写作”自然地携带着平庸化、类型化和争夺曝光率的特征。平庸化的表现凸显为投其所好、偏重于提供轻松的阅读物、写作者丧失独立的思想和立场、煽情化与鸡汤化倾向明显……取悦于市场和读者,争相提供一个易于改编为影视的故事,甚至并不能对文学写作有一种自反性,令人颇感担忧。与此相关联,类型化也更加明显,尤其是迷醉于现实的创作——个人化的私密叙事从未脱离爱情、婚姻与家庭,紧跟时政的写作逐渐靠向黑幕小说、官场小说,都市言情稀松平常,再加上一些奋斗者的失败、成功者的艰辛、平凡人的温馨、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文学影视化与俗世化,尽管并不是缺陷,但千军万马奔赴此一领域,带来的是虚假繁荣与产能过剩。这就不得不导致曝光率的争夺。为了维持市场和阅读的热度,保证聚光灯下的主导地位,在无法用一部作品来长时间占据中心的情况下,作家们纷纷发扬“勤劳致富”的精神,以数量冲击曝光率,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心浮气躁难以沉淀经典作品,于是以粗制滥造获得认可,滥竽充数的结果是进一步导致焦虑忧愁,刺激并加重写作的速度而忽略质量。
写作的职业化、竞争的多样化与阅读的通俗化,是三个较为重要的侧面。作为谋生手段,文学实难以承受一个人的飞黄腾达,但长期以来文学的职业化造成了作家需要依靠作品来生存,并试图以此来致富,写作就慢慢变成一种工具,长期承担着作家名誉与利益的创收。更兼此后各地作協出台相关政策,作品发表的数量与刊物级别直接与金钱挂钩,愈发刺激作家们发扬“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再有就是,近年来,因为教育的普及,凡有写作梦想的人都想在文学的大蛋糕上分一杯羹,写作的竞争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尤其是专业研究者的加入,更是搅乱了文学市场的竞争规则[6]。竞争的多样化既有竞争主体的扩大化,也有竞争途径的复杂化,纯粹文字生产的传统方式逐渐让位于影视改编、校园阅读、游戏版权等。竞争面的扩大吁请作家创作面的铺开,在资本的诱惑下多管齐下也就成为常态。这本身构成了文学市场的一个要素,再加上阅读者口味经过多年的培育,朝着轻快与通俗的道路上迅猛发展,作家们即便推出思想厚重的作品也门可罗雀,庭院冷落,正好与他们所身处的职业化系统不相符合,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规避风险而转向热闹。
不管是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还是老谋深算的世故,“讨巧时代的文学写作”可供观察的点都很多。触碰到社会问题会轻飘飘一笔带过,在私人化的叙事中把个人情绪极度渲染,以类型化获得市场和资本的认可,思想本身的匮乏与缺失造成文学的营养不良,写作能力的老化与难以更新……即便不将诸种问题归于文学的疾病,也至少是不健康的与不负责任的。勉力坚持着“文学的良知”的,反而是非虚构,即便在非虚构的概念已经被严重泛化的当下文坛。
二、阶层固化,或社会结构的稳定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要素或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关系模式或互动模式。”[7]一俟社会结构建立完成,不管是关系模式还是互动模式,整个社会都会调动各种资源来对之进行维持。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秩序由一个运用物理或者心理强制的专门人员的班子加以维护,以保证该秩序得到服从或惩治对它的违反,这时法律便存在了。”[8]当然,他还认为经济因素在构建社会结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基础作用。如果说法律还较为显在、运营着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话,那么在一整套维持秩序的保障性措施系统性地发挥作用之后,所形成的文化模式与认同模式将以隐性且更为决定性、基础性的方式维护着社会结构的存在。“当社会稳定时,适应类型Ⅰ——对文化目标和制度性的手段都遵从——是最常见的,也是分布最广的。……构成所有社会秩序的各种期望是通过社会成员的模式行为而得以维持的。”[9]社会的习俗、惯例,逐渐地演变为“在一个共同体中参与社会荣誉分配的典型群体之间,会形成一种社会荣誉分配方式,对此我们称之为‘身份秩序”[10]。文化模式、身份秩序等将社会结构逐步稳固,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自我认同,于是就有了《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从内在自我意识追问工人阶级后继者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理论探讨。
作为追求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人才的选拔与阶层之间的流动成为促进社会结构完善的重要手段。在社会流动中,“高等教育”又是阶层垂直流动中向上流动的主要手段。研究者也都强调“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受教育者能够获得知识性、专业性和技能性能力,所以高等教育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1]因为高等教育选拔考试的缺失而造成的社会流动、封闭,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九品中正制”等是巧妙的转化,却造成了世家大族的出现。世家大族持续性扩大,变成了如今的“二代现象”,富二代、官二代、文二代、学二代、星二代……是获得利益较多而被关注的群体,农二代、工二代、贫二代……则是在底层奋斗却不能实现阶层流动的群体。甚至工与农的三代、四代乃至于“多代现象”不仅在当下,在历史上的稳定时期也会大量出现。由此导致的“阶层固化”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阶层固化按其生成原因可分为‘身份型与‘资源型。中国的社会流动变迁表明,‘身份型阶层固化是社会流动整体性固化,需要通过制度变革的方式改变,而‘资源型固化是社会流动结构性固化,可通过体制内的政策弥合与机制创新逐步消解。‘结构性阶层固化表现为‘两通畅两封闭,即中层向上与向下流动的相对通畅,下层向中上层,上层向中下层流动的相对封闭。其内在属性决定利益受损群体向上流动的困境,与利益被保护群体维持优越现状向下流动的阻滞。”[12]社会稳定所推动的社会结构的稳固,进而导致文化模式的形成、身份秩序的有条不紊,通过高等教育来获取阶层流动的途径,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许多有志青年人生奋斗的主要手段。但不应该忽视的是,“985”与“211”建设工程与近来“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的持续性推进,导致高等教育本身形成了类似于社会结构稳固的阶层固化现象。
“高等教育的阶层固化现象”,尽管一直存在,却少有人关注。对于“讨巧时代”的“聪明作家”而言,这并不纳入到他们“现实主义”的范畴之中,他们热衷于“他们个人的现实主义”所允许的题材。黄灯《我的二本学生》恰好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尽了二本院校学生们内心隐秘的痛楚、显明的忧伤与无处不在的生存尴尬。“二本学生之痛”成为关注的核心,它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阶层固化现象,并进而将触角伸向整个社会的阶层固化。不同于“讨巧时代”许多文学写作的聪明做法,《我的二本学生》似乎更愿意以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来去侧面观察这些高考制度与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并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去描摹他们的兴奋、欣慰与焦虑、痛楚。黄灯结构全书的方式是巧妙的,开首的《在龙洞》呈现出的是一幅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还在谋求人生发展的二本学生们的生活风景画。“卑微、逼仄、黯淡的角落”[13]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那些刚找到工作却收入微薄、经济拮据的二本学生,以及毕业后生活尚无着落,或者考研一再失败、升迁还有希望却不得不暂时跻身于此的二本学生,只能靠着自己的打拼,试图在高等教育所提供的社会阶层流动中觅得命运改变的一丝良机。而恰是这“一丝良机”成了他们幸福与哀愁的源泉,造就了他们幸福却悲痛的命运。《在龙洞》把卑微与辛酸展示之后,随之黄灯就开始凸显高等教育所提供的社会阶层流动所带来的欣喜与价值,《公共课》聚焦的便是刚进入大学后还处在兴奋阶段的学生们的“时代表情”:高考所提供的竞争机制成就了他们,也即将要吞没他们。随着兴奋劲儿过去,二本学生们逐渐洞悉了社会的游戏规则,“拼爹的时代”让无爹可拼的他们前途只剩下萧索与凄凉。《班主任(062111班)》和《“导师制”》两部分,用特定的例子来展现毕业后走向社会的二本学生。进入公务员系统,跻身于上层,是高等教育提供给他们进行阶层流动的良机。但许多学生因为缺少“背景”和“资源”,而不得不一再跳槽,在就业与失业中不停循环往复地过着人生。“高考没有进入一本院校,没有进入985、211等高校”给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教育背景”一项瞬间将他们定格在固定阶层范围之内,而“资源”的匮乏,更让他们看不到飞跃的希望,“临近毕业,一种看不到出路的迷茫,成为他们真实又沉重的情绪”[14]。
大约碍于当下形势大好的“社会稳定”,作家们很少触及“阶层固化”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连批评家们也缺乏勇气来探讨相关问题,尽管已经有作家对之进行了关注。查找相关数据,《我的二本学生》自出版以来,相关讨论、研究基本上付诸阙如,一片空白[15]。有形无形的压力、有意无意的规避,不管是在作家还是在批评家,都逐渐达成一种“妥协的默契”,即便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显性的现实”,且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领域这已经作为普遍现象在进行理论探索。黄灯的逻辑思路是以文学的方式,怀揣着热切的同情来描摹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一个时代的充满了褶皱的肌理纹路,试图去呈现他们五味杂陈的生命图景,记录时代症候。社会结构的稳定并不必然带来问题,资源与权力集中所导致的阶层固化,在还能具有弹性之时也不会出现疾患,只是这一问题泛化为一代人的集体命运,不但不能减轻且在不断加重,就值得警惕——“文学之为德也”,作为“经国之大业”,也恰是能在隐患已然存在之时,去关注、解析并提请疗救的注意!
三、内卷,一种时代的症候
在《班主任(1516045班)》一章中,黄灯记述了一个来自广东湛江的乡村留守女生秀珊,她身上所留下的乡村的烙印:“多子女、重男轻女、父母关系不和、一个人长大、封闭的村庄、吸毒的堂哥、被引产的堂嫂、像流氓的哥哥、童年捉鱼的快乐、热爱读书的天性、砸粉笔的小学老师、称学生为垃圾的高中老师、妈妈不切实际的期待、热爱写作的梦想、活着就好的淡然、无法留在广州的失落”,以及“没有改变命运的决心”[16],其实浓缩着全中国来自乡村,尤其是偏远、贫穷地区的二本学生们的集体经历。它们也许不尽相同,却较为本真地反映出二本学生们的出身、成长与人生的曲折——如果他们必然会失败,也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份上镌刻着“阶层固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平”。而这些又往往被带进学校,鲜明地体现在学生们的身上。毕竟,“学校不只是教育工具,更是文化生产和洞察的领地”。与此同时,“制度与地方非正式文化互动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和习惯性模式,带来了非预期且通常不可见的结果”[17]。它们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学生,以个人习性的方式,镌刻在他们的身上。自卑、视野狭窄、资源匮乏……即便杀出一条血路也渐渐地滑落入社会分层的漩涡之中,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吸卷进去,前一场竞争与厮杀的高考以相形见绌的方式被映衬出来。
内卷化,是近年来一个社会广泛关注、学者热衷探讨的概念。对于这些二本学生而言,“高等教育”所提供的“社会阶层流动的机遇”掩盖了他们在经受第一次内卷化过程中沦为牺牲品的事实:那些被他们竞争下去而未能考中的学生成为第一轮内卷化的牺牲品,成功进入二本院校的他们也同时面临着接下来的更为残酷的竞争。内卷化这一概念,最早由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提出,但他也宣称自己是借用了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艺术的内卷化”这一概念。在戈登威泽的解释中,艺术的内卷化所指的是艺术形式越发复杂化,但都是同水平的重复与精细化操作,缺乏创新性的进展。他所举的例子就是毛利人的手工制品,并将之称为一种文化类型,“艺术的内卷化”也只是单纯地指向个人艺术创作。格尔茨将这个概念借用过来,分析爪哇人由于没有工业就业机会,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来进行耕作,尤其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不断地把劳动力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上,还要面临着咖啡与糖料等经济作物的竞争,试图以精耕细作的方式来实现粮食产量的增加以供养更多人口。但土地生产力的有限性,导致他们投入的劳动力与农作物的产出率之间不成比例,形成“农业的内卷化”。恪守“勤劳致富”的祖训并未能够帮助有限土地上增加的众多农民,也没能让越过龙门进入大学校园的二本学生获得飞黄腾达的质变——内卷化与其说是一种“自我战胜”的过程,不如说是一种“无奈的无限竞争”。
格尔茨的这一概念,后来被黄宗智引入到对中国农业的研究之中,获得扩大化的理解,而他的分析则更为贴近中国的社会实际状况,对我们理解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不无裨益。几乎与格尔茨所分析的爪哇岛情况类似,华北小农经济的遭遇大体相当。“由于生存的需要,迫不得已为取得最高的短期收益,而过分地集中于单一的经济作物。这样的内卷耕作方式,减低了农场的收入。这是人口压力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后果。再加上地租,许多贫农农场,便无法取得家庭生存所需的收入。”[18]情况稍微不同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因为棉花与桑蚕等经济作物的增加,内卷化现象得到缓解。“商品化的小农经济确实扩展了,但这种扩展主要是过密型增长,而不是真正的发展。棉花和桑蚕的传播均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相联系,而资本投入只有不成比例的增加,因而单位劳动力的平均资本投入反而减少了,单位工作日的平均收入也是同样。总产值,甚至每个家庭的年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是增加了,然而这时因为投入了家庭成员(尤其是妇女、儿童、老人)更多的劳动,而不是由于单位工作日收入的增长。”[19]因为特有的运输网络、廉价的沿海水路往来,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商品化程度要高于华北等地。如果稍微将之放宽,可以看到的是,小农经济与教育状况几乎类似。
资源的有限,包括因地域限制而导致的教育资源、因出身限制而来的家庭资源,在初高中学习时期通过单独个人劳动的增加而获得高考成功的二本学生,就其个人而言是一种内卷化现象;就集体而言,在“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现象中,形成了组织之中的内卷化现象。但不同于农业内卷化,他们毕竟获得了高等教育所提供的階层流动的良机,只不过黄灯所关注的在于升入高校之后所面临的内卷化现象。刻苦与勤劳,几乎是二本学生们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个人资源,而在这种“学习的单位面积”有限的情况下依靠个人劳动无限投入,以期待获取更多成果的方式,类似于爪哇岛和华北地区小农经济的情况。农业的内卷化,与教育的内卷化,虽说并不相同,但就二本学生而言,经历似乎类似。文凭的限制、“特有运输(人脉)网络”的匮乏,都造成他们采取“刻苦与勤劳”的投入也依旧无法获得相应的报酬提升。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也成为他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念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20]
不管是个人性的内卷化,还是集体性的内卷化,亦或者是全社会的内卷化,读书改变命运,其中的希望变得越来越微茫。黄灯并不避讳这样的现实,而选择直面这样的社会问题——实际上,这也并不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正如分析社会结构时所强调的,社会结构的稳固本身是社会发展的反映,更何况所谓阶层固化也才刚开始,并未到板结的地步。《我的二本学生》中借助高等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学生,无论是他们的内卷化获得了成功,还是认清现实而选择了符合自己的道路,都能证明“黄灯式”的书写并非断章取义,阶层固化与内卷化作为社会现象,只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值得关注、值得更多的表达。毕竟,这是我们“时代的表情”之一。就文学而言,讳莫如深者将永远讳莫如深,而直面深渊者往往能看见天空。
四、重审文学的使命,兼及文学伦理学
文学的使命,到底是提供给人以娱乐,还是要深沉凝重以利于他人和社会?是掉进故事的漩涡中,探索曲折与婉转、惊悚与险怪,还是以故事承载人生命运的拷问,以便晓明人类的福祉所在?是以现实主义为名,迷醉于个人的爱恨情仇与悲欢离合,筑造精巧的私人化叙事文本,还是不畏艰难困苦,去真正觅得可靠的精神归宿,以便令劳作而疲惫的身躯获得诗意的栖居?……凡此种种追问,看似都抛给文学,实则是在拷问写作者的伦理境界。重建一门叫作“文学伦理学”的学问,不是要忘却文学作品本身所提供的伦理思想,而在于牵引出作为写作者,该以如何的面目现身于文字的神龛上的问题。
所谓写作者的伦理使命,便在于他所担负起的责任感、崇高感与精神向度的追求。要之,写作者必须肩负起道德、社会与历史所托付的重任,给道德以丰碑、给社会以镜鉴、给历史以担当。他所面对的时代越是贫乏他就越应该丰饶地去书写它,时代越是复杂他就越应该言简意赅地、一针见血地去描摹它。“黑格尔派的批评和泰纳派的批评认为:作品中所表现的历史的或社会的伟大性,简直就等于艺术上的伟大性。艺术家传达真理,而且必然地也传达历史和社会的真理。”[21]艺术的“伟大性”同时是写作者的一种冒险,它可能是要揭示繁荣背面的凋敝、喧嚣掩藏着的残忍、伟大之外的渺小,甚至于太平盛世掩映下的一丝阴影。写作者的责任,或文学的伦理学,要以写作为方式,通过声音的尖锐而唤醒沉迷者,以图规避历史进程中虚假繁荣所伏设下的陷阱。
写作者的使命与文学的伦理学,还要求写作者在对时代、社会和历史进行最为本质性的谛视的同时,更应该兼怀着宽容、悲悯与慈爱之心,关注那些被裹挟进时代洪流、社会大潮与历史趋势之中的个体的卑微的生命存在。但它不同于迷恋于个人性的私人化叙事,时刻都氤氲着人间情怀,是为民请命式的呐喊,也是传己入人式的命运体察。这种使命感与伦理化,尽量地剔除了写作者营私性的稻粱谋考量,更会时刻警惕献媚式的歌颂、讨巧式的聪明,它所谓的责任感,便在于寻求建设性的积极意义、觅取转化性的关注。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里是有慈爱的,尽管这慈爱里总渗透着现实的悲哀与无奈。写作者的伦理,也就在这慈爱的温润中,并通过这慈爱流淌在文本的字里行间。
时代的发展需要社会结构的稳定,而社会结构的稳定又会带来阶层固化,堵塞着高等教育带来的阶层流动,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竞争激烈时被裹进漩涡中也会产生个人性与集体性的内卷化——这些本不是《我的二本学生》的核心。这部作品只不过是“一个教师的良知和良知映衬下女性独有的慈爱与温情”所带来的侧面观察,它也许是“含泪的叙述”,也许是“冷静的旁观”“理性的分析”,但这都不妨碍它流淌出的写作者的使命与一种可以被称为文学伦理学的道德责任感。“文德”之大不在于呼天抢地式的激愤,也不在于苦大仇深式的悲情,更不是八面玲珑式的机巧,而在于不动声色中给予世界以良善、赋予叙事以担当,“经国之大业”也就于焉呼之欲出了。
末了,我们仍旧重返“古中国的素朴教诲”,以重审文学的使命及其伦理:“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22]知乎“非乐”之所非,即知“是乐”之所是!所谓重审文学的使命及其伦理的题中之意,也就不言自明了。
[注释]
[1]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相关注解与翻译还可参见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5页。也可参见李申等:《周易经传译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5页。
[2] 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几乎所有牵涉到古代文论的选本,都会将此文收入,使之成为人尽皆知的文学论断。
[3]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页。
[4] [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吴岳添译,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5] 谢尚发:《80后写作:器物、性事与现代性——以〈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为中心的分析》,《当代文坛》,2016年第6期。
[6] 近年来,“学者小说”逐渐兴盛,跨界现象严重。相关论述可参见谢尚发:《创作与批评的互动:多栖文人及其四重面相——重审文学的多重构成兼及当下批评与创作的互渗》,《文艺论坛》,2020年第5期。
[7] 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6页。
[8][德]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9][美]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页。
[10][德]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对“身份”的界定与认同,也是中国各种“社会阶层分析”类图书所常用的概念。比如认为“身份是社会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指由法律、法规、规范等认可的与一套权利义务相联系的社会位置。所谓身份制,就是通过法律、法规的规定,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身份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或条件作为排斥其他身份群体的正当理由。”参见李强:《當代中国社会分层》,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3页。
[11] 赵红霞、王乐美:《促进还是抑制: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基于CGSS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高教探索》,2020年第9期。
[12] 宋林霖:《社会流动中“结构性”阶层固化:政治学的解释与应对》,《行政论坛》,2016年第4期。
[13][14]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页。书中随处可见这种泛着理性有带着温情的文字,也构成了黄灯书写的一大特征。
[15] 通过中国知网查询,仅有张家鸿的一篇文章。可参见张家鸿:《〈我的二本学生〉:聆听青春的心跳》,《中国青年报》,2020年10月13日。
[16] 黄灯记述这段文字,是通过与学生谈心的口述方式写出来的,其间是否有“有意的择取”不得而知,但她所追求的“非虚构”效果却是十分明显的。引文参见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7—188页。
[17][英]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28页。
[18]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305页。
[19]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06页。
[20]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3页。尽管在文章中,黄灯已经十分克制自己的情感,避免自己流入廉价的同情与悲悯的漩涡之中,但她力图冷静的叙事文字背后,也还是将学生们的悲戚展露无疑。
[21]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页。
[22] 引文综合了孙怡让等的解释,对原文稍有修改。相关引文可参见孙怡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51页。或参见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73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