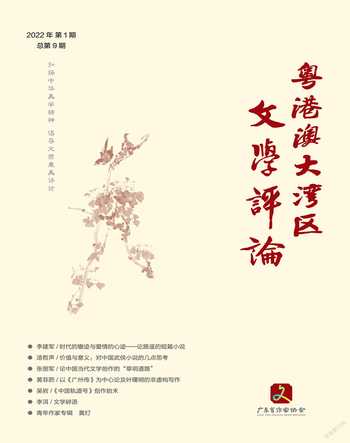乱世苍凉,苍凉乱世
2022-03-14刘川鄂
刘川鄂
摘要:张爱玲涉及战争题材的作品不多,且不直面战争本身,而是以战争为背景,写凡人的凡人性,“正常的人性和人性的弱点”。她最关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中的人性的扭曲,情感的浪费,生命的无辜。文明脆弱,人性苍白,道德蜕变,说不尽的苍凉故事。可以说,张爱玲的相关作品是战争心理学、灾难心理学的形象范本和人性微病历,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精细刻画战争中的人性和人性的战争的精彩篇章。
关键词:张爱玲;战争题材;人性;人性的弱点
1987年秋,正在上海、南京、杭州查阅有关张爱玲硕士论文资料的我,抽空在西湖畔看了一场电影《最后一班地铁》。二战德军占领巴黎期间,戏剧照演如常,剧场比平时更热闹。战争为什么加剧了剧院的火爆?因为待在家里有未知的恐怖,只有在人群中寻求安全感才能忘却恐惧感,抱团取暖,驱逐心魔。战争灾难,淡化了家庭的重要性。
犹太籍的剧场主人兼编剧吕卡斯为了躲避纳粹的种族迫害,一直住在剧院的地下室,继续领导和排练他所编的剧目。这一切全都是通过他的妻子、著名女演员玛丽翁来完成的。每次他都是靠地下室内的伪装通风系统来倾听舞台上的排练,同时他也感觉到玛丽翁和男主角的扮演者格朗惹之间产生了微妙的爱情。考虑到自己的处境,他决定成全他们。但格朗惹见到吕卡斯之后,决定到抵抗运动中去。巴黎解放了,玛丽翁站在舞台上,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拉着情人,向观众频频谢幕。丈夫和情人在平常状态中是仇人关系,而在这种非常态的环境中却变成了同志关系,全拜战争所赐。大敌当前,死活难顾,爱情,天生具有排他性的爱情,关于两性关系的道德,退居其次。战争灾难,淡化了道德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文明中,和平是常态,战争是非常态。所有战争都是人类的敌人,都是人类的灾难,尤其是平民的灾难。
灾难可分为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前者如地震、瘟疫,此为天灾。后者如战争和政治浩劫,此为人祸。当然也有二者混合的灾难,此为天灾人祸。前者触发人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多让人思考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应该说后者的社会含量、人性含量更丰富,对人自身的反思对文明的反思更深刻,这是不言而喻的。灾难具有不确定性、破坏性和长期性,大灾害、大灾难对人们心理的伤害远超想象,所以需要心理援助,从个体层面、群体层面、组织层面、社会层面去预防灾难、救援灾难、重建灾区和心理疏导,应对和医治创伤。[1]作为社会生活的极致表现,灾难往往是人性最活跃的、最彻底的、极端的表现舞台,因此也是深邃敏感的文学家观察和描写的重点领域。反常态的环境中,人的生存方式的某些变化、人性的极致表现,都是作家乐于观察和表达的。很多伟大的文学家都是灾难的见证者、审视者和反思者。“人道灾难对人造成的最深远、最持久的伤害就是对共同人性的扭曲和败坏。 人道灾难因此也成为人性灾难。人道灾难发生以后,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人性和道德秩序再难修复的世界之中,不管他是受害者、加害者,还是袖手旁观者。”[2]
现在中国作家中有几个跟死亡隔得特别近的人,他们往往是人性洞察最深邃的人,作品的人性含量最丰富的人,如鲁迅的绝望抗争(父亲的病与死加速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厌恶与反抗)、沈从文的边民生趣(少年时代见过太多的杀人场面,所以他看淡了生死、看轻了文化)、穆旦(参加远征军的自杀式滇缅大撤退,成天看着战友倒下,自己也差点病死、饿死、被敌人打死)的文明反思、张爱玲(香港战争中的看护经历)的乱世苍凉。
一、去掉一切浮文,只剩下饮食男女
香港战争的爆发,毁灭了张爱玲的留学梦。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气势汹汹,香港惨遭血与火的洗刷。相持了二十多天,英军弹尽粮绝,投降日军,战事遂告一段落。
因为战争,香港大学受到炮火的重创,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被烧掉了,张爱玲的一个个优异成绩化为灰烬。而且她连一张毕业文凭也没拿到便不得不结束学业,重返上海。仿佛命运之神故意要捉弄她,使她永远不能走科班出身的循规蹈矩的读书求学之路。爱玲回忆说:“我在港大的奖学金战后还在。进港大本来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战后校中人事全非,英国惨胜,也在困境中。毕业后到牛津进修也不过是当初的一句话。结果我放弃了没去,这使我的母亲非常失望。”[3]从这话的表达口吻来揣摩,在香港摆脱了日本人的魔爪之后,爱玲本来是可以继续她的学业的,但她没有去。她虽然仍有挂怀,但没有后悔,失望的是母亲而不是她。那时的张爱玲已是著名作家,大红大紫,还在热恋中,她此时没有了当学生的心境。但战争毕竟使她中断了“超级学霸”本来可以延续的童年的留学梦,使她部分地失去了常态生活的可能性,聯系到一系列的言论和作品,她对战争可没有好感。
《流言·烬余录》,可以说是战时单身女郎的百态图,情态各异,千姿百态。一位女华侨,平时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衣装,但她没有打仗时应该穿的衣服,这是她在战争中的最大忧愁。说来是个笑话,但这也是一种真实的女性心理,女人爱美爱装饰天性的病态发挥,令人无限感慨。
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小美人,入学时天真得可耻,问解剖尸体时死人穿不穿衣服。飞机一响,她就拼命喊叫,歇斯底里,吓得大家面无人色;战时粮食供应不够,也正因为不够,便有人努力地吃,张爱玲称之为健康的悲观。
港战打响后,学校停了课。爱玲和同学们参加了守城救护之类的工作,这不仅可以解决膳食问题,而且可以填补因无所事事带来的空虚,于是她们纷纷当上了防空队员和救护员。当防空员时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她看见了一本《醒世姻缘》,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图书馆的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日军轰炸的目标。一颗颗炸弹落下来,越落越近。张爱玲心想,至少等我看完了吧。炎樱,在战争中欣然自乐,冒死上街看电影,在被流弹打碎玻璃的浴室里边洗澡边大声唱歌,像是在嘲讽众人的恐怖。——绝望中的放纵,无奈的任性。
人们都想到过死的可能性,而一旦真的有人受伤,众目睽睽之下的伤者反而因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而颇为自得。伤口怎样发脓,怎样因长新肉而欣喜自怜,怎样以捉米虫而打发时光。——人总是求存在感,求被关注,但是这种方式也太特别。自得的背后是更大的孤独和恐惧。有的病愈而走,有的死亡而终。一个又一个冻白的早晨过去了,人们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她的一个英籍教授战时投笔从戎,没能死在战场上,却因未及时回答己方哨兵所问口令而被打死了。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
人们不敢外出,纷纷抢购粮食,以防挨饿。但仍饿了不少人,爱玲和她的一班爱吃零食的女友们自然也跟着吃苦挨饿。停战后人们又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是记录战时香港居民心态的传神之笔。——劫后余生,常态生活升格为超级享受,人的物质性。
更有不少女孩子为驱散战争恐怖要抓住一点儿真实的人生而匆忙结婚了。战后香港报纸上的征婚广告密密麻麻,缺少工作与消遣的人们都提早结婚了,仿佛两个人在一起比独身一人更容易驱散战争的恐怖的阴影,但这似乎也降低了对精神的需求。
食与性成为最基本、最真实的人生内容。男女同学之间的道德感也松弛了。学生们似无所事事,成天在一起烧饭、打牌、调情——带着绝望伤感的调情,有一次算一次的调情。
男生躺在女生床上玩纸牌,大清早就闯入女生宿舍厮混。清晨的静寂中,不时传来娇滴滴的“拒绝”声:“不行!不嘛!不,我不!”其他人习以为常,决没有大惊小怪,也无人岔岔不平。死里逃生的人的贪欢,人人都能理解,人人都会同情。透过这些故事,爱玲惊讶地发现: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
“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这是一个敏锐独到的人生见解。它不同于平面地从时代、环境等外部因素观察社会的历史学家的眼光,而是文学家们特有的人性的视角。
港战使她眼界大开,她不停地思考着生活的价值,先前对人的认识也得到了实证和矫正。她觉得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似乎仅是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就是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的生活圈子,但却这样难,几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
空袭和警报、逃亡与坚守、伤兵和死尸、正义与自私、求生和求爱、人性与兽性……港战前后极大地丰富了张爱玲的人生经验。她回忆这段生活的长篇散文《烬余录》是现代文学中精细刻画战争中的人性和人性的战争的精彩篇章。它的结尾也是一段名言: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 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4]
她最寒心的是人性的扭曲,情感的浪费,生命的无辜。乱世苍凉、苍凉乱世。反常态的时空里,凸显着人性和正常的人性弱点。
二、“乱世的人,没有真的家”
香港,是成长期的张爱玲体悟人性的“圣地”。港战,给了她观察人性的良机。她的人生观开始在形成,在成熟。她对个人的志向偏于写作方面亦有了信心。“张爱玲的香港故事,呈现了奢华与衰颓、浪漫迷魅和精神堕落并置的复杂图景。这个岛屿,为张爱玲眼中深受传统制约的上海中国人,提供了一面扭曲的镜子;相对于所扎根的上海,香港成了她的自我‘他者。多年之后的1952年,当她被迫离开上海时,她别无选择再次前往香港,并以之为试图开启新文学生涯的临时基地,尔后再移居美国。可以说,是香港,才令她后来的文学写作成为可能”。[5]
不论张爱玲怎样三头六臂,不管她的题材如何变化万千,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是她半个世纪笔耕生涯的专注重心。《傾城之恋》中范柳原的花花公子性格似乎定了型,不可改变,白流苏的婚姻算计似乎很难实现。两个人的谈恋爱无休无止,花样无穷无尽,但永远停留在高等调情阶段。然而,似乎等不了那么久,香港战争爆发了,无论什么人都共同面临着生死、饥饿。他们齐整整地站在人的底线上了,这一对男女结婚了。有人不能理解一场战争使二人结为夫妻,以为这是作者的突兀之笔。作者的用意是明显的:一场战争毁灭了高等调情的场所,洋场气氛淡化了,洋场文明如何不收敛些?质朴的生活逼迫了他们,一对自私的人才能结合。飘在云端的爱情落在了现实的婚床上。假若没有战争,尽管柳原对流苏有情,但流苏永远只是他的情妇,而柳原永远只是一个爱匠而不是爱人。从《倾城之恋》可以看到,人在战乱的残酷现实面前是多么无奈、多么脆弱,不堪一击。
“乱世的人,没有真的家”(《封锁》)。城市因战争而惊慌失措,生活节奏被打乱,人们失去安全感。一声警笛,电车原地停顿,造就了一个封闭的时空。封锁内外是两个迥然有别的世界。吕宗桢有家庭,有事业,但他连为什么每天要上班、下班后要回家都不明白。吴翠远是一严肃得过分、平淡而无生气的女性。“思想,是件痛苦的事情。”但他俩在一个与世相对隔绝的环境中相爱了。封锁期间的他俩与在尘世中生活的他们判若两人,坠入爱河、焕发了活力。但一旦封锁开放,他们又不得不继续扮演着原来在尘世中的形象。纯洁的情如美丽的昙花,刚开即逝。作者通过封锁期间与开放以后的时空变化,表现出尘世与纯情的对立。封锁期间,正是一个纯情的世界。解除封锁,又回到凡俗的人间。
如果说读者们普遍欣赏张氏描绘的常态下的人性及弱点的话(如《传奇》集中的中短篇小说),对《色,戒》这篇因题材的尖锐而显得格外“打眼”的小说,还是应该从这一角度。《色,戒》在特异的状态下探寻人性和正常的人性的弱点,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除了作者关注人性的自觉意识及长期的琢磨之外,与她在这篇作品中调动多样艺术手法为之服务相关。不露痕迹的细节铺垫、精微的心理刻画、高潮中的“反高潮”写法,都相当成功。尤为出色的是“反高潮”手法。美人计历时两年,几经周折,女主人公也费尽心机、尝遍酸苦与甘辛,总算熬到了除掉易先生实现暗杀计划的那一刻,眼见得高潮就要出现,万事俱备,没有任何细节差错,却被王佳芝临时“变卦”把易先生轻而易举地放走了。完备计划付诸东流,常态结果没有出现。这就是“反高潮”——走向高潮的反面。它不过是将人性置于反常态的状态之下拷问、探寻。唯如此,我们才能找到《色,戒》与张爱玲其他作品的相通之处。
如果说政府和社会学家关注的是灾难中和灾难后群体的行为反应,抑郁症、焦虑症等明显具有医学特征的身心障碍,文学家更关注灾后个体身心反应,一些可能当事人不以为然的、没有明显病理特征的潜在疾患。张爱玲涉及战争题材的作品并不是很多,除了这里提到的几部之外,《赤地之恋》部分内容与之相关。而且基本上都不是直面战争本身,而是以战争为背景,写凡人的凡人性。可以说,张爱玲的相关作品是战争心理学、灾难心理学的形象范本和人性微病历。“受害幸存者既是灾难的‘道德见证人,也是后灾难的‘世界修补人。他既反叛灾难的邪恶,也反叛后灾难对邪恶的忘却。他的见证体现的是一种人为自己生命做主的决心。灾难见证是一种宝贵的社会道德力量,它能帮助所有的人在共同人性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6]没有英雄叙事,不是大悲大喜,而是凡人的悲哀,“几乎无事的悲剧”,小人物的常态性格和性格变异。张爱玲刻画了否定性的样本,或者说精细地绘出了病例,做出了诊断,但是她没有开药方。悲哀的人无药可救,悲凉的心没有未来,这的确不是她的强项。
三、说不尽的苍凉故事
“自从文明的社会一经出现,战争和奴隶制就是文明的一对毒瘤。”[7]为政治权力争斗、为经济利益争夺、为宗教文化冲突,战争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特殊存在,造就了社会发展的灾祸与人类生存的动荡,带来人口、疆域、政治、经济、科技等社会人文环境的急剧变化,甚至成为决定人类生存命运的重大转折。功不可没,罪不可赦。
战争题材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格局占有重要位置。“战争是人类存在景况的最鲜明、最全面、最精细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战争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显影器皿,人类的优点与弱点,人类的智慧与愚昧,人类的理性与疯狂,人类的正义与邪恶,人类的高级品性与低级欲望……都可能在这个显影器皿中获得前所未有的甚至是终极性的暴露……所以,战争之于小说创造的诱惑,往往处于一种永恒的状态。”[8]古今中外有不少关于战争文学的经典著作。历史的进程、人性的纠葛、正义与邪恶、和平与暴力、人性与兽性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战争文学是国民性格的充盈展示,人类精神在特殊时期的极端发展。
“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国家主义使时代变得疯狂而混乱,使得她的人生变得无法控制,使她的写作和私生活都备受诟病。正因为亲历了战争,对战争的残酷和绝望有了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认识,国家主义对于她才更像是洪水猛兽。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拿生命去信奉国家主义,这样的狂热造就的不过是无谓的战争。整个世界在二十世纪都沉迷在这个宗教中,喃喃地痴迷在国家民族的想象里,争相为自己赋予神圣的使命。[9]
灾难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进步,危机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创伤,还有与创伤抗争之后的成长。“战争的结局不是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了下来,也不是世界经过胜利者的分配拥有了全新的格局,它最大的结局是人性的改变。人性的改变决定了未来的人类是什么样的人类,它比战争本身更加危险。”[10]如同海明威那样,战争中士兵们遭受的令人难忘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在《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中,在他塑造的尼克·亚当、杰克·巴恩斯和弗里德里克·亨利这样一些反战经典形象中,在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福克纳和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世界经典名作中,从英雄主义、国家主义、浪漫主义三位一体的戰争小说,到怀疑主义的人性探寻、深层拷问弱者本位,是世界经典军事题材文学的重要发展趋势。不管战争有多少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但之于平民就是灾难,之于凡人,就是生命的挣扎和人性的煎熬、撕咬、扭曲。
因为安全没有保障,生计没有保障,生命没有保障,所以家庭也没有保障,有时候只能顾自己一个人。一个人的生活是更加随意的生活,更加没有责任感、没有家庭义务的生活。既然是死是活都不可知,颜面和规矩也就放松下来了。乱世的生活更加个人化。
死生契约,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实在是最悲哀的一首诗,死与生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一生一世也不分开。”好像我们做得了主似的。(《倾城之恋》)
生逢乱世,小人物是做不了主的,谁都做不了主。男人女人做不了主,洋人华人做不了主,华侨土著做不了主,已婚未婚做不了主,穷人富人也做不了主。唯有苍凉。文明如此脆弱,人性的底色如此苍白,道德似乎可有可无,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
[注释]
[1] 时勘等著:《灾难心理学》第一篇“理论方法”,科学出版社版2010年版。
[2][6] 徐贲:《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3] 张爱玲:《对照记》,台北皇冠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4] 张爱玲:《流言·烬余录》,中国科学公司1944年版,第56页。
[5] 李欧梵:《张爱玲在香港》,《南方文坛》,2019年第5期。
[7]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2页。
[8] 周政保:《战争小说的审美与寓意构造》,《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9] [美]维克门(Yohn Wakemen)主编:《世界作家简介1950—1970》,纽约沃尔逊公司1975年版。该书介绍了959位作家。入选者必须为英语世界所熟悉的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参见高权之:《张爱玲的英文自白》,见《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
[10] 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34页。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