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的宽容传统及其现代困境
2022-03-14黄湘
黄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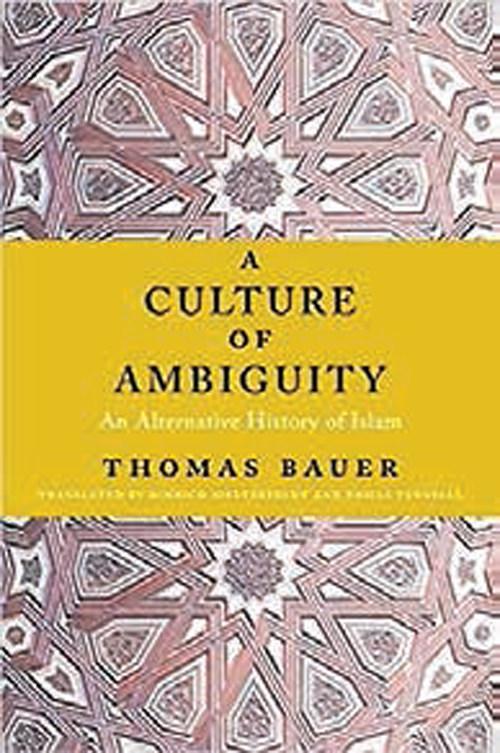
作者:[德] 托马斯·鲍尔(Thomas Bauer)
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定价:35美元
本书深入分析了伊斯兰文明在教义、法律、哲学、文学和性行为等领域的宽容传统,以及这一传统在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逐渐衰落的原因。托马斯·鲍尔是德国明斯特大学伊斯兰研究教授
近几十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撕裂了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结构,而且为美国发动长达20年的“反恐战争”,深度干涉中东和中亚地区提供了借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强化了很多人对于伊斯兰文明的刻板印象,即认为它故步自封,缺少宽容与多元。
事实上,在历史长河中,横跨北非、中东、中亚乃至东南亚的伊斯兰文明曾经远比同时代的欧洲基督教文明兼容并包。只是由于西方现代性的输入,才导致伊斯兰文明的宽容传统在19世纪发生转变,走向式微。德国学者鲍尔(ThomasBauer)的著作《含混性的文化:伊斯兰的另类历史》(A Culture of A mbiguity: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Islam),通过细致的历史梳理,深入分析了伊斯兰文明在教义、法律、哲学、文学和性行为等领域的宽容传统,以及这一传统在进入19世纪以后逐渐衰落的原因。本书德文版在2011年问世,被学术界誉为堪与萨义德的名著《东方主义》媲美的著 作。
前现代的伊斯兰文明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从7世纪伊斯兰教创立到11世纪,称为“形成期”(formativeperiod),当时的伊斯兰世界主要处在大一统的哈里发帝国的统治之下,先后出现了倭马亚、阿拔斯两大王朝。第二时期则是从12世纪到18世纪,称为“后形成期”(post-formative period),鲍尔指出,前现代的伊斯兰文明对于含混性高度宽容,这在“后形成期”表现得尤为明 显。
中世纪和近代初期的基督教欧洲充满了对异端的血腥杀戮和残酷的宗教战争,导致此类劫难的关键原因在于教会和政权坚持自己掌握了唯一明确的真理;前现代的伊斯兰世界则没有宗教战争,也不曾处决异端,因为它搁置了所有对于唯一真理的诉求。基督教文明追求消除模棱两可,这必然导致各方以唯一真理的名义相互竞争,乃至你死我活;与之相反,前现代的伊斯兰教并没有试图消除含混性,而是拥抱它、驯化它,使其成为思想、学术和文化的一部分。伊斯兰文明不仅长期宽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故意制造含混性。
对于《古兰经》文本的各种正统解读,是体现后形成期的伊斯兰文明之含混性的典型例证。《古兰经》中有许多意义含糊不清的段落,前现代的穆斯林注释者认为这种含混性是由真主决定的,是“刺激人类反复阅读文本的神的诡计”。伊本-贾扎里(Ibn a l-Jazarī,1350 -1429)长期被公认为是在《古兰经》解释方面最为杰出和多产的学者,是该领域的最终权威,他不仅接受《古兰经》文本的含混性,甚至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丰富性,认为这体现了真主在文本中的存在,是一种神圣的恩典。他宣称:“伊斯兰社群的学者从未停止(也不会停止)从《古兰经》中推导出迹象、论据、证明、见解等等,这些都是早期学者尚未意识到的,不会让未来的学者感到疲惫。相反,《古兰经》是一个巨大的海洋,人们在其中永远不会到达地面,或是被海岸所阻挡。”
出于对含混性的推崇,早期的《古兰经》学者建立了一套解释学方法,考虑所有可能的解释,而不是只宣布其中一种解释有效,通过这种方式,一种能平衡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的宽容模式逐渐形成。前现代伊斯兰文明对于《古兰经》译本的怀疑也是源于这一假设,因为译本通常只再现了许多可能的含义中的一种,他们担心译文过于直白僵化,没有什么解释的空间。
这种将含混性视为一种恩典的观点,与现代穆斯林学者的论述背道而驰,后者倾向于坚持毫不含糊的解读和“正确”的解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伊斯兰教自由主义改革者、伊斯兰教的批评者都从《古兰经》和先知的著作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经文,然后断章取义地引用它们。这三个群体的政治主张不同,但都具有现代的、“不含糊”的态度,都声称自己知道伊斯兰教的真正性 质。
伊斯兰教的法学名为“费格赫”
(fiqh),意为“深入了解”或“完全理解”,是指从繁复的伊斯兰法源里抽取出来法律上的考量,并通过法学来认识和了解伊斯兰教。长期以来,作为伊斯兰世界多数人群的逊尼派穆斯林通过四大法律学派—哈乃斐派、马立克派、沙斐仪派、罕百里派—来建构“费格赫”。四大法律学派对于特定圣训的正确性持有不同意见,在特定情况下的类比推论也各有不同,但是各个学派都没有把其他学派的观点视为亵渎,它们具有平等的法律效力。这是因为他们相信没有派别可以拥有绝对真理,因此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法学解释可以共存。
与此相反,20世纪的萨拉菲派穆斯林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出于“不容忍含混性”的世界觀,反对法学的多样性。
他们谴责四大法律学派,强调这些学派与《古兰经》或圣训的文本颇有互相矛盾之处,因此应该直接遵循经文而不是遵守法律学派。事实上,他们对《古兰经》和圣训的解读方式本身是独断的,与前现代《古兰经》学者对文本多元解释的推崇态度背道而驰。
当今世界有一种广为流传的看法,认为伊斯兰文明没有区分宗教和世俗领域,从而导致其发展落后。鲍尔激烈地反对这种说法,他指出,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一直存在着不受宗教影响的领域,穆斯林总是能够区分世俗和宗教事务。
前现代的伊斯兰世界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政教合一,只有寥寥几部著作从宗教角度讨论政治权力和国家,而大量赞美统治者的诗歌以及向统治者提供政治建议的著作都很少涉及宗教。许多重要领域,诸如医学、法律和政府管理,都是按照世俗的原则来组织的,并不具有伊斯兰教特征。前现代伊斯兰世界的医生都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并不以《古兰经》起誓,也没有任何杰出的穆斯林医生从《古兰经》中得出具体的医学教 义。
在当今西方的学术话语中,历史上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哲学家都被归为“伊斯兰教哲学家”,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以波斯医师、化学家、哲学家拉齐(Muhammad ibn Zakariyā Rāzī,865-925)为例,此人博学多才,在医学领域发现了天花与麻疹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并最早阐明了过敏和免疫的原理,在化学领域创立了完善的蒸馏和提取方法,发现了乙醇、硫酸和煤油。他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远远超过受《古兰经》的影响。将他的著作归类为伊斯兰教哲学,就好比将康德的著作称为基督教哲学。
前现代伊斯兰文明推崇含混性,与古典阿拉伯语的发展完善有关。在伊斯兰教兴起的最初几个世纪,古典阿拉伯语形成了语法、词汇、修辞等方面的复杂理论,促进了对含混性的迷恋,并为多重语义的修辞游戏开辟了道路,使古典阿拉伯文学形成了华丽的风格。阿拉伯语言学家和修辞学家曾经专注于收集模棱两可的词语,分析模棱两可的文体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创作了数以百计的修辞学作品。诗人、学者、商人、工匠和民间艺人创作了无数的诗歌和散文文本,在其中无拘无束地试验可以想到的各种歧义。这是一种含混性的训练,促使人们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也能培养对含混性的容忍度。然而,今天许多穆斯林和研究伊斯兰文明的西方学者都认为这种含混性是伊斯兰教颓废的标志。
如今,伊斯兰文明经常被描述为在性问题上保守僵化,但是鲍尔的历史研究描绘了一幅不同的画面。早在公元9世纪,阿拉伯医生就撰写了关于性的手册,他们延续了一个古老的、但是在中世纪欧洲被基督教所中断的传统。前现代的阿拉伯医生以务实的方式讨论了性卫生问题,没有受到道德压力的影响。在19世纪之前,性行为在伊斯兰世界被看作是自然的和令人愉快的事情,只要它发生在法律认可的两性关系范围,亦即婚姻之内,就受到提倡和赞美,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没有原罪的概念。
此外,前现代伊斯兰世界认为没有必要区分男性之间的爱情和友谊。从公元9世纪到18世纪,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无数的同性恋诗歌,成为伊斯兰古典文学的一个既定类型。这一传统直到19世纪才结束,主要是由于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影响。19世纪的西方文明从前现代基督教对身体的敌意出发,将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和异性恋视为人的本质属性,将同性恋视为一种非自然的偏离和变态,将同性恋文学贬为低级趣味的色情作品。同时,西方文明对于单一真理的执念,导致其迫使每个人审查自己,相信并接受自己只有单一的性取向,拒绝承认双性恋的可能性。19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以自己保守的性观念为准绳,将伊斯兰世界对于性的开放态度视为颓废堕落,甚至是伊斯兰文明落后于基督教文明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导致了伊斯兰文明在性观念上的剧烈转变,近现代伊斯兰世界逐渐对同性恋采取恐惧、抵制和仇视态度。
前现代的伊斯兰文明提倡多元视角的世界观,接受人类认知的局限性。西方的近代思想则追求单一真理,试图消除任何矛盾和含混性。当今伊斯兰世界的诸多思想派别对于狭隘的单一真理的追求,根本原因在于采用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伦理观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表面上是向传统伊斯兰价值观回归,实际上并非源自前现代的伊斯兰文明传统,而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效仿。
在19世纪以前,伊斯兰文明在政治、宗教、法学、艺术、性行为等领域都培养了对含混性和多元性的兴趣。只是当伊斯兰世界在19世纪与否定含混性的西方文明对峙之后,才发生变化。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对中东社会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像西方那样通过明确的规范来定义自己;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认为需要以僵化的教条主义来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以此维护自身利益和价值观,对抗强势的西方文明。一种全新的、不宽容的、意识形态化的伊斯兰文明因此诞生,无论是原教旨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其模式都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结构的效仿,只允许单一的真理,不容忍多元的意见。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文明已经放弃了对单一真理的执念,转向开放和宽容,伊斯兰文明却仍然被困在单向度的现代性之中。这是当今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根源。
《含混性的文化》的核心观点在于,19世纪以后形成的伊斯兰教自由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都是欧洲现代性的分支,都不容忍意义的含混性,相比之下,“后形成期”的伊斯兰教对含混性采取宽容态度,强调对现实的多视角观照。
这对于理解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启示。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已经与传统中华文化高度融合,例如,明末清初的穆斯林学者张中在《归真总义》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所谓‘虚堂客去山还静,幽谷云来花自馨’,依然适得个本体。此等境界,亦不易到,须是真积力久乃得。满素尔尊者,一日突云:‘我是真主。’此经书有禁,教法不容者,是以为国人所害。然而千载之下,皆识其为得道真人。此其所谓承领真主断法,而不为法缚者欤!或曰,窃闻‘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奈何不能使人礼之,而反为所害。曰:杀之不为其辱,礼之不为其荣。本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这段话信手拈来地运用了儒家和禅宗的话语方式。“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出自唐朝诗人王建的《宫词》,以描述男女之情的艳诗引人开悟,本是禅宗的独创,张中将其移至伊斯兰教的语境中,可谓水乳交融。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文化会通,原因就在于“后形成期”的伊斯兰文明颇具宽容甚至崇尚含混性,提倡多元视角。显然,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应当奉“后形成期”具有兼容并包特征的伊斯兰文明为圭臬,而不是移植受西方思维影响的坚持单一真理的近现代伊斯兰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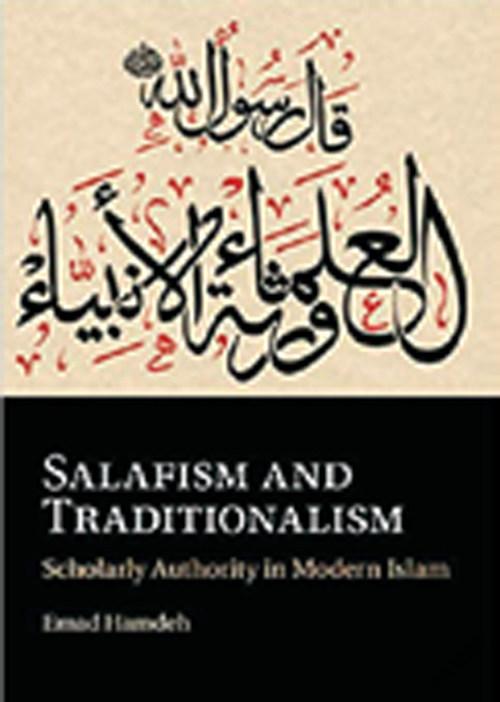
《萨拉菲主义与传统主义:现代伊斯兰的学术权威》
作者:[美] 艾玛德-哈姆德(Emad Hamdeh)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讲述了20世纪兴起的立场保守的萨拉菲主義与相对宽容的传统主义关于伊斯兰教学术权威的紧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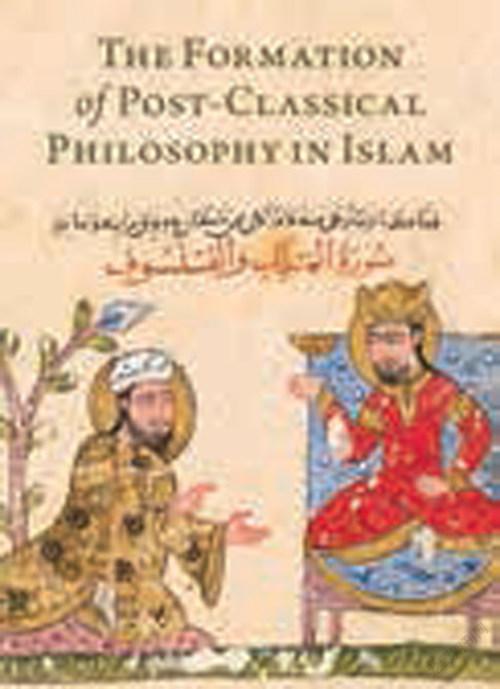
《伊斯兰后古典哲学的形成》
作者:[德] 弗兰克·格里菲尔(Frank Griffel)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分析了12世纪的伊斯兰哲学,并将其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比较。
3378500338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