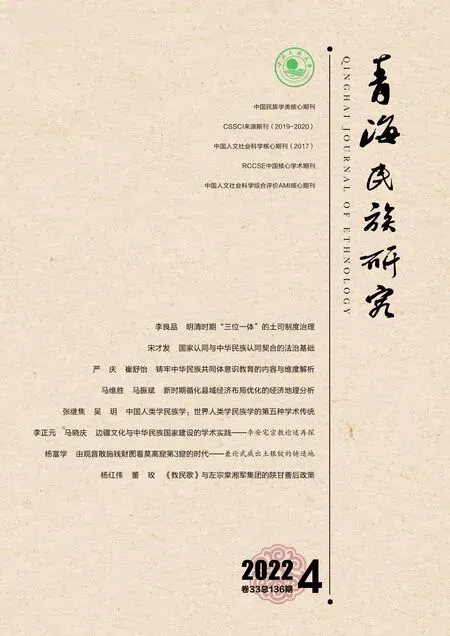明清时期“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
2022-03-13李良品
李良品
(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涪陵 408100)
运用土司制度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是中央王朝、地方政府及各地土司的责任与义务。文中将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地方政府与各地土司利用土司制度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称为“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是作为软性手段运行的,而王朝国家、地方政府与各地土司三者的权力体现的是对其他行为主体的治理和管控能力。在王朝国家通过土司制度治理的过程中,虽然王朝国家赋予土司机构、官民组织、土司宗族一定的“制度性权力”并指导或引导其运行,但中央政府及下设的地方政府在土司制度治理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目前学界与本文完全一致的成果仅有笔者关于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论文1篇①,另与主题正相关的著述有5篇,且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或探讨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或分析土司承袭制度与国家治理,或研究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②。本文以宏观的王朝国家、中观的地方政府和微观的土司地区的视阈探讨土司制度治理,不仅有助于深化土司制度研究,而且对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所启迪。
一、王朝国家的土司制度治理
众所周知,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土司制度层面的权力本身体现的是王朝国家与土司及土司地区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是数百年来王朝国家与各地土司不断博弈的结果。从土司制度治理的层面看,王朝国家的土司制度治理是属于宏观的、主导的治理,自始至终掌控着土司制度治理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土司地区的土司制度治理是属于微观的、被动的治理,自始至终受王朝国家的掌控和制约,是王朝国家主导下的协调治理。明清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事关王朝国家对土司政权的有效治理及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创立、完善和革新土司制度是王朝国家治理的核心举措。明清政府的土司制度治理举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中央政府规定土司官秩
明清时期无论是文职土司还是武职土司,他们均有一定的职衔和品级。在国家治理各地土司层面,他们分属吏部和兵部。在土司制度中,明清政府的杀手锏就是利用土司职衔管控各地土司。历史文献对明清时期各级土司的职衔和品级规定得十分清楚,如指挥使,正三品;宣慰使,从三品;宣抚使,从四品;安抚使,从五品;长官司,正六品;蛮夷长官司,正七品;土千户,正五品;土百户,正六品;土知府,正四品(清为从四品)。[1]规定各地土司的职衔和品级,有利于王朝国家治理。
(二)中央政府颁布土司承袭法规
明清中央王朝在建构土司承袭制度时,为了更好驾驭和控制土司以及土司地区,颁布了一系列的承袭法规,以此彰显明清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如明代政府对土司承袭次序、承袭程序、承袭文书[2]等作出明确规定,并在《明世宗实录》之“嘉靖九年四月甲申”[3]条得以充分体现。据史料载,明代颁发的这份《土官袭职条例》,主要规定了土司守则及承袭程序例规以及内地汉人不得到土司地区重利盘剥买田治地等内容[4]。清代中央政府同样颁发了《土司例纂》,其内容与《土官袭职条例》基本相同,主要涉及土官土司袭替中的争袭、具印甘结、土司亲供宗图及原领号纸、土司承袭次序、支庶子弟酌量给与职衔、土官分袭与降袭、土官承袭处分[5]等问题。
1.控制土司承袭程序
《明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等详细记载着土司承袭程序,“其应袭职者,由督抚察实,先令视事,令司府州邻封土司具结,及本族宗图,原领号纸,咨部具题请袭”[6]。明清政府牢牢把握制定土司承袭流程和操作机制的权力,控制土司承袭程序,达到了王朝国家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治理。
2.规定土司制作承袭文书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明确规定,土司承袭前需制定承袭文书:如明代朝廷要求土官应袭者必须“明白取具宗支图本”“体勘应袭之人,取具结状宗图,连人保送赴部,奏请定夺”以及确认该应袭土司“别无争袭之人”[7]。否则,不准袭替土司职位。明清政府为防止土司承袭过程中出现争袭、冒袭等弊端,要求土司制作“宗支图本”“结状文书”等相关的承袭文书。
3.限制土司家族承袭次序
明清政府制定土司应袭次序是以家族血缘为主,《明会典》载:“洪武二十七年,令土官无子、许弟袭。三十年,令土官无子弟,而其妻或婿,为夷民信服者,许令一人袭。”[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89“土司袭职”条载:“顺治初年定,土官无子者许弟袭,无子弟,许其妻或婿、为夷民所信服者一人袭。”[9]这就凸显了土司应袭对象有土司家族子弟、族属、妻婿等,主要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叔侄相袭、妻婿承袭、同族袭职、母女袭职等承袭次序。明清政府均加强对土司承袭次序的控制,从明代“因俗”而定土司应袭者,到清代土司应袭者不得僭越嫡庶,国家对土司的管控有序化,这表明王朝国家管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能力加强,治理体系也逐渐完善。
4.赐予承袭土司多种信物
明清政府授予各地土司职衔后,为表示土司成为朝廷命官,会赐予诰敕、印章、号纸、驿传玺书、虎符、金(银)字圆符等信物作为凭证。这也成为明清政府管控土司以及土司地区的具体措施之一。如清代“号纸”,不仅是中央政府给某一应袭土司的任命文书,而且是土司承袭文书中的重要凭证。号纸是清王朝赐予应袭土司的信物,且一直贯穿清代始终,如云南永北县属蒗蕖州土知州应袭阿鸿钧宗支图中有“因顺治十六年兵变,遗失号纸,递延未经请补号纸”“后请颁复土知州号纸印信”的句子,在“亲供”中有“颁发号纸一道任事”“至顺治十六年内,兵燹遗失号纸”“并请给号纸印信具详”“颁发蒗蕖州土知州阿为柱号纸一道,并发道字一千四百九十三号纸铜质印信一颗,只领任事”“于是年九月内,接奉号纸一道”“于光绪二十四年奉发号纸一道,准阿继祖承袭蒗蕖土知州职,只领任事”[10]等句子,由此证明清代土司均有清王朝赐予的号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了清王朝对应袭土司号纸的颁发、填写规格与内容、换给、补给、注销等规定,这是体现王朝国家治理和管控各地土司承袭职位的重要法律依据。
(三)中央政府管控土司权力
明朝建立后,在沿袭元代土司制度的基础上“大为恢拓”[11],清代在明代土司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土司制度,使王朝国家管控土司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央政府对各地土司的权力控制是一种软硬结合的控制,大凡常规性权力管控和限制性权力管控,属于软控制,这种控制或以制度为基础的治理,包括行政管理、考核、奖惩、限制、禁止等;凡是剥夺性权力管控,则属于硬控制,这种控制大多以制度为前提的治理,包括直接使用暴力镇压,或以威慑为后盾的法律制裁等。从明清政府利用土司制度管控土司权力的角度看,主要有三类。
1.中央政府常规管控土司权力
明清政府对各地土司权力的常规管控,大多是以土司制度为基础对土司的治理或管控,根据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一是授职。自明代开始,中央政府对土司的授职并无一定标准,特别是对广土巨族的土司,基本上是对元朝归附的故官授职。明代既有以土司“忠勤”情况而决定授予土司官职的大或小(如保靖安抚使跟随朱元璋战败陈友谅有功,升为保靖宣慰司),也有按照新归附少数民族首领辖地之大小、辖区民众之多少而授予官职(如云南湾甸刀氏土司在与中央政府博弈之后)。据文献载:“这湾甸地方,差发比孟定那几处都少,当初他做长官司,衙门也小了。如今升做湾甸州,长官刀景发升做知州,与他金带;副长官曩光升做同知,与他花银带。都与他诰敕,著礼部铸印去。”[12]可见,明代中央政府对各地土司的管控,较之元代已明显加强。清初,土司授职就是“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13];雍正年间之后,土司授职出现两种现象:支庶中的优秀者,可授职;土司分其地、降其级而授职。
二是升迁。明代各地土司盼望官职的提升与调动,或地位与身份的提高,总是千方百计、绞尽脑汁;而中央王朝为了笼络各地土司,给他们一点甜头,也会对“有勋劳”的土司进行“升赏”。明代各地土司升迁途径,或军功,或忠勤,或进献,或纳米升授。如永顺彭氏土司在正德年间、嘉靖年间都以献大木而得以升迁[14]。明代无论是对各地土司升品级,还是加流官名或加虚衔,都凸显了民族平等政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是奖赏。明清政府对各地土司除了朝贡赏赐之外,不乏论功行赏。《大清会典》载:“凡土官有功则叙。经征钱粮,一年内全完者,督抚奖以银牌花红;能严行钤束擒剿盗贼,一应案件于一年内全完者,加一级;完结过半者,督抚嘉奖;军功保列出众者,加衔一等。头等者,加一级;二等者,纪录二次;三等者,纪录一次。”[15]清代对有特大功劳的土司赏给虚衔、花翎、顶戴以及勇巴图鲁等。这是王朝国家以荣宠笼络各地土司的一种举措,也是王朝国家对土司的一种治理术。
四是惩罚。明清政府对土司的惩罚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通过惩处某个土司,以达到教育其他土司的目的,即“以儆效尤”“反叛必诛”。如明代万历年间,在今贵州遵义地区爆发的那场“平播之役”,其实就是“反叛必诛”的真实写照。“平播之役”的最终结果很多史籍均有载,如《明史》有“应龙仓皇同爱妾二阖室缢,且自焚。吴广获其子朝栋,急觅应龙尸,出焰中。贼平。计出师至灭贼,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斩级二万余,生获朝栋等百余人。化龙露布以闻,献俘阙下彩应龙尸,磔朝栋、兆龙等于市”[16]的记载。明王朝将违法土司绳之以法,彰显了明政府对土司的管控更严格,对土司地区的治理更有效。清王朝对土司的惩处主要有“参革”“治罪”“降调”“罚俸”“狱枷”“杖责”等,其处罚比明朝更严厉,其目的在于迫使土司就范。此外,明清政府的土司制度治理还包括宽宥、抚恤、考核等举措,此不赘述。
2.中央王朝限制土司权力
明清时期各地土司权力相对于中央王朝的权力而言,也仅属于土司地区基层社会权力,这种权力受制于中央王朝和土司制度的制约。曾任广西巡抚的甘汝来,于乾隆年间针对当地“恶习不见少移,官则贪渔无厌,民则抢杀频仍”的实情,在《条陈土司利弊议》有直陈土司利弊之记载[17]。王朝国家想要约束土司滥用权力,仅依靠道德力量的作用效果是有限的,需要依靠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土司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土司权力的滥用。明清时期,土司作为土司地区最高权力拥有者,一方面借助“王权”维护地方统治地位,一方面又以王朝国家给与的权力治理基层社会,但各地土司的权力自始至终都受到中央王朝的限制和制约,换言之,王朝国家始终利用土司制度对各地土司予以治理,不让他们信马由缰。
明清政府为强化对土司承袭的限制,规定了许多“禁例”,若违犯中央王朝的规定就不准承袭土司职位。诸如仇杀、兴兵、变乱以及嫁娶违例越省,且与他类结亲及与外夷往来者,子孙永不许承袭。明清朝廷根据土司犯罪程度,规定不准亲子承袭或需另择族众拥戴之人;对犯特定罪被革职的土官,由其本支伯叔兄弟、兄弟之子或其他夷众素服之人来继承。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奏准:“土官袭替定例,必分嫡次长庶,不得以亲爱过继为词,如实系土官身故乏嗣,除笃疾残废,及身有过犯,与苗民不肯悦服之人,例不准请袭外,其承继之子,仍论其本身支派。如非挨次承袭者,不准袭职。”[18]清代对土司承袭制度的管理是极其严格或者说是极其严苛的,当然也收到了极为显著的效果,减少了明代那种由争袭而引起战乱的现象。
3.中央王朝剥夺土司权力
明清政府除了限制土司权力之外,还以各种名目剥夺土司权力,如土司的生存权、行政权、财政权和司法权等,并将土司的有些权力收归流官。
一是剥夺土司的生存权。它是包括生命在内的诸多权利的总称。明清两代凡是犯“谋反”“谋大逆”“谋叛”的土司,不仅要剥夺土司的生存权,更要剥夺土司的生命权。如《大清律例》之《职官有犯》“条例”中明确规定:“各处大小土官,有犯徒、流以上,依律科断。其杖罪以下,交部议处。”明清时期对于犯徒流、迁徙、充军的土司,中央王朝要将他们迁徙到远离原辖区的地方,使他们脱离原有的生存环境,不仅失去了各种权力,而且还有新迁徙地方官员的监督管控,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生存权的剥夺。
二是剥夺土司的行政权。明清政府或通过土司管辖范围与人口调整,或通过改为省级布政司直隶,或通过改属流官政府及军事卫所管控,或通过分地新置土司政区和流官政区,以此逐渐缩小土司的势力范围,中央政府通过土司制度治理,从而使国家秩序在土司地区不断得以推进。而随着明清中央王朝行政秩序的推进,各地土司的内部斗争也逐渐受到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清史稿》卷一百十七“广西土知州”条载:“其不管理土峒者,正六品土官二人,从六品、正八品、正九品土官各一人,从九品土官一人,未入流土官二人”;同卷“云南土知府”条载:“其不管理苗裔村寨者,土通判二人,丽江府、鹤庆州,各一人”;同卷“贵州土同知”条也载:“其不管理土峒者,正六品、正七品土官各一人,正八品土官三人,正九品、从九品土官各二人”。[19]这些土司既然不管理土峒和村寨,也就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只是名义上的土司,因为代表土司实施行政权力的凭证——信印已回收且“咨送礼部销毁”。这说明清代土司的权力越来越小,中央政府对其控制越来越强。尤其是通过分其地、降其职、限其权、虚其衔等举措的实施,使国家治理能力不断增强,有效地维持了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
三是剥夺土司的财政权。土司地区“举凡辖地之户口、钱粮、税收,皆取决于一人之意志。”[20]土司拥有辖区的财政权,指王朝国家规定各地土司应该向中央政府上缴赋税。明清中央王朝对各地土司应该上缴多少赋税都有明确规定,《万历会计录》对各地土司缴田粮就有明确记载。实际上,中央王朝规定土司在其辖区内征税的数额极其有限,但土司在辖区内征税的税名及数额并不确定,有时对辖区内各族民众过度盘剥。因为土司在其辖区内拥有征收赋税的权力,他们巧立名目,在辖区内民众中盘剥是司空见惯。如《缅宁厅革除土司弊政禁约碑》所言:“勐勐土司积习,除征收钱粮正供之外,凡土司一切冠婚丧祭经营修理,无不摊派于民,以致民怨沸腾,动辄滋事。”[21]土司不仅拥有辖区内所有田土的征税权,而且还负责征收差发银等。因此,土司负责征收的钱粮交与地方官府只是他们征收的一小部分,土司在其辖区内征收钱粮多大为浮征,时有征收几倍甚至十数倍之多。由于各地土司征税名目繁多、税期不定,造成土司辖区内民怨沸腾。因此,中央政府利用土司制度治理土司辖区,逐步剥夺土司的财政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现有保存的碑文和略写历史文献中,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
4.剥夺土司的司法权
“土司之治,为专治一人之治;土民有讼,听其裁判;土民有罪,任其处罚。”[22]由此可见,土司在其辖区内拥有司法权。这里的司法权是指各地土司根据土司制度赋予他们在其辖区内针对具体案件的审判权力。司法权是各地土司的核心权力之一,土司在其辖区掌管着司法权,承审辖区内的案件多凭个人喜好,如果土民不服从土司判决,土司“即将其人烧杀或活剐,或五牛分尸”[23]。在清朝中后期,清政府限制土司的司法权,将土司辖区的命盗等重大案件交由流官审理,土官只保留审理民事案件的权力。如《巴塘善后章程》在“设官”条规定:“巴塘从此改设汉官,管理地方汉、蛮百姓及钱粮、词讼一切事件。”[24]该章程在“词讼”条规定:“凡汉、蛮、僧、俗、教民人等大小词讼,皆归地方官申理,无论何人不得干预其事。”[25]改土归流后因各地残存的所有土司均由地方官管控,故土司辖区内的讼诉案件也不得随意处理,小案或自理,大案则必须报流官。[26]
王朝国家运用土司制度治理,其实质就是土司制度赋予王朝国家的权力,这种制度权力源自于王朝国家在土司制度中的身份和地位,这种身份和地位是王朝国家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时被赋予的,这种制度权力是通过土司制度治理主体——王朝国家实现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直接治理和管控而实现。
二、地方政府的土司制度治理
中观视域下的土司制度治理是主体,主要包括行省、府、州、厅、县等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机构,这是王朝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在明清时期西南、中南及西北的一些地方政府,他们作为联结中央政府与土司地区、王朝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中间政权机构,在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环节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下情上达的枢纽作用。[27]土司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是王朝国家治理的实施者和实施主体。
(一)地方政府土司制度治理的权力结构
明清政府在实施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历来采用的是“条块”权力结构形态。其中,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属于“条条”结构中的权力中心,这些部门负责王朝国家土司制度治理的重要资源调控及其分配;西南、中南及西北拥有土司的省份属于“块块”权力结构中心,这些“块块”掌握着地方治理的权力,是王朝国家精神传达贯彻到地方和基层的践行者。王朝国家的“六部”是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政府、土司机构的一根有力的线索,并通过王朝国家的制度制约促进地方政府贯彻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
明清时期在地方上属于王权系统的主要是行省——府、州、县(或厅)——土司机构系统。从明清两代广西王权系统的设置可见,王朝国家通过王权系统把国家意志传达贯彻到基层组织和地方社会。在王朝国家自上而下的王权系统中,明清时期拥有土司的省份自觉形成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从行省到府、州、县(或厅),再到土司机构的整个王权系统,既是国家意志的贯彻者,又是土司制度治理的执行者,也是治理效能的担当者。王权系统保证了国家意志对政府的统领,通过国家意志、王权系统和土司制度治理的系统化运作,王朝国家主导着土司制度治理的方向。
明清时期在拥有土司的省份设置地方基层权力机构,实质上是中央王朝设立在地方并代表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地区的组织机构。从明清政府在土司地区建立的地方基层权力系统看,制度名称主要有里甲制、保甲制,这些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王朝国家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有效治理,其地方基层权力系统的建立是王朝国家土司制度治理有机整体。里甲、保甲、粮长是明清时期土司地区基层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王朝国家通过里甲、保甲等基层权力机构,逐步使国家权力深入到土司地区的阡陌之间。这套纵向地方基层权力系统,虽然层级很低,但在权力体制中十分“接地气”,不仅是土司制度治理的践行者,而且是贯彻执行国家意志的强力保障者,保证了王朝国家意志在土司地区基层社会的纵向畅通和土司制度治理的有效执行。
(二)地方政府土司制度治理的主要举措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意志贯彻执行的强力保障者和土司制度治理的践行者,他们在土司制度治理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现有文献看,明清时期拥有土司省份的地方政府,在制度治理过程中的主要举措有四种。
1.落实土司制度治理的规章和决策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达成,无疑是各地土司与中央王朝政治博弈的结果。政治博弈之后双方约定:各地土司承认中央王朝执政的合法性,自觉遵守承袭的各项规定,认真履行王朝国家交办的朝贡、征调、纳税以及守土、治理地方的各项任务,中央王朝则认可各地土司在其辖区治理的合法性,给予各地土司诰敕、印信、号纸等信物。其中,中央王朝承诺各地土司享有世代承袭的权利,是各地土司是否愿意完成各项任务的根本保障。作为地方政府的各级朝廷命官,在土司地区任职,必须认真落实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各项规章。
特别是在改土归流过程中,地方流官基本上是义无反顾地执行王朝国家的改流决策。无论是明代被动改土归流的90余家土司,还是清代雍正主动改土归流的160余家[28]土司,以及清末在川西地区强制改土归流,地方流官都是积极主动配合王朝国家的决策,认真执行王朝国家的决定。裁革土司是明清两代的基本决策。明代以各种理由被裁革的土司并不少,其原因或“人少官多”“地狭民稀”,或土司犯罪被裁革。如贵州乌罗土府因原隶于其下的治古、答意二长官司叛乱被废除,所辖仅剩三长官司,不足以立府,因此于正统三年(1438年)被裁革;云南陆良州和贵州普定府因土官犯罪而被裁撤。清代往往是“因事”“滋事”“缘事”“因罪”等大量裁革土司。《清史稿》之《土司四》载,贵州思南府蛮夷副长官李慧于雍正八年(1730年),“缘事革职”[29];思明州土司观珠于雍正十年(1732年)“以罪参革,改流”[30]。朝廷命官在处理土司“自愿”或被迫改土归流事件时,均付出艰辛的努力。尤其是王朝国家以武力征剿、平定广土巨族的土司(如平播之役、奢安之乱等),土司作垂死挣扎时,有的地方流官甚至在征剿土司过程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提出土司地区制度治理的对策建议
土司治理系统在实施过程中弊病较多,问题在所难免。因此,在西南、中南及西北的封疆大吏们不时给中央王朝提出土司制度治理过程中的一些对策建议。王廷相在《与胡静庵论芒部改流革土书》中提出“复芒部土官”的建议,朱爕元在《查明蜀省二界疏》《水西夷汉各目投诚措置事宜疏》中分别提出划分“水蔺地界”和“措置投诚把目”的问题,桂萼在《修省十二事疏》中提出“顺夷情”的建议,王家屏在《答蔡龙赐年丈》中建议要分清“田州疆土”,这些对策建议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决策。特别是清代的鄂尔泰、迈柱、张广泗、甘汝来、那彦成、高其倬、尹继善、岑毓英、赵尔丰、傅嵩炑等官员都对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等问题向清王朝提出过很好的对策建议,此不赘述。
3.协调王朝国家与土司地区社会关系
对于明清时期的统治者来讲,维护王朝国家的稳定是其在执政期间追求的根本目标,无论清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还是明代汉族执掌政权,无不如此。明清两朝执政之后,凡各地土司主动“归附”“内附”中央王朝者,都会实行招抚政策以尽快安定土司地区,这是王朝国家安邦治国的首要政治任务。如明代嘉靖年间吏部尚书桂萼希望对两广土酋实现有效的控制,为明朝建立巩固的边疆和屏障,在《修省十二事疏》中针对“广西有田州之征、川贵有芒部之役,劳师费财、生民已不胜苦,今四川又有播凯之事”[31]的实情,提出“顺夷情”的主张,以缓解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官员在王朝国家的授意下,为“顺夷情”,千方百计协调王朝国家与土司地区社会关系。
4.更替土司地区基层社会权力
明清时期各地土司作为中央王朝敕封的朝廷命官,官衔大小不一。但各个广土巨族的土司,在所辖区域内,掌握兵权,管理民政、财赋田粮,设衙门、公堂、监狱,可以拘拿、刑讯,甚至处决反抗他们的人。对于反抗中央政府的土司,王朝国家会严厉镇压,如明王朝平定播州杨氏,杨应龙军事机构中的军师、谋士、督军总管、内司总管、提调巡警、苗头总管、各里头目、领兵议事之人,均不同程度的遭到镇压或处置,播州杨氏土司家族权力以及基层社会结构性权力全部被王朝国家新设置的权力机构所代替。据《遵义府志》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以播州宣慰司杨应龙叛,明王朝命李化龙率师讨灭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四月,明政府分播州杨氏土司原辖地一分为二:属贵州管辖者为平越军民府,属四川管辖者为遵义军民府。改真州长官司置真安州,改播州长官司置遵义县。以播州杨氏土司所属旧夜郎县地置桐梓县、湄潭县;以真州长官司所属旧绥阳县地置绥阳县、龙泉县。以播州宣慰司所属仁怀里及别领长官地置仁怀县。遵义军民府计领真安一州,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真安州复领绥阳、仁怀二县隶四川布政使司。原播州土司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权力全部被流官所接替。
(三)地方政府土司制度治理的成效
制度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它具有管根本、管长远、管全局的作用。无论什么制度,最终要落到实处,必须依靠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是王朝国家运用土司制度治理的践行者,他们是实现王朝国家意志的核心人物,是制度治理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
1.地方政府官员对土司制度治理的正确认知
地方政府官员对土司制度治理的认知是土司制度能否产生治理成效的前提。清道光年间迤西道胡启荣对土司制度治边有深刻的认知:
伏思边吏治边,固以协体制为急务,而尤首以安边为急务,盖协体制犹虚而安边乃实也。若边不安而尚有何体制之可协乎,盖各边情形不同,总须因地制宜,宜则边安,不宜则边不安也。……又如腾越七土司,除缅甸呈进例贡,并该国通知边事有缅子来至内地外,其平日并无缅子来至七土司地方盘踞,若忽有到来盘踞者,亦应立驱使去,方为得体,此不能不协体制以安边之一办法也。[32]
在土司制度与“安边”的问题上,“边吏治边,总以安边为主,而安边尤以因地制宜为主。”[33]应该说,胡启荣等地方官吏对土司制度治边的认识是很到位的。
关于土司制度的弊端,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认识,他们认识到土司制度已经腐朽,不实施改土归流就不能推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鄂尔泰是前人思想之集大成者,其提出的改土归流建议最为合理并被雍正皇帝首肯,他的改流主张更为坚决。如言“苗倮逞凶,皆由土司,……若不尽改土归流,……大端终无头绪,……滇黔必以此为第一要务。”[34]于是,当土司制度不能很好地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时,改土归流就在西南和中南地区大规模的推行。
2.地方政府官员对土司制度的有效运行
地方政府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自觉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运行模式。这套运行模式包括宣传制度、推行制度及监督考核制度。明清政府制订土司制度后,地方政府要向各地土司宣传,使土司家族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如清人黄炳堃等人辑录的《土司例纂》,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土司制度的单行本,其中诸多内容与土司直接相关。作为制度治理来讲,对土司进行考核也是十分必要的,且还必须用于土司继续任职、承袭的过程中。鄂尔泰在《分别流土考成疏》上疏:“流官固宜重其职守,土司尤宜严其考成”。[35]只有将考核土司的任务和压力层层传递,才能消除地方政府的惰性,在制度治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3.地方政府官员对土司制度治理的反馈
明清时期拥有土司的地方政府的制度治理,不仅作用于王朝国家的政府系统内部,而且广泛作用于土司地区的社会领域。因此,制度治理反馈机制对于提升拥有土司省份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不可或缺。如明代万历年间巡抚云南的萧彦,时逢明王朝在陇川用兵,在“副将邓子龙不善御军,兵大噪,守备姜忻抚定之。而其兵素骄,给饷少缓,遂作乱。鼓行至永昌,趋大理,抵澜沧,过会城。彦调土、汉兵夹攻之,斩首八十,胁从皆抚散”[36]的情况下,他向万历皇帝上《敷陈末议以备采择疏》中“议袭替以慰夷心”“议正伦以杜夷衅”“议定疆以杜强暴”“议旌别以风远人”等四条,真实地向明王朝反馈了当时滇西地区的有关情况。
总之,土司制度治理是推进王朝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取得治理效能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制度治理只有通过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与土司制度治理的主要举措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制度治理成效。西南、中南及西北拥有土司省份的地方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作为王朝国家治理的一种“软治理”形态,只有在土司制度与治理体系密切协作的环境下,才能真正发挥土司制度治理应有的作用。
三、土司地区的土司制度治理
明清时期各地土司作为王朝国家权威的地方象征和中央政府行使地方权力的“代理人”,他们在各自辖区的地方社会,不仅注重土司机构自我运行,而且还与官民组织配合运行、与土司宗族协同运行。在一定意义上讲,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土司制度治理不仅是与王朝国家维持良好关系下的治理,而且是在上下互动、多方协同情势下的治理。
(一)土司行政权力结构
土司权力结构是基层社会权力组织体系、权力配置,是在不同职级及不同权力之间具有复杂关系的系统工程。地方基层社会权力既是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也存在权力制衡关系。它在土司制度治理过程中受伦理道德和制度双重约束,以达到有效治理土司地区的目的。明清政府与各级土司的权力结构呈“双塔”状,即中央朝廷、行省、府州县流官政府共同构成了“王权”,各地各职级土司形成严密的“土司政权”,共同治理边疆地区。如《滇事杂档》记载了云南土司行政权力结构各级主体有宣慰司、宣抚司、土州、长官司、土把总、土舍、土巡检、弁目、舍目、寨长、夷目等,这些名称是由具体的土司政权权力主体决定的,并不是土司政权机构的固定称谓。《思茅沿边开发方案》载有:“宣慰司署设四大头目,分管民、财、侍卫、仪仗,设一总头目,为宣慰近畿八寨之主管,下各乡设若干小头目。各勐土司署亦仿宣慰署制设四大头目,每勐土司划分为若干区,每区设一总管、二助理,每区各分数寨,每寨设头目。各勐土司行政,小事自己作主,大事秉承宣慰办理。……数百年本此统治,已养成人民一种行政上之习惯。”[37]土司借助“王权”获取权力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从而维护自身在地方上的统治与权威,在地方流官的监控下实施权力与治理土司地方。基于国家认同与政权合法化,形成了土司行政权力机构。
(二)土司机构自我运行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和国家治理都是在“国家在场”的生境中运行,土司地区的土司制度治理时时处处与王朝国家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各地土司,长期处于王朝国家的“核心圈”与“边缘圈”的中间地带,属于“中间圈”的层次。正因为他们没有与帝国处于“中心—边缘”的对立状态,而是陷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所以,明清时期各地土司始终与王朝国家保持着互动关系,以便土司机构能够正常运行。
1.执行国家的成文制度
土司制度成文法是在“因俗而治”和“依法而治”双重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制度或法规一经皇帝批准就颁行全国施行。明政府对各地土司的官职级别、辖境范围、承袭、隶属、贡赋等制定的成文制度不尽相同。清代的土司制度更加严格,特别是在土司承袭方面,较明代规定更加详尽。明清政府的成文制度,是各地土司必须遵循的法律准绳,它涉及职官、职衔、信物、授职、承袭、朝贡、纳赋、征调等内容,各地土司必须严格执行王朝国家的这些成文制度,尤其土司承袭、土司征调、土司贡赋是重点,否则就有被王朝国家裁革的危险。如服从中央王朝的征调,是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表明,明代永顺被征调56次,石砫土司和秀山土司均被征调19次,各地土司土兵参加军事征调不仅次数很多,而且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2.制定民间法协助运行
土司制订的民间法主要包括土司家族谱牒、乡规民约、习惯法等,它是在国家上位法的基础上规范土司辖区内各族民众行为的民间法。如《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民刑法规》有犯上法规,有关家奴的规定,破坏私人财产及农业、婚姻、财产继承及债务清偿、有关经商及交通的规定,侮辱妇女、偷盗、斗殴杀人等法规。[38]这些诸多法规,是古代傣族封建领主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这些民间法的制订与运行,是王朝国家制度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基层社会的有力补充,有利于协助土司机构开展权力运行。
(三)土司族内协同运行
土司家族内权力结构十分稳固,具体表现在祠堂、族谱、族规、族长等诸多因素的协同运行机制,同时族内权力与中央王权相互连接,处于国家语境之内。
1.土司宗族组织要素协同运行
各地土司宗族与全国各地宗族一样,是土司家族的自我管理,可称为土司家族自治社会。土司宗族是一个血缘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以男人为主体,取得族籍才具有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在土司宗族共同体中,以族长或族正为核心人物,族谱、族规、宗祠、族田为管理手段,从而建立起严密的宗族社会人际关系,这就是宗族制度。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宗族组织大多是通过族规来调整宗族关系,维持土司宗族内部的秩序和尊卑伦理,进而起到加强土司政权统治和维护土司辖区社会稳定的作用。土司宗族之所以有着很强的内聚力,是因为它有着相互联系、控制力强的宗族内在结构。土司宗族组织的各种功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障土司宗族成员的各种基本需求,因而土司宗族组织对于族众来说,是可以信赖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社会群体组织。[39]明清时期土司地区宗族组织的稳定状态除与宗祠、族谱、族长、族田等诸多要件要素密切相关外,宗族规约的作用不可小视。如施南覃氏土司家族的“家训”有 “孝父母”“和兄弟”“厚宗族”“睦乡里”“保祖茔”“勤读书”“端士品”“重农事”“尚节俭”“解仇忿”“慎交游”[40]等内容,这些规定促使土司家族和睦相处,维护社会稳定。可以说,祠堂、族谱、族规、族长、族田等诸多宗族组织要素是加强土司族内协同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
2.土司族内统治阶层协同运行
土司族内权力结构由正印土司和土舍、土目、土弁等族官共同构成。正印土司指符合承袭次序的应袭者通过朝廷制定的土司承袭程序后,直接敕封的宣慰使、安抚使、长官司、土知州等,他们处于土司家族权力的顶端,即土司家族的“大宗”。而土舍、土目、土弁等由土司同宗兄弟担任,被分派土司封地,与土司共同治理土司地区。他们的行政职级虽然很低,但对于土司家族权力结构而言,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起着代理土司的作用。如《滇事杂档》中称呼的“族长”“族祖”“族叔”“族弟”等人,他们在土司家族虽未能担任行政职务,但其身份、地位或辈分较高,同样属于土司家族的组成部分。即便是“族舍”“族目”“族弁”等职,虽行政级别较低,但他们在本家族中却拥有重要权力。正是这些身份、地位或辈分、职位不同的群体,共同构成了土司家族内部的权力结构,且相互协同运行。
3.土司族内被统治阶层协同运行
土司族内被统治阶层主要有土司族人(如《滇事杂档》中称为“族人”“同族”“庶族”等)、土司和族官直接管理的村寨民众,以及土司地区的佃户、佃民等,他们同样在协同土司家族权力机构运行。土司家族权力在土司行政系统和土司家族系统共同管理下逐渐形成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形结构,即正印土司、族官、土民共同构成土司族内权力运行系统。土司借助土司权力与“王权”塑造合理、合法的地方统治者形象,土司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权力网络,从而形成边缘地区的政治中心。在这个“双中心”与“双边缘”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体现了土司地区不同身份、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权力阶差。[41]
四、结 语
从明清时期“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看,或许并没有实现明清政府土司制度治理的预期,但它却体现了“多元共治、上下互动”理念,并为明清政府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讲,土司制度治理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民族地区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第一,“依法治国”是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国家治理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因俗而治”是明清时期王朝国家根据土司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程度及宗教信仰等制定的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民族政策。[42]但纵观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实际情况,“因俗而治”的实施,其目的在于解决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调整中央政府与土司及土司地区、土司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王朝国家由“因俗而治”到“依法而治”的转变,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是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根据我国民族自治地区目前的情况,就国家层面来讲,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尊重和保障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各族民众的合法权益,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但是,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也必须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行使自治权,这是我国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国家治理、实行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
第二,国家制度建设是加强国家治理的根本。明清中央王朝为维护其统治政权及土司地区的长治久安,设计了一套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礼仪等在内的一系列典章制度。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司制度逐渐背离了中央王朝设计的初衷,不仅在土司地区难以为继,而且也没有实现土司制度治理的目标,但明清中央王朝经过不断补充、丰富与完善,已经成为相对完备的治理体系。即便这套制度由于王朝国家的性质及制度本身的规定性无法长期使用,最后只能用改土改流的举措来推动制度治理的历史进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应当吸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必须加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个层面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三,历史上土司地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经验值得借鉴。明清时期的土司地区多为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关系极其复杂,多元共治历史悠久,如官方基层组织、官民共建基层组织以及土司宗族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很有特色。这种“多元共治”的特点在于多元性。王朝国家的制度治理有利于规避和调控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的冲突,构建府州县行政机构、官方基层组织、官民共建基层组织以及土司宗族组织四者协同共治体系,期求实现国家主导、地方负责、社会协同、土司宗族参与的国家治理格局的目标。民族地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也必须围绕社会治理主体边界划分与权利配置制度化,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基层自治方面,构建民族纠纷协调、公共安全建设、社会治安防控、社区治理、社会心理服务等五大体系,构建一套与民族地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相适应的制度治理体系。这种“多元共治”模式,不仅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模式提供历史经验,而且也将成为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参见李良品,韦丽芳:《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三个问题》,《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②参见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李良品:《土司承袭制度中国家治理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李良品,翟文:《明清时期土司承袭制度中国家治理的举措及特点》,《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贾霄锋:《明清时期土司奖惩制度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王琨,李良品:《国家治理视阈下元明清土官土司承袭制度的文书与信物》,《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