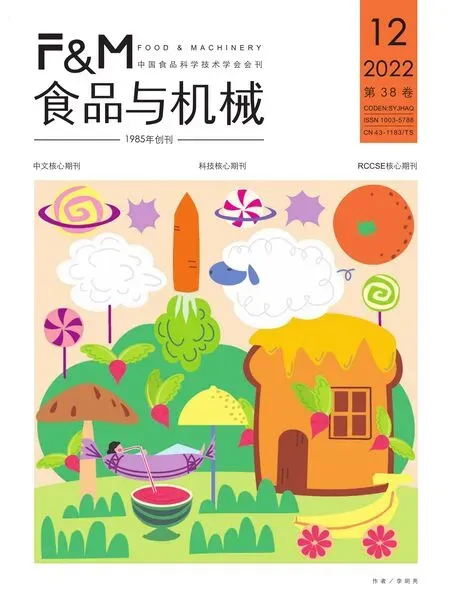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创新机制研究
2022-03-12李曦
李 曦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与传统食品经营行业相比,网络食品具有经营方式灵活、门槛低、信息不对称、制作过程不透明等特点,但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随着新零售平台的注入和网络食品市场规模的拓展,网络食品安全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2016年,中国率先在《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明确“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义务”概念,并先后出台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对网络食品安全制作过程、经营许可等方面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是20世纪末,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提出的概念,该理念强调从社会整体角度看待和解决问题,反对化约主义的还原论以及孤立地看待问题的一种范式,旨在解决政府治理碎片化和分散化造成效率低下的弊端。整体性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被广泛应用于存在碎片化困境领域。整体性治理是立足于公民现实发展需求,运用信息化工具,整合多元治理主体,从而实现治理资源有效性以及治理结果高效性的统一。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范式,有助于回应公民对更好、更快、更优质服务的追求,从而解决互联网背景下,社会治理存在的缺陷。
中国学者对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和安全监管策略。在监管主体方面,存在监管主体力量薄弱、监管理念片面、监管政策执行力度不足、监管权责不对称等问题。为此,应当重塑权责机制、依托技术支持,实现智慧化监管[1]。在监管体制方面,存在专业监管力量缺失、源头风险控制低效、新型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突发等问题[2]。在监管执行方面,田彩霞等[3]提出中国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层面依旧存在法律约束松软、行政监督乏力、监管方式单一、监管执行效果差等问题。在监管模式方面,有学者[4]从监管模式发起、分工和保障3个层面提出了协同监管与信息共享监管的“双效合一”模式,该模式的运用推广有助于促进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高效率、可持续。在监管机制方面,有学者[5]基于反身法理论论述了“组织型治理策略、信息型治理策略、协商型治理策略”在中国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可行性与效能,并构建了制度保障、平台责任、社会共治、信用评价与政府监管五大机制。
综上,中国学者对于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研究,更多侧重客观现状的表层分析,运用跨学科的相关理论对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深层次研究较为缺乏[6]。基于此,研究拟以公共管理学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政策执行、监管主体、监管理念、监管问责四大层面论述中国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样态,并从以上层面探寻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创新机制,为提升中国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提供借鉴。
1 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样态
2016年10月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办法》的出台实施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在食品安全法中明确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义务和相应法律责任的国家;同时成为第一个专门制定《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规章的国家,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2017年1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原则。
由于网络食品交易具有隐蔽性和虚拟性的特征,消费者以互联网为消费媒介,与商家之间极易产生信息不对称,给网络食品经营带来了寻租空间。同时,食品安全维权意识还没有在消费者中完全普及,导致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样态:政策执行存在“象征性”问题、监管问责存在“被动性”问题、监管问责存在“被动性”问题。
1.1 政策执行“象征性”
政策执行的“象征性”是指,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于部门利益考虑,实施替换性执行、附加性执行以及选择性执行,最终导致政策被象征性执行,且政策执行效果流于表面,未达到政策制定的战略高度[7]。政策执行的“象征性”在主观方面体现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与协同片面,是导致执行流于形式的关键。如,在跨国网络食品安全的监管过程中,需要调动市场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局、信息化局等多部门的力量[8]。但是,由于多部门之间的执行效能不足,协同性缺失,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多部门或者按照自身理解的方式开展政策执行,或者由于协同不足而导致政策被搁置。政策执行的“象征性”在客观层面体现在稽查执法方式有待提高。相较于传统食品安全监管,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由于其经营范围、账户信息较为隐匿,交易双方物理空间分离,所以对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专业技术有了更高的要求,依据传统模式实施行政区划下的统一监管有待更新。
1.2 监管主体“碎片性”
监管主体的“碎片化”主要体现在监管主体外部的单一性与内部的低效性。首先,在监管主体外部中,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主体除了政府外,还存在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第三方民间力量。但是在实际监管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力量缺乏监管的合法性基础,处于临时性与边缘性的地位[9]。其次,在监管主体内部中,2013年机构改革之后,卫计委负责食品安全标准设置工作,质检总局负责食品安全检疫、生产等工作,而工商总局、商务部负责部分监管职能。而在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由于涉及部门较多,权利配置复杂,所以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容易出现权责不明、相互推诿的情况。虽然多部门出台《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但是由于缺乏当地政府的牵头主导,多部门尚未实现行政资源集中,导致监管效能低下。
1.3 监管问责“被动性”
完善的权责体系对于监管责任的落实至关重要,但是由于科层制的层级结构限制以及行政体制条块分割惯性,导致中国网络食品安全问责机制的“被动性”[10]。首先,网络食品安全问责对象单一。长期以来,中国网络食品安全问责的对象主要为食品安全行政主管部门,而单一化的政府问责机制难以破除“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的体制性障碍。其次,网络食品安全问责有失偏颇。中国现行网络食品安全问责运行侧重对行政相对人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打击,而对行政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不作为”“轻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失责行为问责力度较低,行政问责对象有失偏颇,导致了食品安全问责浮于表面,“出了问题才发现,出了问题才治理”现象愈演愈烈。最后,网络食品安全问责机制不健全。网络食品范围较广,内容宽泛,涉足的行业与领域众多,在生产、经营和流通多个环节中涉及的行政区域、政府部门较多,责任追溯难以落实,影响了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问责绩效。
2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网络食品安全监管路径创新
2.1 监管问责整体性,重塑权责体系
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要从政治责任、管理责任和法律责任层面构建整体性问责机制。网络食品安全问责整体性就应构建以党管干部为联结,混合性党规为载体,以党规国法为分工,党领导一切为效能的党政同责问责机制。首先,在党委层面,党政同责确立了党委主导的问责机制,地方各级党委主要承担领导责任,开展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工作,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规定下,负责落实党中央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肩负食品安全监管使命,对地方党委问责主要采取通报、诫勉和纪律处分等党内问责方式。其次,在地方政府问责方式上,党政同责确立了行政处分、人大问责和司法追责机制。根据中国层级监督机制,上级政府可对其主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管不利情况提出行政处分。地方各级人大听取、审议食品安全检查和相关规定之外,还可以对违法失职人员实施质询、撤销职务等处分。
2.2 监管主体整体性,搭建参与网络
整体性治理理论更加重视在不消除专业分工、组织边界的情况下,通过长期化的制度协作,实现多主体的协同,从而发挥整体效能的作用[11]。因此,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整体性探索就应该实现政府内部、部门之间以及公私组织之间的跨界合作,构建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企业、公众、基层组织、第三方机构、利益相关者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一方面,要推动食品安全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完善食品安全专业科研机构的设置,跟踪监测网络食品安全领域前言性问题,为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权威性、科学性指导。同时,促进高校与民间组织基础研究的科研合作,充分发挥“高校—企业—民间组织”监管合力作用,为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专业性指导。另一方面,发挥行业协会与社会监督作用。调动消费者、社会组织、媒体等多方力量参与社会监督,完善监督平台,实现有奖举报机制,拓宽举报力量。
2.3 监管执行整体性,重构执行网络
希克斯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实现治理对象由分散走向集中、由部分走向整体、由破碎走向整合。”[12]因此,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执行整体性治理就需以协调、整合和责任为治理机制,重构执行网络。首先,强化中央权威,中央要充分发挥顶层设计作用,出台国家层面的网络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法规,各个行政区域可以在中央总体政策的引导下具体措施。其次,加强事前预警,增强政策执行的技术性。运用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开发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云监测、云分析、云预警”等功能,实现网络食品安全事前迅速预警、手机迅速取证、在线结果分析等,从而有效落实责任意识,提升政策执行主体的事前预警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