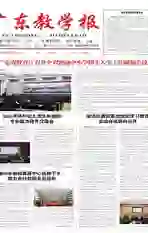双“城”记·致那些沉默的灵魂
2022-03-09付瑶
付瑶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分法是男人与女人。女人,相对男人,作为另一性别的独特命运在中国大地上一幕幕上演着:在北方,呼兰这座小城半年严冬封锁,窒息着一切生命力与反叛力,倏忽而过的春风仿佛成了杀人的利刃;南方,山明水秀的湘西边城茶峒,世外桃源的理想地方也不尽是自然优美……
《边城》中的翠翠,《小城三月》里的翠姨,她们美丽温存,似乎也不乏主见,为何总不能如愿以偿获得幸福呢?在她们身上,看到的是千百年来女性命运的连续和重复,传递的是不尽的凄凉与哀惋。
两人之中,翠翠更近于理想化,沈从文以全知者角度叙述湘西小山城里的人生,清净淡远,仿佛朦朦胧胧轻纱罩着的一幅烟雨山水画,细细品味半晌才能觉出味来,有时简直尝不出味道。而翠姨是萧红以童年的挚友开姨为原型,以第一人称叙述,直接参与故事,分外真切,强烈的抒情风格及女性特有的细腻感受,拣挑出富于暗示性的生活细节,读来委婉动人但作者指向鲜明。
一、茶峒·永久无声的守候
怀着对农人与兵士“不可言说的温爱”,“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沈从文有意造出一个“不知魏晋”、平和无争的“桃源”来,这里水清见底,夹岸高山,仿佛图画一般,这里的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安份乐生,一派安静和平。仿佛看不见压迫和剥削的土地上,生长着明眸黑肤、天真活泼的翠翠。即便如此, 女人的压抑苦痛,并不为这一份和平完全掩盖。
小说的故事中心情节便是翠翠的恋爱与婚姻。这当中起落不休,似乎是运命,似乎是巧合误会,造成许多的弯曲来。按“窥破天机者”的说法,这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的悲剧,是典型的封建文化与拥有生命自由的原始文化即湘西区域文化的对立冲突。对错姑且不论,但作为女性,沉默与等候的命运都早已被决定。小说突出表现的是翠翠作为这出戏里的女主角,不论在恋爱抑或婚姻事件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从恋爱来说,不论傩送还是天保,对自己爱恋对象都有明确选择,并且用积极的行动来表示,天保的夸赞、试探,傩送的盛情邀约,直至两人相约到对面山崖上轮流为翠翠唱歌,都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相比之下,翠翠则显得过分被动,对心仪对象不仅没有明白表示,反而屡次逃避正面相对。这当然可以解释成少女的羞涩,乃至懵懂。但从她会红脸,常想心事,不能忘却与二老的相遇,能领略歌声的缠绵处,直至后来拒绝大老的求婚,可见她的爱恋早已萌芽,即使是少女的羞涩,在恋爱中也显出被动得过分(今天看来),完全没有乃母之风。
翠翠的母亲是与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这是《边城》中的原话,很明显,翠翠的母亲与那个军人在恋爱中处于相对平等、积极的位置,采取的是自由选择的方式,但是背着丈夫,就是暧昧了。后来两人在无法抉择下自杀了,虽然书中写明了理由,初看来总有点奇怪,反复看,联系前后想一想,总算开窍了。女人不守本分,主动勾搭男人,不容于世,即使在保存原始状态的湘西,下场也只有去死。因为对女人的定位与压抑,开始得远比任何一个阶级早;而湘西的原始淳朴,其实也并非表面描述的那么完全。所以会有恰好近两年“因看月而起整夜男女唱歌的事,皆不能如期舉行”,而翠翠竟因哭倦睡熟了,终没有听清二老的歌声,只在梦中(理想的梦境,梦境的理想)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翠翠的封闭被动,不能说没有受到其母悲剧的影响,虽然她仍在内心保留了一些母亲对爱情婚姻的自由选择性情,但外在却只以沉默相对。这种被动性格悲剧一直延续到她的婚事上。在事关翠翠终身的议婚中,她始终是消极被动的参与者。老祖父、傩送、天保乃至顺顺,这些男人不管明地暗地出场多少,都在积极筹划参与着,婚姻尽管是男女双方的事,但女方出面的代表是老祖父,一个作为翠翠长辈的男人。翠翠为自己把握命运唯一增添亮色的行动是以沉默拒绝大老的求婚。仍旧是沉默,疼爱她的祖父尽管与她朝夕相对,两人不需言语也能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沟通,对她的细腻心思活动,尚不能猜透,何况他人?她既把心思密密藏着,老祖父出于怜爱,也把一切隐瞒她。作为女性,受到怜爱与保护似乎是理所当然,但由此造成的无知与盲目、对自身命运的无从把握也似乎是出于自然了。
小说的结尾,老祖父死了,翠翠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和守护者,似乎要主动地把握生活,然而仍有老马兵的做伴与出主意。明白前因后果,仍是无数个日子的沉默与守候。或许那个人回来了,但她的天空里,围绕着那个人,停留在茶峒的某个居所,只有守候那个人的归来与等待他出行的循环,永无止境的等候……
二、呼兰·永远平静的安息
以沉默姿态面对人生,永远守候的日出日落,翠翠作为女性自然又出于“天性”(实则性角色规定,男权制造成)推离和排斥于男人的世界,似乎像茶峒人无知无觉的平淡日子一样悄无声息,而在《小城三月》里,春风吹起翠姨心里的涟漪,观者何等痛心地看到如花一般的生命就那样无奈地凋谢。
三月绿了的原野,“蒲公英发芽了,羊咩咩地叫,乌鸦绕着杨树林子飞”“春风吹到每个人的心坎,带着呼唤,带着蛊惑”,在“这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的日子里,萧红写到,“我有一个姨,和我的堂哥大概是恋爱了。”
为什么是大概呢?作者不慌不忙交代这个姨(即翠姨)与“我家”的复杂亲戚关系。她的外貌风仪,甚而呼兰流行的服装装束,牵到流行的绒线鞋,写出翠姨买鞋的不厌其烦,点明其实翠姨心里早就爱上了这种鞋,只是表面不说。这就自然回到翠姨的恋爱上来:“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事实上,恐怕也没有人会听她的告诉吧。
作者层层铺垫,回环往复,为翠姨作一曲挽歌,写得尤其婉转,不恤用了种种曲笔,暗示、双关与象征等。细节的选择都精妙到位,像写翠姨吃樱桃,手指尖对那樱桃十分可怜的样子,怕它触坏了似地轻轻捏着。一个细节传神写出这个女子娴静优雅的风仪与温存的性情,既而可以联想到许多,如,她的身份地位,她受的教育等,此外还有内涵丰富、剪裁精巧的地方。
翠姨妹妹的订婚,她因之与“我家”——一个相对开明的绅士家庭往来密切,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及与“我哥哥”若有似无的情愫,零零碎碎、彼此关联似乎不大的细节,拼凑出这样一个翠姨:沉静温存,善解人意,安于运命,好像是合乎准则的淑女。另一方面看来,她羡慕佩服读书人,排斥安排的婚事,却一声不吭,内心的压抑痛苦可想而知。由于作者的写作指向异常明确,她的悲剧命运成因就易于揭示了。仍旧是沉默无言,似乎是个性悲剧,然而她生病,她拖延,她要求读书,她病得越来越重,外在压力如影随形,她的母亲、祖父、婆婆……这些人代表的是正统观念,翠姨的沉默也是正统观念压出来的,这个打网球“根本动也不动”的少女,她受到的教育,恐怕也是诸多中国女性所受的教育:顺从安命,不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要有不合宜(自然是合正统观念的宜)的举动。自由与幸福追求的火苗在内心燃烧,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她只能选择死亡。不从心的事,她不愿意,然而她怎能从心呢?死亡成了这个“笑话”的最终注解。永远平静的安息,是无奈的逃避,也是被压抑者的苦痛反抗。
三、尾声
我不知更应该悲悯哪个?是觉醒?!然而,终究只能去死的翠姨抑或不自觉其苦、静静守在渡口的翠翠?写下这篇小文,致所有沉默的灵魂,套用一句话:愿她们在仁厚的地母怀中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