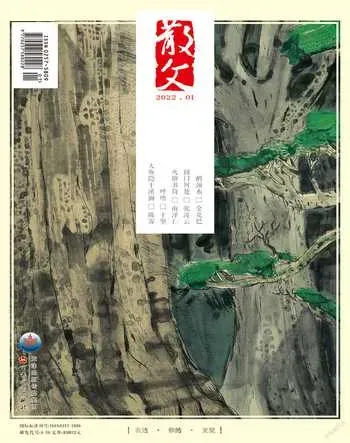秽囊
2022-03-04陈登
陈登
谁都有插导尿管的时候。
全家人排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待医生告知外婆病情时,我这么想着。天高云淡,医院楼下是滑溜溜的大理石斜坡,僵灰色的冬日蛰伏在大大小小的楼房外壁,空气中飘来路人呼吸里的腥。
也许是生肺味道,肯定有人清除了气管里的阻碍,使得所有寒冷直达最本质的呼吸器官,大家互相嗅到对方的内脏,也算悄悄地肝胆相照了。
“呼吸有腥味一般多见于呼吸道感染,如支气管扩张、鼻窦炎等疾病……”掐灭手机屏幕如同掐灭一场病变。这个季节不论人或物,都像被剥了皮的活鱼,在漂满银鳞的大铁盆旁躺着,偶尔抽搐一下,合不上的眼将一小块锈色的天空死死望住。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我抱住手臂,对窗外马路与楼房居高临下地呼出一蓬无力的白霜。
手术室外是天井,水泥墙壁覆盖微微一层青苔,映照浅尝辄止的生死。金属门后的外婆是瘪的,瘦得只有薄薄皮肉挂住骨架,仪器探头从她大腿上的血管插入,蜿蜒又曲折,逆流而上行进至头颅探测血块和肉瘤。据说铁锈就是血腥味,这是一场惨淡至极的血的艺术。
外婆昏昏沉沉,眼皮抬一会儿,又没力气地闭下去,嘴里模糊地嘟囔鸡呀菜呀,家里的房……住院部走廊狭窄昏暗,病痛、哀声、汗臭……家属都挤在靠门的病床旁,守着神志不清的病患。窗帘被风鼓起,阴蓝的影子投在每个人身上。外公坐在床沿,他也瘦,两个瘦骨嶙峋的老人紧挨着,像守着一座枯巢。
傍晚送外公回去,向來灯火通明的院落只开灶屋一盏灯。村庄万籁俱寂,我们围桌而坐,暗黄的光下,饭菜漂浮星星点点的猪油,外公咽下一口,再咽下一口,喉咙陡然滚出长长哽咽的颤音。蒙灰的玻璃窗外空无一物,偶有狗吠,黑夜的轨道被无限拉长,我们仿佛苍茫尘世中唯一的人家。
一切像提琴响亮颤音的尾声,人间笔直下滑,沉没于最原始的洪荒无声。
人就是如此,青春时要金属首饰,老去了要金属刀剪。机器在二十多岁贯穿耳垂,七十岁剖开后脑与腹肠,松果体替你记住千百个昼夜,末尾再细究一生中所有折断与破裂。
阵痛曾是偶然的偶然,然而在它食髓知味地逐渐成为生活本身时,外婆已经无力起身,八十块一盆的中药温水浸过覆满老年斑与青色血管的足背,苦味的热气熏透漏风的老年。干薄皮骨年轻时有果决刚硬的品质,多少个生猛的太阳底下,她在与外公争执后一步步果决地离开嫁入的村庄,走回熟悉的田野。
出村都是下坡路,天寒地冻时能闻到植物抽枝的生涩汁液气味。
小时候,道旁灌木里有荧荧的萤火绿,外婆打着手电走在前边,我停在坡头俯瞰清凉天地。如今远方房屋与山脉乌影如沉默的浪潮,回过头,只看见老房蜷缩成一团小小的灯晕,其中小小的祖辈、小小的儿女、小小的一生,都被缓慢湮没。
几十年前的风吹过油菜花与昏灰公路,斑驳老桉枝叶零落,外婆先是一个人出走,后来背着一个女儿、两个女儿、三个女儿,女儿又生育孙女,一个孙女、两个孙女、三个孙女、四个孙女。
渐渐地,她不走了。
但我还是要走。
2020年9月末,风霜爬上北地高原,我趁夜寄走所有行囊,出租车在还没亮透的天幕下顺国道逆雨直行。空旷辽阔的玉米地弥漫不及散尽的夜雾,冷火湫烟,天白得像一块铁。
后来每每回忆,只觉得自己像《地久天长》里的丽云,一生中的离别都太像离别:不见行人的北方寒冷清晨,黄昏门框中对面海岛稀少朦胧的灯光,小年夜虚张声势的迅猛烟火。她低着头度过了倒伏而默然的一生,将那些闪亮与悲哀的日子尽作灰尘。
车迅速地驶离西安,我麻木远眺,想象脚下泥泞根系一丝丝断裂,终于被抛在年末遥远的朝霞里,朝霞后是僵直困顿的所谓黄金时代,以及本人半悬着的四十五平方米的人间。它一室一厅一卫,空调几乎失灵,暖气还未铺设,比起居所,它更像一个孤独的人生堰塞湖,漂满厚重浮萍。
作为其首任房客,心知十楼在城郊已是高层,窗外灰尘与雨雾弥漫在凹下的墨绿原野,县城相隔数里,灯火飘浮,蜷成圆弧状,如天上街市。窗里头,我没有同党,弯腰清扫地面因漏水而剥落的石灰碎片。打开顶灯,白墙上都是自己的影子,从四面八方收束而来。
顾影自怜与形影相吊该有更具体的情境,于是我在此添置了人生第一面全身镜。它钢筋铁骨,拥有肃穆的黑色包边,方正规整。客厅空旷,那面镜子伫立其中,微微仰面正对不宽敞的飘窗。人类与镜子的纠葛始自公元前六千五百年,智人首次在模糊的黑曜岩石片上与自己的目光产生碰撞,然后是漫长的雕琢与打磨,两面三刀的切分——人与镜,镜与光,你与你。
长夜漫漫,我站在镜前,使得不高的身量在物理反射下被压缩得正好,白色灯罩透出柔和光线照亮身侧墙壁,只要轻轻扭转,就能看见自己微驼的颈如水鸟低伏,有一点儿窝囊的温驯意味。
两侧不甚对称的肩稍稍内扣,是个半括号。
而脊椎骨节段段凸起,仿佛史前两栖冷血动物隔着博物馆玻璃柜被吊起拼接的洁白骨架,实则更像一道拉链齿轮,人可以由此完全铺展,刮垢磨光,掏净血管,光彩地从头再来。
我无言地用镜子看自己的手臂、腰肢、不合时宜的脂肪与关节超伸,看协调与不协调的线条。常年被潜意识甩在脑后的一切幽微浮显,身体是紧密相连的关隘与烽火台,与其相关的描摹如同帘后的月亮,只有自己能望见,人一面背负墙壁投下的残缺阴翳,一面隔着镜面擦之不尽的尘埃,看见倒影里的丑陋与完满。
后来,因不平整双肩与脊背莫名的苦痛,我被迫去做了从脖颈至尾骨的彻底检查。一张张带着温度、柔韧厚实的X光胶片被机器打印,透露出肉身的隐秘事项。从来害怕这样虚虚实实的影片,几根骨头昆虫触角般张牙舞爪,内脏与血肉紧致包裹,黄白黑灰好似魂魄。
真是手起刀落的返璞归真。
胶片上的长条脊柱在肩背处侧弯出一线低矮丘陵,分不清诊断报告上的“左凸右弯”是什么形势,左右判断本就包含过多悖论,我只知道自己身体里有一处弯曲山丘。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的人生都要与这样歪歪扭扭的骨骼做伴,始终本色出演并不笔直的人类,继续泯然众人。
在太多声势浩大的偏倚里,这是微不足道的。
公寓旁边是城郊工地,荧光安全杠与闪烁的红绿信号灯将每个雨夜衬得电影一般,失眠时刻,翻身去看由窗帘缝隙投在白墙上的钢材和玻璃的反光,听着机器的轰鸣,想象一砖一砖一层一层地堆砌建造,躯壳内的血液淙淙涌动,骨骼肌肤在9月的蒸汽里嘎吱作响,好像我也在长——
这个时候会想起外婆。
医院深潭般的夜里,她大概也在失眠。所以我痛恨医院楼外城市彻夜的灯光与凌晨车辆驶过掀起的声浪,它们是世界迫使年老病患抛弃睡眠的信号,也是饱含侵略性的冒犯。
许多年前,外婆因眼疾有过漫长的住院期。无尽的观察周而复始,物理射线定期穿透病人头颅,器械面前人也成为器械,成为由术语、数字、表格概括的疾病工地,要掘地三尺,要刻舟求剑,要大动干戈。精准测量后,针尖几次从太阳穴刺入注射药水,外婆从那一年开始驼背。佝偻瘦小的老人究竟如何将这般疼痛吞下?我没敢问。
诊断说,她将在接下来的余生里慢慢丧失视力。
十年后,入秋前最后一日,我的鼻小柱软骨被豁开一小页。狗牙划过,有瞬间窒息的凉意,酱红色的血液紧接着落满前襟。
當夜无眠,除却忍受双臂推针处的肿痛,我还忌惮鼻尖伤口,想象它们如两片薄薄的叶在彼此乳白色的撕裂切面磋磨,不知能否嵌合如初。忐忑之下翻身坐起,点灯验看,取来棉签点拨。疼痛如针尖扎肉,很轻微,或许伤口也睡意正浓,妄图敷衍着息事宁人。鼻子从未遭遇过如此血光之灾,小小一场祸事牵动整半边左脸,嘴角微翕也怕扯裂合页。无处可去的血液瘀积在鼻尖空腔,使人头一次注意到在我的鼻头下竟有这等所在,月牙形的小仓,一座微型空中楼阁,用以藏匿不为人知的疤痕。
承受血肉之苦的人会柔软,如泥沼温和吞没一只野兽般脆弱地发声,我宽容你,宽容雨水,宽容蚊虫,宽容污浊,让一切下沉,下沉,慢慢吐出泥泡,整片荒原恢复平静,偃旗息鼓。
实际上,等到切身承受生命之痛时,早已无法柔软,无处宽容。
所有微妙的矫情只能算是年轻的恩赐,在真正不得已的痛苦前格外寡廉鲜耻,但也演习般的让人得以模拟肉体终将迎来的苦楚。
——要放大到多少倍,才是外婆的痛呢?外婆因身体麻痹跌倒的痛,外婆的太阳穴被扎针的痛,外婆半醒着,金属探头进入后脑的痛。
摩擦血管的,刮过骨骼的,刺戳肌肉的,那些绵密隐秘的痛,加剧衰老又证明衰老的痛,让尊严荡然无存的痛。外婆神志不清,微颤的手仍试图捂住被单,医生按程序用力掀开,吩咐亲属帮她更换病床。老年人的裸体,不再被当作裸体,而是人体样本,徒剩嶙峋和干燥。
几十年前健壮美丽的女性,最终被岁月带回了曾经芬芳并将永远芬芳的油菜花田埂上,只留身躯任人间消磨,不再回来。
6月,我去探望外婆。
城市是一片薄薄的指甲,线路像甲半月弧线,驶向乡下的车辆狭窄暗淡,不断有附近村子的老人背着背篓上下,用方言絮絮地谈论着蔬菜、粮食、儿女与孙辈。窗外天光粗粝,景物过曝,整个世界被浸泡在大杯白开水里,前路缓慢扇形展开,野山野河迟钝地擦肩而过,
卡尔维诺说过,所谓孤独,只有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途中,才能被人所感知。
整个午后,我们并肩坐在瓦檐下,日影的轮廓从这株梨树默默移到那株梨树,鸡鸭偶尔蹬起雾般黄土,她挽着裤腿躺在椅子里,瘦如干枝般的腿脚被太阳烘烤。老屋后的山坡风拂树叶,我歪头听外婆口齿模糊地说话,有时我俩不动,只看风寂然地追逐院中一片飘零的羽毛。
我的手掌覆盖外婆的手掌,暗黄与细瘦如出一辙,几十年后,它会生长同样的斑点,疏松骨缝终将年久失修,成为X光胶片上所有灰白黄里最脆弱不堪的范例,接着像一片秋叶那样摇晃着坠落,埋进村庄深长空无的夜海。
佛教将凡人的肉身称为“秽囊”。
我平躺时总用指腹轻轻摁压前额,如今二十出头,眉心已然微有酸痛,往后定会生成“川”字纹路,毕竟一生惆怅都要在此流过。万般磨损与新生从茫茫云海中将我捞起,耳语着:你用这般质地,从人生的河里赤条条游过。
肌肉的沟壑与褶皱在当今尚可推针消融舒解,灵魂里如鲠在喉的结节却只能凭自己在光阴的细密缠绕中抽丝剥茧,就像风试图撞碎一片巨云,必得在羽化的边缘里寻找一处破绽。
人,或早或晚,终将成为缝缝补补的病体,茕茕孑立,踽踽地,蹒跚着走入黑暗的河流。
客途终究秋恨无尽。人都是溟蒙地、顺水推舟地踩进一片又一片的光里,将年华给出去,哑然的半生后,世界再还来尘埃。
仍然要活,要活成一棵被劈开的梨木,拖曳已残破或终将残破的秽囊,攥紧已如烟或终将如烟的情谊。
要像夜云无声路过另一片夜云,又在黑暗中回过头安静地彼此注视。
要找到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下午,并排在太阳底下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