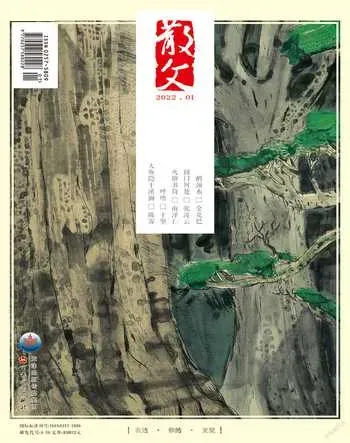一代人,老了
2022-03-04介子平
介子平
长者的车辙
1947年,张中行主编佛学月刊《世间解》,集稿很难,不得已,只好以书札形式向饱学前辈求援,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希望万一掉下一个两个。没想到,朱自清真就写了一篇《禅家的语言》的文章,并很快寄来。“大概是这一年的五月前后,有一天下午,住西院的邻居霍家的人来,问我在家不在家,说他家的一位亲戚要来看我。接着来了,原来是朱先生。这使我非常感激,用古人的话说,这是蓬户外有了长者车辙。”遂在1948年1月刊出,而仅仅九个月之后,朱先生便作古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謝了,有再开的时候”,先生走了,无再回的时候。
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的师生为避战火,开启了南迁之路,且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文学院落址衡阳南岳。据钱穆《师友杂忆》载:“一日,余登山独游归来,始知宿舍已迁移,每四人一室。不久即当离去。时诸人皆各择同室,各已定居。有吴雨生、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而尚留一空床,则以余充之,亦四人合一室。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时局虽艰,各自埋首,且著述有成,趣味无倦。
人们常将朱自清性情的敦温,与闻一多的激昂相对而言。西南联大学生冯契回忆:“闻先生就说:‘做汉学家可以长寿。朱先生说:‘是因为他们长寿,才做得到汉学大师。我身体坏,不敢存这妄想。你却行。闻先生就笑起来:‘能不能做大师,不敢说。活七八十岁,我绝对有把握。”一语成谶,闻先生终年四十七,朱先生终年五十,皆无寿。曾与朱先生同事过的张充和晚年回忆:“闻一多性子刚烈,朱自清则脾气很好。都说他是不肯吃美国面粉而饿死的,我听着不太像,这不像他的秉性所为。”西南联大的旧日风景,之所以为后世仰慕与传颂,不仅仅由于其大师云集,星光耀目,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大师们的做人。
一个身体里,住着两个脑袋,印度有共命鸟的传说:其为一身两头之鸟,共用身体,而思想独立。其中一个脑袋,因嫉妒另一个脑袋拥有天籁般的美妙歌喉,暗生恶念,遂给另一个脑袋下毒,剧毒传遍共有的身体,施毒者最终害人害己。一个身体里,住着两个灵魂,德语有谚: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年老之后,多数人趋于平和。书以平整为善,人以平和为仁,读其文,识其人,胡适曾言:“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染风霜,月琳琅,沿街而行,红尘霭霭,这些残纸上的片言,听一回,除躁一回,听一回,宁帖一回。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心里有数,心里有数不如名师指路。日夕劳忙,于世彷徨,名师指路,求之不得,其未必言语,言传身教矣。拒绝崇高之崇高,依旧崇高。
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5年2月,吴宓秉鹅湖鹿洞遗风,负责筹备清华大学研究院,“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任教之前,王国维亲赴天津,得逊帝溥仪首肯后方成行。未几,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四大导师到位,一时同调,心灵合作,清华园里从此有了长者的车辙。
长者车辙在前,后生望尘而拜,非对其人卑躬,趋其学识矣。
乡愁是妥善的逃世之方
我们谈论乡愁时,谈论的是什么?
旷土尽辟,桑田满野,渺不可见的童年,与故乡是同义词。树大分杈,儿大分家,家未分,你已离乡。时飞则飞鸟入云,时潜则潜鱼从渊,不足喻其疾。
飞云过天,变态万状,年轻尚无故乡的挂念。多少人间惊鸿,转眼成为黄昏里无以辨认的影子。垂暮沉郁,雄风不振,无法言说的晚景里,即便梦游,再找不到好的去处,故乡的存在已然成为一种美好。无视苦难,放大幸福,脱离原始时空,谁都免不了受到怀乡的侵袭。
所谓故乡,集体记忆的象征性符号也,而集体情感结构与一个时代的文化密切相关;所谓乡愁,即不满于现状,与被美化的过去相隔而造成丧失感,化作与故乡割不断的感情。对于初到巴黎的外省青年,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春声忆故乡,现实生活落差越大,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便越多,乡愁想象也越丰富;现实里的人越是焦虑,助人自疗的乡愁便越温柔,只要有了乡愁,不愁活不下去。既对难以融入的现实生活方式反叛,又须臾不可离之,毕竟一旦享受便利,就脱不开便利。流量明星短视频里的人设故乡,虽与你无关,但乡愁成为流行思潮,自有其理,某种文化的流行,本质上是共情的产物。即便终身不曾远游,乡愁依旧。假以自遣而暂忘所遭遇,乡愁是妥善的逃世之方。
回首既往,体会当下,故乡不只是具体存在的处所,更是地标变坐标后心灵的归属。避世高逸逃不脱的故乡,不是地理定位,乃观念所指;不是具体存在的场所,而是心灵的归属感。乡愁的本质,无非家园感缺失后,心灵深处对精神栖息地的追随,黑格尔说世界的本质是精神,故乡便是满纸烟云的精神旅行。舟在河心,青山遥望,回不去的故乡,才是故乡。水族馆的对面隔一条马路便是大海,一只海豚高高跃起,一定看到了它回不去的故乡。
一代人老了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可是秋天过了,种子还没结上,夏天过了,一纸人情尚未还上。年复一年,无非春替秋换,转眼之间,一代人老了。
让人感动的是细节,让人崩溃的也是细节。当有人说出“那时我们还年轻”时,言者闻者一阵伤感。不经意间,时间已吞噬掉许多细节,甚至忘了你的模样,叫不上你的名字。
不想把颓废情绪带给别人,然脸上越是挤出明媚的笑容,心灵越是变得凄凉。有伤感因有情感,越老泪越浅。在别人的葬礼上哽咽不已,在别人的婚礼上,怎也转身流泪。
所有自负,皆来自自卑;所有豪迈,皆来自软弱。振振有词,因为心存怀疑;依依不舍,因为痛恨自己无情。屈指与君别,依稀又一年,海阔天空,一身如寄,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已逝之境因已逝之心,无论怎样道别,总会落下遗憾,而有的人连声再见也没赶上说,便已难觅其踪。孤身一人时,所有佳期,皆让人着急。那是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如今马散边城月,一半的记忆也已不知去向。古典戏剧多以团圆结尾,因为现实恰与之相反,若有邂逅,还会是从前的样子?只要分开的人,无论原先多么热络,也会渐渐疏远。
地老天荒,并不恓惶,倒是人事凋敝,难以不忧不惧。如此短暂,在天灾人祸中闪转腾挪,都算是幸运者。日常生活进入文字世界,有所反思体会,知道自己的认知边际,需要时间的掠过,还需空间的宽容,方能共存共生于无形。看似复杂的生活课题,闭门忘岁月,便可澄澈,鸡毛蒜皮的烦恼,自行消解,反省这事,留给岁月好了。
同一条街,幼时父母牵手学步,不知辜负了哪一场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转眼红粉佳人两鬓斑,如今自己坐在轮椅上经过。始于初见,止于终老,但有些事并未按照常理开始或结束。不是归人,只是过客,时光是永久的话题,只要存在过的事物,都会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无激情不叫年轻人
明月直入,无心可猜。青年的朝气,也是锐气所在,自卑与自负交织,越无知越无畏,个个斗鸡般具有攻击性。既长,知晓世故城府,允执厥中而强音不再。
嵇康志清峻,阮籍旨遙深,二人向来拒绝循规蹈矩,脾气皆了得。至阮籍晚年,便不再臧否人物。1988年6月3日,杨向奎在山东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谈道:“我在中国社科院的同事钱锺书年轻时非常狂妄,因此西南联大不聘请他,他到湖南的一个师范学院教书。别人讲课时他在门外听,听了故意高声哈哈大笑。年老时他的脾气就变好了,现在对人平易谦恭得很。”1939年2月,傅雷应国立艺专校长滕固邀请,前往昆明出任教务主任。自上海动身,一路舟车劳顿,赶赴昆明,当日即参加一个与教学计划有关的会议,只因与他人一言不合,气血自来,二话不说,扭头离席,拖着尚未打开的行李,不顾路途遥远,打道回府。坚守一己的存在,何其不易。二人俱有率性而为、狂放不羁的性情,而那个年代,权力尚不足以支配一切,自己尚可与自己的情绪相处,不用低头俯仰,而有生存的空间。
行为如此,举止亦然。晚年林语堂,依旧仪观俨然,只是对年轻时钟情的西式服装渐生偏颇:“谈到男人,我一定愿意要中国的服装。一件长袍从肩上一直到下面,旁观好像一件寝衣。但是看到外国人的服装,内边附着皮肤的一件衬衫,此外短衣和上衣。在你头边一件东西像束缚狗那样缚着,称之曰‘硬领,而紧紧在你颈上缚着的领带真像狗的链条。”尽管如此理由未必令人信服,一个洞精西学者开始着中式长衫,本就是一种反差。
激进的力量、激情的鼓动固然可贵,然理智的思考、理性的分析必不可少。《余英时谈柏克》云:“一个国家若没有保守的能力,也就不会有改变的能力。没有保守的能力,改变将不免冒着一种危险,即失去其体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激进推动改变,保守则可避免走极端。青年人的转化,顺时也顺势。
无激情不叫年轻人,不激进不叫年轻人。待遇挫折,开始于俗世中寻求立身之本,顺势的路径大致如此。所谓失言,是一不小心说了实话;所谓正确,不过是与人相似而已。考量过多,谋划频繁,意料之外的变故越来越少,情理之中的事情越来越多,久而久之,日子虽也是一天天地过,却愈加接近简单的复制。进入恒久忍耐的日常状态,激情被生活压抑,爱情被琐碎淹没,一如鲁迅笔下的涓生与子君。先行者皆激进者,成功者皆激情者,而人一旦变得世故圆滑,生活的故事性自会虚弱,于人于己均索然无味。
有些场面,无须文字描述,便可感受到其中的力量所在:哪有青年不幼稚,哪有青年不犯错,但青年永远比青年自己想象的要好。年华向晚,沉香的岁月里,夹杂着阵阵陈腐。保持饥饿,保持愚钝,不被时代潮流所裹挟,那要有多大的定力。
趁年轻把坏事做完
大地上你我仅一生,青春更是短暂,禁不住挥霍。风风火火、跌跌撞撞乃青春活力,见佛杀佛、遇魔斩魔也是青春鲁莽,此般情形下,一次说走就走的远足,一场死去活来的分别,一回毅然决然的反叛,一个刻骨铭心的忏悔,那又算得了什么。一掷千金皆为胆,家徒四壁不知贫,总觉得日子还长,有自信可以重来。
上升路不平坦,青春过后,似有所思,不着边际一虚脱。一身疲惫,却两手空空,一地鸡毛,却了无头绪;杯盘狼藉,却饥肠辘辘,枝叶纷披,却上无果实。所以,我在某年五四青年节为年轻人的讲座上,倚老卖老告诫,趁年轻,把该读的书读过,把该喝的酒喝遍,把该看的景看到,却顺口说漏了嘴:把该做的坏事做完。
周作人说:“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人大概也如此。自说,满园荒唐,撷英采华,闪烁其词;他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乃人之常情,不必深究。大慈善家,起家或也残忍,窃国者皆大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已。青春远没有那么复杂,只是该玩耍的年纪,动了真情,该注目的时刻,毛手毛脚。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回过神来陷入无限懊恼。莫道情殇,反误了卿卿,相逢天女赠天书,不如一把火烧尽俄罗斯笔法写的诗,从此塞上鸿雁,芳草天涯。
男生未主动追女生,或因开不了口,女生未主动找男生,还在等着找她。“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今日欢,明日歇,无非露水。暂时有,霎时空,所谓烟花”。双方皆未失却,只是均未得到,也就没能遗留几页故事,呢喃轻如湖上风,有纹无路,胭脂和泪落纷纷,有迹无痕,小说家眼里,好没趣。学习不必超前,更不便速成,否则,童年無童真,青年无青春,中年无乐趣,老年无安闲。
同样,成熟也不能超前,目不斜视,一脸沉着,坐怀不乱,或装,或超人。圣贤只可供,神仙不可仿,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云:“她们老想叫人变得正派。可如果她们见到我们时,我们是正派的,她们根本就不爱我们。她们喜欢的是,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可救药的坏蛋,而在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变成淡而无味的正派人。”
风格与人格同季成熟。一曲凉州声袅袅,到此际离愁多少,佳人肩头,似有风意,佳人不可期,更何况真情佳人。张爱玲说:“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那么你就会原谅现在的我。”对花弄春,淑景已残,“从前的我”,该是怎样的我,参差多态,倜傥不羁。
随心所欲的选择,不考虑挣钱,料也挣不来柴米油盐,不掺杂体面,何来如此知性理智,身后是非谁管得,只任凭喜欢。青春的旅途虽短暂,易迷惘,失去的无法找回,然昂首的自信、从心的尊严、融冰的骨气、刻度的坚强,皆在此间成就。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中年后琐碎苛细的不堪,反衬出年轻时了无牵挂的可贵。单身非不幸,出生一人;结婚非幸福,终了一人。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写道:“结婚以前,自以为就有了爱情,可是,婚后却不见爱情生出的幸福。欢愉、激情、陶醉,这些当初在书本中读来的美好字眼,生活中究竟何所指?”国人更是不堪,在家怕老婆,出门躲警察,购物羞钱少,过街恨车多,单位畏领导,说话嫌嘴拙,提笔悔学浅,过河才知不设桥。
年轻时,以为爱即不顾一切的付出,情怀永在,爱恨不移,自己也能感天动地,侠骨丹心。后来才明白,受伤时无人替你包扎伤口,一路滴血,一路花开,是海棠,还是玫瑰?
察人之过,不扬于他。年轻时的所作所为,哪里是坏事。纵是坏事,哪里能做完?
工夫到了时间也就尽了
世间多少事,工夫成就之,有了工夫,便有了功夫。
我进入过太行吕梁的许多条深沟险壑,凡可耕作之处,皆已开垦,生土变熟地,四海无闲田,无以估量这里留有多少代人的疲惫劳作,工夫乃时间之积累。进化亦然,游鱼上不了天,飞鸟潜不得水。北冥有鱼,其名曰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那是庄子的无限想象。
人何尝不如此。“任何人只要专注于一个领域,五年可成为专家,十年可成为权威,十五年可成为世界顶尖。也即只要你在一个特定领域,投入七千三百个小时,就能成为专家;投入一万四千六百个小时,就能成为权威;而投入两万一千九百个小时,就能成为世界顶尖。如果只投入了三分钟,你就什么也不是。”美国职业发展咨询家博恩·崔西的界定标准,似可参考。何以成为专家,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美国作家马尔科姆·葛拉威尔“成功学”著作《异数》提出了“一万小时定律”,即无论做何事,只要坚持一万小时,便可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当然也有例外,达尔文一生多病,每日仅能工作一小时,阅读十页有用的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看三千六百页左右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而正是这十一万页的书,成就了达尔文一流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的地位。这一万小时如何分割,朱熹以读书为例云:“为学须分老少,年少精力有余,书须多读;若年齿向晚,却宜择要用功,不在务多。”
是定律,即意味着无法摆脱。“许多人说,钱锺书记忆力忒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杨绛这话的意思,是说记忆力超凡的钱锺书也无法摆脱此律。在生命的最初三十年,你养成习惯;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习惯养成你。钱先生的习惯便是读书。晚年时,沈尹默近视已达一千七百度,咫尺不可辨,但他书写的七八尺大直幅上,一寸大小行书,竟达二三十行,每行直下无歪斜,且运气均匀。谢稚柳感叹:“这已经不是靠视力,而完全是凭着自己得心应手的熟练功夫。”肌肉记忆,功夫所来,沈先生的习惯就是写字。
有了习惯,也就有了境界。古龙说:“我靠一支笔,得到了一切,连不该有的,我都有了,那就是寂寞。”懂我的人,不必解释,不懂我的人,何必解释,与其说寂寞是智者常有的一重境界,不如说是古龙的一种特质。他还说:“上帝创造了男人,发现他还不够孤独,便给了他一个女人做伴,使他更真切地感觉到寂寞。”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兴之所在,与君痛饮三百杯,古大侠笔下傅红雪、李寻欢、陆小凤、花满楼、西门吹雪等绝尘侠客,虽曰衣袂飘飘,风度翩翩,却茕茕孑立,寂寞孤单,一醉千日,作者内心写照矣。
冥冥之中,若是存在预先设定的使命,那便是以一寸一寸的光阴,去完成一力一力的工夫。工夫到了,时间也就尽了,生命也该完结了;时间未尽,工夫未透,生命却已挥霍成灰烬。光阴焉能轻与,生命岂敢滥取,有心解酲蒙中,无人身处事外,无论随世的庸愚,还是盖世的豪杰,皆不脱此律。《简·爱》中有句话:“当我们越过坟墓,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雪后江山一笼统,填平了沟沟坎坎,上帝面前,大致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