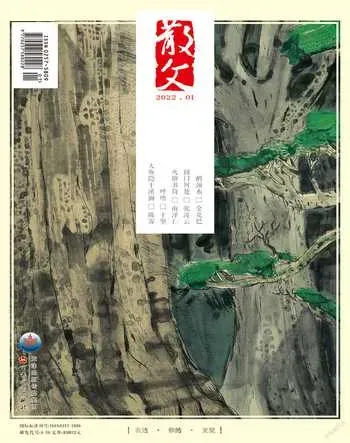鸟劬于泽
2022-03-04王雪茜
王雪茜
我们这次拍摄的目标是一对黑翅长脚鹬。同伴跟拍一对黑翅长脚鹬十几天了,她数着日子,算准了这只长脚鹬的四只卵这几天就会孵化。长脚鹬一般一次孵四只卵,同伴说,如果因意外不足四只时,它会补齐四只再孵卵。雌鸟雄鸟轮流孵卵,孵化期在二十天左右。我还没有亲眼见过小长脚鹬破壳,难免有点兴奋。雏鸟破壳多在清晨,大约此时环境静寂,亲鸟不容易受到惊吓吧。况且,一日之计在于晨,新生命如朝阳初起,一切都是新的。
此时正是5月末,芦苇还在展叶期,翠绿绿的苇叶密密地挨着,仿佛一大片新鲜的玉米地。这个季节,我喜欢在太阳下山以后到这片水塘听鸟。顺着土坝向北,慢慢踱步,彼时万籁俱寂,水面上一只鸟也没有,可我知道,它们就安歇在芦苇丛中。月亮渐渐升起来,风声减弱,天边红黄相间的灯火,像一簇簇火苗不停地闪烁,透着遥远的暖意,鸟鸣时断时续,仿佛古老的催眠曲,漫不经心又舒缓有致。间或能听到“扑啦、扑啦”的声音,为寂静的画面平添有力的一笔,那是鸟的翅膀拍打水面发出的声音。白骨顶鸡的叫声比白天显得稍弱,像小时候肺活量不足吹出的柳哨声;野鸭子一声不出,也许早睡着了;小鷉的叫声很有辨识度,“科科、科科、科科”,快速而连续,带着一丝丝颤音,多么像赖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幼儿。更多时候,我判断不准听到的到底是哪种鸟的叫声,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夜晚,鸟鸣比白天稀少得多,鸟儿们也很少同时鸣叫,常常是东边的鸟叫一声,西边的鸟应和一声。让我意外的是,彼此呼应的也不是同一种鸟。这反倒令我的耳朵格外灵敏,充满期待。
当你真正沉浸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时,耳朵会飞上风中的苇尖,眼睛会嵌入澄碧的水底,喉咙会忍不住发出一声含混的鸟鸣。演奏者们好像知晓了我的来临与关注,鸟鸣声开始交错模仿,声音里加入了某种有意识的音调,谈不上惟妙惟肖,我却听出了歌喉中若隐若现的自豪与喜悦、嬉笑与戏谑。它们有一种天然的能力,可以分辨出谁是它们喜爱和认可的听众,并以独特的曲目表达善意。那一刻,城市的霓虹与人类文明的自负,都显得无比廉价而脆弱。
“是我最先发现这里有长脚鹬的。”同伴打断了我漫出的思绪。在离水塘稍远一点靠近芦苇丛的一块平地上,她熟练地用泡沫板自制了一个小筏子,筏子前插了四根竹竿,似乎想安慰水塘们的鸟,看,我们给自己画地为牢了,绝不会靠近你们哦!最初筏子上要铺设伪装网。观鸟人都知道,鸟类在繁殖期非常敏感,任何一点人为的干扰都会让它们惊慌失措。只是,时间久了,鸟儿们知道拍鸟人并无恶意,也不会刻意打扰它们,见惯不怪,便不再躲避,甚至毫不顾忌地在离拍鸟人几步远的地方觅食。伪装网的铺设环节省略了,同伴把相机的脚架拆掉,用泡沫板做了一个类似大枕头的东西,将相机放在上面,趴在泡沫筏子上调整角度,我则蹲在一边,摆弄望远镜,一声不敢吱。
出乎我意料的是,不远处的几只鸟——两只斑尾塍鹬、一只落群的滨鹬,还有三只环颈鸻,其实早就看到了我们,却全都做出视若无睹的样子,那只滨鹬甚至还对着我们的镜头连摆了几个pose(造型),可爱极了。嗨,谁忍心去惊吓这些自由轻盈的精灵呢?
“这里的鸟已变成‘老江湖了。”同伴笑着小声说。
从望远镜里看去,我们的目标,那对黑翅长脚鹬的巢筑在水塘北边搁浅处,像一只棕色的碟。这只巢主要是由芦苇茎构成,为了牢固和严实,间缠着一些树根、树叶和水草。亲鸟竟然不在,四枚卵丝毫看不出要破壳的迹象。
“亲鸟不会走远,很快就会回来。”同伴颇有经验地对我说。
果然,三五分钟不到的样子,两只黑翅长脚鹬匆匆飞回水塘,雄性长脚鹬先是看了一眼鸟巢,确认鸟蛋还在,便落在鸟巢近处的浅滩。雌性长脚鹬并没有直奔鸟巢,而是悠闲地先觅起食来。两只亲鸟一前一后在塘泥里昂首阔步,寻找食物,它们不慌不忙,步履稳健、身姿轻盈,不时将长长的黑喙插入浅水里。深红色的双腿修长、挺拔,让人想到芭蕾舞演员曼妙的肢体。不远处,三只环颈鸻迟疑地跟在黑翅长脚鹬后面,缩手缩脚。环颈鸻体长仅有十五六厘米,体重仅有四五十克,在体长近四十厘米,体重近两百克的黑白色涉禽长脚鹬身边,简直像麻雀一样小,仆人似的自惭形秽。吃饱肚子的“红腿娘子”立刻飞回了巢,也许离开鸟巢时间有点久了,找不到孵卵最佳体位的雌鹬不断站起又蹲下,努力调整它的两条大长腿,两三分钟后,它终于找到一个最舒适的角度,蹲下了。雄鹬并未离开,在周边警惕地巡视。
鸟在孵卵期,要面对重重危机,故而有“十巢九覆”一说。黑翅长脚鹬的巢,筑在浅滩上,虽然形状、颜色如土丘,又间杂以腐叶、泥土和草根等,极具迷惑性,但仍处于裸露状态,危险还是无处不在。这对“红腿娘子”对周围环境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状态,因为危险并不仅仅来自可目视的范围。同伴说,他们这几年一直在保护黑翅长脚鹬的巢。去年他们就为五對黑翅长脚鹬的巢架设了保护网——用竹竿渔网等将鸟巢几米范围内的地域简单围起来。
“四年前,6月初,大洋河湿地,有一对黑翅长脚鹬选鸟巢的运气不够好,雌鸟刚开始孵卵没几天,就开始连续下雨,眼看着河水涨上来,鸟巢即将被淹没,我赶紧趁亲鸟离开的片刻,搬来一些碎石头把鸟巢垫高,黑翅长脚鹬才得以继续孵卵。”同伴说。
“我拍摄了雨中孵化的视频,每每看着它在雨中安然暖巢孵卵的画面,我心里都会一暖。天下做母亲的莫不如此,人鸟同心。可惜啊……”同伴低下了头,“后来我去拍摄别的鸟,大洋河河水持续上涨,朋友告诉我,那窝雏鸟全部夭折了。那以后,我再跟拍鸟们孵化,就从来没有中途易辙过。”
“亲鸟不能自救吗?比如重新筑个巢?”
“重新筑巢几无可能,时间上也不允许。”同伴顿了一顿,“不过我曾拍到过一对黑翅长脚鹬抗洪自救。就在这片水塘。”
我看过那组照片和视频。大雨过后,黑翅长脚鹬的巢被淹了,鸟蛋都泡在了水里,两只亲鸟心急如焚,它们不断地用嘴从水里打捞能加固鸟巢的东西,小树根、苇茎,可捞出最多的是毫无用处的腐叶。雌鹬围着鸟巢打转,它不敢离开鸟巢太远,雄鹬被伴侣派出去寻找建材,它叼回来几根七八十厘米长的苇茎,啄断后斜搭在鸟巢上。可同伴没有拍到最后孵化的画面,结局不难猜到。
她沉默了,我也说不出话来。看看手机,已经九点多钟,看来今天不可能拍到长脚鹬的小宝宝了。
白尾鹞就是那时出现的,离我们不到十米的距离。白尾鹞雄雌在外形上差异特别大,很容易辨别。我们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只雌性白尾鹞,它的上体暗褐色(雄鸟上体一般蓝灰色),腿黄白色,爪子黄色,嘴上面也带一点黄色。它在水塘靠近芦苇丛的地方扑腾着翅膀,我们发现它的同时,那对长脚鹬也发现了它。不过这只白尾鹞有些反常,我们没有发现它是从哪里飞来的,好像它是从芦苇丛边突然出现的。雄性黑翅长脚鹬先受了惊,它马上飞到高空盘旋,发出拉长的警报声“啾——啾——”,像警笛似的。很明显,这只黑翅长脚鹬属于色厉内荏型,看起来威风凛凛,实则是只“黔之驴”,除了大声尖叫,并没有其他招式。但我知道,鸟类极有智慧,它们可不止有三十六计。黑翅长脚鹬个体战斗能力虽然极弱,却是很有谋略的军事家,遇到危险时,比如猛禽、犬类或人类靠近,它会腾空而起发出尖叫,反嘴鹬、燕鸥等其他鸟听到警报,会联合起来一起抗击敌人(这也是黑翅长脚鹬常常与其他鸟类混居的原因),靠着“狐假虎威”“滥竽充数”的战术,常可化险为夷。
奇怪的是,这只白尾鹞并没有靠近鸟巢的意思,反而向芦苇丛的另一边扑腾。长脚鹬停止了尖叫,它并不想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挑起战争。看得出,白尾鹞急于脱离我们的视线,它努力抖开翅膀,扑棱几下又落了地。我正看得纳闷,同伴却已迅速脱下外套,三步并作两步窜到芦苇丛中,用外衣一下扣住了它。
对我们而言,白尾鹞并不陌生。小时候,大人吓唬爱哭的小孩子,最常用的口头禅便是:“不要哭了,再哭就被老鹞子叼走了。”小孩子并不知道老鹞子是什么,大约以为是妖怪之类很骇人的东西。而我七八岁的时候,常住在山沟里的姥姥家,已经可以识别白尾鹞了。白尾鹞属猛禽,体型稍逊于老鹰,脸型像猫头鹰,喙十分锋利,一些小鸟小鼠小虫小蛇常会成为它的口中食。
可以断定,这只白尾鹞的翅膀受了伤,可伤口并不明显。我们找不到它的伤口,也就无法判断它伤的轻重。目测这只白尾鹞体重在五百克左右,体长差不多五十厘米,携带不便。同伴用装泡沫板的黑色塑料袋捆住了它的一双翅膀,拎着它,打算把它送到车上,拉到宠物医院去救治,未料,刚打开车门,把它放到地上的一瞬间,它就一下子飞跑了。被捆住了翅膀的白尾鹞当然飞不高也飞不远,它拼尽全力扇动翅膀,连飞带跳。我们放下设备,跟在它后面追。
受了惊的白尾鹞尽管翅膀受了束缚,在这片湿地上还是比我们跑得灵活,只要我们靠近,它就飞一段。它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我们追得气喘吁吁,力不从心,可无论如何不敢放弃。折腾了两三个小时,白尾鹞转移了阵地,扑腾到土坝的另一边去了。人追不上,车也开不进去。我们眼看着它飞进了一片废弃的黄泥地里,无能为力。白尾鹞暂时摆脱了我们的追踪,可它的焦虑和烦恼丝毫没有减少,它趔趄地爬了几步,将翅膀完全张开,转过头用嘴去啄塑料袋的系扣,用力撕拽,可塑料袋依然紧紧地勒着它的翅膀根。同伴的眼圈红了。
那是一片不毛之地,不知道谁填了土又弃置不用,被几只蛎鹬暂时占作了领地。蛎鹬是中型涉禽,体型也较大,这几只蛎鹬长得很漂亮,黑色的头,红红的长嘴巴,红红的眼睛。自己的床榻之侧岂容他人侵入(它们当然不能预料,这里也许很快就会开来挖掘机),几只蛎鹬发现了白尾鹞,起初亦步亦趋,后来可能发现白尾鹞受了伤,一哄而上,受了伤的白尾鹞不如鸡,被蛎鹬赶得狼狈逃窜,东奔西突,最终窜进了芦苇丛,从我们的视线里徹底消失了。
在这片湿地里,我从没有见过船。但是有一刻,我会突然想起弥尔顿的一句诗。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湿地或家园是一艘旗舰,那么鸟,就是旗舰上的一支桅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