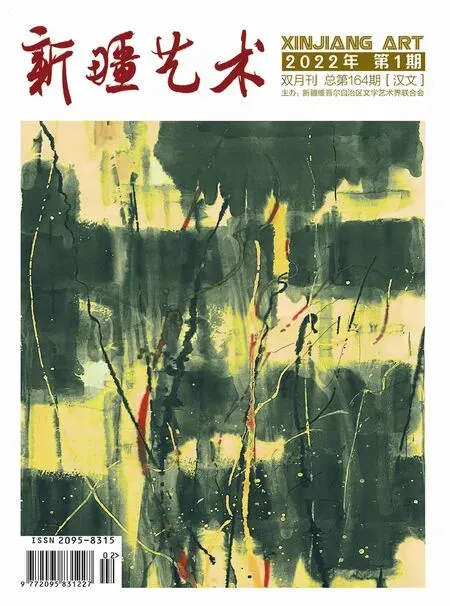《被光抓走的人》:一次对伦理的投诚归顺
2022-03-03□乔慧
□ 乔 慧

在导演《被光抓走的人》之前,董润年是以《老炮儿》《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等多部电影的编剧身份闻名的。多年的专业积累使他执导的首部电影《被光抓走的人》拥有娴熟缜密的四线并进平行蒙太奇结构,表现为:在白光“抓走”一部分人之后,还存在于当下的四组恋人或者家庭各尽所能来应对白光的“审判”。其中,武文学、张燕夫妻为爱制造“伪证”,李楠奔波寻找丈夫的婚外“真情”,筷子为秦山之失踪寻找一个被杀的缘由并为之“复仇”,王杨在刘佳一的质疑中跳楼自杀表明心迹。片名为“被光抓走的人”,但事实上故事里的全部主角,都是“被光剩下”的人。在“抓走”与“剩下”的对立中,以“全景敞视”为牢笼,众人跃跃欲试进行越轨,最终却在光权控制、监视、自我反省之下,完成了对东方伦理与家庭道德的归顺。
一、光作为监视者、权力执行者,地球作为监狱
《被光抓走的人》设置了一个颇为“科幻”的开头:一道突然出现的光带走了一部分人,据影片中的人猜测,这道光可以监视鉴别出夫妻和恋人之间是否相爱,相爱则被带走,不想爱则被留下。在这里,光是监视者,是监视者的目光,这是导演设置的第一层光的作用。第二层是,光作为权力执行者,被用作权力表征,这不是董润年的初创,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就曾说过:“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影片中,看不见光的,没有被光带走的,是“被囚禁者”,而光确实做了这个捕捉和放逐的行为,是权力的集成。福柯认为“全景圆形监狱”是“在中心眺望塔,监视者能观看到所有被监视者,但是不会被被监视者看到”。《被光抓走的人》也借“被剩下的人”之口与新闻强调,被光找到的人是看不见这道光的,“神奇的是,处在光照区域的人们却没有看到光束”“就突然不见了”“凭空消失了”,这也与“圆形监狱”中被监视者看不到监视者趋同。
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曾提出一个”圆形监狱”的概念,被具体描述为“一个像圆环一样的环形建筑,在中央造一座塔楼,上面开很大的窗子,面对圆环的内测;外面的建筑划分成一间间囚室”。在《被光抓走的人》中,导演通过新闻报道隐喻我们所居的圆形的地球为一个整体“圆形监狱”:“相同现象一共出现在全球一百五十三个城市和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也包括海洋、沙漠上的无人地带”,和片中代理校长之言“这一次应该是一次全球性的突发事件”来划定区域范围,还有影片第39 分钟直接出现的地球转动渐渐融入黑暗之中的画面,都点明了消失事件的发生地为整个地球而非局部,且确立了地球与其他宇宙空间相对立的、独立的位置,成为被“光”划定出来的区间,远离“被抓走的相爱的人”的囚居之地。
地球作为“监狱”,实现权力规训的途径是明确的:其一,通过光的审判将“消失在不知何处的”“被剩下的”完全隔绝开来,在其中的人仰望太空,感受到被惩罚的失爱之痛和被嘲笑的失婚之痛,身体与心理的“囚徒状态”为爱与伦理的规训权力规划了一处静谧的、隔绝于世并在对爱犯错的羞耻感支配下自愿隔绝于人的空间。地球作为“总体监狱”,故事发生地宜昌这座城则成为更具体的“囚室”。被光关进来的人意图出去,然而没有第二次机会,只能以“越轨”“越狱”的方式进行试探与挣扎。秦山的不知所踪是其一,留下的是屋子里的血迹;胡建平的人间失踪是其二,找回的是溺毙很久的尸体;王杨的拼死证爱是其三,跳楼骨折后被固定在病床上。

电影《被光抓走的人》剧照
影片多次用诸如“你会羡慕被光抓走的人吗”等等场景或对话以及通过演员的情绪表达,对“消失”的优胜感和“剩下”的卑微感进行强化对比,一遍遍加强所要探讨的全景敞视系统的编码。光的规训功能存在之故,以及规训原则为何,一直有赖于片中众人的主观臆测,被监禁的众人费尽苦心寻找证据,给自己的被抛弃寻找到一个自我编织并深信不疑的理由,在科学家证伪之后依然自说自话,不肯放弃也不敢推翻实则是自己编码的无形无迹的权力机器。
福柯认为全景敞视“体现在对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被光抓走的人》光的作用正是如此,拥有爱的人拥有被光带走的权力,没有爱的人连光也未曾得见。
而“全景监狱”的最终目的地,是让被监禁者将“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成为征服自己的本源”。这也是影片中编码的“光弃之狱”所展示出的最终成果。在《被光抓走的人》中,导演向我们展示了这套编码的双刃剑实质:一方面有人如武文学、张燕夫妇从越轨边缘努力回归,以婚姻的静水流深、烟火温暖代表对监禁的服从与对伦理的归顺;一方面有人如赵峰夫妇自我麻醉,并卖力营销由自身定义的另一套爱情规则体系,妄图与“光”的体系裂土分疆。而即使在后者定义的体系边缘,畏畏缩缩最终败走的武文学又一次越轨失败,否认与张燕的爱情失败也并不能被新体系接受,否认新体系的可行性则无法解释被旧体系的抛弃和对另一段感情的放弃,四面如网,处处碰壁,持续质疑自己之后,彻底走回家庭,以对最初的伦理之光告白“我是爱你的”作为向“光”投诚之礼。
二、“权力的目光”、围观以及自省归顺
如果说光的惩戒性质揭示了软科幻叙事背后权力的规训存在,那么散播的谣言与异样的揣测与被揣测,以及被围观之人的自我检视则成为了全景敞视力量的有力阐释。有学者曾经比较分析当前媒介环境下“围观”与圆形监狱的异同,认为两者之中虽然监视者与被监视者在全景中的位置发生了置换,但“二者所达到的效果却一致”。在本片中,“爱”是什么、“爱的标准”是什么,没有一定之规,也无从讲究法律惩处,肉体的监禁退避了,但惩罚却换了一种形式依然存在:与监狱中的管理者以目光监视犯人相同,社会中众人的围观目光也有监控规训的效果。福柯认为目光就是“权力的眼睛”,其作用在于通过目光这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
《被光抓走的人》中的“权力的目光”在李楠的自述里得到最初的确证:“单位同事都在背后没少笑话我”,而后小韩老师对武文学提问“嫂子最近还好吗”也显现出她作为“他者”的目光关注;直到学校找武文学谈话,说给爱人消失了的朱老师报了高级职称,直接了当地挑明了“围观目光”的权威性:“这不光是照顾谁的问题,这还有一个品德的问题。”被剩下的是道德清白没有在爱情里越轨的人,两个都被光留下的则都有越轨嫌疑。目光首先具备了判断道德高下的权威地位,又以报“高级职称”兼具了社会评定地位区分的权威性质,用“现在大家就是这么想的,你能怎么办”旁证了围观目光权威性的不容置疑。所以接下来众人做的各种看似荒唐的努力,都是出于逃避“围观的目光”的惩罚:李楠粉饰在离婚事件中的主动性,在社区调查时强调“我都要跟他离婚了”;武文学同事跟他一样选择修图作假证明爱人当天不在光照区域;武文学甚至不惜当众暴露夫妻床事来证明爱情尚在,也有人跳楼证明“我可以为了你去死”。夫妻之间爱与不爱并不是要证明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给别人明面上或者暗地里的质疑做一个交代,以此避免权威目光的“如芒在背”。正如钟远波所说,目光使被注视者无法逃避成为“目光的猎物”,最终产生“我应该这样而不该那样”的心理。在消失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有人做出这是“抓坏人”的推测,却没有得到传播,李楠单位有人说是“日本的秘密武器”也无人认可,但当“收爱人”的言论一出,立即成为了公众共识,甚至之后政府与科学界辟谣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社会的群众的“标准”。即使嘴上可以说“咱们都是被人挑剩下的,谁还能瞧不起谁啊”,然而单身被剩的与婚内被剩的人之间又自发形成了优越者与被歧视者的对立关系。所以优越者坚持“收爱人”之说,这是他们在除去法律层面和政治层面,可以抓到手里的权威,可以用自己的目光掌控的权威。影片中,每个人处于被光抓走的恐慌和被光剩下的耻辱的双重迷失之下,婚姻内外的每个人沦为他人审视和自我检视的囚徒;而审视他人的围观者也并未得到解脱与欢欣,而是在另一重质疑中疑神疑鬼,生怕过往的宣判一朝被重新解读,自己沦为新的审判解释的囚徒。被抓走的和被剩下的,究竟谁是赢家,成为了高悬于众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电影《被光抓走的人》剧照
除了宇宙之光、社会围观之外,《被光抓走的人》的最后一层监视机制的实现,在于被规训之人的自我规训。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认为人类本性在社会秩序下会塑造出“镜中自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于是一道不知缘由的光成为一次自省爱情的“镜”,被光抓走的人成为剩下的人所要意图成为的“镜中人”。有人矫枉过正,反省不成,责任旁推愤而杀妻;更多的人则小心翼翼检视自己,希望按照规则将自己变成一个符合规训的“镜中自我”。所以武文学在说“都说被光带走的人是有爱情的,好,没问题。”时语气肯定,表达了对所谓规则的信任服从态度,在强词夺理“那也不代表没带走的人就没有了感情,对不对”低声怯懦且用了疑问的语气。片中主持人李诞说“这道光给了真爱一个标准,同时呢也给了我们一个标准”,自我质疑之后众人开始向“标准”靠近。李楠问遍丈夫的所有外遇,一次次受到自己不了解丈夫、丈夫在家很累不舒服的陈述的打击;刘佳一在男友做出“跳楼”这样的证明之举后去医院照顾摔伤的他,等待完婚;武文学在与小韩老师的婚外恋情中主动开房,等待女方的过程中幡然悔悟,悬崖勒马,最终回归家庭,甚至帮助妻子做饭炒菜。但实际上,问题没有解决,正如武文学在面对代校长安排时候所说的“就算是两个人情感上有问题”已经承认了夫妻不恩爱的事实;面对小韩的时候说“这丝毫没有科学逻辑吗”,以科学回应感情伦理,实际是对爱情的回避和心虚。回归的众人并没有检讨婚姻生活中的问题,更没有试图修正问题,没有反思过不爱的原因与探讨如何爱下去的方略,甚至没有一次谈心。他们只是按照标准来修正自己,使自己回归到“爱”该存在的家庭范围里,只要可以交代跟其他人“没得事”,监控自己不越雷池一步。所以精神的监禁在实现自我归顺目的后比法律惩罚更进一步:片中的众人最终走向对“光”的、对伦理的投诚归顺,证实了全景敞视主义的权力效应。影片中第41 分钟仰拍空空荡荡的教学楼,对比之前同角度拍摄的充满生气的教学楼,巨大的静默已经暗示了规训下的个人走向。在悄无声息的空洞里,众人纷纷走入或者重新回归到婚姻家庭的围城,从而兼具了身体和灵魂的双重顺从。李楠在寻找丈夫的过程中,第三者所提出的用身份证查询通话记录或者银行流水,不管出于刻意或者叙事必须,都使影片营造“全景监视”的意味更加浓厚。或者说,影片在光的“全景监狱”控制之后,事实上逐渐转向众人导向的“共景监狱”,即一种围观结构,是众人对个体展开的凝视和控制。
三、婚姻与爱情、伦理与科幻的思辨
《被光抓走的人》进行的对全景敞视机制的编码是完善的、层级明确的,但它毕竟是新时代的文化产品,爱情规则的规训在真爱无存的前提下充满了落后于时代的气息,一直隐忍的张燕、帮助小三小四小五的李楠、被强奸后认识到了爱情的刘佳一,和想要修正自己挽留爱情的武小蕾,包容丈夫并帮助其建立所谓的新派“爱情机构”的邹莉,甚至于赵峰和武文学等男性,影片中无论男女都执着于爱情,或者仅仅执着于婚姻,非婚无法成活的莫名坚持使他们散发出一种自持与委屈,整部影片也意图营造出类似《小城之春》的伦理禁闭,甚至片中大提琴曲《梁祝》都加强了婚姻为坟墓至死终不悔的沉重基调。但影片事实上是将“爱情”与“婚姻”割裂开来,通过被“光”抓走,生死未知的消失审判或者生不如死的被弃处理,将家庭伦理规训的力量无限放大,进而将“归顺”作为被赋予了最高光荣意志的仪式,将“爱”的自由追寻关联为原罪一般的需要割舍的存在,以死亡威胁和群体鄙视组合交织出抛开婚姻考量爱情之时的越位恐慌。
求爱之人皆需越轨,深爱之人皆溺于苦难。然而在现代人性解放的当下,以“光”为官方权力和以民众围观为民间权力的双重强制性的伦理规约,所具备的强大的规训能力使影片表达的婚姻与爱情之思背离了时代元素,将人的本性与爱的自由向伦理称臣的道德垄断形成恐怖威压,这种家庭伦理道德的正义性被不断拔高,才形成了对“光”的神化过程,也即形成了该片科幻样貌的壳子。然而正如霍尔所说的,“技术的霸权运作成功,有赖于被支配阶级和集团的积极赞同”,科幻之“光”的成立,基础条件是众人对于失去婚姻关系走出家庭界限的罪恶感,和认为被爱人抛弃的耻辱感,这大概也是为何影片最终展现出一种莫名回归的天真的缘由。
对全景敞视主义编码践行严格,却在情感逻辑上无法自洽,对爱情的追寻被放置在伦理守则的对立面,对婚姻关系没有原则的固守成为电影的主题走向,这样的道德倾向导致《被光抓走的人》虽有哲学意味,却无命题深度,最终呈现出在现代性的个体解放与传统性的伦理归顺之间、在西方的“放”与东方的“敛”之间,踱步难决、踟蹰不前的保守气息。
①全景敞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创造的新术语,它们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权力功能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