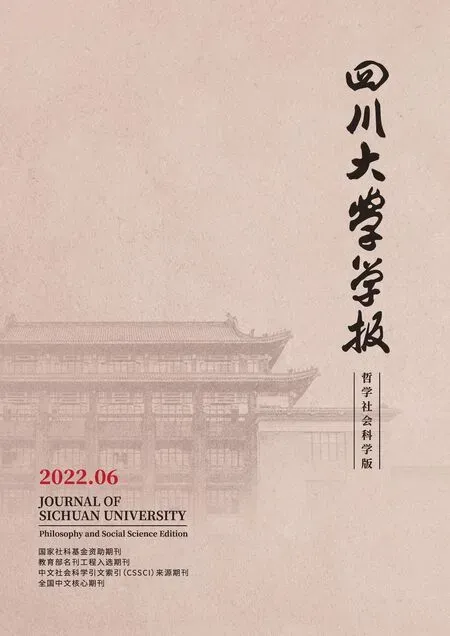西晋名士“约言”观之成因及其文学影响
2022-03-02何剑平刘学涛
何剑平,刘学涛
约言,即以简要之言折难繁理或以省净之言而蕴举多义。西晋清谈以简约为尚,陈寅恪、唐翼明、罗宗强等学者都在论著中指出这一现象,(1)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1页;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75-77页;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1-212页。但未及释证。譬如,西晋名士何以发言遣辞皆推重约言?其约言观与中土本有的论辩言语传统有何承继关系?是何种文化因素或背景导致洛都名士阶层口谈的衍变?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或可裨补前贤研究之所未备。(2)本文所论之“约言”只设定于中土本有的哲理层面的论辩言语传统,未及儒家。是因为儒家所谓“约言”与两晋清谈之“约言”含义不同。如《礼记·坊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514页):“故君子约言,小人先言。”孔颖达疏:“君子约言者,省约其言,则小人多言也。”《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511页)谓孔子编《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以其“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形成《春秋》“约言示义”的笔法。显然,儒家与两晋名士所持之“约言”观实非同一概念,故未在本论文中涉及。
一、中朝名士的“约言”观
魏晋玄学重论疑辩难,包括口头谈论玄学和用论辩体写成书面文字,这种论辩习尚导源于东汉末年识鉴人伦的风气。汉末荐举人才,有为名士“品目”之俗,即所谓“月旦评”,(3)《后汉书》卷六十八《许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35页):“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来又于州郡专设中正一职,选择有人伦鉴识之贤者充任,以评定人物、第其高下,其所作某人行状采取题目之法,简单一二句评语,(4)如王济所作孙楚状,即采取题目之法,《世说新语·言语》第24条注引《晋阳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6页;以下所引《世说新语》文皆出此本,以条标出,不一一注页码):“楚,骠骑将军资之孙,南阳太守宏之子。乡人王济,豪俊公子,为本州大中正,访问宏〔楚〕为乡里品状。济曰:‘此人非乡评所能名,吾自状之。’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仕至冯翊太守。”此外,《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晋阳秋》及《晋书·孙楚传》皆载之。成为汉末荐述后进、选举人才的重要手段。(5)《三国志》卷五十二《步骘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38页)注引《吴书》:“(李)肃字伟恭,南阳人。少以才闻,善论议,臧否得中,甄奇录异,荐述后进,题目品藻,曲有条贯,众人以此服之。权擢以为〔选曹尚书〕,选举号为得才。”此种题目品藻要求品目者具论议才能,被核论者亦须具言语应对之辩才。品目人物可以口头或书面表述,品目若招致疑问,亦可相应采用口头或书面发难;书面品目,持义不同,可以驳议。清谈高论肇端于此。
逮至三国时期,论辩成为上流社会的共同风尚。时人著文讨论,或书函辩答,形成口头(口谈)和书面(手笔、翰墨)两种论辩形式,题旨亦由汉代六经扩至诸子百家。善论议者为时人所崇尚,他们袭采前代名家辩难论辞,著论以精当有条理为贵。(6)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02页。至魏正始年间,洛都的知识阶层清谈日盛,出现追求辞藻的倾向。据记载,何晏与名士共说老、庄及《易》,以“巧而多华”“辞妙于理”为天下士大夫所争效,形成所谓“时人吸习,皆归服之焉”的盛况。(7)《三国志》卷二十九《管辂传》(第821页)注引《辂别传》记管辂与裴使君(即裴徽,徽字文季,曾为冀州刺史)共论何晏名实,裴使君语曰:“吾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又时人吸习,皆归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见得清言,然后灼灼耳。”此期,具口辩才能的名士在处理“理”与“辞”之关系问题时,常为争取论辩之名声而刻意“美其声气,繁其辞令”,追求辞巧,期于必胜,导致玄学论辩中泛滥多言、“辞烦而无正理”。(8)李崇智:《〈人物志〉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93页。这种以辩巧之文眩惑众听的做法,引起一些清谈名士的不满。由此,“不务烦辞”成为魏晋之际中土论议中的言语追求。至西晋,遂形成谈论中的“约言”观念。
推重“约言”较早反映在西晋东都洛阳的中朝名士群里。(9)“中朝”,指西晋。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52页)附录引《晋书目录》:“右晋十二世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都洛阳,五十四年;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二年。晋南渡以后,称洛都曰‘中朝’。”《世说新语·赏誉》第23条:“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晋书》卷六十九《周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51页):“顗在中朝时,能饮酒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称无对。”“中朝名士”的命名源自袁宏,据《世说新语·文学》第94条刘氏注,袁宏作《名士传》成,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10)《晋书·袁宏传》(第2398页)载袁宏作《竹林名士传》三卷。袁宏分名士为正始、竹林、中朝三期,勾勒出东晋之前魏晋玄学发展之三阶段。这种说法,已为历来学者所认同。在此中朝名士名单中,有五位都是“约言”的推重者。其中,《世说新语·赏誉》第25条刘注引《晋阳秋》: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同篇第41条刘注引《名士传》:庾敳,“不为辨析之谈,而举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品藻》第10条刘注引《江左名士传》:王承,“言理辩物,但明其旨要,不为辞费,有识伏其约而能通”;《文学》第12条刘注引《晋诸公赞》:刘汉,与王夷甫友善,“亦体道而言约”。另有《晋书》载:阮瞻,“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11)《晋书》卷四十九《阮瞻传》,第1363页。
在上述五人中,乐广的“约言”为同时代的名士阶层所称道,王衍、裴楷皆赞其言简而自感烦言之无益。事实上,乐广的谈说因言约旨远不仅为同时代人所推重,在之后的太康元年(280)也被当时朝之耆旧、时任尚书令的卫瓘所称赞。(12)唐翼明:《魏晋清谈》,第222页。卫瓘热衷清谈,颇了解“正始之音”,称乐广为继何晏等人之后使清言绝而复闻的关键人物。(13)《世说新语·赏誉》第23条刘注引《晋阳秋》:“尚书令卫瓘见广曰:‘昔何平叔诸人没,常谓清言尽矣,今复闻之于君。’”又引王隐《晋书》:“卫瓘有名理,及与何晏、邓飏等数共谈讲,见广,奇之曰:‘每见此人则莹然,犹廓云雾而睹青天。’”阮瞻对“理”与“辞”主次的处理,与王承言理辩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的做法颇相契合,二人皆能以简约之言折繁理,或者说,王承善以约言而举多义,在论辩中能很好处理“言辞”与“义理”之主次关系,形成论辩言说中不竞繁辞、通理则止的风格,也即是时代所推崇的言论风格。更多的记载也表明,乐广为清谈之领袖,与官尚书令的王衍俱名重当时,在西晋东都洛阳,以王衍为中心,形成一个口头谈论皆以言辞简约而获誉的名士群体。“约言”成了中朝名士的共同特色。
二、“约言”的生成背景
中朝名士谈论推重“约言”有两方面的背景因素:一是中土本有的论辩传统,二是西晋汉译佛典的传播。
有关中土本有的论辩言语传统,就现有文献来看,早在先秦诸子时代即有对论辩语言功能的认识。如刘向《别录》记邹衍谓“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认为辩之为辩,首在于分别事理,明其所指,使人知晓;至于假借“烦文”“饰辞”“巧譬”“引人声”等方式进行论辩,则最终妨碍大道,有害君子。(14)《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70页。《孔丛子·公孙龙》中记录平原君对公孙龙说:“公无复与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辞胜于理,终必受诎。”(15)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3页。所展现的即是论辩立言以理不以辞、诬理之辩其辞终屈的道理。至三国时期,徐干在《中论·核辩》中,对何为“辩”作了明确限定:“辩之为言别也,为其善分别事类,而明处之也,非谓言辞切给,而以陵盖人也。”在徐干看来,论辩的言语只是为了明析事理,而不是靠言辞的凌厉压倒别人,他反对“不论是非之性,不识曲直之理,期于不穷,务于必胜”的蛮横狡辩及“美其声气,繁其辞令”的利口之辩,主张论辩的简约有理有节:“辩之言必约,以至不烦而谕,疾徐应节,不犯礼教,足以相称,乐尽人之辞。”(16)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5-286、278页。有关论辩的名实相符的看法,亦见《孔丛子·连丛子上》(《孔丛子校释》,第454-455页):“子丰曰:‘夫物有定名,而论有一至。是故有可一言而得其极,虽十言而不能夺者,唯析理即实为得,不以滥丽说辞为贤也。……夫论辨者,贵其能别是非之理,非巧说之谓也。’”刘邵著《人物志》,将人流之业分为十二种,“口辨”即为其一。刘劭强调辩者论理宜“不务烦辞”,强调论辩语言的简约性,告诫辨博之人宜戒其辞之泛滥;他在崇尚清谈之道的同时,更留意论辩的名实相符,认为:“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17)以上参见李崇智:《〈人物志〉校笺》,第54、93-100页。强调论辩最基本的规范是遵循事实。至西晋清谈盛行的时代,老子的“无名”“无言”之论、《庄子》“言不尽意”之旨以及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观,都表达了对语言工具局限性与缺陷性问题的认识,这些论点均成为魏晋玄学家争辩和发挥的重要命题。(18)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9页。洛都中朝名士所持论辩的“约言”观应是受到此一思路启示。
除了本土“言”“意”关系论题思路的影响外,更值得探究的还有西晋洛阳汉译佛典《般若经》《维摩诘经》等在中朝名士中的传播及影响。洛都自汉以来,已被佛化,至西晋时更成为佛教中心,这里有佛寺四十二所,(19)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云“至于晋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卷四“宝光寺”条亦云,参见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152页。又,《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291页)云“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有竺法护传译佛典,竺叔兰、支孝龙敷宣《般若经》于河南。与此同时,在“当时谈宗”(20)《世说新语·言语》第23条注引《晋诸公赞》:“夷甫好尚谈称,为时人物所宗。”《晋书》卷四十九《阮修传》(第1366页)记阮修曾与王衍谈《易》:“王衍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有所未了,研之终莫悟。”王衍周围聚集了一批以谈论简约获誉的名士,这些洛都名士与名僧渐相交接。尤其是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大乘经典《般若经》“大行华京”,(21)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放光分如檀以泰康三年,于阗为师送至洛阳,到元康元年五月,乃得出耳。……并《放光》寻出,大行华京,息心居士翕然传焉。”参见僧祐:《出三藏记集》,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65-266页。为当时的清谈名士所传诵,其中的般若“无相”之说尤为名士所赏重,成为持约言谈论的理论依据。
表6 Panel E列示了国有与民营企业科技产出的回归结果。可以明显发现,国有企业在这一轮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中是创新科技产出的主体,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回归中供给侧改革系数13.178和10.263,分别要显著大于民营企业的3.399和4.696。可见国有企业受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的激励最为突出,大幅度增加了专利的申请。而民营企业相对较保守,政策的引导与激励效果差强人意。
何谓“无相”?据后秦鸠摩罗什所译用以解释《般若经》的大乘论典《大智度论·释初品中迴向》中的说法,佛法有二种:一者世谛,二者第一义谛。世谛故,说三十二相;第一义谛故,说无相。(22)《大智度论》卷二十九,《大正藏》第25册,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第274页上。则无相属于第一义谛的范畴。但佛教徒在论议的过程中意识到语言的局限性,认为佛法中的真谛(至理玄致)是不能用语言表述的,所谓“第一义,妙寂离言”,即“无言说乃至离答”是论说的极致。臻此“幽寂无言”之境,若再运用语言说明则“伤其旨”“失其真”。这是从第一层面所说的佛法,即“如”的境界。而要做到如,则须达到无相。然而,实相理深,非一时能悟,悠悠众生,去理殊隔,又须教法开启。所以佛教圣人,虽然了知一切法相不可说,仍然要资借语言以通达津道,假托形像以传真,为众生种种方便说法。正如梁慧皎所言,语言是不真之物,不获已而陈之。(23)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3页。
《般若经》在许多段落谈到语言的局限性。语言作为工具并不能完全展现佛法所要传达的全部内涵,所以在经书的表述中,语言是名字、相、假名。如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沤惒品》中记载佛之弟子须菩提的疑问:诸法本无分别,佛如何以“五阴”(色、痛、想、行、识)及“内法”“外法”“善恶”“道俗”等各种名字概念来区别呢?有如下对答:
须菩提言:“世尊!若诸法不当别,如来云何言:‘是色、是痛、是想、是行、是识?’云何说:‘是内法、是外法、是善是恶、是漏是非漏、是道是俗、是生是死、是有为法是无为法?’世尊!如是诸法将无分别。”佛言:“不也。但以名字数示众生,欲使解耳,亦无所分别。”“世尊!是无名号之法,云何以名相教授众生,欲令得解?”……须菩提言:“世尊!道亦无所有,泥洹亦无所有,云何说言是须陀洹、是阿罗汉、是辟支佛、是三耶三佛乎?”佛言:“是皆因无为而有名,是须陀洹、是阿罗汉、是辟支佛、是三耶三佛耳。”“世尊!从无为而有名耶?”佛言:“不也。但以言说,有是言耳,不从最要第一之义也。所以者何?第一要中无若干行也,亦不施若干,为爱断者故施后际。”“世尊!诸法相各自空,真际不可知,云何知有后际?”佛言:“如是!诸法相空,真际不可知,何况有后际?不知诸法相空者,我为是辈说前后际耳,诸法相者亦无前后。”
这里的所谓“内法/外法”“善/恶”“漏/非漏”“道/俗”“生/死”“有为法/无为法”,皆为佛所说法,诸种命名是佛为教授众生的方便而借假的一种语言概念上的施设工具。佛陀在此明示诸法相本无相,无所分别,然而有众生不知诸法相本空,故为这些人以不同的命名作各种比喻分别的言说以使其解悟。佛将本为无名号之法,示以名相(名言概念)以教授众生,若站在第一义之高度则本无此施设。缘此,《放光般若经·超越法相品》中记佛回答须菩萨提“何等为名字相”之问题时,强调“名字者不真”:“假号为名,假号为‘五阴’,假名为‘人’、为‘男’、为‘女’,假名为‘五趣’及‘有为’‘无为法’,假名为‘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三耶三佛’。”(24)以上引文参见《放光般若经》卷十六、十八,《大正藏》第8册,第113页下-114页中、128页下。这种命名分类只是为言说的方便,而世间的愚人易缚著于这些名相,于中起分别之心,由此不能认识事物之本质。因此智者须告诫众生超越有、无二相,以臻无相之境,即般若所谓实相之境。如何臻至无相之境?《大智度论·释随喜品》中有对般若无相说的概括:
无相有三种:假名相、法相、无相相。假名相者,如车、如屋、如林、如军、如众生,诸法和合中,更有是名。无明力故,取是假名相,起诸烦恼业。法相者,五众、十二入、十八界等诸法。肉眼观故有,以慧眼观则无,是故法亦虚诳妄语,应舍离法相。离是二相,余但有无相相。有人取是无相相,随逐取相,还生结使,是故亦不应取无相相。离三种相,故名无相。若无有相,是中无所得,无得故无出;若法无得无出,即是无垢无净;若法无垢无净,即是无法性;若法无性,即是自相空;若法自相空,即是法常自性空;若法常自性空,即同法性、如、实际。(25)《大智度论》卷六十一,《大正藏》第25册,第495页中。
据此文所举,无相有假名相、法相、无相相等三种,而假名相、法相乃为分别诸法(包括世俗法与佛法)而施设的语言概念。假名相是世俗为认识现象世界而给予万物以不同的名称和概念,而法相则是佛陀为佛法而制定的各种教义教法,此二类皆属名字、相、假名、语言,众生于中易生执著,种种取相,不能以般若智慧认识到世界之本质(即空相)。故须超越离弃假名相、法相此二相,致“无相相”之境。而“无相相”仍未免执著取相,故亦须离弃。以上三相其本质皆无所得,常自性空,即同诸法实相(“法性、如、实际”),而实相法中无有分别,即一相,是无相,般若波罗蜜即无相之法。
无相说在《维摩诘经》中也有表现。思想内容来源于般若经的《维摩诘经》,属大乘中观派的作品,东汉末年传入中土后,对中国文学艺术产生至深影响。三国支谦译《佛说维摩诘经》有一些段落言及佛教之语言哲学观,以下我们以支谦译本、鸠摩罗什译本的对等段落为例:
(一)支谦译《佛说维摩诘经·弟子品》记维摩诘谓须菩提言:“想为幻而自然,贤者不曰一切法一切人皆自然乎?至于智者,不以明(眼)著,故无所惧。悉舍文字,于字为解脱,解脱相者,则诸法也。”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记维摩诘谓须菩提言:“一切言说,不离是相(幻相),至于智者,不著文字。……文字性离。无有文字,是则解脱。”
(二)支谦译《佛说维摩诘经·菩萨行品》引佛告阿难语:“有以清净,无身无得,无言无取,而为众人作佛事。”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菩萨行品》引佛告阿难语:“或有清净佛土,寂寞无言、无说、无示、无识、无作、无为,而作佛事。”(26)以上引文参见《佛说维摩诘经》卷一、二,《大正藏》第14册,第522页中、533页中;《维摩诘所说经》卷上,《大正藏》第14册,第540页下、553页下。引文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鸠摩罗什就“或有清净佛土,寂寞无言无说”释曰:“有形色无言教,如维摩诘默然成论比也。”他以“有形色无言教”类比维摩诘的“默然成论”,并指明后者出自《维摩诘所说经》中文殊师利问维摩诘居士何为“不二法门”的对答段落:
如是诸菩萨各各说已,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师利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
罗什于此段经文有注曰:“夫默、语虽殊,明宗一也。所会虽一,而迹有精粗。有言于无言,未若无言于无言,故默然之论,论之妙也。”其意谓,宾主问答分为两个层次:三十二菩萨及文殊等所说并属言说之教,维摩诘之默然则显示的是绝言之教,二者自有精粗深浅之别。显然罗什赏誉的是后者。僧肇注同于罗什,认为“法相不可言,不措言于法相,斯之为言,言之至也”;(27)僧肇《涅槃无名论》(《大正藏》第45册,第157页下):“然则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无之者伤其躯。所以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须菩提唱无说以显道,释梵乃绝听而雨花,斯皆理为神御,故口为之缄默。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晋人张湛注《列子·仲尼》“用无言为言亦言,无知为知亦知”句云:“方欲以无言废言,无知遣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于言知也。”参见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6页。而竺道生指出文殊言说的过失在于“虽明无可说,而未明说为无说也”,维摩默然无言之原由在“以表言之不实,言若果实,岂可默哉”。(28)以上引文参见僧肇等:《注维摩诘所说经》卷九、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6、155、154、155页。即僧肇所谓“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29)僧肇:《涅槃无名论》,《大正藏》第45册,第157页下。由此可见佛门对无言境界的推崇。
综上,佛为分别佛法所立的名言概念及世俗为认识现象界而施设的语言概念皆有局限性,故须否定名言概念,所谓离言、遣言,最终回归无相之境。中朝名士对般若“无相”之说的看重,与当时《放光经》《维摩诘经》在洛阳流传的传播密切相关,而我们之所以说中朝名士的约言观受到了佛典的影响,这里还有两条昭然著明的证据可示:
一是佛教史传记载了两条中朝名士与西晋释门交游的重要信息,分别为:乐广与《放光经》及《异毗摩罗诘经》的传译者竺叔兰有接触,竺叔兰因具机辩之才而为乐广所赏识;(30)《出三藏记集》卷十三《竺叔兰传》,第520页。阮瞻、庾敳与名僧支孝龙“并结知音之交,世人呼为八达”。(31)《高僧传》卷四《晋淮阳支孝龙传》,第149页。关于“八达”,《世说新语·品藻》第17条注引邓粲《晋纪》,《德行》第23条注引王隐《晋书》,《任诞》第13条注引戴逵《竹林七贤论》,皆提及“八达”之号。旧题陶潜撰《集圣贤群辅录下》(《宋本陶渊明集》卷十,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210页)载,陈留董昶、琅邪王澄、陈留阮瞻、颕川庾敳[一作“凯”]、陈留谢鲲、太山胡毋辅之、沙门于法龙、乐安光逸,并谓“晋中朝八达,近世闻之于故老”。于法龙当为支孝龙,所记其他士人名目与《世说新语》大致相契。《圣贤群辅录》二卷,一名《四八目》,旧附陶潜集中,《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60、1274页)子部类书存目一、集部别集类一详辨其非潜之作,为北齐阳休之误信而增入潜集。然观其叙两晋人物,最晚近者乃东晋安北将军王坦之,撰者必定亲自访之于故老,故未可轻易定其为赝作。支孝龙是竺叔兰的僧友,耽味于般若“无相”之说,尝于竺叔兰初译《放光经》后,“得即披阅,旬有余日”,就在当时西晋名士群中致力宣讲此经。(32)《高僧传》卷四《晋洛阳朱士行传》,第149页。鉴于其与阮瞻、庾敳的特殊交游,《放光经》在当时精英阶层中的传播是完全可以推知的。也即是说,元康年间(291—299)正是《放光波若》《维摩诘经》得到翻译并流传的时间。
二是《世说新语·文学》第18条所记有关“三语掾”的问答:
阮宣子(当为阮瞻(33)本文认为当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09页)引程炎震之说,阮修当作阮千里(瞻)。此主张又见曹道衡、沈玉成:《阮瞻生卒年与“三语掾”》,《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8页;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6页)亦以阮宣子当作“阮千里”。)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
此则记载叙及两件事:一为阮瞻与太尉王衍就儒道同异的问对,阮瞻因善于言说而被辟为掾;(34)逮至唐代,“三语掾”的对答故事有变化,形成两个流传系统:一以“三语掾”为阮瞻、王戎事,载《晋书·阮瞻传》,后《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惠帝元康七年”、《册府元龟》卷二十六“幕府部·辟署一”及《册府元龟》卷八百二十三“总录部·清谈”皆从之;一以“三语掾”为阮瞻、王衍事,如《艺文类聚》卷十九“人部三·言语”、《北堂书钞》卷六十八“设官部二十·掾”、《太平御览》二百九“职官部七·太尉掾”及《太平御览》三百九十“人事部三十一·言语”皆引《卫玠别传》所载此事。前一个系统略去卫玠(或王衍)与阮瞻有关“三语掾”颇具玄理的对答内容。二是卫玠与阮瞻就“三语掾”展开的对答。两件事之间具连续性。第一件事记录的是阮瞻主张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同说,并因此一玄学清谈中之重要命题而得王衍赏重。由王衍、阮瞻的问答,可见“名教即自然”在西晋末已是颇为流行的看法,(35)唐翼明:《魏晋清谈》,第131页。从中亦可见当时思想界取消名教和自然的对立,消弭其差异性,以调和儒道二家的努力。(36)龚斌:《世说新语校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45页。《资治通鉴》系此事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37)其载曰:“戎为三公,与时浮沈,无所匡救,委事僚寀,轻出游放。……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参见《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18-2621页。则此事发生的时间是在竺叔兰所译《放光经》及《异毗摩罗诘经》得到传播之后。这就提示我们,“三语掾”调和儒道同异的问对在语言策略上借助了洛都佛教的影响元素。也即是说,在当时中朝名士群体所接受的知识体系中,除了受老庄之学的影响外,处于同一传播时空的般若学说也提供了同等的启示和参照。世谓阮瞻为“三语掾”,从“三语掾”至“一言”再至“无言”的语言互动,充分体现了当时士子的语言观念,即假名的语言可以被逐次破除、遣去,这种倡导去言、省言的观念自然使我们联想到当时在洛阳流行的般若无相之说、维摩无言之教的影响。佛教新知不仅给当时以乐广、阮瞻为代表的中朝名士及彻底反对“名教”的“激烈派”名士发挥名教与自然相同之义提供了一种协调的理论,同时也给他们的清论注入了遣言去执的哲学思考。在以上汉译佛典新学说传播的语境下,我们若重审上引“三语掾”的这段言寡而旨畅的问答,就会发现它与汉译佛典的关联性不容忽视。
另外,《世说新语·文学》第75条记庾敳作《意赋》成,其从子庾亮见赋,问赋之有意、无意,敳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这使我们想到竺叔兰与无罗叉合作翻译的《放光般若经·学品》中载有须菩提语舍利弗“若意无念时,亦不见有意,亦不见无意”的这段话,用以说明“菩萨意性广大而清净”的特征(同经异译本——西晋竺法护译《光赞经·了空品》中作“有心”“无心”,用以讨论“菩萨摩诃萨心本清净,清明而净”);(38)《放光般若经》卷二,《大正藏》第8册,第13页中-下;《光赞经》卷三,《大正藏》第8册,第166页中-下。而《意赋》中亦有“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39)《晋书》卷五十《庾敳传》,第1395页。可为比类。洛都名士与名僧之交情及于汉译佛典之赏重盖可窥一斑矣。
三、“约言”观的文学影响
前文所论,魏晋知识阶层崇尚清谈,时人著文讨论,或书函辩答,形成口头(口谈)和书面(手笔、翰墨)两种形式;口谈论议优胜者为名流所宗尚。但言理之士有拙于口辩而善于著论者,故口头论辩和书面论议分途并进。(40)《世说新语·文学》第74条云:“江左殷太常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刘孝标注引《中兴书》:“殷融字洪远,陈郡人。桓彝有人伦鉴,见融,甚叹美之。著《象不尽意》、《大贤须易论》,理义精微,谈者称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与浩谈,有时而屈;退而著论,融更居长。”(《晋书》卷七十七《殷浩传》所载同)第73条云:“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虞与广名位略同。广长口才,虞长笔才,俱少政事。众坐,广谈,虞不能对;虞退,笔难广,广不能答。于是更相嗤笑,纷然于世。广无可记,虞多所录,于斯为胜也。”可见,善著论者未必善口头论难,而利口者未必善著论。口头论议常会刺激书面议论文的产生。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多口谈和文藻兼备者。他们用论辩之体写成的清谈文字长于辨难,析理绵密,叙次分明,重逻辑思辨,如嵇康、向秀论文。(4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舒芜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46页。逮至西晋,玄学家兼具口头谈论与用论辩体著文两种才能者寥寥,在口头论辩方面竞逐巧辞繁说,致理义不明之弊。“约言”是中朝名士对于清谈语言的讲究,是理想谈论必备的条件之一,对两晋南北朝文学有至深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约言”作为一种口头论辩之言语方式,为众多耽于清谈的文士所赏重。南北朝时期的史料载录了时人对约言风格的推崇,如《世说新语·文学》第53条云“客主有不通处,张(凭)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第56条记殷浩与孙盛就《易象妙于见形》展开共论,后刘惔至,“辞难简切,孙理遂屈”。据《晋书·刘惔传》,孙盛是先作《易象妙于见形论》,然后简文帝使殷浩难之。此即先著论(书面),然后以论为主旨展开论议(口头)。又,《赏誉》第113条记简文评殷浩清言之不足云“渊源语不超诣简至”;第133条注引《王濛别传》说王濛“谈道贵理中,简而有会”。《言语》第39条云:“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据《宋书·谢弘微传》,谢混族子有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瞻等才辞辩富,弘微“每以约言服之”,混特所敬贵,号曰微子。谓瞻等曰:“汝诸人虽才义丰辩,未必皆惬众心,至于领会机赏,言约理要,故当与我共推微子。”又据《颜延之传》,颜延之极富辩才,永初中(420—422),以儒学著称的周续之被征诣京师,高祖“使问续之三义,续之雅仗辞辩,延之每折以简要”,上又使延之还自敷释,延之“言约理畅,莫不称善”云云。(42)以上参见《宋书》卷五十八、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91、1892页。这意味着,东晋以还,诸多著名文学家都继承了中朝名士“约言”的言说风格,不刻意追求辞胜及辩论技巧。齐永明年间,由临川王常侍朱广之所作《疑夷夏论咨顾道士》,于结尾谈及辩论,谓“若执言损理,则非知者所据”,又谓“维摩静默,非巧辩所追”,倡导“贵不在言,言存贵理”的价值取向;(43)僧祐:《弘明集》卷七,《大正藏》第52册,第45页中。梁刘孝标采摭辩士材料为《世说新语·文学》第58条及陆机《演连珠》第二十四首作注,讥刺如惠施、兒说、苏秦、张仪之辩士以辞辩竞胜的论题难以流存,表现出对巧辞而无理者的不赏重。相似的观点亦见于刘勰《文心雕龙》,如《论说》中谓“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反对单方面为追求辞辩而违越正理的“曲论”;《议对》中认为“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对单纯追求辞辩而造论者提出批评,而此种观点在《诸子》中表现为对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辩的贬斥:“公孙之白马孤犊,辞巧理拙。”(44)以上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8、438-439、309页。亦可见其余绪。
其二是持“约言”风格的中朝名士与文学家的交往影响了文学创作。这方面的典型作家当属陆云。不同于其兄陆机的文章偏于繁缛,如《文心雕龙·才略》中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刘勰在《镕裁》中比较二陆文章风格,认为:“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45)以上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700-701、544页。而陆云的写作崇尚“清省”则当有口头玄学之背景。《机云别传》说陆云“亦善属文,清新不及机,而口辩持论过之”;(46)《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抗传》注引,第1360页。《晋书·陆云传》谓陆云有才理,“少与兄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并载传说陆云赴洛途中与王弼谈《老子》事,谓“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47)《晋书》卷五十四,第1481、1485-1486页。这些记载表明,陆云谈玄简要精到、不尚繁缛,其口辩才能长于乃兄。又据嵇君道(嵇含)语,二陆在元康年间入洛,时洛阳清谈甚盛,所谓“诸谈客与二陆言者,辞少理畅,语约事举,莫不豁然”云云,(48)《北堂书钞》卷九十八“艺文部四·谈讲十三”引葛洪《抱朴子》,董治安主编:《唐代四大类书》第一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4页下。恰可证明陆云论文提出“清省”的审美标准与洛都中朝名士口头谈玄有直接关系。
沈约称西晋元康年间的文学“潘陆特秀”,“缛旨星稠,繁文绮合”,(49)《文选》卷五十《宋书谢灵运传论》,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218页。指出西晋文学的特点是注重辞华,而潘岳、陆机为西晋文学的代表。不过两人的风格也有差异。如《世说新语·文学》第84条注引《续文章志》曰:“岳为文选言简章,清绮绝伦。”第89条记载:“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杨明曾经指出:简章,当即简约章明之意,其意与孙绰所谓“浅而净”相合。(50)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5-116页。这表明,仅就辞采而言,潘、陆似同调,二人文风皆辞藻宏丽,但潘岳不如陆机繁芜,此为何种原由所致?
我们认为,除才性差异,潘岳也应是受到中朝名士中既能玄言又善文藻之玄学家影响。其证有三:第一,臧荣绪《晋书》谓潘岳“总角辩惠,摛藻清艳”,(51)《文选》卷七《籍田赋》李善注引,第337页。所谓“辩惠”,自然与谈辩风尚有关。第二,潘岳所交游者多崇尚玄谈,如其作为贾谧二十四友之首,与石崇、欧阳建等相友善。石崇不仅为清流巨子,且尊崇佛教。(52)《弘明集》卷一《正诬论》(《大正藏》第52册,第8页下- 9页上):“又诬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诛云云。”《世说新语·仇隙》第1条注引《晋阳秋》曰:“欧阳建字坚石,渤海人。有才藻,时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石崇《赠欧阳建诗》说:“文藻譬春华,谈话如芳兰。”(53)《北堂书钞》卷一百“艺文部六·叹赏二十一”,董治安主编:《唐代四大类书》第一卷,第423页上。盛称其既善文藻又富辩才。欧阳建还作有《言尽意论》,是中原传至江左谈名理的杰作,其主旨在说明物先于名而存在,即所谓“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54)《艺文类聚》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41页。之所以用“名”、存“言”,是因为存在辩物、畅志的现实需要,致用须有言教。可以推断,此文当产生于清谈极盛与大乘般若学在洛都中朝名士群中传播之双重背景下。此外,与潘岳友善的夏侯湛,亦文章宏富,且富才辩,潘岳称其为“英英夫子,灼灼其俊。飞辩摛藻,华繁玉振”。(55)潘岳:《夏侯常侍诔并序》,《文选》卷五十七,第2450页。夏侯湛在文学风格上,重气韵而辞采不竞,与当时主流文风有异,这当与其在《雀钗赋》中对“昔先王”为兴道立教而“不留志于华好”之懿范的推重和认同有关。(56)《艺文类聚》卷七十“服饰部下·钗”引晋夏侯湛《雀钗赋》,第1834页;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第三,《世说新语·文学》第70条载乐广“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潘“直取错综,便成名笔”。这昭示:尽管西晋将口头清谈和善于属文两种才能集于一身者不多见,(57)徐樑:《西晋时期玄学与文学不兼容现象之构成》,《文学遗产》2018年第6期。但长于谈论者与娴于属文者之间有结合与互动。西晋玄学家们以主要精力来展示自己的辩论才能技巧,尽管他们当中能谈不能写者居多,(58)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第249页。然而他们当中的贵尚约言的清谈领袖以及口头文采与书面文采兼备的玄学名士,已在理论探讨层面给予文学创作活动以启发和沾溉。
其三是“约言”作为风格类型范畴被运用。如前文所论,约言风格的形成,既有中土的因素,也有来自西晋汉译佛典语言哲学思辨风尚的影响。在清谈极盛之元康年间,大乘般若学当已为洛都之中朝名士所熟知,这些受佛教习染的中朝名士出口成章、便成文彩,然多贵尚“约言”谈论。虽然在西晋言语、文学分为二途,然中朝名士之“约言”已然影响到当代及后来的作家文学。《文心雕龙·时序》中谓“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正是说明西晋知识精英所崇尚的谈论风气对文学文体的影响。“约言”由此作为风格类型范畴被运用。东晋谢尚《谈赋》所谓“斐斐亹亹,若有若无。理玄旨远,辞简心虚”,(59)《北堂书钞》卷九十八“艺文部四·谈讲十三”引,董治安主编:《唐代四大类书》第一卷,第414页上。即是对这种风格特征的概括。逮至梁代,“精约”与“繁缛”对举成为《文心雕龙》文体论的重要术语,如《体性》中论及文章体貌类型,说“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此“八体”包括“精约”与“繁缛”二体。所谓“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核字省句是指文辞的洗练、节省,而剖析毫厘者,指其对义理之剖析精密细微,是义理的分析方法与特点。(60)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续篇)》,《读文心雕龙手记》,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73页。这可以《丽辞》中“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之说相证。而所谓“繁缛”,即“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文心雕龙》有多篇表现出节制繁辞的倾向,如《议对》中云“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并盛称公孙弘之对策“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定势》中云“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镕裁》云“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风骨》云“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61)以上引《文心雕龙》文,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校注》,第675、505、588、438、439、530、543、513页。这些主张均从“繁”与“约”的对比中,突出“约”文的优胜之处。
当然,我们亦应看到,由于以乐广、阮瞻为代表的西晋洛都名士,于口头论辩过度强调“理足则止”,“不务烦辞”,排抑巧言华辞,执于一端,未能将“理”与“辞(言)”融合兼俱,导致诗歌创作文采的缺失、意象的弱化。钟嵘《诗品总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62)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2页。这段文字论及西晋怀帝永嘉时期的诗篇创制对东晋诗坛的影响,其所谓“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正是西晋玄言诗的主要特征。这也说明西晋末年,善口辩的洛都名士们多不善属文著述,他们谈玄崇尚约言,故在处理“言辞”与“义理”之主次关系时,往往未能顾及五言诗原有之文藻特征,而以清言析理之论辩体适之,导致理过其辞,殊乏文采。若溯其源,则持约言观的洛都名士难辞其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