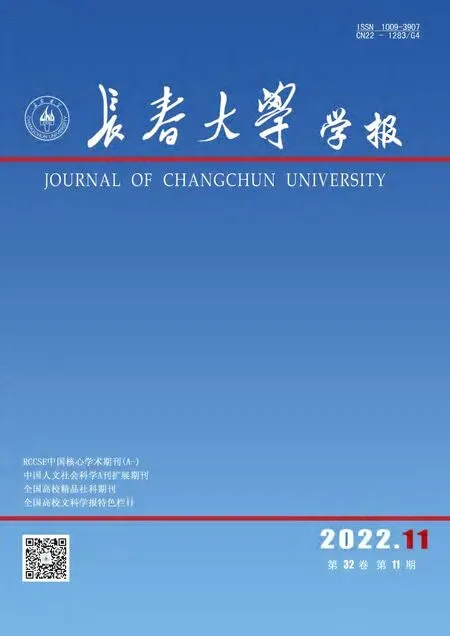新媒体对日本现代童谣的影响
2022-03-02潮洛蒙
潮洛蒙,李 莹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57)
日本童谣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依据其产生的时间和特点可大致分为四类,即江户时代以前的传统童歌(わらべ唄)、明治时期的“唱歌”(しょうか)、大正时期的创作童谣和1945年之后的现代儿童歌谣。日本现代儿童歌谣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战后全新的时代背景、迅速发展的科技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等,都在对日本现代儿童歌谣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也为其多样化发展推波助澜。日本现代童谣的传播已经不再局限于语言媒介和文字媒介,到目前为止经历了广播、唱片、电视、磁带、CD、电影、动漫和网络等多种新兴电子媒介传播手段。根据媒介环境学的传播理论,媒介具有物质性,可以参与建构社会文化与文明,甚至参与建构感知和观念[1]。媒介技术促成的各种结果往往与媒介的固有偏向性相关。笔者认为,在新时期日本现代童谣的传播媒介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及时研究不同媒介对日本现代童谣的影响以及日本现代童谣在多种媒介的作用下产生的变化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观中日两国关于日本童谣的研究,日本学界大多是关于童谣的音乐性、教育性的研究,还有部分童谣史研究以及童谣特质、唱歌和童谣的比较研究等,可以说各类研究视角多元,但其中针对童谣与传播媒介关系的研究尚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东美材的《童谣的近代》[2]一书对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传播媒介产业中首次出现的“儿童”形象的探究;鲸井正子的《童谣唱片的教育意义》[3]一文通过纵观日本童谣唱片的发展来分析童谣唱片的教育意义等。而国内学者对日本童谣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对个别作家或作品的研究,如对金子美玲童谣诗的研究,对竹久梦二童谣作品的翻译研究等,目前还没有媒介转换与日本现代童谣关系的相关研究。整理先行研究后可以得知,日本和国内对于日本现代童谣的研究中,鲜有从新媒体角度对现代儿童歌谣进行的分析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从日本童谣的传播媒介角度入手,分析新型媒体形式对于日本现代童谣的影响及具体表现,以期加深对日本童谣的进一步认识。
一、童谣传播媒介的转变
日本传统童歌产生于儿童游戏中,且大多依靠语言媒介传播。20世纪初期,日本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童谣传播媒介的转换做足准备。明治时期文部省音乐教材的发布及大正时期各类儿童杂志的涌现,促使日本童谣更多依靠文字媒介传播。当时日本正处于高速发展的经济腾飞期,经济的富足打破了日本传统村落聚居的地域特点,城市化加剧了民众之间的人情淡薄,原本“儿童团体”的游戏场所日益消失,日本童谣也随之进入短暂的冷落期。而幸运的是随之出现“生育热潮”,新生儿的大量诞生加之儿童游戏场所重新组建,如保育园、幼儿园等,引起人们对于童谣的关注。作为儿童感知世界的途径和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童谣再度引发热潮。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对于童谣日益上升的需求等多种因素,促进了童谣传播媒介的再次变化。1924年,日本电气公司正式开始无线广播服务,童谣开始具备了通过电子媒介传播的可能性。新媒体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童谣类的广播节目开始出现。1949年,由日本放送协会(NHK)主办的《唱歌的阿姨》节目一经播出广受欢迎,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的粉丝。而进入60年代后,电视的出现给予广播节目一记当头棒喝。电视音画一体的播放效果远高于只能通过声音传递童谣的广播节目,于是,电视开始取代广播成为童谣传播的主要途径。1961年,前身为广播节目《唱歌的阿姨》的电视版《唱歌的绘本》开始播出。大阪朝日放送协会主办的《ABC孩子的歌》也是优秀的童谣电视节目代表之一。童谣节目一夜之间火遍日本,节目中的童谣演唱者也搭上了童谣与新媒体的顺风车,名震一时的有川田正子、安西爱子等。除电视节目外,童谣还作为动漫主题曲出现在银幕上。1966年,奥特曼系列动漫正式播出,其中的插曲、主题曲等时隔多年仍在许多人记忆中闪闪发光。而离现在更近的有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主题曲,如《千与千寻》(2001)中的童谣作品《与你同在》更是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唱,日本现代童谣开始更多地以儿童歌谣的形式出现。
至此,童谣的传播完成了由语言媒介到文字媒介、再到电子媒介的转变,日本童谣在新媒体形式的推动下更多地以现代儿童歌谣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
二、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传统童歌源于儿童对成人劳作时鼓劲的歌谣号子的模仿,在自身游戏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儿童自己的游戏歌谣,也就是传统童歌。借助语言媒介传播的传统童歌具有较强的互动性,语言交际的所有参与者都在现场,歌唱者和受众(听众)能直接参与童歌的诵唱和创作。口语直接传播的方式使传统童歌的趣味性和生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但弊端在于口语媒介的时空局限性易导致大量珍贵童歌流失。尔后在印刷技术的加持下,童谣开始具备以文字形式传播的可能,文字和纸张的使用将原本依赖人类大脑记忆的歌谣以符号的形式保存并流传,突破了口语媒介的时空限制。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及印刷机的广泛使用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明治时期的唱歌以小学音乐教材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部分早期唱歌由于文辞复杂难懂以致传唱度大大降低,但印刷技术的运用保证了这些作品不会在岁月中失传。同时,文字形式的童谣也出现了明确的作者群体,这也促使童谣开始具备思想宣传性和鲜明的个人特色。唱歌通过歌词在潜移默化中推广军国主义思想,以达到培养孩子“忠君”的目的。大正时期的创作童谣中,金子美玲以其独特的视角再现孩子眼中的世界,她的作品在童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文字信息的解读需要一定的阅读能力,品读童谣需要一定的鉴赏能力,因此,文字媒介的使用在为童谣的传播解除了时空限制的同时也设置了不低的艺术鉴赏门槛。《赤鸟》杂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作为儿童读物的代表刊物,《赤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发行数量,甚至中途因为资金运转不周数次休刊,由此可见,具有较高艺术内涵的创作童谣对阅读群体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电子媒介的出现打破了文字符号的桎梏,童谣作品的文字或文字曲谱合一的信息被再度解码成为零门槛的听觉或听觉视觉混合的信息,并开始碎片化传播。日本现代童谣在新媒体形式的作用下逐步以童谣歌曲、电视节目、动漫及电影插曲/主题曲等多种形式出现在人们眼前。经过电子媒介转码后的日本现代童谣的受众群体空前扩大,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咿呀学语的幼儿都可以通过声音和图像接触童谣作品。1969年成立的日本童谣协会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该会以“为现代儿童制作当下的童谣为愿景”,面向世界征集现代童谣作品。该组织举办的童谣大赏、童谣祭等多种活动在社会引发广泛关注。2019年,日本童谣大会银奖得主作品甚至在中国的视频网站上有超过300万的播放量。通过电子媒介数据化的童谣可以实现长期存储的目的。我们现在能欣赏到百年前的童谣歌曲,电子媒介居功至伟。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的推动下,日本童谣不仅完成了从语言媒介到文字媒介的转换,并且突破了时空限制。在新媒体形式影响下,其传播形式空前多样化,更是突破了文字、语言及受众群体的限制,成为面向全人类的作品,最终达到了恒久保存和流传的效果。
三、对内容和主题的影响
传统童歌依靠口口相传延续至今,通过语言媒介传播的歌谣也受限于口语传播。由于语音出口即逝的特性,童歌难以表达过于丰富的内容,其主题内容大多是孩童的游戏玩闹之间的嬉笑日常。
兎 うさぎ/見て 跳ねる/十五夜おつきさま/見て 跳ア-ねる/(ぴよん ぴょん)[4]47
(兔子 兔子看见什么 跳跳望见 十五夜的月亮跳跳)
《兔》这首童谣以问答的形式把兔子拟人化,孩子一边哼唱着童歌,一边把手指竖在耳朵上,弯腰弓背模仿兔子跳跃的动作。这是专属于儿童幼年时代的游戏,是对母亲讲述有关月亮和兔子的神话故事的美好回忆,在母亲的讲述中,孩子了解到「十五夜おつきさま」(十五夜的月亮)可能就是日本古代神话传说中三贵神之一的月读命(「月読命」)大神。月读命神主司月夜,孩子仰望天空时发现月亮上的阴影像极了兔子的形状,因而相信月亮上有兔子和月读命神一起居住。这是传统童歌中神话传说的再现,也是儿童发现和认知世界的重要过程。
尔后,文字媒介的广泛使用促使童谣出现了固定的创作群体,这些创作群体又基于一定的思想理念创作童谣。文字的可视性和阅读性加强了童谣传播思想的功效,明治时期的唱歌利用文字可大范围印刷宣传的特性塑造儿童思想,进而实现军国主义“忠君”教育的目的。大正时期创作童谣对于明治唱歌的反抗也正是由于个人意识在印刷作品中的无限放大,作家可以通过文字表明观点,同样也可以通过文字再度塑造儿童美好纯真的童年生活,唤醒童心,激发儿童的想象力。
新时期的日本现代童谣中,电子媒介多种表现形式相互融合的特征丰富了作品内涵。日本现代童谣作品将传统童歌的趣味性、唱歌的教育意义及创作童谣保护童心的特点合而为一,在电子媒介的作用下发展出了全新的儿童歌谣。日本首部漫画改编动画连续剧《铁臂阿童木》主题曲中唱道:
空を越えて、ラララ、星のかなた、ゆくぞ、アトム、ジェットの限り
こころやさし、ラララ、科学の子、十万馬力だ、鉄腕アトム[4]9
(越过辽阔天空啦啦啦飞向遥远群星来吧阿童木用尽全部能量
善良勇敢的啦啦啦科学之子十万马力铁臂阿童木)
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经受原子弹的摧残不过20年,人们对于科技的力量仍心有余悸,这时的阿童木以“科学之子”——一个拥有人类情感的现代机器人形象出现,缓解了人们对于科技的畏惧。作为「心やさしい」(心地善良的)、「みんなの友だち」(大家的朋友)的阿童木形象甚至让家长对孩子看漫画、看电视等“不务正业”的行为有了改观——阿童木实在是个值得学习的榜样。阿童木作为首个登上日本荧屏的机器人动漫形象,给无数的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有血有肉又十分聪明能干的小机器人,是否在孩子心中播下了有关智能机器人制造的种子?日本现代的智能AI技术十分发达,但始终秉承和平友善的机器人制造理念,这其中是否有阿童木的功劳呢?值得深思。
除此之外,日本现代童谣作品更多的是作为治愈心灵的力量出现。“治愈”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末期,广告中女性演员平和优美的形象给予人们心灵安定的力量。尔后“治愈”一词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日本治愈系列动漫名篇《夏目友人帐》(「夏目友人帳」)时至今日(2021年)已经连载六季,动漫中的情节设定和叙事方式在主题曲中得以延续,其风格如出一辙,同样给予人们心灵安定的力量。第三季的主题曲《我能做的事》(「僕ができること」)中尤为凸显了这一点。歌词内容如下:
在迷茫的日子里忍不住叹息/仿佛真实自己已经消失不见/侧耳倾听也听不到你的声音/我只能不断追寻/今天也继续前进/(中略)/小小的我也可以做到的事/想把心中思念一点一点传达给你。
这首歌谣讲述了在迷茫日子中“我”的不知所措,但“我”仍能不忘初心继续追寻,期待着有朝一日实现自身的价值。“小小的我也可以做到的事”就是坚持。这首歌谣给予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尤其在困惑之时想起,曾有这样一位少年,为了自己的诺言而继续前行,尽管在过程中遭人冷落、不被理解,但依然能保持坚强乐观,用温柔的心对待世界。这种治愈的力量体现在对人们“创伤”心灵的抚慰激励作用,“创伤”在此处指代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不被大众理解,被孤僻、被冷落等。歌谣中的治愈力来自于动漫主人公“夏目”的人物设定,即善良温柔的少年人格魅力。夏目拥有能看见妖怪的特殊能力,在世人眼中妖怪是不存在的,能看见妖怪的夏目也就成了不合群的怪人。但夏目始终以真诚善良的心待人接物,也在和妖怪们的相处中获得自身的成长。歌谣在旋律中再次深化夏目的人格魅力,不仅儿童能在歌谣中感受到前进的力量,成人对这一体验更加感同身受,日本现代童谣作品的治愈力量由引发情感共鸣而得到更好的体现。
至此,日本童谣的主题内容从孩童的日常游戏发展到品德修养,再到保护童心,在新媒体的作用下逐步演变出了新的内涵。日本现代童谣强化了对孩童志向、价值观的影响,同时放大了童谣的治愈力量。可以说,日本现代童谣在新媒体形式的支撑下,将传统童歌的趣味性、唱歌的教育性与创作童谣的“童心主义”糅合在一起,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逐步发展成兼具各时代童谣特色,更是具备鲜明现代特色的童谣。
四、对审美意识的影响
传统童歌在孩子的嬉笑中完成传递,内容和作者都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部分童歌会出现“入乡随俗”的现象。也就是说,童歌内容随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传统童歌带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口语传播是传统童歌的主流传播形式,所以当时盛行的童谣大多朗朗上口、通俗易懂,饱含孩子游戏时的欢乐情感,人们通过童歌也能对当时的游戏情景了解一二。孩子会根据游戏需要改编童歌内容,因而童歌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当童歌内容一旦被固定之后,就会形成程式化的结构,加之大量的重复用语以减少误传、漏传。
セッセノセ パラリコセ/青山土手から 東を見ればネ 見ればネ/見れば見るほど 涙がポーロポロ ポーロポロ/その涙を 袂で拭きましょ 拭きましょ/拭いた袂を 洗いましょ 洗いましょ/洗った袂を 絞りましょ 絞りましょ/絞った袂を 干しましょ 干しましょ/干した袂を 下ろましょ 下ろましょ/下ろした袂を 畳みましょ 畳みましょ/畳んだ袂を 仕舞いましょ 仕舞いましょ[4]249-250
(拍手的节奏/从青山河堤往东看呀往东看/看得直有泪珠流 泪珠流/那眼泪 用小褂擦一下吧擦一下/擦了眼泪的小褂 洗一下吧洗一下/洗了的小褂 拧一下吧拧一下/拧干的小褂 晾一下吧晾一下/干了的小褂 拿下来吧拿下来/拿下来的小褂 叠好吧叠好吧/叠好的小褂 收起来吧收起来)
这首童歌题目中的「青山土手」(青山河堤)会根据孩子游戏的场所变化而发生变化,如在关东、三重、长野等地区演变成「丸山土手」(丸山河堤),北海道地区则为「函館土手」(函馆河堤)。同时,大量重复的「…袂を…ましょ」(把小褂……吧)结构让童歌更加朗朗上口,童歌内容也是形容孩子哭泣之后用身上穿的和服小褂擦拭眼泪的场景。把日常生活场景配以有节奏感的童歌,可以说是在口语媒介的作用下发挥了日语语音节拍性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韵律美。
尔后,印刷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童谣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跃然纸上,书面化的语言具有更强的修饰效果,童谣在文字化之后就容易出现基于某种目的的隐式宣传作用。明治时期的唱歌就是其中例子之一。日本文部省为培养孩子“忠君报国”的德行,试图通过音乐教材中的童谣在潜移默化中达成教育目的。而大正时期《赤鸟》杂志的创刊带动了大量创作童谣的出现,创作童谣的童心主义主题反对明治唱歌的教化目的,为童谣提供了更多思想性的内容。文字化的童谣具备了更强的艺术色彩,与口头传播的童歌不同的是,文字化的童谣更具视觉直观性,所有创作者想要突出的字眼可以依靠文字的不同表现形式来展现,如片假名的使用、假名与汉字的混用等。除此之外,笔与纸的触碰更能激发人的创作灵感,书面文本能促进人的批判性思考,文字的稳定性、物质性使得信息被重复接受成为可能[5]。也就是说,童谣作品印刷出版后具备了可以反复阅读、时常品味、“常读常新”的效果。而不同读者的不同解读也促进了日本童谣多元化审美的发展。
电子媒介作为人类知觉的延伸,放大了各类感官影响的同时,也推动了受众群体审美观的发展。传统的声音传播过于单调,人们对美有了更多的要求。通过电视播放的童谣节目已经不单单是童谣本身,观众需要欣赏童谣的整体效果,其中包括舞台设置、歌唱者的仪态等一系列的视觉美感。与此同时,电子媒介与商业活动相关联,在消费主义的推动下,日本现代儿童歌谣贴近大众且越发注重引发情感共鸣。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受到碎片化知识结构,浅阅读经验,快节奏生活,功利性、娱乐性追求等方面的影响,接受者审美能力下降、审美心理稳定性趋弱、审美心理图式变得简约,人们不愿或不能对作品进行理性思考与分析,而满足于粗略与感性的审美接受[6]。因此,日本现代童谣的创作进一步迎合消费需求,逐渐大众化、平民化,在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也有了更多引发情感共鸣的要求。动漫电影主题曲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作者借助童谣主题曲来表达电影主题,在电影结尾的童谣作品中把电影主题再度升华使观众的情感被推至高峰,以此引发共鸣。网络媒体更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抽象距离,为有相同爱好的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至此,日本现代童谣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有了更加多元化的审美倾向。
五、结语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现代童谣在新媒体形式的影响下逐步完成了从口语传播到电子媒介传播的方式转变,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不仅逐步突破时空的限制,更是突破了语言和文化的限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不断扩大。可以说,日本现代童谣在新媒体形式的作用下成为面向全人类的文学作品。同时,在新媒体形式的冲击下,文字、影音图像等都成为日本现代童谣的艺术表现手法,日本现代童谣逐步发展成兼具各时代童谣特色的作品,也逐步强化了对孩童志向、世界观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更加注重对成人心灵的抚慰和激励作用。在审美意识方面,日本现代童谣有了更加多元化的审美倾向,从传统童歌的韵律美、明治时期唱歌的教育性到大正童谣的鲜明思想性,再到注重引发情感共鸣,日本现代童谣的审美是否更加趋向大众化和平民化呢?值得探究。总而言之,新媒体形式给予童谣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且影响力深远持久。以传播媒介为切入点展开对日本现代童谣的研究,有利于扩宽研究视角和思路,能够为各界童谣爱好者提供更多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