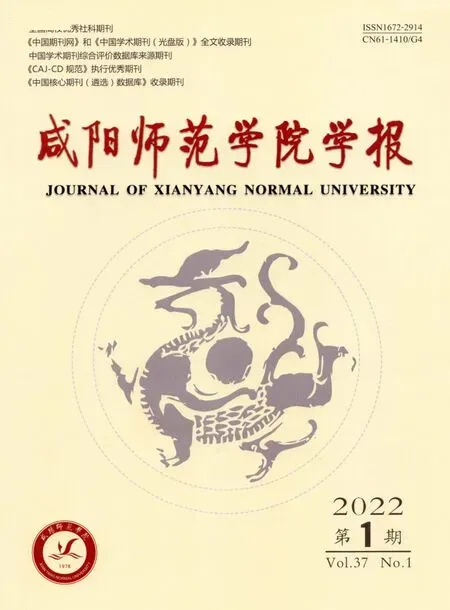直觉·自适·超越:大观园“诗性”生活品格的审美建构
2022-03-01王佳
王 佳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国有“诗性”生活的经验和文化传统,“把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把艺术日常生活化,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1]从庄子“逍遥游”的“诗性”生活理想到清代李渔《闲情偶寄》的“诗性”生活指南,再到现代周作人、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思想与实践,人们对“诗性”生活的追求形成了一个传统。《红楼梦》是中国古典“诗性”生活的典范,“大观园的生活是一种艺术化的日常生活,实现了人类心灵在大地上的‘诗意的栖居’”;“她们(丫鬟)与多才多艺的小姐们一起营造出一个高度艺术化的生活空间”。[1]关于《红楼梦》“诗性”主题的研究,主要关涉诗学观、诗性叙事、诗学活动、诗学趣尚等,与大观园日常生活艺术化相关的研究也只在“日常生活哲学”“休闲美学”视阈中涉及,并未将诗性赋予生活领域,从审美化的角度上进行阐释。王国维对个体生命悲剧性和解脱之途的思考、刘再复的心灵本体论、叶朗“有情之天下”的人生理想论以及孙爱玲对《红楼梦》“以情悟道”诗性哲思的阐释等,皆从生命本真存在的视角探讨“诗性”,发人深省但缺乏系统性。当下,“人生的艺术化”再度成为时代命题,美学视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方兴未艾,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要从“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向“精神层面的审美化”研究推进,审美活动不仅限于物质和外观,同样见于对象目不可见的结构和内核。[2]我们把构成审美活动心理层面的直觉、情感、想象等因素提取出来,并挖掘深层的精神内核,发现“诗性”生活的抽象性就得到了明晰的阐释。本文运用西方审美学理论,结合中国传统诗性文化,考察大观园“诗性”生活的审美结构与精神内核,以期促进“生活审美化”研究在中国的理论运用和实践意义。
一 大观园“诗性”生活:一种艺术化、审美化生活
(一)中西视阈下“诗性”生活的理论建构
何谓诗性?狭义的说,诗性源于维柯提出的“诗性智慧”,是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海德格尔曾提出“诗性生存”命题,提倡“以富有诗意的生存方式不断地通过内在超越即审美生存,无止境地超越其主体性、对象性的限制,实现一种最具本己、最具个性、最有充分自由的存在”。[3]李建中在中国文论的范畴里讨论“诗性”概念时总结:“广义的说,诗性是与理性相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精确一点可分为三个层面:作为语言方式的文学性和抒情性,作为思维方式的直觉性与整体性,作为生存方式的诗意化与个性化”。[4]27虽然这些理论研究的视角和领域不同,但是揭示了“诗性”的内涵包含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两个层面。类比来看,本文讨论生活领域的“诗性”,姑且叫作“诗性”生活,是一种艺术化、审美化的生活,以经营此种生活的主体(人)为核心,考察他们置身这种审美化生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的特征。我们标明诗性生活“品格”,指内涵和结构,将“诗性”视为大观园生活的精神内核和存在方式,与审美学角度的“建构”意图相合。
传统中国缺乏诗性生存的理论但有诗性生存的实践,这是因为“诗性”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本质性归纳。[5]中国诗歌的最早发达导致诗的品格浸润到文化的不同领域并熔铸成中国文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远古时代就有诗言志、歌咏言之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诗性精神更是融入上至政府官员、下至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之中,已经成为人们精神和生活的一部分。”[6]从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来看,它首先是一种“向生命处用心”[7]11的文化,发展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和内圣之学。这种文化和学术强调一种重在综合、长于内心体验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天人合一”思想和道家的一元本体论,以直觉体验把握生命本质,与西方所谓人类的“诗性智慧”相一致。与海德格尔“超越性生存”理论相类似,对于中国文化赋有的“诗性”精神,有论者认为可以用“超越性”概括,[5]如庄子的“梓庆削木”达到物我两忘的化境,孔子的“吾与点也”突出精神价值对功名价值的超越。虽然海德格尔的超越指向宗教性的彼岸,而中国文化的超越性指向人生的此岸,但两种“超越”在审美生存目的和所追求的自由境界上呈现出一致性,即不是对当下的否定和对自身的绝对肯定,而是一种容纳和敞开,它容纳当下并召引更高境界的生命,揭明生命处于一种生生不息的运动之中:超越具体,超越于物,引领开阔,指向无限。[5]一句话,就是追求一种更高境界生活的理想。李建中指出赋有“诗性”的古代文论承担着主体的生命体验,是对儒释道诗性精神的传承,彰显出“生命”是中国诗性文化的核心。[8]由此,“生命”作为生活的主体,自然也成为我们讨论的核心,考察“诗性”生活至少应包含:主体(人)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生命境界三个层面。
中国的诗性文化孕育了众多的文学经典,远古神话歌谣、先秦诸子散文、历朝诗词曲赋予小说戏曲,无不渗透着“诗性智慧”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形成了“诗性生存”的文学文本,昭示追求生命审美境界的理想。《红楼梦》以全息社会图景呈现了古典“诗性”生活的样本,展示出封建社会末期一群“诗性生存”追求者们的审美化生活。
(二)大观园“诗性”生活的审美化结构
大观园是红楼儿女们安放青春和诗性的场所,他们在一起作诗、结社、抚琴、作画、饮酒、赏花,以山水自然为乐,以才情相赏,以艺术化的生活涵养本真性情,摆脱世俗宗法社会的压抑,追求生命的自由境界。探春在提议结海棠社的信中描述的生活,是大观园“诗性”生活的典型:“思及历来古人中,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者,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娣虽不才,窃同叨栖。处泉石之间,而兼慕薛、林之技。风庭月榭,惜未宴集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若蒙造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9]510这种生活的特征是将艺术融于日常,以审美实现对当下的超越,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化生活。
分析这种审美化生活的构成,一是审美时空的构成。以诗社为代表的吟诗赏诗活动由三种关系构成:自然、人际与自我。活动的场景须精心布置,将山水引入庭院,是“山滴水之区”“风庭月榭”“帘杏溪桃”之类,所以探春以“东山雅会”作比,“盘桓于其中”“一时之偶兴”,揭示出因物兴情的创作机制;“醉飞吟盏”隐见醉吟痴迷的创作状态。还需“盘桓于其中的二三同志”“远招近揖”“投辖攀辕”,显其热忱;“兼慕薛、林之技”,示其相赏,构成文学世界里的审美关系。“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显示出女性创作者主体自觉的诗化人格。这种审美时空成为一个包含自然、社会与自我的完整世界。二是审美时空的拓展。诗社是举办诗歌创作和鉴赏活动的团体,与今人纯粹的审美场景(如现代的艺术馆、影剧院、图书馆、音乐厅)不同,大观园人的诗会开在生活圈内,审美时空与日常生活时空相重叠。比之有官位的士大夫,待嫁闺中的女儿们自是可以常常聚集,除了召集诗会,在任何生活场景都可以作诗,大大拓展了审美时空。除了作诗,审美化生活中还包括各种艺术活动,其对生活的渗透方式,借用迈克·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可分为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两种[10]:一方面,他们把艺术当成日常,以绘画书法、下棋观书、吟诗作赋、吹箫弹琴构成日常生活的内容,尤以吟诗作赋贯穿始终,海棠社赛诗、芦雪庵即景题诗、中秋赏月吟诗、赏秋海棠吟诗等,生活的情境无不呈现。另一方面,他们将生活变成艺术,饮酒行令、观鱼逗鸟、扑蝶赏花、斗草听戏、听书游园、节庆祝寿等等,都极富诗意和美感,雪中赋诗啖鹿肉、贾宝玉雪中折梅、游园借水听音、中秋宴月下闻笛都是大写意的生活图景。可以说,大观园人将艺术与生活融为了一体。三是审美经验的引领。从审美经验着眼,这种“诗性”生活并非生活的全部,而是生活过程中那些具有特殊可能性的部分。但审美的目的并不在于某种特殊的满足,而在于无限可能性的实现。[11]20在这种特殊的满足中,即审美发生的那一刻,日常感性经验提升为日常审美经验,便向主体敞开了心理的愉悦、个性的完成、生命的超越等可能性,呈现出审美化生活的意义。这种可能性是无限的,“审美的领域绝不是并列在生活其他领域之外的独立领域,而是各种生活可能性之一”,诸种寻常物皆可嬗变为艺术品,审美时空可以延及整个生活世界。审美根本上是“一种不能脱离人类生活形式来思考的领悟形式”。
我们从思维方式、生存方式、生命境界三个层面出发,审视人在与自然、社会、自我关系中的审美态度,发现大观园的“诗性”生活是一种以直觉为中介、以情感自适为核心、以超越为目标的审美化生活,下文分述之。
二 以直觉为中介:应用感性的思维方式
维柯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提出一切民族共有的精神本源是诗性智慧,是一种感性的思维方式,通过“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把握外在事物的本质。西方现代美学从心理学引入“直觉”的范畴,康德指出审美因素对于我们的知识来说至为根本,直觉“只是在对象被给予我们时才发生,而这对于我们人来说,又至少只是通过对象以某种方式刺激心灵才是可能的”。[12]52沃尔夫冈·韦尔施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区分为“浅表的”(物质世界的)和“深层的”(精神世界与认识论的)两种层次,[2]重构美学的时代命题,就是要促成前者向后者转向,让“感性”重新成为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用直觉、情感、想象去把握世界,并将这一审美原则贯穿人类活动的始终。“直觉”论与中国传统的“心物说”相通,构建了“诗性”生活的思维层面,所谓“诗性”生活就是以直觉为中介,心与物相融、生活与艺术相融的生活。
审美进入日常的心理状态是物我交融,发生机制是用直觉切入生命。柏格森说“直觉”是对生命绝对实在即“绵延”的把握,这种生命的实在是“在时间流动中的我们自己的人格”“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状态都预示着未来而包含着既往”。[13]9-10贾宝玉在大观园的生活始终伴随着直觉对生命意识绵延的体验。他在世俗的眼里被称为“呆气”,“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三十五回),就是他以直觉沉浸于自我与外物融合而成的情境的审美状态。他就大观园春夏秋冬四季之景做了《四时即事诗》,春夜枕上听雨、夏日鹦鹉唤汤、秋夜露湿栖鸦、冬夜新雪烹茶,都是他以自我生命响应大自然生命流动唤起的审美体验。大观园“诗性”生活的主要载体海棠诗社,四次起社作诗皆是因物兴情,所咏对象白海棠花、菊花、桃花、梅花和雪,皆是大观园的应时之景。第四十九回宝琴到贾府,李纨道:“我的主意……可巧又下雪,不如大家凑个社,又替他们接风,又可作诗。”第七十回宝玉应湘云的丫头翠缕之请,到沁芳亭去看好诗,众人见他来时,都笑说:“咱们的诗社散了一年,也没有人作兴。如今正是初春时节,万物更新,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第七十六回中秋,黛玉与湘云商议到“凹晶溪馆”联句,正说着只听笛韵悠扬起来,黛玉笑道:“这笛子吹的有趣,倒是助咱们的兴趣了”。这里的诗兴都发生于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中,正应了袁枚所说“诗赋为文人兴到之作”。从诗歌的创作发生机制看,无论是陆机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还是刘勰的“人察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都揭示了创作者因物随时而感,与自然“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心物关系。
直觉敏锐、善于感物是审美主体具备的天赋,造就了艺术对生活的升华。康德说,感性直观纯形式,即空间和时间,是我们先天具有的。[12]53但真正发掘运用它们的是得天独厚的审美者,比如贾宝玉,作为大观园时空审美者与大观园日常生活参与者,他必然会把这些无意识发生的审美化日常体验诉诸诗歌,融入生命之流。黛玉是最典型的生活艺术家,她选择幽篁茂盛的潇湘馆为住所,是为了听“凤尾森森龙吟细细”;她创造性地装点室内外环境,颇有感时应物的诗人雅趣,比如“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子罩上”“看那大燕子回来”(二十七回),“令将架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于是进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便隔着纱窗调逗鹦哥作戏”(三十五回);她从自然时序变化中得到对自身生命的观照,做出“人笑痴”的葬花之举,秋夜听雨滴竹梢之声心有所感,写下《秋窗风雨夕》词(四十五回),在直觉体验之上更有一层反思。他们用“艺术之眼”将日常物升华为审美物,即联结“被表现世界”的深度与鉴赏者的深度的中介物,[14]616如薛宝钗“雪洞”一般的房间蕴含了高洁独立的人格,黛玉、探春如“公子书房”的陈设亦是古代文人式精神涵养的表征。他们还运用直觉思维和创造力,把生活也变成了艺术:宝钗扑蝶、湘云醉卧是女儿对青春美的直觉和沉浸,起诗社、作菊花诗、作螃蟹诗是即景命题的艺术创作,正月踏雪寻梅众人发现宝玉宝琴红衣立于白雪的美、惜春当即要将之入画,湘云黛玉凹晶馆联诗看到寒塘鹤影随兴引发妙句,贾母中秋节隔水听箫等等……在这种艺术化的、恒在的生活场景中,大观园儿女们的直觉俯拾即是、创造着手逢春,让诗意时时充满生活、浸润内在的灵性。
直觉引起创作的发生除了涉及审美心理和艺术创作的层面,哲学层面上则是如何看待人与外物(自然)的关系,与庄子的“齐物”理论相通。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的“呆气”,类似于濠梁观鱼中庄子与鱼快乐的通感,其背后是“把物看成是具有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15]22即鱼(燕子)之乐,并感受到他与鱼(燕子)之间的亲情关系,即庄子的齐物论。这种观念还被曹雪芹神化处理了,如宝黛下凡前的木石前盟,作为物的两者之间即发生了精神的激发和灵性的触动,是真正的“神遇”。心物相应的例子还有黛玉哭花阴回目,“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颦儿才貌世应希,独抱幽芳出绣闺;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第二十六回)揭示了自然界的声响音调与心理的对应性。此处的“痴”和上文的“呆”对应了“坐化”“虚静”,是一种“静观”的审美创作状态。传统的心物对应论认为,山水具有情感的表现性,尊重物的本真状态,主张与物相契,而不是去支配物,宝玉正是把燕子、鱼、星星、月亮当成有生命有情感的对象而与之平等对话。这些以心物关系为核心的审美体验,发生在大观园的日常感性活动中,将艺术、自然的领域扩展到感官所能触及的所有领域,其意义成就了大观园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
三 以自适为核心:葆有本真的生存方式
“诗性”生活是一种葆有本真的生活,海德格尔提出人的“诗性生存”,是针对现代社会人被物化的状况:人把一切外在物作为实用目标加以索取和追求,自己也沦为实现功利化目的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人成为非本真状态的人,进入丧失意义、丧失自我的困境。“诗性生存”的内涵是:以富有诗意的生存方式即审美生存超越限制,成为“最具本己、最具个性、最有充分自由的存在”。循自然、求解脱,亦是中国道家面对世界“沉浊”、精神起步处的精神倾向。[16]113-114中国的诗性生存虽落实于日常、细节、具体化的生活层面,但也是立足于解脱现实困境、直面自身的主体需求和个性发展。
在《红楼梦》的时代,仕途经济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人成为追求“功名”的异化物,失去生命本身存在的价值。海德格尔说的本真状态,是“面对环境的制约,我是否可以自由选择对它反应的方式”,这种选择是自属的而非他属。陈国学指出《红楼梦》人物在人生意绪上与晚明性灵说相关联,即脱离传统儒家教义,追求任性自适的人生意趣与个体感性的生理存在。[17]其实这种忠于本性的倾向与庄子“自适”的观念相贯通。庄子“适”的思想来源于老子的“自然”,只是将物之外的“道”改造为物之内的“性”,内涵是符合本性的生存状态。《红楼梦》人物追求与庄子自适观相贯通的层面,一是在于不受世俗干扰的纯粹性,二是在于享有安适的乐趣。
宝玉的“自适”,首先在于他对合乎本心的人生追求的选择。他厌弃仕途经济和假道学,追求合乎本性的生存方式,探求生命的意义。他指陈大丈夫“文死谏,武死战”“死名死节”都是沽名而死,“竟何如不死的好”。他设计自己的死亡是:“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第三十六回)死亡是仅属于个体生命本质的一种可能性,贾宝玉突破了儒家传统的死节、死义、死忠、死孝的模式,以纯真的本性创造了自己的死亡方式。[18]庄子视死生为“夜旦之常”“适来时也,适去顺也”“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遵循生命之情、顺应死生之自然,将身与死生存亡化为一体。宝玉之“死的得时”“若有造化”亦是安于命运的安排,但透露出对死亡方式的主导设想,是对自身“情根”本真存在的鲜明意识下萌生主体性的体现,突破了庄子“自适”观委时顺命的消极因素。二者在自适以达到不为外力物役、达到“县解”的积极目的上则保持了一致。
宝玉的“自适”还表现在以情挈情的人际交往中,延展开以审美关系为主导的“诗性”生活。宝玉是天生情种,将对女儿的钟情作为他生命价值之所寄。所谓“意淫”是一种审美体验,追求心意沟通的同时享有适性的乐趣。①吴宓先生在《文学与人生》中认为“意淫”指的是“想象中的爱,审美的爱或艺术的爱”,界定了“意淫”的审美性。他对“女儿”的真情流露源于内心的欣赏和体贴,他被父亲毒打时看到每一个姐妹的“怜惜悲感之态”,只觉“可玩可观,可怜可敬”,觉得“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看到龄官在花架下画“蔷”,想到“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激”,情急之中竟顾不得自己淋雨;把受委屈的平儿拉到怡红院补妆安慰,赞叹香菱学诗“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这种情感生活中的审美体验,前提是将女性作为欣赏对象,超越了阶级和世俗观念的束缚,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抵抗与批判,亦是人之本真天性的敞开与回归。宝玉的“意淫”自然也含有生理冲动,如为“平儿理妆”“香菱解裙”回目中宝玉的表现都有性内涵,但并无行动,并且充满了怜惜,与贾琏薛蟠对女儿的“淫乐悦己”在品格上全然不同。“作养脂粉”的理论注脚是以情挈情,尊重他人的自我实现。如放纵晴雯、理解龄官,使她们各得其情,各遂其欲,按自己的意志和心愿去自由活动,也满足了他一生“务必求兴女子之利,除女子之害”护法裙钗的事业追求。在以情挈情的体贴中,宝玉在对待他人时将儒家推重的等级人伦关系转化为审美关系,在个人的自然欲求与共同的生命完成、人人达情遂欲上实现了统一。从理论层次看,宝玉的“自适”观与庄子最大的不同在于情欲是否属于天然之性。庄子认为外物激发人的欲望损害真性,“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六情是“德之过”“德之邪”“德之失”。但对“真在内者神动于外”的“真悲”“真怒”“真亲”又是赞美的,那么真情即属于“德之正”了。警幻仙子借判词点化贾宝玉:“情天情海幻情身,情若相逢必主淫”,感情的宇宙化生出感情的肉体来,赋予了情以自然生成的属性。因此贾宝玉的真情来自“天分中生成”的“意淫”,必厌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后天之“伪”,这与庄子尊重性命之情、批评仁义伤性相统一,但把庄子对情的暧昧认可张扬了出来。在明清个性解放思潮冲击下,人们高唱男女真情以对抗假道学,就放宽了“德之正”的疆界。在宝玉的认知里,情被纳入自然之德抬高了必然性价值,是对庄子“自适”观的突破。
黛玉的“自适”则表现得更为纯粹,宝黛爱情亦成为大观园“诗性”生活的主线。与宝玉所处“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的经线地位不同,纬线之一的黛玉自适于“情情”,专注于与宝玉之情。她来世间是为了完成“木石前盟”,即便与现实的“金玉良缘”遭遇并无法抗衡,仍坚持二人之情。她的全副眼泪就是对爱情的忠诚,直到爱情绝望泪枯而终。蒋和森说:“黛玉之死,才能说明她对现世人生之执着”。[19]68情是生命的本真所寄,“情情”便是黛玉的诗性生存方式。木石之情来自天命,发展成自适适人的知己情。“将对方引为知己的原因,这就是宝玉和黛玉都顽强地坚守着对于本真自我的忠诚,保持着自我美好的自然个性。”[20]宝黛二人因对仕途经济的否定成为“知己”,在共同对抗大观园外的“风刀霜剑”中结成同盟。除此,这种自适体验是极度愉悦的,二人在共读西厢、暖玉生香、葬花恸哭、旧帕题诗的情境中被激发了共鸣,甚至渔翁渔婆的打趣、稻香村的命名都体现了二人自然趣味的一致。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认为,“体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一种精神的投入,是‘我与对象’之间同感共鸣的活动”。[21]428宝玉安抚黛玉只说“你放心”,黛玉便觉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恳切。二人在心意沟通中感受到强烈的愉悦,以真实的共同体验进入对方的精神世界。但庄子式“自适”要求“生死忧乐无所动心”,宝玉自然是做不到的,黛玉更因情而夭。宝玉对灵秀女儿难以忘情,是他超脱死生忧乐而达到“县解”的羁绊。宝黛知己情的破灭是宝玉从“情痴”到“情悟”的关键,随着大观园的关闭而“情机转得情天破”,终做到无情而自适。
四 以超越为目标:包涵自由的理想境界
这里说的“自由”,指的是在审美和哲学领域实现的精神自由,代表一种理想境界。这种“超越”包含审美体验的自由、个性解放和思想升华的境界。
“诗性”生活赋予“大观园人”一种审美自由感和个性解放。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在谈到诗时他进一步揭示:“诗的表现还有一个更高的任务:那就是诗不仅使心灵从情感中解放出来,而且就在情感本身里获得解放。”[22]188香菱从“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两句中回忆起自己当年上京在渡口泊船时看到的景色,她以融入个人生命体验来读诗,以自然悟入领会诗境,当时前程未卜的阴影,被诗情画意消解,生命的压抑感得到了释放。从外部世界进入大观园世界,香菱才享受到了审美生存带来的丰盈的解放感,而她也因为热衷吟诗作赋,融入“诗性”生活而被批准成为“大观园人”。这群人终日沉浸于诗歌、音乐、绘画各种艺术形式中,体会生命的绵延,直面生命本质,获取瞬间的自由感。庄子的“庖丁解牛”“梓庆削木”描摹了艺术创作予人的审美自由感,所谓“瞬间的自由感”指一种心与物游、物我冥合的状态。同时,突出了技艺上升为艺术后的自由驾驭,如庖丁“以无厚入有间”的从容,梓庆“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的笃定,赋予了主体力量和人格自信。席勒认为自我需要重塑,而审美就是关键环节。大观园儿女对艺术的创造、对生命的思考培育了他们的情操、技能和价值感。他们进而以诗性生存抵抗社会压迫,体验生命之美、自然之美、人情之美,以自主的决断和行动,完成了自我的演进,获得了精神世界的相对自由。贾宝玉超越世俗功名追求诗性生存目标,“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念、价值判断去生活,重新追问、探索人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反思者、批判者和赎罪者”。[23]大观园女儿们以诗意生存寻求女性的生存价值:她们斗草簪花、结诗社、吃螃蟹宴、赋菊花诗、画图寻梅,尽情张扬个性;她们充满活力、率性追求向上的生命,香菱学诗、探春理家、凹晶馆联诗都体现了美好生命的张力;她们不为环境所抑、自主选择生命的目标,薛宝钗矜持自守、黛玉清高任情、探春自尊自强、惜春孤僻狷介,都体现出强烈的个性特征;尤三姐在放浪中持守并以死明志,秦可卿委屈自制、死前对家族命运的担忧,显示出个体面对恶劣环境的弹性,晴雯、金钏、紫鹃、鸳鸯、司棋等都以强烈的方式与异己的社会势力对抗,维护生命尊严。“这是关乎生命质量的前所未见的价值追求,它产生在背离传统价值期待(虽不彻底)与尊重个性舒扬(虽不高亢)的结合点上。”[24]377
但是,现实的不自由毕竟给大观园审美化生活打上了一重阴影,使其呈现出一种悲态,内蕴一层哲思。海德格尔认为,“思想完成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这种思是诗性的,不是思维,而是觉知,是一种“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的态度,它的目的是要把握存在之真理。大观园人都赋有诗化的哲思,他们天资颖悟、具有丰富细腻的情感,常能从日常对人事物的观察和体验中领会存在的真理。黛玉的《葬花吟》就是“诗之思”,它既是一个美丽孤独生命的内心独白,也传达了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普遍悲哀。“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当宝玉听到这些带着巨大伤感的句子,“不觉恸倒山坡上”,由美想到美的凋谢,由爱想到爱的消逝,由今日的欢会想到永恒的孤寂,由眼前的黛玉推及所有亲密的、美丽的女子,推及“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宝玉由一瞬间的感悟触到了存在的深度,这就是存在之思(诗)。这种诗之思使得他们的生活呈现出一种“悲态”美。从个体的痛苦中拔出的美就是一种悲态之美,它具备了审美的意义,便解脱了痛苦本身,成为一种精神的升华。王国维把它叫作“艺术的解脱”,由审美体验引领了心灵的愉悦、个性的完成、生命的超越等可能性,昭示自由的理想境界。
五 “诗性”生活:沟通大观园内外两个世界的桥梁
大观园为这群儿女打造了与现实社会相隔离的自由国度,他们对审美化生活的向往,正是源于对宗法制度下生活的不满。贾元春将这个省亲别墅赐给姐妹们居住是对失去自由的宫廷生活的不满,贾宝玉热爱流连在这个女儿王国是为了规避封建官场的应酬和父亲的世俗教化,香菱被允在大观园生活一年以远离薛蟠家庭的迫害。那么,这种自由是逃避而生的幻象吗?大观园世界是纯粹理想并隔绝于现实的吗?不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建立审美化生活的现实基础。
有研究批驳余英时的“两个世界”理论割裂了《红楼梦》艺术世界的整一性,举证是大观园作为“恶”与“浊”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不纯粹理想,如司棋和表弟偷情,王熙凤暗害尤二姐。[25]其实,王熙凤只是借助了大观园这个隔绝环境,她也绝非大观园儿女,偷情甚至绣春囊事件并非道德肮脏,[26]46且代表了司棋的任情本色,余英时的解释未被推翻。进一步说,大观园世界的纯粹理想性是与人们抱持的审美生活态度紧密相连的,并不因为某个场景和某个事件就玷污了这个世界的诗性。大观园生活的诗性品格是曹雪芹的设定,也是审美主体(人)的选择。诗意和真情作为外部黑暗王国残酷、污秽、虚伪的对立物而存在,最后被现实世界的肮脏所摧毁,正彰显了诗性理想的可贵。在这个国度里,童心者自不用说,半个童心者如宝钗、湘云在这个大观园世界也呈现出本真的一面,葆有闺阁女儿的性灵,“扑蝶”“醉卧”的生命情态显然不可能发生在大观园外的世界。在“怡红风俗”下的夜宴现场,无论丫鬟还是小姐都沉浸于和谐自由、不为礼法束缚的气氛,流露出一派天真。当然,也存在外部世俗世界对这个诗性王国的冲击,世俗与理想观念在内部成员间的碰撞。前者如封建家长对宝黛爱情的干预,后者如“仕途经济”说体现的宝玉、黛玉与宝钗、湘云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但宝黛爱情的知己体验胜过了金玉良缘的世俗安排,童心者对诗性生存的选择始终代表了这个世界的生活理想。
在大观园中,以“诗性”生活为平台,审美世界与现实世界实现了融合。日常生活尽管天天重复,显得单调、平淡,但如果人们能以审美的眼光去观照,它们就会生成一个充满情趣的意象世界。[27]借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生活世界是以一种自然态度经验的世界,以源初浑然的“未分态”呈现自身。[28]宝玉与女儿们的感性思维就是类似于这种混沌的自然感知方式,他们所经验的审美世界与现实世界实现了融合。这种自然感知方式并非诗人才有,甚至是庸俗、虚伪人设的大观园外人物,在诗性活动中也被提升了灵性,同样可以运用直觉思维、体验自适的状态、享受自由的愉悦,比如节庆休闲场景下的贾政和吟出“一夜北风紧”诗句的凤姐。其实,大观园“诗性”生活包含的审美时空和审美经验是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两个世界的人在此共享一个意象的世界。只是,诗性和世俗层面在大观园人的生活中是融合的,在大观园外人的生活中则是分离的,贾政年少时生活的诗性面向被入世后的他割离了。第十七、十八回,贾政让众清客拟大观园题咏而自己不拟,理由是他认为自己“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纪,且案牍劳烦,于这怡情悦性文章上,更生疏了。纵拟了出来,不免迂腐古板”。吟咏性情的山水之作,须得少年心性和闲暇时光,生活在“沉浊”世界的人与以性灵为核心的大观园生活终是隔膜了。但这一触及,引发了他对于青年时代花鸟题咏怡情悦性的回忆,这个大观园、这些假山游鱼就从实际感知物中解脱出来成为审美的对象,从这个与清客应酬的世俗时空中就划分出来一个日常审美经验的时空,在这个时空中贾政也成为了审美的人。可以说,“诗性”生活以审美抵达的瞬间可能性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净化。这又回到前文所论审美引领的无限可能性问题,审美根本上是“一种不能脱离人类生活形式来思考的领悟形式”,正因为如此,才得以突破理想与现实的屏障,与生活相融。
虽然大观园“诗性”生活的内容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距离现代人的世俗生活较远,但其审美品格有其价值。人心对外物的敏感反应(直觉)、人与人出于本真的真诚交往(自适)、一瞬间精神超越现实获得的愉悦和自由感,它们所构建的审美化生活态度,引领现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把握快感与乐感、自由与现实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