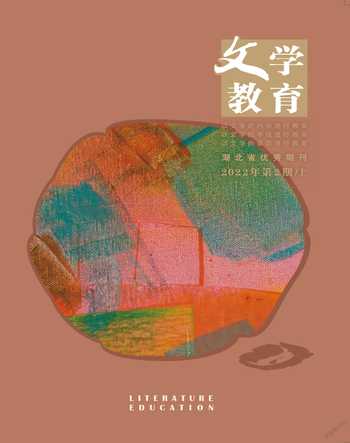鲁迅《故乡》里的三个问题
2022-03-01林小婷于春堂
林小婷 于春堂
内容摘要:国民作家鲁迅于1921年创作的小说《故乡》被编入国内中学教材已久,且日本翻译家竹内好的《故乡》译本也被编入日本初中教材,一直沿用至今。由此,这部作品的经典性和影响力自可不必多言。但文中有几个尚且存疑的问题,比如碗碟是不是闰土藏的、如何理解“神异的图画”等。除此之外,曾有人指出文中的两处“笔误”,但迄今为止,国内文学界还无人对此作出回应。为了不让这份“笔误”一直被当作笔误,本文以日本文学家田中实的“三元理论”为基础,论述这两处不起眼的“笔误”,并以新的视角解读“碗碟”问题。
关键词:鲁迅 《故乡》 廿年 笔误
鲁迅的《故乡》是一篇被收录进中国和日本中学教材中的经典文章,其中的“因年龄关系把斜对门的杨二嫂完全忘却了”和“廿年前的闰土”两处常被认为是作者的笔误。因为正值青春期的大好男儿对一个貌美如花的“豆腐西施”全无印象、以及根据文中时间线进行推算后发现“廿年”的不合理,两处的文本描述令读者产生了疑惑,所以一直被当作笔误处理。日译版本甚至直接把“廿年前的闰土”改成了“三十年前的闰土”,导致呈现在日本中学生面前的译文一直是“三十年”。本文将以田中实的“第三元理论”来对这两处“笔误”进行分析,证明除了文本本身和读者外,还存在着“第三元”,正是受此影响,文本才生出了这两处“笔误”。本文除了对两处“笔误”进行说明外,还采用了新视角对“碗碟是不是闰土藏的”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一.田中实的“三元理论”
田中实是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三元理论”的提出者,曾赴国内各大高校开展过诸多文学讲座。田中实认为,读者在进行阅读时,比起一心只沉浸在文本本身,更应该站在文章外部去理解文章内容,这样才会获得更深入的阅读体验和成长值。
一般的文学理论认为,读者读到某个文本时,关注的往往是故事或情节本身,或“阅读”这一行为往往是指理解文本的“本意”。这两种观点都认为,“阅读”这一行为在文章内部就已经结束了。即,“阅读”只发生在读者和文本这“二元”之间。而“三元理论”认为,“二元理论”存在很大的问题。其一,如果读者一味地追求获得文本信息,就会提高自己对文本产生正确理解的期待值。这种期待值,会局限读者的思维,扼杀读者的创造性,使其陷入对文本的错误理解中。即,这样的读者已经不再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反而变成了一个遵守规则的机器。其二,如果读者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切信息都只能来源于文本,那么读者就会只专注于“看”这一动作。产生了对文本固定的价值标准后,读者就会陷入“利己主义”中去。
而“三元理论”在读者与文本的二元结构之外,又引进了一个外部领域,田中实将其称为“第三元”。“第三元”这一术语的定义尚不明确,但其出发点是“阅读并不是搜集所有的文本信息”。自己所获取的信息并不是文本的唯一解释,在读者的解释之外,存在着一个“包含了所有信息”的文本本身。但由于我们的视野是狭窄的,所以永远也看不见那个“包含了所有信息”的文本。每个人对同一个文本都有自己不同的认知和解释风格,而别人的认知和解释,田中实称之为“他者”。如果读者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自己、对“他者”的理解,那么便可以加深对世界的认识,进一步改变自己。简单来说,读者通过“阅读”的行为进行自我转化,这便是“三元理论”的根本所在。
因而,田中实认为,真正的近代小说中应该包含并试圖解决的是“超越叙事和被叙的二元构造,从而获得真正的客观描写”这一问题。森鸥外的《舞姬》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初期便已抓住了这一问题的核心,但写实主义及自然主义文学则没有直面这一问题,因而不是真正的“近代文学”。芥川龙之介对《罗生门》的改稿便体现了他与这一问题的斗争,虽然他后来在《莽丛中》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使用的是一种理性的方式。而田中实认为,近代小说家中真正克服了这一问题的是中国作家鲁迅。
二.《故乡》中的叙事者
《故乡》中的“我”已离开故乡二十余年,回到故乡后,发现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文中的“我”在回到故乡后的几日就看到了三十年前儿时的玩伴闰土和卖豆腐的杨二嫂,但曾被称作“豆腐西施”的杨二嫂变得令人生厌,以前可爱纯洁的润土也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在闰土喊出那声“老爷……”之后,“我”便感到了与他之间那层“可悲的厚障壁”。
文中的叙事者是“我”,“我”的身份与经历和鲁迅颇为相似,所以,此篇小说的叙事者往往被认为是鲁迅本人。但田中实认为,文末的“希望”却体现出了超越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我”不擅长待人接物,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尚未成熟的个体,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内心解体了的“我”。
(1)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1]。——《故乡》第502页
此外,《故乡》中还出现了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如摘录(1)所示,这段话在小说里一共出现了两次,此时“我”头脑里出现的画面应是夜晚时分,但文本却将其描述成“深蓝色”。有的读者看见“深蓝色”会联想到白昼的天空,而有的读者会想到夜晚。这一矛盾有时也令日本翻译家不知所措,有的翻译家将其译为描述白昼的“紺碧”,有的则忠实原文,译为“深い藍色”。
(2)“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2]。——《故乡》第505页到506页
如摘录(2)所示,杨二嫂对着我说出“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等话语,给读者留下自私、恶毒的印象。但其实杨二嫂也曾经是街里街坊眼中的“豆腐西施”。我以“年龄的关系”来作为自己遗忘这一号人物的原因,但当时的我约莫20岁左右,按照常理来解释,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怎么会对美丽动人的“西施”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因而,《故乡》里暗藏了另一个神秘的世界。即,在叙事者的小说主人公“我”之外,还存在着“第三元”,这“第三元”彷佛是一双无形的手,在神不知鬼不觉地推动故事情节,使得主人公记不清天空的颜色、“豆腐西施”杨二嫂……所以,正是这“第三元”中的叙事者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健忘的人物形象。
三.《故乡》的两处“笔误”
1.“廿年前的闰土”和“把杨二嫂完全忘却了”
网络上有一篇名为《鲁迅<故乡>的两处笔下误》的文章,指出了《故乡》中的两处“笔误”。其一,文章认为,当时的闰土应该是四十多岁,“我”和闰土年龄相仿,所以也应该是四十岁左右。可从文章中看出,“我”最后一次从故乡离开的时间,应该也是“我”最后见到杨二嫂时的年龄。作者在开头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从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四十岁左右的“我”回到了离别二十余年的故乡,也就是说最后见到杨二嫂时,“我”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岁左右。誰都知道,只要发育正常,二十岁左右的年纪不会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也不是对异性毫无感觉的年龄,因此作者说因年龄关系“我”把斜对门的杨二嫂完全忘却了,是不符合现实逻辑的。
其二,文章认为,当作者写到闰土的儿子水生时,有这样几句话:“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项圈罢了。”文章认为这里的“廿年前”也是作者的笔误,因为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闰土已经四十多岁,而“廿年前的闰土”应该是20岁左右。且水生跟宏儿年龄相仿,宏儿当时八岁,水生当时也就是十来岁。由此看来,说十来岁的水生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闰土,就明显是有误的。况且,“我”和闰土“不相见将有30年了”,自那次见面后“没有再见面”,因此廿年前的20岁左右的闰土是什么样子,“我”也应该是不知道的。同时,此处在日译文中被“还原”为“三十年”,由此可见,大多数人认为,这里的“廿年前”应是“三十年前”。
(3)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3]——《故乡》第507页
(4)彼は後ろを向いて、「水生(シュイション)、だんな様におじぎしな。」と言って、彼の背に隠れていた子供を前へ出した。これぞまさしく三十年前の閏土であった。いくらかやせて、顔色が悪く、銀の首輪もしていない違いはあるけれども。「これが五番めの子でございます。世間へ出さぬものですから、おどおどしておりまして……。」——『故郷』竹内好訳
因而,读者往往认为,是由于作者鲁迅的笔误,才导致了小说中这两处矛盾的细节。但不管是“因年龄关系把斜对门的杨二嫂完全忘却了”,还是“廿年前的闰土”,以田中实的“三元理论”来看,其实这正是《故乡》的精妙所在。
2.“第三元”理论视角下的“廿年前的闰土”和“把杨二嫂完全忘却了”
故事中的主人公返乡乘船时,首先引入眼帘的是故乡的远景。而这“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的景象毫无生机可言,跟自己印象中美丽的故乡毫不沾边。我们可看出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归乡时天气较为恶劣,其二是主人公是为搬家而返乡,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心情。故而其眼中早就蒙上一层灰暗的滤镜,以这样的滤镜去端详故乡,自会产生那样“萧索”的效果。为衬托这种氛围,当主人公回到家门口时,对家门进行了一番“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的描写,又借助母亲心情不佳进行了烘托:“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母亲见着主人公感到高兴,但想到搬家的事便又沮丧了起来。
当母子二人聊到闰土时,主人公的脑子里浮现了一幅“闰土刺猹”的神异的图画。原来,闰土是主人公幼时的玩伴,二人谈论过雪地捕鸟、瓜地刺猹等新鲜事情。此处提到,“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
主人公回到故乡,自是需要应酬本家和亲戚。于是这时,闰土出现了。虽然闰土“圆脸已变作灰黄”、手也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但主人公还是喊他“闰土哥”,想对他说上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但闰土却以一声“老爷”,彻底让主人公对童年玩伴的美好期许落空,只感到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
闰土背后钻出来一个小孩,叫做水生,是他的第五个孩子。此时,文中写道:“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回顾上文,我们可以发现,主人公认识闰土应是“三十年前”,而此处的文本却是“廿年前”,即二十年前。
在招呼闰土之前,主人公还见到了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如圆规般的女人”,这便是杨二嫂。杨二嫂住在斜对门的豆腐店,素有“豆腐西施”的美称,可见其年轻时是个美人胚子,但主人公却以“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来对自己忘记这号人物进行了说明。但主人公当时约莫二十岁,正是一个男孩正值青春的年纪。而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竟能忘记住在斜对门的“西施”,着实有些说不通了。
前文提到,真正的“近代小说”中应该包含并试图解决的是“超越叙事和被叙的二元构造,从而获得真正的客观描写”这一问题。而在近代小说家中真正克服了这一问题的是鲁迅。鲁迅在《故乡》中通过设定一个“易于犯错”的叙事者,并将被叙者的“视线”置于叙事者自身无法意识到的无意识当中,实现了“用客体来凝视主体”这一目标,从而获得了凌驾于二者之上的“第三元”视角。所以,不管是“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还是“我把杨二嫂完全忘却了”,都是为了体现主人公“健忘”的特质,这种“健忘”是叙事者自身都未曾意识到的。
主人公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本不在一个世界,但其回到了故乡,便与之发生了联系。而后,回到故乡的主人公和其他人物看似处于同一个世界,实际上却是彼此割裂的存在。除水生和宏儿外,主人公的母亲、杨二嫂、闰土都是彼此孤立的。而主人公这种“健忘”的特质,仿若一条楚河汉界,把其与小说其他人物之间的区隔线描画得更加分明了。“我”记不清与其他小说人物有关的细节,这是因为“我”并未与其他人物共享一个世界。叙事者以为自己的叙事文本无误、叙事逻辑清晰,但其实自己都未曾察觉到已然在叙事过程中把“我”抒写成了一个既是“外来者”、“回归者”,又是“离去者”的人物。
四.碗碟是谁藏的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 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已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4]。——《故乡》第509页
针对这个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闰土藏的,也有人认为是杨二嫂在“栽赃”[5]。认为闰土藏的,是因为闰土当天可以自己去厨下吃午饭,便认为他起了偷碗碟的心思。认为是杨二嫂编排的,是因为杨二嫂嫉妒闰土得了许多好东西,故将碗碟藏起来陷害闰土。但正如前文所述,本文以为,此处存在着超越文本的“第三元”结构,这一元有着凝视小说人物的作用,所以碗碟之谜中必定富有隐喻性,得不到百分百正确的解答。不论是认为杨二嫂藏了碗碟,还是认为闰土偷了碗碟,都是站在故事情节内所作的考量。而站在“第三元”的视角上,应是“叙事者”将碗碟藏了起来。我们可以注意到,同在《呐喊》的另一篇《风波》中,六斤不小心將碗摔在了地上,便被七斤嫂“一巴掌打倒了”,这说明,在当时的年代,碗是极其珍贵的。可见《故乡》中“十多个碗碟”的价值并不可小觑。
扑的一声,六斤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来,捡起破碗,合上了检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连着说“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6]。——《风波》第496页
而根据小说内容来看,“须将家里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新的家具)”,且母亲还说过:“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由此可见,主人公在外地还没有达到特别阔的水平。母子二人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对待价值不少的十多个碗碟,定不会是像文中描述的那样,仅是蜻蜓点水地谈及杨二嫂所言闰土偷碗碟之事。所以,如母亲发现碗碟遭窃,理应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我”,而不应在聊天中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且“我”闻见此事,反应也十分冷淡,二人未就此继续深聊下去。故可以推测,极有可能便是这母子二人将碗碟藏于灰中的。从“我”亲切地称呼闰土为“闰土哥”,以及母亲许诺“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去拣择”中可以看出,母子二人对闰土抱有深厚的情感。所以二人同情闰土,这才在临走的前两三天将碗碟藏于土中,想当作礼物悄悄送给他。而杨二嫂发现碗碟,以为自己立了功,却没曾想实是撞破了一桩好事。
本文在田中实的“第三元”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对鲁迅《故乡》中的两处“笔误”,即“廿年前的闰土”和“把杨二嫂完全忘却了”进行了分析,也就“碗碟是谁藏的”提出了新的解读角度。最后得出结论,证明了“笔误”并非真正的笔误,而是“主体凝视客体”、超越了主体的意识的无意识,即“第三元”的结构,而碗碟极有可能是叙事者母子二人藏起来的。由此,《故乡》的可读性得到了增强,读者也获得了对近代小说新的理解方式,到达了超越小说文本本身的“第三元”境界。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佚名.鲁迅《故乡》的两处笔下误.学科网,2006.
[3]管冠生.谈《故乡》的三个问题[J].鲁迅研究月刊,2021(03)30-35.
[4]田中実.続<主体>の構築―――魯迅の『故郷』再々論.日本文学(2014): 19-30.
注 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2.
[2]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5-506.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7.
[4]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9.
[5]管冠生.谈《故乡》的三个问题[J].鲁迅研究月刊,2021(03)30-35.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96.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YJSCX2021-007)“中日无家可归者生活现状对比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