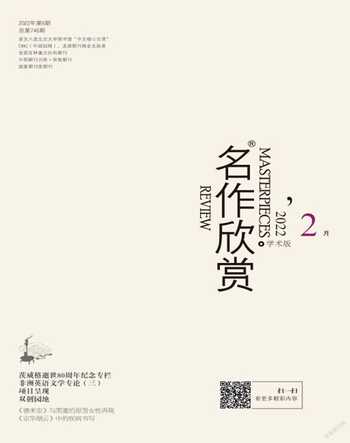从《难逃劫数》看先锋时期余华的创作
2022-02-28王媛芝
摘 要:《难逃劫数》是余华先锋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以对此文本的解读,探讨构筑起余华先锋性文学品质的核心创作观念、叙述方式。对真实的逼近、对必然的把握、对规律的展示使得余华采用了“虚伪的形式”,获得了个人书写的先锋性。
关键词:余华 先锋 真实 叙述
一、他人的目光
《难逃劫数》里,所有出现在他人视线中的人,开始在他人的预知下遭遇厄运。而预知他人的厄运并不能避免自己在别人的目光里走向厄运。由此,作者借助各个人物的目光不断切换叙述视角,一个厄运接着一个厄运,展开自己精心构筑的“劫数”链条。除了老中医,这里面没有人全身而退,但老中医为此只能把自己囚禁在阁楼上,似乎是窥视链条的顶层玩家,却早已付出了自绝于世的代价。
他人的目光也就成为作者的一种叙述手段,余华操纵着这些目光叙述者,由他們打开不同人物的不同经历。目光叙述者冷淡,甚至不怀好意的态度也构成了作者叙述姿态的一部分。
“看与被看”的模式非常明显,故事里的人仿佛都陷入了彼此目光交织的罗网,目光代表着厄运的预言,没有人能够逃脱。在阅读过程中,敏感的读者往往借由阅读的沉浸体验不自觉地将自己带入视线锁链,成为窥视者的一环。于是,自觉的读者把看书的目光异化后,书中世界和现实世界实现了暂时甚至本质上的同化,从而产生了某种无法置身书外的恐惧,阅读与文本间的安全距离被打破,读者的内心波动与作者格外冷静、不着感情的叙述姿态也就形成了强烈对比。这种对比本身也是可以被阅读者感知的,并在被感知的同时放大自身,成为作者叙述魅力的一部分。
“看与被看”的模式难逃鲁迅先生的影响,但余华的运用绝对显现了新的意义。在余华手中,视角与命运结合构筑了梦魇一般的网络,“看与被看”主导了叙述链条,更主导着宿命与劫数的上演。随着叙述(劫数)的展开,模式也就反复提醒读者自身的存在并在其心理层面构成了某种“图式”,传达着无尽的阴谋氛围。成熟的模式逼近某种形象,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指向,对于读者而言,模式网络的形象领悟具有超越语言的意义暗示,透露出更加直接而丰富的内涵。由于先锋书写意义言说的晦涩,形式层的结构形象反而有着更为逼近内涵中心的准确性。
这一叙述模式也内含了余华的另一叙述工具:对时间的运用。关于时间的独特理解和表达是先锋作家的看家本领。在《难逃劫数》中,当下对未来的预见,以及预言实现时对预见时刻的回顾有了穿插错位的空间,作者的叙述自由而精心地穿梭于不同的时态和人物视角,“模式”就更好地克服了叙述展开上的单一性,并对宿命的必然做了迂回与晕染的处理,使其克服了隐含的叙述缺陷,实现了更为复杂的缠绕形态,也反过来加强了劫数之“难逃”,而非对难逃劫数的重复式无力强调。这样,“模式”也就获得了真正的内在生命力,而非仅仅是形式上的虚弱创造。
余华让上帝的目光也进入了窥视链条,至高权威性的上帝在作者笔下成为命运的残酷预言者。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的目光窥视着每一个人,包括露珠的父亲老中医。当作为命运赋予者的上帝也在窥视,甚至主宰着窥视,命运就成为必然的暗算,得救就没有了可能。实际上,上帝的目光早已主宰了叙述,如同作者的叙述主宰了窥视者的转述。
余华把厄运由上帝引导借彩蝶和广佛如何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展示了出来。a“但她同时又似乎感到自己正被一双陌生的眼睛凝视。” “他就这样连续错过了命运的四次暗示,但是命运的暗示是虚假的,命运只有在断定他无法看到的前提下才会发出暗示。他现在透过审判大厅的窗玻璃,看到了命运挂在嘴角的虚伪微笑。”
上帝看他的子民,犹如露珠的父亲窥视露珠。老中医模仿了上帝,这就是他的快感。可以说,老中医是上帝的低劣模仿者,同时,上帝的形象在老中医的缩影下变得阴险。当上帝的目光也进入窥视者的链条,这就进一步固化了难逃劫数,并为其增加了不可抗的宿命感。
人们预知了别人的厄运却无动于衷,唯一作出提醒的是广佛,他明确地告诉彩蝶,命运正在引诱她自杀。但彩蝶对此漫不经心,视之为广佛的诅咒。这也进一步说明厄运不可避免,终究是难逃劫数。
在他人目光的叙述中,被叙述个体本身的心理体验自然被掏空,人物只有行动而没有内心活动,余华最大限度地使“人”成为他想要的某种符号。个体心灵的失语与中间叙述者不怀好意的姿态让读者逐渐跌入了一个异化世界。
他人的目光不但预言别人的灾难,余华还写出了灾难发生后,他人的目光对受难者姿态的贪婪。最为突出的是对彩蝶揭开双眼皮手术纱布后和跳楼自杀时的看客描写。由此,作者赋予彩蝶的美丽也就有了名义上的阴险,彩蝶的美丽就是用来毁灭的,而对美之毁灭的异样审视快感也就成为余华的又一刻画重点。
面对彩蝶的跳楼自杀,两个男性热烈地回顾:“她漂亮极了”“她简直灿烂无比”。这种无视个体绝望情境的由衷赞叹让人感到不适与病态的迷狂,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欲望的尾巴,欲望丝毫没有为死亡的阴影消退,反而在其背景上大放光芒,这里面自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残酷。
但沙子的祖母说:“她眼睛里放射着绿光。”沙子的表妹也十分冷漠,对男性的赞叹表示不屑:“他们是在虚张声势。”她还告诉沙子彩蝶是头朝下跳下来的,正是借这位年轻女子之口,余华详细地描写了彩蝶的惨状,更写出了女性间的嫉妒、仇视,以及其下埋藏的不可消除的对美丽的欲望。
二、自我毁灭
他人的目光,很容易造成一种“他人即地狱”的表象,但余华要表达的显然不止于此。所谓难逃劫数并非他人即深渊,他人的恶毒不是制造彼此的深渊,而是欣赏别人滑入深渊,却无动于衷甚至沾沾自喜,即便受难者是至亲、夫妻、情人、朋友。
《难逃劫数》之所以不是“难逃劫数”的无意义自我阐释,是因为它真正触碰到了阅读者的神经,使其错愕、恐惧,使得读者意识到:人是自己被自己毁灭的。甚至在小说里,欲望的人化或者说人的欲望载体化导致人必定要毁灭于自己。这才是难逃劫数。
露珠怕俊美的东山朝三暮四,便用父亲给的硝酸使得东山面目全非,但正是东山的欲望勾起了露珠的欲望,且两种欲望如此一致,所以东山其实毁容于自己的欲望。而毁容后的东山和当初的露珠一样预感到了被抛弃:“就像当初露珠在他脸上所看到的朝三暮四,他现在在露珠脸上看到了。”借助沙子的眼睛,露珠的命运也被明确,“他感到此刻悬挂在东山脸上的匕首般阴影,似乎在预告着露珠将自食其果”。
东山和露珠是被相同的欲望捆绑在一起的人,与其说是制造了彼此的厄运,实际上是毁于内心的欲望。这种毁于自身欲望的必然性就是小说所讲的“不可抗的命运”——难逃劫数,自我才是自己的真正毁灭者,由此难逃劫数获得了意义非凡的逻辑,余华正是以此为核心构建起作品形式与内容上的先锋性。
同样,广佛与被他杀害的小男孩也是一体的。广佛残杀男孩是因为男孩窥看了他和彩蝶的野合,干扰了他的情欲,但是男孩代表的就是广佛自身情欲旺盛的童年。在被执行枪杀前,广佛早已为着自己的(小男孩的)欲望把自己(小男孩)杀死了。他之所以犯罪被枪决也正是因为他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小男孩不能克制窥看野合,广佛不能克制野合),他无法阻止小男孩的窥看,因为他无法不去野合释放情欲。所以,余华写道:“如今他行将就木,他并不感到委屈,他只是忏悔对那个男孩的残杀,他感到自己杀死的似乎不是那个男孩,而是自己的童年。”
不难想象,余华对广佛残杀小男孩的长篇幅细致、冷酷的暴力书写招致了众多批评家的不满。乍一看,这像是暴力的无意义狂欢,甚至已经走到了写作伦理的边缘(假如它确实存在的话)。但实际上,余华要揭示的是人对自己的毁灭,为了把这个过程表现出来,他把人分离成不同的个体,才完成了这次隐晦而彻底的自毁。笔者认为,写出人们普遍自毁这一事实的余华有着不可置疑的先锋性,他让读者感到别问丧钟为谁而鸣,因为是为你而鸣。
彩蝶毁于自己对美丽的欲望,这是十分明显的。她邀请沙子去看她的双眼皮手术拆胶布仪式,只是为了使沙子在同样被她邀请来的众多美男子面前自惭形秽,她想羞辱他。但她的手术失败了,彩蝶也就以同樣的方式被沙子羞辱了。
人完成对自己的毁灭的过程也会毁灭别人,或者说表面上制造了他人的灾难其实不过是在自毁的方向上更进一步罢了。没有人是单纯的牺牲品,森林的妻子无辜吗?
“在这色彩丰富的呕吐物上,沙子可以想象出她的最后一餐是如何丰盛。同时他惊讶她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胃。”那么大的一个胃,森林的妻子不过也是个被欲望填满的人。她想以吞食老鼠药自杀的方式惩罚森林,但老鼠药却是假的(药厂的财欲,欲望无处不在),以至于她万分痛苦却不能死去以满足惩罚森林的欲望。
三、非理性的合法在于理性的不可靠:非经验时刻的到来
与其说余华的先锋性书写打开了非经验世界的大门,不如说这扇大门是作为一个时刻来到作家生命中的。
《难逃劫数》中的人物都是高度欲望化的人,甚至就是欲望的化身。实际上,谁能摆脱自己的欲望呢?欲望虽然时时被克制,但它依旧存在甚至还会因为过度的压抑而膨胀、畸生、异化,它作为我们精神的固有部分与肉体共生,它的丑陋不过是我们的丑陋的一部分。而表面上控制住欲望的我们引以为傲的理性、文明,它们又有多可靠呢?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写道:“车祸经常在十字路口出现,于是秩序经常全面崩溃。交通阻塞以后几百辆车将组成一个混乱的场面。这场面告诉我们,秩序总是要遭受混乱的捉弄。因此我们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即便是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了装饰。” b
余华把混乱、失序的场景作为书写重心充分暴露,表达的不是对疯狂的极致畅想、对迷乱的另类癖好,恰恰相反,他试图理智而严肃地揭露事实。不是混乱的事实,也不是秩序的事实,而是秩序不是事实,它的下面暗藏着这些一触即发的混乱。所谓非理性,它一直存在,所以理性才必须成为人们的“经验”以搭建“现实”,因此经验的世界并非真实的世界。那要如何展现这一事实呢,如何逼近真实呢?经验世界已不再可靠。
余华想表现他以高度理性看到的真实,经验与经验之下共同构成的事实,甚至于文学的虚构形体使他得以让那些未发生的事实成为他所表现的事实的全部,从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极端的景象,也唯有这种极端性刺激了我们久为经验麻木的自我与世界感知,带来强烈的意识冲击、审美快感、思想震荡。这种文学理念与创作构思的极大跨越无疑会使余华意识到,自己必须在进行书写这一动作之前先对如何书写进行调整,这是先锋时刻的到来,是一个作家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四、先锋建立于对真实、事实的哲学思考
余华所描写的“单位”不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他塑造的人物是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某一点(欲望)的载体,通过这样的“人”的活动,揭示我们内心那被压抑下来的未经触发的现实。而这种压抑必然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我们之所以强调理性就在于理性永远无法控制它无法控制的东西,它们甚至就是理性的母亲。如此说来,我们经历着的世界不过是虚伪的世界,真实没有发生,却一直存在。而余华不写虚假的事物,他要真实,一种高浓度的真实。
难逃劫数之劫数的根源,在小说里反复被命运代替,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余华的“命运”不是神秘主义,更不是无意义填塞。他指向的“命运”是文学化的哲学思考,是以叙述力量打开的规律,是真实。作者用“命运”文学化了他的哲学思考,难逃劫数的宿命论里是人毁灭于自己的必然,是理性之不可靠的真相。
余华描写了众多非理性事件,非理性的叠加需要一个外在逻辑,余华动用了“命运”,但他没有允许这个缺陷的存在,实际上这并不是缺陷,因为作者的理性早已构筑了似乎无理性的命运的面孔。“我开始重新思考世界里的一切关系:人与人、人与现实、房屋与街道、树木与河流,等等。这些关系如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我发现了世界赋予人与自然的命运。……世界自身的规律便体现在这命运之中,世界里那不可捉摸的一部分开始显露其光辉。我有关世界的结构开始重新确立……我感到这样能够体现命运的力量,即世界自身的规律……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像是事先已经安排好,在某种隐藏的力量指使下展开其运动。所有的一切(行人、车辆、街道、房屋、树木),都仿佛是舞台上的道具,世界自身的规律左右着它们,如同事先已经确定了的剧情。”c所谓不可捉摸的,恰恰是作者要以高度的理性、非凡的洞察、敏锐的感知去探索的世界之规律,余华展示的命运操纵的难逃劫数之可怕,不在于神秘主义式的不可预料,而在于这是充分的理性思考下不可抗的必然规律的结果。
在先锋小说这里,哲理已经不是评论家从小说中提炼升华之物,它就是作家创作的主动追求。d先锋时期,余华的书写要的不是一个人物,一个事件,而是支配所有人物所有事件的规律,他要写出一切。因此他构筑的是整个象征体系。人物、环境、情节除了自身的基本功能外,都是余华的符号、工具。
“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河流以流动的方式来展示其欲望,房屋则在静默中显露欲望的存在。人物与河流、阳光、街道、房屋等各种道具在作品中组合一体又相互作用,从而展现出完整的欲望。这种欲望便是象征的存在。”e这一点最直观地体现在余华《难逃劫数》中的人物命名上:东山、露珠、广佛、彩蝶、沙子、森林。
余华让“不真实”(内心世界的情感、欲望形态及其打开的内在景观)的东西真实了,我们却以为他让“真实”(常识的人、现实逻辑及其构筑的经验世界)的东西不真实了,实际上这是高度的理性被麻木的惯性指认的非理性,是此种意义上的孤独书写和精神探索在反抗着。
五、先锋的完成:以“虚伪的形式”达成真实
余华挑战的是文学作品的底层理念,而正是这种个人化、先锋性的文学理念使他认识到再也无法以经验的惯性去描写真实。唯有以虚伪的形式表达真实,以想象逼近事实。
余华自述其文学观念:“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这种传统更为接近现代,也就是说使小说这个过去的形式更为接近现在。”f“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g他对自己的先锋性有着明确的定位:真实。像高玉解读的那样:“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实在的现实,而是事实、想象、荒诞的现实,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h假如你认为《难逃劫数》是真实的,那你必定认为它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是真实的,因为真实永远真实。
比起先锋派标志性的叙述迷宫,余华更加注重迷宫通向的目标出口——真实。实际上,使得敘述迷宫成立的首要条件应该是入口和出口,其次才是这两者之间错综复杂、迷离变幻的叙述通道。某种意义上,出口指向的那片领域或者才应是意义埋藏的广阔之地,局限于迷宫内部的自我缠绕反而愈见无趣。假如优秀的读者不能走向这个出口,叙事的迷宫就是失败的,所谓先锋只能是皮囊。为此,构筑迷宫的不能是没有依据的文字与想象力的狂欢,它不是虚幻、离奇,更非臆造和谎言。
余华非常认同毕加索的一句话:“艺术家应当让人们懂得虚伪中的真实。”他说:“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现得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我不再忠诚于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i
实际上,余华一直与叙述迷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以“虚伪的形式”概括自己作品的讲述方式,强调的正是自己极力把握的真实的内容。也由于这样的创作理念,作者以“虚伪的形式”组织起“偶然的因素”,构筑了一个“非经验非理性”的文学世界,以达到某种真实、必然。
所以,先锋时期的余华几乎不使用具象,存在被象征取代,笔下的人物也不需要有职业、性格,他们是一个很纯粹的符号。拿余华常常运用的“暴力”来说,它可以充分暴露人们内心固有的攻击欲,是欲望的符号之一,是最为“纯粹”的暴力,可以尽情展现人毁灭自己的这一事实,可以代表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对抗。余华不写鸡毛蒜皮的具体的冲突,他直接以暴力冲突这种极端形式来涵盖各种冲突,使得其书写具有冷峻、简酷、超越琐碎的特质,并且这种选材上的理念化过滤与线条化处理也成功召唤了意义层次的纵深与宽广。同时,对暴力的大量使用也展现了先锋作家心灵深处难以排除的紧张感,因此这种暴力有着为作者所偏爱的精神性、崇高性,而非单纯的残酷美学与浅薄的快感释放。
卡夫卡在日记中想象一把熏肉切刀机械而均匀地从一边切入体内。对此,余华在《卡夫卡和K》中评价:“里面的词语将一串清晰的事实连接了起来……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最后‘呈卷状一片片飞出去’时又充满了美感……在想象中展示了暴力,而且这样的暴力都是针对自我。卡夫卡让句子完成了一个自我凌迟的过程,然后他又给予自我难以言传的快乐。这是否显示了卡夫卡在面对自我时没有动用自己的身份?或者说他就是在自我这里,仍然是一个外来者。”j
余华作为先锋作家思考的必然、真实控制着一切,当然也包括自身。因此他们的自我有着一种高贵的脆弱感,甚至始终和自己保持着一份疏离,这种疏离已经远离了观照与超越而走向了另一个反面。正如鲁迅先生在批判的同时没有放过自己,余华明白自己笔下写出的圈套也将让自己难逃劫数,但这种书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却已是最好的疗愈。
《难逃劫数》里,东山最终的解脱是吃了老中医给他的药,禁锢了自己的欲望,但这样的他也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他永久地阳痿了,即便他尚能苟且活下去,他也不能以一个男人自居了。”东山以残缺的代价把自己从畸形的欲望中解救出来,然而这就如同老中医以囚禁自己的代价避免着厄运的目光。这并不能给人希望,反而让人感到人的不可完整,人的必然残缺。在小说的结尾,森林没有看到东山,证明东山从厄运的注视下逃脱。东山看着森林回去了,目光没有停止,故事不会结束,欲望永不消歇,劫数继续。余华以实际的写作,致敬了偶像,如卡夫卡一般,即便叙述结束,悲剧仍然一往无前。
不可解的困境诱惑着余华,东山和老中医是必然的出路还是唯一的出路?森林必将继续厄运的故事。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东山逃往的方向还是森林归去的方向?
a余华:《世事如烟》,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cefghij高玉:《全球视野下的余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7页,第341页—342页,第343页,第339页,第 351页,第225页—226页,第336页,第376页。
d龚自强:《“小说的哲学化”之闪耀与黯淡——余华〈难逃劫数〉叙事解读兼论先锋小说之命运》,《文艺评论》2012年第7期,第90页。
作 者: 王媛芝,山西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