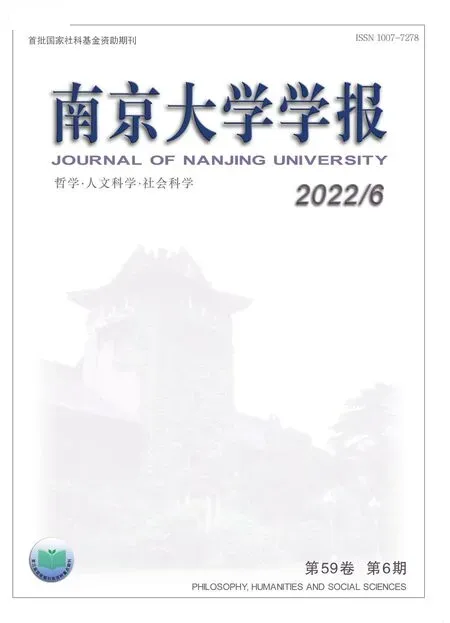“童蒙求我”与中国哲学中的主体意识建构
——关于《周易》蒙卦的一种生存分析
2022-02-24林孝斌谢文郁
林孝斌 谢文郁
(1.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济南 250100;2.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济南 250100)
近年来,有学者明确指出“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是主体性问题”(1)关于从生活儒学的角度对主体性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参见黄玉顺:《主体性的重建与心灵问题——论当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重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中国哲学形而上问题的追问。但该从“哪里”开始切入呢?这里的“哪里”有两面:一是指文本的择取,二是问题的开始。就文本择取看,无论是就中国哲学还是思想史而言,《周易》文本总是奠基性的;就问题看,追问主体性的建立才是根本性的。研究发现,《周易》的蒙卦处于乾、坤、屯三卦之后,是追问主体性建立的最佳文本。(2)就文本的源始性而言,《周易》属五经之一,其源始地位不言而喻,蒙卦又是上经的第四卦,比其他卦具有优先性。从学界的易经阐释上看,不少学者都以该卦文本为基础探讨如何实现主体意识的教育—启蒙等相关论题。因此,本文便以蒙卦为主要分析文本,展开追问主体性是如何建立的这一问题。从当前研究动态看,学术界对蒙卦的相关研究通常沿着探究《周易》的“教育—教化”思想展开。如金景芳和吕绍纲认为“蒙卦所强调的是如何启蒙,如何教育的问题”。黄寿祺和张善文的译注本在蒙卦总论中从“教学两端”的教育思想解释此卦。朱伯崑则从“类别”角度将蒙卦归于“农业卦”。余敦康从卦爻结构角度认为“表面上看来,蒙卦谈的是教育,实际上谈的是政治”,同时他也着力从“蒙昧者—开导者”这一“主体—客体”的双向关系来解释此卦的“启蒙”意义。(3)参见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7页;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页;朱伯崑、李申、王德有:《周易通释》,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年,第8页;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35页。综合以上诸家的解释,他们解卦的主体思路是将“童蒙”与“我”视为两个不同的主体展开分析。
然而,如果将蒙卦置于《周易》整体的思想脉络中看,尤其是置于屯、需两卦间,便会发现屯卦表达的是万物初生于天地间呈现出来的“充盈”状态,蕴含着生命无限的可能性;需卦则着重强调对初生之万物予以“养”,此“养”背后已隐含着某种观念性层次的东西以及引导所养对象走向某种现实性的思想。因此,在“盈—养”之间的蒙卦,预示着从某种“可能性”实现为“现实性”的生存状态。(4)朱伯崑先生曾就《周易》内容指出,就文句说,其内容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以自然现象的变化,比拟人事的变化;一类是讲人事之得失;一类是判断吉凶的辞句。本文对《蒙》的相关分析引入“盈—养”的背景,正是对第一类内容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展开其他两类的理解和分析。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但它又如何与教化问题相关联呢?也许“教育—教化”只是一种解卦思路。我们是否还有别的思路?比如把“盈—养”这种生存状态理解为一个主体的自我成长?自古以来人们对易经的阅读不断,解经思路多样,但很难准确地解读出其本来思想面貌。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回归文本的原始语境,特别地,通过对“童蒙求我”一句的深入分析,提出一种新的解卦思路,即蒙卦是在呈现一个主体从无主体意识状态进入到某种主体意识状态的一种生存态势。或者说,我们将放弃“教育—教化”这种解卦思路,而采用生存分析的进路,呈现蒙卦中的生存体验及其思想史内涵。
一、“蒙”的字义结构、解释思路及卦辞、爻辞间的态势关联
在《说文解字》中,“蒙”乃“王女也。从艸冡声”。段玉裁认为:“今人冡冒皆用‘蒙’字为之。”由此,理清“冡”“冒”二字字义有助于理解“蒙”的意义。“冡”乃蒙的古字,是“覆”义。段玉裁指出:“今字皆作蒙,依古当作冡,蒙行而冡废矣。”至于“冒”,《说文解字》云“冡而前也,从冃目”。《说文解字注》指出“《邶风》‘下土是冒’,《传》曰‘冒,覆也’,此假冒为冃也”“冃目者,若无所见也”(5)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0、637、638页。。根据段玉裁的解释,“冒”义为覆住眼睛使人无法看见。从延伸义看,蒙又与“昧”“愚”“蠢”词义相近。如朱熹在《周易本义》中就指出:“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6)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1页。扼而言之,在源始意义上,蒙指的是一种被遮蔽而未明的存在状态,而产生遮蔽之物,在生活中,可以是有形的(工具),也可以是无形的(如观念)。
据此分析,在“蒙”字所揭示的存在状态中,包含以下五种要素:蔽者(物或观念)、施蔽者(自我、人或事物或其他力量)、被蔽者(即蒙者自身之眼)、揭蔽者(自我、人或其他力量)、现实性结果(失去、重获、扩大可视范围)。“蒙”字的内在结构亦由这五方面构成,在存在态势上主要有两面:一是蔽者仍在(无论是原生的,还是后来再加上的,或者是置换的),二是蔽者被揭蔽者揭开(无论是一次性揭开,还是持续性的揭开)。这五方面的内在结构及两种存在态势共构成为“蒙”。其存在状态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处境的变化形成不同的态势。
何谓“态势”?本文认为,“态势”指的是含有某种权能、力量、方向性的可能性倾向或意向。本文将其转义为从内部规制人或事物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的动态性力量,且其力量之大小受制于其程度之深浅。因此“蒙”字字义内在结构的变化将形成不同的态势状态,从而导向不同的生存样态。既然存在着各种可能性的态势和生存样态,就意味着从“教育—教化”视角解释蒙卦的局限性。(7)这类的文章很多,主要的有刘震:《从〈蒙〉卦看〈周易〉的教育思想》,《周易研究》2016年第6期;王瑾:《〈周易〉蒙卦的童蒙教育思想理念》,《教育学报》2018年第4期;辛翀、宁怡琳:《蒙卦自然观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理念的启迪》,《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因为其思路背后的根据仍将教育放在“受教者—施教者”两个主体间进行讨论,这无形中遮蔽了蒙卦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论和生存论价值和意义。
为此,本文主张结合“态势”概念和“蒙”的字义结构,尊重文本上下关联,将蒙卦置于《周易》文本整体连贯的上下脉络中予以观察讨论,发现:处于屯、需卦间的蒙卦,它与屯卦关系是“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稚小,蒙昧未发,蒙所以次屯也”;与需卦的关系是“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8)李光地:《周易折中》,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年,第44、49页。。因此,以“盈—养”为存在背景,来呈现蒙卦中“童蒙—我”同一主体两种不同状态在各种态势中的发展变化是本文主要解释思路。实际上,这种解释思路并不突兀。早在朱伯崑教授等人的《周易通释》一书中,虽未对蒙卦给出具体分析,却也扼要地指出该卦是:“象征人的美德,只要能坚决贯彻下去,最终还是能冲破外界的阻压,象山泉那样汇入滔滔江河,蔚为大观。”此外,该书在理解震卦时曾鲜明地指出:“从对雷电的一味惧怕和顶礼膜拜,到对它冷静观察而后不惧怕,逐渐又到人们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关心,……最后到认为雷之是否为害,主要取决于人们自己的道德、理智和行为。……整部《易经》以占卜的形式表现出从蒙昧中抽衍理智,从直观中加强理性的认识过程。”(9)朱伯崑、李申、王德有:《周易通释》,第25、13页。总体认为震卦呈现了主体对外界认识不断演进的态势。将此思路引进对蒙卦的分析中,那么蒙卦就呈现为主体性的建立过程。
学界所做的分析对我们理解蒙卦大有裨益。至于在卦名、卦辞和爻辞、爻辞彼此之间的内在连接关系上,“传统的看法是,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但这是一种“怎样”的内在联系,始终无定论。据此才有“学者们根据自己的解释,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周易》理论和系统”(10)朱伯崑、李申、王德有:《周易通释》,第9页。根据朱伯崑等学者的研究,他们认为六十四卦中对每一爻的位置与性质加以“初九”“六四”之类的称谓,乃是后人在编《易传》时附加的,可能并非原始就有。本文也是基于这点,所以在具体分析上并不侧重于这类称谓。。足见,对《周易》的理解,学界并无统一标准,仍受制于研究者的思想结构和情感结构。在形式上,卦辞位于初爻前,是概括性地阐明卦义。爻辞是卦的主体内容,每爻间存在意义的相互关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着重从蒙卦的位置、性质及生存分析的角度对蒙卦给出概要的理解:卦辞主要呈现出“大态势”的生存状态,各爻辞呈现的是不同处境中“小态势”的生存状态。各爻辞间既有“态势”上的关联和过渡,又有彼此间的“张力”和“顺延”。综合来看,卦辞、爻辞及爻辞间的关系呈现出“动态性、张力性、顺延性、趋前性”的特征。我们在以下的爻辞分析中将呈现这个特征。
二、“童蒙求我”:蒙卦的卦辞分析与态势之象
在《序卦传》中,韩康伯就蒙卦所处的位置指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11)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62页。他以“盈”释“屯”,以“养”定“需”,“盈”指的是初生之万物原始生命力的充盈和无限,有待展露;“养”则涉及一定的食物供给,这种“食物”既可以是具体的物质,也可以是具有特定倾向性的善观念和意志。至于“蒙”,作者以“物之稚也”界定,“稚”是关键,它表达的是一种蕴含各种可能性倾向的生存状态,并且在这些可能性之间或者内在层面存在着各种的正反两种力量,故本身就内含了某种潜在的力量博弈。进入“养”时,就预示着在某种特定观念或倾向性中的“培育”,借此将所展望的那种可能性逐渐呈现并转换为现实实在性。
(一)“童蒙求我”:一个主体的两种状态
我们来看蒙卦卦辞:“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12)李光地:《周易折中》,第44页。卦辞首尾用“亨”和“利贞”,表达了一种总体上适合前行的良好态势。卦辞的关键在于“童蒙—求—我”,“初(再三)—筮(渎)—告(不告)”这两种关系结构。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将它们分别指称为A结构和B结构。
在A结构中,如何理解“童蒙”和“我”是关键。先来看“童蒙”之“童”的字义解释。《说文解字注》指出:“男有罪曰奴,奴曰童。”(1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204页。而“奴”则是一种自己无法做主,有别主为之主的生存状态。换言之,由“奴”所表达的“童”是一种不具备自主、自我和独立性的主体意识,综合“童”的分析,故“童蒙”一词表达的是“无法自主、选择且不知所向”的生存状态。对此,朱熹在《周易本义》中将“童蒙”解释为“幼稚而蒙昧”(14)朱熹:《周易本义》,第11页。。这是一种“无主体意识”状态下“可能性待发”的生存态势。
再看“我”字。程颐认为:“六五为蒙之主,而九二‘发蒙’者也。‘我’谓二也……二乃‘发蒙’者也。”(15)李光地:《周易折中》,第44页。所谓的“发蒙”者,是具有“发蒙”能力之人,已然具有一定的主体意识。在“教育—教化”的解卦思路中,“我”通常被释为教育者,是外在于“童蒙”状态中的主体的另一主体。这样一来,“童蒙求我”便存在着两个主体。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外在主体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以上解释思路并未涉及。由此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为,蒙卦要处理的是“童蒙”状态中的主体如何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的过程,并不涉及其他主体。所以,“童蒙”与“我”是同一主体的两种不同存在状态,彼此间的关系系于“求”字。一般而言,“求”是一种能力不足而又有所欲的生存冲动。因“童蒙”乃是无主体意识的状态,故由童蒙自身发出的“求”所指向的目标就是主体意识。我们说,“我”是一种主体意识,“求我”就是“求”这个主体意识。不难理解,“童蒙求我”是在描述这个过程:在“求”这个动作中主体是如何从无主体意识状态趋向拥有某种主体意识的?“匪”是“否定”意。人们往往会从“我”出发来理解自己,认为“我求童蒙”(我去理解自己的起点)。“匪我求童蒙”是要否定这种理解顺序。在“童蒙”状态中,这个主体缺乏主体意识,但可以发展出任何一种主体意识。从解卦的角度看,这个“童蒙”状态中的主体当然可以期待一位启蒙者的到来,从而接受教化,形成一种主体意识;但是,他也可以凭自身而独立地形成自己的某种主体意识。如果存在着这两种发展途径,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只用其中一种途径来处理这个“童蒙求我”过程。我们认为,把“童蒙求我”理解为一个主体意识的形成过程,而不简单地只是一个教化过程,是更为合适的。
在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童蒙求我”不是两个主体间的关系,而是一个主体的两种不同状态。这句话所呈现的是从无主体意识状态走向某种主体意识状态的态势。“求”在于“童蒙”向“我”的敞开和进入。“童蒙”的敞开指向“我”,目的是要成为“我”,一个主体从无主体意识趋向某种主体意识。这里我们不需要格外引入一种外在力量(如发蒙者或教化者等)。反过来看,“我”是一种已经具备了主体意识并且能够作判断选择的生存状态。这种存在状态是在某种主体意识(比如一种善观念)中,并在它的支配下进行判断选择的。“我”所求的,是在我的主体意识中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去求“童蒙”:一个主体在拥有某种主体意识之后,不会追求回到那种无主体意识的状态中。就其进展而言,一旦“我”建立起来,这个主体就会有需要,并进入需卦。蒙卦诸爻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主体在建立主体意识的过程中其凶吉(或善恶)倾向如何?
要之,在“童蒙”中发展主体意识,乃是一种自在自主的过程,而不是在某种固定模式中的成型。
(二)B结构所呈现的生存状态
在A结构的相关分析基础上,再进一步看B结构的意义所在。在B结构中,存在两种相反的状态:“初—筮—告”(B1);“再三—筮(渎)—不告”(B2)。
“筮”是B1与B2的共同界域,是理解这两种状态的关键。“筮”在殷商时期是常见的问天命、占吉凶手段。(16)有学者指出筮辞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又分为三种。一是贞事辞。古代人们对许多事情应如何办,不敢自行决定,于是通过占筮请示神灵。占筮后把请示的事记录下来,作为后来的参考。这就是贞事辞。二是贞兆辞。如吉、凶、无咎等。三是象占辞。本文对《蒙》卦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前两者。参见朱伯崑、李申、王德有:《周易通释》,第9页。关于“筮”,郑康成说:“筮,问也。”也就是说,筮乃是用蓍草占卦以问吉凶的一种方法。(17)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校释》,第23页。程颐也认为这是“占决”之意。(18)李光地:《周易折中》,第44页。故,“问者—筮者—天命”是“筮”法的三大要素。在这一结构中,“筮”所指向的对象是外在于人的“天命”(19)天命意识乃是《周易》文本中极为关键的力量。诸多学者在相关分析中指出这一点。如有学者在分析否卦时就指出“命”乃是天命,有天命而行天命才能无咎。可见天命意识对人现实行动的力量。参见李尚信:《〈周易〉古经泰否二卦本义解读——兼释萃涣大过剥鼎等相关卦爻》,《周易研究》2018年第6期。朱伯崑等学者也认为《周易》时代之人仍然崇信天神和天命,但人的行为在有些事情上在天命面前并不绝对被动,而是有了一定的能动性。参见朱伯崑、李申、王德有:《周易通释》,第11页。或天道。但“天命”不自启不自显,需要借助特定的仪式、手段才能“稍示”于“筮者”,再由“筮者”将所得“天命”之意“告”之于“问者”。在这种传送渠道中,“天命”是在“筮者”的敬畏情感中呈现其实在性的。一旦“筮者”不敬或假装敬虔(比如在“再三”这个动作中),就会出现天命不呈现(“不告”)的情况。而在解读、传输所得天命之意时,“筮者”又受制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情感结构。但是关键在于筮者的敬畏情感。从这个角度看,“问者”亦然:“问者”的敬畏指向天命(他来求问表明他对天命是敬畏的);同时他还要完全信任“筮者”(筮者说什么,他就要接受什么)。“初”表达了“问者”和“筮者”的敬畏和信任;而“再三”则表明他们的这种情感受到损害。
在B1结构中,“问者”对“筮者”完全信任,就能从“筮者”那里获得关于所求之天命(或凶吉)的讯息。而B2结构中则反向说明,对于“问者”来说,他需要在敬畏和信任中接受“筮者”从“筮”中显现的天命讯息或凶吉讯息。在“筮者”那里,“告”还是“不告”则涉及他的敬畏和知识。这是理解B结构的关键。
在B结构中,天命是指向所在,是“问者”和“筮者”共同的敬畏对象。此二者不仅共享了“敬畏”情感,也共享着共同的指向对象。但因双方在知识结构和情感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对同一指向对象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这也决定了他们“问者”和“筮者”的身份差别。但是就天命在双方身上共同的呈现渠道看,天命的实在性也是在这同一的敬畏情感中呈现出来。但因着双方在身份上的差异,导致“问者”除了敬畏情感之外,还需要在信任情感中接受来自“筮者”对天命之意(吉凶)的解释和传送,缺了任何一个,都将导致“问者”求天命的失败。因为一旦某种“疑惑”进入“问者”的敬畏情感或者挨近它,都将导致在“问者”那里“天命”呈现的中断,甚至走向否定天命的实在性。之所以强调“问者”的敬畏、信任情感,是因为“问者”之所以来到“筮者”这里求天命,正是因其在现有的观念认知中不知所措,陷入一定的生存困境;而在敬畏、信任情感中则打开了“问者”接受性的维度,在此维度中,天命作为外在力量得以以某种可能性进入到“问者”的敞开性、接受性中。当这种可能性与他原有的观念认知相冲突时,因有足够的情感支撑,“问者”就很容易放下并否定自己原有的观念判断,从而接受“新”的内容进入到他的观念认知中,最终形成“新”的观念认知,构成“新”的主体意识。“问者”也正以此为起点展开新的生存状态。对“筮者”而言,他的敬畏情感既是保证他向天命的接受性维度,也是确保“问者”对他的信任程度。
因此,无论对“问者”还是“筮者”而言,B结构都要强调:在“天命”面前,不应当行使自身的判断,而应该在一种敬畏中指向天命并接受天命的呈现。可见,B结构要求“问者”和“筮者”放下自身的判断权利。相较于A结构,B结构中的“问者”和“筮者”正是A结构中的“求者”,即从“童蒙”状态进到“我”状态中的那个主体。这里的“筮”也可以理解为“求”。在尚未形成主体意识时,主体在求一种主体意识;但是,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主体意识呢?对于童蒙状态中的主体来说,他只能“筮”。因此,“筮”是对某种未知的固定秩序(天命)的求问,这种求问是在敬畏中进行的。在“童蒙求我”中,“问者”与“筮者”是同一主体。
然而,在“我”的形成过程中,这个“我”作为主体意识会在任何阶段都自作主张进行判断。比如,在“初筮”中得到的结果,对于在某一阶段中的主体来说,如果他根据当时的主体意识进行判断,会认为这个结果不好,从而要求“再筮”。一旦进入判断,对“天命”的敬畏就丧失了。在这种情况下,“筮”不如不“筮”;即使“筮”,天命也不会显现(“不告”)。由此可见,B结构呼应A结构,二者共构为AB结构,该结构要求“我”即“筮者”放下自身主体意识(因为尚未完全)和判断者身份(或怀疑态度),而在“敬畏”中指向天命,接受天命的呈现以推动主体意识的建立。
可见,在蒙卦的卦辞看来,AB结构的结合才是“亨”,亦是“利贞”之状。“利贞”的意思是合适或正当利益。也就是说,当“问者—筮者”不从自我判断出发,而是在敬畏中指向天命时,才能建立一种符合天命的主体意识。只有这样,“童蒙求我”才是在“亨”的态势中。
《彖传》和《象传》对蒙卦的卦辞是这样解释的:“《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20)李光地:《周易折中》,第340、418页。我们知道,《彖传》是理在象后。蒙卦在卦象上呈现的是山水卦,表达的是一种“山下有险,险而止”的意思。“象”背后的“理”可以转述为:“山”指向的是一种天命或天道所在之处,而“蒙”所呈现的状态正是求天命之人欲往此“山”而在“山”下有“险”的状态。“险”指的是一种阻碍,如绊脚石、走错路等险阻。“险而止”表明这种力量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是在可克服或避开的范围之内。那么,是什么最容易潜伏在“山”下而成为一种“险”呢?前面关于AB结构的分析表明,出于主体意识而有的自作主张才是真正的阻碍,它会阻拦“天命”的呈现。换句话说,“天命”是“童蒙求我”的目标,是“筮”的指向,也即“我”的正确建立,当主体在某种主体意识(比如某种善观念)中自作主张时,这个主体就陷入真正的险境中。这是阻碍人上“山”的关键。
当然,在“童蒙求我”的过程中,主体意识尚在形成中,因而并不是特别顽固,此时,“险”在可“止”的范围内。这里,“志应”之“志”从源头上讲是“童蒙求我”之志,而“应”则是符合天命之意。在AB结构中,“志应”表达的是要人放下当下的主体意识,继续在敬畏中指向天命而让天命显现,并进入“我”,使得“我”得以在“天命”中正确地建立起来。
至于“渎”,它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敬畏天命的情感倾向,或者说,如无敬畏天命情感,则无所谓“渎”,也就失去了当有的“至诚之心”(21)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第67页。。当人在判断中要求“再筮”时,等于不相信天命在“初筮”时的显现。这就是不敬之“渎”。分析表明,人的“不敬”表现在人陷入某种善观念判断中,执着于某种主体意识,从而走入“险”境。为避免这种情况,《彖传》末尾才说“蒙以养正,圣功也”,意在指出圣人的功用在于对处在“蒙”状态中的人进行合适的引导,使其“正”,从而避免“险境”发生。“圣功”乃是在“童蒙求我”中正确地建立了“我”,即主体拥有了一种符合天命的主体意识。
《象传》中的“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这一句对蒙卦卦辞的解释关键在于“泉”“果行”“育德”三处。“行”“德”的引入,表明进入了一种修身伦理的层面。从这一点上看,蒙卦所指向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儒家修身观念的思想来源。朱熹和程颐认为,“泉”指的是一种原始性的状态,如水是从泉而出一样。在蒙卦这里,“泉”指的是一种原始性存在状态,即“童蒙”。当人在这种状态中成为君子(追求天命的人)时,他在天命中成就了“求我”这个动作。君子作为敬天命之人,在敬天之中,犹如泉水涌出,按照天命所设定的秩序,展现所有的可能性使之成为现实的生存状态。这里的“果”是源自天命本身而有的呈现;以此“果”指导君子之“行”,就是一种“以果行”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君子的生存是一种保持在天命引导下的生存,是在天命中培育自身之“德”。君子之“德”的培育乃是人在敬畏天命中“童蒙求我”的果实。
三、AB结构视域中“六爻”的生存状态
前文指出的“盈—养”生存背景和AB结构是我们理解和把握蒙卦六爻爻辞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AB结构向我们展示了天命在敬畏情感中所呈现出来的力量及作为可能性来源的天命本身是一种具有势能的“态势”。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对态势的阐释,我们可以对人的未来进行一定意义上的预测。态势隐含着未来变化趋势。本文将“态势”理解为从内部规制人或事物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趋势的力量(有大小或强度的区分)。就此而言,“天命”所昭示出来的可能性一旦进入人或事物内部就成为人或事物自身内部的“态势”力量,它对人或事物的生存状态的改变具有导向作用。由于人或事物的变化离不开一定的“时空”,因此,“态势”自然是在“时空”或处境中展开。
以此观之,蒙卦六爻爻辞所表达的内容正是基于不同处境而展开的各种态势;而且这里的态势是由内部的天命所规制的。通过“爻辞”来呈现这些内部“态势”,就能够向我们展示“天命”在不同的生存状态中所呈现的不同作用。这种处理有助于我们对蒙卦爻辞的理解回归其原始语境,并为思想史上的延伸义理提供有益的解释空间。
(一)从发蒙到包蒙:主体意识发生发展的内外条件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按照朱熹的看法,他认为初六的发蒙是“以阴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当发其蒙。然发之之道,当痛惩而暂舍之,以观其后。若遂往而不舍,则致羞吝矣。戒占者当如是也”(22)朱熹:《周易本义》,第12页。。从位上说,初爻的性质决定了整个卦象的基调。初爻以“六”,故而为“阴”,决定了这个卦的基点是一种“屯”之后初生万物“盈”盛之状,尚处在“无所向”的起始状态。对此,欧阳修指出“《蒙》者,未知所适之时也,处乎《蒙》者”(2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108页。。“发蒙”则意味着,要准备走出这种“未知所适”状态。那么,“发蒙”之“发”的力量源自哪里呢?这是关键所在。
从“发”的字义上看,存在两种力量源:一种是外在力量,另一种是自身内在力量。在以“教育思想”解释模式的进路中,这里的“发”的力量指的是一种外在力量,即给予发蒙者的力量。我们放弃这个解释进路。回到AB结构中,我们认为,这里的“发”的力量源自初生万物自身内在之力量,也就是内在的那种“态势”之力。由于“蒙”自身内在存在多种力量和势能的博弈和流动,它是一种多种可能性力量之间的交织状态,所以,到底事物具体往哪里倾向,内在态势作用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另一面,作为在万物关系中的个体,自然也不可能摆脱外力的作用。
下一步将在引入优良谷子品种基础上,进行谷子种业、谷子规模化种植、谷子及秸秆饲料化、小米深加工产品开发及产业化,全面发展小米“种植、养殖、加工”全产业链,立足保加利亚,形成可复制的盈利模式,并逐步辐射到欧洲其它国家,为我国农业“走出去”做出贡献。
当“发蒙”之状应用在具体的“人”生存状态上时,初爻所说的“利用刑人,用说桎梏”(24)有学者指出“刑”和“说”各自都有两层含义:“刑”有刑法和典刑义,“说”有脱去肉体和精神枷锁义。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第36页。中的“刑人”和“桎梏”指的都是一种外在方式和手段(25)《周易正义》指出:“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刑人之道,道所恶也。以正法制,故利刑人也。”对此,孔颖达在疏中指出“刑人之道乃贼害于物,是道之所恶,以利用刑人者,以正其法制,不可不刑矣”。王弼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9 页。,其目的在于培育人的“敬畏”感,这一点正如程颐所说的“使之知畏……畏威以从”(26)李光地:《周易折中》,第45页。。也就是说,对人而言,处在生存初始阶段中,正是有各种可能性的发展状态,是主体意识的开端,但恰恰是这种多种可能性并存之状,反而使得人无所适从,等同于停滞、无用之状。通过“刑”和“桎梏”这种外在方式使得人产生“敬畏”之感,而此“敬畏”指向的是天命自身。因此,这里的“发蒙”就是让进入生存而主体意识尚处开端时的人先形成对天命的敬畏,并以此为起点开启他的生存。因为没有人可以判断人在初始阶段之中的诸多可能性到底哪一种是对人最有益的,或正确的。但是人必须先建立敬畏情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主体意识。有意思的是,《易经》作者似乎没有对此给出任何理由。为什么敬畏情感必须首先建立呢?且这种敬畏情感最终必须指向天命(作为正确主体意识的发展方向)?
人是在一定的现有秩序中从“童蒙”出发的。他是被给予的,因而在阴位上,为阴爻。这里提到的“刑人”,可以理解为人生活在现有各种规范中,接受规范,形成习惯。这种“刑人”对于“童蒙求我”是有利的,因为这些规范的强制性可以培养人的敬畏情感。但是,它们也可以规定人的主体意识发展方向。这里,如果在“刑人”中未能建立敬天情感,而是仅仅给人加上“桎梏”,人在童蒙状态中的所有可能性就会被限定了。也就是说,一旦“刑人”陷入“桎梏”,就不利于“童蒙求我”。在起点上,规范是必需的,但不能被桎梏。爻辞中的“以往吝”,意思是,当规范成了桎梏时,就不是好事了。因此,程颐强调外在规范的作用在于培养敬畏之心。主体意识在敬畏中开始发展是一种开放性的发展。敬畏面对的未来有好的和不好的两个方向。在敬畏中,人才能谨慎面对,寻求好的方向(天命所定),避免坏的方向(违背天命)。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在字义上,“包”有“包容、包涵”义(27)王弼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易正义》,第 40 页。关于“包”解释为包涵义,参见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第37页。。从象数的角度看,“九二”是内卦之主,是本卦的第一阳爻。朱熹称此为“统治群阴”(28)朱熹:《周易本义》,第12页。。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人的主体性开始突出。分析人的生存状态可以看到,处在“九二”这一位置的人,开始统辖(“包”)“童蒙”中的所有可能性。主体性突出是主体意识建立所必需的,因而是“吉”。主体是在敬畏中统辖这些可能性的,因而寻求让“天命”进入自己的生存。作为统辖者,他必须拥有责任感。建立责任意识是他的主体意识建立的第一要务。
爻辞提出“纳妇吉,子克家”这一生存态势来说明主体意识中责任感之形成。人的责任感是要在面对他人时才会出现的。小时候,父母为他负责一切。虽然他也可能学会负责一些小事,但是,真正担当责任是在娶媳妇之时。“纳妇”意味着成人的开始,多了一份“丈夫”的角色,自然需要开始形成与“丈夫”角色相配(29)《周易正义》中指出:“‘妇’谓配也,故纳此匹配而得吉也。此爻在下体之中,能包蒙纳妇,任内理中,干了其任,即是子孙能克荷家事。”王弼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易正义》,第 40 页。的责任意识,如照顾妻子、抚养子女等。在这种家庭伦理的态势中,所形成的责任意识是有助于生存的,符合天命秩序的。而且在家庭中这种责任意识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需要更多的包容。
“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勿”字说出此爻想要表明的主题是一种否定性的或要避免的生存状态,是要求当事人的主体意识中自我制约的态势,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宜盲目躁进。(30)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修订本)》,第54页。从象数角度看,此位是“不中不正”,从生存倾向上看,处在此时空中时,要注意从自身而出的某种决定或决意。爻辞中的“勿”字说出了一种生存中的判断选择。这是一种带着某种主体意识的做法,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在九二位上生存状态中的人要在敬天情感中统辖各种可能性,首先要建立责任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判断选择。在九二爻那里,娶妻养子是有助于责任意识建立的。此爻则特别指出有所不为,即“用取女,见金夫”这类做法不利于责任意识的建立。故“《象》曰:勿用娶女,行不顺也”。虞翻认为是:“失位乘刚,故‘行不顺’也。”(31)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11页。今亦有学者指出:“六三以阴柔之质而居阳刚之位,不中不正,浮躁妄动,被上九的权力财富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不顾自我的身份人格主动前去追求。这种追求行为不顺,根本不可能结成阴阳相应的关系,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32)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第37页。
这里需要一些文字说明。“用取女”的“取”字大都被理解为“娶”。我们认为,前面用“纳妇”,这里再用“娶女”,重复一件事,文字上前后缺乏呼应。而且,这里“女”还得用“见金夫”来说明,不但文体不顺,且有强词夺理之感。此外,这种解释还把“用”字忽略不顾。换个角度看,“取女”和“金夫”可以看作是一类富有的给予者,其中的“取”和“金”都是收获满满的意思。“用取女,见金夫”的意思,指的是当事人在和这种人交往时可以不劳而获。然而,这种生存状态是不利于责任意识之建立的。对比之下,亲躬才是长远之道:“不有躬,无攸利。”反过来说,只有“有躬”(亲自作为),才能“攸利”(长远利益)。因此,责任意识是在自己的亲身作为中建立起来的。
(二)从困蒙到击蒙:主体意识建构的张力
“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此爻的“困”字指称一种没有主意的生存状态,乃处不好之境。(33)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第71页。余敦康在解释此“困”时,也指出这是陷入穷困之地。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第38页。“童蒙求我”是要求主体意识的建立,要求主体建立责任意识,并在责任意识中形成一套有秩序的观念体系,以落实他的责任。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人在建立有秩序的观念体系时出现一种困境:在进行判断选择时自相矛盾,比如,此前决定做A,现在却在做非A。在生存中出现如此的矛盾就不免陷入困境,称为“困蒙”。对比之下,困蒙不是童蒙。童蒙是各种可能性待发状态,困蒙则是在主体意识中的自相矛盾。人在困蒙中,如果继续前行,就一定走向自相冲突。因此,在困蒙中,人只能退回童蒙状态,即放弃已经建立的那种主体意识,重新建构新的观念体系。童蒙本来是在先的,是主体意识建立的起点。这里重新出现在困蒙之后,作为困蒙的出路,一方面,表明主体意识在建立过程中陷入困境;另一方面,表明主体回归可能性状态并非倒退,而是摆脱困境的必要步骤。
从象数上说,六四爻辞在朱熹看来是一种“既远于阳,又无正应,为困于蒙之象”。换言之,此时的生存者离正确的引导太远,无法得到正确反应,只能够在各种混乱的意见中徘徊受困。所以,对于如何走出这一“困”蒙之状,朱熹说:“能求刚明之德而亲近之,则可免矣。”(34)朱熹:《周易本义》,第12页。朱熹的这一解释同样在程颐和后来的注《易》者处可见。(35)具体参见李光地《周易折中》中的程传、集说等各种解释。李光地:《周易折中》,第47页。
与“困蒙”状态相对的则是六五中的“童蒙”状态。如果说“困蒙”是因为丧失对天命的聆听和受各种外在善观念的迷乱,从而致使主体意识发展受阻的话,那么就要回归“童蒙”。朱熹在解释六五中的“童蒙”时,说:“柔中居尊,下应九二,纯一未发,以听于人。”(36)李光地:《周易折中》,第47页。程颐等人更是提出,生存者要以“至诚”之心来应对。在这里,他们强调的重点在于生存者要回归童蒙状态,在敬畏中静待天命显现。可见,在他们的理解中,困蒙之状乃是生存者在尚未成长起来的自我主体意识中陷入了一种杂音不断、正音不听、困惑不已的生存状态。
由此可见,“困蒙—童蒙”之间的关系是生存状态的两面,也是生存的张力所在。对一个具体的生存者来说,在这种张力中徘徊和进出是常见的事。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从象数的角度来看,上九爻是非正(阳爻据阴位),非中(不是二爻与五爻),但是得到了周围爻位的应和,特别是其据于六五爻位之上。(37)刘震:《从〈蒙〉卦看〈周易〉的教育思想》,《周易研究》2016年第6期。《象传》说:“利用御寇,上下顺也。”可见,此爻的关键在于“击”和“寇”的解释。我们先来看“寇”的解释,按照《屯》卦中六二爻辞中的“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中“寇”的文法含义,“寇”指的是一种不遵守秩序的生存状态。程颐在解释此爻时,也同样是以“非理而至者”来解释“寇”字。(38)李光地:《周易折中》,第419、40、41页。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注》中指出,“寇”为“暴也”(39)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244页。,指一种破坏秩序的暴力状态。因此,以“无秩序”来指称这种“寇”是合适的。对“寇”有了这种基本性理解,“击”的意思就很明确了。“击”与“暴”有类似的地方,指称外在力量的作用。不过,它们的手段和出发点却不同。
“击”呈现一种对立双方的外部冲突,即一方要破坏另一方。如果一方在“击”时无意于建立秩序,而是仅仅要破坏对方的秩序,那么,这种“击”就是一种暴力,属于为寇行为。如果一方在“击”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现有秩序,或用自己的现有秩序对抗暴力行为,那么,这一方必须自己在遵守规范中“击”,属于防御行为。因此,这里的“击蒙”是在建立秩序,包含着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意思。
《说文解字注》释“御”为“使马”(40)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58页。,即驾驭,引申为使秩序化。这里,“御寇”的意思就是驾驭那些不遵守秩序的人。由于这种驾驭是一种强制性动作,因而也称为“击”。本爻辞认为,“击蒙利御寇”,但“不利为寇”,强调的是,童蒙求我是一个走向秩序化的过程;或者说,主体意识的建立是要建构一种秩序化的观念体系。《象传》说“利用御寇,上下顺也”,意思是,“上下顺”指向一种秩序化。只有在秩序中,才能有“上下顺”的生存状态,才算达到了“御寇”的成功。朱熹等人从“治蒙”如何“适宜”的角度来解释“上九”爻辞,和我们这里的解释思路基本相同。
我们把上九爻置于AB结构中来理解,可以发现,“童蒙求我”作为主体意识生成过程,起于敬畏情感的建立,顺应天命秩序,培养责任感,并在秩序与无序的张力中,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击”的冲动,是把秩序加在无序中,并不断扩展秩序的冲动。这个冲动最后指向天命秩序,形成了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体。如果这个个体是人,那他的主体意识可以从我们自身的主体意识中去加以理解;如果这个个体是万物之一,我们则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内在秩序和自身需求的事物。万物并行,各有所需。这就进入“需”卦的态势。
结 语
《周易》六十四卦的成象离不开作易者在具体的生存状态中的观察和体悟。这些卦表达了当时的思想者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在阅读这些卦辞和爻辞时,只有分享他们的生存体验,才能进入对它们的理解。本文以态势这个概念来理解卦象,至少在蒙卦中,我们发现,《周易》作者对人的主体意识之生成过程有细致而深入的观察和体会。这些观察和体会构成中国思想的起点。每一卦象都呈现了一个态势,呈现出《周易》作者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所观察并体会到的世界的方方面面。
本文放弃从“教育思想”解释蒙卦的传统思路,转从“敬畏情感—天命力量—主体意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来阐释蒙卦所展现出来的主体意识的建立过程。这一解释思路可能会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因为易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系辞下》),其中的“人道”就是“主体意识”之道。也就是说离开主体意识的“人道”研究和义理挖掘是丧失生存性意义的。反向可以说明,研究“人道”需要从某种主体意识出发,但究竟该是怎样的一种主体意识呢?是犹如西学意义上,尤其是自“笛卡尔—康德”脉络意义上形成的“主体理性”意识,还是如自“路德—齐克果”意义上的“主体接受性”意识?我们认为,本文的意义不是在于择取一端,而是基于人的生存分析,指出人在生存的维度上,既有接受性维度,又有主体理性的维度,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两重维度的张力,这才是“人道”的深层意义所在。正如《周易》指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无论这里的“人”还是“心”,都指出“主体意识”作为认识者的重要意义;而“人”总是复杂的,也是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情感结构的复合体,如果不深入展开主体意识深层次的结构世界,那么所谓“人道”的理解和认识总是无法触动主体自身及其他主体的。
其次,借由蒙卦分析所打开的天命维度可以看到《周易》哲学研究中的“神圣超越”性维度。(41)近来有学者侧重从“神圣超越性”视角来重新解读儒家哲学的相关经典文本,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关于从“神圣超越性”角度重释《周易》文本,参见黄玉顺:《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周易〉与现象学的启示》,《周易研究》2020年第2期。很显然,本文并非从“位格性”意义上指向这种“超越性”,而是在“哲学性”维度上指出,天命作为从殷周以来不断“人文化”的力量,仍然深潜在作为主体之人的接受性维度和主体理性维度的心灵深处。激发或重新呈现出这一力量,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动主体性的发展与完善。就中国哲学而言,一直以来,“天道—人道”的言说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而《易传》则是起点或奠基性的。虽然其具体内容因时代性差异需要摒除,但是其深刻的认识论和生存论的奠基性意义则是不可或缺的,乃至是生死攸关的。换言之,借由蒙卦所打开的对“天道—人道”模式的理解是有追根溯源性意义的。
最后,对蒙卦的生存分析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呈现出中国哲学中隐含的认识论维度。文章所指出的“敬畏—信任”情感构成了主体内置的“情感结构”,打开的是由天命所代表的“可能世界”,而该情感结构则是该可能世界之实在性得以呈现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主体不断生成“新的主体意识”的来源所在。无论是原有的主体意识还是新的主体意识,总之是共构成为主体的思想(观念)结构,成为主体在生存中进行选择判断的“根据”或“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