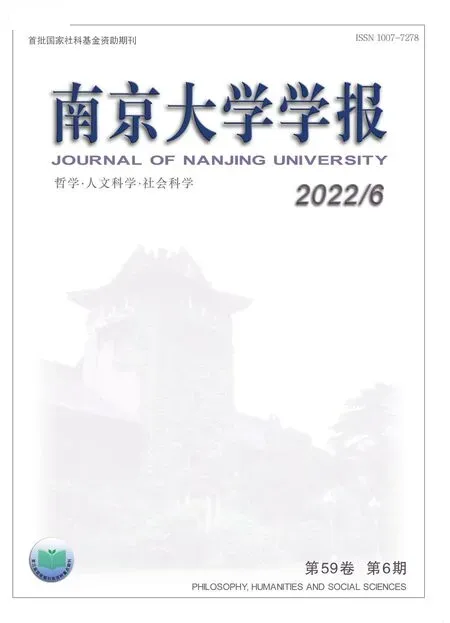《资本论》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货币权力批判
2022-02-24温权
温 权
(1.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23;2.伊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植根于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政治经济学“书写”。问题的关键在于后者究竟因循何种线索得以“言说”?诚然,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部分指出:该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并不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反而对“这些规律本身,……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青睐有加。(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这表明,《资本论》以破解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因循何种“铁的必然性”为要旨。此外,反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市民社会是产生法或国家等政治权力的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论断,又能看出: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其“铁的必然性”恰好印证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权力。它不单是传递资本主义政治性权力的“以太”,更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普照光”。这种特殊的社会性权力,正是装在每个人衣袋里的货币权力。(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106页。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本质可视为社会化的货币权力。与之相对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以货币权力的社会化形态变迁史为线索。它作为一种“抽象力”,同时涵盖对资本主义“是其所是”的演绎,对资本主义“从何而来”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去往何处”的预测。
一、资本主义“萌芽史”的货币权力批判
马克思的货币权力批判直指“资本主义何以可能”,他试图从货币权力社会化的开端处,探寻货币权力本身对资本主义的“预先决定”效应何以可能的社会史条件。诚如其所言:“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98页。不言而喻,以“生产—生活资料占有者”与“劳动力出卖者”在“市场”中的相遇情节为核心展开的“世界史”,既涉及作为货币权力当事人的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各自的“形成史”;又关乎二者纠葛其中,并因此是货币权力发祥地的市场“流通史”。二者蕴含货币权力起源的真相,本质上构成资本主义的史前史。(4)Jaques Michel,Marx et la Société Juridique,Paris: Publisud, 1983, p.76.从中,马克思试图揭示资本主义诞生的两个历史性前提:
其一,是农村土地所有制的资本化与城市商业财富中资本因素的泛化。它们同时塑造了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两种社会角色,故被视为资本主义权力体系得以确立的始作俑者。对此,马克思基于不同视角分别谈到:一方面,“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即作为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并取代土地而成为社会立足基地的雇佣劳动,起初是由现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就是说,是由作为资本本身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这不外是雇佣劳动从城市传播到农村,即雇佣劳动扩展到社会的整个范围”(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5页。。应当说,资本化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即现代土地所有权)对雇佣劳动的“创造”,既言明货币权力凌驾于劳动之上;又暗示货币权力独立于土地之外。加之雇佣劳动本身的社会化过程因循“从城市到农村”的轨迹,这就决定了雇佣劳动真正的历史生长点,是栖居于城市中的货币财富。在马克思看来,后者就是商业—高利贷资本。鉴于此,从另一方面,他又尖锐地指出:“在资本借以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的那种形态出现以前,为什么资本发展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而在这两种形式上发展为货币财产,关于这一事实的全部历史可以归结为:产品首先是在流通中发展为交换价值,首先是在流通中变成商品和货币。”(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14页。在此,马克思为以交换价值形态出场的货币权力,及其对资本主义因何所是的本体论证明,提供了认识论依据。但问题的焦点随即转移至:以交换价值为主旨的流通如何占据主导地位?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这无疑是质询“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整个生产”?按马克思的判断,“这部分地取决于这种外来影响的强度(即对外贸易的传播文明的作用——笔者注),部分地取决于本地生产的生产要素……已经发展的程度”(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12页。。以之为切入点,他首先肯定:只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展现出来,因为对外贸易使剩余产品中包含的劳动作为社会劳动发展起来,……并且在实际上使抽象财富有了意义”(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6页。。不难看出,“抽象财富有了意义”,暗示货币权力披上了交换价值的外衣。惟如此,“剩余产品”才能堂而皇之地成为社会劳动的目的,从而埋下资本主义出场的伏笔。这就从历史的结果层面反衬出,作为贸易主体的城市商业(高利贷)资本,才是借“货币权力社会化”之势,将历史本身推入资本主义怀抱的原初动力。就像马克思所说,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以大规模的出售为前提”,所以“作为商人资本的职能的商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7-128页。但必须认识到,该论断有其明确的适用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一再强调货币权力的社会化也取决于“本地生产要素之发展程度”的原因所在。何谓“本地生产要素”?在马克思那里,它无异于城市商业资本意欲消解的“旧生产方式”。但商业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0页。。显然,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不过是取代旧生产方式的“某一”而非“唯一”的新生产方式。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城市商业资本中的货币权力,在“旧生产方式本身”中找到社会化的途径。
于是,话题就重新回到城市商业资本通过改变农村土地所有制形式,创造雇佣劳动的历史机理上来。马克思不失时机地补充道:雇佣劳动或交换价值的产生,以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它预示“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其中,小土地所有制是从古典时代延续至中世纪,最终以日耳曼形式呈现的典型欧洲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于前者,它不仅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公社社员所属土地的私有财产关系;而且还具备使货币成为独立社会力量的城市商业基础。这就保证了,农村土地所有制关系能够“回应”城市商业资本对交换价值的要求。从而,通过转变原有的所有制结构,为货币权力的社会化创造条件(即产生雇佣劳动)。反观亚细亚形式,一方面它所建构的公社是凌驾于一切个体之上的最高所有者,故每一个体都是共同体的偶然因素,而没有形成真正的私有财产关系;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的无差别统一无法为货币自身社会力量的形成提供充足的商业环境。(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5、467、469页。这既意味着货币权力在此不具备社会化的条件;又确证了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为目的而展开的对农民的剥夺,只在西欧具有历史的必然性。(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5页。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偶然性本质才被揭示出来:其原生性取决于货币权力是否遇到社会化的历史条件,而这却是与货币权力无关的“历史恩惠”随机选择地缘的结果。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6页。。
其二,是财富生产的集中化与社会劳动属性的去政治化。如果说农村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商业资本的互动,给出了资本主义只能以货币权力社会化为前提的历史依据;那么,马克思之后就必须要揭示这种互动关系怎样产生资本主义的深层历史机理。话题始于他对农村土地所有制为何要呼应城市商业资本并转变自身结构的原因性分析。对此,马克思曾提及一个关键的线索,即“只有在商品流通……以及交换价值在货币和货币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上的独立已经发达的时候,资本才有可能形成”(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页。。不可否认,作为资本主义的前提要件,若要交换价值在货币的各种不同形式上取得发达的独立样态,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剩余生产就必须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原先的“生产方式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失去了超然于社会联系之外的性质”,变得只能以社会化的生产秩序为圭臬。其历史节点就是货币地租的出现。因为它在地租的给付方式上,以抽象的货币取代具体的实物为开端,将“传统的合乎习惯法的关系”,转化为“由契约规定的、按成文法的固定规则确定的纯粹的货币关系”。如此一来,“一向置身在农村范围之外”的城市商业资本家就能够通过租赁土地,把“城市中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产品只是作为商品,并且只是作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来生产的形式,带到农村和农业中来”。于是,在城市商业资本家向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身份切换中,“一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888、900、902-903页。
从既成的历史事实来看,这最先反映为以“自由的农民财产”为核心建构的小土地所有制趋于消亡。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莫过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3页。。惟有如此,货币权力的社会化才能成为必然态势,而制约资本主义出现的偶然性要素也将不复存在。马克思指出,这完全是因为“小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故而,包括农村家庭工业以及公有地在内的小农经济“补充物”,势必在工商业的发展和高利贷的盘剥中日渐萎缩。(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12页。与之相对应,不断成熟的商业经营模式,又“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外部的普遍联系”,即以货币权力为尺度的社会生产秩序中。(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5页。这样一来,财富生产路径的集中化就成为货币权力社会化的显性要件。它不仅从生产关系层面反证了,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社会形态更迭的根本原因;更揭示出,虽然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必然产生资本主义,但货币权力一旦抓住社会化的偶然性机会,而生产力发展的轨迹又恰好与之重合的话,资本主义的产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资本关系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流通行为中,在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的不同的基本经济条件中,在他们的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不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为资本职能。(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9页。
显然,当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现身生产过程的原因归结为,它“已经存在”于买—卖双方彼此抵牾的“基本经济条件”之中时,社会化的货币权力对资本主义的决定作用就获得了充分的历史理由。因为,货币权力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劳动的一般化。反观古代世界直接的“强制”劳动,抑或在中世纪被打上“特权”烙印的劳动,都是尚未摆脱自然属性故“处在特殊化状态的劳动”,而非“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由此,资本主义就必然同时涵盖“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以及对“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肯定。(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00、203页。在马克思看来,后者无疑是财富生产集中化的最终旨趣,前者作为先于生产的“已经存在”的原因,恰恰意味着劳动本身将祛除以“强制”或“特权”为内核的政治属性。马克思又补充道,既然资本主义在这里“只产生于买和卖,产生于作为所有者的买卖双方的行为”,那么“这种关系本身就不包括政治等等的关系”,而是通过把“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转化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改变双方的社会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货币权力一方面迫使“劳动强度打破独立生产者或仅仅靠外部强制而劳动的奴隶所遵循的惯例”(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17、223页。;另一方面,又保证与城市商业资本共振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取得纯粹的经济形式,并助其摆脱“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697页。。如此一来,货币权力就拥有了绝对的排他性,而追求以价值交换为尺度的剩余财富,便成为社会生产不断打破旧有限度的惟一动力。这同时说明,社会劳动的去政治化无异于货币权力社会化的隐性保障。它既确认了,货币权力取得绝对的排他性,是其社会化倾向从偶然到必然的历史临界点;又勾勒出,隐伏于剩余财富中的货币权力,在社会生产突破旧有桎梏之际,以“价值交换”取代“政治强制”为手段,将生产力的后续发展悄然纳入剩余价值积累的逻辑,从而把历史本身篡改为资本主义的史前史。
二、资本主义“成熟史”的货币权力批判
诚然,马克思在剖析“城市商业财富—农村土地所有制”与“财富生产手段—社会劳动属性”间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再现了货币权力借交换价值之手取得社会化契机,并导致资本主义诞生的全部历史性机理。但他同时意识到,这仅仅是“萌芽性”而非“成熟状”的资本主义。因为,“资本找到现实生产过程,……最初只是在形式上使它从属于自己,丝毫也不改变它在工艺上的规定性。资本只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不仅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而且改变了这个过程,赋予生产方式本身以新的形式,从而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3页。。从中不难看出,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熟”,既是社会生产从“形式依附”到“内容重构”的嬗变;又是货币权力从“抓住生产”到“创造生产”的跃迁。它们共同勾勒出资本主义从“因何所是”到“确如其是”的发展历程,并据此成为马克思阐释“利润化的货币权力怎样维系资本主义合法性”这一问题时,所遵循的认识论视角。以之为线索,马克思发掘出两个前后相继的关键历史阶段:
首先,是劳动分工的去自然化阶段。其中,涉及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的变迁。应当说,劳动分工的去自然化意味着劳动本身被货币权力裹挟程度的深化。它体现为资本对劳动组织形式的自然演进轨迹进行干预。其开端可归结为旧式的集体劳动变为协作。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协作”,就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佣人数较多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和资本本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88-389页。。
显然,协作的“自然发生性”,劳动只能以资本主义方式被社会化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劳动的社会化之于劳动剥削的“有利性”,三者在马克思那里其实是一回事。它们共同明确了,以协作为开端的劳动分工是货币权力将自身的社会属性转译为劳动的自然属性,从而为资本主义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提供了关键的依据。对此,马克思专门指出:
不再是在工人之间分配劳动,而是工人被分配到各个不同的过程中去,……它把执行每一种特殊职能的劳动剥削归结为枯燥的单纯抽象,归结为某种简单的质,这种质表现为始终如一的单调的同一动作,工人的全部生产能力、他的种种才能都为了这种质而被剥夺掉了。(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6-317页。
毫无疑问,“劳动剥削被归结为单纯抽象”是剩余价值升格为利润的现实反映,而“简单的质对工人全部生产能力的剥夺”,则表示以利润形态示人的货币权力祛除了劳动剥削的起源性记忆。它们共同预示,简单协作向工场手工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这不仅是因为“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为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惟有工场手工业“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更取决于,工场手工业既保证“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又促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15-416、418页。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以“劳动”和“资本”为当事人的价值交换,才能成为社会生产持续进行的必要环节。此时,货币权力就以“工资”为媒介,真正地走出“资本”,并在实质上将“劳动”改造为自己专属的统治对象。就像马克思所说,一旦劳动力的出卖采取工资形式,那么“它的买卖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买卖相比,就没有什么更引人注目的了”。(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7页。其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性的劳动不再依托刚性的他人监督,转以柔性的自我规训为前提。这集中表现在,与萌芽期的资本主义尚“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吸吮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形成鲜明反差,资本主义在之后几个世纪的发展中,已然使工人“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力的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12-313页。马克思将之称为“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并认为这才是“交换价值”取代“政治强制”以及从社会生产对资本主义的“形式依附”切换至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的“内容重构”的本质所在。
其次,是自由竞争的常态化阶段。它成形于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的过程。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它符合资本本性,符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符合资本概念的东西,……自由竞争越发展,资本运动的形式就表现得越纯粹。”换言之,自由竞争的完善程度可视为衡量资本主义成熟与否的关键尺度。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继续补充道:“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必须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43页。显然,所谓“拐杖”不啻为政治强制力,而“资本抛开拐杖”则表明货币权力借自由竞争之手取得绝对排他性。若以生产角度观之,这只能是资本化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并推动货币权力不断弥散的直观显现。后者“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0页。。从而,通过完善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按自己的规律”实现自身。这从相反的方向说明,生产方式的跃迁势在必行。对此,马克思专门提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一产物,又生产出机器。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因此,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26页。
从中可知,工场手工业无法“全部掌握”并“根本改造”社会生产的原因,恰恰是机器大工业登场的理由。而机器大工业对全部社会生产的掌握,又以取消“固定化”的局部劳动为前提。惟如此,笼罩在劳动分工之上的最后一重自然属性才能消失殆尽,并引起劳动本身彻底的“均质化”。马克思将之归结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平均状态”,以及“在极不相同的民族中形成禀性和素质的平均状态”。(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9页。值得一提的是,均质化的局部劳动一旦遭遇社会化的货币权力,就会再度转变为“流动性”的一般劳动。这等于承认劳动的自由变换,以及“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些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61页。。在这样的情境中,自由竞争就获得了两副面孔:它不仅关乎不同部类的资本争夺利润能力的高低;还涉及在流动性上存在差异的劳动力获得再生产机会的大小。于是,自由竞争就演化成所有社会成员均被裹挟的常态化现象,而货币权力也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关系,并成为“某类行为”(即价值交换)将“另一类可能性行为”(即生产劳动)结构化的保证。(34)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2、114页。这同时预示着,与自由竞争的常态化并行不悖的劳动均质化趋势,对资本的部类性壁垒予以取消,从而促使利润在劳动的流动性中,同样呈现出不受资本属性制约的“平均化”样态。这无疑是化身为“利润”的货币权力再度抽象为“平均利润”的历史原象。从中,马克思实际上明确了一个基本事实:虽然“资本能够形成并支配生产”的前提,是“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但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才是商品生产取得统治地位的保证。(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0页。这就从货币权力层面,给出了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依据。
三、资本主义“转型史”的货币权力批判
可以推知,资本主义的完全成熟就是货币权力的彻底社会化。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集中体现为:“资本转化成的普遍社会力量同单个资本家对于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它从侧面印证了货币权力社会化的必然后果,就是“把物质生产条件改造成为普遍地,从而是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1页。这不仅意味着“货币作为资本”能从一个“物”变成一个“过程”(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0页。;更揭示出“货币就是资本”,且只能将特殊的“物”视为普遍的社会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二者共同引申出货币权力取得生息资本形态的“当下性”与“原初性”历史机理:
一方面,货币权力赋形生息资本的“历史当下性”理由,源自社会分工精细化的直观后果。马克思认为,“互相补充的各个生产过程越来越分裂为独立的生产过程”,无疑是资本主义日臻成熟的标志。这意味着,当“商品生产的物的条件,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作为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产品”时,“资本家也必须以相同的规模作为货币资本家出现,或者说,他的资本必须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规模将会扩大”。(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3页。显然,马克思暗示了,私人性的资本终究无法满足货币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的要求。这反映在,既然“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展,它就越……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的那样一种规模”(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2页。,那么囿于私人资本并服从市场竞争法则的有限货币权力,就只能是被世界市场本身的无限货币权力所扬弃的一个环节。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50页。了。也正因为信用制度的自然基础不断扩大,生息资本才最终成为货币权力开显自身的重要载体。而另一方面,其“历史原初性”理由,则可追溯至产业资本常态化的现实条件。按马克思的理解,虽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产业资本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但它在形成之初却以“更为古老的形式”,即商业和利息形式为前提。它们作为生息资本的支柱,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时,才能成为受产业资本支配的“一种从流通过程派生的形式”。(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19页。该过程既涵盖产业资本对生息资本的“压制”;又涉及产业资本利用信用制度对生息资本进行资本主义“改造”。(42)马克思认为“对生息资本实施暴力,强行降低利息率,使生息资本再也不能把条件强加于产业资本”,是一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最不发达阶段的形式。而在发达阶段则依托信用制度对其进行改造。从历史趋势看,该过程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相吻合;从特定的历史内容上讲,该过程又是对旧式高利贷的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19-320页。
应当说,货币权力达至生息资本的“当下性”与“原初性”理由,实则以“信用制度”为支点,再现了资本主义是其所是的逻辑闭环:倘若市场本身的无限货币权力对私人资本有限货币权力的“扬弃”,表明信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然结果”;那么产业资本从“压制”到“改造”生息资本的嬗变过程,则意谓信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然条件”。惟如此,马克思才透过“信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发现“从各资本的竞争巧妙地过渡到作为信用的资本”的历史必然性。(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33页。而以信用为基础的生息资本的典型,不外乎银行业和股份公司。它们的区别仅在于,抽象货币权力同具体劳动剥削彼此疏远方式的差异;而共同点都是,资本“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就促使“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13、494-495页。。与之相对应,为社会资本开显的货币权力,也因此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化。马克思认为,后者集中体现为三重历史效应:
第一,因货币权力的实体化而引起的资本增殖无痕化效应。资本主义的最终实现预示货币权力的完全社会化。相较于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熟的各个发展阶段,货币权力尚作为抽象形式操控具体劳动;此时,它已然摆脱生产的“质性限制”,并因循价值的“量化积累”,彻底实现了自身的实体化。以之为切入点,马克思阐释道:“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运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制造货币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系。”(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04页。显而易见,货币权力的实体化不啻为社会关系的物化;而价值增殖痕迹的消弭则反证了,物化始于商品的抽象形式(量化的货币)对商品具体来源(质性的劳动)的抹煞。其实质可视为剩余价值在利息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上,获得超出任何想象的量之实体。(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49页。这同时引申出,社会化的货币权力擦除资本增殖痕迹并取得实体形象的本质,可视为劳动切换自身社会外观的频次达至极限的结果。后者体现为,劳动的“社会活动形式”(即主体形式)与“社会存在形式”(即对象形式)间彼此让渡的速率,被货币权力强行加快。(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4-65页。按马克思的理解,这无疑是资本为实现价值的最大积累,而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并缩短循环周期的极端形式。只不过,无论社会生产水平的高低还是资本循环周期的长短都有严格的历史界限。这才决定了货币权力只能企及量的实体化(纯粹数额性的货币值),而不能达到质的实存(真实存在的社会财富)。至于资本的无痕化增殖,毋宁是货币权力的障眼法罢了。
第二,与货币权力的弥散化相呼应的资本统治稳固化效应。当货币权力以生息资本示人,就表明它不仅使自己成为取代政治权力的惟一社会权力,更暗示这种社会权力须按资本要求随时发生结构性变动。前者不难理解,无非是类似利润率、财富构成,抑或工资波动等经济性因子,“在社会生活中以比许多国家法律大得多的力量和更加毫无顾忌的得以实施”(48)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70页。。其实质无非是,货币权力对社会关系的直接掌握程度在不断强化。然而,马克思却意识到,生息资本的真正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为所有人提供了分享货币权力的机会。其典型例证,不外乎“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据此,马克思既肯定,这种情况 “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又强调,只有“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才越巩固,越险恶”。(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679页。二者同时表明,货币权力对社会关系的直接掌握,尽管是资本主义成熟的标志,但远非资本统治可高枕无忧的保证。否则,已然取得绝对排他性的货币权力,就不会再度借助陈旧的政治力量镇压此起彼伏的工人反抗。正因为如此,生息资本通过信用制度为被统治者预留上升通道的策略,就是资本主义不断调整自身的权力格局,从而凭借权力主体的“不确定性”,最大限度地为资本统治增加“确定性”筹码。它深刻地揭示出,货币权力的彻底社会化就是社会本身完全服从“经济最大化的内在规律”(50)米歇尔·福柯:《什么是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8页。,并剔除所有影响资本统治的扰动因子。
第三,由货币权力的复杂化所导致的资本剥削模糊化效应。话题始于,生息资本以纯粹技术性方式,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发生结构性重组。这集中表现为,旨在运营并维护信用制度的技术性业务,作为一种特殊的、大规模进行的活动,“落到了为整个资本家阶级服务的一定的职能人员身上,并集中在这些人手中”(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6页。。于是,被生息资本集中的就不仅是货币权力,还包括产业资本向货币资本让渡时,所形成的全新社会职能性群体。他们以货币经营者或管理者的身份,横亘于产业资本家和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之间,并扮演全新的社会角色。这就使原本界限明晰的社会权力划分,被再度精细化与复杂化。其消极后果,莫过于“劳动”与“剥削”间的混淆。对此,马克思明确谈道,一旦利息形式促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产业利润这种质的形式,即产业资本家……劳动的工资形式”,那么“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剥削剩余价值),……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这既意味着,资本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这种异化的现实行动之外”;又暗示了,“剥削”将成为一种与雇佣劳动的社会规定看似一致的“劳动”。这就导致“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被等同起来”(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4-355页。。从中,资本主义不仅获得了价值稳定增殖的技术依托,而且还为尖锐的阶级冲突找到了必要的缓冲地带。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产业资本家转移到货币资本家或管理者那里,并凭借重构社会群际格局的手段,混淆了被剥削者的斗争动力。
四、资本主义“消亡史”的货币权力批判
应当说,货币权力的形态变迁轨迹,既折射出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熟”及至“完善”的发展序列,又见证了货币权力的社会化层次由“秘而不宣”经“昭然若揭”终抵“形神兼备”的历史谱系。据此,马克思认为,商业财富、商业利润以及商业信用,与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实则是互为前提的共轭关系。这就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证明,既然反映货币权力社会化程度的一定财产形式,构成理解特殊历史形式的起点(53)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5-126页。;那么,随着货币权力的整体规律被认识到,对资本主义一般历史形式的批判就势在必行。因为“对整体的完全认识,将使这种认识的主体获得这样一种垄断地位,而这种垄断地位就意味着扬弃资本主义的经济”(5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73页。。以之为开端,马克思之后的任务就进一步转化为,从货币权力的历史脉络中发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证据。这又体现为两个层次:
一方面,加快货币权力社会化节奏的手段,反过来成为瓦解资本主义统治的诱因。毋庸置疑,货币权力的社会化节奏与资本累进增殖的效率相一致。而后者又取决于社会生产与流通的周期。正因为如此,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和银行信用制度,才在资本主义的自我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以机器为动力的生产模式恰恰预示,“直接劳动本身”将不再是“生产的基础”和“财富的源泉”。如此一来,“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这等于宣告,以交换价值为开端的资本主义面临崩溃的风险。(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105页。至于信用,可视为资本在流通领域中把可能取得的未来收益整合进当下的财富额度,从而使有限的货币权力获得看似无限的积累可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信用的最大限度,就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因此,信用只是营造出一个有关价值无限增殖的想象。而“想象”背后,则是以财富积累为外观的债务积累。这既说明社会化的货币权力已被无序性的债务空洞所取代;又预示“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而牺牲掉商品的价值”(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46、584页。,将是货币权力社会化的惟一结局。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摧毁。
另一方面,提升货币权力社会化层次的举措本就隐含资本主义终结的端倪。马克思认为,这完全是社会生产的本性使然。对此,他专门提到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事实: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尽管“土地作为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同工人阶级对立”,但“土地所有者,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那么重要的生产职能的执行者,在工业世界中也成为无用的赘疣”。(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2页。表面上,这无非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取得主导地位后产生的“历史遗迹”,但马克思却从中发掘出资本主义本身成为“文明遗迹”的证据。他指出,“生产以这种对立和矛盾的极端形式转化为社会生产”,同时意味着“实际劳动过程中生产工具的公共使用”。如此一来,既然“封建主的要求依照他们的服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而成为多余的东西的程度,转化为纯粹过时和不适当的特权,从而迅速趋于消灭”,那么与封建主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类似,“资本家作为……加速这一社会生产,从而加速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的职能的执行者,就依照他们以社会名义获取利益以及作为这一社会财富的所有者和社会劳动的指挥者而飞扬跋扈的程度日益成为多余的人”。(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01页。于是,伴随货币权力的人格化执行者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就只能宣告终结。况且,不断完善的信用制度也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结果,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也必将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后者意味着,社会劳动不再是货币权力社会化的结果,而是社会化的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走向协作的开端。诚如马克思所言,“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主义完全无关”(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95、435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毋宁是资本主义消亡的起点。
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化的货币权力,已然把握到人类文明演进的总体脉络。在他看来,“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应当说,作为人类文明的过渡性阶段,资本主义既是对“人的依赖性”的否定,又是被“自由个性”所否定的“物的依赖性”。它自身就是货币权力社会化的限度,并暗示人类文明在当下只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即社会性的独立个体扬弃社会化的货币权力。
这就引申出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取代资本主义的确定性。对此,马克思专门谈道,“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5页。。反观资本主义,正因为社会化的货币权力攫取了社会劳动创造的“自由时间”,本该全面发展的社会性个体才被“异化”。故而,更高级文明形态的任务,便是将自由时间还给社会性个体。于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就不再是获得剩余价值,“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1页。。按马克思的理解,这预示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8-929页。。显然,“盲目的力量”就是社会化的货币权力。它之所以“盲目”,是因为“社会化的人”单独进行的“个别劳动”,要想成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开展的“社会劳动”,就必须以物化的共同体,即货币为中介。正因为如此,更高级文明形态的内核,便是自由人联合体自觉控制“物”的力量。对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自觉地把它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改变。(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6页。
从中不难看出,自由人联合体对“物”的自觉控制,不仅体现在直接的物质生产层面,更反映在以人自身的再生产为目的的社会分配领域。对马克思来说,后者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源于“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一切职能和活动”,而“所有的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0页。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文明形态的跃迁归根结底是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发生质的改变。否则,任凭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达到怎样的层次,它都可能陷入“盲目”境地。须知,社会化的货币权力仅仅是一种“物”的权力而已。这就从相反的方向说明,“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必然是对所有“物”的权力形式不断进行自觉祛除的文明形态。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它既“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又“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页。至于“最彻底的决裂”,本身就是不断切换主题的历史性过程。这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专门强调分配方式随生产者的历史发展而改变的原因所在了。
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逻辑确定性,就包含“资本主义之后是什么”的未来不确定性。对此,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将之归结为,“相同的经济基础……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894页。。应当说,所谓“相同的经济基础”,就是指“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74页。,也就是共产主义所有制。而后者“在现象上的变异和色彩差异”,恰恰折射出这种更高级文明形态的本质,就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货币权力的“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间的对应关系为切入点,通过揭示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熟”及至“消亡”的全部历程,从总体上建构出检视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递进序列:在认识论层面得以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既是资本主义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其所是的“实然根据”,又是对资本主义之后的文明形态进行逻辑学预测的“应然基础”。这既从货币权力的社会化脉络中提炼出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逻辑必然性;又在克服物性权力的选择方案内勾勒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将以何种面目示人的逻辑可能性。它不仅是对资本主义“何去何从”的历史演绎,更是对共产主义“前世今生”的科学预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资本论》中表现出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乐观态度。诚如其所言,虽然共产主义是物质生活条件“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但“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却是一个更为长久、困难的过程。(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7、8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