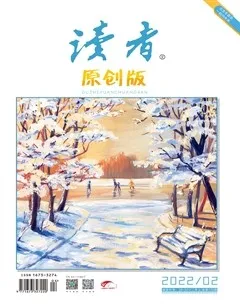二手书
2022-02-24南在南方
南在南方
颇有微词的事,像十五的月亮不明朗,像久候客却不至,像熄火的二手车。“二手”这个词,有点儿说不上来的含混,二手书却例外—心仪已久,忽然遇着,就算蒙尘,也有得手的兴味。
有一则黄侃先生的轶事,说他嗜书如命,一次能买千册!家里到处都是书,生计成问题,夫人埋怨说:“一双眼睛怎么看得完?”黄先生说:“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裹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宴尔之时最乐吗?”
看书之乐,好像可以附和黄侃。不过,爱看书的人,大多囊中羞涩,虽然可以去图书馆,总归是不方便,不如家里坐卧随意,购买二手书就是更好的选择。
民国时的一位作家写他逛琉璃厂,看见二手书《戴氏注论语》,要价5元,他只肯出一半,伙计不卖。他转身要走,伙计咬牙让到4.5元,他还是走了。回家给友人写信说了这事,友人就买下来给他送去。小小的一波三折,却能看出他的高兴。
我頭一回看那位作家的书,是20多年前。我初来武汉,那时街上有好多书店,图书亦卖亦租,租金20块,一次只能租一本,还了再租。
看那本书的感觉像是听老者抿着嘴唇不紧不慢地说事情,偶尔还嘴巴干,腔调有点儿凝滞,这个体验前所未有。看了一个月,最终是要还的,结果书店不见了。于是,这本二手书成了我的,倍感高兴。
如此便能时不时地看,像是一条长长的藤,顺着他的藤,摸出了许多瓜,诸如作家清少纳言,俳句家松尾芭蕉。
我买过许多二手书,有的比原价高出好多,大多数都便宜,最便宜的一回是用秤称的,三块钱一斤,其中就有《查令街十字84号》。海莲·汉芙说:“你们若恰好经过那儿,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它良多。”一家旧书店,一个读书人,卖与买之外,彼此牵念。信中说:“春意浓浓,我想读点儿情诗。别给我寄济慈或雪莱,我要那种深情款而不是口沫横飞的……”
我也在汉口一家旧书店断断续续地买过书。书店老板坚持了许多年,不肯关门,竖在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代写文书,劝解纠纷”。他还试着做些别的补贴家用,只有剃头这事成功了。老式的剃刀,他要在裤子上荡几荡,一会儿就剃个圆溜溜的脑瓜出来。后来书店还是关门了,不过,他依然坐在之前店铺的附近经营着剃头的生意。前些天遇到,他拍拍脑袋说:“好多年前,你叫我留意《塞耳彭自然史》,却一直没有。”我不胜唏嘘。

二手书免不了留下前主人的勾画,我手上的一本旧书里,前主人写了34个“真好”,除此之外不着一字。也遇到一位有趣的,书里留下一句:“亚莉的门牙张开呀,放一颗黄豆,过几天能长豆芽。笑起来有酒窝,就是有点浅,醉我足够了。”
像一个爱情故事,情不知所起,亦不知所终。
九月从陕南老家返回城里,心里满满的,又是空空的,临睡翻翻松尾芭蕉的集子,看他写:“晚秋九月之初,回到故乡。北堂萱草经霜而枯,至今已了无痕迹,一切皆面目全非。兄弟姐妹两鬓斑白,眉梢多皱。只道一声‘多多珍重’,自无言语。长兄打开护身符袋说:‘拜一拜母亲的白发吧。对于久别归来的你,就像浦岛之子打开百宝箱,你也须眉皆白了呀!’”
眼里一热,脸上跟着一热,我慌忙起床去了书房,那里有一个小小的袋子,里头有一把梳子,那是我刚刚辞世的母亲留下来的,想要从上面找到一根白发,却是干干净净的。
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有点像二手书,分明在这儿,却又准备着流离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