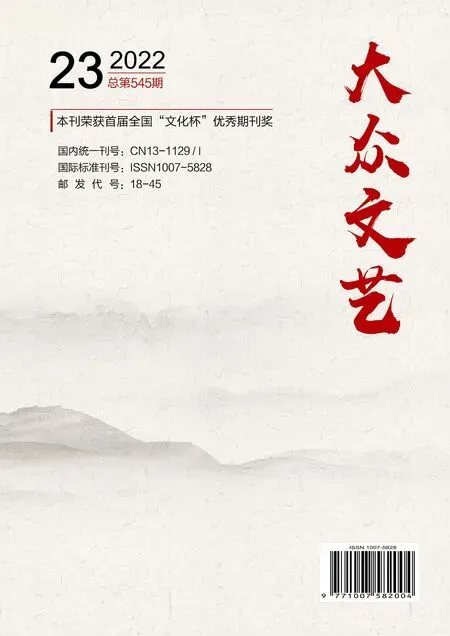从主体到身体:电影观众研究中的物转向*
2022-02-23郭燕平
郭燕平
(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广东广州 510631)
“观众”一直是视觉文化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而观众研究的核心正是要为理解“人与媒介”的关系提供阐释的框架,其背后指涉的是:媒介内容的接收、审美经验的感知、受众的主体性等一系列问题。电影研究的学者为“观众研究”的理论化和学科化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基于电影预设的理想观众(viewing subject)与实际参与的电影观众(moviegoer)两者的区分,他们发展出了两种主要的研究范式。
一类关注电影文本本身(Spectatorship),从精神分析与符号学的路径进入,分析电影如何生产出某种观看的位置,以便形塑或迎合观众的欲望,从而构建出观看的主体。从早期的电影评论对观众行为的规范,文艺批评对读者审美的考察,再到社会科学对观众的量化研究,现代媒介与观众(读者)的互动关系一直是不同人文学科共同探讨的议题。然而,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了精神分析-符号学电影批评,观众研究才被升华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通过吸收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思想,以让·博德里为代表的学者重构了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他将电影的放映内容、放映空间、放映设备与影像投射看作是整体性的“电影装置”(cinematic apparatus)。这种设置创造了一个无意识的环境,将观众放置在特定的观看位置上,在电影观众上。与此同时,电影装置把影像设置为被观看的客体,将观众设置为观看主体。观看的过程中,电影展现着一系列连续运动的叙事性影像,主导着我们的凝视(gaze)。让·博德里进一步借用拉康关于“镜像阶段”(mirror stage)的论述,指出在这一想像性(imaginary)的虚构世界,观众得以认同着(identify)银幕里的故事或角色,以及那个“全知全能”的摄影机之眼。
劳拉·穆尔维发展了让·博德里的观点,并引入了性别研究的视角对观众的主体性作出创造性分析,进一步发展了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借助对好莱坞经典电影的叙事结构和镜头运用等分析,她揭示出这些电影文本普遍预设了一个理想的男性观看主体,而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往往沦为被凝视的客体。这使得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由于沉浸于电影的世界,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个男性主体的观看位置,以便形成对电影角色的认同,从而获得观影快感。[1]与此同时,这一分析也打开了女性观众学的研究路径:如果电影均预设了男性为理想观众,那么如何看待女性观众的主体位置,她们如何从电影中获得观看的快感?
作为回应,Teresa de Lauretis和Mary Ann Doane都发展出新的视角来阐释女性观众的主体性,她们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观众主体的流动性。Lauretis提出的是“双重认同”的概念。她认为女性观众不一定只认同电影叙事中的男性角色,她们既可以认同电影叙事中的正面主角,但也可以认同那些反派配角,这些反派是以阻止叙事发展的面貌出现的。这一理论概念为女性观众打开多元的认同空间。[2]而Doane则提出了“伪装”这一概念来解释女性观众认同的复杂性。她认为可以将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理解为某种面具式伪装,特别是以玛丽莲梦露这类的女明星为代表,女性观众通过识别出这种面具的存在,与电影预设的观看位置保持距离,既能沉浸其中又能游离于电影叙事之外,从而得以在电影观看过程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3]
另一类关注电影观众本身(Audienceship),借鉴人类学和口述史研究的方法,援引观看者的个体经验与自我表述来分析他们对文本的反应和感受,这类研究强调受众在文化接收过程中的主体性。上述以电影文本为中心的“观众研究”(Spectatorship)忽略了现实中电影院观众的具体经验,造成了文本观众与经验观众分析之间的巨大鸿沟。正如Stuart Hall在著名的文章 Encoding/Decoding中指出的那样,存在着多种的受众与媒介交往的模式,来自不同阶级、族裔的观众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观众往往在文化接收中能扮演积极参与、抗拒与协商等角色。[4]与此同时,2000年代电影研究领域经历了一定程度上的“历史转向”,旨在突破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号召将电影实践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中考察。这些都是对既往的精神分析-符号学这一主流的研究范式的反拨。[5]Jackie Stacey的关于好莱坞电影女明星粉丝的研究成为经验性观众研究的范本。她摒弃精神分析-符号学的电影批评方法,转向民族志的研究。通过收集历史上电影观众的真实反应及事后回忆,她进一步建立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实际进行文本解读的女性观众之间的关系,发掘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真实经验着的女性观众。[6]
从观众研究(Spectatorship)到受众研究(Audienceship),标志着对观众主体的讨论从以电影文本为中心转向以具体经验为基础。尽管在研究方法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两者均考察的是观众之于特定电影文本的接收问题。无论是把“观众”当作是抽象的主体位置还是具体的内容接收者,这些研究都预设了主体—客体的观看结构,较少看到观影过程中观众与放映空间、媒介物质的互动关系。当观众成为了认知主体,电影这一媒介也就成为了纯粹的客体。
近年来,这种研究思维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主要的挑战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电影现象学反思了主客二元的局限性,强调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来看待电影与观众的关系,观众被看作是构建电影整体认知“完形”中的一环;另一方面,物理论和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起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电影这一媒介的特性及其对人的影响。“物转向”作为新兴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对长期主导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三种观念发起挑战。一是打破“主体——客体”二元的分析框架,这与后现代立场不谋而合,由笛卡尔式理性主导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被颠倒了,不再是人怎么控制物,而是物怎么限制人。二是重新界定“物——非物”的边界。新兴数码技术的普及,计算机技术的泛化,这些技术革新带来了新的物质形态,恒定不变的物理属性无法应用于对新物质的解释,物及物质性亟待被重新定义。三是对“身——心”二元论发出诘问。自尼采、福柯、梅洛庞蒂始,身体不再被认为是精神的囚笼,曾经被忽视的肉身重新显现,人的身体性被重视起来,向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体发起挑战。
在电影现象学和物理论的双重影响下,一些电影学的学者主张以电影经验(Film Experience)这一概念来取代“观众主体”,打破主客二元分割,以便重构关于电影与观众关系的讨论。“电影经验”于是取代了“主体位置”或“受众经验”成为思考观众研究的新切入点。随着早期电影研究(面向过去的电影学)和后电影理论(面向未来的电影学)的兴起,用于分析传统的迷影体验(cinephilia)的观众研究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7]当某些观影经验并不与电影的内容直接相关,而是关涉到参与者在电影放映空间中经历的经验发生、形成乃至转变的动态过程,既有的观众研究则无法解释这些多元的电影经验。学者Tom Gunning关于早期观众的研究很能说明这一点。他指出早期电影中的观众更多地是被电影技术的新奇效果而非电影叙事所深深吸引,而观众不再是被固定于某个观看位置的主体,而是成为伸长脖子看热闹的看客。[8]与其说早期观众关心的是电影的内容,还不如说他们在意的是电影给他们带来的惊奇感受。
“电影经验”于是取代了“主体位置”或“观众经验”成为思考观众研究的新切入点。根据卡塞蒂的分析,电影经验(Film reception)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电影接收(Film reception)。Francesco Casetti将“电影经验”理解为是“银幕上的声画触及我们感观的时刻”。他认为我们并不是看见电影,而是我们与电影相遇,观众是这场“事件发生”的主角。电影经验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它扩大了观众研究的范畴,摆脱了“主体认同文本”这一框架,将对电影文本接收之外的经验也纳入考察对象。另一方面,电影经验消解了观众为主体、电影为客体的分野,将观影理解为是一种交互关系。
电影经验理论和物理论的兴起为观众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特别是启发了学者看到观众的肉身性。如果说传统的观众研究着重考察的是观众作为理性主体的观看经验,那么电影经验理论引导我们去考察“去视觉中心化”的具身化经验,特别是观众除了视觉感受之外的触觉感受。Linda Williams的开创性研究带出了观众经验中的肉身性。通过对色情和恐怖片的分析,她指出这些影片的观看者接收到的首先是一种身体上的感受,身体最先会给出反应,可被称之为触感式视觉性(haptic visuality)。[9]Laura Marks和Jennifer Barker都把他们的讨论集中在观众和电影之间的“接触”。Marks将电影概念化为一种皮肤,能够通过触感视觉唤起观众的感官记忆。而Barker则认为电影对具身化观众的渗透比皮肤更深,甚至触及五脏六腑。[10]
对观众身体性的重视,恰恰是为了跳出长期以来围绕观众主体性开展研究范式。在这种背景下,Richard Rushton重读了德勒兹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德勒兹设想的理想观众实际上是彻底消极被动的观影身体。与阿多诺所批判的消极观众不一样,德勒兹理解的消极观众具有激进的政治能量。在电影面前,任由身体被电影所牵引,这种情动的状态(affect)使得观众放弃对理性主体的掌控,经历一种主体客体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作为物的电影也经历了拟人化。Vivian Sobchack她没有将“电影经验”简单理解为观众(主体)接触电影(客体)而得的主观感受;而是将电影这一“物”转化为观看的主体。在Sobchack对电影《钢琴课》的精彩分析中,她提到观众并不只是在看电影,电影诉诸于身体性的感受而非单纯视觉性的,具有肉身性的画面带给观众一种触感,观众肉身的感受被调动起来。从而观众与电影经历着类似互为主体的过程。[11]Shaviro更进一步指出在某些触感电影中,电影仿佛具有主体性,通过加剧情欲的张力来诱惑观众。电影放映本身是生产一种情动空间(affect),观众在不断的情感调动过程中放下了那个作为主体的完整的“我”。电影与观众的主客位置被颠倒和互换。[12]
由于过度重视观众的本体位置,既有的观众研究较少看到观影过程中观众与放映空间、媒介物质的互动关系,容易忽略观影经验中“物”所扮演的作用。近年来,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起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引导我们跳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看到在社会网络中“非人”(non-humans)和人一样是构建关系的“行动者”。这一思路启发了我们重新考察电影观众研究中人与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