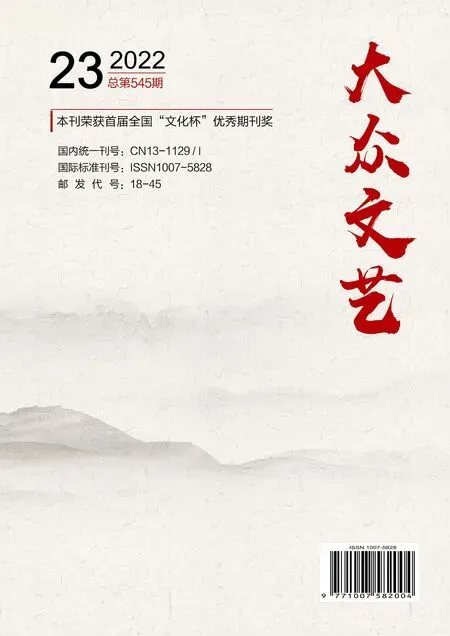汉代漆耳杯动物纹样研究*
2022-02-23路瑶
路瑶
(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江苏南京 210013)
动物纹样是对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各类神话传说的演绎和集合,也是历代器物装饰纹样的延续和发展。它作为汉代漆耳杯主要的装饰纹样之一,通过含蓄、转寓、谐音等方式将飞腾跳跃、拖曳长尾的奔龙,挺胸昂首、婉转回眸的雷凤,神态自若、悠闲自得的游鱼,举止飘逸、潇洒自如的飞鸟,洒脱豪放、四肢飞腾的神兽描绘的神采飞扬。特别是简洁流畅的线条、疏密有致的构图再加之抽象语言的描绘,彰显动物纹样的独特美感。
一、汉代漆耳杯概况
耳杯作为饮酒时使用的器具出现于东周时期沿用至魏晋时期,到了汉代,漆耳杯的生产及制作规模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景。陈振裕先生在《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一书中提到:1972年-1973年间,长沙马王堆1、2、3号墓出土漆器600多件,其中漆耳杯竟有252余件之多;1973年-1975年间,湖北江陵凤凰山8、9、10、12、167、168号墓也出土321余件完好漆耳杯;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汉代漆器多达700多件,包含了漆耳杯20余件及700余耳杯残片;80年代,在江苏徐州北洞山、山东昌乐东圈、广东广州南越王墓、江苏邗江甘泉、江苏仪征烟袋山、湖北江陵张家山、河南南阳麒麟岗、安徽芜湖贺家园、山西朔县赵十八庄等地均有发现汉代漆耳杯及其残片……①由此可见,漆耳杯已成为与汉代生活密不可分的实用器具。再者,“通过对有漆器出土的汉墓和出土漆器纹饰的整理,有漆器出土的汉墓大约有130座,其中漆器上有动物纹饰的有93座”。②由此不难看出,动物纹样是汉代漆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装饰纹样,这类纹样同样在漆耳杯的装饰中也得到了充分的渗透。
二、汉代漆耳杯动物纹样的类别
(一)动物纹样的类型:现实与非现实
动物纹样可分为现实动物与非现实动物两种,最常见的现实动物纹样有鸟、鱼、蛇纹等。其中鱼纹作为中国传承千载的传统纹样,早在原始时期就出现在彩陶的装饰之上,古代人崇尚鱼,因鱼与“余”谐音,期望幸福美满;再者,古人认为鱼类有旺盛的繁殖能力,借此祈求自身多自作孙[1];所以以“鱼”作为装饰纹样出现在耳杯上便有祈祷吉祥、祈求繁盛之意。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三鱼纹漆耳杯”便是“鱼”的范例。耳杯的杯腹中绘有一朵对称的柿蒂纹,柿蒂纹的四周围绕着三条姿态各异的鱼儿,灵动的线条勾勒出鱼儿在水中相互追赶、相互嬉戏的身姿,口中还不断从吐出卷云般神须,显得一副闲然自得、逍遥无边的神态。虽然它们仅被描绘在耳杯的边缘位置,但与中心的柿蒂纹相比更有视觉张力。除此之外,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三鱼纹漆耳杯”、荆州高台28号墓出土的“彩绘鱼纹漆耳杯”和江陵毛家园1号墓出土的“彩绘三鱼纹漆耳杯”等都是用流畅的线条将鱼儿表现得活灵活现的经典作品。同时,鸟纹也是在漆耳杯中频繁出现的现实动物纹样。例如安徽长天6号汉墓出土的鸟纹漆耳杯和贵州清镇平坝15号汉墓出土的鸟纹漆耳杯纹样,两者在鸟纹的处理上都以流畅的线条和明快的色彩为主,用漆绘的方式将鸟儿勾勒出一副在花丛林间自由飞翔的情景,似乎也是表现出汉代人民“托物寓情”的思想观念,以现实动物纹样来憧憬美好的未来生活。
除此之外,在汉代漆耳杯的装饰中还出现了非现实的动物纹样,其中常见的有奔龙、凤鸟、龙凤、神兽纹等。历代人们都将龙视为权利和神武的象征,认为龙可以呼风唤雨、祈求太平,因此将它奉为神灵,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2]。所以,在出土的漆耳杯中以非现实的龙为装饰纹样也是较为常见。从湖南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女巽墓出土的云龙纹漆耳杯中可以看出:龙的身型细长似蛇,有足有爪,有首有角,有尾有翼,与云纹相互呼应,整体看来龙腾舞动,张弛有度,虽然耳杯的表面积有限,但在视觉上给人一种不被束缚的延伸之感;通过自由想象和夸张变形,将原本刻板印象中神态威猛、威严肃穆的奔龙表现得活力四射又不失可爱。
(二)动物纹样组合形式:独立与适合
独立纹样即一种单独存在并与周边无联系且完整的纹样,它是构成漆耳杯动物纹样的基本单位,多出现于耳杯的腹部中部及杯底上方等部位,力求稳中有变,在变化之中寻求安定美感。
在汉代漆耳杯的纹样中以凤鸟和鱼为主的单独纹样最为多样。例如湖北省荆州高台28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凤鸟纹漆耳杯颇为代表性。一只鼎立在杯腹中央的凤鸟与耳杯周边的几何纹样相互呼应,虽然只有几条简洁流畅的线条,却勾勒出凤鸟饱满的身形,颇有流动奔放的艺术感。凤鸟纹“黄氏”漆耳杯同样也是单独纹样,却描绘出凤鸟在卷曲流畅的云海之中自由自在的奔腾、徜徉、驰骋的神态。同时,鱼纹作为吉祥图案,也常常被单独绘制于耳杯之中。湖北省沙市周家台35号汉墓和湖北省荆州高台28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鱼纹耳杯都是以鱼的造型单独出现在耳杯中部,形象刻画细致,连鱼身的鳞片也被描绘得入微到位。单独纹样多以动物个体形式为主,以追求画面对称的效果,以达到结构平稳规则,富有浓郁装饰的意味,也是汉代漆耳杯中中最为常见的单独纹样表现形式。
不同于单独纹样,适合纹样在构图上更追求形式感,讲究灵活多变、画面生动,注重纹饰有高低起伏、轻重虚实的变化,尤其是营造出配比均衡、重心平稳的视觉效果,力求整体稳定和坚实。动物适合纹样是根据汉代漆耳杯特有的造型特征进行排列组合的,比较常见的组合有将纹样绘制于耳杯的腹中、耳杯外壁、双耳表面及耳杯底部等处。这些适合纹样为了传递造物精神,也有将现实生活中风马牛不相及的动物组合在一起,以促成意象化的自由适合纹样。例如1986年江陵毛家园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三鱼纹漆耳杯就是这样一个实例。耳杯腹中用金、朱红、灰蓝绘制一只昂首挺胸的凤鸟,周围有三条首尾相连的游鱼紧紧围绕。现实生活中游鱼和凤鸟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动物,一个则是人们为了祈祷美好生活杜撰出来的神物,两者是完全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平行时空里的,但却巧妙的出现在同一个耳杯中,构成了新颖的动物适合纹样形式。
(三)动物纹样的表现语言:抽象与具象
抽象与具象是汉代漆耳杯动物纹样中最为常见的表现语言。抽象和具象的动物纹样大多数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汲取养分,以表现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和对自由的无限渴望[3]。但抽象和具象的表现语言在描绘动物时各有侧重。根据图像的观察和比对,可以比较清晰的得知具象的动物纹样在描绘的过程中选取了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鱼,鸟、虫、鸡等动物为描绘对象;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三鱼纹耳杯,杯腹中描绘了三条游动的鱼儿,细看其自然摆动的鱼身便可发现三条游鱼中绘有鱼鳞、鱼鳍、鱼鳃等细节,如果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对其仔细观察和了解的话,不能如此真实的还原这些特征。然而对于抽象动物纹样的把握上又有了不同的理解。虽然同样都是来源于某一种具象动物,比如鸟、鱼等,但又不拘于直白的具象表现,通过分析、加工、改造并经过变形、夸张、谐音等方式对其再创造,使之成为理想化、装饰化的抽象语言。例如变形鸟纹、变形鱼纹、变形龙纹、变形凤纹等都属于抽象语言的范畴。凤纹就是汉代时期漆耳杯中最为常见的抽象纹样之一。《说文》中记载:“凤,神鸟也”。现实生活中没有凤鸟的存在,它是当时人们对这一种神鸟理想化的写照。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凤纹漆耳杯由凤鸟头、蛇身、鸡爪组成,凤鸟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现实动物局部的还原和组合,这样的再现绝对是人们意向出来的结果。同样是对于凤纹抽象的理解,安徽天长6号汉墓出土的凤纹漆耳杯却是另外一幅神态。耳杯中的抽象凤纹样更像是飞鸟的形象,身姿飒爽、孤傲自赏的样态与前者无相同之处。这也看出抽象的凤鸟纹样是往往是对具体的动物形态的重新认识和领悟,加之意识思想后产生的联系及想象,是对精神世界中虚无缥缈的事态进行意向的表现。
(四)动物纹样的色彩搭配:统一而不单一
朱色和黑色通常是汉代漆耳杯的主要髹饰色彩,其次是黄色、蓝色、灰色等色漆辅助装饰。这样的色彩搭配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组合,要通过长短粗细、笔直卷曲的线条相互交织,各类图案的相互组合才能描绘出统一又不单一的色彩。
汉代漆耳杯主要以朱漆髹饰黑漆勾勒和黑漆髹饰朱漆勾勒的髹描方式居多,构图上以繁简结合的形式为主,例如湖北省荆州高台28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凤鸟纹漆耳杯就采用了朱漆髹饰黑漆勾勒的髹饰方式。在大面积朱漆的映衬下,几笔精悍流畅的黑色线条将凤鸟刻画得栩栩如生。虽然只有黑红两种简单色彩,但强烈的色差却活跃了观者的视线,并随着线条平仄顿挫,自然地构成了这种游动般的色彩,形成了一种统一的装饰语言[4]。彩绘三鱼纹漆耳杯与彩绘凤鸟纹漆耳杯不同的是,它是由黑、金、朱红、灰蓝等多种色彩相互交织构成的动物纹样耳杯。这种纷繁的色彩不仅是由单一色彩向多种色彩的转变,而且能够刺激人们视觉,引发“见色生情”的情愫,产生各种情感,从色彩中体会冷暖、强弱、远近等,或因明快而兴奋,或因深沉而寡欢,这也是由色彩搭配引发的对美好世界的向往生动写照。康定斯基在色彩论述时说过,色彩除了能对纯感官起到效果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效果--“色彩的心理作用:在这种情况里,显露出来的是色彩的心理力量,它引起的是精神的震撼。初始的单因素的感官力量就这样成为一条色彩借以深入人们精神的道路”。③
三、动物纹样在汉代器物造型中的运用
汉代时期动物纹样不仅在漆耳杯装饰方面得到大量运用,在器物的造型上也得到了广泛的施展。江苏扬州西湖乡胡场14号西汉晚期出土的银扣彩绘鸭形漆勺很巧妙的运用了鸭子的外形特征,将鸭颈作柄,鸭身为勺,有大面积蓄水空间。此漆勺不仅准确把握鸭子的外形特征而且又巧妙的将鸭子的身型与水勺完美结合,构思独特且制作精美,将美观与实用功能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湖北江陵雨台山56号楚墓出土的猪形漆盒同样亦如此。于此同时,动物纹样也陆续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类器皿之中[5],比如食器中的碗、盒;生活用品里的几、案、屏风;女性梳妆打理时使用的漆奁上也绘制有丰富的动物纹样;甚至丧葬用品中的漆棺、面具等用品都描绘了丰富的动物纹样。在汉代官吏文人的印章中、汉代的画像砖、汉代锦衣方面都出现了各类的动物纹样[6]。这些动物纹样或通过写实形式或是变形夸张的表现形式,不仅在各类器物上构成类精美的画面,而且还仿造动物的外形制作了很多美观又实用的动物形象的器皿。汉代人借助各类动物形象以表达对动物的喜欢和崇拜,更是生活的感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生命的渴望,祈求通过对这些瑞兽的精神寄托得到幸福和平安。
结语
站在汉人的角度来看审视当时的审美需求,他们认为特定的动物形象具有吉祥安康或趋吉避凶或的意味,加之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各种关于动物的神话传说和奇特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论话题,也已经变成了汉代不可或缺的描绘群体,具有特定的时代象征意义和神秘的吸引力。然而,“它们并不是表面的动物世界的形象,相反,而是以动物为符号或象征的神话---巫术世界来作为艺术内容和审美对象的。”④例如镇墓兽以奇特的造型成为神兽的化身,作为一种冥器被放置于墓中,起到镇墓辟邪的作用,形象怪诞逼真且刻划精细,这种特殊的动物造型和装饰,也许正是向人们展示了某种宗教或哲学的奥秘吧。
注释:
①陈振裕.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M].文物出版社,2007.第8-32页.
②吴亚.汉代漆器动物纹饰的重要性探析[J].美与时代:上半月,2011(3).第46页.
③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M].李政文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32页.
④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3).第118页.